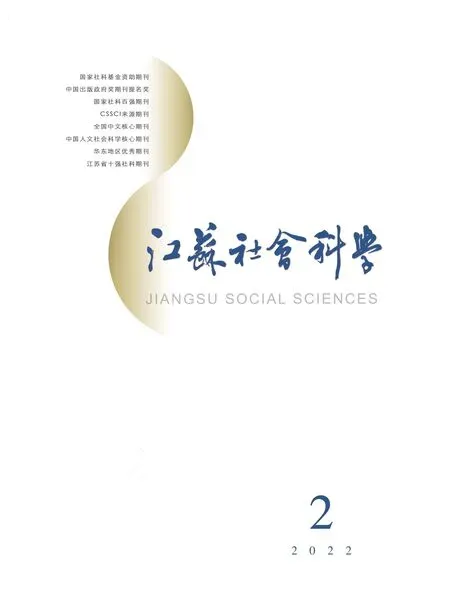民初平政院制度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
吴 欢
内容提要 在行政审判机构的立法定位背后,民初平政院深层次的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值得挖掘。考诸史事,民初平政院由辛亥元勋宋教仁“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并“参酌中国古今官制”而命名和倡设,盖意在取法“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之古意而彰显共和宪制之精神。宋教仁殁后,政治强人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力排众议设置平政院并为之做政治背书和执行保障,呈现出借由平政院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许。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位政见主张多有不同的民初政局关键人物,在通过平政院“平政致治”这一问题上却分享了相同或近似的理念和考量,民初平政院也因此成为彼时“帝制走向共和”之际国家治理秩序转型和重构的重要参与者、推动者和见证者。民初平政院制度蕴含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折射和印证了殊值鉴察的制度与人事相须相成关系。
在中国近代法制史上,1914年成立的北洋政府平政院不仅是对大陆法系德日法族行政法院制度的异域移植,而且具有兼收并蓄古今中西治理(更具体地说是治吏或吏治)资源的时空特色[1]吴欢:《兼收并蓄:比较视野中的民初平政院》,《法大研究生》2018年第1期。。但学界关于民初平政院的主流观点,多是借由彼时粗疏的法律法令,认定其为地位暧昧、功能不彰且人事尴尬的行政审判机构[2]参见武乾:《论北洋政府的行政诉讼制度》,《中国法学》1999年第5期;张焰辉:《民初建立法治国的实践——以平政院裁决为中心》,台湾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总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54—535页。。相关成果多是对平政院发展演变与制度设计的梳理介绍,或是因袭陈见对其运行实效加以贬抑,抑或仅将其视为在当代中国倡设行政法院的一种历史佐证[3]解志勇:《行政法院:行政诉讼困境的破局之策》,《政法论坛》2014年第1期。,至于该制度建立的具体情境和深层次考量则较少被论及,尤其少有学者深入论析宋教仁和袁世凯这两位民初政局枢纽对平政院制度的重大影响。事实上,民初平政院不仅是彼时中国最高且唯一的行政审判机构,其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中还蕴含着重要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在“帝制走向共和”之际,革命党人宋教仁秉持共和精神提出了设立平政院的构想,所谓“窃国大盗”袁世凯则将宋氏的构想付诸实践并赋予平政院作为治理者的政制地位。在当代中国行政诉讼已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之际,有必要重回百年起点,重思民初平政院,重省民初法政变革的经验教训。本文意欲在清末民初以来“平政致治”新境遇亦即国家治理秩序转型与重构的宏观视野中,窥见近代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奠基与流变之内在机理。
一、行政裁判:平政院的立法定位
治官治吏、协和官民是古今中外治理者必须回应的治理难题。中国古代存在众多以廉政监督为旨趣的“民告官”救济途径,近代西方则根据不同法制传统形成了以大陆法系“二元制”和英美法系“一元制”为典型的行政审判体制。1840年以降,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开启,传统“民告官”制度设计逐渐让位于近代行政诉讼法制,但围绕究竟选择何种行政审判体制进而建立何种行政审判机构,仍然不乏争议和反复[1]吴欢:《清末民初行政诉讼法制中的“民告官”传统遗存》,《北方法学》2014年第2期。。
早在1906年,清廷即有裁撤传统都察院、筹建行政裁判院的设想。在那场官制改革中,清廷公布了《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表明其选择了大陆法系(德日法族)于普通法院外另设行政审判机构的“二元制”模式。《草案》共21条,第1条规定“行政裁判院掌裁判行政各官员办理违法致被控诉事件”,第2—7条规定行政裁判院的组织与构成,第8条规定行政裁判院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第9—11条规定受案范围和起诉程序,第12—13条规定审判组织和审判方式,第14条规定审判回避制度,第15条规定一审终审原则,第16—18条规定审判官独立原则,第19—20条规定审判辅助人员职责,第21条规定后续《行政裁判院章程》和《行政裁判法》制定与实施事宜[2]黄源盛纂辑:《平政院裁决录存》,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印行,附录三之“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第1283—1285页。下引该《草案》序言,以及北洋政府相关立法,均出自该书附录三,兹不赘注。。由此可见,《草案》兼有行政裁判院组织法和行政审判程序法的混合性质。
设立行政裁判院的改革方案引发了传统都察院的存废之争。此点前人多有论及[3]李启成:《清末民初关于设立行政裁判所的争议》,《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唯需强调的是,这场争论引起了革命党人宋教仁的持续关注。1906年10月8日,正在日本流亡求学的宋教仁在日记中批评清廷官制改革谓“较之以前旧制仍多,职分犹不如耳”[4]《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8—269页。。五年后的1911年8月初,业已回国宣传革命的宋教仁再次介入争论,撰文《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直抒胸臆,以期“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与中国自古设立都察院之精意”[5]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2页。。事后来看,宋教仁这两次心语傥论,竟成为近代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变迁的运思兆基,也暗示着民初平政院的命运纠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宋氏所欲斟酌调和的“立宪政治之通例”与“中国自古之精意”,俨然构成了近代中国法制变革不可偏废的两大关节。可资佐证的是,1906年《草案》序言开篇亦曰:“谨按,唐有知献纳使,所以申天下之冤滞,达万人之情状,与御史台并列。今各国有行政裁判院,凡行政各官之办理违法,致民人身受损害者,该院得受其程控,而裁判其曲直。”这表明,彼时立法者也存在以中国旧制比附行政裁判之用意或曰策略。由此可见,尽管清廷与宋氏分属不同阵营,但在建章立制上,二者似乎也有一些共同语言。
清廷将拟设的行政审判机构称作行政裁判院,而非献纳使司抑或行政法院,当是受到日本行政裁判所制度及其立法用语的直接影响。台湾地区学者林纪东早已指出,清末民初的行政诉讼法制,系受日本明治宪法的影响,而其间接的渊源,则是欧洲大陆法系的德奥等国[1]林纪东:《清末民初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研究》,台北《“中研院”法学期刊》2007年第1期。。就行政法理而言,行政审判、行政裁判、行政诉讼在近代早期中日学界本是互通互用,都指向官民纠纷裁判;所不同在于,行政诉讼是从原告角度描述司法权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过程,行政裁判和行政审判则是从裁判机关角度描述这一过程[2]赵勇:《民国北京政府行政诉讼制度研究——基于平政院裁决书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7页。。1890年日本明治宪法和行政裁判法颁行后,实定法和理论界使用行政裁判提法较为多见,模仿德日的清末官制改革遂将拟设的行政审判机构命名为行政裁判院。
值得注意的是,1906 年《草案》序言对域外主要国家的行政审判体制有一番评析:“英、美、比等国,以司法裁判官兼行政裁判之事,其弊在于隔膜;意、法等国则以行政衙门自行裁判,其弊在于专断;唯德、奥、日本等国特设行政裁判衙门,既无以司法权侵害行政权之虞,又免行政官独行独断之弊,最为良法美意。”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大陆法系“二元制”和英美法系“一元制”行政审判体制的特点和优劣,还从“二元制”行政审判体制中区分出德日模式和意法模式,可谓准确到位。彼时英美等国由普通法院管辖所有诉讼案件,但普通法院针对行政案件的裁判,在专业性方面或有欠缺,即所谓“其弊在于隔膜”。意法等国虽设有国家参事院(最高行政法院),但囿于“部长法官制”,实则变成行政机关自己当自己案件的法官,故“其弊在于专断”。而作为清廷模范对象的德国,早在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即有帝国裁判所之制,帝国瓦解后各邦国陆续设立独立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行政法院,即“特设行政裁判衙门”,再度统一后于1875年制定行政法院组织法和行政诉讼法。奥地利同样于1875年制定行政法院设置法,规定一审终审原则、诉愿前置原则等,并于维也纳设立最高且唯一的行政法院,可谓日本行政裁判所之蓝本和民初平政院之远祖[3]吴欢:《兼收并蓄:比较视野中的民初平政院》,《法大研究生》2018年第1期。。《草案》序言进而总结陈词:“今采用德、奥、日本之制,特设此院,明定权限,用以尊国法防吏蠹,似于国家整饬纲纪,勤恤民隐之至意,不无裨益。”此番自我表达或许说明立法者仍昧于行政裁判之真意,而落入廉政监督之窠臼,但确乎为民初平政院的治理功能埋下伏笔。或许是考虑到审判二字更具司法意涵,且已有《大理院审判编制法》(1906)之用例,清廷在1908年和1911年先后发布的“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和“修正宪政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又将行政裁判院改称行政审判院。但直至武昌首义,清廷一直没有实际设立行政审判机构。
辛亥之初,宋教仁不期然成为主国是者,受命起草《鄂州约法》,遂一展建章立制才华,在继承清廷1906年《草案》“二元制”行政审判体制基础上,进一步将向行政审判院提起行政诉讼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4]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612页,第157—159页。。这种做法也为其他省份效仿,《浙江省军政府约法》和《江苏省临时约法》均沿用行政审判院的提法和相关规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宋教仁又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不仅延续《鄂州约法》有关规定,还第一次明确提出设立“平政院”作为行政审判机构[5]陈顾远先生认为,“说起平政院这个名称来,据张怀九先生云,还是国父在南京临时政府所命名的”。见陈顾远:《双晴室余文存稿选录》,作者1965年自印,第169页。笔者认为此说不确当,南京临时政府政制创设实赖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恐无暇“命名”此一具体官制。宋教仁提出“平政院”名称的直接证据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载缪全吉编著:《中国制宪史资料汇编》,台北“国史馆”1991年编印,第44页。该草案题注为“宋教仁草拟,民国元年一月孙大总统向参议院提出”。。这一设想尽管未获通过,却被后来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吸收[6]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0—612页,第157—159页。。由此,平政院作为行政审判机构的名称和地位获得了宪法性确认。从纵向来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这番规定无论是条文位置还是审判体制,均与《鄂州约法》如出一辙,更与清廷1906年《草案》遥相呼应,只是机构名称有所变化。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暂的存续期内未及设立平政院,直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任务才被袁世凯落实。1914年3月31日,大总统袁世凯以教令形式公布《平政院编制令》,是为平政院的组织法。该法第1条规定:“平政院直隶于大总统,察理行政官吏之违法不行行为,但以法令属特别机关管辖者,不在此限(平政院审理纠弹事件不防及司法官署之行使职权)。”第16条规定:“平政院院长(肃政厅都肃政史)由大总统任命之。”由此可见,北洋政府平政院制度继续借鉴德日法族“特设行政裁判衙门”的做法,并赋予其直隶于大总统的超然地位。1914年5月17日,袁氏又公布《行政诉讼条例》,后经参政院修改定名为《行政诉讼法》,于1914年7月20日施行。此外,北洋政府还制定有《诉愿法》《纠弹法》《平政院处务规则》《平政院各庭办事细则》《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平政院各庭评事兼代办法》等配套立法,近代中国行政诉讼法制得以草创。1914年《行政诉讼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典。该法第1条规定:“人民对于左列各款之事件,除法令别有规定外,得提起行政诉讼于平政院:(一)中央或地方最高级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者;(二)中央或地方行政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人民权利,经人民依诉愿法至最高行政官署,不服其决定者。”第4条规定:“行政诉讼经平政院裁决后不得请求再审。”在此逐级诉愿制和一审终审制下,平政院遂成为彼时中国最高且唯一的行政审判机构。1914年5月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约法》(袁记约法),保留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行政诉讼的规定,再次肯定了以平政院作为“特设行政裁判衙门”的德日模式[1]夏新华等编:《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474页。。虽然在此后的几次制宪活动中,主其事者基于不同的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形势,有过以普通法院统一受理所有案件的设想或规定,但平政院一直在事实上存续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直到1928年北洋政府统治结束才闭院。
回顾民初立法史,自1912年宋教仁首次提出建立平政院的设想后,平政院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立法定位都是行政裁判(审判)机关。这一定位无疑是正确的,但也可能只是表面的。民初平政院的地位与性质颇为复杂,这在前述清廷1906年《草案》序言中即显露端倪。为了厘清平政院的真实属性,着实有必要与民初“帝制走向共和”的时局和政情相参照体认,尤其是回到宋教仁倡设和袁世凯力推平政院之本意与初心,认真检讨他们的设计理念与建制考量。
二、共和精神:宋教仁的立政归旨
清末民初行政审判机构的名称经历了从清末“行政裁判院”到辛亥“行政审判院”,到最终定名“平政院”的变化过程,而自宋教仁1912年以“平政院”取代“行政裁判院”后,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均沿用不改[2]当时即有学者以“平政院”为题讨论行政审判制度,如汪叔贤:《论平政院》,《庸言》1914年第4号。“五四”前后还有文学家以“平政院”对译法国行政法院,可见于法国作家莫泊桑短篇小说《保护人》较早的中译本,见《莫泊桑短篇小说集》,李青崖译,商务印书馆1923/1924年版。至于1928年以后,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六法”体系的建立,行政审判机构名称转而全盘西化为“行政法院”,中国气韵殆尽矣。。考虑到宋教仁在1913年即英年早逝,我们首先需要解释,宋氏选取的“平政院”名称蕴含着怎样的设计理念,为何能被广为接受,进而揭示从“行政裁判院”到“平政院”之变潜含的法政意蕴。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平政院”已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不宜变易,但我们试图指出其更深层次的原因。
这里的深层次原因首先在于,“平政”二字具有“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的固有词源含义,易于国人理解。据黄源盛先生考证,古汉语中“平政”本不连用,“平章”则源远流长:“‘平章’之义,乃辨别章明。‘平’为‘采’字讹。《尚书·尧典》:‘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百官。百官以功受姓。平章百姓即定姓别族之义。《史记·五帝本纪》作‘便章’,《尚书大传·唐传》作‘辨章’。《新唐书·百官志一》:‘贞观八年,仆射李靖以疾辞位,诏疾小,三两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此。中叶以后,凡实际任宰相之职者,必在其本官外加同平章事衔称,意即共同议政。宋代有平章军国重事,专以位置年高或望重之大臣,位在宰相之上。金元有平章政事,位次于宰相。元代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则为地方高级长官,简称平章。明初尤沿袭,不久即废。”[1]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总第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页。黄源盛先生这番考证的关键在于“共同议政”四字,而“平政”则是“平章政事”的简称。如果说黄先生的考证属于引而不发,只是暗示“平章(平政)”在中国传统政治话语和实践中具有“共同议政”之治理内涵的话,赵勇博士则明确指出:“平政一词古已有之,《荀子·王制》中即有‘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所谓平政,《汉语大辞典》解释为修明政治;修明,乃整饬昭明的意思;而‘平’字也有整治、治理的涵义。可见,平政有整治、治理政治的意思。从平政一词即可看出,对平政院这一机构,立法者更多的是关注其在治理政治方面的作用。正因如此,1914年《平政院编制令》不仅赋予了平政院行政审判权,还在平政院内设立肃政厅及肃政史,职掌纠弹及行政诉讼事务。”[2]赵勇:《民国北京政府行政诉讼制度研究——基于平政院裁决书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页。结合两位学者的语用学和语义学考证,宋教仁以平政院命名新生的中华民国的行政审判机构,盖有发掘“平政”所象征的中国传统政治(政制)的共和精神基因之用意,进而寄寓着宋氏对平政院的“共同议政”“平政爱民”“平政致治”之定位与期待。这并非无端揣测,而是有所张本。
宋教仁选取“平政院”作为民国行政审判机构名称的直接缘由,今人当然无从获悉,但他早年的日记透露了值得重视的信息。1904年至1907年,宋教仁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常因生活拮据而承担译书工作,并以翻译政治法律类书籍为主。据《宋教仁日记》,这段时期宋氏翻译了《日本宪法》《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俄国制度要览》《澳匈制度要览》《澳匈国财政制度》《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各国警察制度》《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大陆法系特别是德日法族的政法书籍,以及《美国制度概要》《英国制度要览》等英美政法书籍,甚至还有《一千九百〇五年露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等反映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作[3]参见《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所引译事散见各篇日记,恕不枚举页码。。这就为宋教仁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和日后在南京临时政府建章立制成为民初政制设计师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基础。当代学者陈旭麓所撰《宋教仁集》序言亦指出:“在向西方学习中,宋教仁最感兴趣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制度。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用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过这些东西,以便为中国的未来绘制蓝图。”[4]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序言第8—9页。1906年11月8日,宋教仁受托翻译《普鲁士王国官制》,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书系日人从德文译出者,官制、官名多系日本语,不可与汉文通,译时须参酌中国古今官制,则其相似者以易之方可。”[5]《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第302—303页。这段译事心得说明,宋教仁在译定中西官制时并非机械沿用日本译法,而是提出了“参酌中国古今官制”的原则。目前无法得知宋教仁在这些译作中对各国行政裁判机构究竟采用何种译法,但是其1906 年12 月30 日日记有直接交代:“译《普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完。其末为中央行政官署,首内阁,有伯里玺天德(即内阁总理)、副伯里玺天德各一及以下各官;次外务省,归并德帝国掌之;次度支省,次民政省,次学务省,次司法省,次陆军省,次农务省,次通商营业省,次工务省。各省中皆有尚书、侍郎。以下各官,则或有或无,其编制则有条不紊也。”[6]《宋教仁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92页,第302—303页。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平政院”,但宋氏针对普鲁士王国各种官职机构的译法,确乎贯彻了“参酌中国古今官制”的原则,是为其创设“平政院”译法的又一佐证。
考虑到清末以来行政诉讼法制总体上效仿德日法族“特设行政裁判衙门”,而宋教仁“参酌中国古今官制”的译事心得恰好是在翻译《普鲁士王国官制》时得出,且其时与清廷1906年《草案》公布相去不远,特别是宋教仁还在稍早的同年10月8日针对清廷官制改革作出了“较之以前旧制仍多,职分犹不如耳”的批评——虽是批评,倒也暗含着对“以前旧制”在职分设置上的肯定,故此可以合理推测,宋教仁此时已对行政裁判院之名称心存疑窦。可资补强的是,在此期间,宋教仁还耗费心血编写《汉文学讲义》,研究汉语音训、翻译语言等问题,并倡导和践行“中国新纪年”,即坚持推广和使用黄帝纪年,可见其对包括“治平天下”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政制的重视。更直接的证据在于,1911年8月,宋教仁在论及都察院存废问题时曾提出改都察院为惩戒裁判所并设立独立行政审判机构之主张:“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与中国自古设立都察院之精意,唯有改为官吏惩戒裁判所之一法,则庶可以折中至当矣乎。”[1]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2页。其时,相距宋教仁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中提出平政院之制度设想不过数月。其中所谓“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庶几与前述“参酌中国古今官制”交相辉映,完整呈现了宋教仁建章立制的设计理念,并最终服务于“折中至当”的“中国自古精意”。
如此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何宋教仁在1911年10月沿用清廷行政审判院的提法,转身又在次年1月创造性地提出平政院的名称。先前沿用清廷旧称,或许是因为武昌首义事发仓促,宋教仁无暇细绎其理,聊备一时之需;及至临时政府成立在即,中华民国百废待兴,宋教仁开始通盘考虑新生共和国建章立制的设计理念,继续沿用清廷旧称已不合适,而宋氏也有了新的计较。正是因为宋教仁在政治设计和官制名称上坚持参酌古今和斟酌中西的立场和理念,所以他选择了颇具中华古意又有时代精神的平政院。正如孙中山先生在“五权宪法”理论和实践中,将传统中国考试与监察制度同近代西方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巧妙结合一样,宋教仁也在行政审判及其配套制度上,将传统中国诉愿陈情和御史监察制度同近代西方行政诉讼制度融贯一炉。如果说孙中山是中华民国之父,宋教仁则在某种程度上堪称平政院之父。宋氏以中国传统政制中具有“共同议政”职能的“平章政事”之简称,并寄寓“平政爱民”之期待,作为新生的中华民国审理官民纠纷的机关名称。此举极大昭示了中华民国作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建政精神,也高度契合了清末民初“帝制走向共和”的时代主题。事实上,“共和”一词同样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固有词汇,其核心含义就是共同治理、协和谋国。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共和”古义与近现代“共和国”理念可谓不谋而合[2]张凤阳:《共和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正因为宋教仁此番别出心裁的设计理念,载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平政院”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都是行政审判机关的当然名称,更因其蕴含“共同议政”和“平政爱民”的建政精神,遂在民初政制架构和治理实践中具有特殊地位与意义。
需要附带提及的是,广义上的民初平政院其实并非只有一所,北洋政府平政院也并非最早一家。就后者而言,1912年响应辛亥革命的新疆伊犁起义中,杨缵绪等人成立的新伊大都督府曾设平政院长之职[3]朱培民:《辛亥革命在新疆的胜利和失败》,《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但由于伊犁起义旋即失败,新伊大都督府所辖平政院并未实际运行。就前者而言,1920年代初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的广州军政府也有过平政院之制[4]欧阳湘:《近代广东司法改革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虽然二者并不在本文研讨范围之内,但也说明宋教仁所定“平政院”之名称被各界政治势力广为接受。
三、治理向度:袁世凯的建制考量
从清末到民国,最重要的时代主题就是“救亡图存”。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威胁和宪制共和的制度优势面前,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从器物到制度到思想诸多层面,均感受到“技(己)不如人”的窘迫和压力。为了因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困境,不仅要“开眼看世界”(如林则徐),还要“师夷长技”(如洋务派),乃至“全盘西化”(如新文化运动急先锋)。由此,传统中国明君清官良民之治理愿景,转为立宪共和民权之宪制追求,传统治理秩序亦逐步瓦解而向近现代治理艰难转型。具体到法制层面,从清末“变法修律”到民国“六法体系”,大抵都是以法制之进化求主权之独立的法政思想产物,大抵都是救亡图存时代主题之下的法制救国行动。
以此种救亡图存主题和治理转型视角,来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行政法制变革进程,当会发现,清末拟设行政裁判院,其重要缘由就在于,传统“民告官”制度设计中的都察院体制被认为无法因应君主立宪抑或主权在民政治变迁下的治理秩序建构需要,无法充分实现对民权的保障和对官僚的监督。时人贺绍章即撰文总结当时争议双方观点[1]贺绍章:《都察院改废问题》,日本《法政杂志》1911年第8号。。无论是所谓“改革派”与时俱进的法政主张背后隐含的文化自卑感和政制西化性,还是所谓“保守派”因循守旧的政治观念背后潜藏的文化自主性和政制优越感,都是救亡图存重压下,应予同情理解的见识与努力。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时人对于官民纠纷解决机制在古今治理秩序中的共通性地位与意义,尚未能有充分的自觉与真切的认识,又未能妥善处理政治转型过程中新旧制度与具体人事之间的抵牾与冲突,以至于清廷的变法改革大多处于“预备”或“草案”状态,并最终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下被激进的革命洪流冲击得自身难保。
出人意表的是,革命党出身的宋教仁,在辛亥初年草就共和政制蓝图时所秉持的基本设计理念,却是在立宪共和政体之下“参酌古今官制”和“斟酌立宪政治之通例”,以符合“折中至当”的“中国自古精意”。宋教仁所设想的行政审判机构与传统都察院之间,也并非水火不容、非此即彼,而是有望“调和新旧一举两得”。宋氏所谓的参酌、斟酌、调和,与其说是妥协乃至软弱性,不如说是对清末民初这个过渡时代之过渡属性的清醒认识,其背后则是宝贵的共和精神与立宪技艺。宋氏这种审慎、克制与温和的气质,殊与他时他日他人之激进风潮不符,却与彼时彼刻彼境清帝逊位、五族共和的建政潜流(相较于武昌首义、种族革命的建政显流)相暗合[2]参见高全喜:《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惜乎天不假年,宋教仁不幸于1913年3月遇刺离世,其建立平政院的设想,也一度被其革命同志所摈弃。1913 年10 月,由国民党籍议员主导制定的《天坛宪法草案》第86条规定:“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但宪法及法律有特别规定者,不在此限。”此举固然是为限制袁氏权力,维护民主法治,但如此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无物、因人而设事改制的“宪法工具主义”倾向,终究与其欲达致之终极目标不相符合,甚至连其谋求的直接效果也毫无所获。此后的“袁氏当国”,乃至军阀混战,莫不可以从此番反复中窥见端倪。
在《天坛宪法草案》作出不设平政院的草拟规定后,袁世凯当即通电全国指出:“今草案第八十六条‘法院依法律受理民事刑事行政及其他一切诉讼’云云。今不按遵约法另设平政院,使行政诉讼亦隶法院。行政官无行政处分之权,法院得掣行政官之肘。立宪政体固如是乎?”[3]吴宗慈主编:《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大东书局1924年版,第52页。袁氏此语,本于约法明文,着眼治理实践,其言之凿凿,虽国民党人以革命自居,以宪法是求,也难以逃脱诘难。于是,袁世凯这位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反动人物,却继承了政敌宋教仁的遗志,不仅设立了平政院,还在平政院内设立肃政厅,成了宋教仁难得的政制知音,真可谓是“袁承宋志”。我们无意在此为袁氏做翻案文章,但如果真正秉持同情理解之立场,应当体察袁氏当国面临的内忧外患格局和重建秩序重任。
具体到平政院之设置,其直接指向的就是民初官场腐败盛行、民权难以伸张之现实弊病,更深层次的考量则是协和官民冲突、重建治理秩序。这正如袁世凯在要求各官署举荐平政院官员的命令中所说:“迨改革以来,秩序未复,贪猥杂进,纲纪荡然,当局者恒滥用威权,同列者辄扶同徇隐。用人以爱憎为取舍而公论不彰,判事以喜怒为是非而真情益失,甚至筦榷者从事侵渔,典军者寖多骄蹇。流弊所趋成为风气,法令所布视等弁髦。中央勤求民隐,岂能一体周知,小民徒报烦冤几至无从呼吁。”[1]中华民国《政府公报》第684号,1914年4月3日。袁氏此论,尤其是开宗明义的“改革以来,秩序未复”等语,并非危言耸听。民国初年的国家治理的确弊病丛生,除了外交上的列强环伺,军事上的南北征战,政治上官僚作威作福风气和地方离心割据趋向始终存在,虽名为民主共和国,但民权难伸,自由难觅,以致民间颇有“北洋不如大清”之悲叹。袁世凯的历史功过是非姑且不论,但此番拯救时弊国艰、重建治理秩序的议论主旨不可因人而废。于是,袁氏决定:“亟应将平政院从速设置,并参酌旧制,体察国情,于该院设置肃政厅,俾于行政审判之外兼有纠弹官吏之权,期挽颓风而臻上理。”[2]中华民国《政府公报》第684号,1914年4月3日。在接见首批肃政史时,袁氏亦训话曰:“吾国自入民国以来,仕途庞杂极矣,特设肃政史一官冀有所补救。”[3]《总统训诫肃政史之演词》,《申报》1914年5月30日。纵观袁世凯“参酌旧制、体察国情”等语,对照宋教仁“参酌古今官制”等语,足证二人在平政院设计理念和建制考量上颇有“平政致治”之共鸣。从袁氏命令和训词中亦可看出,平政院在设立之初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行政审判机构(审理行政诉讼事件)和行政监察机构(审理纠弹事件),其制度功能在行政审判与行政监察之外,更有着涤荡官场颓风、调和官民冲突、重建治理秩序的考量。换言之,在宋教仁、袁世凯等民初政制设计者眼中,平政院不仅仅是消极被动的行政诉讼裁判者,抑或官吏违法纠举者,而更应当是积极主动的治理秩序建构者、参与者和维护者,是民初政制与政治不可或缺的治理者[4]吴欢:《论民初平政院的治理权能与角色》,《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平政院的治理者地位,不仅源自宋教仁秉持共和精神的命名和倡设,也在袁氏前番命令和训词中获得政治背书,还在《平政院编制令》等实定法中获得立法确认。但更为重要的是,袁氏还于1914年6月颁布《平政院裁决执行条例》,为平政院裁决提供执行保障。该条例共5条,照录如下:“第一条 行政诉讼事件之执行,对于主管官署违法之命令或处分,得取消或变更之。第二条 行政诉讼事件经评事审理裁决后,由平政院长呈报大总统批令主管官署按照执行。第三条 主管官署对于行政诉讼事件,不按照平政院裁决执行者,肃政史得提起纠弹,请付惩戒。第四条 纠弹事件之执行,涉于刑律者,由平政院呈请大总统令交司法官署执行;涉于惩戒法令者,由平政院长呈请大总统以命令行之。第五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施行。”根据黄源盛先生的统计,平政院14年存续期内裁决的近200起案件(其中变更和撤销裁决约占48%),几乎没有遭遇执行障碍,全部得到行政官署的尊重与执行;即便在袁氏生前和死后不乏质疑和撤销平政院的声音,但袁氏之后的北洋政府领导人和行政官署,仍大体沿袭了对平政院裁决的尊重与保障的立场[5]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总第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6页。。至1917年肃政厅被撤销,时任大总统黎元洪仍修正颁布前述条例,仅将第三条改为“主管官署对于行政诉讼事件不按照平政院裁决执行者,平政院长得督促该官署执行,并呈报大总统”。凡此种种,均证明和强化了民初平政院的治理者地位与角色。
体认到民初平政院的治理者地位与角色之后,再来审视其各项本兼职能。根据《平政院编制令》等相关实定法,平政院不仅作为一个机构具有行政审判和行政监察的主要职能,其最高领导人(院长)抑或具体法政人(评事),还具有参与宪法解释会议、司法官惩戒委员会、审计官惩戒委员会、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文官高等典试委员会的资格,此外还有以平政院裁决省议会与政府争议、审查全国议员选举资格和监督行政机关国民会议选举的规定和实践[1]吴欢:《论民初平政院的治理权能与角色》,《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在治理者的定位下,平政院所谓的行政审判职能,不仅是消极应对“民告官”案件的需要,更是古今中西矛盾交织之下,通过审理“民告官”案件,实现伸张民权、走向共和的时代重任之举。平政院的行政监察职能,也不仅仅是民初政治斗争的工具,而且是在帝制向共和转型之际,从严治官、整肃纲纪的救弊之举。至于平政院所担当的广涉民初政治实践的各项治理职权,则更加凸显出平政院的治理者定位。换言之,在民初宪制共和秩序框架尚不完备的过渡时代,作为一个隶属于大总统而又相对独立超然的中央政制机构,平政院拥有参与宪法解释、法官惩戒、议员选举、文官选任、文官惩戒等重大政治治理活动,以及裁决机关权限、审查议员资格、监督国会选举等广泛治理职权,深刻地介入了宪法秩序、立法秩序、司法秩序和行政秩序建构实践,或曰,平政院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了民初国家治理秩序转型与重构的进程之中。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民初平政院的深层次政制地位与功能问题做出回答。机械的规范推演无法揭示平政院的真正法律属性,带着部门法局限以今视昔也无法理解平政院的真实政制功能,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民初治理转型,投向平政院的治理实践。基于此种认识,我们将平政院界定为民初国家治理秩序转型与重构进程中积极而能动的治理者。这种定位与定性是可行的。首先,从理论上来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都不是单纯的审判机关,其司法判决中必然带有治理决断。即便将平政院视为行政审判机构,其也是彼时中国最高且唯一的行政审判机构,其所做出的行政诉讼裁决天然地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进而蕴含着决断性。其次,在民初“帝制走向共和”之际,确实需要有能力、有担当、有智慧的治理者参与建构国家治理秩序。这也正是袁世凯前述命令中所说的“改革以来,秩序未复”。最后,平政院的设计者宋教仁和创制者袁世凯皆对平政院寄寓了“共同议政”“平政爱民”的共和精神,以及整顿纲纪、重建秩序的治理期待。
申而言之,关于民初平政院制度的共和精神与治理向度,或曰通过平政院“平政致治”的国是共识,还可以根据“平政院”的名称,进行近似“望文生义”的体认。所谓“平政”,实为“使政平”。这里的“平”字,首先是一个动词,是治(国)和理(政)的意思。更为重要的,这里的“平”还隐含着价值判断或曰结果期许,寄寓着民初政制设计者对优良治理秩序的追求。由此,平政院不仅是一个行政诉讼裁判者,更是民初国家治理秩序的建构者;不仅肩负着参与国家治理秩序建构的重任,而且潜含着“对治理者的治理”之重要内涵。换言之,民初平政院承担着“治官治吏”这一古今中西共通的治理职能,进而蕴含着“平政致治”的制度期许。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平政院系由革命党人宋教仁首倡其事且其壮志未酬,但仍然被政治强人袁世凯力排众议建置成立,并为之做政治背书,提供执行保障。不宁唯是,无论是袁世凯本人,还是后续当国者,无论是中央行政官署,还是地方行政官署,均对平政院的审判与裁决保持相当程度的尊重——这一结果,不仅是当时反对平政院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恐怕也是平政院的倡导者们,包括宋教仁和袁世凯,所意想不到的(尽管也许他们乐见其成)。这也印证了黄源盛先生的判断:“观夫古来任何政策的举措,成于制度者半,成于人事者亦半。”[2]黄源盛:《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载范忠信、陈景良主编:《中西法律传统》总第6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