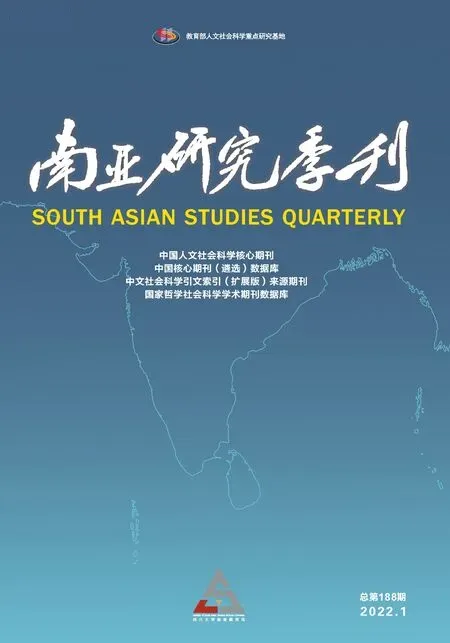美国撤军后阿富汗塔利班的变化与挑战 *
杨云安
【内容提要】 美国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塔利班由此重新执掌阿富汗最高权力,阿国迎来新的权力洗牌。阿富汗国内各种环境条件和塔利班自身都在过去20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塔利班的领导结构、军事力量、战略战术运用、与其他派系的关系等都发生了变化。重新上台的塔利班所面临问题和挑战的复杂性可能要超过其想象,如国内民族矛盾,处理好与各类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关系,解决财政收支问题,确保政府运转。此外,塔利班还要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国际社会处理好外交关系,推动国家现代化进程,提高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这些问题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塔利班政权如何应对值得关注。
一、塔利班面对新的阿富汗
2021年5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将在9月11日之前从阿富汗完全撤军,这标志着美国在阿富汗持续20年的反恐战争落下帷幕。2011年,美国以策划“9·11”事件为理由,指责阿富汗塔利班窝藏“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头目本·拉登及支持者而发动阿富汗战争。在付出大量人力、财力、物力的代价后,留下阿富汗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撤军回国。“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相关花费达2.313万亿美元,2324名美国军人和4.6万多名阿富汗平民死亡,与战争相关的死亡总人数达24.3万人(含巴基斯坦人)。”(1)杨超越:“美国撤军阿富汗后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1期,第56页。撤军标志着美国阿富汗政策的失败,这将引发新一轮各方博弈。阿富汗临时政府建立后,社会整体保持稳定,但是各种爆炸事件时有发生。“2021年8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政权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在阿富汗制造了多起袭击事件,造成上百人死亡。”(2)高蕊:“阿富汗西部发生炸弹袭击致7死9伤”, 2022年1月23日,http:∥www.news.cn/mil/2022-01/23/c_1211539697.htm,2022年3月4日。频发的爆炸事件给阿富汗重建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困扰着阿富汗临时政府。
阿富汗地缘重要性相比20年前大大提升。彼时的阿富汗是一个封闭国家,处于塔利班牢牢控制之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牵涉不深。今天的阿富汗地缘影响力大大提高。基于安全和地缘利益考虑,伊朗、巴基斯坦、印度、欧盟、俄罗斯、中国甚至包括已经撤军的美国都不愿也不会置身事外。20年反恐战争没有给阿富汗带来稳定,反而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有利的生存土壤。“基地”组织残余势力、“伊斯兰国呼罗珊分支”(简称“IS-K”)、“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等恐怖组织都将阿富汗作为活动基地,并不断发展壮大,严重威胁着周边国家的核心安全利益。中国作为阿富汗的重要邻国也深受其害。塔利班与各类恐怖组织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使其难以在短时间内与周边国家恢复正常的外交关系。随着塔利班临时政府的建立,这些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也会有新的动向,这值得各国关注。虽然美国从阿富汗完成了撤军,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对阿富汗事务完全撒手不管,其仍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阿国政治局势。塔利班如果无法有效控制阿国内局势,阿国将再度陷入混乱,甚至再次爆发内战。该地区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也可能会趁机发展壮大,向周边国家或地区扩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周边国家必须与塔利班当局保持着接触和联系。这些因素提高了阿富汗的地缘影响力。
塔利班在阿富汗战争中一直坚持抵抗,逐渐赢得了对手和国际社会的事实承认。反恐战争没有消灭塔利班,反而让塔利班成长为阿国一支更加成熟、强大的政治力量。塔利班也学会了与外部世界保持接触,改变了以往的孤立状态。近年塔利班积极对外交往,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释放谋求和平的意愿,配合军事战场的行动,获得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事实承认。2015年以来,塔利班代表团先后以各种外交方式与俄罗斯、印度、中国、美国等大国保持外交互动,与巴基斯坦、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也一直维持着密切联系。俄罗斯、中国都公开表态支持阿富汗人民管理本国事务。美国也从一开始不承认塔利班,到和塔利班展开谈判,最终默许塔利班重新掌握政权。这些外交活动为塔利班顺利重掌权力提供了有利条件。2021年11月28日,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表示,阿富汗愿与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和经济联系;针对一些邻国的安全忧虑,公开声明打击恐怖主义分子,不允许任何恐怖势力在阿富汗活动。阿富汗政府此举意在撇清与各类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的关系,同时赢得周边国家信任,拓展外交空间。
阿富汗国内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占领期间除了大力援助阿富汗之外,也通过现代化方式改造阿富汗,尽管成效不显著,但是也达成一些成果。阿富汗人均GDP超过500美元;(3)The Word Bank:“The Country Profile of Afghanistan”,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views/reports/reportwidget.aspx?Report_Name=CountryProfile&Id=b450fd57&tbar=y&dd=y&inf=n&zm=n&country=AFG, 25 March 2022.城镇化率有所提高,城市人口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农村人口占比从2000年77.8%下降到2020年的73.9%”(4)The World Bank:“Rural Population of Total Population-Afghanistan”,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P.RUR.TOTL.ZS?end=2020&locations=AF&name_desc=false&start=1960&view=chart, 25 March 2022.;通信、电力、交通、医院、学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较快发展;受教育人数大幅增长,有大量阿富汗人口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阿富汗拥有手机的用户已经超过2000万户,覆盖超过80%的人口。在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阿富汗取得的成绩也非常显著。全国现有1.3万所学校,有适龄入学儿童800万,其中38%是女生,全国共聘用教师17万名。”(5)张吉军:“阿富汗战后重建面临的困境及出路——以政治机会理论为视阈的分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48页。妇女权益保障和社会经济地位得到提高。2021年12月3日,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颁布一项保护妇女权益特别法令,规定“成年女性有婚姻自由,不得强制女性结婚;不得将女性视为私人财物,不得将女性用作解决争端和消除敌意的物品”。(6)张欣然:“阿富汗当局颁布保护妇女权益特别法令”,2021年12月3日,http:∥www.news.cn/2021-12/03/c_1128129565.htm,2021年12月20日。这些规定至少表明塔利班当局妇女政策的转变,这对提高妇女群体的社会地位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为了赢得民众支持,塔利班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安抚人心,消除民众忧虑和恐惧心理。今天的阿富汗是一个更加现代化的国家。阿国民众特别是城市人口接受了现代文化洗礼,从衣食住行到沟通交流、教育、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首都喀布尔已经具有了现代城市的特点,塔利班面对的已经是日益开放和现代化的都市。
二、塔利班自身的调整和变化
塔利班的社会基础相比以往有了较大改变。过去20年塔利班吸纳了更多普什图部族和其他民族的民众,以扩大自身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在被美国和“北方联盟”推翻政权后,塔利班隐藏于阿富汗民间,其领导机构体系化整为零,迁移藏匿到巴阿边境和普什图部落地区。这期间,虽然塔利班最高领导人奥马尔病逝,继任领导人曼苏尔也因美军轰炸身亡,但是其领导机构并未瘫痪,一直保持较强的领导力,有效指挥了塔利班展开对政府军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的袭击。藏匿于部落区的塔利班领导人也和当地部落长老建立了密切关系,后者为塔利班提供庇护、信息情报、人员补充、物资供应等帮助。塔利班蛰伏农村后与部落进一步密切联系。“塔利班通过农村的毛拉,建立了与部落社会的联系,通过毛拉招募成员,劝导部落首领归顺,搜集情报等。同时,塔利班给予部落社会一定的安全保证,默许农村种植罂粟,并为在农村招募的成员发放一定的工资等,为部落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在这种环境下,大量的部落组织归顺塔利班,成为它的地方武装和政治力量。”(7)闫伟:“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历史逻辑”,《现代国际关系》,2021年第8期,第4页。塔利班有了更加广泛支持者,这是其剿而不灭的重要原因。“根据民调数据,2019年,在以普什图人为主的扎布尔和乌鲁兹甘省,半数以上的民众同情塔利班。”(8)Tabasum Akseer, John Riegereds.,A Survey of the Afghan People: Afghanistan in 2019,The Asian Foundation, https:∥asiafoundation.org/where-we-work/afghanistan/survey/,2019, p.69.以部族为基础的族群体系支撑起了阿富汗国家架构。普什图部落一直有反对外族入侵的传统,由美国扶持的阿富汗临时政府在很多普什图人眼中就是傀儡政权,不能代表阿富汗,不能代表普什图人。而塔利班以民族主义和普什图传统为号召,赢得了越来越多普什图部落的支持。
阿富汗塔利班的军事战斗力明显提高。塔利班掌握的军事力量在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时期大都被消灭,剩下的只能隐藏于民间。随着阿富汗战局焦灼,特别是美国对阿富汗的占领越来越引起周边国家不满和抵制,各方势力博弈色彩更加明显。塔利班的战斗力获得了显著增强,军事人员素养、武器装备、战斗技能和战斗意志都明显提高。“据美国国会研究报告分析,截至2020年1月,阿富汗国防与安全部队约有28万人,而塔利班仅有约6万‘全职’战士。”(9)王娟娟:“特朗普政府阿富汗政策的演变轨迹、战略逻辑及未来走向”,《南亚研究》,2020年第4期,第113页。塔利班武装人员数量虽然不占优势,却能和美国及其扶持的阿富汗政府军长期周旋,并且迫使美国最终决定抽身撤军,塔利班的军事力量相比20年前明显增强。这其中不排除有某些政治力量的扶持,甚至提供某些军事援助。美国就曾指责伊朗向塔利班提供武器和人员援助;巴基斯坦也一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为恐怖组织提供帮助。美国撤军后,在阿国内遗留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美国遗弃在阿富汗的武器军备的总价可能约为850亿美元。这些被遗弃的武器包括:近2.2万台装甲车、35.8万支自动步枪、176具火炮装置、8000辆卡车、100多架直升机以及运输机。”(10)王金志:“俄高官:美国遗弃在阿富汗武器可能流入世界任何角落,带来不愉快意外”,2021年11月3日,http:∥www.news.cn/mil/2021-11/03/c_1211430490.htm,2021年11月10日。据俄罗斯国防部长透露的消息,塔利班已获得超过100套防空导弹系统,这使其军事实力获得极大改善和提高。
塔利班的领导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是还没有十分稳定。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一手创建了塔利班,并凭借精神和政治领袖的超然地位建立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体制。他还组织亲信、重要盟友仿照普什图传统议事会组建了各种委员会,分别负责财政、后勤、情报、军事、宗教等,这些委员会领导人构成了以奥马尔为核心的塔利班领导层。这种领导结构保证了奥马尔的权威地位。各委员会在奥马尔领导下承担政策咨询、制定、执行职能。奥马尔死后,阿塔赫尔·曼苏尔继任领导人,他后来遭遇美军空袭身亡。2016年,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被推举为新一任领导人,但他缺乏奥马尔的超然地位,只能将最高权威和权力部分让渡与各委员会成员,实际上是通过放权维系领导机构稳定,各委员会领导人获得了较大的自主权。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资历较浅,也不是军事领导人,性格相对温和,能为各方所接纳。他能够协调各方利益,弥合主张分歧。阿洪扎达之下的重要领导成员还包括负责塔利班武装力量的穆罕默德·雅各布,负责哈卡尼网络的希拉祖丁·哈卡尼,负责外交和政务的阿普杜勒·加尼·巴拉达尔。这三人名义上服从阿洪扎达,实际上都有很强的独立性。雅各布在奥马尔死后一度被塔利班内部作为最高领导人人选,目前在临时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哈卡尼担任内政部长,巴拉达尔担任副总理,在塔利班内部是资深高级领导人之一,主要负责外交谈判、对外联络。他曾代表塔利班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签署关于美军撤离的《多哈协议》,也曾于2020年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成为第一位与拜登通话的塔利班领导人。2021年9月21日,塔利班宣布“毛拉扎基尔(Mullah Abdul Qayyum Zakir)担任国防部副部长,萨达尔·易卜拉欣(Sadr Ibrahim)担任内政部副部长,上述两人均效忠阿塔前领导人曼苏尔且都手握重兵”。(11)王世达:“阿富汗大变局:地缘政治和安全格局的演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1期,第20页。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高级领导成员负责或者协助负责具体事务,如宗教事务、司法审判等。阿富汗塔利班的权力结构从奥马尔时期的圆锥形向扁平式集体领导结构过渡。在建立全国政权后,随着中央政府治理国家事务的集权需要,扁平式权力结构必然会调整,这可能引起内部权力斗争。此外,塔利班内部也一直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这表现为包括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成员多次被传出死亡讯息。“在塔利班公布临时内阁名单后,有很多传言称原来被普遍认为可能担任总统或总理,但出人意料地只在临时内阁中拟担任代理副总理的巴拉达尔,和‘哈卡尼网络’因为利益分配和理念分歧发生严重冲突,之后被软禁或者被打伤。虽然塔利班进行了辟谣,但是巴拉达尔的低调和之前的活跃形成了强烈对比。”(12)朱永彪:“阿富汗重建面临的挑战好出路”,《人民论坛》,2022年第5期,第107页。这说明塔利班内部存在较大矛盾,可能会因权力斗争产生内讧。阿富汗在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权力结构也必然会进行相应调整,这个调整过程很可能会伴随流血和冲突。
领导体系多元化是塔利班内部派系分化的重要原因。塔利班在过去20年中一直面临美军围剿,中央权力机构即政治领导体系大幅削弱同,而各地分支组织开始壮大,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特别是以军事领导人为代表的派系势力强大。随着美国开始承认塔利班的存在,负责外交谈判事务的领导人影响力开始上升;负责传经和思想宣传的宗教力量也一直发挥着组织和动员作用。塔利班的重新崛起是其在政治、外交、军事和宗教等多个领域成功经营的结果。外交政策使其赢得了国际支持、援助,加快了美国撤军步伐;军事斗争提供了强有力的战场支持,促使美国决策层决心撤军;宗教宣传扩大社会影响力,凝聚起成员战斗意志,拉拢了地方军阀和普什图部族势力。但这也造成塔利班内部分化形成不同的派系,尽管他们对外都从属于塔利班组织,但对内却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国外学者曾将塔利班分为温和派和极端派,但实际情况可能更复杂,不能简单地以温和或极端的政治态度来划分。2021年5月,塔利班组织的声势浩大的“联合进攻”,在战斗中不同派系各自为战,暴露出不合的苗头。其中,军事领域的表现最为明显。塔利班直接掌控的武装包括临时政府国防部长雅各布所掌握的武装力量、哈卡尼网络、红色部队和拜德尔313部队等,这些武装力量构成塔利班军事力量主体。一些地方实力派包括规模不等的军阀、普什图部落长老及其控制的军事力量名义上也服从塔利班指挥。从阿国目前的局面看,塔利班控制了阿富汗大中城市,在乡村基层地区则任由地方势力保持事实上的割据。随着塔利班政府建立,优化权力结构、整合领导体系是必然之举。在权力分配考验面前,塔利班究竟是保持团结、守住浴血奋战打下的江山,还是上演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一幕值得关注。
在对外交往方面,塔利班一方面与地方势力如地方军阀、普什图部落长老联系密切,另一方面重视外交工作,学会了与世界打交道。塔利班与周边国家一直保持较高频次的互动,如访问、对话等;与伊朗、巴基斯坦、俄罗斯都保持了对话和联系,充分利用国际舞台扩大自身影响力;和美国也是既打也谈,并且通过谈判桌实现了很多目标。随着塔利班临时政府的建立,其争取国际承认、推动恢复重建、获得发展资金、解决国内人道主义危机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帮助,良好的外交环境有助于上述目标的实现。
此外,塔利班在赢得胜利的过程中与前阿富汗政府和安全部队内部一些人士也建立某种联系。例如,根据联合国2014年发表的报告,“2013年,塔利班在全国373个地区中仅完全控制了4个,其势力所达范围仅占全国的4%。”(13)Juergen Kleiner,“How Many Lives Do the Taliban Have?” Diplomacy & Statecraft,Vol.25,No.4,2014,p.712.2015年塔利班起发起攻势,政府军节节败退,仿佛一夜之间失去了战斗力。“至2018年初,塔利班实际控制和非常活跃的地区占到了全国面积的70%,覆盖人口规模达到了150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14)杨舒怡:“阿富汗安全局势堪忧塔利班已威胁到七成国土”,2018年2月1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02/01/c_129803063.htm,2022年3月25日。“2021年9月,塔利班已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15)谷玥:“阿富汗塔利班说已完全控制潘杰希尔省”,2021年9月6日,http:∥www.news.cn/2021-09/06/c_1127832902.htm,2022年3月25日。至此,阿富汗全境都被塔利班掌控。阿富汗安全部队是由拥有美军装备并由美军训练建立起来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队伍,一直获得美军情报和火力支持。面对武器装备较差的塔利班军队,其表现出的战斗力却令人汗颜。即便是考虑到了美国撤军大背景造成的军心动摇因素,也很难解释为何占据优势地位的政府军节节败退。结合现在塔利班对外交政策的娴熟应用,存在一种可能,即塔利班与阿富汗政府军的部分官员或军官建立了合作关系。后者在政府或者军队内部为塔利班提供了鲜为人知的协助。2020年2月29日,美国与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协议明确了美国撤军计划表。“塔利班几乎零成本地达到了此前追求的目标,即自身地位合法化、维护内部团结、扩大国内外影响力以及削弱阿富汗政府权威等。”(16)朱永彪、苗肖阳:“特朗普政府的阿富汗战略评析”,《当代世界》,2020年第5期,第32页。2021年拜登政府上台后,撤军进程大大加快。美军在首都喀布尔的大撤离造成了巨大混乱,塔利班却在第一时间将战线推进到了喀布尔郊区。由此可见,塔利班掌握了较为准确的信息情报。虽然不清楚塔利班的信息渠道,但是从阿富汗政府和军队软弱涣散的表现来看,内部人士出力是大概率事件。
三、塔利班当局面临着多重挑战
阿富汗国内民族矛盾较为尖锐,民族仇恨不易消解。塔利班成员主体是普什图族,该民族是阿国内第一大民族,约占阿人口的40%。近代以来一直掌握阿富汗最高权力,与其他民族积怨甚深。无论是苏联占领时期还是美国主导阿富汗时期,普什图族与其他民族的武装冲突和仇杀都不间断。2001年,塔利班曾策划过针对哈扎拉人的屠杀,“北方联盟”在进军喀布尔、推翻塔利班政权过程中也大肆屠戮过普什图村庄和部落。2016年在哈扎拉人聚会上,也曾发生多起自杀爆炸事件。“2018年3月,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诺鲁孜的哈扎拉地区炸死33人。9月,一名自杀炸弹手在喀布尔的一个哈扎拉摔跤俱乐部杀死了多达30人,第二名炸弹手又炸死了26人。2018年10月,塔利班开始对中部省份乌鲁兹甘和加兹尼的哈扎拉人居住的地区发起攻击,造成数百人死亡,数千人流离失所。2019年3月7日,喀布尔哈扎拉人集会遭到迫击炮袭击,造成11人死亡,95人受伤。”(17)张冰冰、王晶:“族群冲突视域下的阿富汗国家重建”,《国际研究参考》,2020年第8期,第42页。阿富汗的民族仇恨延续数百年,很难在短时间内冰释。卡尔扎伊政府和加尼政府为了照顾少数族群利益,在权力分配上对少数族群有所让步,但这也引发了新的矛盾,各方都不满意新的权力划分,都希望掌控更多权力。由于“阿富汗各族群都想扩大本族群的势力,扶植自己的代表进入政府以为本族群谋福利,由此产生的官僚机构的民众认同度极低,而许多官员为了连选连任,不得不以本族群的利益为首要”。(18)同上,第42页。阿富汗国内的塔吉克人、哈扎拉人、乌孜别克人都在联合政府时期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和资源,如今随着塔利班政府上台,他们与普什图民族的地位再次翻转。除了民族矛盾,普什图内部实际上也存在不同的部落间的矛盾。塔利班虽然获得了普什图一些部落的支持,但是也有很多部落反对塔利班,他们也多次派人暗杀敌对部落长老,部落间矛盾一点也不逊色于民族矛盾。
塔利班当局需要处理好与境内各种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关系。“哈卡尼网络”是活跃在阿富汗的一支政治力量,一直与塔利班当局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在1995年宣誓效忠塔利班,一直是塔利班领导层的重要成员。该组织因多次组织、策划恐怖活动已被联合国和美国列为恐怖组织。“该组织成员多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偏远部落,盘踞在阿巴边界山区,约有5000~15000人。”(19)Wolf S:“The Fallacy of State Rhetoric: Pakistan, Haqqani Network and Terror in Afghanistan,”SADF Focus, No.13, 2016, pp.2-15.除此之外,在阿富汗境内还有20多个国际恐怖组织,“其中‘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哈卡尼网络’‘巴塔’是本地区最大的三个恐怖组织,各有3000~5000名战斗人员;第四大组织‘伊斯兰酋长国高级委员会’(塔利班拉苏尔派)有1000名战斗人员;‘基地’组织、 ‘乌伊运’和‘虔诚军’各300名战斗人员;塔里克·吉达尔组织(TGG)有100~300人;巴塔分支‘自由人党’ (Jamaat-ul-Ahrar)有200余人;‘土伊运’有100多人;‘伊斯兰圣战联盟’‘达瓦慈善会’(Jamaat-ud-Dawa)各有25人”。(20)外交部:阿富汗动态,2019年6月30日,https:∥www.mfa.gov.cn/ce/ceaf/chn/afhdt/t1677005.htm,2022年3月26日。在美国占领时期,各种极端组织在打击美国这个共同目标下调节彼此关系和行动。随着美军撤离,彼此间如何处理好关系是个较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极端组织不但关系到阿富汗局势,也将影响塔利班政府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美国尽管撤出阿富汗,但是对阿富汗事务仍保持影响力,特别是对阿境内恐怖组织十分关注。在美国与塔利班签署的和平协议中,“塔利班承诺将与活跃在阿富汗境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切割,并保证让阿富汗不再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攻击美国及其盟国的‘庇护所’”。(21)“Agreement for Bringing Peace to Afghanistan between the Islamic Emirate of Afghanistan which is not Recogn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s a State and is Known as the Talib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igned)”,29 February 2020,https:∥magazine.mohaddis.com/home/articledetail/106835, 25 March 2022.“俄罗斯担心‘伊斯兰国’将在阿富汗,特别是在阿富汗北部沿着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边界设立基地。伊朗也担心叙利亚逊尼派‘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涌入不仅会与阿富汗的什叶派穆斯林产生矛盾,也会给伊朗自身带来安全威胁,增加其东部边界的不安全感。”(22)朱永彪、魏丽珺:“周边大国博弈背景下的巴阿局势”,《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第55页。乌兹别克斯坦对“乌伊运”动向十分关注,中国担心在阿富汗境内活跃的“东伊运”组织会以阿富汗为基地向中国新疆渗透,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塔利班曾公开声明不允许任何恐怖组织在阿富汗从事威胁他国的活动。“重申‘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东伊运’‘巴基斯坦塔利班’‘俾路支解放军’‘真主军’,以及其他恐怖组织不能在阿富汗领土上立足。”(23)钱中兵:“阿富汗邻国外长会联合声明”, 2021年9月10日,http:∥m.news.cn/2021-09/10/c_1127846097.htm,2021年10月17日。这些表态安抚了周边国家的情绪,但并不能打消它们的疑虑。可以肯定的是,塔利班当局无法将这些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特别是那些与其关系密切、曾经共同反抗美国的盟友驱逐出境。塔利班当局会约束它所能影响的极端组织,如“乌伊运”,该组织的很多人员、资金、装备都来自塔利班。对于那些有很强独立性的组织,如被美国和联合国宣布为恐怖组织的“哈卡尼网络”及其领导人哈卡尼,塔利班如何处理有待观察。塔利班上台执政以来,“哈卡尼网络”已经制造了数十起爆炸案件,严重威胁阿国内安全。这些爆炸事件所针对的既有政府目标,如警察局等,也有民用目标,如清真寺、医院等。他们的目的是想将阿富汗局势搞乱,最终达到掌控阿富汗的政治目的,这是他们与塔利班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2020年‘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共发动60次袭击,但是今年(2021)截至11月中旬已达334次。此外,阿富汗境内的绑架、抢劫、谋杀等犯罪事件自8月中旬以来也呈现激增的状态。”(24)朱永彪、刘彦彤:“美国是阿富汗系统性危机的根源”, 2021年11月29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5mBTHCzbM3,2021年12月10日。塔利班加大了对该组织的打击力度,迫使其离开阿富汗。截止到2021年11月,塔利班“捣毁了‘伊斯兰国’在喀布尔省、楠格哈尔省和赫拉特省等地的21处据点,逮捕了该组织600名武装分子。”(25)史先涛:“阿富汗塔利班宣布已逮捕6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2021年11月11日,http:∥www.news.cn/mrdx/2021-11/11/c_1310304455.htm,2021年11月20日。这些恐怖组织既有来自中东的恐怖分子,也混杂了部分前政府军警人员,还吸收了部分阿富汗民众,这加大了打击难度。“小部分阿富汗前政府情报人员及军人倒戈投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以求生存和抵抗塔利班。这些人员大多在美国受过训练,近期一直陆续加入在阿富汗北部活动的极端组织。”(26)王金志:“阿富汗前政府军成员加入IS以对抗塔利班,多数为美国训练”, 2021年11月2日,http:∥www.news.cn/mil/2021-11/02/c_1211429127.htm,2021年11月10日。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组织或者恐怖分子可能与普什图地方部落长老建立了一些密切联系,打击他们势必会激化塔利班与地方部族的矛盾。长期在阿富汗活动的“东伊运”组织和塔利班当局共同抵抗美国,属于同一战壕的战友。塔利班基于多重考量,会加强对“东伊运”组织的约束。但是相比“乌伊运”,“东伊运”独立性更强,意识形态方面更加极端,不会轻易接受塔利班的劝告。无论塔利班采取安抚策略还是打击策略,客观上都会使本地区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外溢化。因此塔利班当局既要承受相关国家的压力,也要面对如何与这些组织维系彼此关系的难题。
重新掌权的塔利班实际上面临的最大挑战是经济问题。塔利班当局需要解决好财政问题,维持中央政府的正常运转。阿富汗一直没有建立良好的经济体系,国际社会的持续援助为政府正常运转提供了大部分财政收入,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过去20年,阿富汗经济主要依赖外国援助,这种援助不仅对经济发展无益,还滋生腐败。阿富汗不能一直依赖援助,阿经济建设应建立在国内发展和自给自足的基础上。”(27)徐海知:“阿富汗代总理呼吁国际社会承认塔利班政权”, 2022年1月22日,http:∥www.news.cn/world/2022-01/20/c_1128280191.htm,2022年3月3日。“阿富汗社会发展还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汇率不稳、工业基础薄弱、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部门腐败成风、办事效率低下等制约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28)张吉军、张婷:“政治伊斯兰与阿富汗社会发展之逻辑关系辨析”,《南亚研究》,2018年第4期,第109页。在卡尔扎伊、加尼政府时期,阿富汗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援助,世界银行的贷款援助也具有重要地位。“自2002财政年度以来,美国国会已为阿富汗拨款超过1260亿美元,其中约63%用于安全,28%用于发展(其余用于民事行动,主要是预算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29)“Afghanistan: Background and U.S. Policy In Brief”,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122/13, 21 September 2021.世界银行累计为阿富汗提供了超过40亿美元的援助,未来4年每年仍然需要60~80亿美元的资金维持政府运转和发展经济,这对塔利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2021年8月,美联储冻结了阿富汗央行美元资产,“2022年2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就所冻结的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资产签署行政令,计划将其中一半资产(总额70亿美元)用于赔偿‘9·11’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30)刘阳:“美公布冻结阿富汗资产使用计划,塔利班谴责”, 2022年2月12日,http:∥www.news.cn/world/2021-11/17/c_1128074221.htm,2022年3月3日。此举遭到阿富汗临时政府和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塔利班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加大对公共安全、民生领域的投入,资金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除此之外,由于地方实力派控制着地方财政税收,塔利班中央政府与地方实力派将围绕财税、安全、司法审判、民生等问题展开长期博弈。特别是财税方面,在重重困境之下,各类非法贸易,如毒品种植、走私,可能会成为一些政治势力获取资金的重要途径。
毒品贸易在阿富汗始终没有禁绝,很多部落将毒品种植作为发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塔利班也曾从中受益。塔利班曾经为了获得国际社会承认,曾采取过很多禁毒措施,但是都没有坚持太久。根据联合国估算,仅在2018—2019年,塔利班就通过毒品贸易赚取了4亿多美元。这相当于塔利班总收入的60%。毒品贸易在奥马尔时期一直是塔利班当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阿富汗战争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毒品贸易,使阿富汗毒品销量一度下降。随着塔利班卷土重来,毒品经济又死灰复燃。这些毒品贸易在塔利班的保护下,通过周边国家,如乌兹别克、塔吉克斯坦,转运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洲国家,为塔利班赚取了大量的活动经费,构成了塔利班赖以存在的财政基础。 “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估计,毒品经济约占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的19%至32%。”(31)[美]塔米姆·安萨利著,钟鹰翔译:《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334页。鸦片生产提供了约40万个工作岗位,已经成为阿富汗国内重要的产业支柱。“阿富汗的罂粟种植和毒品生产不减反增,种植面积超过13.1万公顷,鸦片种植则接近6000吨,占全球产量的90%以上,每年为毒贩、军阀和塔利班等组织带来的收入超过30亿美元。”(32)张吉军:“阿富汗战后重建面临的困境及出路——以政治机会理论为视阈的分析”,《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第49页。毒品贸易难以在短时间内根治,这将极大影响塔利班的国际信誉和政府权威。如何处理毒品贸易问题不但影响阿富汗的财政基础,也将影响其与周边国家关系。新一届塔利班政府如果不能赢得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和支持,将难以克服这些困难,最终导致其国内局势恶化。据阿富汗研究中心经济问题专家苏菲扎达提供的一份列表显示,塔利班除了毒品贸易,其他收入还包括采矿、税收、走私以及捐助。这些收入相对毒品收入不算很多,但是随着塔利班政府整合国内秩序,恢复社会生产,这些收入的重要性必然会大幅提高。
塔利班需要处理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获得国际承认,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制裁和封锁政策限制阿富汗临时政府,不会轻易和阿富汗建立外交关系。面对西方国家的孤立,如果不能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阿富汗仍然不能真正走出战乱泥潭,恢复和平秩序。西方国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商品进出口、金融服务等方式限制阿富汗临时政府,为塔利班执政制造重重阻力和困难。重新掌权的塔利班不再自我孤立,而是选择和周边国家尽快恢复正常、友好的双边关系。塔利班政府建立后多次发表外交声明,表示愿与世界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积极争取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美国撤军使本地区大国博弈局势有所缓和,但是非传统安全压力将会上升。周边国家,如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国,都在阿富汗有很多利益,是阿富汗事务必然的参与者。塔利班既要协调各国利益,使这些国家不过度干预阿富汗事务,为阿富汗和平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也要维护自身利益,阻止其他国家插手阿富汗内政,避免制造危机和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塔利班政府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将十分考验他们的执政能力。
塔利班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国家权威建构。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直是塔利班近代以来的政治目标。阿富汗历届政府都为此努力,但是受到国内外因素干扰迟迟未能实现。阿富汗历届政府从未实现对基层地区的有效控制,而是依靠部落实现间接管理。现代政治管理模式与传统部落自治形成某种制衡。塔利班第一次掌权后陷入内部冲突泥潭,没有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也无力推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它沿袭了普什图民族传统的部族权力结构,对地方部族的自治地位和自治权力充分尊重,实际上是承认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卡尔扎伊政府与加尼政府在国家治理方面也没有动摇阿富汗社会的基础。在广大城市、农村地区,中低层民众仍然是部族成员而非阿富汗国民。“一个普什图人会这样描述自己:‘我首先是普什图人,其次是一个穆斯林,最后是阿富汗人。’”(33)缪敏等编:《阿富汗概论》,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年,第83页。塔利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阿富汗部落力量。或者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实际上是由于其没有真正将阿富汗政府的根基在乡村建立并巩固起来,给塔利班再次崛起留下了机会。美国对阿富汗的治理实际上停留在了阿富汗城市社会,无法深入广大乡村社会。持续数十年的战乱不断打破旧的势力平衡局面,不同部落间的力量此消彼长,这激化了各部族争夺生存资源的矛盾斗争。在中央政府长期缺位的背景下,矛盾冲突无法由最高国家权威调解和处置,普通阿富汗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无法建立。阿富汗历届政府困于争权夺利的内斗和抵抗外敌的侵略,无暇顾及推进国家建构和治理。部落权威实际上是阿富汗民众心中的最高权威,代替中央政府承担国家职能。现代公民意识缺失,民众部族身份不断被强化,政府公信力没有存在的现实依据和基础。塔利班政府如果不能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也将面临和历届政府一样的命运:建立一个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代表阿富汗国家,在地方上则失去控制权,将权力让渡给地方实力派,形成新的割据局面,新政府不过是在中央政府层面重新进行了一次权力洗牌。从塔利班的对外声明看,它有意推动国家建设,包括呼吁民族和解,强化民族主义精神和国家意识等。但这显然不是通过声明就能实现的目标。阿富汗国家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塔利班再次执掌阿富汗最高权力对塔利班当局、阿富汗人民和国际社会都是一个难以预知的挑战。阿富汗近代以来饱经战乱,人民始终无法过上和平的生活。尽管被称为“帝国坟场”,实际上阿富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阿富汗人民的血泪和牺牲虽然换来了某种意义上的独立,但是始终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塔利班如果能够带领阿富汗人民真正掌握自身命运,走上和平发展道路,对阿富汗人民、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是最好的结果。只是不知道塔利班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是将阿富汗带上和平发展的康庄大道,还是在内外矛盾的困境中让阿富汗再次陷入混乱的泥潭?从目前的情形看,塔利班执政的前景并不乐观,它面对的挑战既有积重难返的老问题,也有新世纪的新挑战。塔利班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治理好国家,还需要时间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