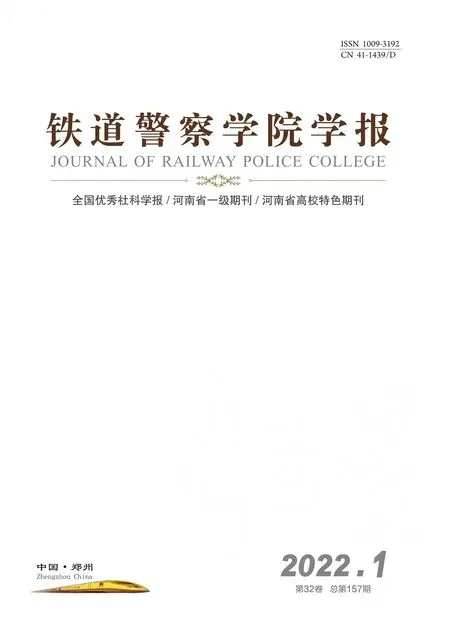破窗理论研究综述
徐晓宇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38)
2020年疫情期间,引起全美轰动和骚乱的弗洛伊德事件①美国当地时间2020年5月25日,明尼苏达州警察因怀疑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使用假钞而将其强行按倒在地,跪压致死。美国警察暴力执法的行为不仅引发了全美抗议示威活动,而且蔓延到全球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两千多个城镇。参见:弗洛伊德之死如何“点燃”美国,https://www.chinanews.com.cn/gj/shipin/2020/07-28/news863597.shtml.再次将公众的愤怒导向警察暴力执法行为,破窗理论被指责为因赋予警察“视整个社区为无序的、危险的、可疑的以至于是有罪的信念”[1]3、应负起理论上的责任而再次进入公众视野。破窗理论作为指导警察策略和警务改革的理论依据,最早产生于20 世纪80 年代的美国,最初运用于应对美国城市化进程中居高不下的犯罪率和公民退出公共生活领域所导致的城市衰败。随着纽约市警察局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开展的一系列恢复城市秩序、提高生活质量等警务活动取得的卓然成效,破窗理论迅速为大西洋两岸的警察所青睐,甚至成为遍布全球的警察策略指导理论。我国在警察执法领域引入破窗理论则始于21 世纪初,20 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实施“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在该政策推动下,我国学者放眼看世界并移植了该法律理论。随着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我国“全能型政府”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警察任务也随之产生巨大流变,破窗理论中长期为我国学者所忽略的“警察权威支持下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的价值进一步显现。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破窗理论,为新时代警察执法中服务理念和服务职能的转变提供切实可行的策略。
一、破窗理论的历史研究
(一)破窗理论的国外发展脉络
破窗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法国古典自由派经济学家、政治家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Claude Frédéric Bastiat)。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巴斯夏就在其经济学著作《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That Which Is Seen and That Which Is Not Seen)一书中提出了作为经济学谬误的破窗理论,即谬误的产生是由于决策者只看到眼前或短期可见的后果[2]。后来,美国经济学家亨利·黑兹利特(Henry Hazlitt)对破窗理论进行了拓展,强调了行为或政策对所有群体造成的影响[3],这也为破窗理论走向社群主义奠定了基础。
将环境因素与犯罪理论联系起来的研究虽然始自孟德斯鸠,但将其切实付诸实践则是近代两位美国建筑师完成的。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Jacobs Jane)关注失序、恐惧与生活质量之间的联系,并于1961 年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提出了城市设计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与日俱增的领地意识与自然监督的重要性、“小改变”和“另一种街区安全观”①参见:Prashan Ranasinghe. Jane Jacobs’framing of public disorder and its relation to the’broken windows’theory[J].Theoretical Criminology,2012(16):63-65.originally published online.1,July,2011。作者以批判“时间中心主义”(chronocentrism)的立场,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简·雅各布斯1961年的经典之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构建了公共秩序混乱问题的理性研究,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破窗理论的先驱。另外,凯林也多次提及简·雅各布斯及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参见: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M].陈智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2、18、109、137、245。;美国犯罪学家和行为建筑学家奥斯卡·纽曼(Oscar Newman)1972 年在其著作《防卫空间》(Defensible Space)中通过进一步验证空间管理及设计与公租房之地区犯罪问题之间的必然联系而提出了“防御空间理论”②参见:刘广三,李艳霞.犯罪预防的新思路:利用环境设计预防犯罪——奥斯卡·纽曼的“防卫空间理论”述评[J].刑法论丛,2008(2):432-455。另外,乔治·凯林在研究纽约市收复地铁的行动方案中认为“车站经理计划”反映了奥斯卡·纽曼的想法,参见:乔治·凯林,凯瑟琳·科尔斯.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M].陈智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38。——这些观点为破窗理论提供了关注社会秩序与生活质量问题的视角。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Philip Zimbardo 则通过一项人们对放置于不同社区、不同状况的汽车所进行的不同行为的对照实验,检测并支持了破窗理论③Philip Zimbardo 教授把一辆没有牌照和引擎盖的汽车停在Bronx 区的一条街上,把另一辆对比车辆停在加利福尼亚Palo Alto 的一条街上。停在Bronx 区的车辆在被遗弃后不到十分钟就遭到了破坏者的袭击。首先接近车辆的是一个由父亲、母亲和年幼的儿子组成的家庭,他们拆走了散热器和电池。而24 小时之内,事实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然后随机的破坏也开始了——窗户被打碎,零件被拿走,内饰被撕毁。孩子们开始把这辆车当成游戏场所。而大多数成年“破坏者”则是衣着得体、外表整洁的白人。而停在Palo Alto 区的车则超过一周也无人碰触。然后Zimbardo 教授抡起大锤开始砸车。不久,过路者也开始加入。几个小时之后,车辆被掀翻了,而且完全毁坏了。这次,破坏者仍是一些外表看起来相当可敬的白人。参见:James Q. Wilson and George L. Kelling.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J].Atlantic Monthly,1982,Vol.249.No3:33。。
威尔逊的老师爱德华·班菲尔德在其1970年发表的著作《尘世之城》(The Unhevavenly City)中提出的“贫困文化”与犯罪性行为之间的关系④班菲尔德认为,穷人因为陷入一种贫困文化中而几乎不可能得到政府的援助。尽管他几乎比任何人都更有闲暇时间,但下层人群的冷漠(也可以说是漠不关心),使得他几乎不会对自己生活的处所做最简单的修缮。他不会因为尘污或破损而烦恼,也不会关心公共设施的短缺,如学校、公园、医院和图书馆。事实上,当有这些设施存在时,他们更有可能无心地甚至是故意地破坏它们。参见:Edward Banfield.The Unhevavenly City:The Nature and the Future of Our Urban Crisis[M]. 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1970。也对破窗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赫尔曼·戈尔茨坦也早在1977 年就提出警察应该对打击实际犯罪与控制对犯罪的恐惧感采取不同的措施,并强调后者更为重要[4]。
当然真正让破窗理论声名鹊起的还是威尔逊和凯林,二人在观察纽瓦克市步行巡逻经验的基础上于1982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上发表了文章《破窗理论:警察和邻里安全》(Broken Windows:The Police and Neighborhood Safety),他们“用一扇破窗图像,解释若无人确实地维护,邻里社区可能堕入失序,甚至犯罪的境地”[5]。该文章一经发表便引发公共政策、刑事司法、警务和宪法(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法律保护)等领域的疑问,挑战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警务的发展,也重新打开了警方和其他刑事司法单位不愿意承认的潘多拉魔盒[6]3,有的媒体甚至称其为“警务活动的圣经”“社区警务的蓝本”[7]。破窗理论指导下的一系列政策、改革和行动在降低美国犯罪率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几乎引领了第四次警务革命的发展方向,世界各地竞相仿效。
理论界的研究也更加丰富。有的从实证主义出发,基于经验的方法对该理论应用于实践所取得的效果进行评价,大多数则通过一系列实验对该理论的关键性命题进行验证,主要集中在:控制破窗警务,各个城市社区层面的无序程度、公民对无序的感知、无序与自治、无序和严重犯罪、无序和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以及破窗理论对犯罪预防的影响等。
(二)破窗理论的国内发展脉络
破窗理论在我国最早进入公众视野始自经济学领域,1998年刊登在《中国企业家》上的一组经济专家分析我国灾后重建问题的《从经济角度看水灾》一文中,于杰以批判的角度提出破窗理论在灾后重建中是不可取的,否则会导致经济持续萎缩的后果[8]。但实际上,早在1995 年,鲁旭东就关注到了失序与犯罪之间的联系,他在文章《法律与无序——中国南方的犯罪问题》中提到,社会控制不力、政府人员腐败、道德危机、私欲膨胀是南方近几年犯罪率持续上升的原因[9]。
第一篇与警察执法相关的文章则是2000 年陈小波的《破窗理论与社区治安》,文章简要介绍了破窗理论的由来及主要观点,破窗理论与社区警务之间的联系以及社区警务在美国的实践,文章内容基本上是一个粗线条的框架性介绍[10]。
第一篇与犯罪学相关的文章则是2005 年庄劲和廖万里发表的《犯罪的情境预防原理》,但破窗理论只是作为其犯罪情境预防的基本理论之一——环境犯罪学理论——的一部分而提出的,基本上也是对其内容的一个简单介绍[11]。同年,夏菲在《论美国警政的发展与特点》中,将破窗理论作为以预防犯罪为目标的警政理论进行介绍,指出破窗理论是以犯罪预防为中心任务的社区警务的主要理论依据[12]。同年的另一篇文章《论美国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但同时指出了破窗理论主张扩大警察对社区的非正式控制,也介绍了作为社区警务组成部分的“问题解决警务模式”[13],这其实与威尔逊和凯林最初的主张——警察一切任务的目标就是解决问题——相一致,只不过夏菲未能阐述二者的关系。也是在同一年,王世洲和刘淑珺在《零容忍政策探析》中指出,破窗理论是“零容忍”政策的理论根据和强有力支撑,强调警务工作应当变被动打击为积极预防[14]。
可以说,2005年是我国破窗理论应用于犯罪预防的理论元年,至此破窗理论开始进入我国关注犯罪及相关问题的学者的视野,成为警察打击和预防犯罪政策的理论支撑之一。在关于示威游行的接处警机制、反腐败“零度容忍”预防机制、环境犯罪学与社区警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政策、监管安全、“零容忍”执法、暴力袭警、流动人口犯罪、反恐警务、社区安全治理与社区建设、社区警务、谣言传播、聚众哄抢犯罪防控、犯罪规制模式重构、交通管理、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农村恶势力犯罪防控等领域,都开始运用破窗理论加以论证①参见:董树平.纽约示威游行处警机制分析[J].公安研究,2006(02):90-92;杨爱华,李小红.破窗理论与反腐败“零度容忍”预惩机制[J].中国行政管理,2006(04):102-106;丁湘.环境犯罪学与社区警务[J].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1):59-65;黄豹,廖明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S1):109-111;沈培菊.浅析袭警事件控制中破窗理论的运用[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1):22-26;李本森.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0(05):154-164;朱兴祥,张峰.论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犯罪控制[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1(06):73-76;刘晓农,叶萍.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犯罪控制[J].河南社会科学,2013(04):54-57+107;马雯娜.破窗理论对聚众哄抢犯罪防控的启示[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12):155-157;姜涛.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01):85-100+174;蔡一军.破窗理论视角下中国社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启示[C].中国犯罪学学会预防犯罪专业委员会、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犯罪学论坛(第四卷·上册)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10;陈小彪,李瑞华.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 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J].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20,34(01):24-42;简筱昊.破窗理论视角下农村黑恶势力犯罪防控研究[J].运城学院学报,2020,38(01):36-41;等等。。自此之后,破窗理论开始进入犯罪学专家的视野,犯罪预防、犯罪治理、犯罪的“零容忍”等相关内容的研究占据了破窗理论的半壁江山。
当然,破窗理论在我国除了应用于与预防和打击犯罪以及警察执法相关领域以外,也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大众传媒等。
(三)破窗理论的国内外发展脉络评价
总体来说,国内外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已颇具规模,尤其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日本、韩国,破窗理论得到了长足而广泛的应用①参见:Dennis N. & MallonR.Confident policing in Hartlepool. In N. Dennis(Ed.),Zero Tolerance:Policing a free society[R]. London: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1998:62-87,105-125;Swanson,K.(2013).Zero tolerance in Latin America:Punitive paradox in urban policy mobilities.[J]. Urban Geography,2013,34:972-988;[日]上田宽.犯罪学[M].戴波,李世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257;Jhon Tag Chol & Jisun Park.Multilevel Analysis of Disorder Policing and Fear of Crime in SouthKorea[J]. Asi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2019,14:113-127。。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学说,破窗理论的内容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统一的、具有规范性意义的研究框架。因此,对破窗理论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十分必要,这不但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破窗理论的理论建构,也有助于其实践经验的发展和丰富,更有助于我国学者在借鉴其经验时进行批判性思考研究。
二、破窗理论研究现状
(一)破窗理论的国外研究现状
1.对破窗理论的介绍和警务运用
1982 年威尔逊和凯林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破窗理论:警察和邻里安全》可以说是最早将破窗理论与警察执法联系起来的研究。威尔逊和凯林通过对新泽西州的“安全整洁社区项目”的观察,以及该项目实施5年后华盛顿特区警察基金会基于一项主要在纽瓦克(Newark)进行的谨慎控制的实验数据的分析和评估,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家和警察的视角出发,得出:如果一栋建筑物的窗户被打破了而且不予修理,不久剩下的窗户都会被打破,这种现象不管在良好的社区还是破败的社区都一样会发生。他们认为可能的原因是一扇经久不修的破窗会给人一种无人关心的暗示,即打破更多的窗户也不会付出什么代价[5]。当代美国“零容忍”执法策略、基于环境设计的犯罪预防、犯罪的情境预防、社区警务、问题导向警务、地点导向警务、热点警务、预测警务等警务模式几乎都受到了该理论的影响。
然而,威尔逊和凯林并没有止步于表象和原因的探讨,他们进一步观察到,为了应对这种恐惧,人们会相互回避,削弱控制,而非选择报警,因为在当时的政策规定、社会学家的期望和人们的认知中,警察变成了打击犯罪的战士,而维持秩序的责任对他们来说即使没有被忘记也已经变得很弱了[5]。威尔逊和凯林进而提出,警察在维持秩序方面的作用的实质是加强社区自身的非正式控制机制,他们提出破窗理论的初衷也是用于证成警察如何加强自然社区的非正式控制机制以最小化公众场所的恐惧[5]。可以看出,破窗理论的根本前提是认为无序和不文明行为的日益增多加剧了居民的恐惧,导致他们陆续搬离其住所,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也因此减弱,同时鼓励了那些破窗者。基于此,警察可以通过处理一些轻微违法行为的举措来预防和减少严重犯罪的发生以维护社会秩序。该理论的重点是警察如何通过处理无序行为来恢复社会秩序,而这一点却是长期以来被误读——尤其是被我国学者所忽略的关键内容所在。
1997年,凯林和凯瑟琳·科尔斯出版了《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继续关注美国公众领域失序行为的控制问题,主要探讨以何种方式与何种程度保护公众领域才能在牺牲最少个人自由的前提下管理公共领域的秩序。他们指出,要想恢复和维护秩序,就要重新定义警察的角色,即警察作为社区问题解决者,而不仅仅是打击犯罪的战士[6]248。由此,再次表达了破窗理论对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的青睐之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公民参与机制等策略。
而凯林在1999 年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一项研究报告《破窗理论与警察自由裁量权》(“Broken Windows”and Police Discretion)则对警察通过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解决问题、调解纠纷、维持秩序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警察自由裁量权”表示了持续的关注。凯林认为,在破窗理论的指导下当前的警务工作在社区内正处于转型期。警方更频繁地参与到创建和培育与社区居民、企业、宗教组织、学校和社区协会的伙伴关系中来。警察在司法程序中的作用要求警察部门更加致力于制定详细的政策、具体的指导方针、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指南以规范不可避免的自由裁量权的使用,并且和公众一起设定标准,支持公众参与自己的生活管理[15]。可见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以及应用该手段完成维持秩序功能的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问题及其应对一直是破窗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
此后,专门研究破窗理论的专著虽然不多,但是但凡涉及犯罪预防、警察执法及警务模式的著作,都会诉诸破窗理论。例如,英国的戈登·休斯在其1998年出版的《解读犯罪预防:社会控制、风险与后现代》中介绍了破窗理论,并指出英国内政大臣杰克·斯特劳于1997年提出的关注和治理社区内和街头的粗野、不文明行为及失序现象的“零度容忍”政策就是对破窗理论的发展演变,其认为该政策虽然有些锋芒毕露,但对英国当时的一系列社会状况的改善提供了帮助,如重新建立邻里之间的相互尊重,培养公民的观念,克服反映后现代社会城市环境基本特征的恐惧文化综合征[16]。罗伯特·兰沃西和劳伦斯·特拉维斯合著的2003 年第三次出版的《什么是警察——美国的经验》中也介绍了破窗理论,认为它论述了公共秩序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关系,并赞同凯林和科尔斯在《破窗效应:失序世界的关键影响力》中的观点,认为由物体损坏和人际的不礼貌所表现出来的混乱创造了一种滋长犯罪的气候,警察维持秩序是一种最终控制实际犯罪水平的策略,除此之外,维持秩序也是警察机构自身的一个目标[17]。肯尼斯·J.皮克和罗纳德·W.格伦索在其2010年第五版《社区警务战略与实践》中提出,破窗理论是把奥斯卡·纽曼对建筑物设计的焦点转移到整个社区,暗示了一个属于看护的区域的自然迹象和社会问题迹象,而这些通常都是吸引罪犯到这个区域犯罪的一种不文明标志[18]。
可以看出,这些专著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大都是对该理论的介绍与直接运用,主要是应用研究,缺乏对该理论自身的审查与反思。2014 年欣克尔(Joshua C.Hinkle)发表的“Broken Windows Thesis”[19]以及苏泽(Sousa W.)和凯林的合著“Order Maintenance Policing”[20]就是对破窗创理论的概述及其在警察实践中应用的研究。
2.对破窗理论内容的检验与扩展
更多学术研究则热衷于检验和扩展破窗理论最初的原始论点,例如无序、对犯罪的恐惧、社会控制的失效和犯罪四个要素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并呈递进趋势,无序与犯罪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当无序的状态达到一定规模或无序的活动非常频繁时,可以引爆犯罪行为。美国学者斯科甘(Skogan W. G.)1990 年就在“Disorder and Decline:Crime and the Spiral of Decay in American Neighborhoods”中研究了失序和城市衰退之间的关系[21]。沃勒尔(John L. Worrall)则基于观察实验的一组数据于2006 年在文章“Does targeting minor offenses reduce serious crime?Aprovisional,affirmative answer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ounty-level data”中分析回答了治理微小失序行为与减少犯罪率之间有无关系[22]。
对地点、环境因素的热衷研究则来源于破窗理论认为地区环境对人可以产生强烈的信号暗示,对败坏居民生活环境的失序行为应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及时制止和纠正以防止信号扩散和传播,针对濒临衰败的“临界点”地区应加强社会控制,“提高生活质量”及其他维持秩序的警务活动可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感,有利于群体守法意识的提升。沃勒尔 2006 年在“The discriminant validity of perceptual in civility measures”中研究了人们是怎么感知文明秩序的失效的[23]。欣克尔和杨(Sue-Ming Yang)则于 2014 年在“A new look into broken windows:What shapes individuals’perceptions of social disorder”一文中研究了个体关于“社会失序”的概念是如何形成的[24]。查普尔(Allison T.Chappell)、蒙克·特纳(Elizabeth Monk-Turner)和佩恩(B.Payne)则在发表于 2011 年的“Broken windows or window breakers: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nd social disorder on quality of life”中研究了身体紊乱和社会失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25]。拉纳辛哈(Prashan Ranasinghe)在“Jane Jacobs’framing of public disorder and its relationto the‘broken windows’theory”中讨论了Jane Jacobs的街区安全观与破窗理论的关系[26]。泰勒(Ralph B. Taylor)运用依据1981年到1994年收集的数据所开展的小组研究设计,调查了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90多个街区上的犯罪和犯罪的恐惧感,找到了犯罪在地点上具有长期高度稳定性的证据[27]。大卫·威斯勃德(David Weisburd)和他的团队分析了1989年至2002年这14年间西雅图市街段上的案件情况,发现50%的犯罪案件集中发生在4.5%的街段上[28]。劳伦斯·希尔曼(Lawrence Sherman)的团队分析其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研究数据并与费城研究中的违法聚集行为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通过犯罪发生地的地址来预测犯罪的可靠性要比通过罪犯的身份来预测犯罪高出六倍[29]。威斯勃德和希尔曼关于犯罪在地点的聚集性研究支持了将警察热点巡逻勤务作为一种犯罪预防的有效战略。
威斯勃德、特乐普通过长期观察非法倾倒事件和犯罪轨迹特征之间的关系及不同群组之间轨迹特征的对比,发现社会失序行为的变化和街段层面的犯罪变化以及社区集体效能水平之间存在直接而强烈的关系[30]。此类研究结果将警察执法的目标从犯罪热点拉回了对这个地点社会生活状况的关注,强调了运用社区警务和其他警务策略来提升该地点上居民非正式社会控制能力的重要性。
凯林和苏泽用分层线性模型来评估破窗警务对纽约市凶杀案影响的假设,他们综合纽约市警察局各个管辖区域横向和纵向的数据,基于合并的、横向的时间序列设计,将警察服务区作为分析单元,将单元区域层级上的四种暴力侵害案件(谋杀、强奸、抢劫及严重伤害案件)作为因变量,将警察服务区一级的轻罪拘捕及该区域男性青年、失业人数、涉毒人员出院登记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发现轻罪逮捕与暴力犯罪的综合测量显著相关,即轻罪逮捕平均数高的区域,暴力犯罪下降更多[31]。凯林和苏泽的研究结果支持了破窗警务与区域内的暴力犯罪密切联系,而其他观点则没有体现出来。
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克里斯蒂安·克雷斯(Wouter Steenbeek)和沃特·斯坦贝克(Christian Kreis)教授则认为对破窗理论的实证检验实际上应该检查威尔逊与凯林所主张的“公共秩序正在恶化但并非无法恢复的”这些不温不火的地区,而不是热点地区。为了检验威尔逊和凯林针对警力资源配置提出的“应当在最破败的地区引入秩序维持警务的政策策略”,克雷斯和斯坦贝克在2015 年对荷兰阿姆斯特丹市近2000 个地点进行系统的社会观察并获得数据,用一种系统的方法来识别无序或混乱程度相似的区域(从平静到倾斜、到犯罪猖獗)而形成了报告“Where Broken Windows Should Be Fixed:Toward Identification of Areas at the Tipping Point”[32],其结论是一个行政区域可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程度的无序,热点分析不能识别出中度无序的区域,这阻碍了对破窗理论基本实验的测试,混淆了破窗理论和秩序维持警务研究的结果。克雷斯和斯坦贝克的研究结果可以部分解释维持秩序的有效性的证据为何仍然没有定论。
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警察权威性参与下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尤其是公民参与的作用。萨姆·休斯敦州立大学的任凌教授、赵继红(Solomon)教授和美国东北大学的赫妮(Phil)教授对得克萨斯州霍顿约1100 名居民进行了电话调查,研究了警方记录的传统调查数据和他们利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工具对每个有社会妨碍犯罪/混乱事件记录的居住者的住宅调查信息,使用结构方程模式检验破窗理论的几个核心命题,即威尔逊与凯林提出的一系列具体连锁效应:不受关注的持续性混乱,增加了对犯罪的恐惧,从而导致社区社会控制的弱化,并最终对公民参与犯罪预防活动的决策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序事件对无序感有显著影响,无序感则会增加个人的不安全感,进而降低集体效能感,而这与公民参与犯罪预防的积极性与集体效能显著相关。这些发现适用于各种由集中劣势指数分类的邻里环境[33]。任凌等人的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破窗理论的提出,即通过公众参与等方式将因恐惧而退出社区生活的居民重新纳入秩序恢复活动中可以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集体效能,挽回对政府的信心,恢复社会秩序。
3.破窗理论的反对声音
当然,自破窗理论提出以来,自由主义者对它的攻击和批判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游行示威、诉诸法院等。
美国费耶特维尔州立大学恩戈奇·C.卡马鲁教授(Ngozi C. Kamalu)和马里兰大学埃曼努埃尔·C.奥尼奥兹利(Emmanuel C. Onyeozili)教授指出,破窗理论战略实施以来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它将有限的社会资源转用于惩罚和监禁,给刑事司法系统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从而破坏了传统的社区警务所重视的警务行为的有效性;少数族裔受到不公平待遇,尤其是在“拦截、拍身、搜查和逮捕”中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性执法,削弱了公众的信任,损害了公民正当程序权利,使执法在弱势群体眼中失去了合法性,从而对刑事司法系统产生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他们甚至认为破窗理论在纽约市的成功被不成比例地夸大了,该市犯罪率的下降并不是破窗战略的结果,而是由于经济的改善、青少年男性人数的下降以及吸食快克可卡因等毒品现象的减少[34]。
最近一位英国社会学教授亚历克斯·S.维塔莱对破窗理论甚至是敌视的,其在2020 年出版的《警治的终结》一书中提到了滥用武力问题,而这只不过是警察过度执法问题的冰山一角,他指出美国超过200 万人在监狱、看守所中,400 万人处于缓刑或假释的状态,很多人被剥夺选举权,大部分人被释放后很难找到工作,与家庭的纽带被摧毁,进而被推向更严重、更具暴力性质的犯罪,这都是破窗式执法的后果。维塔莱指责威尔逊站在种族主义的边缘,将贫穷黑人的劣根性归结于其犯罪行为的重要生物学决定因素。维塔莱认为破窗理论神奇地颠倒了通常所理解的犯罪与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主张贫困与社会解组是犯罪的后果,而非原因,而“底层阶级”日渐增多的无序行为威胁着城市的基本结构[1]248。维塔莱认为破窗式执法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非常保守的尝试,试图将生活条件衰退的责任转嫁给穷人,并指出所有社会弊病的解决方案在于不断增加侵犯性的、攻击性的和限制性的执法行为,这就涉及更多的逮捕、更多的侵扰,并最终表现为更多的暴力。当不平等持续增长,就会导致更多的无家可归者和更严重的公共无序状态。只要人们继续赞同以警力管理无序行为,我们就会看到警察权力和权威的边界持续扩张,而这将以人权和公民权为代价。维塔莱给出的方案是,需要更新培训制度、强化问责机制,并且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对警治的指导和监督,需要摆脱战士心态和军事化策略,必须改变警察文化,不再执迷于使用威胁和暴力的手段来控制穷人和社会边缘人群。但维塔莱又指出,只要警察的基本使命保持不变,所有这些改革都不可能实现,因此警治永远不会是一项能为社区赋权的公正且有效的工具,更不会是促进种族正义的工具。任何真正的警治改革议程都必须以被赋权的社区取代警察来解决他们自身的问题。维塔莱的观点显然是激进的、极端的,部分原因也在于他对威尔逊和凯林提出的破窗理论的误解——只看到破窗理论强调对微小失序行为的治理,却没有看到他们更青睐在警察权威的参与下用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解决问题,没有看到破窗理论对警察服务职能的强调和重视——颇有些自说自话的“稻草人谬误”。
(二)破窗理论在国内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应用层面,如社会治安、犯罪预防、环境犯罪学研究、犯罪控制、犯罪规制模式等领域,且往往和其衍生策略“零容忍”政策相结合进行讨论。
1.社会治安方面
北京大学的王世洲教授在《零容忍政策探析》中对“零容忍政策”的含义、历史、理论根据、社会实践和评价进行了探讨,认为该政策有可能成为我国当前社会治安工作新方向。王世洲认为“零容忍政策”在运用破窗理论时存在着片面性,他尤其指出破窗理论虽然承认在必要时启用正规的刑事司法程序是重要的一方面,但同时也强调这种措施只有在与其他多种警察策略相结合时才有效[14]。王世洲强调了警务工作应给与社区其他机构的合作以应有的重视,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对那些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积极打击和严格执法上。可以说,王世洲教授是我国研究破窗理论的学者中看到警察权威参与下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重要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学者之一。黄豹教授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零容忍理论研究》中指出,破窗理论是“零容忍”策略的理论基础,在我国践行“零容忍”策略就标志着要依法行政、严格执法,但这又不同于“刑罚世轻世重”。黄豹认为不必担心破窗理论及“零容忍”策略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因为其不具攻击性与对抗性,而仅是对已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置而已[35]。值得一提的是,社会学博士储卉娟在梳理社会学对警察的研究和影响时已认识到,破窗理论所强调的并不是打击犯罪,而是将治安的源头转移到重建安全社区,认为占据警察日常工作量80%的处理微小失序琐事的行为反而是警察完成其打击犯罪职能的主要方式[36]。
2.犯罪预防方面
杨爱华教授在《破窗理论与反腐败“零度容忍”预惩机制》中介绍了破窗理论及其衍生的“零容忍”政策在社区治安中的成功应用,并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破窗理论与腐败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了以教育预防、监督控制、制度约束和金融监控机制建构的反腐败“零度容忍”预惩机制。杨爱华认为,破窗理论关注了细节、暗示纵容作用、积累破坏作用、公民对警察机关的信心以及对自己生活的安全感之间的关系,而我国香港地区在廉政建设方面关于举报范围的“零度容忍”策略也是杨爱华教授所赞同的[37]。王秀梅教授在《论贿赂犯罪的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惩治对策》中则认为破窗理论与“零容忍”本无必然的关联性。但她同时认为,对于贿赂犯罪如果不采取“零容忍”态度的话就会出现“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王秀梅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从破窗理论中解读出了“社会容忍度”这一概念,认为不文明现象的存在及其惩治力度所暗示的社会可接受度影响着违法犯罪行为的产生、发展甚至质变。王秀梅认为贿赂犯罪挑战的就是社会容忍的极限,如果惩治力度不足,达不到预防和遏制贿赂犯罪频发的目的时便会出现“破窗”效应。王秀梅认为在我国采用“零容忍”对策打击贿赂犯罪可能会因缺乏预防这一环节而折损刑法谦抑性,建议借鉴垒球比赛的“三击法”惩治贿赂犯罪[38]。事实上,王秀梅并没有认识到破窗理论真正的价值在于“预防”而非“打击”,而且其所说的“三击法”在美国1994 年通过的《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条例》中也早有规定,即俗称“三振出局法”的再犯、累犯加重处罚制度。
3.环境犯罪学方面
赵秉志教授研究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的CPTED 理论时,在《CPTED 理论的历史梳理及中外对比》一文中直接将破窗理论视为一项犯罪学理论,认为其与CPTED理论是在逻辑上相互对应的同一犯罪学思想的两个方面。赵秉志教授认为,破窗理论回答的是“犯罪如何发生”的问题,CPTED理论回答的则是“犯罪如何治理”的问题。破窗理论指出了环境对犯罪有重大影响,不良环境对犯罪具有诱导作用;CPTED理论以破窗理论的结论作为展开设计的原因,即可利用良好环境对犯罪的抑制作用通过环境设计来预防犯罪。赵秉志认为,许多以破窗理论为前提的扩展研究都从不同的正面、侧面验证了破窗理论的真实性;而实务界诸如纽约市犯罪预防计划、社区警务等社会治安工程的巨大成功都是建立在破窗理论的基础之上[39]。蒋云飞博士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进行分析,对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和行为进行研究,得出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并建议政府通过“场域控制”,即引进“情境预防”策略及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来加大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以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40]。
4.犯罪控制方面
刘晓农教授在《破窗理论与流动人口犯罪控制》中指出,破窗理论在防控利用特定环境进行犯罪方面具有突出的优势。刘晓农也是基于犯罪学的视野,比较了破窗理论与传统犯罪学的区别,认为破窗理论的重点在于研究犯罪发生的机会或概率,揭示犯罪动机产生的情境、发生犯罪时的周边环境,以及犯罪活动中受害人受保护程度等。刘晓农认为,破窗理论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中的群众路线有着内在一致性特征,他们的契合点主要在于公众参与。刘晓农还介绍了英国的邻里守望活动,认为对我国加强流动人口犯罪防控具有借鉴意义。刘晓农描述了嘉兴市管控流动人口时采取的警民巡逻相结合的尝试方式,认为这是破窗理论的一次有效尝试,尤其主张加强教育以提升居民自身的犯罪防控意识[41]。虽然刘晓农对破窗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犯罪学领域,但其对于公众参与的重视也印证了该理论青睐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的合理之处。
5.犯罪规制模式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破窗理论对刑法的关怀。姜涛教授在《破窗理论与犯罪规制模式的重构》中指出,破窗理论的重大贡献在于其以实证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到并且相信无序、违法和犯罪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姜涛是第一位将破窗理论与刑事立法联系在一起的国内学者,他也看到了破窗理论对警察维持社会秩序时所采取的执法力度的指导意义,进而认为刑事立法模式应该回应这一要求,为警察重点治理微罪的执法行为提供立法上的支持。姜涛认为,破窗理论作用于刑法理念的这种产物对我国以结果取向为犯罪认定模式的刑法提出了挑战,应当借鉴破窗理论的启示将犯罪预防的关口前移,在犯罪结果还未出现前明确积极地预防可能导致重罪的微小失序现象、违法行为及轻罪。姜涛认为,破窗理论与我国现有的一些法律实践的契合性使其具备了在我国刑事立法借鉴过程中的本土化基础,鼓励走出警务活动的狭窄领域去研究破窗理论[42]。可以看出,姜涛也看到了破窗理论在犯罪学领域以外的巨大价值。
6.破窗理论内容本身
伍德志博士从心理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出发,在《论破窗效应及其在犯罪治理中的应用》一文中分析了公民守法的原因往往是由于信息匮乏而对他人的盲目模仿与跟随。伍德志认为破窗理论挑战了传统法律理论关于守法理性的解释模式,破窗效应的产生往往源于公民与政府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而这是政府执法能力有限性及暴力制裁信息价值弱化的必然结果。伍德志建议政府可以利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种信息差异,甚至扩大这种认知鸿沟,通过改良社会环境、设计可防卫空间、整治不文明行为与轻微违法犯罪行为、强调警力的象征性存在等一系列减少“破窗”的印象管理策略来尽可能放大实际非常有限的社会控制能力,形成人人都在遵纪守法的普遍印象,从而增加潜在违法犯罪者的风险认知,最终达到减少违法犯罪的效果[43]。伍德志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从人类的有限理性出发,从认识论的角度对破窗理论进行了解读。
7.对破窗理论发展脉络的梳理
李本森教授在《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一文中虽然对破窗理论进行了历史溯源,但主要是从实证主义角度出发,将环境犯罪学视为破窗理论的前身,所以其进行的工作可以说是对“环境犯罪学”的溯源。李本森也梳理了破窗理论在美国的实践及围绕破窗理论所产生的争议,认为虽然对破窗理论的批评或质疑不断,但破窗理论对美国警务活动的实际影响却不可动摇,而且破窗理论已经在实质上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当今的警务模式,尤其在犯罪控制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44]。李本森认为破窗理论对我国犯罪防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打击和预防街区和居民类犯罪以及犯罪学研究都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另外,李本森提出了“警察与社区应当建立合作关系,强化社区的自我控制力”作为破窗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这也是对警察权威参与下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作为警察执法手段的认识。
(三)破窗理论国内外研究现状评价
破窗理论发展至今,国内外学者对该理论的研究与争论终究是在事实与价值层面展开的。首先,在事实层面,学者热衷于无序、对犯罪的恐惧、社会控制的失效和犯罪四个要素之间关系的检视,对无序与犯罪之间是否存在临界点以及环境因素对人的犯罪动机的诱导也颇有兴趣,对破窗理论及其衍生政策在实践中的运用方式的检视与设计及其运行效果的评估也十分关注。而在价值层面,对破窗理论的评价与判断则始终围绕着安全与自由、秩序与权利这两组充满张力的价值并试图取得平衡。不可否认的是,破窗理论及其支持者往往是偏向前者的,即“安全”与“秩序”始终是破窗理论追求的最高价值。破窗理论无论内容如何发展,最终都是为其“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终极目标服务的,而这对于以自我为中心、坚决捍卫自由与权利的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容忍的,“侵犯人权”“牺牲贫困者、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的利益”成为他们批判破窗理论最常见的理由。总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专业视角出发,对破窗理论加以检验、评估、解释和完善,既理顺了破窗理论自身的逻辑,又完善了破窗理论的内容体系。
三、破窗理论研究的特点
(一)国内外对破窗理论的重视程度不同
针对美国当时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来说,破窗理论是最直接有效的策略,其目的是恢复和维持社会秩序,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取得了斐然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学者还是政策制定者都十分重视破窗理论。大多数美国学者的专著,但凡涉及警察执法、警察政策、警务策略或者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都会为破窗理论留出一席之地。而我国早在引入破窗理论之前,就已经在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了,依靠密切联系群众以提升其可感知的安全感。1983 年的“严打”政策与破窗理论对微小失序行为的打击异曲同工,有效应对了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为政法工作的主旋律,我国又探索出群防群治、治安联防、平安创建、巡访、社区警务等各种私人参与警察治安治理的改革尝试[45]。可以说,这些适合我国当时国情的政策、策略都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智慧结晶,是我国土生土长的“破窗理论”。当然,“社区警务”到底是本土的还是舶来品仍有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早在20 世纪末学者介绍破窗理论之前,我国就已存在“片警”制度,虽然当时还没有“社区警务”这个概念,但是实质上已经是警察与社区成员密切互动并以和谐方式解决问题的工作理念了。
(二)国内外对破窗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同
国外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采取实证主义的方式,这一方面与20 世纪60 年代在美国已蔚然成风的以警察为田野调查对象的社会学研究热潮有关,另一方面,破窗理论的经验性来源也决定了其现实面向。作为一项经验性理论,破窗理论本来就是威尔逊和凯林基于对“纽瓦克步巡实验”的观察而得出的,而不仅仅是限于理论层面的探讨研究。这就注定了破窗理论自身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而,此后学者对它的研究不是基于其自身内容的真实性检验,就是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而这些几乎都是借助于观察实验,经由统计建模完成的。而国内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应用层面,在对该理论的内容进行简单介绍之后,或者最多分析一下破窗理论在国外的实践效果,就转而论述该理论对我国相关制度的启示,这种“拿来主义”倾向的借鉴方式向来会产生“水土不服”的副作用,而且会使理论自身的功能与价值大打折扣。此外,国内学者对破窗理论的研究几乎都是囿于犯罪学领域,如姜涛教授所言,之所以出现上述局限,归结到方法论上,盖源于仅从犯罪学视野思考破窗理论,而没有把问题分析的视野扩展到刑法学领域。法学界对于这一理论的解读存在着明显的短视现象,这为今后的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42]。对我国学者而言,不论是在研究的方法上,还是在应用研究所覆盖的领域方面,破窗理论都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三)对破窗理论的哲学审视不足
任何理论或者行动都有其思想根源,一般在应用该理论作为政策指导之前,我们应该对其自身有全面的认识:有益的、适合于本国国情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纳,而那些可能存在的先天缺陷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则是我们必须谨慎避免的。但是,这些缺陷往往是隐性的、内生的,只有在对其追根溯源的基础上才可能有更深刻的把握。即使在其土生土长的美国,破窗理论相关政策的执行在取得短期有效的成果之后又导致了一系列后劲更足、伤害更大的严重社会问题。哲学作为具备严密逻辑系统的思维运动,包含着阐释世界或指导实践的元理论与元知识,其追求的是“绝对”意义上的思想[46]。然而,对某一法律现象、法律概念、法学理论进行哲学层面的思考有时不但无法使问题得以澄清,反而有可能更趋复杂和混乱。这不仅因为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还因为我们在思考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法律流派思想的影响,同时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各种先入为主的目的和价值。而且不同的哲学视角会影响以目的和价值为尺度所作出的法律要素的重要性取舍,最终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在研究破窗理论之前,省思该理论的哲学源流实属必要。而纵观国内外学者,几乎没有对破窗理论的哲学追问,更缺少对破窗理论思想根源的研究,然而这是理论完成自身的审视与反省所必不可少的,也是理论保持内在活力和不竭动力的源泉。对破窗理论自身的内容,以及根据破窗理论制定的策略、政策和制度,及其在实践中的运行进行哲学省思,为其合法性解释提供达成合意的可能,是国内外研究者亟须面对的课题。
四、破窗理论研究在我国的未来之路
目前,破窗理论在我国还只是由于其打击和预防犯罪的价值而囿于犯罪学的一小块天地中。破窗理论所包含的更具价值的内容(警察权威支持下非正式社会控制的手段)在我国则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而未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在新时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基层治理要求下,警察更多的是发挥其服务职能,在多方主体参与下,通过警察权威的在场,选择更加温和的、侵损性更小的非正式社会控制途径保证问题的顺利解决。破窗理论以“解决问题”为警察首要任务的观点和理念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尽管理论根植的思想渊源、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不同,但“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共同面临的“安全发展观”“风险预防”“风险规制”的主题却再次向破窗理论伸出了橄榄枝,不论是其基于正式法律的强制手段,还是基于警察权威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手段,都是警察维护“安全”“有序”价值任务的执行手段,究竟选择哪种策略通常取决于警察对它们各自在达到维持秩序的目的方面所起作用的预估。
一般来说,警察追求的是控制事态,在他们觉得干预维持秩序的合法性权威并不明显,或者需要解决事态的犯罪性不是显而易见的时候,他们大多倾向于采取一些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手段以减少受到抵制的可能性。而公众被观察到的反应也是欢迎警察“在秩序需要他执行法律的时候去执行那些宽泛的法律,在不必要的时候忽略法律”[47]。北京大学的王世洲教授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破窗理论承认,在必要的时候启用正规的刑事司法程序是重要的一方面,但它同时也强调,这种措施只有在与其他多种警察策略相结合时才有效[14]。可惜的是,论者未能在此意义上展开更多论述。总之,警察权威支持下的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在维持秩序警务中的优先性与重要性是破窗理论提出者们更加青睐的解决问题方式,这也与我国警察机关在基层治理中所采取的群众路线下警察主导、多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多元化防控解决机制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因而在我国更有价值空间。
余论
破窗理论作为一项经验性理论,由于其针对性和有效性而受到学者和实务界的普遍欢迎,而且也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在学者的研究和检验中得到发展。但是,经验只有经过理性反思才能上升为真理,国内外学者对破窗理论自身的审视和反省不足,导致在破窗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些政策会因该理论的先天缺陷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该理论在美国实施初期的“零容忍政策”几乎是把贫困者、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排除在社会之外,此外还造成了大量监禁、警察暴力执法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对该理论的思想根源和法哲学基础进行本源上的回溯,以期对其有一个更深刻、更全面、更中肯的认识,也有望为其以后的借鉴者在制定政策策略时扫清雷区,避免误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