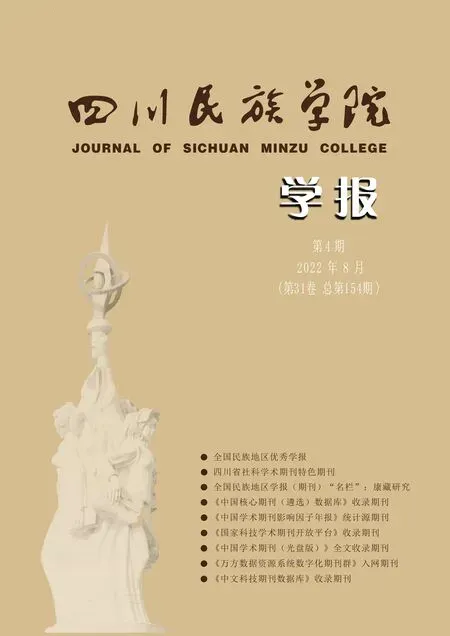多元英雄观视域下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及叙事
朱茂青
(四川民族学院,四川 康定 626001)
符号和形象是文化的深层次标示,挖掘各民族共有的文化符号和形象,构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弘扬内涵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加强中华民族认同的有效路径。在各族各地悠久的交流交融史中,民间文学不断吸纳各种文化因素,蕴含了许多共享的文化符号,“英雄”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符号之一。挖掘中国多民族地区的英雄形象及英雄叙事,对于理解中国各地各族民间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建造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家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以多民族频繁交流的康巴地区为例,通过对不同语境中的英雄观的梳理,在康巴社会发展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探析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演变、塑造过程,以及英雄故事叙事特点,考察康巴民间文学与汉文化中英雄观、英雄形象、英雄叙事方面的异同。
一、不同语境中的英雄观
人们崇拜的对象由对神的敬奉转向人自身时,英雄即从凡人中脱颖而出。事实上,中西对英雄的理解同中有异,古今有别,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英雄观交互影响。西方英雄史诗中的英雄概念,包含了个体本位价值观念。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极力张扬个体的健美、智勇和才能,积极追求爱情、权力和荣誉,视个人荣誉重于自身性命。史诗凭借众多英雄形象,主要弘扬“英雄时代”的英雄主义理想。英雄史诗本质上表现出赞美人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的人本主义思想,反映出热爱生活、积极乐观的思想精神状态。这一强烈的生命意识、重视个体价值、浓厚的个体本位意识也是希腊以及整个西方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英雄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含义。先秦时期,“英”“雄”作为两个概念,都有本义、引申义到多义并存的发展过程。其中,在引申义阶段,二者均表示“杰出人物”,只是从时间上比较,“英”的引申义晚于“雄”,而且,“雄”的内涵中特别强调“勇武”这一特质。之后,“英”“雄”分别作为赞美人物品格的褒义词,其概念内涵的演变经历了以下过程:由与“圣”“贤”等语义相近、互用,到区别于强调天命、注重道德完善的“圣人”“圣贤”等概念,“英”“雄”更多地作为强调才能的品格褒义词,再到形成具有专门意义、能够比较人的才能等级的品格褒义词,如“英”“俊”“杰”“豪”等,并以“英”作为最高层级人物品格褒义词的固定用法。最终,在强调天命、注重道德的“圣人”“圣贤”观念遭受严重冲击而趋于衰微的历史背景中,“英”“雄”被搭配铸为新词。“英雄”概念的应运而生是历史的必然。
“在崇拜‘英雄’、喜说‘英雄’的汉末三国时代,‘英雄’一词被空前广泛使用: 既可称帝王,也可称人臣;既可称他人,也可自称;既可称武将,也可称文臣;既可特指,也可泛指。”[1]刘劭的《人物志》中专章论述“英雄”:首先,给“英雄”下定义,“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1)参见:鹿群.人物志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4:79.刘劭对英雄的界定,主要为三个层面:一是对人才的评判标准;二是泛指一切智勇双全之人;三是指文武皆备,且能驾驭人才的创业帝王。英雄概念产生于三国时期,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当时社会环境动荡,反而形成了思想领域的真空地带,造成思想的活跃;二是兼收并蓄的用人制度;三是其时出现的个性主义思潮。三国时期的混乱和割据反而促成异常活跃的社会思潮,个性主义思潮兴起,英雄内涵中对于个人价值和贡献的强调,恰与三国时期的个性主义契合,因此,英雄概念是社会时代的产物。[2]
近代,英雄概念又注入了新的内涵,救亡图存的背景之下,加上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的进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又为“英雄”注入新的内容,即平民性与民族性,并相应扩展了其外延。汉末三国时代的英雄,更多的是从个人力量和智慧的优秀程度等方面进行定义,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比较。而梁启超的英雄观,更多从英雄之于群体(民族、国家)的价值和贡献进行考量,考察重点即是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所谓平民性, 则是指英雄的平民化趋势, 即梁启超提出的“无名英雄”说。也就是说,英雄不再是少数“胆识、勇气、智慧超群的杰出人物”,而是广大的平民百姓。[2]
在康巴文化传统中,人们将英雄与懦夫相对应,强调英雄的勇气、胆识,如“勇士若不自量,头破血流自己酿。男儿有英雄懦夫之分,但生命却无粗细之分。”[3]98“远处射箭非好汉,近前挥刀是英雄。懦夫葬送生命前,常常面迎英雄汉。”[3]126“猛虎般的英雄,狐狸般的懦夫。英雄活在沙场上,懦夫死在逃路上。”[3]127英雄是平凡的人中产生的,如“英雄出自穷苦的汉子中,利剑出自破裂的刀鞘中。”[3]99英雄有胆识,不怕死,在战场上体现价值和建功立业,如敦煌藏文卷中的松巴谚语:“英雄胆气壮,不惧怕死亡;贤者智慧高,知识难不倒。”[4]48甘丹格言讲到:“智者不重美衣食,而以美誉为光荣;请看英雄不他求,专要战场得胜利。”[4]349-350格萨尔史诗中,智勇双全的英雄典马,在探敌时唱道:“男儿在太阳底下扯闲话,都说我是英雄汉;姑娘在炉边烤火扯闲话,全说我里外都能干。如今大敌压国境,从前的豪言看今天。为国为众探敌情,纵死沙场心也甘!”[4]121
如上所述,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观,既有汉末三国时代的强调勇气和胆识的个人主义英雄的含义,有个体间的比较,如英雄与懦夫、英雄与穷人;到了部落和酋邦时代,经过文人的改造,英雄又具有了近代梁启超所言的依据在群体中的贡献和影响而定义的内涵,这在上文所引的松巴谚语和格萨尔史诗中,体现最为明显。《纳日伦赞传略》中也描写了一位平凡之人毛遂自荐的故事(2)这个故事强调了平凡之人是如何抓住机遇,脱颖而出,由平凡之人上升为英勇之士的过程。当然,这类故事的原型可于《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见到。该故事的启示还在于,研究区域的民间文学,依然要看到区域间的文学交流影响,同时也更表明故事叙事的跨区域和跨族群之特点。:君臣商议平息达布叛乱,选用将帅时,平民僧果米钦挺身而出,誓平叛军。[4]61
二、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及叙事
对康巴民间文学中英雄叙事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故事结构、叙事方式、叙事者与作品间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以探究其是如何讲述英雄故事的,这样讲述的原因何在。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叙事主要是由神话(3)这类神话流行于藏族文化中,并非康巴独有,且受到后世宗教人士、历代文人的不断改造、定型且叙事固定化。换句话说,此类神话的流传,恰是受到宗教和文字的双重影响。如苯教文献中记载,聂赤赞普是古代天神下凡为人主,与汉文化中的伏羲、后羿相似。由于受到书写文字和书写工具的影响,叙事方式偏于简约化,英雄叙事不得不保留故事的主干部分而尽可能删掉故事丰满的细节、个性化和区域文化的特色,使得英雄故事失去了丰富性和生动性。除了书写工具的原因,也与这些英雄叙事过早完成从民间叙事向文人叙事的转换有关。或者说,代表了王统和现实统治者的庙堂叙事的形成。在这里,口传到书写的过程中,大量信息失落,民间英雄叙事被篡改、排斥甚至边缘化。、史诗和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叙事构成。神话和史诗中的英雄叙事,固然是重要的研究内容,然而,对民间故事中英雄叙事的研究则可获得重要的民间信息。严格地说,民间叙事是与庙堂叙事相对但又互补的方式,在民间故事传说中,虽然存在大量反映上层意识或者符合统治阶层思想伦理的内容,但是,仍可从其中探查或多或少的民间因素。在此,以《格萨尔》和民间故事为例,对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及叙事特点进行剖析。
(一)《格萨尔》中的英雄形象及叙事特点
据降边嘉措的整理,《格萨尔》在中国、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巴基斯坦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史诗流传带。[5]康巴有名的谚语中就说到:每个藏族人的嘴里,都有一部《格萨尔》。《格萨尔》中有诸多的英雄形象,各有特色。《格萨尔》的叙事主题多是降妖伏魔、抑强扶弱、抗击外敌,使百姓过上平安生活。格萨尔的出现,标志着藏地英雄时代的来临,民众关注点由神转到人,转向自己的生活。战争中的英雄享有先前神的地位,同时也具备一定的神性。不朽的格萨尔就成了半人半神的形象,他有神的威力和神通,也有人的禀赋和气质。作为神,格萨尔来自天界,是白梵天王的第三子顿珠尕尔保,为降妖伏魔、救护人间生灵,他自愿到人间做黑头人的君长。作为人,他出生于王族。(4)这种叙事模式,在藏文史籍亦有类似的描述。如作为藏族史籍早期历史记载的“木之本、水之源”的《柱间史》,对后世藏文史籍的影响很大。观世音为了教化雪域众生,化身作了吐蕃君王——松赞干布。另一流传甚广的是聂赤赞普自天而降为王的故事。若从叙事而言,这体现了上层、宗教、文本与民间、百姓、口传文学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过程。经过不断加工,格萨尔集诸多称号于一身,军王、救星、英雄、君主、长官、统帅、首领,后来还加上了佛教内容:白梵天王的儿子、莲花生化生、佛祖的高徒、佛教的维护者、千位佛祖的使者。[6]但格萨尔的本意,通常理解为花蕊,言格萨尔之英武、聪慧。也就是说,从人的层面来看,他的形象底色是英雄。在史诗中,也特别强调了勇敢与力量之于英雄的重要性。敦煌文献中说,能勇斗野牛即为英雄。史诗中赞美甲察等英雄,能逮住野牛,而后将野牛撕成几段,以此来夸赞他们的英武。这也是英雄的重要标准:一是勇敢,对付野牛有生命危险,胆小者,难与其较量;二是气力,没有超人的力量,就难斗过野牛。(5)对个体英雄特质的强调,在现存的民间故事中有大量体现。但是勇敢与力量太过实在,仅凭人间的大力士和勇敢者形成的英雄似乎并不能将其从凡人中区分出来,英雄必然还要有一些其他的特点,在格萨尔史诗中,人们没有抛弃神话和宗教,而是在其中寻找英雄的灵力,既使得英雄的个性特质更加丰满,也使得英雄的伟力能率领部落进行规模宏大的战争。
格萨尔的一生经历大致为:英雄特异的诞生——英雄苦难的童年——英雄立功称王——结婚——征战——英雄凯旋(或战死),以这样的模式来叙述,其模式化倾向一目了然。整体故事如此,在具体的情节中也设置了类似的模式。比如英雄奇异的诞生情节,从情节构成的元素(英雄父亲有三个妻子,无子,向天神祈子,从肉囊中诞生等),可发现具体的叙事情节也呈现出模式化。格萨尔的变身情节,既显示其机智,又展示其神奇的本领,变身情节的反复运用,就成了一种叙事模式。(6)不仅在《格萨尔王》中,在《江格尔》和《玛纳斯》中,叙事风格都十分相似。石泰安从英雄的特征,如英雄的化身、相貌,以及英雄的成长过程,如落难、称王等,进行细致的分析,[7]再次证明了英雄故事的叙事模式化倾向。除叙事模式化外,叙事的繁复性也是突出特点。英雄史诗演唱都运用重复叙事(情节重复/语言重复)、排比、夸张、比喻等方式,反复渲染场景,使故事表现得生动丰满。反复叙事,使节奏减慢、故事进展缓慢、叙事呈繁复化倾向。史诗英雄叙事的模式化和繁复化,原因是作为活态史诗,这样的叙事便于艺人的记忆和传播,也为了听众的理解。(7)关于这种叙事的理论解释,美国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的《故事的歌手》的第四章中,专门讨论了这种叙事语法(narrative grammar)。
(二)民间故事中的英雄形象及叙事
1.凡人型英雄故事
此类故事中,主人公均为世间凡人,但是凭借超凡的力量和本领,更因勇于承担、牺牲奉献的精神,凡人成了英雄。传奇英雄故事大多追求情节的曲折多变,而凡人型英雄故事则直接讲述主人公的英雄壮举,少有对人物出身和超凡能力的详细介绍,主要强调主人公的善良孝顺等凡人的伦理道德因素。在《雍珠姑娘》中,因具有同情心,平凡的巴登获得神灵帮助,勇斗财主,最后让百姓自由而愉快地生活。[8]259《骑虎勇士》中,扎西并无特异之处,只因善良,帮助老鹰而获得回报,在土司的陷害中脱身,反将作恶的土司除掉,从而拯救了全寨的百姓。[8]123《砍柴人与老虎》中的砍柴人因救助老虎,由平凡之人成为拯救当地免受外族侵略的英雄。[8]270
凡人成为英雄的另一条件是聪明智慧。如故事《养子和天意》,在诸多巧合中,聪明的养子当上国王,又以灵敏机智化解磨难,最终成为百姓拥戴的国王。[8]150在康巴民间故事中,阿口顿巴的故事一般归于机智人物故事类型。若从英雄的以强扶弱、勇敢智慧方面来讲,阿口顿巴也应属于一个机智勇敢的民间英雄。他言语犀利而幽默,对待封建统治者及上层宗教人士毫不留情,类似于梁启超所言的“无名英雄”,在别人需要帮助时,他能挺身而出,行英雄之实。
因为作为普通人,缺乏超凡的能力,所以其英勇行为的结局往往是自我牺牲。不过,也正因为壮举和献身,英雄受到百姓敬奉,具有了非常的身份与地位。如《张三疯子》,讲述的是一个整天疯疯癫癫、蓬头垢面的异常人,拯救乡亲,勇斗土司,最后人们发现他是具有灵力的英雄而加以供奉。[9]
2.传奇英雄故事
与凡人型英雄故事不同,传奇英雄故事中,英雄虽然是凡世之人,但是长相奇特、能力超常,往往还能得到宝物、神助。[10]康巴传奇英雄故事虽然具体内容各异,但模式却类似:奇异能力——落难——远行——神助——拯救百姓、完成英雄转化等。在众多母题中,经常出现大力母题,众多幻想型英雄故事中,都将力大无穷作为英雄的特质,而大力士故事也是传奇英雄故事中最吸引人的部分。在《卓呷和恩巴》中,一个汉地的青年猎人,身体魁梧,相貌不凡而且特别勤劳勇敢,他通晓鸟语,能捕获飞跑于悬崖上的山羊岩驴,能赤膊制伏老虎。后来他离开汉地远行到康巴亚柯地方的高山打猎,获得藏名“恩巴”,即猎人之意,同时,他还具有藏族社会特别看重的精巧的雕刻技艺。他与东家美丽温柔的卓呷产生感情,订婚后,雕刻了卓呷的木像,雕像意外流至王城,被荒淫无度的暴君发现,卓呷被抢入宫。恩巴远行寻找恋人,以智慧(与国王换装)杀死暴君,成为新国王,他大力促进生产,举贤任能,整军经武,使得国家富强、百姓安康。[8]118-121这则故事情节和叙事结构完整,叙事模式上具有典型性:超于常人(胆量、力量、聪明,多才多能)——远行异乡——获得认可——爱人受难——再次远行——智勇双全、杀死暴君——成为君王,拯救百姓;同时就个人层面而言,故事强调了恩巴成为英雄的另一优良品质:孝敬双亲、忠于伴侣,表现了较明显的孝与忠贞观念。
故事将个体与群体相联系,这更多是基于汉藏文化语境,英雄的个人利益、追求始终与群体利益相结合,表现了英雄品格的社会伦理意义,也反映出对人的社会性的思考和认识。同时,可以看到,“力”与“勇”被演绎成了英雄重要而突出的人格禀赋。但也应该注意,对“力”的推崇在逐渐减弱,而对英勇顽强精神的渲染在逐渐增强,这反映出英雄观的变化。《卓呷和恩巴》主人公在困顿难行之时,听到布谷鸟的歌声“找幸福要坚强,遇困难勿灰心”,更加坚定了信念,勇敢地继续前行。[8]120
英雄观的变化与文学叙事的本身演化关联,也是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映射。人类最初面对缺乏认知、难以掌控的自然,深感自身的渺小,因此,自然生发出对力量,特别是超凡之力的渴求。随着个体和社会的发展,人对自身及自然有了更多的认识、把握,由此产生的自信使人不再将征服自然的希望冀于幻想中的神力,而是落实于普通人面对艰难困苦时,坚韧顽强、勇往直前的意志和行为中。同时,孝顺与夫妻忠贞、白头偕老的观念,也赋予英雄人物更多的跨文化特质,使英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由英雄成为君王的叙事模式,一方面有与卫藏君王英雄叙事相似的地方,如陌生的、来自远方的人或上界的神,异地为王。在《以善报恶》故事中,人才出众、英俊威武、富有爱心、饱受磨难的出生于王室的二儿子,经过受难的水路到异国为王。[8]161另一方面,又受到汉地英雄徙边史叙事风格的影响,如《卓呷和恩巴》中的英雄叙事。王明珂就历史文献中的模式化叙事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归纳出叙事的模式,即英雄流落于异国他方,凭借出众的才能成为本地统领,其后裔也世代为王。在此类“历史”文献中,英雄祖先往往从失败者到王者,但这些失败者促进了落后地区的发展。他指出,这类情节以及较为固定的叙事模式,实际是在传达汉文化所居的核心地位,以及在血缘、空间、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边缘性。[11]这种叙事模式具有普遍性,不仅在古代中国,而且在欧美也有此类叙事模式。著名人类学家加纳纳什·奥贝赛克拉(Gananath Obeyesekere)认为,西方文化中的一种神话模式——西方文明世界的人到远方异国,常被当地土著奉为神或王。[12]
然而,与上述叙事模式不太一样,《卓呷和恩巴》中,为王者是基于个体的男儿志在四方的追求,从遥远的汉地远行至康巴,凭借的是个人的勇敢和技能,以及汉地文化与藏地文化的互补(雕刻技术)而深受当地人欢迎,因而获得了本地人的姓名并得到认同,再以英雄历经磨难,最终成为代表个人和群体利益的、集勇气、孝顺、忠贞等道德伦理因素于一身的完美英雄和贤君形象。这里体现的是康巴多元文化包容相处、彼此补充、互为主体的重要特点。叙事中没有汉地正史英雄徙边记中的中心与边缘的意味,同时,西藏民间文学英雄观中神的因素,在康巴民间故事中也大大消褪。类似的叙事模式还可以在故事《勇敢的扎西》中梳理出来:扎西为解救民众而勇斗龙王,因其孝心感动龙王,最后在龙王帮助下,在陌生的国度当上国王。[8]272
在1980年后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所整理的民间故事中,《卓呷和恩巴》的叙事结构比较完整、情节和语言也较为丰富,这得益于收集者邓珠娜姆对汉藏文化的稔熟。美中不足的是,故事的翻译整理,只有译者的姓名、年龄及工作单位,缺少了故事的出处、收集时的情境和细节,以及讲述人的年龄、职业、经历、教育程度、故事如何获得等背景信息,影响了我们对本故事的进一步解读。
三、结语
通观前述作品,史诗英雄和传奇英雄均有无穷之力与非凡之能,史诗英雄故事中,英雄是群体的代表,半人半神,具有无上神力,能够操控、主宰世界;而传奇英雄故事则更多突出个体的超凡能力。故事对英雄之“力”的强调,体现了人对自我的认识与自我崇拜,也是人对征服自然、掌握世界的想象与渴望。英雄的精神和品格,则是英雄故事的重要表现内容。通过“英雄远行”“英雄磨难”“英雄建功立业”等叙事模式突显英雄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勇敢无畏的精神。凡人英雄故事主要从伦理道德层面着力显示英雄的品质和精神。“勇”是勇敢、有胆量,是英雄最显著的特征,表现出人类敢于面对异己力量,奋勇抗争,坚强不屈的精神。这透视出人们关注点从神到人的变化,从对神性转向对自身主体精神和本质力量的肯定与称颂,英雄观也随之有了更多现实价值,有对善良、智慧等品格的褒扬。
同时,康巴民间故事与汉文化中的英雄观既有联系,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群体原则和对“力”“勇”的追求两个层面。首先,群体原则贯穿康巴英雄故事,成为其中鲜明的主旋律,个体与群体始终联系在一起。群体观念也是汉文化的重心,就儒家而言,忠君报国即为其英雄观的核心。其次,康巴凡人英雄故事也突出个体的“力”与“勇”,同时也强调智慧、聪明的重要性,这与汉文化的影响有关系。汉文化语境中的英雄观很少强调超越凡人的力量,即使展露出勇武过人的禀赋,也往往是基于现实人的合理描述。在汉文化中,“勇”被置于“智”之后,勇的目标仍然是对“仁”与“义”的追求,儒家英雄观也是注重智慧甚于重视勇敢。
总之,康巴史诗英雄和传奇英雄叙事中,着力推崇体魄、力量与人格精神,这是早期人文生态的产物。同时,受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追求“力”与“勇”的英雄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开始倾向于宽厚与智慧,流露出柔和的色彩。康巴民间文学中呈现的英雄形象、文化气质、伦理内蕴、叙事模式及其与汉文化英雄观的联系,源于其作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因此,研究康巴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和叙事风格,对理解中国民间文学的共性,构建共有精神家园,不无裨益。
——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