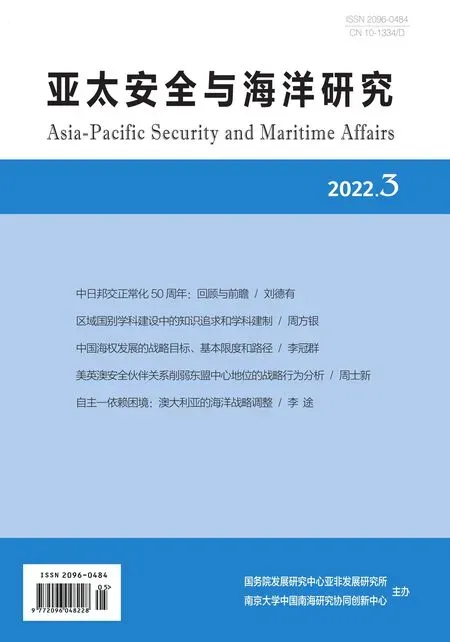自主—依赖困境: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调整
李 途
内容提要:自主—依赖困境,构成了澳大利亚海洋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征。一方面,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认知,决定了澳大利亚需要采取与强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安全;另一方面,对同盟承诺限度的认识,则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能力。澳大利亚在“自主防御”与依赖盟国之间的调整、转化与挣扎,不仅贯穿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发展的始终,也体现了澳对地区安全环境及澳美同盟关系的认识。从“自主防御”的提出、发展到“回归”,澳美同盟与“自主防御”的关系也经历了相互冲突、相互借重,再到相互补充的过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澳大利亚的“自主防御”政策最终回归与强国结盟的传统,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实现自身安全,但其内在的矛盾和悖论无法避免。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是典型的两洋国家,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广袤的大陆及四面环海的地理特征为其提供了天然的安全屏障。然而,历史与地理的冲突,导致澳大利亚具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与不安全感,对亚洲国家始终抱有戒备心态,由此形成的自主性与依赖性之间的困境构成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发展的核心特征之一。一方面,与“强大的海洋国家”结盟是澳大利亚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传统;另一方面,“自主防御”却成为自越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防政策和海洋安全战略的核心概念。2020年的《国防战略修订》标志着澳大利亚国防战略自主的回归,但是2021年美英澳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建立又进一步强化了澳大利亚的对美安全依赖。厘清自主—依赖困境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对理解澳大利亚海洋安全战略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一、海洋国家的地理悖论与自主困境
海洋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海军战略不同的是,它指的不仅仅是海军在海上的军事行动,而是“一国从海上投射力量影响陆地事态的能力”。(1)Albert Palazzo,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Australian Army,”in Albert Palazzo, Antony Trentini eds.,Projecting Force: The Australian Army and Maritime Strategy, Canberra: Land Warfare Studies Centre, June 2010, p.6.影响一国海洋战略制定的因素众多,包括国家实力、地理位置、海洋文化、民族特性、历史经验以及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等等。对于海洋国家而言,海洋战略的目标包括实现海洋的开发和利用,维护海上安全、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以及维护海上贸易通道安全等等。但对于大国而言,海洋战略总是与海权和海上争霸联系在一起。而海权对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2)参见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李少彦、董绍峰、徐朵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海权还是一国走向世界霸权的必要条件,16世纪以来的世界霸权国均为强大的海权国家。(3)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Thompson, Sea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8.
对澳大利亚这样的海洋国家而言,发展海洋战略是其应有之义。但是,澳大利亚在历史上却很难被称作是一个海洋大国。“历史与地理的冲突”,构成了澳大利亚“现代安全困境的核心”,直接影响着澳大利亚的战略与安全决策。(4)Michael Evans, The Tyranny of Dissonance: Australi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 of War 1901-2005, Land Warfare Studies Center Study Report, No.306, February 2005, p.25.作为一个在语言和文化上隶属于西方,但在地理上又位于亚洲南端的国家,澳大利亚具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与不安全感。一方面,无论从语言、种族、文化和价值观来看,澳大利亚都属于欧洲文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坐落于亚洲最南端的地理现实,又使得澳大利亚不得不与亚洲国家打交道。再加上澳大利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有限,无法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和军事投入,因此,寻求大国的保护就成了澳大利亚外交与国防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长期的历史实践过程中,澳大利亚产生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即认为必须与“强大的海洋国家”结盟,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二战前,澳大利亚主要依赖大英帝国作为国家安全的保障。二战结束后,澳大利亚转向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关系。由于作为盟国的海洋大国足以提供强大的海上力量,澳大利亚只需在联合行动中承担起陆地军事任务的责任。(5)D.M.Horner, “The Continental School of Strategic Thought,”Defense Force Journal, No.82, May/June 1990, p.42.这一独特的历史发展进程,造就了一种大陆的(而非海洋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这也导致澳国防政策的制定长期以来缺乏海洋意识的指导,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认识。(6)Michael Evans, “The Third Way: 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y Research Paper, No.1, May 2014, p.7.海洋更多地被看作是陆地的安全屏障,而非向外扩张的跳板。尽管从历史上来看,澳大利亚不乏跨越海洋进行远征作战的军事传统,一战期间澳新军团(ANZAC)在加里波利海战中的英勇表现还成了澳大利亚现代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但是这种军事传统和海战经验并没有就此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的主流战略思潮,凸显了“大陆主义在澳战略文化中的主导地位”。(7)Michael Evans, The Tyranny of Dissonance: Australia’s Strategic Culture and Way of War 1901-2005, p.34.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与海洋战略重要性的提升,澳大利亚逐渐确立了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础地位。但是,“历史与地理的冲突”,仍然影响着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自主性。如同其外交和国防政策高度依赖盟国一样,在如何发展海洋战略的问题上,澳大利亚也无法摆脱盟国的影响。澳学者亚历克斯·特维斯(Alex Tewes)等认为:“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更多地体现为与盟国的关系,而不是对地区战略环境变化的直接反应。”(8)ALex Tewes, Laura Rayner and Kelly Kavanaugh, 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Research Brief, No.4, 2004-2005, p.6,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04-12/apo-nid583.pdf [2022-03-16].与强大的海洋国家结盟,为澳大利亚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安全保障,但反过来也限制了澳国防政策的独立性和海洋意识的发展。这也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却很难称作是一个海洋大国的地理悖论。
如果说对地区安全威胁的认知,或者说对“历史与地理冲突”的认识,决定了澳大利亚需要采取与强国结盟的方式来维护自身安全,那么对同盟承诺限度的认识,则决定了澳大利亚必须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能力,减少对盟国的安全依赖。由此形成的自主—依赖困境,贯穿着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的始终。
首先,同盟的利益并非总是一致的。特别是在不对称同盟中,盟国对地区和全球秩序的理解容易出现分歧和差异。(9)参见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1页。对大国而言,它们更为关注全球均势的变动及其对自身地位的影响。相反,对于地区小国来说,由于它们对全球均势影响较小,而来自地区的威胁对它们影响更大。对全球大国来说,小国在地区事务上的追求可能无关紧要,因此拒绝提供援助。美澳同盟的历史也表明,美国并没有对澳尽完全的援助义务。1976年,正是出于对美国在印尼问题上能否提供支援的担忧,澳大利亚正式提出“自主防御”的概念,减少对盟国的安全依赖。1999年的东帝汶事件,凸显了美国地区安全承诺的限度,加剧了澳大利亚发展海洋战略的紧迫感。
其次,大国时常将其战略利益凌驾于小国的战略利益之上,要求小国为其全球战略服务。为了获得大国的安全保证,小国不得不追随盟国的全球战略,不断展现出忠诚与投入,以期盟国在未来的危机中能投桃报李。二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就追随美国参与了多次海外军事行动,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90年代的海湾战争、冷战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然而,与强大的海洋国家结盟,并不能总是保证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反而可能会带来同盟牵连的风险,限制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自主性。
特别是当大国实力出现衰退时,必然会要求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同时减少其承担的海外义务,以降低同盟维系的成本。2016年以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削弱了美国全球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拜登政府匆忙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进一步削弱了盟国对美国领导地位的信心,澳大利亚开始重拾“自主防御”概念,加强海上威慑力量建设,对冲美国可能随时抽身离开的风险。
然而,澳大利亚在追求“自主防御”的同时,却将目标错误地设定为中国,为此必然要加强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从而再次回到依赖“强大的海洋国家”的路径。总之,自主—依赖困境,构成了澳大利亚海洋发展战略的核心特征。澳大利亚在“自主防御”与依赖盟国之间的调整、转化与挣扎,不仅伴随着澳大利亚海洋战略发展的始终,也体现了澳对地区安全环境及澳美同盟关系的认识。
二、相互冲突:从“前沿防御”到“自主防御”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成立后,其海上防御仍然依赖于英国皇家海军,每年需向后者支付20万英镑的防务费用。1909年,面对德国海军崛起的威胁,英国同意各自治领组建自己的海军舰队。最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耗资370万英镑打造了澳大利亚历史上、也是大洋洲历史上第一支海军——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包括1艘重型巡洋舰、6艘驱逐舰、3艘轻型巡洋舰、3艘潜艇。(10)参见张天:《澳洲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37—238页。一战期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参与了英国在太平洋和黑海地区的作战任务,但其指挥和调度权仍归英国掌握。一战结束后,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受制于英国削减海军军备的需要,澳大利亚也不得不缩减海军规模,废弃了曾经作为主力舰的“澳大利亚”号巡洋舰。(11)ALex Tewes, Laura Rayner and Kelly Kavanaugh, 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Research Brief, No.4, 2004-2005, pp.7-9,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04-12/apo-nid583.pdf [2022-03-16].到1923年,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的军舰数量已经从一战时期的23艘削减为11艘,而且由于缺少燃料,大部分军舰都无法正常工作或者只能在近岸活动。(12)Michael Evans, “The Third Way: 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y Research Paper, No.1, May 2014, p.10.
(一)澳美同盟与“前沿防御”
二战初期,澳大利亚的主要任务是配合英国派遣远征军前往中东和北非地区作战。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南下进攻东南亚,彻底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周边安全形势,加剧了澳大利亚的安全紧迫感。1942年,新加坡的陷落标志着英国势力在东亚的衰微以及日本威胁的临近,澳大利亚开始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护,为美国提供军事基地,同时着手从中东等地区撤军。二战结束后,世界分裂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孤悬于太平洋的澳大利亚极力寻求与美国建立正式的同盟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澳大利亚全力配合美国出兵朝鲜,为澳美同盟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1年9月,澳大利亚、新西兰与美国三国共同签订《澳新美同盟条约》(ANZUS),美国自此成为澳大利亚最为重要的盟国和长期的安全伙伴。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外交和国防政策重心开始从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在澳大利亚看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好方式就是通过“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ce)将防线尽可能往北推进,让东南亚成为澳大利亚的北部安全屏障,为澳大利亚提供防御纵深。“前沿防御”战略实际上是澳大利亚联邦成立以来的国防政策基础,但是冷战的大格局为其增添了鲜明的反共色彩,澳大利亚将共产主义的扩张视为最主要的安全威胁。(13)ALex Tewes, Laura Rayner and Kelly Kavanaugh, 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Research Brief, No.4, 2004-2005, p.13,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04-12/apo-nid583.pdf [2022-03-16].
1953年10月,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决定组建“英联邦远东战略预备军”(Far East Strategic Reserve),保护马来亚和英联邦在东南亚的利益。1955年2月,澳大利亚加入美国主导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将前沿防线推进到马来亚以北地区。1965年5月,澳大利亚正式派军队参加越南战争,将其作为“保证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必须付出的代价”,澳大利亚担心,美国一旦撤出东南亚会给该地区带来巨大的军事真空。(14)参见张建新:《澳大利亚出兵越南:原因、后果和教训》,《世界历史》1999年第1期,第43页。通过参与英、美主导的军事行动以及与东南亚部分国家签订的集体安全条约,澳大利亚为其“前沿防御”战略的实施构建了稳定的基础。而且,由于“前沿防御”恰好与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有着大致相同的地缘支点,这也为澳“前沿防御”战略的实施提供了便利。
“前沿防御”战略的优势在于,澳大利亚不需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护其漫长的海岸线,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离不开盟国的安全保障。从结果来看,尽管“前沿防御”战略在冷战期间维护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但它也进一步加剧了澳大利亚对盟国的安全依赖,限制了澳大利亚国防和外交政策的独立性。这也是澳大利亚在二战结束后追随美国参加朝鲜战争、介入印支事务,并最终参加越战的重要原因。在澳看来,维持英美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和介入,对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7月,英国工党政府正式宣布将从1971年起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地区撤军。1969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发表关岛讲话,宣布在亚洲实行收缩战略,鼓励亚洲国家承担更多的安全与防御责任。由于缺少海洋大国盟国的支持,澳大利亚长期以来实行的“前沿防御”战略失去了重要的基础和支撑。
(二)“自主防御”概念的提出
越战的失败促使澳大利亚开始反思和调整其国防政策和对外关系。澳1976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正式提出“自主防御”(self-reliance)的概念,标志着澳大利亚国防与安全政策的重大转变。《白皮书》称,“依赖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提供军事援助,已经不再是澳大利亚的国防政策”,澳需要“形成能够实现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15)Parliament of Australia, Australian Defence(1976 Defence White Paper), 1976, https://www.aph.gov.au/About_Parliament/Parliamentary_Departments/Parliamentary_Library/pubs/rp/rp1516/DefendAust/1976#_Toc427840412 [2022-03-17].事实上,除了越战失利的因素外,澳大利亚的政策转变与美国在印尼问题上的态度有着直接关联。尽管澳大利亚将印尼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但是由于印尼问题并不直接涉及美国的安全利益,澳大利亚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在这一问题上破坏与印尼的关系向澳提供支援。(16)Stephan Frühling,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 and the Concept of Self-Re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5, 2014, p.535.历史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1963年,在印尼反对马来西亚联邦成立的过程中,澳大利亚联合英国、新西兰支援马来西亚,但是美国认为印尼的军事行动并没有构成对澳本土的威胁,也就不属于《澳新美同盟条约》的范围,因此拒绝进行直接军事介入。
在这样的国防背景之下,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也呈现出相对独立的倾向,主张通过本土防御来维护自身海洋安全,将西南太平洋和东南亚地区作为海洋战略的重点方向。当时的惠特拉姆政府很快与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并陆续从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撤军,结束了将东南亚作为澳大利亚“前沿防御”阵地的历史。1973年,澳取消了歧视亚洲移民的“白澳政策”,并于次年与东盟建立了“对话伙伴”关系。1983年,澳大利亚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墨尔本”号退役后,澳大利亚决定不再建造新的航空母舰,意味着霍克工党政府不再愿意执行积极配合美国的“前沿防御”战略。(17)参见宫少朋:《〈蒂普报告〉引起的澳大利亚国防政策大辩论》,《外交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第68页。
1986年3月,保罗·蒂博(Paul Dibb)向澳大利亚国防部提交了《国防能力评估报告》(也称“蒂博报告”)。报告认为,澳大利亚当时并不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大规模军事入侵的可能性不大,建议澳放弃“前沿防御”战略,采用“拒止战略”(strategy of denial),也即通过层层防御,阻止任何潜在的敌人登陆澳大利亚本土或切断澳周围的海空通道(sea-air gap)。(18)Paul Dibb,Review of Australia’s Defence Capability, Report to the Minister for Defence,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6, pp.1, 50,https://www.defence.gov.au/SPI/publications/defreview/1986/Review-of-Australias-Defence-Capabilities-1986.pdf[2022-03-20].“拒止战略”本质上是防御性的,主张限制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行动范围,不再强调地区安全、同盟关系以及远距离投射在塑造地区和全球安全局势中的作用,特别是与“前沿防御”战略相比,“拒止战略”并没有对澳美同盟的重要性给予过多重视。(19)ALex Tewes, Laura Rayner and Kelly Kavanaugh, 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 Department of Parliamentary Services, Research Brief, No.4,2004-2005, p.15,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04-12/apo-nid583.pdf[2022-03-16].
由于“蒂博报告”过于“消极被动”遭受了广泛批评,1987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在“蒂博报告”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白皮书重申“自主防御”的重要性,主张通过“纵深防御”战略(defence in depth)来维护澳大利亚本土及周边海空通道的安全。与“拒止战略”相比,“纵深防御”更为强调进攻性能力建设。与此同时,白皮书还指出,澳国防政策的重点不仅包括本土防御,还包括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澳美同盟关系。(20)The Defence of Australia 1987,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87,http://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1987.pdf[2022-03-20].
从“蒂博报告”到1987年《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完成了从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到在维持澳美同盟的基础上逐步实现“自主防御”的过渡,结束了国防政策的“十年徘徊期”。(21)参见宫少朋:《澳美安全合作的纠葛与前景》,《美国研究》1992年第2期,第68页。由于“自主防御”提出的本意是为了在没有盟国援助的情况下维护澳大利亚本土的安全,“本土防御”(defence of Australia)是其应有之义,也就是说,此时霍克政府的海洋战略仍然是“内向的”(inward-looking)、“大陆主义的”。澳大利亚将印尼的苏哈托政权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国防战略也专注于防止海空通道受到来自北方的袭击。其结果是,澳更为注重陆基飞机和潜艇的发展,忽视了海上军事投射能力的建设。1983年,澳大利亚唯一一艘航空母舰“墨尔本”号退役后,失去两栖作战能力的澳大利亚海军更像是一支“黄水海军”,而非“蓝水海军”。(22)Michael Evans, “The Third Way: 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rmy Research Paper, No.1, May 2014, p.20.
三、相互借重:从“本土防御”到海外行动
冷战结束后,曾经被两极格局掩盖的地区矛盾和冲突加剧,地区安全成为影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海洋战略在澳大利亚国防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一)地区危机与“本土防御”
澳1994年的《国防白皮书》强调了“本土防御”的重要性,并指出“澳大利亚的安全与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繁荣密不可分”,“澳大利亚需要保持对亚太地区的战略介入,为地区安全贡献力量”。(23)Defending Australia, Defence White Paper 1994, Canberra: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 1994, p.3, https://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1994.pdf [2022-03-23].1997年公布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报告》(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指出:“地区冲突不仅与澳大利亚的安全有着直接关联(至少会产生重大影响),而且更有可能发生。”(24)Department of Defence,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1997, p.12,http://repository.jeffmalone.org/files/defence/SR97.pdf [2022-03-24].报告还强调,由于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条件,任何针对澳本土的袭击都来自海上,因此海洋方式(maritime approaches)而非大陆方式更适合于澳的地缘战略环境。(25)Department of Defence,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Strategic Policy, 1997, pp.36, 43-44,http://repository.jeffmalone.org/files/defence/SR97.pdf [2022-03-24].这份政策报告首次提出将海洋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标志着澳过去20多年以来的国防战略思考出现重大转变。
1999年8月,东帝汶进行独立公投后,安全形势急转直下,暴力冲突事件频发。为此,联合国安理会决定批准成立一支以澳大利亚为首的国际维和部队,前往东帝汶执行恢复和平与安全的任务。澳大利亚曾要求美国提供地面部队进行支援,但是由于美国担心会破坏与印尼政府的关系,不愿意进行大规模军事干预。而且,美国国防部对科索沃的人道主义行动已颇感疲惫,不愿意再次卷入东帝汶的维和行动,因此只提供了后勤支持,凸显了美国对盟国安全承诺的限度。鉴于东帝汶局势关乎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澳表示,即使没有美国的参与,澳也准备出兵东帝汶。澳还表示,“在亚太地区不能等待美国带头恢复秩序,地区问题应该由地区本身起带头处理的作用”。(26)转引自《分析:澳大利亚为何积极出兵东帝汶》,《中国青年报》1999年9月30日。
除了同盟承诺的限度外,东帝汶危机也暴露了澳大利亚国防军在应对地区危机事件中的不足,加剧了澳大利亚发展海洋战略的紧迫感。由于缺少大型的两栖登陆舰,澳大利亚的兵力和物资运输能力有限,导致澳即使在东帝汶部署小规模的维和部队都存在困难,海上力量建设刻不容缓。2000年的《国防白皮书》正式使用“海洋战略”(maritime strategy)一词,提出“自主防御”“海洋战略”“积极主动”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三原则。其中,“海洋战略”指的是“控制澳大利亚周边的海空通道,防止敌对力量进入,并为本国力量提供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27)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2000: Our Future Defence Force, 2000, pp.XI, 47,https://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2000.PDF [2022-03-26].尽管澳大利亚认识到了海上力量建设的重要性,但在澳学者看来,这一时期的海洋战略仍然建立在“海上拒止”的基础上,缺乏海上控制和海上力量投射的内容,因此更像是“大陆国家的海洋战略”,而非英美海洋国家“真正的海洋战略”。(28)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prepared by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Trade, June 2004, p.47.
(二)反恐战争与海外行动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中东与反恐事业。作为美国最坚定的盟友之一,澳大利亚以美国本土遭受攻击为由宣布启动《澳新美同盟条约》,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美国的忠诚与支持。2001年10月,澳大利亚宣布派军队参加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2002年10月的巴厘岛爆炸案,进一步改变了澳大利亚对地区安全形势的看法。
澳国内围绕对美同盟义务及国家安全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主要形成了以下两种看法:以保罗·蒂博和休·怀特(Hugh White)为代表的地区主义者坚持“本土防御”原则,认为澳大利亚国防军应该致力于防止任何通过北部岛屿的“海空通道”对澳本土进行的攻击。作为“大陆主义者”,地区主义者认为澳的国防政策应该由特定的地理条件决定,而不是受不断变化的政策、事态的影响。“9·11”事件所代表的跨国安全威胁只是暂时的,亚太地区传统的国家间安全问题更为重要。相反,在以罗伯特·希尔(Robert Hill)为代表的全球主义者看来,“本土防御”政策是不切实际的“地理决定论”,无法反映地区与全球变化了的现实。全球主义者以海洋主义为战略指导,他们认为,澳大利亚是依赖贸易的海洋国家和西方自由民主国家,“9·11”事件开启了新的全球化的安全议程,澳国家利益的实现需要发展一种有限的、但有效的远征力量的支持。(29)Michael Evans, “Security and Defense Aspects of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in Jefffrey D.McCausland, et al., The Other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at the Start of the 21st Century,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7, pp.281-282.
辩论的结果最终以全球主义者胜出。澳《2003年防务修订》指出,澳美同盟的威慑作用以及大国关系的缓和,意味着澳本土不太可能遭遇传统的军事袭击。相反,澳大利亚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因此,澳大利亚的安全不再局限于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而是具有全球性,海外行动成为新时期澳大利亚的主要作战任务。(30)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A Defence Update 2003, 2003, p.23, http://www.defence.gov.au/ans2003/Report.pdf [2022-03-27].这也标志着澳大利亚改变了过去20多年所奉行的“本土防御”战略,将国防战略重心转向参与美国领导的海外军事行动。2003年3月,在未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伊拉克战争。
2004年6月,澳联邦议会外交、国防和贸易委员会发布了首份《澳大利亚海洋战略报告》,指出专注于海空通道安全的国防战略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需求,未来“加强型”的海洋战略应专注于发展维护澳大利亚本土安全及地区内非领土利益的能力。(31)The Parlia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prepared by Joint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Defence and Trade, June 2004, p.69.在美国的支持下,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也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干预政策。早在2003年7月,澳大利亚派遣2000人组成的维和部队,前往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帮助当地恢复秩序。2006年5月,澳大利亚再派1400多人组成的维和部队帮助东帝汶平息因退伍军人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霍华德政府还积极响应小布什政府的“先发制人”策略,提出要对亚洲邻国的恐怖主义目标实施“先发制人”式打击。
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海外部署能力和军事投射能力与1999年的东帝汶危机时期相比都有了极大的提升。这也是自越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防军在海外行动最为活跃的时期。(32)参见李凡:《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28页。反恐合作为澳美同盟强化提供了新契机。除了配合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外,澳大利亚还借助美国的支持实现其海洋战略目标。一方面,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可以确保澳能够继续获得美国先进的军事情报和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的现代化转型。根据双方于2000年签署的《在国防装备和工业方面加强合作的原则协议》,澳大利亚获得分享美国高科技军事技术和装备的特殊地位,此前只有英国能够获此“殊荣”。另一方面,通过参与美国主导的海外军事行动,澳大利亚极大地提升了本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除了中、美、日、印外,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唯一一个能够在海外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33)William Tow, “Deputy Sheriff or Independent Ally? Evolving Australian-American Ties in an Ambiguous World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Vol.17, No.2, 2010, p.276.
(三)海洋战略的基础地位
2009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地区转移以及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的失败,海洋问题的重要性在澳大利亚的政策辩论中再次得到重视。(34)Michael Evans, “The Third Way: 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rmy Research Paper, No.1, May 2014, p.22.早在2008年9月,陆克文在公开演讲中提出:“澳大利亚需要提升海上军事实力,以保护澳大利亚的海上交通线安全,支持陆军的海外军事部署。”(35)Kevin Rudd, “Address to the RSL National Congress Townsville,”September 9, 2008,https://pmtranscripts.pmc.gov.au/release/transcript-16112 [2022-02-01].2009年公布的澳《国防白皮书》,明确将海洋战略作为未来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36)Albert Palazzo, “Maritime Strategy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Australian Army,”in Albert Palazzo, Antony Trentini eds., The Australian Army and Maritime Strategy, Canberra: Land Warfare Studies Centre, June 2010, p.5.,海上军事能力建设成为这一时期国防建设的重点,包括发展远程对陆攻击巡航导弹(LACM),以及将潜艇数量从6艘扩充为12艘等。这些都表明澳大利亚致力于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均衡、更为强大和更具灵活性的地区军事力量”,以区别于以往的“大陆主义”的本土防御战略。(37)Jack McCaffrie and Chris Rahman, “Australia’s 2009 Defense White Paper: A Maritime Focus for Uncertain Times,”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3, January 2010, p.71.
整体来看,经历冷战结束十余年的发展,澳大利亚逐渐确立了海洋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基础地位。与海洋战略发展相伴随的是澳大利亚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借助于反恐合作,澳大利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当双方的战略目标一致时,澳美同盟的存在对澳大利亚“自主防御”的实施具有重要助益。在这一阶段,面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同盟框架是支撑澳大利亚实现“自主防御”的最佳方式,自主防御与澳美同盟在实践中“不仅是可以调和的,还可以相互促进”。(38)参见李家成:《相互借重:冷战后美澳同盟不断强化的深层动因》,《美国问题研究》2010年第2期。但是,当双方的战略目标存在显著差异时,特别是在如何认识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澳美同盟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对澳大利亚的“自主防御”形成挑战。
2004年8月,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唐纳(Alexander Downer)公开表示:“如果台湾海峡发生冲突,澳大利亚没有义务根据《澳新美同盟条约》帮助美国协防台湾。”(39)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Relations,”China Brief, Vol.5, No.8, 2005,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china-factor-in-australia-u-s-relations/ [2022-02-21].这一表态引发了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2005年3月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面对美国方面的施压,澳大利亚转向了一种更为模糊性的立场。唐纳称:“如果台海发生冲突,《澳新美同盟条约》会被启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决定参战。”(40)Mohan Malik, “The China Factor in Australia-U.S.Relations,”China Brief, Vol.5, No.8, 2005,https://jamestown.org/program/the-china-factor-in-australia-u-s-relations/ [2022-02-21].尽管霍华德政府刻意在这一问题上保持战略模糊性,但是一旦中美关系发生变化,澳大利亚必然面临着在地区安全问题上选边站队的困境。
四、相互补充:“自主防御”的回归
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以及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在最大的经济伙伴和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之间,澳大利亚面临的选边站压力越来越大,其国防战略和海洋战略也随之进行了调整。
(一)从“亚太”到“印太”
2011年11月,作为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同意美国海军陆战队从2012年开始以轮换部署的方式进驻澳北部的达尔文港,到2016年驻军规模增加至2500人。这也是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澳大利亚最大规模的驻军行动。2013年1月,吉拉德政府发布上任后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将澳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从全球反恐向亚太地区转移,追随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的动机十分明显。(41)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the Cabinet, Strong and Secure: 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January 23, 2013, https://apo.org.au/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files/2013-01/apo-nid33996.pdf [2022-02-13].2014年6月,澳美签订《军力态势协议》,为美国在达尔文港轮换部署计划提供了法律基础,并规定了双方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的具体措施。
随着美国重返亚洲进程的加快,澳大利亚也开始重拾“印太”概念。(42)早在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就已经将“印太”思路贯彻到军事战略之中,提出建设“两洋海军”的构想。参见许少民:《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与前景》,《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22页。2013年澳《国防白皮书》正式将“印太”作为完整的战略系统进行描述。与冷战时期“前沿防御”战略强调“印太”的陆地属性不同,如今的印太战略更为强调“印太”概念的海洋属性,注重海洋战略的重要性。(43)参见许少民:《澳大利亚“印太”战略观:内涵、动因与前景》,《当代亚太》2018年第3期,第126页。《白皮书》明确提出:“澳大利亚需要一种海洋战略。地区军事现代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提升,削弱了澳大利亚广袤大陆的地理优势。”(44)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2013, pp.28, 30,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 [2022-02-13].与2009年《国防白皮书》相比,吉拉德政府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不将中国视为“对手”,认为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是中国经济增长导致的“自然和合理的结果”(45)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2013, p.11,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 [2022-02-13].,体现了澳大利亚在对美安全依赖与对华经济依赖之间力求平衡的政策。
但是,澳大利亚在追随盟国、扩展全球影响力的同时,“自主防御”的重要性却逐渐遭到忽视,特别是在国防预算受限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吉拉德政府时期,200多亿美元的国防预算遭到削减。特别是在2012年,澳大利亚的国防预算同比下降了10%,仅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6%,为1938年以来的最低值。(46)Mark Thomson, “We’re Still not Paying Enough for Defence,”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June 3,2013,https://www.smh.com.au/public-service/were-still-not-paying-enough-for-defence-20130603-2nkuy.html [2022-02-14].美国对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搭便车”的行为也颇为不满。2013年澳《国防白皮书》更是首份没有对“自主防御”概念进行“合理解释”的国防政策白皮书,不仅没有对澳大利亚应该在何种情况下采取自主防御进行必要的说明,反而将“自主防御”与地区安全合作联系在一起,强调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与其他国家加强地区安全合作。(47)Stephan Frühling, “The 2013 Defence White Paper: Strategic Guidance Without Strategy,” Security Challenge, Vol.9, No.2, 2013, p.46.要知道,“自主防御”原则最早就是澳大利亚为了应对澳美在地区安全危机问题上的利益分歧而提出的。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及美国对盟国需求的提升,澳大利亚不顾中澳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依赖性,选择通过强化澳美同盟的方式来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对华认知越来越负面。在2016年2月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中,澳大利亚声称中国的国防政策应该“更为透明”,应向地区邻国提供“保证”;强调澳中双方在一些地区和全球安全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战略利益”,特别是对中国在南海的陆域吹填活动“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感到担忧。(48)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16, pp.42, 44, 58, 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 [2022-02-21].为此,澳大利亚决定将“提升自身的军事实力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印太海洋安全形势”作为未来的国防政策重点,宣布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99亿澳元的国防预算,并承诺2020—2021年的国防开支达到GDP的2%。(49)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16, Canberra, 2016, p.24,https://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docs/2016-defence-white-paper.pdf [2022-02-21].澳大利亚还为海军提出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军事采购计划,包括将“柯林斯”级潜艇数量从目前的6艘增加至12艘,新增3艘“霍巴特”级防空驱逐舰、9艘反潜护卫舰以及12艘近海巡逻舰,并建造12艘新型潜艇。
在安德鲁·卡尔(Andrew Carr)看来,2016年《国防白皮书》表明澳大利亚的全球地位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变。由于国际战略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实力的相对下降,澳大利亚开始从“全球中等强国”(global middle power)降级为“地区强国”(regional power)。尽管从表面来看,“印太”概念的采纳似乎是地理范围的扩展,也即从之前的“亚太”到现在的“印太”,实际上却是战略范围的收缩,也即从之前的“全球”到现在的“印太”。(50)Andrew Carr, “No Longer a Middle Power: Australia’s Strategy in the 21st Century,”Focus Stratégique, No.92, Ifri, September 2019, p.27.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需要像地区内的中等国家一样,将国防资源集中在邻近地区,减少全球义务和全球范围内的同盟责任。澳大利亚不再像以前一样过度参与印太地区之外的海外军事行动。
(二)海洋战略转向
2020年7月,澳大利亚国防部公布了《2020年国防战略修订》及《2020年军力架构计划》,将印太地区作为澳大利亚的直接战略利益区和国防规划重点。相较于2016年《国防白皮书》,澳大利亚认为它的战略与安全环境出现明显恶化,包括中美战略竞争激化,大国的强势行为正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非传统安全威胁和“灰区行动”引发地区冲突,周边国家加强军事现代化等。澳决定放弃十年“战略预警期”(strategic warning time)的提法,认为它不再适合作为国防政策制定的基础。澳大利亚国防军需要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引发战争的“突发性危机”。莫里森甚至将现在的印太地区安全形势与20世纪30年代二战爆发前的欧洲相提并论。(51)Scott Morrison, “Address- Lunch of the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Prime Minister of Australia, July 1, 2020, https://www.pm.gov.au/media/address-launch-2020-defence-strategic-update [2022-02-17].
为此,澳大利亚决定在未来十年内投资2700亿澳元用于加强国防能力建设,其中2020—2021年的国防预算为422亿澳元,以兑现国防预算达到GDP2%的承诺。新增国防预算用于购买远程反舰弹道、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提升网络和信息战能力以及增设新型水下监控系统等,标志着澳大利亚国防战略的重大转变。澳学者称,《2020年国防战略修订》是冷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国防政策“最为鹰派的转向”。(52)Joseph Camilleri, “It’s Time to Strip ‘National Security’ of Its Sacred Cow Status.Part 1,” John Menadue, July 6, 2020,https://johnmenadue.com/joseph-camilleri-its-time-to-strip-national-security-of-its-sacred-cow-status-part-1/ [2022-02-18].在“防御性”话语的包装之下,莫里森政府扩充军备的行为,实际上带有“进攻性”本质。澳大利亚从美国购买的武器装备,明确用于未来帮助美国切断中国的海上航线,并限制中国受到攻击后的反击能力。(53)William Briggs, “Morrison Beating the Drums of War,”John Menadue, July 5, 2020,https://johnmenadue.com/morrison-beating-the-drums-of-war/ [2022-02-18].
在新版国防战略的背景下,澳大利亚的海洋安全战略也发生了转向,主要呈现出两大特点:首先,澳大利亚表示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来维护自身的安全”,发展“独立的威慑能力”,凸显澳希望发展独立自主的国防能力,减少对盟国的安全依赖。(54)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2020 Defence Strategic Update, p.27,https://www1.defence.gov.au/strategy-policy/strategic-update-2020 [2022-02-17].澳大利亚的战略定位开始从一个主要作为支持联盟行动的“防御性力量”,向依赖于自身的常规“威慑性力量”转变。(55)Euan Graham, “Australia’s Serious Strategic Update,”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July 3, 2020, https://www.iiss.org/blogs/analysis/2020/07/apacific-australia-defence-update [2022-02-19].澳学者认为,这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制定中“主权”的回归。(56)Richard Brabin-Smith, “The Return of Sovereignty to Australia’s Defence Strategy,” East Asia Forum, August 11, 2020,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8/11/the-return-of-sovereignty-to-australias-defence-strategy/ [2022-02-19].尽管澳大利亚仍然强调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随时可能抽身离开的情况下,澳大利亚越来越需要依赖于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本土安全。其次,澳大利亚的国防重点转向“直接利益区”(immediate region),也即“从印度洋的东北部,经过东南亚的陆地和海洋,到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南太平洋”。如前所述,冷战结束以来,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如今,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重点越来越集中在周边地区,对“参与海外军事行动的兴趣逐渐减退”。此前,莫里森政府在决定参与美国组织领导的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犹豫。(57)Stephen Dziedzic, “Australia’s New Defence Strategy Unveils a Significant Strategic Shift in Foreign Policy to Meet New Threats from China,” ABC News, July 2, 2020,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7-02/australias-new-defence-strategy-strategic-shift-foreign-policy/12412650 [2022-02-20].
“蒂博报告”的起草者保罗·蒂博认为,无论是从地缘战略范围还是军力结构重点来看,澳大利亚的海洋战略都在重回20世纪80年代的“本土防御”,将“直接利益区”作为澳国防政策的重点,区别于此前的全球主义和远征军事行动。(58)Paul Dibb, “Is Morrison’s Strategic Update the Defence of Australia Doctrine Reborn?”, ASPI, July 9, 2020,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is-morrisons-strategic-update-the-defence-of-australia-doctrine-reborn/ [2022-02-19].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一方面是因为印太地区地缘战略重要性的提升,另一方面是因为印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过去,只有在相对安定的周边安全环境下,澳大利亚才有可能在远离澳大利亚本土的地区支持盟国作战。(59)Peter J.Dean, “2020 Australian Defense Strategic Update: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The Diplomat, July 22,2020,https://thediplomat.com/2020/07/2020-australian-defense-strategic-update-the-revenge-of-geography/ [2022-03-15].如今,这一安全环境已经发生变化。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的实力出现相对下降。为了应对中美关系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周边国家纷纷加强军事部署和军备开支,地区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地区国家的军事现代化,也逐步消解了澳大利亚国防军的技术优势,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将安全重点集中在周边地区。
(三)澳美同盟的强化
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是,随着大国战略竞争的升级,澳大利亚“在联盟框架下实现自主防御”的战略已经发生了倾斜,过去强调“自主防御”,如今强调“在联盟框架下”,对美军事依赖进一步强化。(60)Kim Beazley, “The Alliance-dependence Grows as Our Options Narrow,” ASPI, May 1, 2018,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lliance-dependence-grows-options-narrow/ [2022-02-21].2021年4月28日,澳大利亚宣布花费7.47亿澳元升级澳洲北领地的四个军事基地,并扩大与美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同年9月15日,澳英美宣布建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加强三方在印太地区的安全合作和技术共享。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英将帮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
2021年11月12日,澳英美三国签署《海军核动力信息交换协议》,该协议首次允许美国和英国与第三国分享其核潜艇机密。这也是自1958年美国与英国分享核潜艇技术以来再次与盟国分享该技术,澳大利亚也将成为全球第7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的战略优势,再加上澳大利亚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符合美国强化岛链包围圈的意图,从而遏制对手的远洋作战能力,特别是抵消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61)参见胡峰笙:《美英澳军事同盟与美国战略转向》,《世界知识》2021年第22期,第13—14页。澳总理莫里森公开表示:“中国在进行大规模的核潜艇建造计划,澳大利亚也有权利基于国家利益这么做。”(62)“Australia Shrugs off China Anger on Nuclear Subs,”Yahoo Finance, September 16, 2021,https://finance.yahoo.com/news/australia-shrugs-off-china-anger-025333693.html [2022-01-21].
2022年4月5日,美英澳三国领导人举行了电话会议,评估了AUKUS联盟的进展,称对澳核动力潜艇计划目前取得的成果感到满意,并承诺在高超音速和反高超音速导弹、电子战能力和信息共享领域开展新的三边合作。(63)“AUKUS Leaders’ Level Statement,”The White House of United States, April 5,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4/05/aukus-leaders-level-statement/ [2022-4-18].作为美国推进其“印太战略”的重要举措之一,AUKUS不仅仅是一项核潜艇协议,它也是拜登政府强化全球联盟战略的重要步骤,反映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以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Kurt Campbell)称AUKUS 是美英澳三国“决定性的”针对中国的努力,将成为拜登政府时期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64)“In Conversation: Kurt Campbell,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Coordinator,” Lowy Institute, December 1, 2021,https://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conversation-white-house-indo-pacific-coordinator-kurt-campbell [2022-02-25].
AUKUS协议凸显出大国战略竞争的新重心在于海洋领域。美国担心,其在东亚近海等区域的海上主导优势将逐渐被中美间的均势所取代,为此需要拉拢盟友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制衡。(65)参见胡波:《全球海上多极格局与中国海军的崛起》,《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6期,第15页。澳之所以放弃2016年与法国达成的常规潜艇计划,不惜牺牲与中国的关系而扩大与美英的安全合作,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更为先进的武器和动力系统,而且是通过纳“投名状”的方式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圈的核心成员国,从而获得更高的同盟地位和更稳定的安全保障。2021年9月21日,在联大会晤期间,拜登表示“没有比堪培拉更亲密的盟友了”,莫里森则回应称澳美“一直保持着有利于自由国际秩序的伙伴关系”。(66)“US has ‘no closer ally than Australia’, Biden Says after Aukus Pact,”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1,2021,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sep/21/us-has-no-closer-ally-than-australia-says-biden-after-aukus-pact [2022-03-17].
澳大利亚的终极担忧是,实力和意愿的下降,会导致美国在未来将力量撤出亚洲,从而迫使澳大利亚不得不单独面对亚太地区的强国——中国。出于对被“强大的盟友”抛弃的担心,澳大利亚投入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通过强化军事与安全合作,以及紧密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澳大利亚进一步强化了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投入了更多维持同盟的“沉没成本”。(67)Thomas Wilkins, “Re-assessing Australia’s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Age of Trump,” Security Challenges, Vol.15, No.1, 2019, p.29.与此同时,面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美国实力出现下降以及推行全球收缩战略的现实,澳大利亚必须加强独立自主的国防能力。在如何应对中国的问题上,“自主防御”与依赖盟国形成了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效果。
五、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内在悖论
从“自主防御”的提出、忽视到“回归”,澳美同盟与“自主防御”的关系也经历了相互冲突、相互借重,再到相互补充的过程。历经半个世纪的发展,澳大利亚的“自主防御”政策最终还是选择强化对盟国的依赖,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合作来实现自身安全,“与强国结盟”仍然是澳海洋战略的关键性因素。正如澳学者斯蒂芬·弗鲁林(Stephan Frühling)所言,尽管自1987年以来澳大利亚一直试图寻求国防力量实现“自主防御”(self-reliance),但澳大利亚从未追求、也不可能实现国防力量的“自给自足”(self-sufficient),因为澳大利亚需要依赖盟国的武器装备、情报信息,以及后勤和其他方面的支持,1987年以来的《国防白皮书》都明确强调了这一点。(68)Stephan Frühling, “Australian Defence Policy and the Concept of Self-Relianc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68, No.5, 2014, p.536.
尽管澳大利亚认识到,它的海洋战略需要随着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当前的调整仍然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和冲突。
首先,澳大利亚错误地认为,澳中关系紧张体现了中国“强势”的外交政策,因此选择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来对冲中国崛起的风险。(69)Graeme Dobell, “The Evolution of Australia’s China Challenge,” ASPI-The Strategist, May 18, 2020,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the-evolution-of-australias-china-challenge/ [2021-03-20].殊不知,正是澳大利亚急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支持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政策,破坏了中澳双方的政治互信,才导致了双边关系的持续下滑。2018年8月,澳大利亚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和中兴参与澳大利亚的5G网络建设。澳大利亚也成为全球首个禁止中国网络供应商进入其5G市场的国家。2020年3月份,澳大利亚在疫情问题上大搞政治操弄,成为最早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和全球大流行进行独立调查的国家。同年7月9日,莫里斯公开批评中国在香港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澳大利亚也成为继加拿大之后第二个宣布暂停与香港的引渡协议的国家。2021年11月,澳国防部长达顿公开表示,如果美国采取行动“保卫台湾”,澳大利亚不支持美国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AUKUS协议对澳大利亚而言,更像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赌注”,认为美国“将会在与中国的大国战争竞争中胜出,并继续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性和稳定性力量”。(70)Damien Cave and Chris Buckley, “Why Australia Bet the House on Lasting American Power in Asia,”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7, 2021,https://www.nytimes.com/2021/09/16/world/australia/australia-china-submarines.html [2022-02-11].莫里森总理更是将与美英的核潜艇协议视为“永久伙伴关系”(forever partnership)的象征。(71)“PM hails new subs deal as ‘forever partnership’,”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eptember 16,2021,https://www.afr.com/politics/federal/pm-hails-new-subs-deal-as-forever-partnership-20210916-p58s3t [2022-03-17].但是,在美国实力下降、实行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削弱了美国的联盟信誉,拜登政府虽然坚持多边主义和依赖盟友的传统路径,但是其倡导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并未脱离“美国优先”的老路,在阿富汗撤军、AUKUS协议以及俄乌冲突事件上表露无遗。
其次,澳大利亚过于高估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认为在大国战略竞争时代可以通过与中国对抗的方式树立一种“独立自主”的中等强国榜样,结果却适得其反。一个国家的安全,不仅取决于它的军事实力,也取决于它塑造国际环境的能力。过去,澳大利亚曾积极扮演“中等强国”的角色,推动多边主义,在倡导核裁军和消除化学武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倡议建立亚太经合组织,以及坚决反对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帮助澳大利亚迅速融入亚太地区议程。但是,选边站和一边倒的国防政策,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国防战略自主性和外交政策影响力。
澳大利亚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扩充军备,以一种“针对”(against)地区而非“联合”(with)地区的方式寻求国家安全,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和军备竞赛,反而让澳大利亚陷入了一个更加不安全的境地。(72)Sam Bateman and Anthony Bergin, Sea Challenge: Advancing Australia’s Ocean Interests, ASPI Strategy report, March 2009, pp.52-53.这也构成了澳大利亚海洋战略的安全悖论。澳前总理保罗·基廷批评AUKUS协议强化了澳对盟国的依赖,称“200年过去了,澳大利亚仍然试图通过英国来寻求澳大利亚在亚洲的安全”。(73)“Former PMs Split on Security Pact with US and UK,”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September 16,2021,https://www.afr.com/politics/federal/former-pms-split-on-security-pact-with-us-and-uk-20210916-p58s54 [2022-02-26].战略错位和利益捆绑,严重限制了澳大利亚发挥地区影响力的能力。近些年来中日关系和中印关系相继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中澳关系仍然处于“冷冻期”,双边战略与经济对话也被无限期暂停。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互补性很强,澳试图以牺牲经济利益的方式追求所谓的“国家安全”,结果可能得不偿失,盟国却从中受益。据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的统计,2020年下半年澳大利亚对华出口(铁矿石除外)总额比2019年下半年减少了40%。(74)Jacob Atkins, “The Costly Toll of Australia’s Trade War with China,”Global Trade Review, March 31,2021,https://www.gtreview.com/news/asia/the-costly-toll-of-australias-trade-row-with-china/ [2022-01-21].在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期间,澳大利亚对华红酒出口下跌了45%,即使对英国、新加坡等地的红酒出口增长了12%,也远不能弥补失去中国这个最大的红酒出口市场的损失。(75)“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Wine Exports to Mainland China are Way Down, But It Remains the Top Market,”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ly 22, 2021,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41996/china-australia-relations-wine-exports-mainland-china-are-way?module=perpetual_scroll&pgtype=article&campaign=3141996 [2022-03-21].在煤炭方面,自2020年11月份开始,中国已连续六个月没有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对华煤炭出口却屡创新高,从2021年1月份的27.9万吨上升到4月份的97.4万吨。(76)“China-Australia Relations: US Coal Continues to Fill Void Left by Ban on Australian Exports, Canberra Report Say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une 30, 2021,https://www.scmp.com/economy/china-economy/article/3139209/china-australia-relations-us-coal-continues-fill-void-left [2022-01-22].
六、结 语
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处于深度的调整与重构中,澳大利亚在国际新秩序中的地位和利益,不可能仅仅依靠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关系就能实现。过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将自身的安全利益与美国的霸权利益捆绑在一起,反而会加剧同盟牵连的风险,使自己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与对抗中,推升大国战略竞争与军事冲突的风险。要想实现真正的“自主防御”和国家安全,发挥地区强国的影响力,澳大利亚需要摆脱仅仅从澳美同盟的思维框架看待问题,以理性的视角正视中国的崛起,减少在国际问题上对美国的战略依附,从国家利益而非同盟利益出发,制定本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
事实上,澳大利亚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之间如何解决分歧。霍华德政府时期,受益于中美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澳大利亚得以在中美之间维持平衡的外交关系,并为扩大自身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反,过于高估自身实力,急于选边站队,只会限制本国的外交活动空间,最终损害自身利益,沦为美国的“副警长”。作为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第三方,澳大利亚应该发挥建设性的沟通与桥梁作用,促进亚太地区整体的和平与稳定。最为理性的选择是保留所有选项,避免加入一方来遏制另一方。即将到来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也许会给中澳关系的转圜带来新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