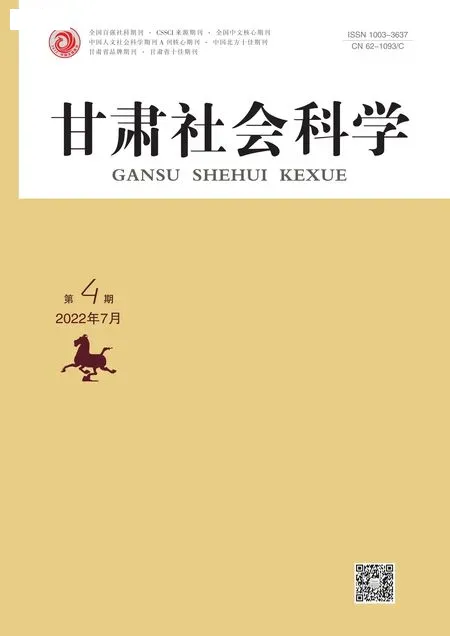秦文化与中国“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欧阳坚
(政协甘肃省委员会,兰州 730030)
提要: “大一统”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夏商西周时期随着“中土”“中国”“天下”“海内”和华夏四夷等观念的流行而萌芽。春秋以来,以儒家为代表的诸子学说系统提出了以仁政王道和恢复周礼为特征的大一统国家观。后经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和吕不韦整合诸子学说的创新改造,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战国晚期历代秦王特别是秦始皇将其创造性运用于政治实践,促进秦国迅速崛起和完成统一,进而创建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由此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兼容开放和与时俱进的秦文化及其特有的心怀天下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文化观、富国强兵的发展观和奋发有为的事业观,正是“大一统”思想付诸实施和成功的主导力量。
所谓“大一统”,是先秦以来列国政治家和各派学者对未来“中国”的理想设计和理论建构,它以“天下”“海内”疆域的统一,华夏与四夷多民族的统一和文化认同为主要追求。这一思想源于三皇五帝时代,萌芽于夏商西周三代,成形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后期“七雄”中的秦国通过兼并战争,将这一思想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并获得成功。因此,秦王朝的建立,让追求统一成为历史上中国发展的大势和正道;由此而上升为主流文化的秦文化,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制度和文明。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学者顾颉刚第一次明确提出秦朝为中国统一之始:“中国的统一始于秦,中国人民的希望统一始于战国;若战国以前则只有种族观念,并无一统观念。看龟甲文中的地名都是小地名而无邦国种族的名目,可见商朝天下自限于‘邦畿千里’之内。周有天下,用了封建制以镇压四国——四方之国——已比商朝进了一步,然而始终未曾没收了蛮貊的土地人民以为寰宇统一之计。……到战国时郡县制度普及;到秦并六国而始一统。”[1]随着秦史研究特别是秦早期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秦文化与“大一统”之关系受到学界的关注。这是秦文化研究走向深化的反映。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等学者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秦文化研究序幕,王国维先生对“秦公簋”铭文作了考释,在《秦都邑考》中对秦人都邑作了考证[2]。20世纪30年代,苏秉琦先生等学者对宝鸡周、秦、汉墓葬进行了三次发掘,综合考察了墓葬葬俗文化,第一次将秦文化从周文化和汉文化中单独区分出来[3],开启了秦早期历史及其文化研究的先河。这在当时国内部分学者主张文化“全盘西化”的情况下,具有重大的文化和学术意义。20世纪40年代,陈秀云首次提出了“秦文化”概念,认为秦文化延续了夏商周文明,承袭了夏商周文化,既有地方色彩,又富有中原气息,仍然是“中国本位文化”。其观点颇具洞见,惜未受到学界重视。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陕西一批东周至战国墓葬的考古挖掘,对秦墓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受到学术界关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以来,秦都雍城、咸阳、栎阳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等重大考古发现,掀起了研究秦文化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系通过在甘肃地区的考古发掘有重大收获,揭开了秦文化渊源讨论的新篇章。20世纪90年代,遭受严重盗掘的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经抢救性清理发掘,为研究秦人历史文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21世纪初,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机构联合启动早期秦文化调查、发掘与研究课题,先后对清水李崖遗址、天水董家坪遗址、甘谷毛家坪遗址及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西山坪、鸾亭山、六八图、四角坪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考古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为我们探讨秦人早期历史和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考古佐证资料。
伴随秦早期文化重要遗址的不断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秦文化特别是秦早期文化研究成为研究热点。秦文化的概念、来源、内涵、特点和影响等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王子今认为,秦文化有区域文化的涵义,早期的秦文化属于部族文化的性质。秦文化突变深受法家思想影响,上升为秦王朝统治的主体文化和主导文化。秦文化既有积极奋进的、迅速崛起的、节奏急烈的文化风格,又有鲜明的创新理念、进取精神、开放胸怀、实用意识、技术追求等特点,具有积极因素[4]。雍际春认为,秦早期文化是一种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和进取精神、好勇尚武精神、强烈的兼容性和博大的开放性,质朴实用的风格四大特点[5]。艾荫范认为,秦国主动向中原列国学习,同时吸收北方草原文化精髓,注重继承创新,对不适宜发展的制度、习俗和观念等进行了系统革新[6]。这些代表性观点,不仅对秦早期文化的渊源、面貌、特征和影响进行了梳理和揭示,拓展和深化了秦史、秦文化研究,而且推动秦文化研究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相联系,并从长时段、大视野和微观化加以审视,标志着秦文化研究迈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新境界。
随着秦文化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开始对秦“大一统”的现象和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大一统”的概念、渊源、内涵、流变等作了深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子今、晁天义、陈跃、路高学等学者的观点。王子今先生先后发表《〈史记〉“天下一统”“海内一统”》[7]、《“一天下”与“天下一”:秦汉社会正统政治意识》[8]、《秦统一局面的再认识》[9]等系列文章,对“大一统”思想的来源和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传统正统意识和秦统一等进行了考证梳理和积极评价。晁天义认为,对于“大一统”的理解,春秋晚期与西汉时期不尽相同,东汉时期与西汉时期也相去甚远,晚近以来与此前的理解结果则仅有形式上的相似之处。尽管每一种理解都自认为最符合“大一统”的本义,但是其实都直接或间接、明显或隐晦地表达了理解者所处环境的要求和理想,因而带有特定的时代印记[10]。陈跃认为,“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其内涵是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自秦以后,疆域一统和“华夷分治”成为汉至明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清代对“大一统”进行全新的阐释,突破了此前的“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突出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从而实现了“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11]。路高学认为,先秦道家为秦汉“大一统”的建立与巩固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论根基,先秦道家的“一”既是万物的本根,也是治身的标准,又是治国的方式,还是理想的天下秩序;既为法家主张的“大一统”政治秩序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又为新形势下儒家“大一统”伦理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宇宙论的基础[12]。王震中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历代王朝都把统一规模作为当时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在思想意识上仍旧是统一的,割据势力往往把自身说成是正统,把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从秦汉上溯到春秋战国,作为社会的转型期,其“大一统”思想,既有人们对于统一的理想,更有夏商西周三代王朝国家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结构这一历史渊源[13]。不难看出,学术界关于“大一统”问题的研究,追根溯源无不从秦文化和秦统一切入,则中国传统“大一统”思想,其理论创新和政治实践均与秦文化和秦统一密不可分。
由此可见,“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大一统”思想成为秦文化强势崛起的重要内容。秦文化不仅推动秦人从边陲弱小部族一步一步走向强大,而且在转型发展中秦文化既上升为主流文化,也在完成统一中实现了“大一统”政治实践的成功。“大一统”思想的成功实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以华夏正统为政治合法性依据的追求。本文就此从“大一统”思想的渊源、成功实践、理论基础和时代意义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先秦时代:“大一统”思想的发韧与奠基
“大一统”理想中国的政治诉求,渊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周易·系辞下》认为“天下之动,贞失一者也”。这说明三皇之一的伏羲时期,已经有了天下的时空统一和整体认识观念,有了天人合一、天下一体的思考方法,这成为天下一统的思想萌芽。从三皇部落联盟到五帝酋邦古国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成果及相关文化都能清楚地看到,早期华夏文明与文化的发展,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并呈、趋于一体的发展态势。而且,以中原地带和华夏族群为核心,农耕文明优势对周边地区和人群产生极强的吸引力、辐射力和感召力。从尧舜禹到夏商西周,这个共同体通过分封、盟会、朝见、征伐等措施,一方面,强化和凸显了自己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随着核心意识的强化进而萌发了“大一统”的政治追求。如夏启通过“钓台之会”以号令诸侯;商又称为“中商”“中土”,以四方诸侯为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商王、周王都自称为“余一人”;周王又自认为是上天之子——天子,并有了华夏居中,四夷环绕四方的华夷一统观念,由居中的华夏即“中国”和周边的四夷共同构成了天下,而天下为周王所有。
“天下”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即所谓“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诗·小雅·北山》又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见“天下”观念与追求和认同统一的意识紧密相连。春秋以降,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四夷内侵,中原华夏族民族意识空前高涨。齐桓公首倡“尊王攘夷”,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号令诸夏,欲“霸诸侯,一匡天下”。孔子作《春秋》主张“大一统”,强调夷夏之辨首先在文化,而且夷夏可以互变。并对“天下”的内涵做出多重解释,《礼记·大学》认为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中庸》记载“子曰: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又说 “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主张“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下天下畏之”;《礼记·礼运》则首倡大同学说。孔子对理想天下的设想和描述,实质上就是对“大一统”国家的美好憧憬,并对儒家及诸子思想产生巨大影响。
进入战国时期,周室已沦为诸侯大国的附庸,失去了政治上一统于周的法统价值。于是,思想家们纷纷探讨政治统一、华夷一统的新路径,赋予“大一统”新的内涵。在这一时期成书的儒家经典和诸子学说中,《周礼》主张政治上建立强大的一统王朝;《管子》提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与中国诸侯“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尚书·禹贡》设计出理想中“大一统”的“九州”说和“五服”说;孟子提倡仁政和王道,主张大国“王”天下,强调“用夏变夷”;荀子提出“一天下”主张;邹衍创立“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墨子·尚同》提出“一同天下”;《庄子·天道》主张“一心定而王天下”。特别是《春秋》公羊学说则在继承儒家及孟、荀“大一统”思想的基础上,对“大一统”做出权威解释:“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解释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14]进而提出《春秋》所载242年为“三世”说,即早期据乱世为“内其国而外诸夏”;中期升平世为“内诸夏而外夷狄”;后期太平世是“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大小若一”。从而将“大一统”与进化的历史观有机结合,标志着“大一统”理论业已系统化,并对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产生积极影响。《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15]董仲舒进一步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强调共同性的“大一统”已成为人们国家观念的基本认知信条。
不难看出,在诸子学说和儒家经典中,天下——中国——“大一统”已成为一个天然一体的政治上、文化上、道德上的国家统一观念。而且,这样的中国就是三皇五帝,特别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圣王明主政治理想的继承发展。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室衰微和群雄争霸,列国纷纷变革图强,而各国民众饱受几百年的战争和动荡之苦,渴望停止纷争,实现天下太平与天下一统。由此可见,“大一统”既是中国早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成为周秦之际社会上下共同的政治诉求。
三、秦统一六国:“大一统”思想的成功实践
在春秋战国趋于成熟的“大一统”,是以儒家仁政王道理念为核心,以复兴西周礼制为旨归的思想。在法家创新改造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军事和霸道为途径,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并被秦国运用于建立“大一统”王朝的政治实践。
在大国争霸中,后来居上的秦人在法家学派创新“大一统”理论的基础上,迅速将其运用于实现统一的政治实践。以商鞅变法为例,其全方位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为秦国强势崛起和“并吞寰宇”打下坚实基础。商鞅主张“任法而治”,通过“壹赏、壹刑、壹教”,将强化君主王权和实现国家统一有机结合。秦相吕不韦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形式,以儒家政治思想为主体,吸收法、墨、名诸家思想,集先秦诸子学说于一体,主持编写了集大成式的《吕氏春秋》,试图在整合各家学说基础上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帝国提供完整的治国方案,在《有始览》中认为“乱莫大于无天子”[16]299。在《孟秋纪》中提出“胜者为长,长则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16]158。在《仲春纪》中主张统一国家应该兼容华夷,“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16]54。吕不韦还发挥五德终始说,提出统一王朝周是火德,结束春秋战国分裂而再度实现统一的新王朝将是水德,为秦的统一提供理论根据。据统计,《吕氏春秋》中“天下”一词出现达281次;另一位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韩非子》中“天下”一词出现267次①。韩非继承诸子中进化发展的历史观,主张对社会政治问题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提出“强匡天下”,主张“夫凡国博君尊者,未尝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于天下者也”;坚持性恶论为基础的暴力论,对儒家仁义道德学说持批判态度,视人际关系为利害关系,进而提出一套“尊主安国”的君主集权专制理论体系,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7]。韩非以法、术、势相结合的法家理论为核心的君主专政政治学说,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巩固政权、结束中国长期动荡分裂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政治需要,其思想被秦王政全盘吸收,并成为秦国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李斯在辅佐秦始皇的治国实践中,明确提出“师今”,反对“师古”,主张以现实作为制定政治和法律规范的出发点,用国家法律来判断一切。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主张君主要独揽一切大权,并不择手段地防止大权旁落,达到“主尊严”“国家富”“君乐丰”[18]2539-2563的效果。可见,法家学派在继承诸子天下、一统等观念基础上,在强化君主集权的同时,也吸收和融合了各家理论之长,形成儒表法里、以道为根,更具操作性和现实需要的新“大一统”理论。
秦王嬴政正是在以上“大一统”学说和法家思想的基础上,杂糅法、道、墨、兵、阴阳五行、神仙家等思想,以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创造性运用于统一战争和“大一统”秦王朝的制度构建,“奋六世之余烈”,仅十余年就扫灭六合,同时远征南越,西北斥逐匈奴,实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建立统一的天下。为了巩固“大一统”王朝,秦始皇通过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实行法制等政治措施,统一度量衡和车同轨等经济措施,改革家庭制度和编户制度等社会管理措施,书同文、行同伦和匡饬异俗等文化措施,南开五岭设三郡、北击胡貊修长城、移民实边等军事措施,实行华夷一体的民族融合政策等,创建和确立了一整套多民族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体制和制度,并构建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根基,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文化传统。因此,毛泽东主席曾说“百代都行秦政法”[19]。
总之,“大一统”秦王朝的建立,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不仅承上启下,而且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秦国的统一进程,并非商灭夏、周代商那样的朝代更替,而是改变分封制奴隶制的国家制度,建立了郡县制封建制的国家制度,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是一次打碎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国家再造,是一次上自君王、下至百姓对组织管理机制的变革,是社会阶层建构和社会运行模式创新基础上的国家重建。因此,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更替,不论统一政权还是分裂政权,或者少数民族政权,对入主中原和正统的追求,正是“大一统”传统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从此,视“大一统”为常态,分裂、动荡为非常态,已成为国人评价历代王朝得失和历史走向的基本标准。
四、秦文化:“大一统”思想的精神支撑
秦文化是伴随秦人漫长曲折的兴起和建国而生成,又随秦国的发展和时代环境变化而转型勃兴,并在兼容博采、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中,发展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是在继承上古以来一统国家治理观念基础上,学习借鉴六国文化和戎狄等少数民族文化,逐步创造了立足统一政治追求的政治文化、官僚文化、法律文化、农耕文化、尚武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等,成为秦国实现和巩固“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精神支撑。
循着秦人西迁和兴起的时空轨迹不难发现,秦人的历史和发展道路极为独特。它既有夏商时代大起大落、艰辛备尝的西迁历史,又有西周近三百年在陇右西垂与西戎交错杂处中族体形成、重新兴起建国的独特经历。如秦人在陇右的兴起与发展就深深打上了甘肃地域、人文色彩。如陇右复杂多样的山川地貌和林茂草丰、环境良好的自然条件,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诞生于此和距今八千年前的大地湾文化以及原始农牧业的起源,到马家窑彩陶文化大放异彩和齐家玉文化与青铜文明的肇启,以氐羌西戎为主的畜牧文明等人文氛围,为秦人的兴起和文化创造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嬴秦入居天水后,与西戎既斗争又融合,立足固有传统,以顽强的适应能力因地制宜,迅速发展农牧业以壮大经济。非子以善养马著称,被周孝王征召在汧渭之间为周室养马大获成功,因功封为附庸,赐邑于“秦”,而其“秦”之称号即源于毛谷草的禾本植物[20]。这正是秦人因地制宜,发挥原有懂鸟兽之言的优势,既善于畜牧又长于农业,在天水入乡随俗发展农牧经济的典型反映。嬴秦以灵活的变通能力,主动学习先进的周文化和西戎畜牧文化,广收博采为我所用。如秦人在文字、文学艺术、礼仪制度、葬仪制度等方面,广泛吸收以周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21]。秦文化中的屈肢葬、金器、铁器、动物纹样、铜鍑和短剑的使用、墓葬壁龛与围墓沟,来自陇右土著西戎。尤其是贵族墓的壁龛习俗,直接来源于陇山两侧的羌戎文化[22]。从西周中期清水李崖秦邑遗址墓葬多商式风格陶器与葬俗并有个别西戎寺洼文化陶器出土,到礼县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西山坪等秦文化遗址与西戎寺洼文化遗址的交错分布,再到春秋时期甘谷毛家坪遗址秦文化与戎族墓葬共存的演化历程,体现的正是秦与西戎文化碰撞和交融发展的实际。秦与西戎是甘肃地区有据可考的最早开发者和甘肃地域文化的开创者。秦穆公霸西戎之后,陇右等地被秦人经营为稳固的战马基地,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多难的部族命运和特殊的生存发展环境,赋予秦人发展和文化创造极为深刻的影响。于是,根植于陇右独特的环境和人文氛围而生成的秦文化,以华戎交汇、农牧并举为特征,具有意志坚定、功利进取、开放包容、尚武坚毅、富于创新等文化特质。成为持久影响秦人、秦国崛起发展的精神基因和性格底色,引领秦人逐步崛起,以穆公霸西戎为标志,秦国进入诸侯大国行列。
进入战国时期,在群雄角力和竞相变法改革以图强大的浪潮中,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以富国强兵、移风易俗、改造社会为目标,确立法家学说为治国理论和根本方法。采取推行县制、迁都咸阳等措施,打破了旧有的政治生态,为君主专制和政令畅通奠定了基础;经济和军事上通过农战政策、军功授爵制度,使富国强兵大见成效;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广纳六国贤能之士,形成布衣将相竞相效命国家的局面,为变法图强提供了人才保障[23]。奖励耕战和移风易俗的推行,收到了“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良好效果[18]2234。由《史记》卷六八《商君列传》可知,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18]2234。以迁都咸阳为例,咸阳作为秦国、秦朝都城历时144年,正与秦国强大和实现统一相一致。其都城布局结构和设计理念在继承传统基础上更多地进行了创新和超越,体现了法家思想和“法天”思想,形成了以“新”“尊”“博”为特征的“大一统”大国都城的新气象[24]。因此,咸阳的设计和建设正体现了以超越商周王城和列国国都,适应王权至高无上为规划设计追求,“履至尊而制六合”的王权尊严,并以宏大广阔、气势恢宏凸显其博大胸怀和气质。商鞅变法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也推动秦文化华丽转型。转型后的秦文化在保持原有特质的基础上,具有了崇法重刑、耕战为本、军功授爵和实用功利的新特点,并激励秦国出现以令行禁止的法治精神、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家国一体的天下胸怀和坚忍不拔的坚强意志为表征的社会新风尚。借此文化优势,从秦孝公到秦王嬴政七代秦人致力秦国强大,完成统一,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五百多年列国争霸、战乱纷争的动荡局面,“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
不难看出,一部秦文化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秦人上承三代文化之精粹,兼容西戎文化之养料,博采列国文化之长,统摄融汇农耕、游牧两大文明于一体,多元融通和创新升华的文明结晶。这种文明演进的背后,既有服务于天下一统的先进理念的支撑,更有服务一统的国家制度的支撑,并最终以秦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实现了国家统一和文化的整合,“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这种“别黑白而定一尊”,主要通过强硬的手段推行有关政策和理念,实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统一。尤其是“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为“大一统”打上了鲜明的标志,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一体延续,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既多元绽放,又持续汇入主流,形成了基于统一的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秦文化是这一进程的主导力量。
五、传承创新:秦文化的历史启示与时代意义
秦人、秦国、秦王朝虽然都成为过往,但秦人及秦文化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新阶段,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存和精神财富。古往今来,人们不禁会问后来居上的秦人何以能够在群雄争霸中脱颖而出,终结动荡纷争的旧时代,开创“大一统”的新时代。一般而言,追求统一的政治抱负,积极进取的先进文化,顽强拼搏的民族性格,始终重视军事实力,比较彻底的变法改革等,无疑是助其成功的主要因素。但从更深层而论,还有以下四点非常重要。
(一)心怀天下的价值观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都不能缺失核心价值观,秦人从大国附庸到历史边缘,由历史边缘到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主角,进而打碎旧秩序,建立新世界,其始终不坠的是顺应历史趋势和时代呼唤,心怀天下,对以“大一统”为标志的核心价值观的坚守。从秦人建国之际秦襄公僭越礼制,以天子之礼设畤祭天,到秦穆公以“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自居,从秦武王举鼎绝膑到秦王嬴政伏六王而定天下,能看到其问鼎中原、一统天下之志由来已久、一脉相承,而且付诸实践,咬住青山不放松,聚沙成塔、久久为功,终获成功。
(二)与时俱进的文化观
秦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秀的特质,其特色和优势来自秦人宏阔的视野、开放的心态、进取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在秦文化中,对周文化的继承无疑是其主体成分,但在秦国社会,并未因此而受周礼束缚趋于保守。如血缘宗族和世袭贵族对秦国政治的影响远较东方六国为弱,故以地缘为主的郡县制在秦国、秦王朝得以推行。再如后起的秦人虽然在文化上并没有产生像东方六国那样的大思想家和重要的学术流派,但却在重用六国人才并将新的思想文化创造性运用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发展的社会实践方面,不仅遥遥领先,而且非常成功。究其根本,就在于秦国形成了因地制宜、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文化观,由此确立了其文化始终能够趋向先进的优势地位。
(三)富国强兵的发展观
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和兴盛,既需要正确的道路方向选择和先进的治国理念引领,也需要强大的国力支撑,二者缺一不可。秦国在致力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始终重视经济发展和技术应用,兴修水利,推广铁器、牛耕,以农为本,奖励耕战,是秦国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有力支撑。特别是到战国后期,华北平原、关中平原、四川盆地三大经济区秦国独占其二,而且还拥有陇右等西北战马基地,其国力已远超东方六国,《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富十倍天下”。可见,国力雄厚、兵强马壮是秦国实现和巩固“大一统”的根本物质基础。
(四)奋发有为的事业观
坚忍不拔、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是秦人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也是秦人上下一心、埋头苦干、讲求实效,开创强国事业和实现“大一统”目标的精神力量。秦文化中敢为人先、坚忍不拔、奋发图强、求实进取、刚健尚武、令行禁止、追求进步、开放兼容等精神品格,业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支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
纵观人类历史,几千年间,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但从波斯帝国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从古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在各领风骚数百年之后,无不消亡解体。唯有“大一统”秦王朝在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基础上所奠基的古老中国,虽历经分裂与动荡,饱受侵略与宰割,却仍然一次次浴火重生,走向复兴,与天地同在,同日月永光,昂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历史上先进的“大一统”思想和秦文化所奠定的“大一统”文化的意义及价值正在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25]。秦人在兴起、建国、东出、统一的奋斗历程中,形成了务实创新的价值追求、开放包容的进取精神、尚武坚毅的民族性格、令行禁止的法治观念、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等文化特质和品格,对后来“大一统”国家的形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意识的孕育,产生了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我们要对秦文化中先进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养分和智慧力量,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26],有利于我们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行稳致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 释:
①“天下”一词在《韩非子》中出现267次,参见周锤灵、施孝适、许惟贤主编:《韩非子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28页至第429页;陈奇猷校注:《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51页,第309页,第1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