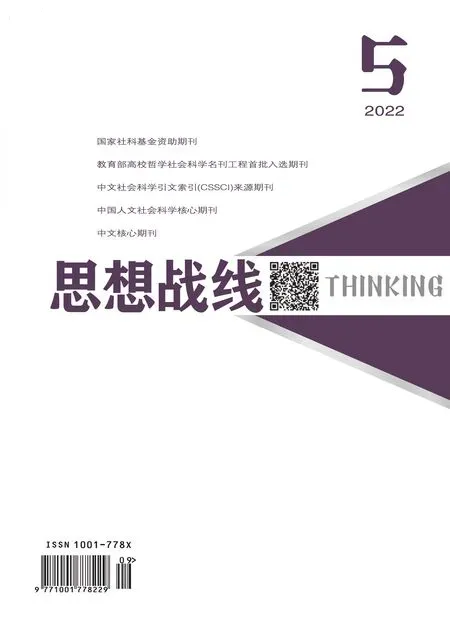水权制度演进与明清基层社会
——以云南为中心
董雁伟
水权制度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产权制度之一。明清时期,云南地区的水权制度逐渐走向完善,水权制度深度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对基层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术界在明清云南水利发展和水利纠纷等方面已形成了一批代表性的研究成果,(1)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吴连才:《清代云南水利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马 琦:《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思想战线》2016年第3期;王 伟,张 琦:《明代云南的卫所与水利纠纷》,《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等等。但对水权制度的演进及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还需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阐发。本文以水利碑刻和水册为资料,探讨明清时期云南水权制度的发展、演进及其在基层治理中的意义。
一、从轮牌制到水册制
明清时期,云南水权制度经历了一个由轮牌制向水册制发展的过程。明代初期,军民田水利纠纷突出,在卫所屯垦区域出现了轮牌制。立于宣德年间的《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详细记载了轮牌制的实施经过:
今照得即日农忙在迩,各执碑(牌)面,将所呈原分水例于上,逐一明白开写。如遇栽秧之时,照旧分水灌田,毋容争夺。今置坎字号牌面开发,委官收掌,军民务在遵守。所委官员,至期会同有司、委官亲议。各屯军民相参田处,常川点闸,毋致失误农时。(2)《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1,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
所谓轮牌制,即由官员颁给写有水例的“坎字号牌面”,上刻代表水的坎卦并写明水例日期和分数。“水牌”既是水额的分配记录,也是用水许可和执照,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临时产权证的作用。明朝初期,轮牌制成为云南地区水权配置的重要方式。如赵州北箐沟实行“铜牌轮次”,(3)万历《赵州志》卷一《地理志·沟洫》,载《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志之二),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年,第30页。蒙化府和蒙化卫均设有“分水圆牌”,(4)《均平水利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2,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890页;《永定水利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05页。嶍峨密罗冲“十三轮水头各执团牌一面,每遇耕耘之时,每轮放一昼一夜,每日俱以卯时交接”。(5)《重修无量寺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68页。轮牌制是官方权力干预之下的一种水资源分配方式,水牌的实质就是配额用水的授权书。
明代中期以后,官府不再发给水牌,轮牌制逐步向水班制或水排制演进。水班制在洪武时期已经实行于民田的水权配置中,永昌府孝感泉“立成班口,分大小先后。大班口一尺五寸,小班口七寸五分,大班口由一班至八班止,小班口由一班至四班止。其轮流次序,格外著有班水规条”。(6)《孝感泉四村班水碑》,载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33页。到嘉靖万历年间,分班、分排灌溉进一步在各地普及,“军民田地,俱有次序”。(7)万历《赵州志》卷一《地理志·沟洫》,载《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志之二),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年,第28页。较为典型的如赵州巧邑里,将受水人户分为十小甲,“依期鱼鳞周放”。(8)《巧邑水利碑》,载黄正发等编《弥渡古代碑刻辑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方国瑜先生指出,云南各处通渠灌溉,农忙时多有分班轮次,就是明代的成规。(9)方国瑜:《明代在云南的军屯制度与汉族移民》,载林超民编《方国瑜文集》第3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62页。总体而言,轮牌制、水班制主要实行于农忙用水时节,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无论在轮牌制还是水班制之下,水权的稳定性都还比较弱。
明代中后期,水册制度在洱海地区发展起来。嘉靖时期,洱海东岸的大场曲、小场曲和双廊等村开始实行水册制,“佥水利老人一名,印给水簿一本”,将轮放日期“并南北山形,沟势于上印刷”。明代的水册类似于轮流放水的登记册,由官府颁给并由“分水老人办置格眼文簿填注”而成,用于登记各村轮放日期,如“大场曲二日,小场曲、拴廊一日”,(10)《水利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5529~2530页。对水额没有进行规定。
到清代,水册已成为水权配置的主要依据。与明代出现的水册不同,清代水册是在官方监督下由士绅主持制订的一种水权登记册。水册记载了用水各方的土地面积、受水份额、受水时刻等内容。水册由士绅及水长等水利管理人员保管,是水资源分配的主要依据。水册一旦制定,就具有地方水政法规性质,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是稳定的。(11)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从现存水册的内容看,水册大多强调一种“以垂后裔”的功能。因此,水册就不再仅仅是临时的用水授权证书,而是变成了一种长期稳定的产权凭证。
现存的《五村会图册》是清代形成于云南县禾甸五村的水册。雍正年间,云南县对境内龙沟、大小麻拉海和许长海进行修浚,竣工后将“各村田亩水例,合照县前碑记,永为定规”,(12)《一沟三坝水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祥云金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5页。立碑一通并颁订水册。水册“公计田亩多寡之数,分析用水多寡之份,悉无偏私。又恐利在易起争端,定为水册,开载姓名,各注水份于下”。水册编订完毕,当地士绅又请知县张汉“钤印,并取一言刻于册首”。(13)《许长水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祥云金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8页。部分文字据原碑及《王村会图册》校订。在水册序言中,知县张汉强调了水利的重要性和颁订水册的目的,从而增强了水册的权威性。
《五村会图册》内绘龙沟、大小麻拉海和许长海附近山形地貌及上简、阿狮邑、上淜灯、新生邑、下简等村的用水额度。与同时勒立的“一沟三坝水利碑”相比,水册中的用水单位由碑刻中的“村”细化到“户”,用水额度由碑刻中的“昼夜”细化到“分”。如阿狮邑水例:
阿狮邑水一昼夜,原额六十分,今细分为一百分:杨弘信五分,杨弘礼三分,杨谦一分,杨让一分,杨天文一分(余59户略)。(14)《五村会图册》,同治三年(1864年)抄本,杨国旺先生收藏。
新生邑水例:
新生邑水例照县前碑记,同左所、湾平村,一昼二夜;田亩三十双,东至下淜灯界,南至阿狮邑界,西至左所,北至湾平村界。新生邑水分:杨正传一分,段甲保一分,杨正谊一分,杨存义一分,杨存礼一分,杨存智一分,杨存信一分,杨存仁半分,汤祖成保一分,赵祖武一分,赵回祖半分,杨常生半分,杨蕴半分,杨受祖半分,杨坤半分,汤执敬半分,汤全金一分,汤立忠一分,杨长寿二分。(15)《五村会图册》,同治三年(1864年)抄本,杨国旺先生收藏。
从水册的保存和流传来看,水册由各村士绅收执保存,被视为五村水利分配和管理的核心依据。水册“序言”中记载:“论水例印簿,先前仅存一本,当日系下淜灯王举人之子生员王世泽收执,后又本此印簿抄录七本,五村分收”,咸丰时期毁于兵燹后,又“于既失之中复寻一册”,当地士绅“商斟速将此册藉抄,以垂后裔,即以息争端”。新抄成的水册由五村士绅收执,“上简村文生李鼎壁收执一本,阿狮邑罗国春收执一本、上淜灯武生王宗哲收执一本,新生邑杨文秀收执一本,下简村汤谧收执一本”,“尤愿后之人谨守勿失,永作指南之车可也”。(16)以上内容载《五村会图册》,同治三年(1864年)抄本,杨国旺先生收藏。
水册制是水权配置走向稳定的产物,水册的功能也在于维持水例的长期稳定。品甸王海是清代云南县重要的灌溉设施。品甸王海,“一名小牧舍海,在县东北十里,分团山坝水贮陂中,灌城北十三村田亩,各有定例”。(17)光绪《云南县志》卷三《建置志·水利》,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5,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379页。现存的《品甸王海水例清册》中,详细记载了清代品甸王海水利纠纷和水例分定的历史,下分“号数、水名、次第、碑文名色、水分数目、现管名色”等条目,详细记载了各户水例,时间跨度从崇祯四年(1631年)延续至清末,(18)《品甸王海水例清册》,民国年间抄本,杨晓曦先生收藏。体现了水权配置的稳定性。
水册制的出现和推广具有重要的进步性。与轮牌制相比,水册制更强调水权的稳定。在轮牌制之下,用水额度是短期或临时的,不同年份的用水额度可能因水情、地情的不同而发生改变,其水额、水分是非固定的。从明初十八溪军民轮牌分水的情况来看,军民田各可得到全部水源的149/307和158/307,双方大约各占一半,(19)张海超:《移民、稻作与水利建设:明清时期大理盆地的生计变迁》,《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1年第3期。水例分定与田亩多寡之间还没有形成明确的联系。水册制则直接将用水额度与田亩多寡联系起来,水册中需要登记用水田亩数额,“公计田亩多寡之数,分析用水多寡之份”,除非地权关系发生变化,否则水分额度就能保持相对稳定。
二、从轮灌制到定额制
明清时期云南水权制度的另一个变化是由轮灌制向定额制的发展。在水权配置中出现了秩序轮放、计量轮放和定额轮放三种主要的分配方式,体现出计量化、定额化不断加强的趋势。计量化、定额化的水权配置方式使水利分配更为稳定,同时也将水权分配的重心由村社下移至农户,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基层水利关系。
秩序轮放是轮灌制的初级形态,也就是水利分配中常见的上满下流。上满下流是农业灌溉中最自然的一种用水习惯,常被时人称为“常理”“定规”。清代《紫鱼村分水碑》将上满下流称为“历久无异”的“定规”。(20)《紫鱼村分水碑》,载李兆祥主编《嵩明县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三乡十一坝水利碑记》也称:“上满下流,古之常理,近水居民均沾灌溉,宜也。”(21)《三乡十一坝水利碑记》,载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禄丰卷》上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3页。清代太和县兴隆村议定的水例中也规定“须上满以下流,自首以至于尾,勿得私意自蔽”。(22)《永卓水松牧养利序》,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43页。这种上满下流的灌溉习惯直到近代仍存在于部分区域的水资源分配中。如在大理喜洲地区:
灌水的方法,一向按古例是“上满下流”,即上边的田流满后才放给下边的田。因此,近山的村子,靠近水源,能先得充足的水源,愈往下边水就来的愈迟,栽插也就愈迟。如晨登村在水头,能栽小满秧,其次是江渡村、上下院塝、新登村等栽芒种秧,再次是市上街、旧城南等栽夏至秧,又次是寺上下村、城北、村东村,一直到河涘城、沙村等从小暑到大暑才能渐次栽秧。(23)《大理县喜洲白族社会经济调查报告》,载《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一)》,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28页。
上满下流虽然操作便易,但是山区水源渺远、田亩分散,若按上满下流之法则一些田地就无水可放。因此,在一些地区又有“自远而近”的放水原则。清代赵州弥渡永泉海塘,在放水时采用“自远而近”之法。(24)《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自远而近”的原则,先放水尾再及沟头,不仅确保了沟尾土地的灌溉,而且能充分激励沟道下游的农户参与水利合作。但是,不管是自远而近还是由近及远,这种轮放制度旨在维持灌溉秩序,缺乏对用水额度的计量和规定。
计量轮放是轮灌制的更高一级形态,即对水分进行计量,具体表现为对用水量的核定和水分分配,以明确农户在一定时间内使用一定水量的权利。对水资源的分配进行计量,适用于水源短缺的地区,可以在水资源分配中有效避免“强者无水而有水,弱者有水而无水”的情况,(25)《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更有利于水资源公平分配。
明代初期,按尺寸或昼夜进行计量分水的做法就已经出现。洪武初年,永昌府吴安屯等四村民众按尺寸分定水班,大班口一尺五寸,小班口七寸五分,轮流放水。(26)《孝感泉班水碑》,载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3页。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军民则以“昼夜”和“分”为单位对十八溪用水进行分定,如河尾西山涧水,“军左所三日三夜,民二日二夜”,杨南村沟水“军前所二分,左前所五分,民水三分”。(27)《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1,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云南府昆明县宝象河也以“分”为单位按比例分水,《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记载:“宝象河自小板桥分派,古制:中竖月牙尖,以三七分引水。一入官渡十四村人户,用水七分;一入旧门溪四村人户,用水三分;上有大耳村沟口,用一瓦之水。”(28)《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96页。总体上看,明代前期的水分计量仅存在于部分地区,主要实施于军民田的用水分配中,水例中“分”的计量也不够明确。
明代中期开始,计量分水的情况变得普遍起来。正德、嘉靖时期,大理府宾川州已经对水源“分定尺寸,安立水板钜口均放”。(29)《本州批允水例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万历时期,赵州巧邑里则按昼夜分定水例,建设水仓及分水暗沟,“各下二纂木,以时启闭,上建纂房各一间”。(30)《巧邑水利碑》,载黄正发等编《弥渡古代碑刻辑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禄丰县则出现了将尺寸、昼夜综合计量的分水方式,《前所军民与彻峨庄丁分水界碑》记载了当地军民“依水刻次第轮分溉”的情况:
一坝水五分,易朝科、易朝卿放一昼夜,何国宣放一昼夜,许在亭同放止。二坝水三分五厘,许为相放二分五厘,百户石之屏放一分。三坝水五分五厘,百户刘华放一昼夜,许登高放一昼夜,许在亨放一昼夜。四坝水四分,百户石之屏、佃彭加选放,又拨田水一分二厘,共二分二厘半。五坝水两刻,每刻分八厘半,许在亨放一昼夜,解其蕴放一昼夜,许在极放一昼夜。(31)《前所军民与彻峨庄丁分水界碑》,载云南省禄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禄丰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20~821页。
到清代,计量分水的方式得到了普遍推广。以放水量(尺寸)或放水时间(昼夜)为计量标准的分水方式在云南各地已经成为一种常制、常例,并被认为是维持灌溉秩序的有效手段。正如大理《阳南村水例告示碑》所言:“水利所在必定水例。例者,有规有条,利利息争之常道也。”(32)《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
水分计量方式的出现和推广与分水技术的进步是密切相关的。清代,石平、石闸、石纂等石质分水工具已经得到广泛运用。在洱海流域,“村民于涧口甃石设立水平,石面凿成溜口,谓之水分”。(33)光绪《浪穹县志略》卷四《水利》,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8,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47页。滇池流域则使用闸枋、石矶进行分水。羊堡头大小两村使用闸枋放水,“门坎石落平,底石、闸口宽三尺五寸,高三尺四寸半”,放水“只准用闸枋,不准用草饼”。(34)《钦加道衔署云南屯田粮储分巡云武地方兼管水利道张为碑》,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97~398页。倪家营、塔密苴等村使用石矶分水,“于分水过中处所镶砌石矶,左右分放,沟底、河底镶定底石,两边用石镶砌”。(35)《毋易成规碑》,碑存昆明市呈贡区倪家营村宝乐庵。宜良小龙洞口安置石槽分水,玉龙村石槽“上深五寸四分,下深五寸七分,宽七寸三分”,下伍营石槽“上深五寸三分,下深五寸四分,宽九寸二分”。(36)《小龙洞口放水石槽碑》,载周恩福主编《宜良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2页。石矶、石槽与石平类似,通过控制水口的宽窄、深浅对水源进行度量和分放。相较于传统的月牙尖分水和草饼分水,石质分水工具对水分的计量更为科学和准确。
清代后期,民间对水分的计量进一步精确化,定额轮放的方式随之出现。定额轮放制下,用于分配的水分总数是固定的,分配到各户的水额也相对固定。这是一种适用于新建水利设施的轮放方式。光绪二十年(1894年),云南县上赤河尾村修筑公塘一座。《新成堰记》记载:
公议水分,以拾陆分零拾伍寸伍分为定,每年各照合同水册所载水分分放,不得争多论少,村众允服……新修堰塘水分共拟以十六分零十五寸五分为定。因使占罗姓长文海埂,准水六分;湮浸罗镇堰塘,准水二分;其余八分零十五寸五分,合村公放后,再修海埂,加高培厚。湮没熊姓塘,再准水五分;湮及罗姓小堰,准水二分;共以二十三分零五寸五分为止……每分定香二尺,挨次轮放,周而复始。(37)《新成堰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449页。
从碑文可知,堰塘水分是经过公议、会计等流程而确定的。水分的总额首轮以八分零十五寸五分为定,后续放水以二十三分零五寸五分为定。在定额之下,用水人户依照水册按“每分定香二尺”进行灌溉,各户水额也保持了固定。
定额制的前提是水权的长期稳定。在稳定的水权形态下,水例“旧例”逐渐变为定额的基础。前文提及的“一沟三坝”于雍正四年(1726年)编订水例,到同治四年(1865年),雍正水例已经被定为“原额”而用于定额分配。(38)《水利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401页。又如,乾隆七年(1742年),云南县杨知颖等人借贷皇本银,“照十一分拼工,修乐耕堤坝塘上下二座”,按照出工分数,将水“照十一分平放”,水例逐步成为长期稳定的“旧例”。到光绪年间,原有的十一分水被确定为水分定额。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云南县水利碑》来看,由于水分总额和各户水额的固定,水分出现了继承和杜卖的情况,如杨家政、杨家声继承杨芳租遗水分,其余水分也各有权利继承人,段姓继承人则将水分“杜卖与杨培龙”。(39)《云南县水利碑》,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31页。这说明,水分的定额化促使水权向稳定的财产权方向转化。
水权配置的计量化和定额化对明清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计量分水促进了水利分配的精确性和稳定性,有效减少和消弭了基层水利纠纷。其次,水权的计量和定额让水权配置逐渐可控、可管,体现了明清时期水利管理精细化、技术化的发展特征。再次,计量分水和定额分水进一步加强了水权的稳定性,为水权的继承和买卖创造了条件。在计量化和定额化分配之下,村庄或农户的水分份额与其参与水利建设的投入密切联系。农户不出夫役,“即将本人田亩水分革去不与”,(40)《一沟三坝水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祥云金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7页。极大地调动了农户参与水利建设的积极性。
三、从无偿制到水租制
水资源从无偿使用到有偿使用是明清云南水权配置的又一个重要变化。水资源使用费是水资源产权实现的一种经济方式。在关中等水权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唐代以后一个农户是否交纳“水粮”,被视作是否拥有水资源合法灌溉使用权的主要标志。(41)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水资源的紧缺促进了水资源有偿化使用的进程,民间出现了缴纳水利银、水租等有偿用水的形式,水租制成为优化调节水资源分配的机制。
水利关乎国赋民生,然而灌溉用水作为一种自然资源,民间长期以来都习惯于无偿使用。民间观念大多认为“水利固系公物,灌溉则有定规”,(42)《重立北沟阱水利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91页。水资源的分配虽然要遵循秩序和定规,但对水资源的利用却是无需付费的。清代以前,在水资源分配中可以见到让水、赠水的记载,(43)《本州批允水例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112页。然而是无论是水的有偿使用,还是水的买卖都基本不见。水资源的有偿使用是在水资源紧缺加剧的背景下出现的。
“水费”是清代以后云南水权配置中出现的新现象。“水费”由官府征收,是水资源的国家所有权借以实现的方式。康熙时期,云南府晋宁州出现了官府征收水费的记载,据《岁科两试卷金水利碑文》载:
照得本州盘龙、达摩二坝,源出东北,其水甚小,田地颇多,屡屡争斗截挖。昔年,前任凿其弊端,立有成额,虽高低得以均匀,而水价安置尚属不妥,殊非长计。本州莅任之初,时遇送考,目击通学诸生卷金无措,已经捐俸买给,特一时之济,不能永久。次查二坝水价从前似属耗费,无济于公,应宜酌以为岁科两考卷金,倘或不足,诸生捐添,如或有余,以作科举卷价,且恐异日更易,合行立石以垂永久。其盘龙坝递年自十二月十五日始至次年三月头龙止,每昼夜水价银一钱。达摩坝自十二月十五日始至次年立夏止,每昼夜水价银五分,俱着坝长收计交库,试期支领买备试卷,各庙住持不得干与,仍禁生员不得克当坝长,各宜遵守。(44)乾隆《晋宁州志》卷二七《艺文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水价银”即水费,主要面向官修水利工程的受益户征收。乾隆时期,永昌府也出现了“水利银”的征收。乾隆《永昌府志》载,永昌府每年“实征水利银二两”。(45)乾隆《永昌府志》卷十一《田赋》,北京:方志出版社,2016年,第80页。水利银主要征收于保场三沟,“西山沟水利银八钱,放水二尺;中沟水利银六钱四分,放水一尺六寸;河底水利银五钱六分,放水一尺四寸”。(46)《三沟碑记》,载杨升义主编《施甸碑刻》,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13页。水费征收是官府在田多水少的情况下,通过货币方式配置水资源,以维护水利设施和兴办社会公益的重要方式,也是水权定价和货币化的开始。
除了官府征收的水费之外,清代民间水利灌溉中已普遍存在水租制。与水费不同,水租由水利组织进行征收,主要用于民间水利设施的修建、维护以及举办乡村公益等方面。立于民国初年的大理《南庄约学堂水碑记》追溯了清代以来水租形成的历史过程。碑文称:
有田有水,轮牌分灌,通例也,无所谓水租也。水有租者,惟中三约则然。南庄阱水,自古分为十牌,各立名目:一下厂,二官下,三队伍,四桥头,五、六古城,七抄漠,八百姓,九南庄,十季庄。有明朝古碑可证。当日按村摊分,想必无租。继而田多水少,而水乃有租矣。(47)《南庄约学堂水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4,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717页。
该地由于“田多水少”,清代即开始征收水租。如碑文中提到的季庄,据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所立的《季庄水碑记》记载:
河上湾自古有南庄阱季庄水一牌,十二日一轮。凡同沟共井之区,均资其灌溉焉……今将零者积之,定水为二十分,每轮或日或夜,每分租七斗,共纳租十四石,又赎得大水十九分半,中三分□旧置一分半,共计大水四分半,亦以七斗一分招租。(48)《季庄水碑记》,载唐 立编《明清滇西蒙化碑刻》,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2015年,第233页。
不仅用水户要缴纳水租,水分还可以用来“招租”。该地光绪十年(1884年)的一份水利契约中也记载:
立实卖水契人左大有、左大勋,因有祖遗排水半河,昼夜相连,坐落伏虎寺箐内……复转卖与本姓合族天醮公项下……任随公内管业招租。(49)《蒙化中南庄水契》,杨韧先生收藏。
延至民国,该约各村都缴纳有数额不等的水租:
宗旗厂应有租四石,顾旗厂应有租二石五斗,古城村应有租二石五斗,上南庄应有租五斗,河上湾应有租二石五斗,下南庄应有租二石五斗,中南庄应有租一石,谢旗厂因有租二石五斗,罗华闭夏村应有租二石。(50)《南庄约学堂水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4,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717页。
云南地区水租的出现始于清代初期。乾隆年间,石屏、宜良等地已经出现了征收水租的记载。在石屏州异龙湖流域,宝秀兰梓营村民按水班轮流用水,用水户均须上缴一定数额的水租作为公益经费。据该村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勒立的分水碑记载:
伍内原有龙树冲水贰昼夜,租四石,送入本庙,但□日李极、王浩、李敬宗、王永治、张希国十九人等与孙姓控争,使银十二两扣租一石一斗五升,实纳二石八斗五升。犁花冲水,头班王铭等捐一两,应沟至底方止,或放两头井中;二班王联辉等;三班蒋永福等;四班王□……家良等。各班捐水租一斗三升,共三斗九升,送入本庙。(51)《兰梓营清理纳粮分水碑》,载唐 立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东京:东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86页。
在滇中宜良县一带,各处积水堰塘也通过征收水租的方式来调节水源蓄放中的利益关系。上沟塘子“每年公议抽收水租,以补塘子内水淹之田”。(52)《上沟塘子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433页。响水沟则对军田征收水租,“每年收与水利,二月初一议事公用”。(53)《响水沟碑(一)》,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254页。
作为水权配置的一种形式,水租多按照受益田亩的数额进行征收。道光年间,通海县小新村堰塘照田征收水租,“照田给银,每工田,公补银三两或二两”,“水钱收归下元会”。(54)《扎塘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31~332页。南宁县雅户村所立的《雅户乡规民约碑》也记载了当地按田亩多寡征收水租的情况:
清明水公放。清水,放者每亩三百文,包栽。洪水,放者每亩五十文。后,有添水后,每亩加一百文;概放洪水者,不取。龙潭水公放,每亩水价公议。每正月至二月初六日止。以后救济秧田、苗圃,间有余水灌田者,每亩亦是三百文。(55)《雅户乡规民约碑》,载范利军主编《曲靖市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75页。
在部分实行计量分水的地区,水租也按照“分”“班”或“昼夜”进行征收。呈贡过山沟在水例分配中,左沟“分水三分”,右沟“分水七分”,因而左沟各村需要“上纳沟粮六升”,右沟则“公纳沟粮一斗九升”。(56)光绪《呈贡县志》卷八《续修水利》,载林超民等主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29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太和县南阳村则按照“昼夜”征收水租。水利碑记载:
一拟羊皮箐水六昼夜,三月十五日后一昼夜作钱一千五百文,四月初十外一昼夜,作钱两千文,四月二十外一昼夜作钱二千五百文,五月初十外一昼夜作钱三千文,二十外一昼夜作钱三千五百文。黑龙箐水每月一昼夜作钱三百文。均为乡约应役之费,亦照旧规无异。一拟羊皮箐水在六月内一昼夜,议定灌田有用者作钱一千五百文,下河无用者不许作钱,亦照旧规。(57)《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
水租以征收实物为主,也可纳银抵扣,如上引石屏兰梓营水租“银十二两扣租一石一斗五升”。到清代后期,水租多以货币方式进行缴纳。水租租额根据水情和丰歉而浮动,如宜良县沈伍营永济塘将受水之田分为三等,“先得水者为头,中得水者为中,后得水者为下”,水租按照岁之丰歉也按三等进行征收。(58)《沈伍营永济塘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02页。水租缴纳是用水户必须履行的义务,拖欠或拒缴都可能受到处罚,如宜良县桥头营永济塘规定:“塘水救济秧田,必须照田收钱,为岁修之资;倘有不出水钱者,公议每工罚钱二佰文入公;塘外扯着塘水之田,必须照田上纳水租;倘有拖欠者,公议每工罚谷二斗入公。”(59)《永济塘碑》,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51页。
水租制的出现,是清代水权制度的重要发展。水租不仅反映了水资源的价值,也是水资源产权的实现形式。水租的征收实现了水资源的有偿化使用,不仅提高了水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而且有效维护了用水秩序。清代,水租还逐渐成为了乡村公益经费的重要来源,除用于水利设施的维护外,还用于乡约应役、乡村教育和地方慈善等方面,促进了基层社会关系的发展。
四、水权配置与明清基层社会
水权配置是传统时代水利治理的核心问题。水权反映的不是人与水的关系,“它是一系列用来确定每个人相对于稀缺资源使用时的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关系”。(60)[美]埃瑞克·G.菲吕博腾,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产权与经济理论:近期文献的一个综述》,刘守英译,载[美]罗纳德·H.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年,第148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那样:“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17页。这意味着,水权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即一种社会关系。因此,需要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角度对传统时期的水权问题进行认识和把握。
明清时期,云南水资源配置虽然因水资源类型和利用方式的不同而表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但整体的发展趋势是水权制度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水权配置向计量化、定额化发展,水资源管理的技术化和精细化提升;另一方面,水权配置逐步走向稳定,从水权不清到厘定水权、分定水例,最终实现了水权的稳定。水权制度的发展对乡村社会关系产生了影响。
(一)分而有序:水权分配与基层治理
水资源的合理配置是乡村社会秩序形成的基础。“天下有利必有争,水利关国赋民生,争尤莫免。故水利所在必定水例。”(62)《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作为水资源配置结果的水例,不仅维系着灌溉秩序,也关乎基层社会秩序。公平有序的灌溉秩序是传统时代基层社会稳定的体现,因而水例的分定也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清代大理太和县河尾铺推登村烟户长期共放水源、共办伙甲,但因章程不清、水例不明,于道光三年(1823年)分定水例。据碑刻记载:
自古推登村烟户住居三巷,火甲、水利未曾派定章程,多生口角。今合村公同妥议,于本年六月内,将火甲、水利分为三分。遇火甲至期,三分承办;及所挖涧水,每巷一日三分轮流灌溉。章程既定,永守成规,其合村所存公项银两,已经三分均分执掌。嗣后,三巷人户即有盛衰,不得倚强凌弱,紊乱旧章。(63)《河尾铺推登村火甲水利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336页。
清代,基层社会治理逐渐体系化,赋役分摊和水利分配机制的完善代表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入。在这一进程中,水权配置也更加兼顾到社会效应,水资源利用从重分配向重治理转变。
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明清水权分配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一是水例的分定兼顾了基层社会组织。水资源的分配直接决定于田亩坐落、地势高低和水源远近等因素,但明清水权分配又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基层社会组织,使得水权分配与里甲均徭之间产生了一定的关系。明代赵州巧邑里按小甲轮流分放。(64)《巧邑水利碑》,载黄正发等编《弥渡古代碑刻辑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清代宜良马军村“其水每照各户门差而放”,(65)《均平水例永远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18页。蒙化则实行按约分放,“南庄大箐之水,一约分放一月,三约各有两分,勿容紊乱”。(66)《蒙化水利碑》,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163页。太和县阳南村的水例分定也是基于里甲差徭。《阳南村水例告示碑》记载阳南二村水利:
据康熙存碣:北有黑龙箐每月贰拾肆昼夜之小水,南有羊皮箐三四五六月共陆昼夜之大水,以二村同里甲差徭并有肆贰分同放之例,寓分于合,寓让于均,诚历古不逾之例也。(67)《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
水例分配与基层组织的交织和重叠,将水利分配与里甲赋役进一步整合于同一个治理体系中,提升了基层治理体系的效能。
二是水权分配的会计化特点更为突出。明代的水权分配还存在按比例分配的现象,而在清代水权分配计量化、定额化的趋势之下,水权分配的技术性加强,专业化、会计化特征更为明显。水权分配要“公计田亩多寡之数,分析用水多寡之份”,(68)《许长水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祥云金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8页。又要“每年估水势之深浅,按户计用”,(69)《洋溪海水例碑》,载大理白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祥云金石》,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74页。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在清代的水利管理中大多存在一类专门从事会计的管理群体,他们通常被冠以“总管”“分管”“管事”等称呼。在云南县,水利设施的修建和水权分配都离不开这一群体,民众还“公议酬总管一人,功劳水一寸;酬分管四人,功劳水各一寸”。(70)《新成堰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449页。尤其在民众集资修建水利的过程中,会计流程更是贯穿始终。光绪末年,云南县禾甸明镜灯、黄联署两村扩修青水堰塘和润泽海,“以拾股修理,每股拼银一百两,每股每轮放水一昼夜”。从现存的《青水堰塘润泽海碑记》来看,资金核算及水分分配都记录周详、会计严谨。(71)《青水堰塘润泽海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507页。
清代水权分配方式的变化,使乡村中的士绅以及水长、沟头等水利管理人员的地位更为突出。明初,官府在水利分配中还需派水利官员“常川点闸”或临场监督,(72)《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1,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崇祯时期开始从民间佥选“水利老人”管水和分水。(73)《水利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29页。到清代,国家对水利的管理由微观层面变为宏观层面,官方除了处理水利纠纷和应乡村社会的请求认定水利规约外,退出了对水利事务的具体管理,水资源的分配完全由乡村社会内部组织和实施。
在水利分配中,水长、水利和沟首专司水源分配和坝堤维护,并由地方官员“赏给沟首、水利匾式,以示鼓励”。(74)《响水沟碑(一)》,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253页。水长等水利人员因为直接掌握着水的分配,在乡村社会中具有较高的地位。士绅则通过控制水册、水规,进而控制了水利的分配权。水册、水规由士绅主持制订,士绅在灌溉秩序紊乱之时“邀同合约士民,齐集文宫,公议水规”,(75)《清代民国时期安排马米厂河用水的两个文告》,载马米厂米姓村志编纂委员会编《马米厂米姓村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106页。又在古碑旧例遭受损毁时“抄藏宝秘”,召集“合村会议,照旧重修古碑”,(76)《宾川县水例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33页。主导了水利的分配和管理。在赵州弥渡巧邑里,虽设有水夫“巡水看守,关锁纂房”,但作为水利管理中枢的纂房,仍由士绅“掌钥”“觉察”并“依期鱼鳞周放”,可见士绅在水权配置中的核心地位。(77)《巧邑水利碑》,载黄正发等编《弥渡古代碑刻辑释》,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8年,第118页。以水利分配为中心,乡村基层形成了“士绅—水长—农户”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强化了乡村社会的权力差序格局。
(二)寓分于合:水权配置与区域整合
产权的特征是排他性的,因而就水权分配而言,这是一个分的过程。但是从产权的本质看,水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又存在着社会整合和区域整合的功能。《阳南村水例告示碑》中专门强调,水例只有“寓分于合,寓让于均”,才能成为“历古不逾之例”。(78)《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也就是说,水例分配既是一个划定权属边界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同利益主体合作与协调的过程,这是水权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共同决定的。明清时期,云南地区水权制度逐步完善,水权配置也逐渐走向稳定,稳定的水权配置在跨村社的区域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一个流域范围内,稳定的水权配置是社会整合和区域联合的基础。从地方志来看,明代方志中记载的“水例”和分水之制较多,而清代有关分水的记载已经消失不见。以大理赵州为例,万历《赵州志》中记载,明代东晋湖用水有制,定西岭南多地的军民田地“水利各有定规”,北箐沟“有铜牌轮次”灌溉,黄草坝圣母塘水也以“轮放”的方式灌溉田地。(79)万历《赵州志》卷一《地理志·沟洫》,载《云南大理文史资料选辑》(地方志之二),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年,第27~30页。到清代,道光《赵州志》只记载各处沟洫、堰闸“旧有水例”,水例分定似已约定成俗。这可以说明清代中后期的水资源条件有所改善,但从水权发展的路径看则是水权逐渐稳定的表现。
明清时期,云南水利纠纷众多。水利纠纷从根本上说是水权社会属性的体现。水利纠纷调处的过程,既是各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协调的过程,也是水权从不稳定走向稳定的过程。以太和县阳南营头、营尾二村的水利纠纷为例,据水利碑记载,阳南二村因箐水问题不断发生纠纷,“乾隆讼矣,同治争矣,光绪丙子复大争”,“阅年余而章程未定”,光绪三年(1877年)在官府干预下得以拟定用水章程,解决了用水纠纷,尔后两村民众“盟诸心,志诸石,世世息讼无争,同享美利”。(80)《阳南村水例告示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本主庙官圆堂。又如乾隆年间,云南县美长村、总府庄和小新庄福星户发生水利纠纷,纠纷调解之后当地士绅分定水例,编订水册,现存的《总府庄花名水海册》分为总册和子册,水册序言中详细记载了水利纠纷的经过和水分的由来。(81)《总府庄花名水海册》《新庄福星户水册》分别由罗钰臻、杨晓曦两位先生收藏。新水册的颁行使这一带的水权走向稳定,此后三村共修水利,再无纠纷。
稳定的水权配置为不同区域、不同村落的整合提供了条件。清代,在一些坝区和流域内部出现了因共建、共用水利设施而出现的“水利共同体”。如弥渡五十三村自古共用南、北及马桑沟三阱之水。明清时期,“轮放各照日期,古规实难紊乱。凡放阱水,村民定期遵守”。(82)《重立北沟阱水利碑记》,载赵志宏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190页。在乾隆二年(1737年)、嘉庆三年(1798年)和二十一年(1816年)立有水利碑。以三阱之水为中心,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用水规则,分排水、轮水两项,水规长期保持稳定。以北沟阱为例,乾隆二年的水例规定一直到清末民初仍被沿用和执行。在长期的用水实践中,五十三村逐渐形成了一个跨村落的团体。《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记载:
五十三村奚以名为团体而名也,然五十三者统词也,实则八十余村焉。旧时分隶三属,所居村落,星列棋布,势如散沙。乃能集合而成团体,虽时世有古今,人事有代谢,而此团体则愈久而愈固者,其故何□?曰:“以有因以相维相系也。”其因为何?曰:“玉皇阁者,五十三村团体之总因也,而南、北、马桑沟三阱之水,及各斗醮香火之公款、公产,又其团体之分因焉。”(83)《五十三村公田水利碑序(一)》,载赵志安编著《云南水利碑刻辑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9年,第544页。
可见,由于水源的共同灌放,当地八十余村结成了跨区域和跨村落的“团体”,形成了以玉皇阁为核心的水利共同体,实现了跨区域的村落联合。
明清以来,由于用水、分水而形成的共同体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延续,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首先,水权的稳定为共同体的维系提供了产权基础。水利共同体以共同获得和维护某种性质的“水利”为前提,“共同的水利利益”是共同体成立与维系的根本基础。(84)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从云南的情况来看,水权的稳定使得“共同的水利利益”成为可能,从而成为了村落联合的纽带。其次,水租制度为共同体的存续提供了经济基础。水租作为公益经费,主要由醮会或土主庙等乡村组织收储和代管,在水利设施维护和乡村公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次,水册制度为共同体存续提供了制度保障。水册是共同体关系的契约化、文本化表现。前文所述的《品甸王海水例清册》详细记录了当地小牧舍、高伍屯等“海下十三村”的水分情况。当地在品甸王海建有龙王庙,每年腊月三十及正月十五“品甸王圣诞”之时,海下十三村都要办会祭祀,小满节则当众开闸放水三天,习俗沿袭至今。(85)《重建品甸王庙碑记》,碑存大理祥云品甸海龙王庙。又如《五村会图册》在册首即记载五村士民“创修龙王、土主、圣母等项殿宇,聿修祀典”,以及此后多次重修的过程。由此看来,水册、水租和民间信仰相辅相成,支撑并强化了以水为基础的区域整合,为水利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