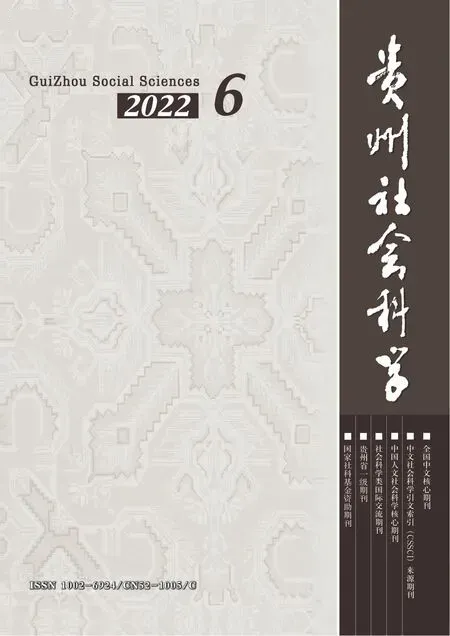明代“诉讼”律例与地方治理
余同怀 李子煊
(安徽理工大学,安徽 淮南 322001)
明代“诉讼”律12条,涵括整个诉讼程序。根据诉讼程序,这12条大致可以分为提起、受理、审理、终结四个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令、条例、事例、则例、大诰、榜文、告示禁约等法规,构成“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对于诉讼进行规范,所强调的是自下而上陈告,所追求的是实情,无论是对诉讼人,还是受理官员,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诉讼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深远的,与地方治理息息相关。但也应该注意,君主专制政体下,“君主本人是不负责任的;他不在法律之下,因为他是不对任何法律制裁负责的”。①同样,与这种政体共生的官僚政治也会影响法律的具体实施。
一、“诉讼”律例的规范作用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规范着诉讼行为,对诉讼制度也有很大的影响。“在探寻、把握传统诉讼时,必须对德威、宽严和轻重关系做一番实质性研究,方能揭示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且内容极其浩繁复杂,同时发展又颇具有关联性的中国传统的真谛”。②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不但在明代予以执行,也直接影响到清代,从“此大清律即是大明律的改名也”,③可以看到清代对于明代法律的全面继承,不过, 亦有所发展。
首先,对于诉讼者及受理官员的规范。明代“诉讼”律有12条,条例在万历年间勒定为25款,按照诉讼程序,涉及到提起、受理、审理之前、受理过程中,对整个诉讼程序都有所规范,其中有10条律以及10余条例,都是约束官员行为的,对于诉讼者规范更严格。按照治官束民的原则,明列罪状,设置刑罚标准,看似律例与其他法规有些冲突,但没有违背律的精神。正如王锺翰先生所讲:“例原以辅律,非以破律,所谓‘例因案入,例实由律出’也。”④条例与其他法规,总体上脱离不开律,但在量刑定罪方面,可以不局限于律所规定的刑罚,更增加例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效用,这种有体系的法规,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明代“律例”法规体系,既有常规大法,又有“权宜”之规,往往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变化而修订。律是根本大法,朱元璋颁布时就讲到:“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负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将孚佑于无穷矣”。⑤他有立法者的气势,子孙及臣下,不敢乱其成法,也就决定《大明律》的根本法地位,其子孙在不更改成法的情况下,以条例、则例、事例、榜文,禁约等法规来补律之所不备,以及应付当时的社会形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法规,其出台都不是统治者凭空臆想而来的,有着严格的程序,有奉旨、奉命、核准、覆准、题准、奏准、议准等不同的形式。即便是地方官发布的告示禁约,也要得到上一级的批准,在颁布的时候有“奉府批”“奉道批”“奉院批”,类似巡抚、巡按这样的大员,也要申明“奉旨”,可见程序之严谨。虽然这种“批”往往是表面文章,却也制约下属任意胡为。从地方官颁布的有关“诉讼”方面告示禁约来看,也都在律例规定的框架之内,亦可见律例的规范作用。
再次,在“诉讼”律例法规体系明确规范下,早期的地方官大多能够认真执行,诉讼还是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在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明史·循吏传》中,大多数循吏都有办理词讼方面的政绩,而为时人所称。如成化时,应天府丞李堂,奉命“分莅属县,剖理词讼,检查钱粮。句容县给事中赵钦,罪犯不法,连坐无辜,淹禁屡岁,公(李堂)承委,片言折之成狱,独置钦重典,远近称快”。⑥正德时,河南卫辉知府翟鹏,“接受词讼,吏莫容其奸,虽事情重大者,亦不隔宿,事结,吏书止供书写,不得高下其手,民称为翟青天”。⑦弘治时,大名府知府韩福,“两入觐朝中,吏士夹道指之曰:‘此大名韩知府也’。人比之包孝肃云”。他面对累年不决逮系者数百人的大狱,“征首恶者数千人,谕以理法,即日决”。⑧江西巡按芮钊,在“江西地大民众,词讼填委,素称难治,公(芮钊)至布条章,谨约束,抑强扶弱,令行禁止,于是境内大治,吏民畏威而怀德,啧啧称颂,以为前此所未有”。⑨湖广宝庆知府杨淳,在“词讼盈庭,一判数千,继旬百人,再旬十人,期月之间,浮风丕变”。⑩由此可见,“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众多官员严格执行的情况下还是发挥着地方治理效用的。
又次,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的细则,在一定程度上规范着司法官们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以“告状不受理”而言,规定地方官必须受理词状,哪怕是户婚田土钱债等“细事”,不受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地方官都按一定的时间,定期接受和审理词讼,以“牌”的方式向属民公开揭示,还允许民众前来观审。这就能够接受民众的监督,即便是这种监督在地方官强势的情况下形同虚设,但民众不服,声言上控,竞相传言,还是能够使地方官不敢过分地妄作非为。风宪官们承接词讼也能够纠正不少冤假错案。如洪武时,御史俞士吉“出按凤阳、徽州及湖广,能辨释冤狱”。御史严震直“数雪冤狱”。值得注意的是,此后的风宪官们往往亲自审录罪囚,已经不再是主察地方官司法审判的不法不公,而是承担起司法的责任,其监察职能与司法职能的重叠,不但导致司法程序发生变化,而且使地方官在办理词讼时平添许多顾虑,影响到地方治理。
最后,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也是司法官们所能够依恃的法律体系,在皇帝以及权臣、阉宦公然违反“诉讼”律例法规体系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进行抗争。“明代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意气风发的时代,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极盛。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在历代也是罕见的,越是受了廷杖、挨了板子,就越是觉得风光,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越高。”针对违反“诉讼”律例法规体系的行为,士大夫也是敢言的。如面对厂卫办理词讼,臣下能够以祖宗之制,要皇帝把办理词讼之事交回法司。厂卫之所以办理刑狱之案,乃是“正德年间刘瑾、钱宁等,相继擅权”所致,因此请求“皇上念祖宗之法,畏上天之戒,收回成命”,把审理之事交回法司。还有例证:“今天下一应词讼,内则从三法司,外则从按察司及抚按衙门。祖宗以来,守为成法。况东厂原奉敕谕,责在缉事,专为京城,其永平府系直隶地方,远在千里,纵干人命赃私,自属彼处抚按衙门,东厂委的不应受理,又不当辄与闻奏。”“厂卫当遵照敕书,察访不轨妖言,人命强盗重事,其军民词讼,不宜干预。”虽然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毕竟是抗争了。对于在外镇守太监,他们也提出:“军民词讼,一切事务,并不得干预。庶官无掣肘之难,民免剥肤之苦,地方得以宁谥矣”。“南京内外守备衙门,止为守御而设,不宜滥受词讼,侵法司之权。”对于上官滥受词讼,也能够提出让有司官员,“罪可开释者,勿拘成案,勿狃避嫌,勿狥上司之意,词讼严滥受之禁,听问开和息之门”。这些人之所以能够义正辞严,所赖者乃是“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及祖宗之制。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作为传统的基本法律,在整体上能够规范当时的诉讼行为,也有一定的成效,虽然在君主专制与官僚政治双重影响下,具体实施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许多变数,但总体上保持了诉讼的制度有序。其时形成的以律例为主,以其他法规形式为辅的法规体系,基本上为清王朝所承袭。
二、“诉讼”律例实施困境
明代“诉讼”律自出现以来就利弊共存,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以条例进行补充,形成了律例体系,但不免要面临许多困境。面临这些困境,统治者时常以事例、则例、榜文、禁约等法规形式予以调整,其方针虽然是“大率遵旧制行之”,但面对变化的社会形势,往往很难摆脱实施上的困境。
首先,“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君主专制政体下难以施行的困境。明王朝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一切法律与制度的制定都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官吏权贵的划分,仔细考察起来,无非是专制君主及揽权者们弄权斗法的结果”。朱元璋在“明刑所以弼教”的旗帜下,以重刑为“明刑”,以重惩“奸顽”为“弼教”。他在律外用刑时,总是反复强调不是“朕不教之于先也”,凡是“不从朕教”的,都被认为是“奸顽”。朱元璋为了控制天下的官吏,允许耆民率领百姓捆绑官吏,赴京交他“法办”,直诉成为当时人们经常采用的方式,“敢有阻挡,其家族诛”。这种完全打破正常自下而上的诉讼体制的做法必然导致诉讼上的混乱,之后不得不回归制度,因而规定:“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官司,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辄赴京师,亦不许家居上封事,违者罪之”。但《大诰》的颁行,使这种禁令则完全失去效用,以至于“州郡小民多因小忿,辄兴狱讼,越诉于京,及逮问,多不实”。在这种情况下,又对越诉者采取全家发往化外,本人枭首示众的残忍手段予以打击。政策上的反复,也导致“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实施上的困境。“即使在法律和制度不正义的情况下,前后一致地实行他们还是要比反复无常好一些。”从明王朝有关越诉方面反复颁行的禁令来看,可见王朝政策上的反复,也给一些人利用政策的变化,谋求私利提供了方便。在正统以前,臣民诣阙为地方官员申请免罪或奏保者连绵不断,其中也不乏“不顾廉耻,私自主使所属官吏,并情熟粮里人等,虚捏浮辞,连名保留,甚至具本诣京奏保”。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出台禁令,不再允许臣民诣阙为官员吁请,对于直诉也增加许多限制,原本直诉得实勿论,也变成虽实也要坐罪。这种反复无常乃是君主专制政体最容易出现的事情,更会使人们只相信天皇圣明,青天在上,而不相信法律,其“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实施的困境也显而易见。
其次,政治腐败导致“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往往成为具文。贪污腐败在国家出现以后就一直伴随着权力存在,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不可能根除贪污腐败,但权力的存在方式又决定其必须受到制约,如果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存在,将是人类的灾难。君主专制政体,不但君主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受到君主宠信的权臣、阉宦的权力也难以得到制约。如正德时,刘瑾专权,“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余两,往往贷于京师富家,复任之日,取官库所贮倍偿之,其名为京债,上下交征,恬不为异”。严嵩专权,大肆受贿,“自其省礼部尚书直至削官为名,贪贿活动贯穿于仕途的始终。从诸生到亲王,从朝臣到边将无不向其行贿馈送,少者几百两,多者十几万两”。由此“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亦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此权门贿赂之往鉴也”。在天不能雨粟,地不能够生金的情况下,这些贿赂的钱财从何而来?必然是一级一级地勒索,总是民脂民膏。以诉讼而言,在地方官能够得到陋规之中,不能够属于大者,正如海瑞所讲:“令萃百责,大抵刑教十之一、理财十之九,百职惟令,临财惟琐惟多”。虽然在诉讼方面所得仅仅占地方官陋规收入的不到10%,毕竟也是他们能够支配的一项钱财。海瑞能够从诉讼纸赎中拿出万两白银筑城,则可见这笔钱财不少,也无怪乎地方官在办理词讼时对纸赎特别关注。“故事,词讼罚纸,后有患其侵渔,议以谷代,而贪夫反得乘以为奸。”将罚纸变成粮米,却不想这些官员利用粮米进行经营,贵粜贱籴,反而盈利。官员利用制度之便,明为办理词讼,实际上勒索钱财,“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实施的困境也可想而知。“吏治所以日坏者,总由情面太重,钱神太灵。”“贪官污吏之多,一般人总喜欢用‘民族性’或‘风气’一类玄学性质的背景去解释,以前者而论,仿佛中国人是天生成贪污似的;以后者论,又仿佛有一二出类拔萃的人物出来表率一下,风气就会改变过来似的。”然而,“特殊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所造成的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与封建主义混合统治形态”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下才有突出表现,“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在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性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腐化则源自这种“奉上安下”的制度设计,因为其本身变数是很大的。作为下级官吏只要搞好与上司的关系,只要搞好与皇帝及权臣的关系,就能够保住和争取更大的利益。在唯上是从的情况下,作为法律规范的“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往往成为大小官员可以利用的工具。
再次,“诉讼”律例与其他法规之间的矛盾导致“诉讼”律例法规体系难以实施。明代的法律体系,既有常行之法也有权宜之例,而例的内容又不仅仅是条例,“可以说,每一重要法律的制定和废止都有其缘由,都蕴涵着立法者明确的思想动机”。这种思想动机,大多数是基于当时的社会形势,难免缺少长远的眼光,更会与既定的法律有冲突,特别是在祖宗之制不能够改变的情况下,律是不能够改变的,例则难免应时,在具体实施问题上,依律还是依例,抑或是依其他法规,自然会导致实施上的困境。以“越诉”律例来说,律内规定迎车驾、击登闻鼓,得实者免罪。例内则规定不分虚实,立案不行,仍将本犯枷号一个月发落。在具体实施上,就应该问罪,并且立案不行,其直诉渠道则完全不通。如嘉靖四年,“时登闻鼓下状词甚多,有引刀自伤,以明其冤者”。嘉靖帝则指斥刑部说:“迩来内外法司,多不能为民分理冤抑,故奉诉纷纭。自今凡有奏状,即宜择可行者行之,毋徒立案废阁,以致冤抑无伸。”既然例内规定立案不行,又要求择可行者,法司是依律还是依例,反而无所适从了。律内规定事重者,从重论,律中相关各条却没有充军、枷号的规定,是依律还是依例,法司也很难决定,只能够上请。上行下效,凡律与例难以抉择的时候,无论是地方官还是法司,都要上请,给具体办理词讼者平添许多困扰,也增加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最后,“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与诉讼途径的矛盾。明代中叶以后,相继增加了巡抚、镇守中官、兵备道等,不但使布政司、按察司成为附庸,并且使巡按、巡抚、镇守中官、兵备道、守巡道等逐渐行政化、财政化、军事化、司法化。按照《宪纲》的规定,这些具有监察职权的官员都有办理词讼的权力,臣民到他们那里去投诉,既没有越诉之罪,还能够取得“批词”,当然也会给具体审理词讼者带来困扰,以至于“中外问刑官,往往任意偏听,不审察事情,或狥私受嘱,不畏法度,颠倒是非,致令衔冤负屈之人,辄入禁中伸诉,至有自缢死者”。臣民冤屈不能够伸,地方官也只能够惟上司的马首是瞻,为了不被这些负有监察职权的上司在诉讼方面挑出毛病,只好曲意奉承。如正德时,桂萼在为丹徒知县时,就是因为“执古傲上,不能狥时曲媚,见辱于知府林魁,更改湖州、武康、成安三县,低徊十余年”。那些握有举劾大权的人,为了树恩,推举的多是大官,弹劾的乃是小官。一些大官被弹劾,也是因为“亦非其人之果不贤也。或负气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则受人指嗾,为之快忿者也”。所被推举的小官,也是“亦非其人之果贤也,或最有力者也,不然则其亲与故也”。也就无怪乎“在外藩司府县之官,闻有钦差官至,望风应接,惟恐或后”,最终是“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畏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多头上司,不仅仅导致“诉讼”律例法规体系难以实施,也加剧了政治腐败,更影响到地方治理。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既有来自法律方面的,也有来自人为的。在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明代,连《大明律》都很难说是天下之法,遑论“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了。君主不信任臣下,上级不信任下级,而“权力的唯上性,不仅表明君臣之间的主奴关系,而且加深了各级官吏对君主、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的依附关系。权力的变更性,既说明官吏自身权力在分布的秩序内经常流动,也表现出宦海沉浮、仕途叵测的恐惧和危机。权力的竞争性则包含着权力的独占性和排他性,进而表现出许多令人瞠目的激烈、残酷、奸诈、虚伪、苟且、曲从等现象”。在这种情况下,“首脑人物多是不诚实的人,而要求在下的人全都是善人;首脑人物是骗子,而要求在下的人同意只做受骗的呆子;这是极难能的事”。君主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就是奉上安下,而对上竭尽欺骗之能事,也是奉上体制之必然;对下使出各种残酷高压手段,更是安下体制常见的现象。“按惯例,制裁被分为两大类,奖赏和惩罚即积极和消极制裁。认为受法律管辖的人们会选择一种,躲避一种。”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以治官束民为宗旨,无论是官还是民,选择对自己有利,躲避对自己不利,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出现司法审判的“六滥”。民间的健讼、缠讼,也就不能指望“诉讼”律例法规体系能够予以规范了,而是有更深的制度根源与历史背景。
三、“诉讼”律例与地方治理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作为时代的产物, 曾经在确保诉讼能够重实罚虚,按照自下而上诉讼程序施行,以及治官束民、规范词讼等方面发挥过作用,有效地保证诉讼能够顺利进行。对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进行研究,并不是为了弄清律例法规体系的内容,了解其具体实施情况,而是在于分析和评价,总结经验教训。
首先,“诉讼”律例法规体系规定的直诉问题。自朱元璋开始,明王朝一直重视直诉的问题,即使在直诉多不实的情况下,也没有不允许直诉。从条例里可以看到,允许直诉的事情,乃是叛逆机密等项重事,其中包括各级官吏的不公不法行为,对于不干己事及个人冤屈,则是予以严厉禁止的。由此可见,直诉主要是关系到朝廷社稷安危以及吏治,而不是为了臣民能够申诉冤屈所设,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有关吏治问题,则是要使天下官吏不能够胡作非为,这就要加强对官吏监督,尽可能地扩展朝廷的耳目,以便使那些官吏,即便是“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易其辞”(《韩非子·有度》)。要求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一切听命于君主,否则便是“有违行君之令”和“欺君乖上”之罪,而罪不容诛。允许臣民直诉各级官吏不公不法,是与这个原则相适应的。不能说明代直诉制度设计完全合理,但至少可以减少民间因为自身琐事及不干己事来到京城缠讼,何况还有监督各级官吏之功效。
其次,“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允许臣民以多种途径提起诉讼,给予臣民以争胜伸冤的机会。明代负有监察职责的风宪官都有追问刑名与理断词讼的权力,其本意是以风宪官监察地方官的司法,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值得注意的是,臣民到风宪官处去陈告,不承担越诉之罪,不但使地方官难以办理词讼,也给所谓的“奸民”“豪强”以挟制官府的机会,再加上风宪官大多数好揽权作威,往往使地方司法混乱化,以至于“今民间所苦,第一光棍,第二贼盗,而兵扰次之”。因为这些豪强光棍,“外则胥动浮言,挟制官府,内则雠杀复业良民,及听招新民,各诬以罪,使之不得宁居”。这些豪猾奸顽,“往往投托影射,生事害人,就轻而避重”,常常有“奸顽妄捏赃私,排陷官吏者”。在这种情况下,迫使地方官“乃惟巡按批问词状,或委勘事情,则禀其意而亟为之”,他们只能够惟权是尊,“至于审刑议事,考核官吏之际,与夺轻重,皆惟巡按出言,而藩臬唯唯承命,不得稍致商榷矣”。特别是一些致仕还乡的缙绅,“一到故丘,贪饕狼籍,结纳上司,挟制府县,交通关节,利己害人,颠倒是非,报复私怨,甚者欺压宗族,待尊长如路人,凌夺乡里”。这些缙绅、士绅与豪强“奸顽”,充分利用制度之便,动辄控告两院,获取批词,挟制官府,已经成为常态,因此出现不少劣绅。“劣绅继承了历史传统里最污秽的一面,官绅的勾结虽则使政府权力严密控制着基层社区的农民,阻碍着民权的发展,可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逼上梁山,造成集体农民的武装叛变。从农村到市镇,从市镇到都会,今日何处不演着这种官绅勾结压榨小民的例子!劣绅变成了腐化政治机构身上的一个毒瘤……”从司法的角度看,按照层级审理,乃是司法程序的根本,而打破层级,就会破坏司法秩序。本来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人民都认为只有贪官污吏,没有不圣明的皇帝,打官司也是认为能够打到皇帝那里,就一定能够获胜,结果却是“豪强奸顽”挟制官府,“无知小民”投诉“青天”,使原有的司法体制荡然无存,没有取得安定社会、澄清吏治的效果。
再次,诬告不实与匿名告罪问题。按照“诉讼”律例规定,诬告反坐,只要是被诬告者没有被执行死刑,诬告者就不会被判死刑,匿名告罪者乃是绞,则可见明代重视实名陈告。诬告者实名,若是查出其牵连人数众多,造成重大危害,即便是予以加刑,也不能够称之为过。如洪武二十七年,“温州府乐清县民为锦衣卫卒诬告,逮至京。事白,卫卒伏诛,赐民钞人十锭,遣还,免其今年田租”。这个诬告牵连人众,都被逮捕至京,给被诬告者带来重大的精神与财产损失,将诬告者诛杀,给予被诬告者一定补偿,应该是顺应人心之事,故《明太祖实录》将此作为朱元璋的治行予以记载。匿名则是“小人假公法报私忿诬陷忠良”。甚至“专以私揭匿名,或虚捏他人姓名,阴谋巧计,无所不至”。害人却找不到人进行核实,若是按照匿名告罪进行办理,不但会增大办案成本,也容易形成告奸,会造成社会恐慌,影响到王朝的统治秩序。
最后,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有关教唆词讼的问题。“教唆词讼”律仅仅分为三个层次:对于故意教唆者按照诬告量刑;对于受雇诬告,除了按照诬告量刑,还要按赃罪追究责任;对于教令得实则无罪。这个层次很清楚,但具体罪状不明确,因此条例增加许多罪状的描述,且有加重处罚的条款,对于有扛帮、全诬十人以上、用财雇寄、兜揽受雇受寄、专一挟制官吏、骗害良善、起灭词讼、欺打平人、结成群党、捏词缠告、制缚官府等罪状者,首重教唆越诉与直诉,其次是结成群党,再次是挟制官府,最后是起灭词讼与捏词缠告。这表明立法者对于教唆词讼的态度,教唆赴京越诉与直诉,有祸乱朝廷之嫌;结成群党则危害社会秩序;挟制官府乃是破坏统治秩序;捏词缠告则是无理取闹,因此在处罚方面也存在等差。提到教唆词讼,就会与讼师联系在一起。明代地方普遍有“代书人”,乃是官方允许的撰写词状之人,在官府的掌控之下,至少在一些“细事”诉讼方面,能够发挥劝息的作用。由于民间对官府的不信任,找官设代书人,则认为他们是站在官府的立场上,讼师却会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这就导致官设代书人难以为生,没有人愿意当代书人,而讼师却因为包揽词讼,上者能够“以此道获厚利成家业”,下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赡俯仰”,即使不能够发财致富,至少也可以为生,“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既然朝廷没有明令规定讼师是非法职业,官设代书人又很难发挥作用,就应该形成一定的管理制度,进行行业自我约束,或许可以消除诉讼方面一些弊端。不建立行业自我约束体制,加强官府的监管,一味地以“讼棍”“教唆”罪名实施打击,就很难取得实际效果。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设计理念方面存在讼简词实、疏通讼途、治官束民、治虚重情等特点,在设计缺陷方面存在讼乱官不宁、讦告多诬陷、上批下难从、讼息民不安等问题。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诉讼关乎社会的稳定。权力加强和政权稳定,是统治者考虑的第一要义。法律具有确定性、公开性,是对社会行为的一种规范,稳定的王朝要以法律为基础,而法律的完善及实施则是政权稳定的一种表现。在法律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才能有效控制治臣民,使其不对政治统治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诉讼”律例法规体系的制定,有助于法律制度的建设,是统治者一种灵活的统治策略。多种途径的诉讼,为皇帝与上司了解治下民情提供便利,通过平民的申诉之口,来暗察地方吏治之弊。为了防止地方官员蒙蔽“圣听”,派遣风宪官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运作,考察地方官员的治理情况。如果地方官员勤于政事,理政讼明,那么就不会有积案,诉讼就会少,越诉及京控、直诉案件就不会频繁发生。在统治者看来,“无讼”是天下大治的终极目标,也是长治久安之道。如果官员公正严明,明察秋毫,而非贪赃枉法,结党营私,那么也就会大大降低诉讼的发生。诉讼是不可避免的,地方官员若能够秉公处理,就能够达到讼息民安。从明代历史来看,确实有不少地方官能够这样处理。统治者通过法律的制度性建设和非制度性的儒家伦理规范,要把诉讼限制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大权独揽,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
明代地方官既负有行政责任,又兼理司法审判,集侦查、逮捕、刑讯、控诉和审判职能于一身,行政权与司法权交错重合,权力高度集中。为了防止地方官专断,朝廷的监察相当严密,特别是明代中叶以降,地方既有巡按,又有巡抚,还有镇守中官,形成“三堂”架构。在地方上原有的都、布、按三司也依然存在,而布按二司的副职,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成为守巡道的长官,皆有巡视监察的使命,办理词讼也成为专责。除此之外,还有兵备、提学、抚民、巡海、清军、驿传、水利、屯田、招练、监军、督粮、协堂、驿传、盐法、抚治、漕储等诸多的道,都有监察地方官之责,且能够办理词讼。因为司法权从属于行政权力,无法真正达到监察制衡的目的。在权力的运作过程中,地方官员的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又会使监察形同虚设。在疏通讼途的情况下,给官民提供诉讼的便利,有些冤屈往往能够通过上诉与直诉的方式予以得伸,官员的徇私舞弊及腐败也常常因此而暴露。从地方治理的角度来看,“诉讼”律例法规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监督官员的功效。
明代“诉讼”律例法规体系的一些缺陷,也给一些刁钻健讼、借讼渔利的人提供便利。朱元璋曾经采取非常手段,“若城市乡村有等起灭词讼,把持官府,或拨置官吏害民者,若有此等,许四邻及阖郡人民指实赴京面奏,以凭祛除,以安吾民”。其后世子孙对于唆诉刁健之人也深恶痛绝,特别是对那些影响社会秩序稳定的刁钻健讼之人,一直持严惩的态度,甚至赋予地方官以立毙杖下的权力。在统治者看来,这些人“上侮朝廷,下虐良民,为害深重”。他们往往“诉一事而添捏数端,告一人而牵连十数,上以欺诳朝廷,下以冤陷良善”。教唆词讼不但会扰乱人心,威胁到统治秩序,更关乎地方治理。
注 释:
① (奥)凯尔森著,沈宗灵译:《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② 李交发:《中国诉讼法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第257页。
③ (清)谈迁著,汪北平点校:《北游录·大清律》,中华书局,1960年,第378页。
④ 王锺翰:《王锺翰清史论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3册第1701页。
⑤ 《明太祖实录》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条。
⑥⑦⑧⑨⑩ (明)焦竑辑:《国朝献徵录》,学生书局,1984年,第2143、2371、1252、2550、42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