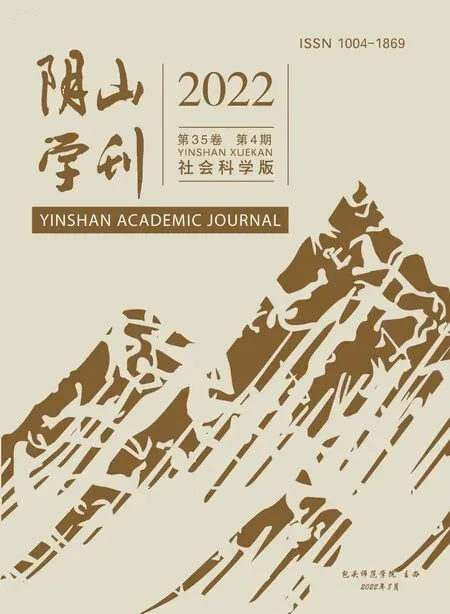朔州昭君墓真伪考辨
闫 涛
(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王昭君名王樯字昭君,号宁胡阏氏,是一位美貌出众且正直坚毅的女性,她克服千难万险远嫁匈奴,为汉匈和平稳定做出巨大贡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因此昭君作为中国自汉朝两千年来维护和平的代表人物,是各朝各代各族人民怀念吟咏的对象。昭君虽不曾途经中国北方的每一寸土地,但在我国北方遍布着数座有迹可循的昭君墓,昭君墓的修建体现着人们对昭君的哀思与对安定生活的向往。王昭君墓葬位置历来是昭君相关研究的议题之一,《汉书》《后汉书》等史书并未对昭君埋葬位置进行记载,林干和马骥在所著《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一书中提出:“在内蒙古和山西北部,传说中的昭君坟墓有十几处之多”[1],翦伯赞先生在《内蒙访古》中也写道:“据内蒙的同志说,除青冢外,在大青山南麓还有十几个昭君墓”[2]391。王绍东教授和汤国娜通过对历代文献和民间传说的梳理,对分布于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的十余处昭君墓葬进行了系统的分析[3]。学者孙利中认为:“现存于呼和浩特南郊的汉墓遗址,应该就是汉代王昭君的墓葬”[4]。宝音先生认为:“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昭君坟,实为成吉思汗古尔伯勒津高斡夫人之墓”[5]。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山西朔州青钟村昭君墓为王昭君所葬之处,郑凤岐和齐宏亮先生所写的《昭君坟茔今安在——王昭君葬在朔州市青钟村的几个证据》[6],以及武步成先生所作《关于王昭君墓的几点考证》[7]为其代表文章。笔者认为昭君墓在山西朔州市的观点缺乏可信的依据,故撰此文辨其真伪,疏漏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王昭君变文》史料价值辨析
在论证山西朔州青钟村昭君墓真实性的文章中,创作于唐代的《王昭君变文》被大量引用,其中部分章句甚至被当作该研究的重要依据,但笔者认为在昭君墓位置探究中应该谨慎使用《王昭君变文》,理由如下:
首先《王昭君变文》并不是史料价值高的史书典籍,而是一部文学作品。“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四万余卷古代遗书。”[8]1创作于唐代的《王昭君变文》也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发现的。《王昭君变文》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王昭君变文》第一次以说唱文学的形式塑造了王昭君这一已经长期流传的形象,使得一个之前主要在文人中流传的文学形象逐步走向了民间”[9],由此可见其是一部文学作品。基于其文学作品的性质,近现代学者对于它的研究也并未把重点放在史料价值方面,而是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关于《王昭君变文》的创作时间的研究;二是关于《王昭君变文》的文本研究”[10]。
最后是《王昭君变文》虚构想象的内容较多,用其研究汉代历史易出现偏差。《王昭君变文》中某些章句可与史书典籍相互印证,但更多的内容需要我们细心辨别,如“解剑脱除天子服,披头还着庶人裳”一句[8]277,用“天子”来指代匈奴单于显然与史实不符;又如“昭君昨夜子时亡,突厥今朝发使忙”一句[8]277,“突厥之名最早见于《周书》卷二七《宇文测传》。《传》载西魏大统八年(542年)以前,突厥每岁于河水结冰后……据此可见,突厥的兴起当在六世纪中叶”[13],变文作者用6世纪中叶兴起的突厥指代西汉末年的匈奴,显然与史实不符。
包括唐诗在内的文学作品可以适当地运用在历史学研究中。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其著作《治史三书》中言及他把诗篇当作史料,严耕望先生认为:“近代研究唐史,以‘诗’‘史’互证,自推陈寅恪先生为最著”[14]145,而自己“以‘诗’证‘史’,只是从浅显处着手,就‘诗’的表面意义加以运用,以显现史事之面目”[14]146。陈寅恪先生学术水平之高自然毋庸赘言,严耕望先生的学术成果也极为丰富,在此有谦虚之意。从上述话中我们能领悟到,诗词等文学作品可适当运用在史学研究中,但前提必须是与史料结合,相互佐证,这样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亦能令人信服。总而言之,《王昭君变文》在昭君墓位置相关研究中可信程度不高。
二、关于昭君墓在山西朔州青钟村的考辨
《昭君坟茔今安在——王昭君葬在朔州市青钟村的几个证据》一文作者为证明其“王昭君葬在青钟村的可能性极大”的论点[6],从匈奴单于庭位置到昭君墓葬的距离、汉朝北方与匈奴边界的位置、受降城的位置几个方面展开论述,论证山西朔州市昭君墓真实性,经过分析最终得出昭君墓葬应在朔州的结论,笔者认为其文章结论不可信,理由如下:
(一)匈奴单于庭位置问题辨析
持昭君墓在山西朔州市观点的学者认为:“安葬昭君时是从单于牙帐(即今呼和浩特市)出发,共走了600里路,才到了安葬的地方”[6],提出“经考证,从呼和浩特市单于牙帐出发经右玉杀虎口到青钟村,其距离正好是600里”[6]。其认为单于庭应当在今呼和浩特,并由此推测王昭君墓的位置,实际上这样的论述是经不起推敲的。
关于历史上的匈奴单于庭在何处的问题,《史记》仅记载冒顿单于统治时期,匈奴“单于之庭直代、云中”[15]2891,“直”指直对、面对,代郡与云中郡的辖境较为明确,代郡“辖境包括今内蒙古兴和县、商都县等地”[16]35,云中郡“主要辖有今呼和浩特平原大部”[16]3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匈奴单于庭的位置应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及乌兰察布市直对的阴山以北地区。匈奴单于庭的位置历来被学者所关注,如曹永年先生认为:“冒顿单于(公元前209—前174年)以前,单于庭头曼城在今巴彦淖尔市乌加河北的阴山中”[17]。学者邱树森对这一问题所持的观点与其相近,认为匈奴应有南北共两处单于庭,并在文章中写道:“战国以来,匈奴之统治中心最早在阴山……这样,单于南庭在阴山之中是无疑的”[18]145。至于匈奴北庭的位置,他的结论是“单于庭应在今色楞格河之南、厄尔德尼满达尔东南二百余里、鄂尔浑河以东一带求之,当属无疑”[18]148。由以上学者研究结论可知,匈奴头曼城也就是所谓匈奴单于南庭应当在阴山山脉中,其地水草丰美,对于“随畜牧而转移”的匈奴民族来说[15]2879,应当是极为适宜其生存的环境。
位于阴山之中的头曼城为匈奴早期的单于庭应当并无争议,但匈奴单于庭的位置也并非一成不变,至于西汉中后期匈奴单于庭的位置,我们可以依靠时间线索进行分析。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匈奴迁至大漠北部[15]2910,而今呼和浩特地区位于漠南,所以呼和浩特所辖地区在这一时期应归汉朝所管辖,因此说单于庭在呼和浩特是没有史料依据的。
西汉宣帝、元帝统治时期,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危机重重,争斗不断,作为稽侯栅呼韩邪单于在腹背受敌的危难下,与汉朝缔结了友好盟约,最终统一匈奴各部。经过对《汉书·匈奴传》的梳理,我们可以得知呼韩邪单于的统治重心依时间推移,应有以下几处,首先他在“西击握衍朐鞮单于,至姑且水北”之后[19]3790-3791,成为匈奴单于,从而“归庭数月,罢兵使各归故地”[19]3795,我们可以推断,此时匈奴单于庭在漠北。其后“单于自请愿留居光禄塞下,有急保汉受降城”[19]3798。说明因受到郅支单于的威胁,呼韩邪单于曾将统治重心置于光禄塞下,“光禄塞东起自五原郡北面的阴山后面,西北伸延至庐朐(河名,在今蒙古国境内)”[20]45-46,结合“五原郡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以东地区、包头市及伊盟东北部”可知[16]34,汉代光禄塞的范围应大致相当于今内蒙古包头市北部向西北至蒙古国境内一线,距离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最后“呼韩邪竟北归庭,人众稍稍归之,国中遂定”[19]3801。因王昭君生活于这一时期,所以唐代诗人所写的匈奴王庭最有可能指代此处,但这时的匈奴单于庭在漠北地区,与今呼和浩特市相距甚远。
另外,考古资料也能够为匈奴单于庭不在呼和浩特这一结论作证。“两汉时期的匈奴墓葬集中分布在杭爱山以北,色楞格河下游支流吉达河、奇科伊河以南,巴彦山克鲁伦河中游以西,萨彦岭伊德尔河以东地区,这与文献记载匈奴民族主体及其统治中心的分布范围基本吻合。”[21]说明匈奴民族的主要活动范围应在这一地区,这一地区基本为以今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为中心的广阔地域,而且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在地理位置上相距极远,也佐证了匈奴单于庭不可能在呼和浩特的论点。当我们将匈奴墓葬位置研究范围再次缩小,可以明确在今蒙古国“匈奴大型墓葬主要分布于蒙古中部偏北的省份和与蒙古中北部和西北部接壤的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和图瓦地区”[22]。匈奴墓葬大量出土于这一地区,更让我们坚信匈奴单于庭不在今呼和浩特地区。近年来匈奴单于庭相关考古也取得进展,如中国与蒙古国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称:“在蒙古国中部地区发现距今约2000年的疑似匈奴单于庭‘龙城’遗址”[23],虽然此遗址没有被最终确认,但也能为探究单于庭位置提供借鉴。
最后法官宣判我净身出户。依照现行的婚姻法,夫妻双方若有一方犯生活作风问题,才会被剥夺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而净身出户。我就像那种生活作风出问题的男人。
从呼和浩特地区考古发掘来看,匈奴单于庭也并非在呼和浩特地区。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大学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沙梁子村揭露一处距今约2000年的西汉中晚期疑似大型粮仓建筑基址……根据建筑基址上发现的沟槽结构以及出土遗物判断,此遗址很有可能是西汉大型粮仓建筑基址”[24],基于这一汉代粮仓的出土,我们可以清晰地推断出:在西汉时期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地区是汉朝的管辖范围,既然这一地区归属汉朝,那匈奴单于庭便没有安置在此处的可能。
纵观匈奴崛起、强盛至衰落的历史,从未有将匈奴单于庭置于今呼和浩特也就是汉朝时定襄郡的记载,换言之即使唐朝诗人由于年代久远,将匈奴单于庭位置与对应年代相混淆,匈奴单于庭几乎没有可能在今呼和浩特管辖范围内。
(二)“蕃汉界头”位置问题考证
《王昭君变文》描述汉哀帝时派使者“入于虏廷,慰问蕃王”[8]286,返回时“行至蕃汉界头,遂见明妃之冢”[8]290,由此郑凤岐、齐宏亮先生提出“‘蕃汉界头’也应该是雁门关附近,‘明妃之冢’当指青钟村昭君墓”[6]。其认为《王昭君变文》所描写的是汉朝使者行走到汉朝边界,在距离雁门关不远的青钟村见到昭君的墓葬。汉朝使者出使时雁门关并不是汉朝与匈奴的边界,所以作者的这一观点应该被重新审视。
《王昭君变文》中描述汉朝使者返回途中在“蕃汉界头”看到了明妃之冢,笔者认为此处的“蕃汉界头”指汉朝与匈奴的边界,而不是变文作者所生活的唐朝与突厥及回纥的边界。因“蕃汉界头”这一概念是在《王昭君变文》中被提出,所以针对这一问题我们也应回到变文中寻找答案,首先《王昭君变文》习惯将匈奴记作“蕃”,例如描述王昭君去世时言“一依蕃法,不取汉仪”[8]281。其次在《王昭君变文》中,“汉”指代汉朝,变文描述王昭君“如今以暮(已沐)单于德,昔日远承汉帝恩”[8]248,此处汉帝与王昭君所嫁的匈奴呼韩邪单于相对应,所以“汉”应指代汉朝,如果没有特殊说明,我们有理由认为下文“蕃汉界头”中的“汉”也指代汉朝。再次《王昭君变文》作者生活于唐代,若“蕃汉界头”指唐与突厥及回纥的边界,作者应记载较为确切的地理位置,而不是使用这样一种较为模糊的表达方式。
汉朝与匈奴的边界位于何处的问题,我们应当从史籍中寻找线索。《汉书·地理志》记述:“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19]1543,由此来看,我们可以由秦至汉,以时间为线索,探究“蕃汉界头”问题。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秦朝的北方边界比较清晰,《史记·秦始皇本纪》描述秦朝疆域“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5]239,意为秦朝北守黄河,边界从阴山延伸至辽东。《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至汉初匈奴冒顿单于“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15]2891。利用这部分史料的记载,我们能够对当时汉朝与匈奴边界进行推断,匈奴的左中右领地分别与汉朝的上谷郡、代郡、云中郡以及上郡相对,以上所举四郡均属于汉朝管辖,所以汉朝北方与匈奴边界当在四郡辖境的北侧沿线一代。
汉朝北方与匈奴边界发生重大变化应当发生于武帝时期,武帝于太初三年(前102年)“派光禄勋徐自为兴筑五原塞外城障列亭,并派路博德筑塞居延泽上,于是构成了汉王朝最北一线的军事防御设施,也是将汉王朝的疆域固定在外长城一线上”[25],此举导致“匈奴自阴山北撤,而后又西北迁徙,失去了南下中原的战略要地”[25],从汉武帝时期长城所处的位置,我们也可以大致推测出汉朝与匈奴边界的位置,应当是在阴山以北。
汉元帝时王昭君出塞,汉哀帝时使者出使匈奴,因为其均为《王昭君变文》记述的内容,所以这一时期的汉朝北方与匈奴边界当为研究的重点。西汉中后期汉朝北方与匈奴的边界变化较小,“汉宣帝、汉元帝曾与呼韩邪约定,长城以北地属匈奴”[26]。由上文可知汉长城的位置,从而我们能够推测此时的汉朝北方与匈奴的边界当在长城沿线。元帝将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时,呼韩邪单于向汉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19]3803,“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19]3803,侯应以为呼韩邪的建议不可行,最终元帝要求“勿议罢边塞事”[19]3805,由此可见在元帝统治时期,汉朝北方边境比较稳定,边防策略也与之前基本相同。“元帝以后,汉王朝虽逐步走向衰落,但边境地区由于武、昭、宣三代的经营,已经基本无事……成、哀两帝时期,西汉王朝疆土保持不变”[27]。从此直到西汉末王莽代汉以前,汉朝北方与匈奴的边界较为稳定,因此结合武帝时期的长城位置,以及汉哀帝时期较为稳定的汉匈关系,我们可以推测此时的“蕃汉界头”,应当在长城一线而不是雁门关附近。
关于汉代“蕃汉界头”是否在雁门关的问题,考古发掘也能提供理论支撑。“目前在汉代司隶校尉部以北的长城沿线,包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北部、宁夏全境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都发现了数量众多的汉代墓葬”[28],另外“汉代是包头地区行政设置时间最长的朝代,在三百余年的统治中,留下了大量的古城址和古墓葬”[29],由此能发现位于雁门关北部的内蒙古中南部以及内蒙古西部的包头等地,均有一定数量的汉代墓葬遗址,汉代墓葬遗址的存在说明这些地区应当是属于汉朝管控,所以位于这些地区南部的雁门关所在区域,也是汉朝的领土,不可能是汉朝北方与匈奴的边界。
雁门关是汉朝北方与匈奴边界的说法,存在的另外一个错误是雁门关并不出现于汉朝,因为“战国秦汉时期有了雁门山,也有了雁门郡,不过还没有看到有关雁门关的记载。”[30]学者杨丽也提出:“秦汉时期没有雁门关一说,时称勾注塞或‘雁门险阻’,至北魏建都平城时,重新建关才称雁门关”[31]。并且给出了相应的位置,“秦汉时期的雁门关在今关城西南约5公里,在今代县白草口乡和太和岭乡之间的分水岭上”[31]。此外我们查阅谭其骧所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可以发现,代县的地理位置在西汉时北方重镇马邑的东南方向,由地图所见应当与当时汉朝北方与匈奴的“蕃汉界头”相距甚远[32]17-18。综上所述,“蕃汉界头”在雁门关的论述缺乏史实依据。
(三)唐朝受降城在朔州问题辨疑
郑凤岐与齐宏亮先生认为《王昭君变文》中“只今葬在黄河北,西南望见受降城”一句所提到的受降城的地理位置[8]282,应当在今山西朔州市,推断“唐朝时的受降城在朔州也有一座”[6],学者武步成与其观点一致。但经过系统分析,笔者认为此说并不可信,可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论证:
第一,是其在引用材料时出现错误,一是引用时断章取义,未能全面征引材料;二是所引材料本身有误。在考证朔州的唐受降城真实性时,其依据的是《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唐受降城有三,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33]以及《汉语大词典》“唐筑有三城,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34]的记述。但经过对原著的查阅,我们可以发现其在引用两部辞书时,均未引用重要章句,从而导致得出错误结论。《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唐受降城有三,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皆在黄河之外”[33]。《汉语大词典》记述受降城“唐筑有三座,中城在朔州,西城在灵州,东城在胜州……《新唐书·张仁愿传》:‘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骑施,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虏南寇路’”[34]。经过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作者在引用时将受降城位于黄河之外与黄河以北这样重要的内容遗漏,导致出现知识性错误。当我们查阅同类型辞书时也能够发现,《中国地名词典》记载朔州时写其“名胜古迹有崇福寺、翠华山”[35],并未提及唐代中受降城及青钟村昭君墓。
对于作者遗漏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和《汉语大词典》中关于唐代三受降城建在黄河以北的记述,笔者认为可信。张仁愿将受降城设于黄河以北的史实,除上文提到的《新唐书·张仁愿传》可以证明之外,《旧唐书》载:“朔方道大总管张仁亶筑受降城于河上”[36]146,《明史》记载:“唐三受降城在河外”[37],也都可以为其提供史料支撑。毫无疑问今山西朔州市青钟村在地理位置上属于黄河以南,而史料记载唐代三受降城的位置都在黄河以北,所以青钟村应当没有唐代受降城。
至于“中城在朔州”的描述,有学者注意到此问题,并提出“中、西受降城皆在丰州,而非朔州和灵州”[38]。另外通过对《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进行查阅,可知唐代朔州位于胜州的东南方[32]34-35,假若中受降城修筑于朔州,则会出现中受降城位于东受降城东方的布局,显然不符合常理。同时我们也能从地图中发现唐代三座受降城的位置,与今日山西朔州市距离较远。由此可见唐代中受降城位于朔州的说法确实缺乏有力依据。至于唐代三座受降城的位置,我们可从史籍和考古发掘中寻找答案。
第二,通过对有关唐代受降城相关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史书对唐代三座受降城位置的描述较为明确。《元和郡县图志》记:“东受降城,本汉云中郡地,在榆林县东北八里,今属振武节度”[39]115,李逸友先生考证:“东受降城城址在今托克托县托克托城的大皇城”[20]78。《元和郡县图志》记载:“西受降城,在丰州西北八十里。盖汉朔方郡地,临河县故理处”[39]116,也就是说唐代西受降城的位置与汉朔方郡接近,“西受降城城址在今乌拉特中旗乌加河乡库伦补隆村”[20]78。经过对唐代东、西受降城修筑位置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两城的地理位置在史书中较为明确,且都没有修筑在今山西朔州市的可能,同时也并无考古发现能够推翻《元和郡县图志》等史籍关于唐代东、西受降城位置的记载。
关于中受降城的地理位置,《旧唐书》记载:“以拂云祠为中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皆据津济,遥相应接”[36]2982,描述唐代中受降城在拂云祠,《资治通鉴》解释为“祠在拂云堆,因以为名”[40],拂云祠的位置也较为明确,拂云祠原在突厥控制区域内,后张仁愿在这里建中受降城,“拂云祠的大方位当在黄河北岸附近,具体位置就在中受降里面”[41]444。《元和郡县图志》也记载:“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汉武帝元朔二年更名五原,开元十年于此城置安北大都护府”[39]115。可将中受降城的位置进一步确定在秦朝的九原郡。“突厥将入寇,必先诣祠祭酹求福,因牧马料兵而后渡河”[36]2982,对突厥人而言,祈福希求庇佑应当是极为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说其坐落于雁门关附近的朔州市青钟村,不仅不符合“河北岸有拂云神祠”的史实[36]2982,而且有违突厥人不会将祈福的场所置于唐朝所统辖的朔州附近的常情。另外关于中受降城的较为丰富的考古资料也有力地证明中受降城在朔州的说法站不住脚。“中受降城城址位于包头市郊区共青农场所属的敖陶窑子,平面呈方形,周长约1500米,残高约1.5米”[20]79,同时发掘“遗物中的盘口高颈陶壶、折沿盆和粗白瓷碗,包括‘开元通宝’钱,同为典型的唐代遗物;三彩盘和单面饰有沟纹的条砖都具鲜明的辽代特征”[41]443-444,城址中遗物证实其确为唐代中受降城,由文献记载以及考古发掘来看,中受降城在朔州的说法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值得注意的是受降城并非唐代所独有,汉武帝太初元年“汉使贰师将军广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将军敖筑受降城”[15]2915,西汉时公孙敖奉命修筑汉受降城,这座受降城的遗址位于“今巴盟乌拉特中旗东部阴山北”[16]32,因此即使《王昭君变文》中的受降城是指汉受降城,其地理位置也没有在山西朔州市的可能。综上所述,我们有理由认为山西朔州市拥有一座受降城的说法可信度不高。
三、结语
在《内蒙访古》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王昭君究竟埋葬在哪里,这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多的昭君墓”[2]391。各地的昭君墓葬体现着历朝历代人民对王昭君的崇敬。“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2]390所以存在于我国内蒙古、山西、陕西等地的昭君墓葬的真伪并不是最重要的课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曲解历史,对历史发表不客观的观点。
正如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所言:“现在的确出现了一种史学民粹化的现象或倾向”[42]。其中一个特征便是一部分人“随意泛化历史,将所有涉及过去的内容都当成历史,自以为了解过去就有资格谈历史,甚至评论、研究历史”[42]。北京大学的赵冬梅也提出:“我国有悠久的史学著述传统,普通民众对历史也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这种兴趣往往不以‘求真’为前提。”[43]为避免这样的现象出现,我们在进行王昭君墓葬位置研究时,应当把历史研究的落脚点放在可信度高的史书典籍中,利用更为权威的史料佐证自己的论点,《汉书》《后汉书》等史书中有关王昭君的记载较少,这是昭君墓葬位置研究的难点,但即使如此,也不应在史学研究中完全依赖文学作品。近年来伴随着考古发掘技术的提高,考古学成果与日俱增,简帛文献的出土以及器物的发掘都为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借鉴,至于昭君墓葬的真伪问题,我们也理应期待考古发掘为我们带来突破,将考古成果与史书典籍相结合,尽力还原昭君墓葬的真实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