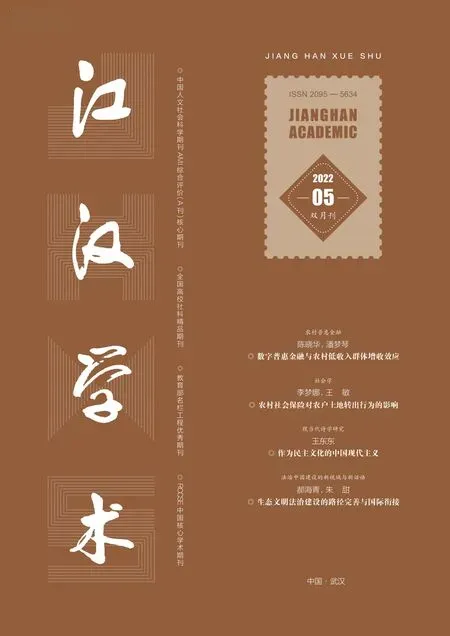作为民主文化的中国现代主义
——重识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
王东东
(山东大学 文化传播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9)
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在1940 年代已经成形,但迟至1980 年代才结集成书,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文化政治难题与征候。实际上,新诗现代化理论隐藏的是袁可嘉对作为民主文化有机构成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思考。现代主义诗歌或新诗现代化与民主的关系是袁可嘉的重要思想探索之一,如果不是最为重要的话①。要认清这一点,就必须回到作为“政治时代”的1940 年代,意识到袁可嘉展开论述之时的抗辩性语境。相对于1940 年代中后期一直占据主流的左翼民主诗歌,他将民主文化和价值“投射”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艰难运思,构成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一种被遗忘的文化身份,以及一种难以摆脱的“晦涩”的文化命运。
一、新诗现代化与民主
从“批评与民主”到“诗与民主”,将“民主”一词从“人民诗歌”“民主诗歌”的“统一”或“独裁”——均为袁可嘉用语——中剥离了出来,可以看到袁可嘉的具体思路:诗的民主化首先要求批评的民主化,这一民主化的过程就是将民主的价值追求“内化”在诗歌创作行为之中的过程。而另一方面,这同时又是袁可嘉将新诗现代化或戏剧化理论在民主语境中加以“深化”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同时性”可以证明,民主话语与新诗现代化的话语实际上构成了袁可嘉诗与民主思想的二重奏,二者相互配合,在“同一和差异”中产生了更多繁复的旋律。袁可嘉不断整理甚至调整自己的思想更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并不讳言自己行文中或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这些“重复”构成了他思想旋律的练习。
因此,在研究袁可嘉诗与民主的思想时,有必要时时将二者关联起来,比如将袁可嘉最为成熟的文章《诗与民主》与《诗的戏剧化》(均写于1948 年)等量齐观,甚至做一个前者对后者思想的“覆盖”而却并无“后设”的危险。由于奠定袁可嘉二重奏话语的《批评漫步》与《“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均发表于一年前;而袁可嘉最早发表的两篇文章《论诗境的扩展与结晶》《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均为1946 年),相互间也可以形成对民主的反思与对诗艺的反省的对位关系。其实在袁可嘉的论辩对象“民主诗歌”中更鲜明地存在着民主话语与诗歌话语两种话语的协调问题,但因为没有标示现代主义这个特殊的诗艺形式,更因为缺少对诗歌创作过程的独特理解,它简陋、粗浅的诗歌话语显得更多从属于民主话语甚至是民主话语的附庸。袁可嘉对后者的指责是,它们由“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而导致了“说教”与“感伤”:
……说明意志的作者多数有确切不易的信仰,开门见山用强烈的语言,粗砺的声调呼喊“我要……”或“我们不要……”或“我们拥护……”,“我们反对……”,表现激情的作者也多数有明确的爱憎对象作赤裸裸的陈述控诉。说明意志和表现情感都是人生的大事,完全是必需的而且是值得赞美的。因此这两类诗的通病——或者说,它们多数失败的原因——不在出发的起点,因为起点并无弊病,也不在终点,因为诗篇在最终总给我们极确定明白的印象,够强烈而有时不免太清楚,而在把意志或情感化作诗经验的过程。
而诗的唯一的致命的重要处却正在过程!一个把材料化为成品的过程;对于别的事物,开始与结束也许即足以代表一切,在诗里它们的比重却轻微得可以撇开不计。……
由于这个转化过程的欠缺,新诗的毛病表现为平行的二种:说明意志的最后都成为说教的,表现情感的则沦为感伤的,二者都只是自我描写,都不足以说服读者或感动他人。[1]
对袁可嘉这段话,刘继业有一个精彩的评价:“‘过程’,成为现代主义新诗和包含政治感伤性、说教性的‘人民派’新诗在艺术上的区分点和试金石。袁可嘉用‘过程论’更进一步、更深层次地阐释了新诗的感伤以及其他流弊的产生,‘过程’成为考察新诗的一个基本视角和诗学标准。”[2]刘继业由此总结出“题材、主题和艺术过程的两种偏执”。但实际上,袁可嘉之所以对艺术创造过程如此重视,正是因为他将民主的价值内化在了这个环节中,甚至将民主等同于一种特殊的“现代主义”的诗歌创造方式,这造成了袁可嘉与占据主流的“民主诗歌”的主要不同。而现代主义诗歌带来的晦涩问题,也和袁可嘉民主文化观念之下的批评尤其诗歌创作密切相关,甚至是难以摆脱的一个因素。
然而,晦涩既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虽然在袁可嘉这里它更多被当作一个形式问题来处理,《诗与晦涩》是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系列中的第三篇论文,对晦涩的思考和对“政治感伤性”以及稍晚时对“诗与主题”的批评联系在一起。袁可嘉认为晦涩一共有五种“主型”,但他在分析时似乎结合了成因、动机和效果,因此实际上他的分类有点混乱,虽然并不妨碍他卓见频出。他首先谈到了“现代诗人所处的厄境”,由于“传统价值的解体”也就是共同文化的丧失,现代诗人对于读者来说不得不是晦涩的;第二种源于现代诗人的一种偏好,或从不同历史文化包括文学文本中——这从袁可嘉主要以艾略特的《荒原》为例可以看出——汲取元素并综合之,或“完全摆脱历史,只从日常事务的巧妙安排,而得综合效果”;第三种现代诗的晦涩是由于“情绪渗透”,举例则为艾略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里一段戏剧独白,袁可嘉论证说:“我们往往不能一时确指他们的真意或作用;而只能就全诗主要情绪变化方向获取延长性的情绪感染”,但这一类晦涩疑与第二种晦涩重叠;“第四种晦涩是由现代诗人构造意象或运用隐喻明喻的特殊法则所引起,也就是现代诗中最可明确辨认的性质之一”[3];第五种晦涩为诗人“荒唐运用文字”或基于潜意识而写诗,路易·麦克尼斯在《诗的晦涩》中也对此加以批评,这篇文章早经穆旦在1940 年译出并在1941 年发表于香港《大公报》上。第一种类型可谓是晦涩的社会成因,这一点是左翼民主诗人和袁可嘉共同分享的,而中间三种都是晦涩的艺术成因,恐怕为“现代主义”所独有,而第四种晦涩——这一种实际上可以涵盖中间三种,可以说是深入到了现代主义诗艺的本质——堪称现代诗的晦涩的荦荦大端,也最值得注意,对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晦涩难懂的指责,其主要原因就在这里。袁可嘉试图将包含晦涩的现代主义诗歌纳入民主文化的语境,其难度可想而知,但并非不可行,但假若他想要让左翼诗人也承认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也可以属于民主诗歌就难上加难了。袁可嘉也坦白了他对左翼民主诗歌的感受:
……颇有一部分失之过分认真的人们相信,信仰上的差异是他们不能欣赏一部分诗作的基本障碍:具体的例子表现在这样的谴责里:“你们不能领会人民诗的好处,是因为你们根本不赞同人民派的政治路线;如果你们同情——不要说共同来积极争取——他们推进民主的努力,你们一定会赞美他们的诗作!”个人听见这种责难不止一次,仔细想过却不接受这个判决主文;固不问我们是否无条件地完全同意某一部分人士的政治路线,但诗与信仰的关系决不会单纯到一是二,二是一的地步;我不是教门中人,但我热爱许多好的宗教诗(如克劳岱尔的《带给玛丽的消息》);三十年代直接参加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奥登派总够普罗了吧,我也竭诚赞赏其中许多成功的政治诗作;麦克里须总够人民的吧,我也爱读他的广播诗剧,可是对于我们自己的人民诗作的赞美,我却总觉得十分踌躇;原因也许很多,但决非信仰作梗,因为在争取民主的信仰上,我自信与别人并无不同……[4]
袁可嘉的特出之处在于,他可以饱含理解地看待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念,但对于他来说,一些左翼民主诗歌似乎缺乏与政治观念相称的足够的艺术技巧、高度与说服力。袁可嘉无法接受后者“强调集体的,阴暗面的,粗犷的,属于狭义的感情(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于粗砺的情绪的陶醉”[4],这些在他眼中都犯了“感伤性”的毛病。左翼民主诗歌在内容上“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活力的唯一表现形式”,而在形式上则“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没有一种艺术不要求‘力’,适应今日政治环境要求的诗作尤其应该有力。但我们的阅读经验使我们相信,今日有不少诗作者不幸地以诗意的粗劣代替了力。任意的分行,断句,诗行排列的忽上忽下,字体的突大突小,成林的惊叹符号的进军,文字选择的极度大意,组织的松懈,意象的贫乏无力,譬喻的抄袭、不确,都足以说明这些急欲显示伟力的诗作的奇异地无力的原因,因为我们明白知道,只有成熟的思想配合了成熟的技巧的作品才能表现大力。”[5]形式与内容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对袁可嘉来说,显然有什么样的民主观念,就有什么样的民主诗歌。在对左翼诗歌技巧的分析中,袁可嘉显然将矛头指向了“马雅可夫斯基体”。袁可嘉还谈到了另一个形式问题,“对于民间语言,日常语言,及‘散文化’的无选择的、无条件的崇拜”[4],民间语言和日常语言的结合显然应该是指袁水拍山歌一类的歌谣体。
二、民主诗歌的两种途径
虽然袁可嘉并没有点名批评左翼诗人而只是笼统地一笔带过,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他和左翼诗人之间作一下对比,以更好地认清二者在诗歌形式上的差异。以袁可嘉在《漫谈感伤》中指责的《文艺复兴》1947 年6 月号“诗歌特辑”上李白凤的《颂诗》为例:
你
真理的战士
劳动英雄
爱护真理的人底血液
脉络相连的河流
我们底方向是
民主自由的大海。
你们
生长在群众中
如金在砂中
砂石因你们而光耀。②
与现代主义诗歌的“晦涩”比起来,它最大的特征可以说是“明晰”。“诗歌特辑”中闻一多的两首诗《肉搏》和《致敬》也是如此,《致敬》写一位抗战名将在“内战”中解甲归田,正见出当时知识群体将“反内战”等同于“民主”的思路。这种思路在臧克家的《宝贝儿》中贯穿始终,李白凤在评价其中的《人民是什么》一诗时说:“人民觉悟了,他们已经开始用罢工、请愿、组织工会……的直接行动来表示他们底欲求了;今后,在民主运动的觉悟里,他们将更积极地站起来,使广大的群众联合在一起,选择他们自己所要的政府。”[6]最后一句可以说“预言”了左翼民主诗歌由讽刺到歌颂的转向,而这种转向与内战的发生、发展和终结相呼应,应该是左翼民主诗歌在这一时期的特点。李白凤在《颂》中的“民主自由的海洋”的措辞也可以让人联想到臧克家的诗集《民主的海洋》。然而,臧克家富有表现力的诗歌形式得益于闻一多良多,他将这种“新月派”的技巧用于表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内容而获得较高的象征地位,而后来的左翼诗人如李白凤就没有这么幸运。这自然和他们写作的时代脱不了干系,对于左翼民主诗歌的后起之秀来说,如果追求艺术上的难度的话显然会受到批判,而如果不追求的话他们又很难获得认可——不是来自对立面而是就来自左翼民主诗歌内部——这甚至构成了左翼民主诗歌在美学上的难题甚或悖论。他们不太可能做到像臧克家那样将美学水平和政治水平紧密结合而不会过分偏斜于任何一方的“中庸水平”,然而,这个中庸水平如何判定显然不无主观,即使臧克家在1940 年代后期也受到来自左翼民主诗歌阵营内部的批判③。《文艺复兴》“诗歌特辑”中还有很多现在已不知名的左翼诗人,在数量上绝对压过现代主义诗艺的操持者和模仿者,可以充分表明左翼民主诗歌的“衍生性”。“衍生性”并不等于或出于复制:左翼民主诗歌的标准要求使得很多左翼民主诗歌是无效的,要么是对方的政治水平不够,要么是对方的美学水平不高。但它绝不会否认有自己的美学标准,因为那样无异于承认它就是美学水平不高的诗歌。
对于1940 年后期大面积出现的民主诗歌来说,袁可嘉在艺术上的指责应该说并不离谱。再来看看当时的几本诗集,黄宁婴的《民主短简》、海涛(叶淘)的《向民主进军》、苏君夫编的《民主诗歌》。其中艺术成分最少的《民主诗歌》显然非常看重“宣传”效果,它一共分为“练兵、生产、民主之声、颂”四章,“练兵”中有不少左翼批评家引以为豪的“枪杆诗”,鼓动人们杀敌作战,应该属于袁可嘉批评过的迷信“力”的诗,“颂”中则有“列宁颂”“斯大林颂”等。《民主短简》《向民主进军》都是出自左翼知识分子之手的民主诗歌,虽然不一定符合“工农兵方向”的正统要求。黄药眠肯定了《民主短简》很强的“政治性”和“政治目的”,“这是中国的进步的智识者,以诗的形式写出来的政治宣言”,但同时又不满于“从内容到形式,作者的诗,还是智识分子的”[7],表现出要将相对“中性”的民主诗歌转化为“新民主主义文艺”的强烈要求。这和亦蓝对海涛(叶涛)的另一本诗集《考验》的态度其实是一致的,这位《诗号角》的批评家甚至无法满足于仅仅“向左转”。黄药眠在文章结尾说:“有人爱把黄宁婴和马凡陀相比,我觉得两相比较起来,马凡陀的诗多接触到大都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近代都市人的机智,用的词句比较口语化,歌谣化,但黄宁婴的诗,则多从政治着眼,立场和风格也还是一般智识分子的立场和风格。因此在普及化的意义上看,在其所影响的范围上看,还赶不上马凡陀的。”其实,黄药眠在诗歌技巧上对《民主短简》也有挑剔,一是“理智的成份比较感情的成份浓厚”,二是“从诗的结构和形式说,有些诗也是过于单调而缺乏变化”。黄宁婴尚且如此,何况那些不知名的左翼民主诗人了。这和袁可嘉的说法又有一定相似之处,虽然黄药眠的最终导向不可能是现代主义。这一点可以说明,民主诗歌的“衍生性”难免会出现袁可嘉所谓的“技巧粗劣”的问题。
将袁可嘉与袁水拍比较一下也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发现。1940 年代后期的左翼民主诗歌中除了袁可嘉显然没有人的影响力可以和化身为马凡陀的袁水拍相比。除了各种“马雅可夫斯基体”的变形,马凡陀的“山歌”可以说是左翼民主诗歌的另一条道路,也即将民间语言和日常语言结合的“歌谣化”道路,当时即有论者说:“玛耶可夫斯基诗的擂鼓的音节,号召战斗,唤起俄罗斯人的革命的情绪。马凡陀,这城市的代言人,他紧握着城市的脉搏的跃动,向迅速变动的恶的现实,挑战,讽刺,告诉城市人怎样服膺民主的真理。不过,这不在本题之内,搁下不谈。”[8]然而,袁可嘉的诗歌趣味其实相当广泛,他在写出《马凡陀山歌》之前对现代主义诗歌也并不陌生,翻译有“奥登一代”的重要诗人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的三篇诗论《论当代英国青年诗人》《反抗中的诗人》《现代诗歌中的感性》,占了他的翻译作品《诗与诗论》④近三分之一篇幅。此书还收有一篇俄国批评家D.S.Mirskhy 的《惠特曼——民主之诗人》,也足见袁水拍在1940 年代初就热衷于“民主诗歌”和“民主诗人”的话题。在这一点上,袁水拍和徐迟的转变有相似之处,后者也在《美国诗歌的传统》一文中大谈特谈“民主主义诗歌传统”。这种转变不应该仅仅被看成是民主观念的差异所致,而是还有诗歌形式方面的差异推波助澜,虽然左翼批评家在论述他们的“转变”时总会强调民主观念的差异:“在通向人民文艺的道路上,马凡陀的山歌就是一道好桥梁,它的首要的功用,在于打破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为自我而讴歌的个人主义的诗歌传统,教育人民去拥抱现实,投向斗争,起码在精神上使他们要求改变现实;虽然,没有能够做得顶好(自然,这与他的忙碌的工作及比较狭窄的市民生活圈子有关),但他是勇敢地正确地这样做了。——敢于或肯于放弃自己出身阶级及生活现状的优越感,而拾起来人民的或接近于人民的东西自如地应用起来,好比穿惯西装的人甘心穿起破烂的衣服做一个勤劳的清道夫去倒垃圾,那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然而,袁水拍却不管。”[9]另一位批评家则给马凡陀以很高的评价:“……诗在民主阶段,必然要产生新的体别,他尽了开拓的责任。”[10]而对于袁可嘉来说,民主的诗歌或作为民主文化的诗歌需要现代主义的“难度”设计,即使受到“晦涩”的指责,他也不愿意“倒退”到“明晰”的左翼民主诗歌;而对于袁水拍来说,以现代主义形式出现的民主诗歌越来越难以实现,到后来甚至变得不再可能,他必须“前进”到“明晰”的左翼民主诗歌中。
三、形式的政治:晦涩的位置
而他们自身的诗歌“形式”在对方眼中都会被忽略不计。在袁可嘉看来左翼民主诗歌的形式是“匮乏”的,左翼批评家也根本想不到要去分析袁可嘉现代主义的诗歌形式——如果他们攻击现代主义诗歌为“晦涩”,倒说明他们意识到了形式的问题——而只需强调政治观念的崇高性:“诗歌,在今天已经担起了民主与反民主的积极的战斗的任务。像那些‘枪杆诗’‘藏头诗’,正在教育了大众,对于现实社会的认识和向往与明天的召唤,并且坚定了大众的意志。”这位论者在引用了袁可嘉的《上海》《南京》两首诗之后,并未做任何形式分析,直接攻击袁可嘉说:“叫他做封建残余和买办洋奴的代言人,是毫无愧色的,与沈从文只能代表封建性的一面和胡适林语堂亦能代表买办的一面,真不能同日而语。”[11]当然左翼民主诗歌的形式也并非全然是“匮乏”的,而是还产生了独特的“现实主义”的“体系”,然而,这一体系在袁可嘉看来却属于“浪漫主义”。这也许就是二者视野的不同。袁可嘉认识到了对方不仅在文学上属于浪漫主义,他们的政治观念同样也脱胎于浪漫主义,虽然他对后者着墨不多。简洁地说,浪漫主义的政治观念要求他们像对待艺术一样对待历史,也就是将之作为人类的一种“创造活动”来看待,于是左翼民主诗歌就产生了“创造历史”和“创造诗歌”的内在矛盾,当“创造历史”在1940 年代中后期对于他们来说变得可能和愈加迫切,“创造诗歌”这个任务就不得不处在附属层次而只能以一种“功利论”的“反映论”的模式出现:这就是“现实主义”的自圆其说,它声称解决了“政治浪漫派”的内在矛盾。而对于袁可嘉来说,他宁愿将这种创造的原则限制在个人生活尤其是个人的美学活动之中,他要求的是一种不受干扰的公民权意义上的自由,而左翼民主诗歌则以阶级的名义要求历史创造的自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或“积极自由”。⑤无法否认的是,左翼民主诗歌同时创造了自己的美学形式并且构成了1940 年代民主诗歌的主流。艾青、田间、绿原、臧克家、袁水拍等都参与创造了它的美学形式。其中艾青起到了最大的开启作用。绿原甚至构成了其中的异类,但他也暴露了左翼民主诗歌“浪漫主义”的真相,他对现代主义技巧的偶然运用虽然会被(唐湜)注意到甚至与穆旦相提并论,但毕竟这是一个缺乏政治考量的纯粹美学观照,“七月派”和“九叶派”的瓜葛并非偶然,而是渗透着那个时代在民主观念上的差异。对于袁可嘉来说,现代主义的面目虽然“晦涩”,但就像那个时代的公民权一样异常珍稀,他自然不会放弃,而他反唇相讥以“政治感伤性”也是苦心孤诣。如果我们不错误地因为他会在另外的时代找到知音而将他贬低为生活在另一个时代的人,就必须承认他是一个慧眼独具的天才甚至跨越时代且迄今难以超越的批评家,虽然这些作品写于他25 岁到27 岁之间。
袁可嘉虽然属于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但他几乎从不作政治民主方面的论述,而更多诉诸民主文化,后者在他眼中的“现代主义”中得以生发和涵养,于是就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艺术问题,即“晦涩”问题。最终是艺术上的晦涩问题成为了袁可嘉诗与民主思想的症结,更成为检验他的“诗歌民主”——与“民主诗歌”的形容词用法不同,民主一词在袁可嘉这里被用作动词——的“试金石”,这出人意料但也尽在意中。以袁可嘉在《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作为标本的穆旦为例:
时 感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它说:我并不美丽,但我不再欺骗,
因为我们看见那么多死去人的眼睛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当多年的苦难以沉默的死结束,
我们期望的只是一句诺言,
然而只有虚空,我们才知道我们仍旧不过是
幸福到来前的人类的祖先。
还要在无名的黑暗里开辟起点,
而在这起点里却积压着多年的耻辱:
冷刺着死人的骨头,就要毁灭我们一生,
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12]
对于袁可嘉激赏的“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来自“人民的文学”一方的声音说:“诗人所要的却是‘我们只希望有一个希望当做报复’,这里面不但没有一点真实的人生的活的气息,而那‘希望’也微弱得连死人的喘息和呻吟都不如了”⑥。对这位左翼批评家,钱理群评价说:“一个‘希望’与‘绝望’纠缠为一体的分裂的自我对于他是不可思议的,在他单纯的信仰中,对‘希望’(理想,未来,信念……)的任何置疑都是一种背叛:这才是他感到怒不可遏的真正原因。”[13]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分裂的自我”。其实分裂的自我也同时是内战中“分裂的人民”的一个镜像,而“在不同中求和谐”的真实含义则是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诗性平衡器。所谓“民主的反讽”虽然由袁可嘉提出,他却未来得及对他推崇的诗人进行综合的阅读尝试。在民主与现代主义诗歌的关联中,他的确也对“晦涩”问题关心有加,当政治民主被缩减为“文化民主”和“诗歌民主”,晦涩就成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虽然它可以通过“民主的反讽”在根本上加以解决,因为这意味着让“现代主义”在“民主政治”的“镜子”前看到了自己真实的身影⑦。袁可嘉承认“现代诗中晦涩的存在,一方面有它社会的,时代的意义,一方面也确有特殊的艺术价值”[3],而对于晦涩在20 世纪诗中独特的“社会意义及艺术价值”[14]如此津津乐道,至少可以说明,袁可嘉相信只有在“民主文化”的环境中才能保护“晦涩”的存在权利和可能有的价值。此时即使在自由主义作家内部对“晦涩”的看法也不一致,在1948 年11 月北大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除了沈从文提出的“红绿灯”的问题还谈到了晦涩问题。朱光潜对“晦涩”发出了异议:“荷马的作品如今读来我仍感兴趣。现代诗人的晦涩虽好,但不太好。语言的功用应在使人了解。”[15]袁可嘉则解释了晦涩的两个理由,“一为现代文化的高度综合的特性”,“其次,现代诗的晦涩可以从现代诗是对于19 世纪浪漫诗的反动上去了解的:浪漫诗是倾诉的,现代诗是间接的,迂回的,因此习惯于直线倾诉的人就不免觉得现代诗太晦涩难懂了。”[15]他坚信中国文学会从简单走向复杂。冯至发表了相反的意见:“文化的发展也可能从复杂走向简单的。”而废名则认为:“袁说的话很对,但太抽象一点。诗人是小孩子,不必等到文化成熟再动手作诗的。”[15]这一方面说明晦涩的问题与现代主义相伴始终,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说明,在政治民主被缩减和替换为文化民主时,“民主文化”本身也可能不得不是“晦涩”的。
注释:
① 近年来,对于这一话题的深化讨论和回应有:段美乔:《“民主文化”: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体系的民主国家内涵》,《诗探索》2010 年第1 期;张桃洲:《重构新诗研究的政治学视野》,《文艺争鸣》,2017 年08期;姜涛:《“民主诗学”的限度——比较视野中的“新诗现代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4 期。
② 李白凤:《颂》,《文艺复兴》,1947 年6 月号“诗歌特辑”,第420 页。“诗歌特辑”同时有李白凤和臧克家、袁可嘉和陈敬容等人的作品。袁可嘉在1947年9 月的《漫谈感伤》中说:“读过一遍《文艺复兴》今年六月号诗歌特辑的人恐怕很少抬得起头来,再有勇气、胆量替新诗作个预言的;不管有些人说的多么好听,事实俱在,乐天派不妨读读这些诗去;我不禁要问:诗,你到哪里去?”袁可嘉这篇文章应该是也是导致第二年对他的“集体批判”的原因之一。虽然袁可嘉在此处并未提到任何具体诗人,但他不会不注意到在1947 年初批评过他的李白凤和臧克家的作品。
③ 阿虎:《评臧克家〈生命的〇度〉》,《新诗潮》1948 年第3 期“新诗底方向问题”,第11-13 页。与张羽的《南北才子才女大会串》恰在同一期。
④ 袁水拍:《诗与诗论》,森林出版社,1943 年渝初版,1946 年 沪 再 版 ,1948 年 8 月 3 版 。 此 书 另 外 还 有“云海版”,足见其影响力。
⑤ 参照以赛亚·伯林的论述:“受灵感支配的政治家通过他的创造性的权力,推进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追求更大程度的自由,就是说,意识到他自己是那种非经验的、‘神圣的’和创造性过程——世界‘精神’的流溢——的一部分,这不应再按照日常的中产阶级的推理来解释他的行为;因为他的行为能够自我证成,一如天才画家或受灵感支配的诗人在他们的官能处于最紧张的时刻的为其所为,换言之,当仅仅是对内在和谐的感知和对肉眼看不到的内在关系的想象‘控制住了他’,他就变成了创造性精神前进的值得崇敬之个人。这样说来,自由在于一种直觉的、非推论的,也许是半意识地自我认同于神圣的灵感。它是一种‘超验’的行为,就是说,它不是根据经验术语能够理解或分析的。”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时代的政治观念》,亨利·哈代编,王岽兴、张蓉译,新星出版社,2011 年,第 214-215 页。卡尔·施密特对政治上的“浪漫派”的批评与伯林的浪漫主义的自由或“积极自由”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施密特认为浪漫派具有一种“机缘论态度”,而这种态度,“在其他东西——大概是国家或人民,甚至某个个人主体——取代了上帝作为终极权威和决定性因素的位置时,依然能够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最新表现就是浪漫派。因此,我建议如下提法: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subjektivierter Occasionalismus)。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做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见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再版前言”,第 15 页。瓦尔特·本雅明在“政治美学化”与“美学政治化”之间的区分似也与此相关,乔治·斯坦纳曾抱怨本雅明语焉不详未及展开,见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62 页。
⑥ 初犊:《文艺骗子沈从文和他的集团》,《泥土》第4辑,1947 年9 月。本节论述受到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启发,特致谢忱。
⑦ 穆旦显然是最能体现袁可嘉批评理念的诗人,也是一个将民主价值内化于诗写过程、从而完成了“民主的反讽”的诗人,参见王东东:《穆旦诗歌:宗教意识与民主意识》,《江汉学术》2017 年第6 期。袁可嘉、穆旦的自由主义诗学理念与表现出中间派倾向的冯至颇为不同,但都与左翼诗学有很大差异,同样关心政治的冯至最终发展出一种颇为抽象的存在诗学,可参见方邦宇:《诗的中断与诗的“中年”——以冯至、闻一多、朱自清为中心的讨论》,《江汉学术》2022 年第1 期。有必要呼唤一种具有政治哲学视野的诗歌批评与研究。近年来,在当代诗歌批评领域也存在着“体认批评的哲学基础并打开批评的政治潜能”的理念及其实践,参见周瓒:《“坛子轶事”:近四十年当代诗歌批评发展线索纵论》,《江汉学术》2022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