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寓言下的精神镜像
崔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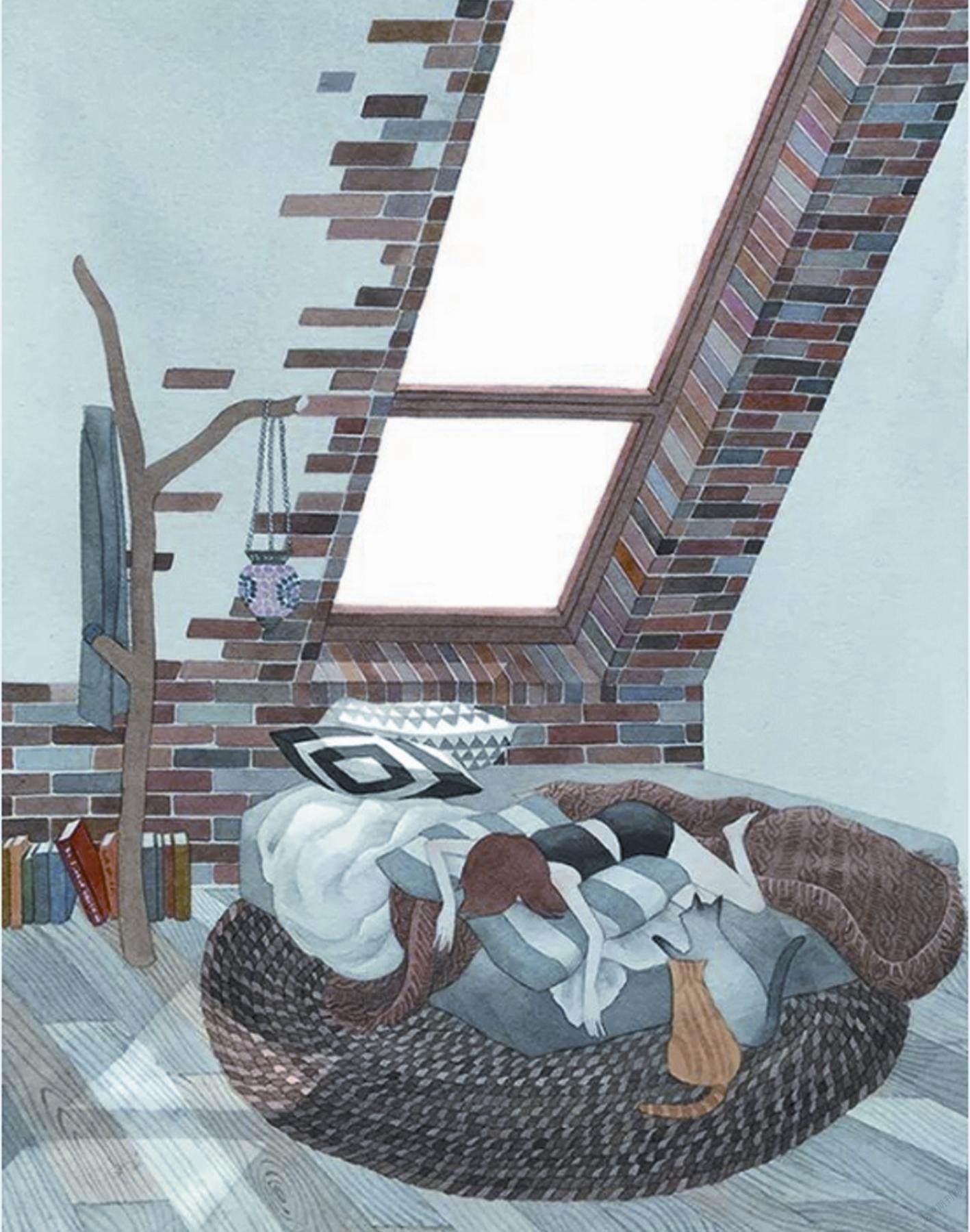
摘要:作为80后作家,孙频是当今文坛中的翘楚。在空间理论的观照下,孙频小说通过展示人物的情感命运,显示出人物在家、火车等共享空间中的性格凝结,表现出人物在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互动中的精神走向与自我拯救。在二者的交锋中,人物最终成为失败的自我拯救者,这成为孙频笔下人物情感与命运的常态。这一方面解决了学界对其笔下人物精神走向的争执,另一方面也归纳出孙频小说创作的大体模式。而在“空间寓言”中显示出的作者的思索,或许是孙频今后创作的风门水口。
关键词:空间寓言 共享空间 私我空间 孙频 救赎
作为80后作家,孙频是“比较纯粹的严肃文学追随者”[1],是当今文坛的中坚力量,她的作品频繁出现于《收获》等文学期刊和“赵树理文学奖”等文学奖项中。其作品不同于如韩寒、郭敬明等其他80后作家所携带的标签,而始终保持着对于纯文学的热情。对于其作品中的主人公的最终情感走向问题,在相关研究文献中主要分为两个方向:希望或绝望;成功或失败。在希望与绝望的交锋中,本文试图考察孙频作品中主人公在“空间寓言”中的情感轨迹以及是否实现自我救赎,从而归纳孙频的创作模式。
一、共享空间的构建
人类聚居后共享空间不断扩大,并且共享空间越发具有社会属性,直接表现为建筑、交通和山林等,在其本质上呈现出价值认同与情感趋同。在孙频小说中,家、火车、学校、画室、走廊、街道等为常见的共享空间,但又有悖于共享空间普遍的常规化、制度化等特点,从而建构起异端化的共享空间,在掌握着话语权的同时制约或激发小说中的人物情感。
孙频小说中的故事发展与高潮基本上都是在“家”中展开。“家”作为物理现实空间,应该是给人以温暖依靠的场所,这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取向。但在孙频小说中,“家”已然成为变异的空间,人物在变异的“家”中走向进一步的孤独与绝望。“家”对于邓亚西就像“围城”,楼下的商贩每天希望有朝一日能住进这楼房,而她却认为自己生活的家是如同广寒宫似的囚笼。随着第十一位租客——李塘的到来,让她逐渐感受到家的样子并且很快与李塘组成新的家。这两个人都在新组成的家里寻找自己的目的,邓亚西是为了摆脱以往的梦魇,而李塘则是为了在新家中寻找自己的“药引”。不幸的是,他们俩的目的一直没有在新家中接轨,反而差距越来越大,難以弥合。李塘在新家中寻求“药引”无望后则另寻他处,而邓亚西则对新家的幻想彻底破灭,新家不仅没有给到她所希望的陪伴,反倒将她推向深渊。苏小军的家承载的不是他与纪米萍的爱情,而是纪米萍的偏执与狂热,苏小军的无奈与烦躁。纪米萍宁可辞掉工作或是在两地间奔波抑或在楼道坐上几夜,也要来到苏小军的家中见到他。这个家是空洞而无味的,在这里他们没有爱情的甜蜜,有的只是性欲与冲突。也许纪米萍给苏小军的家涂抹了一些爱情的颜料,但苏小军马上又将其粉刷干净,不留一丝颜色。为了上学而远离老家,张银枝无言地被继父强暴十年,她所能做的就是握紧学费心中做着无声的反抗。噩梦般的吕梁山老家为她日后的生活铺上了灰暗的底色,她无法逃避少年时在老家的阴影,即便是在葡峰山庄也是如此。桑立明在家中十七年如一日般照顾着患有精神病的妻子,为了能够专门照顾好妻子,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在这里读者似乎看到了家的温馨,但实则不然。他对于妻子的照顾早已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道义和良心,从而不得不年复一年将自己与妻子绑在一起。当张银枝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他痛下杀心,与其说是为了让自己与妻子解脱,莫不如说是为了自己与张银枝的未来。这个家早已成为一个同时捆绑着三个人的枷锁,一个同时羁押三个人的囚牢。
现代交通工具是给人方便的载体,为的是能让人们更好更快地交流。而孙频小说中的交通工具已然不是为了正常的情感寻觅,而是为了畸形的欲望搬运,承载的是一种卑微与怨恨,信念与愧疚。纪米萍为了心目中所谓的不同于妓女的爱情,坐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即使买不到坐票,也要一路站到太原。她明明知道她所面对的会是苏小军一次又一次的冷漠与打击,但仍会不厌其烦地奔波于两地,将自己的卑微不计次数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为了惩罚丈夫邓安城的沉默与无力,余亚静不惜离家出走,乘坐火车不停地追溯自己的四个前男友,火车也就成为余亚静与前男友私会偷情的工具,成为余亚静发泄对丈夫怨恨的“帮凶”;张银枝为了能够见到桑立明,每一个季节都会坐一晚上的火车硬座前往榆林与桑立明见一次面,即使到了后期桑立明下了“逐客令”,但她仍不厌其烦地坚持四年,哪怕刚回到家又转去榆林。这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信念,张银枝把桑立明视为神父,在火车上的一次次被折磨成为她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从而抚慰她凄冷的生活;夏肖丹学生时代年少无知,追求新鲜与激情,在奔驰车内被追求者“摸一把”。多年后,已经成家的夏肖丹在出租车内听到司机讲到的现如今女大学生荒唐的事情后,不惜在出租车内又让司机“摸一把”,这与为了寻求学生时代的刺激与放纵而代替车费的“摸一把”不同,而是一种对于她曾经过错的忏悔与愧疚。
在具有常规化话语的共享空间中,主人公们开拓出一个个不同于模式化制约的异化共享空间,他们在这种张力中完成了个人性格的凝结。他们在共享空间中找到自己的归宿,找到自己精神情感的最后指归,在内心深处寻求救赎之路,哪怕迎接他们的是黑暗的深渊。
二、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互动
共享空间的扩大则伴随私我空间的萎缩,共享空间越发管辖挤压私我空间,于是私我空间逐渐内化,转化为私人的精神情感领域。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不是并列或线性交替关系,而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人物在不同的共享空间中伴生不同的私我空间,衍生出不同的情感指向。与此同时,私我空间的情感变化又使人物在共享空间中走向不同的人生命运。
邓亚西因被男友所伤而产生的内心苦涩与孤独,使得她多年来独自一人身居在公寓中。如果说公寓是她身体挡风避雨的安家之所,那么公寓中的画室则成为她内心自我安慰的妥协之地。在共享空间中的情感伤痕使得邓亚西深居在私我空间中的情感闭塞与焦虑中,日复一日地在画室中重复地画着同一幅画,画着同样的人物与场景,“她把他们背得太熟了,熟得快掉渣了,她能把他们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纤毫毕现地画出来”[2]。在她的私我空间里,挥之不去的永远都是自己、前男友与情敌“三人成宴”的场景,希望能在这个画面中实现自我对现实的妥协。就在这时,作为备受妻子折磨的租客李塘出现在她的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中,使得原本抑郁的邓亚西重新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开始主动地走向大众世界。她原本将李塘视为自己的“药引”,欲借李塘爬出自己的孤独世界,企图在新的家庭中回忆旧的家庭记忆,寻求幸福的安定感与自我安慰。但事与愿违,将对方看作自己“救赎草”的双方都没能救治彼此。她再一次被情感的欺骗攻陷,又一次窝藏在自己的画室中,躲避在孤寂与惨淡的私我空间中。张银枝幼年时在充满黑暗的吕梁山老家中备受凌辱,逆来顺受地像继父的情人一样在母亲身边待了十年,顺从与麻木成为她内心的底色。即使多年后,经营着葡峰山庄的张银枝名声在外,但她仍逃脱不了自己私我空间中的羞耻与空虚,愈发察觉自己渴望暴力,甚至渴望被强奸,渴望在共享空间中被凌辱。但自从遇到桑立明这个“药引”后,她开始不再自我驯化,不再渴望暴力,而是在与桑立明交往的同时寻求自身的拯救,自发地追求着内心的希望,奢求着自己的“黎明”。夏肖丹幼年与母亲相依为命,在一个缺少父爱被人歧视的环境中长大,那节断指是她幼年的“圣物”,一直提醒自己不能懈怠。在工厂房区共享空间中,夏肖丹沉沦在自我孤独的精神世界里,在独处的空间中享受孤独、忍受孤独、渴望孤独,激情在孤独地存在中酝酿与爆发,燃烧或复燃。直到上大学后,她才没有“圣物”的笼罩,在纷繁复杂的大学环境中渐渐迷失自己,青春放纵成为她的内心主调。母亲的又一次“断指”将她从迷离边缘中拯救出来,自此,她再一次被“圣物”笼摄,渐渐走向平稳的生活,追求安心与平静。在上海的出租车上,她在共享空间中以局外者的身份得知如今的女大学生正在走自己曾经的路,记忆再一次在她的脑海中翻阅,这时的她才彻底幡然醒悟。
“当找到一个庇护之所时,我们将看到想象力用无形的阴影建造起墙壁,用受保护的幻觉来自我安慰,或者相反,在厚厚的墙壁背后颤抖,不信赖最坚固的墙壁。”[3]在孙频的小说中,主人公大多都是在与他人乃至社会等共享空间的接触及冲突后,走入私我空间的自我救赎或自我消沉,又反过来影响着自己在共享空间中的走向,这既如苏小军被纪米萍感化下的忏悔,从而寻求纪米萍的归来;也如邓安城被妻子余亚静逼迫下的绝望,以致在浴室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三、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互动反思
空間将时间悬置,保存着千万个时间记忆与感情碎片,人应该处理好空间与时间的关系、现实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关系。人应该既能在共享空间中自由发展,又能在私我空间中向上独立,而不是只停留在自我享受的私我空间中,抑或在共享空间中身陷囹圄,更不应该在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中都备受煎熬。
孙频小说中得到救赎后的主人公是否真的能够在私我空间中得到解脱?是否真的能够重新走进共享空间?又能否在共享空间中立足与发展?除了邓亚西和邓安城等外,孙频对于其他人物的命运似乎并没有直接给出答案。邓亚西与李塘婚后的无望,使得她又回到了精神牢宠似的画室,“三人成宴”的人物由自己、前男友和情敌换成了自己、李塘与黄发女孩,但各自代表的角色仍然是固定的。即使身体生活在共享空间,但她也不可能逃出私我空间,最终只好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生,永远沉陷在内心的孤寂与幻想中。邓安城将余亚静视为牟小红的替身,对余亚静的不管不问实则是在对牟小红的补过。当这一幻境被打破后,邓安城则失去了“精神之根”,在浴室中自杀。试想,除了邓亚西与邓安城,其他人是否能走出悲痛的私我空间而在共享空间中成长呢?《不速之客》的结尾处,虽然暗示着苏小军的悔意与纪米萍的回归,但是双方的感情基础不是出于爱情,而是纪米萍出于情感补偿需要卑微地对苏小军单方面地讨好,这样的关系未必会长久。张银枝虽然四年如一日般地到榆林见桑立明,但她与只在自己山庄居住不到一个星期的客人之间真的会有爱情吗?正如她自己所言,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出于一种信念。她三番五次地去见桑立明享受的是被折磨的过程而非最终的结果,一旦这个过程结束,她真的能与桑立明安心地在葡峰山庄生活吗?夏肖丹虽然在出租车内彻底醒悟,但是所谓的醒悟是被断指“圣物”统摄的,是外部强加给她的精神支柱,一旦没有“圣物”的管控,她真的能悔悟吗?真的能在私我空间中追求平稳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大多数情况下孙频并没有让主人公得到完全意义上的拯救。他们在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互动冲突中,虽然得到自我救赎,但那是不完整的救赎。他们在不彻底的救赎中很难再走进共享空间,或是一直存在于共享空间中得不到救赎,或是永远滞留于救赎后的私我空间,或是在只有短暂的自我救赎后又重新进入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冲突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在共享空间与私我空间的交锋中失败的自我救赎者,他们最终的走向是绝望与失败,而非希望与成功,这在《我们骑鲸而去》等新作中同样如此。
这种创作设计或许是孙频有意为之,正如孙频在谈论自己的创作时,表明自己的创作正是为了补偿自己“所有的缺失与渴望,所有不为人知的爱与悲伤,补偿生命中的种种苦难”[4],但也或许是孙频的文学实践难题,她无法为人物构建一个未来。当然,我们并不强制作家回答任何问题,但我们希望作家能够在面对情感、人生和命运等问题时,能够给出一条作家希望看到的道路,能够让读者看到作家给人物设计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世界图景”。在“空间寓言”中显示作者的思索,这或许是孙频今后创作的风门水口。
参考文献:
[1] 孙频.女人与女人,女作家与女作家[J].文艺争鸣,2016(4):36.
[2] 孙频.三人成宴[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15.
[3] [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 张逸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3.
[4] 孙频.用文字和世界对话[J].山西文学,2010(6):39.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