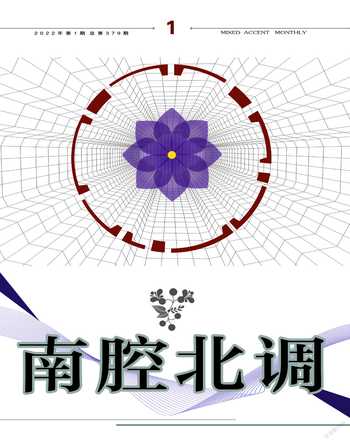论田中禾作品中的母性崇拜意识
朱颖颖
摘要:本文通过对田中禾的作品中具有母性的女性形象的梳理与归纳,从他的作品中对母亲的歌颂与依恋、母亲身上体现的独立意识、一些具有母性意识的女性形象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进而探究他的作品中的母性崇拜的形成原因。相较于当代其他男性作家,田中禾的母性崇拜书写超越了男权视角的关照,突出了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自主意识,这种书写更显示出田中禾的男女平等观念。
关键词:田中禾 母性崇拜女性形象 独特价值

母性崇拜是中国文学中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化主题,最早可以追溯到母系社会。在母系社会中,人们“知其母,不知其父”,女性的生殖功能使女性有了比男性更高的地位。比如:女娲被人奉为“地母神”,关于女娲的神话传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母题之一,她身上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生的希望和母爱的力量。当生产占据社会生活的大部分时,男性自身的优越性呈现出来,在父系社会中,已经产生的母性崇拜并没有随之消失,反而成为一种神圣的存在,并流传后世。仅从字面意思来看,母性崇拜是指作家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描写女性时,作家对女性倾注更多的正面信息,突出女性身上的母性因素和美好的特质,久而久之,作家形成一种崇母恋母的情结。田中禾在小说和散文随笔中描写了许多具有母性的女性人物形象,这种女性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可以反映出他的母性崇拜意识。田中禾本人也多次提到母亲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女性书写的执着。本文以母性崇拜为主题,对田中禾作品中的女性人物进行归类和研究,探究他的作品中母性崇拜的表现手法,以及他产生母性崇拜的原因所在,借此进一步揭示出与其他男性作家相比,他的作品中的母性崇拜的独特之处。
一
母性崇拜对田中禾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受,是一种心理情结,“是历史地积淀在中华民族文化意识极深之处的‘原始情结’,是炎黄子孙同自己的本土文化之间永远割舍不断的情感‘脐带’,是中国人的一种‘准宗教’。”[1]这种浓厚的情结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进而转化成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有的明确可感,作者将其刻画得非常鲜明。比如:《父亲和她们》中的肖芝兰和林春如,作为主人公和叙述者,讲述马文昌和她们之间的情感故事和人生经历。《匪首》中具有“神性”色彩的母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适当的时机出现并推动着故事向前发展。描写这样的女性形象,不仅体现作者的独立与平等的女性观,同时也体现作者的母性崇拜意识。此外,田中禾一些作品中的女性并非他着力刻画和突出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隐藏其中但又引人关注。比如:散文随笔《同石斋札记·花儿与少年》中“过年八题”这一栏,主题是作者在回忆少年时代家中过年的相关习俗,母亲依然处在其中,故乡的一切似乎都与母亲有关,母亲的身影隐藏在主题之后。对于《模糊》中“二哥”的母亲,作者虽然没有用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她,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她在作品中的分量,在儿子受到委屈或者困难的时候,母亲永远站在身后,抚慰着孩子的心灵。“他的作品中总有一种母亲信息的传递或母亲氛围的笼罩,总有或具体或模糊、或隐身或显形的母亲存在,总给人一种母亲在场的感觉。”[2]这也恰恰说明了母亲在田中禾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进而说明母亲早已融入他的心灵深处,在作品中不自觉地就想要去歌颂她,赞美她。
在田中禾的大多数作品中都存在着一个母亲形象,她可能是现实中存在的母亲,也可能是具有象征性的母亲形象。作者在塑造现实中的母亲时,将女性的坚强、宽容、真诚、温情等美好品质在母亲身上体现出来,着力去描写母亲,颂扬母爱。《十七岁》中“进步的田琴”这一章写母亲坚强地撑起这个家,不仅将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自己也成为街道上的活跃分子。《印象》中二哥受到妻子的背叛回到家中,母亲给予他无限的温情与怜爱,在母亲的呵护下,二哥变得不再颓废与难过。《落叶溪》是一部笔记小说,以孩子的视角来进行描写。作者在答记者问时说:“这个集子可以说是母亲和故乡的遗产。多数故事来自母亲讲述的小城逸事。”[3]因此,孩子視角下的母亲充满了爱与宽容。田中禾的母性崇拜意识,不仅局限于现实中的母亲,从更深层次来讲,他同时也注重书写象征性的母亲形象。母亲在作者笔下是以怀念故乡和描写大自然的方式来呈现的,作者心中这份崇母情结通过象征性描写进一步升华。在田中禾笔下,故乡与母亲是一体且不可分割的。在随笔《花儿与少年》“故园乡风”这一主题之下,作者不仅写乡情、乡愁、故乡的习俗,而且还用大量的篇幅描写母亲,言语中表达着对母亲的回忆与思念。更为重要的是,他将故乡和母亲相融合。在《我心中的泗洲塔》中,他这样写道:“我在异乡灯下,在书案与方格之中,茫然四顾,知道母亲已经与故乡的塔融为一体。”[4]在《故园一棵树》中,他写道:“在物质和精神的困厄中,母亲和大椿树成为生活的象征。”[5]在田中禾看来,母亲与故乡中的塔和大椿树已经化而为一,成为精神和希望的象征。他在《唐河人》序中发出感慨:“无论声名远近,不管地位高低,对于故乡,我们都是她永远的孩子。”[6]无疑,他已经把故乡作为自己的母亲去看待。田中禾同样热衷于描写大自然的一切,热爱自然可以说是他的一种天性。在某种程度上,大自然是一种泛化的母亲,比如《匪首》中的母亲,具有神性和自然性,母亲不仅仅是个体的母亲,当她出走后,作者更是把她当作了人类的母亲,具有自然的特性。
田中禾对母亲不仅有赞美与颂扬,更为突出的是表现出对母亲的崇拜。这种崇拜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深化到作者的内心深处。在田中禾写作过程中,不自觉地就会把母亲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所带给自己的影响写入作品中,表现出一种对母亲的敬仰与崇拜。即使一篇与母亲不相关的作品,同样能够体现作者的母性崇拜意识。在散文《吃喝二题》中,作者讲述的主旨思想是美食,但是文中依然会多次提到母亲曾经对他说过的话,母亲已经融入作者的生命中。母亲在作者笔下一直是正面的形象,具有一切美好的品质,不仅包含传统文化形容正统女性温柔敦厚的品质,同时也有现代女性所具有的独立坚韧的优秀品质。“作者在母亲身上浓缩和凝聚了中国传统母亲几近完美的人格精神,母亲身上体认着中国传统母亲文化性格,她是作者崇拜母亲心理情绪的一次大宣泄。”[7]田中禾本人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对于女性有崇拜和怜爱之情,这种感情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田中禾具有崇母情結,相应地就会书写一些歌颂母爱、依恋母亲的文章。他在描写母亲时,以一种仰视母亲的姿态,表达着对母亲的爱与感激:在语言上,表现出一种孩子气的语气;在整体叙述上,呈现出一种温情和依赖。在散文《梦中的妈妈》中,作者用无限深情回忆已经去世七年的母亲,言语之中透露着思念与依恋。作者用“爱抚、安慰、教诲、温暖”这样的词来表达母亲给予自己的爱。文中写道:“现在便觉得是一个顿然失去母爱,不得不在冷酷的人世孤独旅行的大孩子。”“太多的母爱塑造了我,使我永远娇漫、任性,不知世事,不愿意长大。”[8]作者在回忆母亲的同时,作为对照,在母亲那里,他永远扮演着一个娇宠的孩子形象。在这篇散文中,作者笔下的母亲,即使发怒,也是“嗔怒”,抱怨着惯坏了孩子。在《独自远行》中,作者写到自己对母亲撒娇,这些描写表现着作者对母亲的依恋程度之深。《落叶溪》视角独特,作者曾说小说中的“我”无关乎年代,一直都是一个孩子。因此,作品中描写的一切都是以孩子的思维和口吻来书写。孩子能够知道的事情,一般来源于他所看到的和听到的,在一定程度上,文中“我”的母亲也就随着“我”无处不在。作者接受采访时说,这个作品是关于故乡和母亲的。因此,文中“我”在看待周围的人与事的同时,母亲的言行思想也通过作者描写了出来。
田中禾的作品里写了许多具有美好品质的母亲,这些母亲心地善良、温情化、富有慈悲感和怜悯心,更为重要的是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不依附于男性,具有明显的主体意识。田中禾尤其注重尊重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独立的精神,强调女性的生存状态。在传统的书写中,母亲通常是作为弱势群体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即使歌颂与赞美,更多表现出传统女性勤劳善良的美好特质,强调女性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很多时候“辛劳一世的劳苦妇女被人记起母亲式的形象特点,因而成了慷慨、博大、宽厚、能承受命运给予的一切大地之母”[9]。新时期以来,在有些作家的作品中,母亲的描写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伟大形象。比如:莫言的《丰乳肥臀》,用“丰乳”和“肥臀”来表现女性身体的丰满与生殖能力的强大,作品中上官鲁氏与不同的男性结合,目的是生育出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种书写虽然表现出母亲的伟大,但是同样也突出女性所处的卑下地位。作者将女性设定在这样一种情境下,反而显示出作者男权视角下的女性崇拜。
田中禾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十七岁》可以看作是他的自传,从中可以看到他的童年故事。这部作品讲述了家族故事,书写家庭成员各自十七岁时的人生经历。父亲去世早,母亲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养育五个子女。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全家人的依靠与支撑。文中没有表现出母亲抚养和教育的艰辛,反而呈现出一种女性坚韧和智慧的一面。她用自己的才智,经营家中的店铺,并且用自己的经历与见识教育着下一代。《十七岁》中的母亲,尽管处在中国经历重大变动的年代里,但是还能够将家庭引领向上,无疑是一个强大的女性。“从十七岁的田家小妮子到张家媳妇,再到寡居的张二嫂,再到田琴的身份转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紧随时代波折前行的女性形象,这是母亲不断地自我身份调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母亲开明的思想和阅世的深度。”[10]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是作者献给母亲的书。在正文开始前的部分有一则日记,上面记录着母亲去世后安葬那一天的感受,借此表达作者对母亲的怀念。另外,《匪首》中的母亲相较田中禾其他作品中的母亲有很大不同,这里的母亲能够预知未来,能通过事情的表象追溯到本源。后来母亲出走、归隐自然,突出母亲身上具有隐喻性和神性的一面,文中的母亲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形象,更像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的母亲。在《匪首》中,母亲算不上主角,她隐藏其中,但似乎又无处不在,从而增加了母亲的神秘性。
田中禾也着力描写了一些充满母性光辉的女性角色,这些女性有的不是作为母亲的角色,而是以妻子的身份出现,她们的丈夫受到女性的爱护与拯救,在妻子母亲般的关怀与体贴下,恢复朝气与生活的希望。《父亲和她们》中的肖芝兰,作为马文昌的童养媳,一直都没有得到他的认可。但是肖芝兰依然全心全意地对待他,甚至抚养着他和别的女人生的孩子,肖芝兰看待马文昌并不像丈夫,而像是自己的孩子。文中叙述人马长安这样写道:“娘喜欢用‘那个不讲理的’‘那个浪荡鬼’‘那个混货’来称呼父亲。”[11]“在我娘面前也像个乖孩子似的唯唯诺诺,甚至出门换什么衣服都要先问问她。”[12]另一个女性林春如也说:“文昌,兰姐她不像你的女人,更像你的母亲。”[13]肖芝兰作为妻子,但她身上表现突出的却是母性的一面,对丈夫说的是“疼他”“别给我惹是生非”等等这样的话。女性所具有的母性和妻性在肖芝兰身上交织在一起,她自己也分不清楚。这样一个看似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反而作为强者的男性正是在她的“庇护”下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作者将肖芝兰这样受封建文化压迫的女性,作为其中重要的叙述人,也体现了作者所赋予她的平等意识。正如刘思谦所说:“田中禾让肖兰芝这些‘她们’中的‘这一个’从被遮蔽的幕后走向台前,以和马文昌、林春如同样的主体性言说来言说自己,言说马文昌和林春如。”[14]田中禾超越了男性作家常有的男权思想,将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女性与男性之间的关系平等化。《模糊》中给予章明爱怜的女性同样有这样的母性特征,小六的到来,给予潦倒落魄的章明以母爱般的温存。田中禾设定这两部作品中的男性虽然有知识有文化,但经历坎坷,会遭遇类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落难”的情节模式,而身边的女性则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来帮助和抚慰男性受伤的心灵。在这一过程中,女性身上所具有的母性被激发出来,成为男性的依靠。这也是田中禾母性崇拜意识的一种体现。
三
童年经验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印象深刻的,这是一个人踏入世界后最初的记忆,对人的一生都会产生无尽的影响,对于作家来说尤其重要。童年时期的经验很多都会被作家当作题材和原型出现在文学创作中。童庆炳认为童年经验是一种先在意向结构,会对作家的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童年时期的环境、家庭和父母,以及他所经历的欢乐或痛苦,这些都会深深地烙印在作家心中。田中禾出生在河南南阳唐河县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家境殷实,家中一共五个孩子,田中禾是最小的一个,家中亲人对他的关照也就相对比较多。田中禾自己说过他是个幸运的人,有一个智慧而坚强的母亲。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但是,在田中禾三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从此,家庭的责任和重担就落到了母亲的肩头。父亲在田中禾童年记忆中几乎是缺失的,是母亲担起了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这也就意味着田中禾更多地体会到母亲带来的温暖、柔情的一面,而父亲威严、理性的一面在田中禾记忆中是不存在的。“从文学要求感性、诗意和情感这个角度看,‘母亲意象’对作家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因为母亲对塑造作家的丰富的活跃的内心世界、培养美好的情操和伟大的同情心,起奠基的作用。”[15]在田中禾的作品中,可以充分体会到他内在的情感和情怀,这些与母亲带给他的记忆有着必然的联系。在一次采访中,田中禾说:“追根求源,我对女性的崇拜、怜爱,与三岁丧父、一生依恋母亲有关。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我小说里的女性总有一种母性的坚韧、包容、宽宏和自尊。我写不出女人的邪恶。不忍心让笔下女人暴露出人性的阴暗和肮脏。”[16]童年经验分为丰富性经验和缺失性经验。父亲的缺席,是他童年经验的一种缺失,而这种缺失的经验恰恰成为田中禾创作的一种动力和源泉,无形之中成为他产生母性崇拜的根源之一。比如,艾青因为从生下来就被家人认为是“克星”,失去亲人的关爱,被放在农家抚养,即使后来回到自己家中,依旧得不到父母的疼爱。但是艾青在大堰河那里得到补偿,这种缺失性的经验,使得他后来创作出具有博大的爱的诗篇《大堰河——我的保姆》。在某种程度上,艾青的诗篇中也呈现出一定的母性崇拜意识。
除了母亲,田中禾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还有妻子。他说:“我人生的最艰难岁月全靠两位女性支撑。一位是我的母亲,一位是跟随我漂泊半生、无怨无悔奉献全部情爱的妻子。她们是我精神的支柱,困境的依靠。女人是男人坚强的后方。她们是世界的灵魂,真正的上帝。”[17]田中禾在二十二岁时与小自己一岁的妻子结婚,从此妻子伴随着他度过之后的风风雨雨。田中禾把女人看作“灵魂”“上帝”,用来仰望的“神”。妻子的陪伴与呵护,让田中禾对女性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模糊》这部作品充分体现作者的温情化书写,章明的两任妻子都背叛了他,甚至第一个妻子在批斗大会上公然污蔑他、栽赃他。但是作者并没有写出人性恶的一面,作品中的“我”后来寻找“她们”后,却把“她们”看作自己的亲人,对“她们”充满了一种同情和惋惜的心理。这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种心理情结和情感取向。作者对女性的宽容与怜惜,与成长中所受母亲的温情和成年后妻子的爱怜不无关系,是她们让作者在心理和情感上崇拜母性,依恋女性。
作为华夏儿女,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田中禾也不例外。他曾说:“温柔敦厚之道,是中国传统写作的标准要求,我这个骨子里反传统的人,笔下的作品却大体符合这个要求,这与儿时的教育有关。”[18]反抗传统的田中禾,却能够遵循传统去书写符合儒家规范的角色,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温和宽厚的风格。他在描写女性时,具有相当明显的平等意识,即使是写女性非善的一面,也多了几分宽容。最为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对男性而言,建功立业要比创造幸福家庭更重要,而对于女性更多的是相夫教子,家庭是女性生活的核心。因此,母亲对于孩子性格的塑造和情感的影响要更为深远。对于田中禾来讲,父亲的缺失,使得他受母亲的影响更加深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产生母性崇拜意识的又一促进要素。
小 结
母性崇拜是一个持久的话题,而且贯通古今,在当下的文学文化中依旧占据一席之地。田中禾的母性崇拜意识主要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女性,她们身份地位不同,性格差异明显。比如:《匪首》中温柔且富有灵性的荞麦,包容且蕴藏智慧的母亲;《父亲和她们》中隐忍且饱含母性的肖芝兰;《十七岁》中坚强且极为明智的母亲等等。这些都是田中禾着力刻画的富有母性的女性形象。他也多次强调自己对女性描写的执着,希望再写两部以女性为中心的长篇。
目前当代文学中有很多男性作家具有不自觉的男权意识,他们即使赞美女性、崇拜母性,但更多的是一种男权视角下的赞美与崇拜,反而透露出男性视角下二者之间地位的不平等。比如张贤亮笔下的女性《绿化树》中的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黄香久,莫言笔下的女性《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等等,他们极力书写女性的贤良淑德与牺牲精神,反而映照出作家内心深处的男权意识。田中禾能够与笔下女性人物感同身受,从而写出最为真实的感受。在作品中,叙述者常常隐没在人物语言与行动之后,叙述者的立场通常与人物融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叙述者、作者和人物之间思想与态度是统一的,只有这样,叙述人才能写出这些女性的内在心理特征和内心感受。此外,田中禾看待女性相比其他男性作家具有更强的平等意识。他强调人性美,在写作中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人文关怀。他笔下女性的个体意识较为突出,呈现出一种不依附于男性的独立性。他笔下的女性对生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而男性角色能力被弱化,不谙世事,依赖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作者弱化了男性角色,从而突出女性的独立地位。这也就使得他的作品中母性崇拜意味较为浓重,而非打着母性崇拜的旗号去书写伪女性崇拜。
参考文献:
[1]仪平策.母性崇拜与审美文化——中国美学溯源研究述略[J].中国文化研究,1996(2):95-100.
[2]梅惠兰.母亲:永恒的生命底色——田中禾创作论[J]中州大学学报,1997(1):42-51.
[3]田中禾.同石斋札记·落叶溪[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380.
[4][5][6][8]田中禾.同石斋札记·花儿与少年[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9:71,67,64,83.
[7]陈继会,曹建玲.历史·人性与诗性眼光——田中禾的文学世界[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93-98.
[9]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9.
[10]刘军.十七岁:个人切片與历史还原——田中禾《十七岁》阅读札记.[J]扬子江评论,2011(4):64-68.
[11][12][13]田中禾.父亲和她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7,7,123.
[14]刘思谦.“她们”中的“这一个”与“另一个”[J].中州学刊,2011(6):220-226.
[15]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16][17]舒晋瑜.田中禾:没有人强迫给你的大脑植入芯片[N].中华读书报,2019-11-27(18).
[18]李勇,田中禾.在人性的困境中发现价值和美——田中禾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2(2):106-109.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