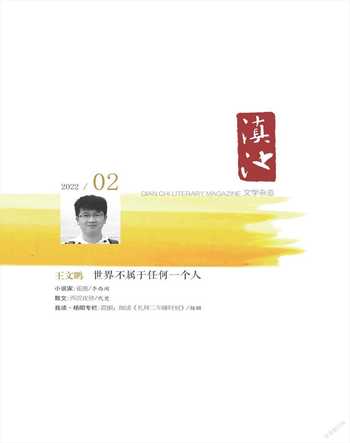震颤:细读《礼拜二午睡时刻》

杨昭 1965年3月生于云南昭通,昭通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出版《诗人的魂路图》《温暖的钟声》。曾获得高黎贡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奖项。
一
火车刚从震得发颤的赤褐色岩石隧道里开出来,就进入了一望无际、两边对称的香蕉林带。
这是马尔克斯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的第一个句子。这个句子的主语是“火车”,一列完全听从马尔克斯英明指挥的火车。它不但将一对悲苦的母女在礼拜二午睡时刻从异地按时运送到了马孔多(这座镇子我们在读《百年孤独》时就开始瞩目了),还在这篇小说里充当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小说后面写到的那群在神父家窗外探头探脑的吃瓜群众:首先,它是个动态的形象,而在文学作品的开头部分先让动态形象露露脸,就很容易风过无痕地吹拂到有心读者的潜意识;其次,由于它是动态的形象,它便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方式运动着,载着故事,载着生命,载着因果,载着由来和对目的地的期待或瞎猜,连接起前方和后方、歷史和现实,着实为作家省去了在作品里啰里啰嗦地交代、辛辛苦苦地铺垫的不少麻烦;再次,它像魔术师或催眠师伸出来的一根有名堂的指头,跑到哪里便指点到哪里,既别有用心又不露痕迹,让读者顺着它的指点而开始凝神注意被指点的事物,渐渐滋生出自己也身在作品所写到的诸般现场情境中的幻觉。此刻,这列火车已从一条隧道里开了出来,就像一句脏话已经脱口而出无法收回,故事情节便只好朝着它该去的地方行驶下去了。
我知道像我这种咬文嚼字地读一篇小说的做法肯定会激起不少读者的义愤,但在读马尔克斯这样的伟大作家的伟大作品时,又确实只能这样读。有时候,错过我们自以为无关紧要其实却是作家惨淡经营出来的某个句子,某个词,甚至某个字,我们就很有可能跟不上大师前行的步履。
这列火车牵引着“刚”和“就”这两个表示时间的副词。“刚……就……”的句型,是能够指涉时间的“过往←当下→将来”三个向度的典型的马尔克斯语式。马尔克斯的语言,信息的密度总是很大,并且那些信息常常因为时间的三个向度相互间的缠斗而隐藏得很深。而那些信息在表达上又总是非常有用。比如当下正在奔跑着的这列火车,就关联着被它抛在身后的隧道和朝它迎面而来的香蕉林带。岩石倔头倔脑的硬挺感与香蕉树风情万种的婀娜感、石头赤褐色的厚重感与香蕉林灰绿色的清新感、隧道的狭窄感与香蕉林带的开阔感,这些事物所呈现出来的各自独有的物性,以及这些不同物性之间所形成的强烈的反差,被并置在同一个句子的平台上,于是这个句子内部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积蓄起一种不和谐的能量,这种能量就会因为内部不断增长起来的语压而不得不自己寻找一道喷涌的小孔或者渗出的口子,不易察觉地从当下现实事物的确切层面,悄悄溜到过去或未来恍惚的心理层面与象征层面。在这里,岩石隧道和香蕉林确实就是哥伦比亚大地上如假包换、质感真切的岩石隧道和香蕉林,但与此同时,它们又不仅仅是它们自己,它们还是一个个活物,一个个生命,甚至是一个个灵魂,拥有着它们自己的气场。那条隧道由于火车的驶过而被“震得发颤”,但它又拿使它发颤的火车毫无办法,只能停在它自己所在的位置和时间里震颤。所谓隧道,其实就是活生生地在岩石的身躯上凿出来的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洞。小说中这个大洞的震颤,我觉得应该属于一种灵性的震颤。我之所以这样觉得,是因为我读过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火的记忆》等正在被捅着或已经凝血的作品。现在,这列对马尔克斯言听计从的火车已钻出了隧道,它的身后是“赤褐色的岩石隧道”。而赤褐色,不仅是矿藏丰富的哥伦比亚山地的本色,也很接近拉丁美洲印第安原住民的肤色,不知为何我还觉得它很像殖民时代与资本入侵时代拉美人在无数次反抗中流下的血变干后的颜色;火车驶入了绿色的香蕉林带,那些香蕉,正是《百年孤独》接近尾声时写到过的外国香蕉公司强令马孔多镇的人们种植的香蕉。在香蕉公司打工的拉美人举行的罢工被镇压后,原本用来拉香蕉的火车,拉着三千多具拉美人的尸体,慢吞吞地、血淋淋地驶过了马孔多甚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梦魇。就算眼前这列刚刚驶离岩石隧道的火车跟当年那列拉尸体的火车不是同一列火车,它们身下的那条铁路也肯定是同一条铁路。它也许还记得当年泼洒在它身上的那一汪接一汪的腥血。
顺便说一下,最近两年我学习写诗,常常偷偷运用马尔克斯的这种逆向互补的语式,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在一个句子里并置上完全相反的事物以获得表达的张力。我经过反复多次的语句实验感觉到:这招确实很好使。
二
火车前行,指点着沿途铁道两边的“牛车”“狭窄的小道”“空地”“煤烟气”“装有电风扇的办公室”“红砖砌成的兵营和一些住宅”“阳台”等富含时间信息与心理信息的新事物。短短的一百多个字,却拥有着极高的像素和极强的分辨率,仿佛我们自己此刻正亲自坐在这列火车上往车窗外东张西望。其实那列火车何尝又不是在指点着它自己?它自己又何尝不像一枚硬生生钉进拉丁美洲古老头颅的钉子,何尝不像一根猛然戳进马孔多的眼眶里的手指?
“你最好把车窗关上。”女人说,“要不,你会弄得满头都是煤灰的。”
这篇小说里出现了第一句人物对话,祈使句。前半句是一种命令的语气,很硬,很干;后半句补充出了命令的理由,并交代清楚了这篇小说的故事发生的时代是火车还在靠烧煤来驱动的蒸汽机车的时代,但语气照样是硬邦邦、干巴巴的。我们只知道说话人是个女人,而这世上的女人有几十亿个,她究竟是其中的哪一个呢?
这正是马尔克斯叙事的精准和精微之处:在这女人以一种突如其来并自呈性格的语音的方式进入小说之前,读者的注意力一直都在一根手指(火车)的指点下专注地,或是漫不经心地打量着变动中的景物。现在,趁这根手指还来不及收回来指点它自己,趁火车自身的影像还没被调整好焦距,趁读者还没看厌沿途那些并不值得多看几眼的景致,本小说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突然以听觉而非我们刚刚习惯了的视觉的方式登场了。突兀地出现,也是引起读者关注的一种叙事策略。
既然是人物对话,读者的下意识里就会隐隐涌起一种期待,等着某个人回应的话语响起。
但是没有人搭腔。小说只紧接着写了这么一句:
小女孩想把窗子关上,可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
注意:小女孩没有说话,她对女人说的话的即时回应只是一个关窗的动作。这个动作细节有点像画家在画室里画人物素描,一开始时,虽只有简单的几道笔画,却已勾勒出了人物的大形。尽管小女孩不说话,我们也立刻便能感觉到她是个很听话的孩子,而绝非我们见识过的那类家境很好却很叛逆的问题女孩或准问题女孩。“车窗锈住了,怎么也拽不动”,原因是小女孩太小了,而世界又太大了;小女孩太弱了,而世界又太强了。她绝不是世界的对手,她很无力,她很徒劳。
但她又试图做点什么。
小说开始写到了车厢,以及车厢里的这对母女。影像越来越清晰,甚至连小女孩摆放“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一个塑料食品袋和一束用报纸裹着的鲜花”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小小细节的锐度也彰显了出来。她们是那么的贫苦,鲜花似乎是一种跟她们不太搭的奢侈品,但她们又确实随身带着一束鲜花坐在火车上,而且那束鲜花还裹着起保护作用的报纸,尽管这层印满了各种说辞的保护也很徒劳。
她们带一束鲜花来马孔多镇干什么呢?
为女人定影时,马尔克斯写道:
……整个旅途中,她一直是直挺挺地背靠着椅子,两手按着膝盖上的一个漆皮剥落的皮包……
跟她说话的语气一样,女人的外貌、身形、穿着、身体姿势都是干巴巴、硬邦邦的。她本该具有的女性柔美特征不知被什么力量榨干了,夺走了。
小说刚刚提及的“她们仅有的随身物件”里并没有列出这只被女人用两手按着的旧皮包。难道这只旧皮包不是她们的随身物件?马尔克斯干嘛要写这只看起来在这篇小说中似乎派不上什么用场的旧皮包?这会不会是小说大师的一次小小的笔误?
所有我能找到的马尔克斯的作品我都认真阅读过,从没发现过他有过任何一篇败笔之作。他年轻时当过记者,新闻写作把他的笔尖磨得异常锋利。成为国际知名的小说家和电影人后,他的写作更显出了慢工出细活的功夫味。在《写作——“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我”》一文中,他写道:“我必须无情地约束自己,才能在八小时里写半页纸;我和每个字摔跤搏斗,几乎总是它们最终获胜。但是我却那么顽强不屈……”(《两百年的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创作》,朱景冬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要在马尔克斯的作品中找到真正的败笔或语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他的作品的阅读经验告诉我,什么时候当他的作品里露出了“破绽”,你先别忙着瞎激动,那些“破绽”,往往正是他故意抛给你的诱饵,他在它们上面费尽了心机。你如果轻蔑地、草率地匆匆忙忙断定它们就是个bug,那你就难以真正进入他小说的幽深地带。
我们先别死盯着这只漆皮剥落、形迹可疑的旧皮包,这篇小说中值得留心的地方还多得很呢。
空荡荡的三等车厢里,母亲很疲惫,“低着头,昏沉沉地睡着了”。小女孩则总想做点什么,即便不管做什么都很徒劳,她也不顾酷暑的折磨,“到卫生间去,把那束枯萎的鲜花浸在水里”。
然后她们吃饭。妈妈递给小女孩一片奶酪、半个玉米饼和一块甜饼干。那块小孩子们通常都很爱吃的甜饼干,这个小女孩却没吃,她把它塞进了袋子。人在旅途,通常都会在下意识里滋生出一种孤独或者自怜的心理,通常都会狠下心“奢侈”一把,在车上吃一些平时只能怀着崇敬的心情眺望着的昂贵食品。我猜,小女孩平时是吃不起甜饼干的。
接下来,妈妈先后对小女孩说了几次话,每次小女孩都没有回话,每次她都只是用一个很懂事的动作来回应妈妈干巴巴的、僵硬的、简单的、命令式的话语。后来,妈妈说出了更不近人情的话来: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女人说,“接下来就算是渴死了,到哪儿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女孩点点头。
火车驶近了她们的目的地马孔多镇时,母女俩开始收拾她们带来的物品:
女人把装着吃剩食物的袋子卷起来,放进皮包里。
注意:这里又提到了没被归入“随身物件”的那只可疑的旧皮包,女人往里面塞的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吃剩的食物。在大街上,在校园里,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年轻人把没吃完的这类食物随手扔进垃圾桶里。
小女孩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又稍微离开窗子一些,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母亲也用温和的目光看了她一眼。
母亲终于温和了一瞬间。再不温和,再继续板着脸,母亲形象就快要被写成极端化、概念化的木乃伊了。这至为珍贵的温和的一眼,立刻就起到了让我们对她另眼相看的效果。如果我们返回去重温她此前对小女孩说过的每一句语气严厉、生硬的话语,便不难感受到它们当中其实都深藏着一份因竭力克制着而非常难以感觉到的母爱。生活的艰辛、世界的无情、命运的残忍,让一位母亲忘记了温柔,让她在话语中流露关切和爱意时,也显得干巴巴、硬邦邦的。如果是外人,很可能完全感觉不出她那些话语里的温度。此刻,母爱的本性终于无损地显露出来了,即便那么短暂,一丝丝爱的暖意,也足以让我们不惧整个世界的冰冷。这份爱意的稀少唤起了我们对更多的爱的温暖的渴望,但马尔克斯管住了自己,坚决不写母亲对女儿的滥情。正因为少,所以才更显出了珍贵,更能够刻骨铭心,就像雷平阳献给我们这个薄情寡义的时代的那滴“针尖上的蜂蜜”。
可是我仍然觉得很压抑:小女孩的各种动作让我在感到她很乖的同时,又隐隐觉得她也许很不幸。只會默默地做事而一直不开口的小女孩,她会不会是个哑巴?
三
母女俩沿着巴旦杏树荫悄悄地走进小镇,尽量不去惊扰别人午睡。她们径直朝神父的住处走去。
这是礼拜二午睡时刻,一个中年妇女——神父的妹妹告诉她们:神父在睡午觉。母亲的态度和语气一如既往地干巴巴和硬邦邦,没有丝毫让步或作罢的意思,神父的妹妹只好让母女俩进了屋。
母女俩不顾天气炎热从异地乘火车前来马孔多镇,特意避开了礼拜日和礼拜一因放假、收假而乘客较多的日子,特意选定了礼拜二这样一个乘客稀少的时机,特意选择了午睡时刻这样一个不容易招致马孔多镇上的闲人们围过来看热闹的时辰,只是为了向神父借用一下公墓的钥匙,给女人的儿子、小女孩的哥哥,一周前死去的少年卡洛斯·森特诺上坟。
神父问他们想去看哪一座墓,母亲讲了两遍儿子的名字,神父还是不明白。
“就是上礼拜在这儿被人打死的那个小偷。”女人不动声色地说,“我是他母亲。”
当一位母亲向别人说起自己的儿子,却不得不说到儿子的小偷身份时,我不知道她当时怀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神父也不知道。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神父的脸唰的一下红了。他低下头写字。
我们非常有必要留意一下神父脸紅这个细节:他作为一位类似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体面人物,面对着一个小偷的母亲,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贫穷、早衰的中年妇女,无论说到身份、地位、处境,还是谈及信仰、道德、口碑,当这个女人盯着他看时,他完全应该内心里充满着优越感,完全有资格道貌岸然,完全可以大义凛然、脸不变色心不跳。要知道,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人,任何时候都是可以对别人大声武气地说话的。但是,他的脸“唰的一下红了”。马尔克斯为了把读者邀请进小说现场作了多么细心的努力,出其不意的脸红居然还带有“唰”的音响效果。
跟写母亲干硬形象时意外地写到她的温柔注目一样,马尔克斯在此处刻画神父形象,也运用了一笔反转就写活人物的方法。刻板的神父居然也会脸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意外,值得我们放慢阅读的速度,想象、揣度一番。他的脸一红,他的人之初的可爱立马就从他多年累积起来的灰暗无趣的人生经验的重压下逃逸出来了。我想象着当他处于有位陌生人正在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的特殊境遇时,下意识里也许立刻就担心起自己曾经有过的某段有违信仰的隐私被人看破,因此立刻便脸红了。那会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呢?我觉得他的脸红不太可能是由于此刻他面对的是个异性而引起的,因为他面前的这位强忍住悲痛直盯着他的女人,从外观上看,其性别特征和魅力早已所剩无几,不足以让一位老男人脸红。毕竟,从神父说话做事一本正经的风格来看,从他那间窄小、简陋的客厅兼办公室的简朴陈设来看,他也还算是个中规中矩的老派神职人员,心底还是应该有所敬畏的吧。尽管他信仰的激情已消退得差不多了,但多少也还应该残存着勉强够用的那么一点点吧。这次突如其来的脸红,很可能意味着至少在几秒钟里他做了一次灵魂的自我反观与短促清洗。马尔克斯从来不对他笔下的人物进行标签化、类型化的处理,从来不对其作出“老子说了算”式的论断。他写的人物都是立体的、自身充满着诸多内在对立元素的、时刻等待着读者以自己的角度和方式去解读的。他善于在读者基本上已对某个人物产生成见之际,用一个小小的、反向的细节轻轻点染一下,使这个人物大面积的形象底色一下子就变得鲜活、生动起来,让读者领悟到该人物形象的多样性、可能性。这种表现效果有点像大观楼长联里的“更萍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
小说一开始那句话中所写到的,由火车所驶向的香蕉林与被它抛在身后的岩石隧道之间形成的极性,在整篇小说的语言行进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某一面被刻意暗藏起来了。这种暗藏其实就是在为小说的叙事蓄势,当时机成熟时,一直被暗藏着的那股力量就会产生出震颤人心的爆发力。例如表面上又冷又硬的母亲,内心里却对死去的儿子充满了最为炽热、强烈、深沉的爱,这种爱是无法一直被遮住的。当后来神父质疑她没有把儿子教育好时,她丝毫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立刻就为儿子的尊严进行辩护。她那克制的、听不到一丝呜咽的平静语调所产生的震颤效果,胜过了任何呼天抢地、一把鼻涕一把泪式的直接抒情。
四
少年卡洛斯·森特诺上个礼拜一凌晨三点在试图进入寡妇雷薇卡太太家行窃时被她一枪打死了。这位不幸的雷薇卡太太用《百年孤独》中最重要的人物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送给她防身的那只左轮手枪打死了少年卡洛斯·森特诺。马尔克斯向他自己写过的长篇小说杰作借势,把奥雷里亚诺上校身上那股神秘的宿命气息带入了《礼拜二午睡时刻》中:奥雷里亚诺上校赠送给寡妇雷薇卡太太的这支左轮手枪,寄托着这位为民族独立、自由而舍生忘死的大英雄对一位不幸女子深切的同情和关爱。而守寡已经二十八年,与外人几乎没什么联系更谈不上有什么冲突的雷薇卡太太,未必真的就需要一支手枪来自保性命。就算是她宅邸中的某些财物真的被少年卡洛斯·森特诺成功偷走了,她也照样能继续活着。这支手枪对于她,与其说是一件武器,不如说是一种饱含着亲人般的安慰的珍贵礼物,一件纪念品。她一直把它藏在衣柜里,那天凌晨才生平第一次在黑暗中开枪,而且开枪时她还闭上了眼睛。没想到,她根本看不到的、位于门板另一面的少年小偷就被她一枪击中了鼻子。这次意外,是由一种无形的力量主使的。马尔克斯仿佛当时就亲自在场,而且同时既在屋里又在屋外,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用朴素、洗练的文字精准地还原了他当时“亲身经历”的那一刻的现场情景:
枪响之后,周围又寂然无声了,只有细雨落在锌板屋顶上发出的滴滴答答的声响。她随即听到门廊的水泥地上响起了金属的碰击声和一声低哑的、有气无力的、极度疲惫的呻吟:“哎呦!我的妈!”
震颤的枪声紧接着寂静,听觉恢复正常后又先传来了雨声后传来撬门工具落地声,随后才传来呻吟声。这一切全都诉诸听感,节奏变化极为真切、合理的听感。深藏在这种听感背后的,是一种也许可以感觉到却无法言说出来的命运感。这种命运感,我们早已在《百年孤独》中的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身上感受过多次。
“这么说,他叫卡洛斯·森特诺。”神父写完,嘴里咕哝道。
“森特诺·阿拉亚。”那个女人说,“是我唯一的儿子。”
只有做母亲的,才会特别强调她的儿子是“唯一的”。“唯一的”就是至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就是失去什么都可以,唯独不能失去“这一个”的。这个“唯一的”,对她来说就是整个世界的支撑。
刻板的、颇不耐烦的神父终于在笔记本上写完了向他借公墓钥匙的女人的身份信息,让她在指定的位置上签字。
女人把皮包夹在腋下,胡乱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小女孩拿起鲜花,趿拉着鞋走到栏杆前,两眼凝视着妈妈。
请注意:这里第三次写到了那只旧皮包,而且母亲并没有因为要腾出手来签字而将它暂时放在桌子或是椅子上,也没递给离她很近的小女孩,而是将它夹在自己的腋下。它在小说中的每一次出现,始终都紧贴着这位母亲的肉身,仿佛它真的不是母女俩的随身物件,而属于母亲身体的一部分。
“您从来没有试过把他引上正道吗?”
女人签完字,回答说:
“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
“我告诉过他,不要偷穷人家的东西,他很听我的话。然而过去,他当拳击手,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
肩负着匡扶世道人心重任的神父语气委婉、优雅地责备母亲,母亲则毫不迟疑地向他证明自己的儿子是个好人,而且是个“非常好的人”。“他很听我的话”,这就意味着母亲在把儿子的偷窃行为的一大部分责任往自己身上揽,承认自己不但是儿子偷窃行为的知情者,而且还是指使者。养尊处优的神父,怎能体味到走投无路者活着就已经身陷地狱的悲剧!
卡洛斯·森特诺,这位少年小偷,这位卑微且悲惨的早逝者,却又是一位真正的男子汉。为了养活瘦弱、早衰的妈妈和年幼、早熟的妹妹,在当小偷之前不得不去当了一名拳击手。他所当的,绝对不可能是那种既为高报酬而战也为荣誉而战的俱乐部选手型拳击手,而是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里常见的,专门挨揍以满足观众变态的施虐或受虐心理,报酬却少得可怜的拳击手,否则他怎么可能“常常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呢?
“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女孩插嘴说。
原来小女孩并不是哑巴,她终于说出了她在这篇小说中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是的。”女人证实说,“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尝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滋味。”
五
“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小女孩说出的这唯一的一句话,开启了我对这篇伟大小说的“创造性误读”之旅。
如果她和妈妈有钱为哥哥立一块碑(我说的是“如果”),小女孩这句每个字都滴着鲜血的话,应该被作为墓志铭深刻在墓碑上。
“不得不”,确实是不得不。如果还有选择其它谋生方式的机会和可能,谁会去热爱专门挨揍的拳击手或者又危险名声又很臭的小偷之类的本职工作?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份子,作为走投无路的可怜人,这两个身份猛一看都纯属他个人自觉自愿的选择,下细一想却完全出自那种看不见的暗黑力量对他的强制安排与霸凌。当命运的重拳猛然劈面击来时,他松动的牙齿在震颤;当闭着眼睛的寡妇雷薇卡太太被命运的魔爪托着双手朝他开枪,当那颗被命运特意挑选出来的子弹从一支不同寻常的左轮手枪中射出来击中了他的鼻子时,他的生命发出了最后的震颤。他一生中的这阵最后的震颤如此持久,至今还在马尔克斯的文字里抽搐着:
死者的鼻子被打得粉碎,他穿着一件法兰绒上衣,一条普通的裤子,腰上没有系皮带,而是系着一根麻绳,光着脚。镇上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这里的“镇上”,我把它读成“世上”。
“光着脚”,马尔克斯毫无文彩的这三个字,恰恰就是此处震颤得最剧烈的字眼。作为一名小偷,因为要翻墙,要逃跑,一双合脚的鞋子是必不可少的、最起码的装备。但是,直到死去时,他光着脚。这双光着的脚,把震颤从死者的身上传递到了读者的心中。
六
在这篇译成汉语后仅五千多字的短篇小说里,马尔克斯为每个有名有姓的人物都配备了一两样具有标志性质的道具,比如为儿子配备了一根系在腰上的麻绳,為神父配备了两把公墓的钥匙,为小女孩配备了一束鲜花,为母亲配备了一只旧皮包,为不幸的寡妇雷薇卡太太配备了一把让一个家庭陷入更大不幸的左轮手枪,为神父的妹妹配备了一把既能遮阳又能遮雨还能遮丑的,寄托着善意心愿的阳伞。
事实上,这些精选出来的道具,全都是它们的主人的副本形象。
麻绳:小偷要快跑,要翻墙入户,裤子松松垮垮的会很碍事。儿子卡洛斯·森特诺并不是不可能从自己偷来的钱物中挤出一点点来为自己置办一根皮带,一双鞋子,但他之所以偷东西,是为了让妈妈和妹妹活下去,而极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他在自己的腰上系了根麻绳。中国人常常会在向别人诉苦或者号召别人吃苦以便自己能够捞取到更多的好处时,大谈特谈“勒紧裤腰带”这句半真半假的屁话。而这句话如果用在卡洛斯·森特诺身上,则完全不带半点夸张的色彩,它就是发生在当小偷的儿子卡洛斯·森特诺身上的事实本身。这根麻绳裤腰带,就是一种悲惨、绝望的生存状态,就是另一个无法死去的卡洛斯·森特诺。它扭动着、纠结着,紧束着自己一生的羞耻、恐惧、悲愤、梦想和动摇。
公墓钥匙:神父不仅要管理活人们的精神秩序,还要管理死者们的身后事宜。钥匙并不是什么稀罕物件,尤其是公墓的钥匙,更非普通人翘首期盼的东西。在平常日子里,谁会想到去公墓里溜达遣兴、谈情说爱、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但任何人都总会有那么一天不得不到公墓去,不是自己亲自去就是为亲朋好友而去。这时候,谁管理着教区公墓的那两把不起眼的钥匙,就意味着谁掌握了世俗世界与另一个世界双重的权柄。这是一种象征,一种待遇,对广大宗教信众来说,它比职称更令人垂涎。别人只能短暂地借用,只有资深的神职人员才能长期拥有对它的支配权。当母女俩来到神父家办完借用公墓钥匙的繁琐手续时,小说里写道: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内侧的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在女孩妈妈的幼时的幻想中,甚至在神父本人也必定有过的幻想中,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两把其貌不扬的钥匙,被三个人内心里纯朴的幻想加持,更被救赎的盼望加持——三个年龄呈现阶梯状的人都不约而同地相信或者曾经相信:“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的”。
這两把钥匙还被无情流逝的岁月加持——它“上面长满了锈”。这就意味着它们同时具有神圣的光环和俗世的锈蚀的双重属性。神父的倏然脸红与老于世故,他对母女俩的真诚担心与麻木不仁,与这两把公墓钥匙的双重属性彼此映射,互相渗入。
鲜花:直到小女孩在死去的哥哥的尊严受到神父的质疑和冒犯之际终于说出“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这句话时,我才猛然醒悟到:为什么惜墨如金的马尔克斯,会在《礼拜二午睡时刻》里几次写到小女孩对备受炎热折磨的鲜花的悉心照料。
热是这篇小说的环境要素之一。
初读这篇小说时我曾有过一个疑问:既然母亲对自己“唯一的”儿子爱得那么刻骨,既然“那时候,我每吃一口饭,都好像尝到礼拜六晚上他们打我儿子时的滋味”,这位母亲为什么不在儿子惨死后的第一时间赶到马孔多镇为儿子收尸,为什么不把儿子的遗体带回他们一家人生活的地方安埋,而要任人将其葬在异乡的教区公墓里,一周后才带着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儿来马孔多镇上坟?这显然很不合情理嘛。
但当我试着把热当成叙事功能强劲的一个角色来解读时,我的满腹狐疑顿时便消散得无影无踪:马孔多的热之厉害,在《百年孤独》里我们早已领教过。那种精心经营出来的语境里亦真亦幻的热,仿佛使世界发起了高烧。这种热是对无助的生灵的一种煎熬,它对一具遗体而言显然也不怀好意。在火车还在靠烧煤才能奔跑的时代,通讯和交通条件都还很落后,马孔多镇的人们怎能容忍尸体腐坏后的气味对他们的折磨,怎么可能等到查明了来自外乡的死者的身份后设法联系上死者远在异地的亲属,再等到死者的亲属赶来收尸?铁路公司又怎么可能允许一具已经腐坏了的尸体被抬上列车?先草草掩埋了再说才是明智之举。
被特意渲染、强化过的热,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等众多小说中众多狂热人物与狂乱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是在小说中做了好事(此处特指暗助了马尔克斯的小说写作)却不愿留名的狠角色。在马孔多,热是一种古老,也是一种现在进行时态的存在和行为。那一束被带到马孔多镇来的鲜花,内涵着多少最真挚的爱,多少最透明的敬意,多少最赤诚的感恩,多少最深切的怀念。小女孩每次照料这束鲜花,都用不着妈妈的吩咐,她一直都在主动地默默分担妈妈的痛楚和重负。小女孩怕这束柔弱的鲜花受不住酷热的折磨而过早凋零,她以感人至深的动作小心翼翼地照顾着它。她不知道她饱含着敬念的动作早已成了一种如泣如诉的生命的仪式,她不知道自己也是美丽而柔弱的、正在承受着折磨的、极其容易枯萎的鲜花。我心深处,不时会冒出一个模模糊糊的不祥预感:也许命运也会遗传,这个过分早熟的小女孩,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小一号的她的母亲。她未来的人生,也许还会重蹈她母亲悲剧命运的覆辙。
旧皮包:穷苦至极的母亲,却拥有一只皮包。尽管这只皮包已经旧得漆皮剥落,但它毕竟是一只皮包,否则行文严谨的马尔克斯一定会写到漆皮剥落后它露出来的仿皮革质料。在火车还要靠烧煤才肯跑动的年代,商人们还没来得及奸诈到在其它廉价材料制成的包上刷一层漆来冒充真皮包的水平。
她从哪得来的这只皮包?
她的家庭,是个让读者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不对劲的家庭。这个家里,那个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男人缺席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最重的那一副应该由那个男人来承担。如果他挑起了重担,他的儿子就不会在异地行窃时被人一枪打死,他的妻子和女儿也就完全用不着冒着酷热大老远乘火车到马孔多镇上来借什么公墓钥匙。
但马尔克斯在这篇小说里对他一个字也没提。
这只有点神秘意味的皮包当然有可能是捡来的,或者由少年卡洛斯·森特诺偷来送给母亲的。但联系到那个没有被作家提及的丈夫和父亲,更有可能是他当年送给自己妻子的,因为他的妻子也必定年幼过、年轻过、值得一个想娶她的男人送皮包给她过;因为使用到现在,这只皮包已旧得漆皮剥落。
皮包的基本功能是用来藏比它自身更贵重的物品。但在《礼拜二午睡时刻》里的这只皮包,在第二次被写到时,母亲往它里面塞的,只是用塑料食品袋包好的母女俩吃剩的食物。除了食物,这只旧皮包里还藏着些什么更好的东西呢?
也许有母女俩的回程火车票,也许有证明身份的材料,甚至还有可能藏着少得可怜的零钱,但我敢肯定,这只旧皮包里绝对不会像许多女人的皮包里那样藏着昂贵的化妆品。
在我的想象中,这只让身心俱疲的母亲一路上都用双手按住,在不得不腾出手来签字时也要夹在自己腋下的旧皮包,里面所藏着的最贵重的东西,一定是小女孩那句话里提到的那个东西:
她儿子的全部牙齿!
小女孩那句话里说的是全部牙齿。如果只是一两颗牙齿被拔掉,随手扔了也就扔了;但小女孩说的是“他不得不把牙全都拔掉了”,爱儿子爱进骨髓里去的母亲,怎么可能把带着儿子血迹的牙齿统统扔掉?她带着女儿在礼拜二午睡时刻赶到马孔多镇来,除了在儿子的坟前表达一下哀思,一定还有亲手把儿子身体的这一部分也埋进土中的意愿吧。
在小说的最后,母亲婉拒了神父等太阳落山天色昏暗后再去上坟的建议,婉拒了神父的妹妹想借给她们的那把既能遮阳更能遮羞的伞,向神父兄妹说:
“谢谢。”那个女人回答说,“我们这样很好。”
“我们这样很好”,因为这世界绝不可能只是为某一个他说了才算的大人物才存在的;因为任凭命运怎样欺凌我们,也没让我们的心变得像它一样邪恶、凶残、阴冷、黑暗、变态和猥琐。我们很不幸,但我们并没有因为不幸而从人变成非人,我们这样很好。
母女俩来马孔多,是为了给儿子/哥哥上坟。但坟地在哪个位置,她们在坟前是如何表现的,有没有人追来看热闹等等情形,马尔克斯一个字也没写。小说的最后一句是:
她牵着小女孩的手朝大街走去。
因为苦难和隐忍,更因为尊严、独立和对亲人的挚爱,这一对牵着手朝大街走去的母女,走成了拉丁美洲的母亲和女儿,走成了圣母和圣少女。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