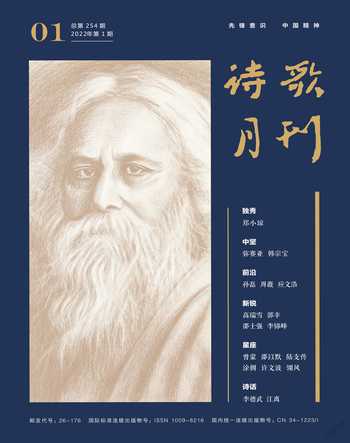我看“江南风格”
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我和胡人、方石英等几位朋友去潘维家里,那时潘维经常参加野外的聚会,有时也邀请我们去他家坐坐,他的厨艺不错,特别是鱼汤炖得非常鮮美。我在他那里看到刘丽安女士资助印刷的两本诗集,潘维的《诗五十首》和叶辉的《在糖果店》,制作得简单而又漂亮,而更吸引我的是那些诗,比如翻开来就能看到的潘维的《第一首诗》,我想我确实为这里语言的变形和感官的互通着迷。还有叶辉诗集的同名诗作《在糖果店》,这个场景童年时的我也是熟悉的,而里面生发的情感与想象,对一个青年人来说,则是那么的精准,他渴望“生活在别处”。于是,我向潘维借了这两本书回去读。
在这之前,我还曾买过朱朱的诗集《枯草上的盐》,诗集名很有意思;绿色细格纹的封面很漂亮,后来才知道是蒋浩设计的;里面的语言极具特色,感受力细腻惊人,节奏也富有音乐性,比如那首《小镇上的萨克斯》。我把一首喜欢但这本诗集未收的诗作《波浪》用钢笔抄在诗集的空白页上。我那时并没有更多想到一点,就是这些诗人都可以归于“江南风格”的名下。
我是一个地道的江南人,祖籍是江苏吴江,出生在浙江嘉兴,经历了乡村里的童年和小镇上的少年时期。平原乡村里的桑林稻田、晚霞炊烟、池塘河流以及夏日夜间的璀璨星河给了我最初的美感教育。虽然有同村的伙伴经常嬉戏,但仍有大片的独处时间。母亲让我在晒谷场看场,驱赶偷食的鸟雀和鸡,我就坐在深秋阳光下,一边翻字典一边看繁体插图本的《三国演义》和《西游记》。后来在我的诗歌中渗透着的孤独与宁静,也许可以追溯到这时的生活。三年级之后我就到濮院镇上跟父亲住一起,那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小镇,河流星罗棋布,镇北的主河道两边保留着木结构房屋,很多人家里都有石阶可以下到河面洗衣服。父亲每个月都会带着我去看电影,我们一起走在小镇昏黄的路灯下,泛着反光的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却没有多少言语。让人想到吕德安的诗句:我们走在雨和雨的/间歇里/肩头清晰地靠在一起/却没有一句要说的话(《父亲和我》)。
我想确实有种地方性的东西,源于共同的生活背景:相同的环境、风俗、文化,可以深深地楔入一个人的记忆,影响着性格、气质的形成。我们能在诗歌中轻易地辨认出我们共有的部分,感到亲切与阅读的喜悦。比如在朱朱的诗《给来世的散文》第一节中,那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生活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时的冲突与杂糅感,我曾在一篇与我夫人合撰的文章中谈及过:“朱朱注意到本地传统所具有的韧性和张力,当它们受到新的潮流冲击时,仍然在风尚之外,成为一种回声、一种隐性的精神源流继续在运转。”(吴宜平、江离《轻逸、自治与自我塑造——当代新诗的江南视角》)
江南是一个流变的地理概念,唐以前主要指的是洞庭湖南北和赣江流域,也就是湖南、湖北长江以南和江西。随时代的变迁,江南指称的区域逐渐东移,现在大致指的是苏南、皖南、上海和浙江。江南气候温暖,山水清秀,风光旖旎,令外地人艳羡。江南也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这里是吴越文化带,其中又以吴语文化为主。在唐宋时期,这里已经是全国经济的重心,人们生活富足,日常生活精致讲究,百姓人家也重视读书,文风昌盛。文学上也形成一种独特的“江南风格”。唐初魏徵曾将之前数百年南北文学的差异概括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即是说江南文学具有一种重形式的唯美倾向。江南有时也被视为颓废耽乐之风的代名词,就像杜牧的《泊秦淮》和林升的《题临安邸》所描写的。
说起比较典型的当代江南诗人,或者说比较符合他人对“江南风格”预期的诗人,我会想到陈东东、潘维、叶辉、朱朱、庞培、刘立杆、陈律、苏野、飞廉等,尽管他们中有些喜欢被称为江南诗人,有些不一定喜欢,但他们确实有许多共同的特征:
一是执着于纯粹的诗艺。不算典型江南诗人的韩东八十年代提出“诗歌到语言为止”和陈东东早年提倡并且实践的“纯诗”,从意图上来说有一致性,就是为了保持诗本身的纯粹性,尽量避免政治话语和文化意义的附着对诗的左右,让诗更多地成为自生性的艺术。不过在具体写作实践中,有些诗人对文化意义似乎欲拒还迎,表现得更像是轻政治而重文化。比如苏野和飞廉的写作中,都着力于接续古典文化和空间的尝试。吴地诗人将对古典文化的喜爱以及将生活审美化的取向,转化为在诗歌中对语言的讲究,往往精于修辞,写作十分自律,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产量也谈不上十分可观。
二是轻逸丰盈的写作风格。这里我再次引述上文的观点:“感受的丰盈与精微、修辞的细致与精妙融合成的纯粹的审美感觉,一种盘旋于现实之上的轻逸。尽管他们有能力面对现实进行出色的梳理,但对现实的凝视很快就会转向远处……确实,在促成诗歌的众多要素之中,他们坚守着“诗是语言的艺术”这一首要的信条,其次才会考虑诗是以言志,是增进对自我与世界的认知还是为葆有感受力以及情感的丰富性,尽管我们绝大部分时候很难把语言艺术的优先性与题材或者意义中心分割开来考虑,就像我们也看到这些诗人的失败的作品,在缺乏情感力量的参与或者人文的基座支撑的时候,修辞就会变得枯萎与干涩,成为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而不再是微妙的感知性的力量。”这里最后提到的是典型化江南风格的一种危险,当过度执着于修辞而忽略了现实的根基,诗就会失去它的生命力。
三是他们的诗歌处理方法与园林山水和盆景造型的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园林盆景属于袖里乾坤,对自然之道的领悟是通过这样一个中介来达成的。而江南诗人同样不是直接面对和处理宏大的题材,通常会采取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隐喻暗示来言此及彼,也即所谓一叶而知秋,从个体来领会整全性的事物,这与北方诗人更愿意直接面对整全性的事物差异较为明显。此外,江南诗人性格都像是“散人”,不爱热闹抱团,这点与具有袍哥传统的巴蜀诗人相去甚远。有意思的是除去北京这个诗人的聚集地,这两个地方就我看来也是当代诗歌最为活跃的地方,无论数量和质量上都十分可观。
当然江南诗人并非都具有典型“江南风格”,比如韩东、梁晓明、沈苇、陈先发、杨键、余怒、胡弦、沈方、池凌云、蒋立波、泉子、育邦、臧北、游离、胡桑等。按梁晓明的话说,外界对江南诗人的理解和预设往往等同于江南的风雅,却忽略了江南的风骨。更为可能的是,除了风雅和风骨,还有更多的路径和风格。如果仅以典型的江南风格来看待江南诗歌,就会忽视其本来的丰富性。比如越文化中就有刚直激越的传统,鲁迅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吴文化也不乏这种具有差异性的东西。而“江南风格”通过不断对外界的习得,也会产生各种变异,它并非凝固和恒定的。
就我个人而言,自身气质中有对“江南风格”的天然认同,基本上上面提到的几点在我的写作中都有存在,并且也从各位师友的作品中受益不浅。但在题材选择或者说在写什么的问题上,我更多展现的是一种热情的沉思,而非轻逸。这可能与自己从小喜欢并学习的形而上学专业有关,比如《几何学》一诗,以超现实和玄想的方式,关注的是宇宙稳定的平衡性结构,以及所有个体和整体之间的一种天然的联结,无论是浩瀚孤寂的星体之间,还是在人和人之间、人和物之间。或者像《重力的礼物》一诗,探讨的是诗人能否在破碎的世界里,重新黏合起充满意义的生活,赢得一种终极的价值。尽管这些诗主题比较宏大,但处理的方式中,仍会让诗在感性与智性、小与大、轻与重之间保持平衡。
如此众多的江南诗人,他们的写作是否给予了当代诗歌一种独特性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否属于典型的江南风格的诗人,总体上,他们对感受性的重视,他们对个人的身体感知作为出发点这种强烈的身体意识,是非常具有价值的。
江离,1978年生于浙江嘉兴,现居杭州。著有诗集《忍冬花的黄昏》《不确定的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