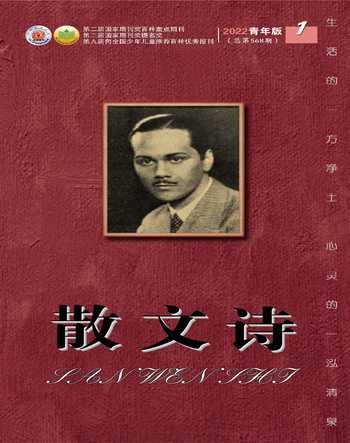怀念书
鲍伟亮
雨夜与友书
祊河水依旧流淌,我在一场雨中回溯往昔。
许是一滴夜色荡漾出波纹,遗忘的便回归岁月,化成泥、氤氲的雾气,抑或是化成某种模型,留给下一批匹配者。
如果不曾遗忘,偶尔打捞出晾晒,便惶恐不安。是的,除却水流一成不变地淌过旧渠,余者均善变,往与今擦肩的洪流静悄悄打磨出符合时宜的砖瓦,垒就光滑的墙壁,反射出现实的无瑕。看,那透明的弧线,彼此在白日里闪烁。
朋友,我们雨夜的呐喊遗落在曾经的那个春夜,褪去嫩黄的梧桐也已忘记了春水的滋养,那些未曾表达的词语逐渐塌陷于岁月的黑洞,不再需要疯狂奔驰。
胸臆回缩,蜕变出成长的砝码,闭合交流的灵魂便诞生出尾鳍,竞跃在时光的长河,一往无前。
朋友,即使我们未曾攀爬过同一座山,却曾在同一条河边对视,畅想未来的轮廓,一如青春的诗意点缀我们茂密的发丝。如果今日是真实的,或许我们都曾怀疑过昨天,那虚假一般的欣喜,或许便是欢聚的隐喻意义。
朋友,走过这场雨后,便抵达了新一个夏天,我不知你何时离开这座城市,正如你不知我已回归。你听,祊河嫩绿的银杏叶翱翔,正回旋起曾经的笑声。
惊蛰草木
雨水如期而至,春雷的讯息酝酿于一个久违的节气。
仿佛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被阳光撕破,又或是故乡的春风将它卷入高空的漩涡,无形且萧瑟的枷锁渐渐消匿。只有春草,汲取着融雪的养料,尽情生长。
沉睡的事物已然苏醒,不再是冰冷的金属,拒人千里。暖风和煦,去年深秋相约的那窝燕子,想必正征服着浩瀚的汪洋,飞往炊烟之下花香浓郁的那户人家。
鸟鸣、风声,农具梳理大地。
拖拉机登山的呐喊声,响彻村庄。
春风抚过麦苗青葱的绿发,忽然弹奏起春耕序曲,这古老的音乐淌过山川河流,淌过墓碑和沉睡的大地子民,淌过思考和智慧的岁月。那些秀发是骨头,是犁,是风和梦,起舞在高低参差的土地;是浪,曾清洗过一代又一代孩童的眼睛,最终变成了线,扯着一只只远去的风筝。这是草木的世界,一切生而平等,给予所有生命以庇护。
河流,湛蓝的镜子,镶嵌在山下,麦田的身旁。波纹不间断过滤着阳光,那些金子,闪烁在风中,飘忽嬉闹。浣衣的妇人正涤洗寒冬的灰尘,坝头有了笑声,沉郁的绳索裂开,鲜活的村庄依旧亲切。
菜园被重新开垦,呼吸的泥土,重新回归母亲的角色。
待春来,草木及草木一般的事物,遥望东山桃花夭夭,十万瓣枝头开放,十万瓣落成泥土,春天便诞生了统一的灵魂——在一个新的季节,守护一个比去年更加宁静的村庄。
怀念书
幸好,肉体的死亡只有一次,我不再经历人前的撕裂之痛,只在黑夜里,梦里,漫长的十年之后,除去石台缝隙杂生的苍耳,凝视人间的最后一缕温度。
那是一个夏天。雨后,我反复强调这个时间节点,生怕行走的机器掉落下一枚螺丝,从此,隔断了记忆的始发地。毕竟,当年一同缅怀的故人们,早已回归泥土,他们是乡间的一声布谷,是春草的一丝起伏,是干涸的时间未起的波澜,徒留行者,一如未曾跳脱的鱼儿,以人类之身,悄声低语。
不期而遇的感知混杂着记忆熬炼的芬芳,随往事切割结茧的创口,缓慢渗透,不留痕迹,只待某个偶然的触动,大坝决堤。
日光洒满我回溯的皱纹,惊觉离世的故人业已寻不到返乡的长路,东山新披桃花的晕红,南河已无白杨鸣蝉,那些散步的年迈者,被时间一条条擦亮颤巍巍的脚步。
西岗,杏花从未失约于清明,氤氲的晨雾掩映烟岚,思念总在春归的季节寄向远方。自从翻土,杏花便敛于一场冬雪,留下树影孤独地感受春寒料峭。
黄土或许需要直白的倾诉,那些粗糲的肩膀羞于人前柔软,于是,寄托的祝福便在清明的节气里拥挤,年复一年。
怀念,或许将止于怀念,异乡没有清明,一声夜晚的叹息盖过白日的漂流,随后又淹没于漂泊的时间洪流。
直待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