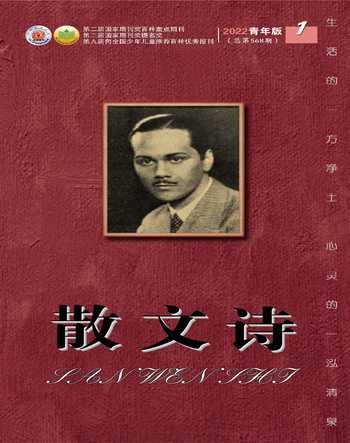信仰的闪电
望秦
白 鹭
沃尔科特放养在文字里的白鹭踩着暮色起舞,飞过河谷和田野,稀稀落落的炊烟缠绕着它们。
时间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像我对一只白鹭的消失爱莫能助,在这唯一的尘世,人们只是用余光照着灵魂,为了生存,几乎已耗尽了一切。
在冬日,我有一间书房,隔着阳台可以见到少量的光,它们刚够照亮一个香炉和一盆红掌。生命和信仰之间呈现出的默契,使我拥有了片刻安静。
翻书的声音轻柔,暗香浮动,每个字都有各自的使命,或生或死,或明或暗,作为一个最小的笔画,我渴望一缕光。
一缕光是一片湿地,和湿地上小片的天空。
白鹭还行走在暮色里。
沃尔科特已经走远了,他乘着上帝的步辇,化身文字的宫殿。
而我还留在人间,在错乱的命运沼泽里一步一踉跄,梦想之翼沾满了污泥,我甚至来不及在离去之前,按自己的方式活一回。
他写到,在可能是最后一年的时光里,写最好的诗,画最好的画。
那我呢?在最好的年纪里,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林家铺子
每个时代都有一爿临街的铺子,寄养着生活的油盐酱醋和酸甜苦辣,開门关门之间,比换天更可怕的是一天天的收支是否平衡。
历史像群众演员一样,在街道上来回地走,消失的光阴都沉积在柜台上,一个失效的算盘再没有过正确的计算。
北直街上,梧桐树落光了叶子。空落落的枝条顶着残缺的天空,街上行人很少,寒风充当了冷漠的顾客。
金店最是富丽堂皇。橱窗里的金牛、金鸡、金币保持着高高在上的生活态度,寒风仍在吹,有些冷,自古以来从未退去。
曾经火爆剡城的手撕面包,只留下香味还没有散去,人们总是在不断更迭的新鲜感里迷失。
消失的店铺比故事更多。
当我沿着记忆穿行在陌生的街道,除了路灯发出洁白的光,电线在天空织网,再也不见那些年隐秘的店铺、小酒馆,或者古玩店。
宿命仍在继续。仍是茅盾先生眼里的大泽乡,或者老通宝的春蚕和秋收。
永恒的敌人
雨落下来,鹅卵石的街道变黑。
小小的深渊,在石子之间打开。
——扎加耶夫斯基
在一座老式的教堂前面,人们停留了一个短暂瞬间,暮光从屋檐垂下来。上帝没有参与对灵魂的指引,是自己,在将自己放逐的过程中,接近了真相。
沿广场来到这里,所有路口已经消失,一扇紧闭的门边,站着沉默的天使。
影子填充着生命,在我们不可见的角落,耷拉着的时辰越来越薄。
我几乎听见了一声嘶鸣,从未知的维度里发出。
穿过这座城市,我们看见更多广场和教堂,看见更多和时间对峙的人,看见更多败下阵来的英雄。
一个异域的黄昏,在酝酿之初就被赋予了不同的文化和语言。当我在遥远的暮色里读到:
我们不知道,我们无法知道,
我们是否得救
当时间终止。①
注:①引自扎加耶夫斯基诗句。
尘世以上的爱情
我独自出发,承受着铁面无情的命运之压迫,最后精疲力竭。最终,孤独和寂寞引领我穿过隐藏在深处的河流,那淙淙之声是天使的琴音,是无边旷野的快乐和爱情的韵律。
半明半暗的天边总有人踟蹰不前,是错过了上帝的马车,还是仍未寻见自己,在光的丛林里迷失。
我期盼安宁。在我目光所及之处,只有夕阳和你。
影子越过了溪涧。
我喜欢在火光里读一本诗集,聆听火焰在泥墙上行走,烧红了木头里的铁钉,一缕来自往事的风吹着我。
孤独不会轻易屈服。当我久久沉溺在文字里,一个已经失效的地址令人无比沮丧,所以,痛苦都有了根源。
而我无能为力。
灵魂极度地焦虑,被静谧的暮色笼罩。①请将我最后的爱还给上帝,当时间收回了一切,这是我唯一留在尘世的遗物。
注:①引自米拉·洛赫茨维卡娅诗句。
山巅之险
坐在午后的江边,我快要睡着了。
声音一下子离得很远,仿佛隔着无数时空,突然想起一个关闭视觉很多年的老人,他是否困扰于声音的远近和真幻。
溪水从竹筒上流下来,时间漫过了水缸,向着上叶坑、桃树湾流去,它们穿过了栅栏、竹林和岩石,点燃了沿途的月光。
月亮一直悬挂在山间。照亮了一个孤独的老人,和他的柴垛,荒草,残墙。
一个人只有习惯了孤独,才真正接近了人生的真谛。
返景入深林,听瓦片上星辰的絮语,听山道上奔跑的小兽撞翻了月光。
合上斯奈德的《山巅之险》,就像合上了一座山,一条河,一段往事。
我鞠躬,双手合十,告别。
这些黄松木——我们分享了它们的空气、雨水和太阳。①
自然到了极致就是禅,就是诗歌,就是一个人能够抵达的最远的地方。
松木,松鼠,鸬鹚,夜鹭,甚至山谷,湖泊,皆是充满了灵性的神。我无意离开命里的静海居,当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仍是火堆旁边的少年,给你念海子的诗。
注:①引自斯奈德诗句。
沙之书
有些蓝从一开始就有摄人心魄的力量,一湖沙丘和阁楼荡漾在月牙泉,芦苇摇动清风,细碎的蓝散落在沙砾之间,犹如无法捡拾的记忆和梦想。
树影和城市镶嵌在天空边缘,黯淡轮廓是历史起伏的线条,是炊烟和战火,是葡萄美酒和青纱帐。
暮色归途。
天色从沙粒上滚下来,覆盖了沙丘与亭台,泉边亮起的灯光恍惚,并非人间——沙漠,泉水,老树,阁楼,少女。
行走在沙子上,我想象着一个僧人翻动经书的声音,想象着工匠正往墙壁上作画,想象着烛光摇曳,飞天起舞。
此后,已无夜色需要珍藏,在无休止地流动之后,所有沙子都是一座悬崖。
佛经一般的大风①,吹过沙丘,夜行人穿过丝绸一样的夜色,沙粒们停在泉边,等待着佛乐和灯光的洗礼。
每个世界都有一种慈悲,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将我们点亮。
像沙子。
它有最轻的尘世,和最重的灵魂。
注:①引自万小雪诗句。
无眠的夜晚
接近5点,我最后的一丝睡意也被消磨殆尽,我只是做梦,这比清醒更让人疲惫。①
我的5点是铃声和梦境的汇合处,朦胧是枕畔的时辰,一点点剥开意识。那无穷渊薮的影子和风声,那腐朽的栅栏和火焰,隔着睡眠抵达的远方。
只有偏头痛,将夜晚设置成一个个深渊,掉落或飞翔是同一回事,疼痛带来的落差令现实痉挛,使夜色错乱。
偶尔,有一些无比悠遠的记忆,跨越了生死,跨越了时间序列。它们比偏头痛更令我手足无措。
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发生或从未发生的事,裹紧了灵魂。
夜晚的秘密,似乎不仅仅关乎时间和明暗,正如我看到的灯影,穿梭梦里梦外,穿梭不同的时空。
铃声带来的间隔,是一个梦的结束,是另一个梦的开端。
我在不辨方向,不辨真幻,没有起始和终点的梦境,做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注:①引自卡夫卡日记。
约 会
我将拈着话头拈着我的未磨圆的诗句
重来。且飙愿:至少至少也要先他一步
到达
约会的地点
——周梦蝶《约会》
我将听着雨声抵达梦境。关于夜的深浅,我可以不提;关于河道的影子,我可以不提。只是你,一个似真似幻,亦人亦仙的存在,使我终日难以释怀。
夜火是否还在燃烧?洞穴深处的寂静是否已经潮湿?
浮在岩壁上的青春早已消失,当我们还守着枯瘦的躯壳,怀念一条曾经丰盈的河流。
雨水不断落下来的夜晚。
我听见了来自虚无处的声音,像一段未解的经文,一支无解的签。唯有沉迷,使时间有了片刻空白,我得以偶遇自己。
之后。有人站在月亮投影的河谷,水流潺潺,所有梦都是湿的。
包括那句谶言——约会都是上一世的未尽之事。
更深的镜子
1 ▲ 这是一面陈旧的镜子,映着一张不完整的脸,皱纹在镜面上越陷越深,它们是时间的另一座深渊。
几道裂纹穿过面颊,微微扭曲后续接上的表情有些落寞,窗外的冬天依然那么深。一群鸟飞过对面的楼房,电线如同枯萎的树枝,站在风声里已经许久了,不断被收割的事物,在记忆里沉寂,或者喧哗。
阳光在墙面上游动,吻过一枚铁钉和它的伤口,吻过一张蜘蛛网和网中央的寂寞,吻过一本日历和它的吉凶未卜。
镜面是模糊的。模糊了之前和之后的一个刹那,也模糊了站在镜前和镜后的人。我们都是来自镜外的世界,却总是试图寻找镜子的秘密。
在指尖相触的一刻,有种无比遥远的窥视感,顺着那一丝凉意进入了我们。
无关时空,这样的窥视感将伴随我们一生。
在镜子里看见另一个自己,这是多么荒诞而不解的事。当灵魂一分为二,当我们看到更多的自己从虚无中诞生出来,却没有一个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
寂静很深。一整面墙都面临无处不在的裂缝,只有镜面永远是完整的,不管碎成多少块,它的世界依然完好如初。
2 ▲ 镜前灯总是坏的。错误的光学带来诡异的影子,有时候,寻找自己是一种冒险。
有谁自带一种光芒,可以在镜中呈现真实的自己,上帝或者佛陀,唯有赋予存在和不存在以同样的意义。
总有一天会失手打碎自己的。当我们终于脱离了一,回归到无穷的时候,我们靠什么维持另外一种形式的存在?
在一面镜子之外,在一种虚无之内。重新定义和虚构一个人生来就携带的那种距离感。如果必将与自己相遇,何不倒空一些时辰,让对视更加空旷,让孤独更加纯粹。
“别了,”垂死的男人对着他们举到自己面前的镜子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再见。”①
注:①引自瓦雷里诗句。
地理书
曾经梦想做一个考古学家,行走在丛林和荒原,古墓或水泽。
背包里的手铲,探铲,比色卡,都染上了古老神秘的气息,比史书更可靠的是时间和它的宽容。
荒草还原了天空,河流带走了城镇。一千年,或者两千年,皇权早已旁落,祖庙回归了荒芜。只有农民仍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比权力更持久。
四季轮回交替,简单赋予了人们草木之心。
历史放下偏见,风吹着万物。
人间沧桑,当死亡也消失不见。究竟是什么赦免了时间?当我行走在虚无主义的天空下,将遇见哪一世的你?
岁月仍在大地上酝酿,一场雨,或者一片荒芜,石头滚落山巅,历史之外的事件是谜,是偶然和必然。
文字匍匐着前行。
穿过了尘烟和落日。穿过了石碑和生死。
当所有文字都有了来世,而我仍没有等来自己。
玻璃光
1 ▲ 花雨还没有远去,沾湿衣襟的是你眼眉低垂的柔情。
天光微醺,暮色是屋檐下无风而动的铃铛,一阵轻过一阵,直到灯影浮现在石径上。
是谁续上了梦里的花香?记忆是最好的酿酒师,当爱微醺,世间万物也有了醉意。
我站在石阶下,只看见佛祖端坐的莲台,一排蜡烛已经燃烧很久,摇晃的时光都兑现成了信仰。
等雨停。等清扫石阶的僧人。等来自无限时空里的漂流瓶,在此刻打开。
2 ▲ 你站在濯缨亭外,暮色沿着崖壁垂下来,朱梅体内深藏着理学之气:理学者,形而上之道也。
更加形而上的是爱,是缓慢时光里的对视。
一种寂静落在梅树和亭台之间,俯身听一条石径的耳语,听一株草体内的远方和潮声,听你忽远忽近、忽明忽暗梦境的回声。
米芾题在岩壁上的字仍然清晰——面壁。我想起写过的诗句,面壁,无壁,若心有壁,尘世如井。
是的,我是多么愿意做一个你的囚徒。
3 ▲ 当下山的路只剩一种感觉,高低错落仿佛人间坎坷。你说,这样的夜若有暗香袭来,又该醉倒多少信徒。
路边的天王殿已经关门,我们双手合十,权当拜别韦陀了。仪式是生命的一部分,来去之间,有什么能令灵魂心安——除了爱和信仰。
放生池外是山门。人间不远,红尘不远,拾级而下的时候,突然想到,我的人间已满,该如何安放生死。
早晨和入口
一半身体被封印的时候,我们还能以半生半死的状态继续写诗吗?
还能继续用旧身体去感悟,继续用时间和灵魂去敲打每一个词,甚至音节吗?
但我相信有人做到了。
当他用一只手弹钢琴,用另一只手写诗,用一半的行动来阐释生活,无论是大海,还是林间空地,万物都有入口。
琴键得心应手。温柔的音锤敲打。
音色是绿的,活泼而安宁。
音乐是斜坡上的一栋玻璃房
那里石头在飞,石头在滚。①
我的觉知里一片黑暗。
是这一栋透明的玻璃房将我寻见,在影子落入无限循环的时候,我听见了来自内心的声音。
像山谷一样清幽,像溪涧一样灵动。每个字都发出淙淙的声音,将我带往遥远的海岸。
江边的阳光时隐时现,一阵风从背后吹来,我怕它们弄乱了书上的文字。
怕它们在两种语言之间错位,穿插,直到再也寻不见。
时间还是宽容的。
在我合上最后一个意象时,午后的光影还有些形状,在树丛和江水之间。
注:①引自特朗斯特罗姆诗句。
水面波纹
更令我痴迷的,仍是那斧柄。
在两次或者更多次的解读里,我看到了木头不同的纹路,它被握住,然后甩出去。
我没研究过掉落,和回旋的概率,只听见它深深地砍入另一根木头。
“伐柯伐柯,其则不远。”用一把斧头砍出斧柄的样子,正是因为心里有一把斧头。
所以,我一直在砍伐,直到把自己砍成自己的形状。
之后,我发现更多的山谷,寺庙,溪流,鶗鴂,月光。
穿行在丛林里,万物安静,我等同于一只蚂蚁,或者一块石头。我忽视了自己的触角和纹路,逐渐融入更靜谧的世界。
水面起了波纹,那是云的褶皱,还是时间的鳞片?远山从模糊到清晰,像是谁掀开了一层帷幕。
蕨丛、李树和草丛中的
小动物①
直到暮色渐渐抹去了远景,我只看见脚下一小块泥地,长着南天竺,和野百合。
注:①引自斯奈德诗句。
春的临终
想起小鸟在天空消失的日子,想起春天的终点,和一座山冈上守望的星辰。想起二十亿光年的孤独,想起悲伤的天使,和一座寺庙里似有若无的钟声。
当我盘坐在夜晚的中央,窗外是绵延的灯带,是车声,和一路铺展的远方。
一切都是干净的。
从一个词开始的叙述,从一个背影打开的故事,在不断翻页的过程中,我听见了内心深处惴惴不安的声音。
语言是思想的副页。
我把一切都喜欢过了,可以无休止地凝视着自己,凝视着时间带来的意义。
白天是梦境笨拙的补充,我记下了现实世界不曾出现过的事物,自以为可以稍稍接近灵魂。
在我读到,人们只是倾听一种声音,只是倾听一个世界①,似乎一下子得到了安静。
只剩下一种声音,在天空下回荡。
注:①引自谷川俊太郎诗句。
同义反复
带走倒影的水流进心灵,
如青草依偎的叹息。
语言在反复中获得了新的意义。像流星不再局限于夜空,语言在不断穿梭中进入肉体,进入灵魂,直至生死。
我进入过语言吗?
在时间的河岸,一个徘徊复徘徊的影子,终究只是融入了更大的阴影。
当河水漫过了堤坝,一个个修剪往事的夜晚,恍惚刹那,又恍惚永恒。
直到一轮山月被引入窗口,在长久地对视之中,我渐渐明悟了,寂静无关声音和色彩,而是一种空旷。
由内而外的空旷,蔓延至思绪的每一根触须,所有悸动都已沉寂。
像鸟儿被取缔它的痕迹。①
我留下一个越来越淡的影子,伏在书桌旁,用书写代替做梦。
用语言代替醒悟,用忏悔代替爱情。
注:①引自德拉戈莫申科诗句。
思想录
将思想录播在久远的时空,一个面临困境的人,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悸动和哀伤。
从数学跨进哲学,从时间跨进灵魂。当我沿着一个人的足迹久久徘徊在街头,不是路途太远、太模糊,而是太清楚了,万物一目了然,终点就在那里。
只有上帝是一个意外。
他在永恒的光芒里,不为照耀而照耀,不为预告而预告,一切都是注定的。
像里尔克听见了天使的声音,帕斯卡尔几乎站在了上帝的身侧,以他瘦弱的病躯阐释着关于宗教,关于信仰的根源。
人的天性完全是自然。
偏见导致错误。
时间治好了忧伤和争执,因为我们在变化,我们不会再是同一个人。①
我更喜欢这样的思索,带来了一种深入人性的东西,简单,自然,纯粹。
在浩瀚的九百多条思想集萃里,有无数光点等待着我们去发现,与之对视,与之相容,这几乎是宇宙最初的样子。
注:①摘自帕斯卡尔《思想录》。
老辰光
1 ▲ 注定有很多时光不会老去;
比如你,比如安昌街头的茶肆。
近午的老街上,突然有了流水和它的影子,像寂静之中微漾的音乐。
续水,对视,沉默,看乌篷船摇着橹,经过石桥和摄影师的镜头。
当光线落在你脸上,世界化作神秘纹路,我確信自己听到了遥远的神谕。
桨声里的午后,毫无破绽,就像你此刻的恬静和危险。
是什么弄乱了墙上的光影?
当我在等待中试图还原上一刻,而时间从不会复述无规则的世界。
它们一旦消失,记忆就开始模糊,世上本没有完整的往事。
2 ▲ 安静是可以听见的。
酱鸭,酱鱼,酱鹌鹑,挂在临河的绳子上,透过来的阳光都有了秘制的酱味。
历史和光阴的气息,使我沉醉于这一刻。无须过桥,无须撑船,甚至无须走动,这寂静,本身就是最神秘的。
其实,时间并不带任何色彩,这最无疑和最可疑的物质,一旦深入进去,就再无别的灾难了。
它将完成一切,却和我们毫无关系。
我还是打不开自己,就像无法根除的偏头痛一样,疼痛让我清醒,孤独让我自在,而爱情让疼痛和孤独绽出了万般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