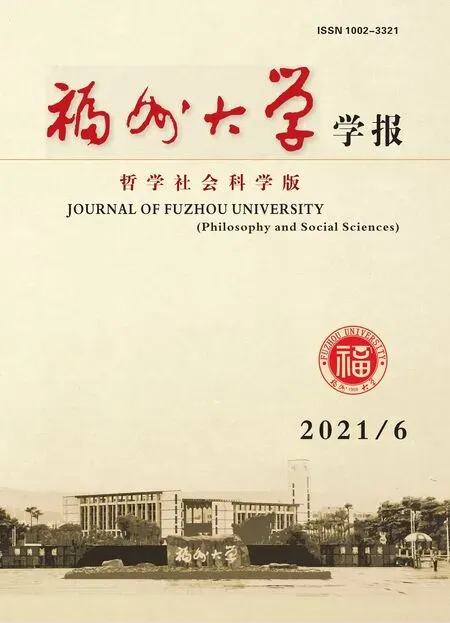琵琶协奏曲《春秋》的艺术特征论
吴慧娟 廖丹滢
(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
唐建平为琵琶和民族管弦乐队而作的大型协奏曲《春秋》完成于1994年9月,是应国际儒联的委托,为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而创作的。[1]该曲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古朴典雅的旋律,复杂高超的演奏技巧,庞大而辉煌的结构等特点,成为近现代大型琵琶作品中演出最为频繁、最重要的作品之一,2003年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选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作品之一。
这是一首单乐章的标题协奏曲。乐曲由引子和四个部分构成,各部分均无文字标题,而只用速度标记:引子:慢速-渐快-中速-散板;第一部分:中速抒情-稍激动-稍快-散板;第二部分:快速-突慢;第三部分:稍渐快-中速-渐快-稍慢;第四部分:急快-散板-慢至极快。本曲融合了奏鸣曲式的某些原则和传统套曲的结构元素。这部协奏曲是目前琵琶类大型作品中上演率较高的一部,全曲篇幅长大(共666个小节),编制宏伟,风格鲜明,匠心独具,有相当的演奏难度。作为一首标题协奏曲,其标题性构思的实现方式与《花木兰》[2]和《草原英雄小姐妹》[3]迥然不同,在协奏曲体裁的四个原则方面,本曲也有许多特殊的表现。
一、“得意”而“忘形”:对“奏鸣曲式”原则的大幅度“化解”
引子(第1-43小节)用的是慢板,以深沉厚重的气势先声夺人,借用了传统戏曲中紧拉慢唱的手法,充满张力,此外还预示了在全曲中具有重要结构意义的一个音乐元素——增四度音程。作曲家本人曾说,这个音程来自于春秋时期在历史上的纪元数标:公元前770-476,722-430。独奏乐器以散板式的扫弦入场之后,演奏了一段古风性的吟诵调,级进与大跳(七度、六度)结合的旋法,丰富的变音,偶尔出现的增四度音程,不仅奠定了全曲典雅脱俗的基调,而且也预示了主题所包含的主要音程,见谱例1:

谱例1:《春秋》引子里的吟诵调旋律
第一部分(第44-87小节)相当于奏鸣曲式的主部,这个主部较有特点,并不像传统的西方奏鸣曲式主部常有的动力性和简约性特点,其古朴典雅的性格倒是更像西方奏鸣曲式的“副部”。见谱例2:

谱例2:《春秋》第一部分主题
第一部分是一个带反复的二部曲式(AABB′),A段由独奏乐器呈示,E徵调式,紧接着由乐队复述一次;B段先由乐队呈示,随后由独奏乐器进行变奏,以散板奏出,兼有装饰变奏与性格变奏两种性质,同时它也具有“导出”的性质,即,仿佛是第二部分的引子。
第二部分(第88-271小节)相当于奏鸣曲式的副部。整个第二部分由两个对比性乐思不断重复、变奏、扩充构成。第一个乐思是舞蹈性的首次出现于第88-101小节,3/4拍与2/4/拍交替,先由独奏引出,紧接着由乐队合奏,其形态上的鲜明特征是四分音符旋律中加有附点,听起来喜气洋洋,精神抖擞。见谱例3、4:

谱例3:《春秋》第二部分舞蹈主题a

谱例4:《春秋》第二部分舞蹈主题b
第二个乐思是“奔跑”性的,首次出现于第102-115小节,拍变为4/4拍,其标志性的形态特征是快速运动的16分音符,这个主题在独奏和乐队声部来回游走,见谱例5:

谱例5:《春秋》第二部分“奔跑”主题
第二部分在情绪上与古朴典雅的第一部分构成鲜明对比,从位置上看这里好比是奏鸣曲式的副部,但从性格上看,以其欢快的速度和丰沛的活力,它倒更像是“主部”。这种颠倒错位、模棱两可的感觉,是作曲家尝试融合中西两种结构原则的“副作用”。还应指出的是,这个“副部”不是仅仅被“呈示”,而是包含了许多“发展”的元素。
第三部分(第272-473小节)兼有插部和发展部的性质。说它是插部,是因为在此有对新曲调的集中呈现;说它像发展,是因为这个曲调是由呈示部里的素材派生而来的。第282-300小节是新主题,独奏乐器以轮指演奏感伤的旋律,如在慢乐章里那样。由于这个曲调里也频繁出现七度、六度大跳和增四度音程,故而很容易教人联想到引子里的素材,仿佛是对引子中独奏散板旋律的“重组”。第301-326小节可看作是插部第二主题的呈示,它以对插部第一主题的重复开始,仿佛是它的扩充演变。独奏乐器以泛音方式奏出新主题,它在音调上影射了古琴曲《梅花三弄》的主题,D宫调式,在本曲中这个主题的原型是主部第188-192小节的管乐声部上的旋律。由于上述两个“插部”主题都是由呈示部的素材派生而来,故而它们的陈述便已带有了“发展”的性质。从第327小节起,作曲家开始对方才插部第二主题进行发展,发展的方式包括改变其力度、演奏媒介、织体,以及旋律加花、织体加厚等,篇幅很大,一直持续到第473小节,也就是整个第三部分的末尾。
第四部分(第474-666小节)兼有华彩段、再现部和尾声的功能。总谱上虽然没有出现“Cadenza”的字样,也没有独立的华彩乐段,但华彩乐句随处可见,作曲家使用了扫弦、并弦、滑弦、绞弦、快速弹挑、连续滑音、轮指等演奏技法,非常出彩,扣人心弦。第508-512小节是对副部中“奔跑”素材(乐队和独奏交替连续16分音符)的再现;第625-636小节是对引子中独奏素材(慢起渐快的扫弦)的再现;第642-650小节是对主部材料(四分音符夹杂附点)的变化再现,保留了旋律骨架,节奏被拉长了一倍,同时也改变了性格(由古朴典雅变为高亢雄壮);第651-666小节是基于主部主题素材片段的紧缩而写成的尾声。
这部作品综合了西方奏鸣曲式的核心思维与中国传统套曲的某些原则,在总体面貌上显得十分“另类”:它保留了“呈示-发展-再现”的大致轮廓,反其道彰显了主、副部之间的对比关系,模糊了再现部里素材回归和调性服从的传统。但它的音乐素材高度聚合,论证发展较为充分,对比、统一的原则毫不含糊,秩序重组之后的“升华”效应亦十分明显,因此也可以说它基本领略了奏鸣曲式原则的“精神”,用所谓“得意而忘形”来形容这部作品的曲体结构之于奏鸣曲式原则的关系,大抵是贴切无误的。
二、以“竞奏”作为乐思发展的主要方式
引子(第1-43小节)部分,独奏和乐队的关系以“协作”为主,只在末尾的一段独奏吟诵调中,出现了乐思的对峙。二者协作的方式有三种:其一是先后的“预示”与“承续”的关系,如在开头前8个小节中,乐队中的打击乐器以慢起渐快的散板形式进入,随后独奏乐器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乐队发挥了铺垫和引领的作用;其二是独奏和乐队某些声部的齐奏,如第9-13小节,独奏乐器和打击乐器组的梆子以同步的节奏共同复述开头的节奏动机;其三是“主奏”与“伴奏”的关系,如第5-13,18-24,27-29小节,独奏声部是主导性的乐思,而乐队则以和声性的长音相伴随。第37-43小节的独奏部分具有“导出”性质,可视作乐曲入调上板的前奏。
在第一部分(第44-87小节),独奏和乐队仍然维持着“协作”关系,只是方式略有变化:抒情的A主题首先由独奏乐器领奏(第44-60小节),三个升号调,E徵调式,乐队演奏支撑性或呼应性的乐句予以跟随,此时二者是“领奏”与“助奏”的关系。当独奏呈示完主题之后,乐队随即接过主题,完整地进行了重复(第61-70小节),这种“呈示”与“复述”的方式也体现了独奏和乐队的相互支持的“协作”关系。从第71-87小节里,二者的关系有所互换:B主题首先由乐队奏出,随后由独奏乐器做变化性的复述(兼有装饰变奏和性格变奏两种成分),二者是“呈示”与“变奏”的关系,由于乐思相同,故而仍可认为是一种协作性的互动。
在第二部分(第88-271小节),独奏和乐队的关系显得更为丰富,总体来说,它们以“竞奏”为主,兼有“协作”。“协作”在此有三种方式:第一种表现为“呈示”与“复述”的方式,例如,当独奏在第88-94小节呈示过舞蹈主题之后,乐队在第115-125小节予以复述;第二种是“领奏”与“助奏”的方式:在第95-101小节,当乐队合奏舞蹈主题时,独奏乐器演奏泛音为之“增色”;第三种是“齐奏”关系,即独奏乐器重复乐队的主旋律声部,例如在第119-125,138-151,160-172,217-221小节。至于“竞奏”关系,具体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二者交替演奏相同的素材,你追我逐,其乐融融,如第102-114,175-187,197-208,229-252,253-259,263-271小节,都是如此;另一种方式是二者交替演奏不同的素材,相互对比,互不示弱,如在第126-137和152-159小节,乐队合奏出舞蹈主题的片段,而独奏乐器则用“奔跑”主题予以回应,这种关系也持续了较长的篇幅。
在第三部分(第272-473小节),独奏和乐队之间有了更密切的协作与交往。总的来说,在插部两个主题呈示(第272-326小节)时,独奏和乐队是“协作”的关系,而当作曲家开始发展插部第二主题(第327-473小节)时,独奏和乐队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为“竞争”关系。插部第一主题的呈示(第282-300小节)是由独奏乐器领奏,乐队以连绵的旋律为之助奏,二者构成对位。插部第二主题呈示时,独奏和乐队在节奏上甚至变成了同步,“协作”的关系更明显。插部中的发展部分大概有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第327-354小节,独奏和乐队以极端对比的力度交替演奏同一个动机,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戏剧效果,二者是“竞争”关系;第二阶段是355-401小节,独奏乐器逐渐加快速度来发展乐思,乐队也以逐渐增强的声势——开始时只用弦乐和一种打击乐器,随后逐渐加入管乐和其他打击乐器——紧密跟随,二者是“主奏”与“伴奏”的关系;第三阶段:第402-456小节,是由乐队自身以不同乐器组为单位来发展乐思,独奏乐器休止,这段音乐具有“乐队协奏曲”的架势,并将音乐情绪推到高潮;第四阶段:独奏乐器重温泛音旋律,乐队充当伴奏,二者又恢复了“主奏”与“伴奏”的关系。这段音乐的力度很弱,考虑到在此之前时乐队全奏的高潮,而在此之后的第四部分也是以极强的乐队全奏开始的,故而这一段实际上发挥着“间奏”的性质。
在第四部分(第474-666小节)里,独奏和乐队除在少数片段内处于“协作”关系之外,在其余大部分篇幅里都体现为热火朝天的“竞奏”方式。少数的“协作”关系体现在以下三处:第一处是第483-491小节,二者是齐奏关系,即独奏乐器重复乐器的某些声部;第二处是第513-543小节,独奏正在炫技,而乐队从旁“指点”,一度也表现为齐奏;第三处是第625-637小节,其中由独奏作为领奏,乐队中的弦乐器以持续的颤弓来进行助奏,并渐渐改为在三连音节奏上持续推进的全奏;第四处是第642-657小节,独奏和乐队以齐奏的方式进行协作,节奏上越发缩短,渐成猛烈爆发之势。这四个协作的片段篇幅都不长,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它们具有“引入”和“过渡”的性质(也可能是为了给独奏者提供喘息的“气口”),而更大的篇则表现为二者的“竞争”。例如:在第492-507小节,独奏和乐队以模进的方式进行交替;在第508-512小节,独奏和乐队回忆副部中的“奔跑”主题(16分音符),二者在呈示部里就是竞奏关系,此处亦然。在第544-566小节,独奏和乐队以密接的方式对比、模进并互动,很有动感。在第576-609小节,独奏和乐队以“卡农”方式(前后间距2小节)展开竞奏。在第658-666小节,二者由“竞奏”转变为“合奏”。此间乐队演奏的是4分音符上的模进性乐句,而独奏又是以16分音符的震音与之“赛跑”,直到最后三小节变为同步,二者最终在极强的合奏(变为柱式和弦)中结束。
综上所述,独奏和乐队在这部协奏曲中有着非常丰富的互动感应,它们既协作又对抗,织体丰富,效果突出。特别是在对乐思进行发展时,“竞奏”几乎成了最重要的方式,这在协奏曲体裁中是很能出彩的。“协作”的方式也有多种,其中以“领奏/助奏”者居多,“主奏/伴奏”者居次,偶尔也有“齐奏”的片段。总体而言,在这部作品中,独奏的参与性虽然很强,却并没有给人以“垄断”或“独霸”的印象(由于受炫技风尚的影响,西方19世纪的协奏曲作品中常见这一弊病),乐队仍具有丰满的性格和独立的尊严,二者确乎都是平等的“主角儿”,它们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平等互动,很好地彰显了协奏曲体裁的独特魅力。
三、音响对比以纯形式范畴为主,较少涉及对“音乐形象”的影射
在引子部分,独奏乐器演奏着慢起渐快的散板式节奏,独奏的加速渐快蓄积了越来越强烈的张力,等到这种张力达到极点时,乐队以强奏方式突然闯入,从而将独奏的张力尽情释放。这个笔法在引子中出现多次,可谓大起大落,大开大合,极端的力量对比不仅增强了音乐的戏剧性,也使乐曲的开场具有了恢弘的气势。
在第一部分,音响对比主要体现在两处,第一处是独奏乐器呈示主题之后交由乐队进行复述(第61小节处),这里主要不是力度的悬殊,而是音色的对比。第二处是该部分末尾,独奏乐器以“快起渐慢”过渡到“慢起渐快”的连接性散板,随后由乐队演奏热烈欢快的“副部”主题(第95小节处),这里的对比不仅在于力度上的差异,而更是音乐情绪上的变化。
在第二部分,独奏和乐队有大篇幅的竞奏段落(第102小节起),二者演奏的素材时而相同和时而对比,但在力度和音色上的差异非常明显。在第179-272小节即插部主题的发展过程中,独奏乐器总是奏以炫技的快速音流,而乐队则间或奏出主题性的乐节,二者的对比更多在于音型和姿态。
在第三部分,出现了全曲中最大胆也最具特色的音响对比(第308-353小节),独奏和乐队交替奏以“梅花三弄”的变化主题,乐队是极强的全奏方式,器宇轩昂,而独奏乐器则是泛音形式的单音,孤高清越,如前所述,这段音乐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二者的对比不仅在于力度和音色,更在于音乐的姿态和性格。
在第四部分,伴随大篇幅的炫技和竞奏段落,出现了更为密集和多面的音响对比。当独奏通篇炫技(第474-491,520-543小节)时,表现为富有活力的“奔忙”姿态,而乐队此时主要是“帮腔附和”,紧密跟随,二者的对比在于音型和姿态。独奏和乐队的竞奏(第492-512,544-599小节)有两种方式,当二者以相同的素材竞奏时,音响对比更多体现在力度和音色方面,当二者以不同的素材竞奏时,音响对比更多体现在气势和姿态方面。
此曲是一部“写意性”的标题音乐,而不涉及对特定事件、场景和形象的描绘,故而其中的音响对比更多是体现在若干纯音乐范畴上,比如音乐的织体、音型、音色、力度方面。至于音乐的性格、情绪和姿态,虽然带有一定的表现意味,但并不构成明确的所谓音乐“形象”的对比。
四、以“华彩句”代替“华彩段”,并将华彩段化入再现部
这首单乐章协奏曲没有独立的、被标作“Cadenza”的华彩乐段,但在再现部里却通篇使用了具有高难度演奏技巧的华彩性乐句,其中包括:扫弦、滑弦、并弦、绞弦、快速弹跳、轮指等。除此之外,在全曲的引子、主部呈示的末尾(第83-87小节)、副部呈示(第二部分第103-114,127-137,146-159,68-174,179-187,199-221,233-249,263-271小节)、发展部(第三部分第354-376,384-402小节)里也有很多独奏乐器炫技的片段。在西方古典时期的独奏协奏曲中,华彩段本来就是位于再现部之内的,精确地说,是位于再现部里的结束部的末尾,也就是尾声之前。可以认为,本曲中作曲家将华彩段“化入”整个再现部的做法是对西方协奏曲体裁传统的一种“活用”。另一方面,再现部通篇炫技的这种写法,又使人联想到西方协奏套曲的末乐章(独奏乐器往往也是通篇炫技),由于这个再现部与尾声是合一的,所以它确实也就像是个末乐章。另外,西方协奏曲第一乐章里的华彩段通常要回忆主题而不仅仅是炫技,本曲中的华彩段由于完全融合于整个再现部之中,故而华彩片段自然也涉及了主题素材,然而就主题再现的“片段性”(而不是一个完整部分)而言,它不太像是再现部里对主题的“回归”,而更像是华彩段里对主题的“回忆”。总之,协奏曲的炫技原则在本曲中有充分的体现,而且,高难度的演奏技巧几乎总伴随有对主题的发展,并同时与乐队保持着密切交往,所以丝毫不显得浮夸和空洞, 真正体现了协奏曲体裁在审美上的精华内涵:(在与乐队的)竞争中彰显(独奏乐器的)卓越,同时又勇于负责、免于浮夸(炫技要关切主题)。
五、借题发挥、自由写意:标题性构思的实现方式
这首协奏曲题为《春秋》,根据作曲家的自述,创作本曲是“想要借‘春秋’这一题材和儒家音乐上的韵意来发挥我对数千年中华悠久文明成就的崇敬、热爱和追溯之情”[4]。总的来说,这是一部“写意”性的标题音乐,它没有像《花木兰》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叙述一个连贯的情节,也没有像《春江花月夜》那样勾勒一幅诗情画意的景象,而是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古朴典雅的历史氛围(特别是对古风吟诵调的运用),表现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史诗气度(富有气势的开场,辉煌壮丽的结束,中间则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戏剧场面),回唤了一种厚重深沉的文化传统(鼓声、钟声、戏曲元素、古琴音色),进而折射了一种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对古琴曲《梅花三弄》音调的影射,是想借梅花的“凌寒傲放”之姿来象征出文人士大夫坚韧脱俗的品格)。
总之,在这首协奏曲中,音响对比、主体互应、炫技性原则体现得都很充分,对“竞奏”手法的大篇幅运用,使得以上三个方面均增色甚多。中国和西方的许多协奏曲作品,往往都更注重探索独奏和乐队“协作”与“对比”,而对于二者的“竞争”与“对抗”方式则探索得不够,甚至许多名家的协作曲(比如肖邦的两首钢琴协奏曲)也会因此而逊色。鉴此,可以说,本曲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是非常可贵的。但与此同时,奏鸣曲式原则体现得较为薄弱。奏鸣曲式原则在民族化的过程中偏离规则较多,虽然照顾了主、副部素材之间的对比,也有对呈示部素材的发展,但素材“之间”的交往却不够充分(它们更像是“各自”发展),此外,乐思的再现过于模糊,总结得不够有力,其“升化性”不是借助于对乐思的重组而是借助于主体之间的密切交往与独奏乐器的通篇炫技来实现的。
至于作品的标题性构思,由于不是协奏曲体裁的必备要素,因此也不是评价协奏曲价值的必须参照。就本曲而言,作曲家是以抽象的“写意”方式来诠释“春秋”这一预设性标题的,主题素材具有特指性,能够有效“切题”,旋法上也破费匠心,不失古韵。《梅花三弄》音调所能影射的人文寓意,令人遐想。作为文人士大夫意气风骨的象征,许多古琴音乐都能令人联想到“坚忍不拔、孤傲脱俗”的品格,作曲家不从春秋古琴曲中取材,而是诉诸于晚近得多的晋代和明代。故此,笔者认为这首协奏曲作为纯音乐的价值要高于它作为标题音乐的价值。
注释:
[1] 李吉提:《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唐建平的琵琶协奏曲〈春秋〉析评》,《人民音乐》2014年第3期。
[2] 白耘歌:《琵琶协奏曲〈花木兰〉的音乐分析》,《北方音乐》2018年第8期。
[3] 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谈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人民音乐》1977年第4期。
[4] 唐建平:《琵琶协奏曲〈春秋〉创作札记》,《人民音乐》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