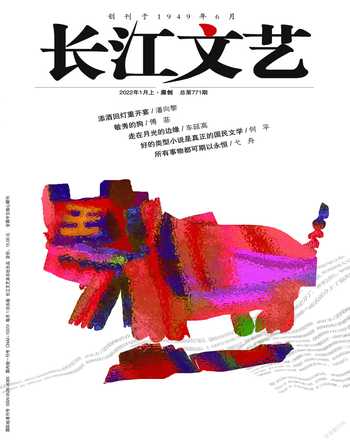纸上的灯塔
张双
江西历来是文学生长的一方沃土,山川溪湖氤氲而生的宋诗美学和书院文化滋养了诸多文人墨客,生于上饶的作家傅菲无疑是这一文脉十分突出的“继承者”,他的作品延续了“江西诗派”真诚及物的现实主义品格和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况味。近年来,傅菲孜孜不倦地开垦耕耘着自己的散文园地,“晨兴而至,戴月而归”,扎实而丰盈的作品产出让散文园地呈现出愈发蓬勃葳蕤的文学景观。且不难发现,这片园地大都以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郑坊盆地为坐标系,绕北河与枫林村点状式镶嵌其中,构成人物和故事生长的半径。本期开设的新专栏“灵兽录”中的散文作品《敏秀的狗》依然是郑坊故事的分支,亦是傅菲继《元灯》《盆地的深度》《斯似兰馨》之后与《长江文艺》的缘分再续,且这些作品都已被收录进他即将出版的新散文集《元灯如歌》中,穿越时空的相遇与沉淀,或许会使它们生发出更为丰赡而奇妙的意味。
新专栏“灵兽录”顾名思义是一组与灵性动物相关的作品,傅菲将视线聚焦于与人类亲密接触、心灵相通的诸如狗、马、猴、鹿、熊、牛、狐狸等不同科目的哺乳动物,书写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动人故事。《敏秀的狗》是新专栏“灵兽录”的开篇之作,心性善良、与世无争的柿子湾村民敏秀在一天早上刷牙时被一支飞来的自制冷箭射中脑门意外身亡,而这场意外的唯一目击者是一条敏秀养了多年、亲密无间的黄狗。线索荡然无存,凶手销声匿迹,破案似乎遥不可及。而狗与生俱来的忠诚、敏感和执着弥补了无法言语的不足,用自己的智慧和方式探寻真相的蛛丝马迹,这也解释了文章开篇的疑问:“敏秀的狗在路口蹲了好几年,它眼巴巴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在望什么?”在傅菲的笔下,与敏秀朝夕相处的狗似乎已然超越了动物的身份,而拥有着“类人化”甚至“超人化”的品格和灵性:狗从小被敏秀用鲜奶喂大,是一个十分黏人的“小跟班”,会自己抓山鸡送给敏秀作为回赠,除了敏秀及家人的喂食,未经允许其他人投喂一概不吃,即使敏秀死后也不例外。狗与敏秀情感的牵连似乎已经深入骨髓而成为一种本能,每年敏秀的忌日狗都会准时出现在坟地守灵,无法解释的灵性还体现在敏秀丈夫德钟因煤气中毒死去的日子,狗对着德钟住处的方向破了嗓子似的叫了三天,似乎预感到意外的来临。直到与敏秀同样淳朴善良的收破烂的老森出现,狗才暂时结束了孤独的流浪生活,并将对敏秀的情感延伸在了老森身上,相互治愈,彼此慰藉,一颗心陪伴着另一颗心,绵长而深情。而八年后当狗凭借敏锐的嗅觉和恒久的记忆捕捉到熟悉而痛恨的凶手的气味时,傅菲巧妙地用戏剧化的处理让狗完成了复仇使命:当初因偏差射死敏秀的職业偷狗人在杀狗厂被吊死在他们团伙精心打造的杀狗杠杆装置的绳圈中。完成了使命的狗,与过去作了了结,和老森开始了新的生活,“敏秀的狗”也真正地成为了“老森的狗”。
这是关于敏秀的狗的故事,也可以说是我们本土化的“忠犬八公”的故事。除了“灵兽录”中的十二组动物叙述,对自然生灵的关注和书写一直是傅菲近年来散文创作尤为浓墨重彩的部分,并被赋予了“自然文学”的标签。一如他所秉怀的信条:“生灵颇具崇高的美学、尊贵的伦理学、和谐的社会学,是生命的道德律和启示录。我们与之共生、彼此救赎。”万物生而有灵,不被打扰的诗意栖居以及相互融合的平等共处都是我们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且一旦这些纯然而长情的灵兽与人的情感发生黏连,存在的意义就变得更加凝重而深远。因此,你可以在《红嘴山鸦之死》中看到一只叫“寡妇”的红嘴山鸦因为修鞋匠老鳏夫光春的救命之恩和收养之义而终身守护不离不弃。光春把“寡妇”当孩子般细心照看,“寡妇”将光春视为“鸟生”的唯一。直至光春临终死去,鸟站在床头和棺木上,‘呜呀呜呀呜呀’,叫声很破碎。”最终出现在光春坟头鸟的尸体,无言地昭示着红嘴山鸦以“决绝殉葬”的方式履行着超越时空、生死相依的誓言。《刀与猴》则是一个关于人与猴从杀戮到救赎最终“美美与共”的故事。以杀猴为忌的屠夫父亲为救身患“脱症”的望春,需取活猴身上的猴胎入药,不得已干起了杀猴的行当。从杀猴救命到卖猴骨牟利,偏离的动机幻化成无形的诅咒阴翳着整个家庭。“我”患上了一见杀生就发“羊痫风”的怪症,母亲因意外流产而终身不孕,父亲也一见杀生甚至荤腥便习惯性呕吐、不得安宁。最终父亲放下屠刀,在山谷间与猴为友,与鸟为伴,护养牛羊,吃素食细耕作,用毕生修为洗赎杀戮之罪,完成与动物的和解和灵魂的救赎。在傅菲的笔下,人世间的因果造化在动物身上同样适用:无论是对丑恶之人本能的睚眦必报,还是对温善之人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动物与人的福报与恩怨都会在某个时刻应验,并会像执念一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久弥深。
从2002年创作以来,傅菲始终将散文作为写作的唯一文本并陆续出版了20余部散文集。保持如此高密度高质量创作的源头活水便是温情敦厚的郑坊大地上的一切。他像一位匍匐前行的方士,双脚深陷土地,根须交错其中,身上沾满草屑与露水,沉浸式地感受并记录着这里的人、物、事。他的散文主题多样,题材纷繁,不重复别人,亦不重复自己。他衷情于写猴,于是有了《灵猴》《刀与猴》以及“灵兽录”中关于猴子的新作,但每一篇都有独特的角度和侧重,“每一个”都是独特的“这一个”。他写历史烟云中的家族命运和尘埃里的芸芸众生,他们是无数为革命事业奉献生命的志士,是传承赣剧的“大悲旦”,是善良厚道、替先祖赎罪的木雕匠人,是做土陶的手工艺人,是亡灵前跳傩舞的“墨离师傅”,他们对生活对命运绝不妥协,即使处于绝望之境,也仰头眺望星光,他们是如灯盏散落大地的“光明使者”(《木与刀》)。他写故乡的古老物件,“每一件故物,里面都住着一个故人。每一件故物,都是一个器皿,盛放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审视悲悯的目光关注乡村的振兴与发展(《故物永生》)。他写山川草木和花鸟鱼虫,汲取美国自然文学之父约翰·巴勒斯在生活和审美上给予的双重养分,在广袤而幽闭的乡野之间,静心观察物种的演化与生态多样性的嬗变,力图呈现盆地四季的野性之美(《风过溪野》《鸟的盟约》)。
这些散文的篇幅大多超过万字,且多用短句,句式错落,这便意味着对叙事容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傅菲从独特本真的个体经验出发,借助多变的视角和多重的线索,不断激活历史的纵深感、故事的鲜活感和物象的层次感,让笔下的文字如青花瓷器般结构朴素工巧、肌理细腻密实,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具备小说的质地,是当下散文创作别具一格的存在。他的散文创作不炫技、不虚浮,而是以情制胜,以诚动人,或隐忍克制,或酣畅淋漓,有治愈救赎的温情,有挺拔超然的风骨,有直抵心灵的力量,有理性睿智的哲思。他用自己对散文的理解和写作实践,不断接近并抵达温克尔曼式“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文学理想。尤其是在自然文学领域的耕耘,傅菲以“万物生动”的整体性视野自觉呼应着新时代关于“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国际公约,乐此不疲地践行着亨利·贝斯顿《遥远的房屋》中的呼吁“抚摸大地,热爱大地,敬重大地,敬仰她的平原、山谷、丘陵和海洋”,并在文本作出了深情的补充——“以及这之中的一切生灵”,在人与自然“和合共生”的双向奔赴中捕捉存在的意义, 为当下自然文学或生态文学的主题创作提供了一条颇具前瞻性和使命性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