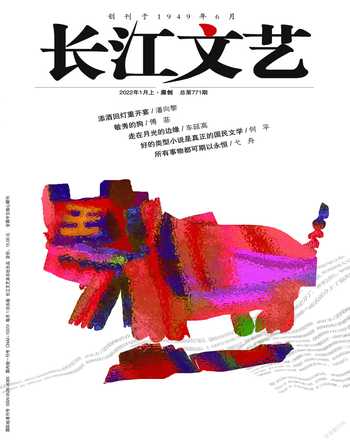滚石不生苔
别鸣

软剑一柄,捅入鼻腔,直插肺叶。石旗终于翻身,咳嗽喷涌,仰躺喘息,在宿醉中挣扎。空气中弥漫酒精气味,大概又摔碎几瓶烈酒,石旗以为瘫卧VOX酒吧,手掌乱摸一气,赤身紧裹被褥,想来已被抬回酒店客房。他歪头一看,身下却是牡丹花旧床单,循光线望去,水泥阳台上,父亲石代全正手握硕大绿喷壶,不断向两把木椅喷洒消毒。石旗心头一紧,昨晚酩酊大醉,意识混乱却方向笃定,戴口罩夜奔三百多公里,坐动车搭的士换摩的,真就回到了兰矿新村五栋一单元504室,阔别五年的老家。
初夏阳光透明,酒精如锐器,逼迫呼吸,阳台上两把桐油木椅闪烁金红,石旗恍惚看见妈妈坐椅上摇晃,哼唱催眠曲,自己口含乳头,拼命咀吸,呛奶,咳嗽,呕吐。木椅上一一摊开石旗所穿黑皮搂、牛仔裤、花衬衣、平角内裤,地上旧报纸上摆放皮夹、身份证、拨片、手链,还有黑皮靴,父亲用酒精均匀喷洒消毒。父亲双手叉腰,看了看床上,发现石旗已醒,转头朝楼下,扩胸伸腿,狭窄阳台里绕圈,嘴里连报步数。
阳台上江风正劲,父亲似乎早已风干,比石旗记忆里轮廓至少小了三圈,像瘦小的猿。父亲脸褐,双颊下凹,罩肥大灰西装,戴旧框眼镜,眼镜腿一黑一黄,头发油腻打卷,白了大半。石旗背回的芬达琴箱,斜靠阳台围栏,箱面布满酒精滴痕。父亲稍事锻炼后,还是忍不住放平琴箱,打开箱盖,举喷壶准备继续消毒。石旗不得不开口喊,停手停手,我的琴受不得潮。琴箱已开,父亲扭头望他,表情不解。石旗坐起身,箱里塞了大半瓶黑方酒,并不见他弹奏多年的淡蓝色芬达琴。父亲嘴角轻咧,鼻孔哼两声,抬起喷壶,酒精喷雾往箱中直洒。石旗盯着喷雾依稀折射七彩,反复回忆那把钟爱的电吉他。淡蓝琴体,特意请老琴师做旧,边缘描画60年代披头士乐队崇尚的佩斯利花纹,复古式黄铜琴桥,火焰枫木琴颈,五年前在什刹海百花深处,花三万八从吉他师傅巨巨手里购得。听巨巨讲古,这把琴是当年录制系列唱片《中国火》时,录音师从国外背过来,成就了国摇经典,意义非凡。
琴去哪了?石旗看见父亲喷罢酒精,端详黑方酒瓶上商标,轻轻摇头,咂嘴冷笑。他顿生悔意,还是不该回来。他想起昨晚演出后的酒局,所有人都喝兴奋,抱成一团,又笑又哭。石旗以为自己最清醒,他再三提议大家向上举杯,感谢当年兰矿兄弟魏涛,没有和他约定,自己不会坚持走下来;感谢那位著名相声艺术家的公子,如果没有那档火出圈的乐队选秀节目,他们的繁花乐队早就解散,卖琴的继续卖琴,办班的继续办班,送外卖的继续送外卖,当中介的继续当中介。繁花乐队首次完成十城巡演,虽然演出地点都在观众不足五六百人的LiveHouse,但终究算是赚到了第一桶金。演出前,阿梵举手机,给他看巡演收入,打头是二,共六位数。石旗一激动,破了自己定下的演出戒律,在乐队其他成员登台后,一口气灌了半瓶红酒,斜挎吉他冲上舞台,脚踹效果器,猛扫琴弦,乐声轰鸣,整场喧嚣。
石旗从枕上抬头,看见左右靠墙打小熟悉的红漆木家具,墙壁贴满他从兰矿幼儿园小一班到兰矿中学高三(三)班所获奖状,床头墙上悬挂九幅家庭相框,家里物件摆设和五年前没变化,一模一样。父亲喷罢酒精,撩开门帘,外屋洗手涮壶,电视新闻声响起。父亲发喊,别装睡了,懒什么懒,馒头稀饭在桌上。石旗有点蒙,恍惚从来没离开过,还活在小时候放寒假,趴枕頭上又赖一小会。他撑起头盯墙看,在相框里寻找妈妈。右上那张,是妈妈和父亲相识不久,在兰矿后山顶上,一棵老松下两人眺望远方,彩色据说是后来添上去,二十多岁的妈妈身穿蓝工装,两颊绯红,两根长辫子,正年轻。中间那张妈妈单人照,是石旗和妈妈一道搭中巴去县里照相馆所拍,妈妈尽力在微笑,可能因为照相灯刺眼,眼里看到闪烁之物,双眼月牙一样,头发一丝不苟,脑后挽了一个髻,照片上虽然看不到,但石旗记得那天出发前妈妈举木梳梳了很久。妈妈说,我想去照相馆拍张照,以后用得着的那种,怕万一来不及,到时候差张照片,就让你跌份了。左下是张两人合影,十八岁的石旗和魏涛,跳跃半空,飞翔定格,是妈妈端着魏涛他家那台相机,延时加连拍而成,记得妈妈按快门时很开心。
石旗听见父亲连连咂嘴,带拉长的丝音,他打小就熟悉到生理性厌恶的喝酒声响。石旗赤身跳下床,像过去一样猛擂衣柜门,外屋顿时安静,只剩电视里女播音员语速极快念叨。阳台上衣裤被酒精腌着,石旗开了衣柜门,柜里三格,还是五年前妈妈分类,整齐叠放的他的衣物。妈妈找矿上裁缝铺做的五条蓝布短裤,放在上格,他取过其中一条,套住双腿,拉到腰间,还没转身,蓝布就四分五裂,碎片落在腿脚间,发黄松紧带圈在肚脐。石旗擤了擤鼻子,从柜里找了旧牛仔裤、蓝格衬衣穿上,积尘扬起,淡淡樟脑味。他掀起门帘,父亲果然又在喝酒,左手端玻璃杯,右手持筷从碟子里夹油炸花生米,一颗颗往嘴里送,盯着电视看,并不睬他。石旗拖开木椅,铝锅里舀碗稀饭,小筲箕里拿白馒头。父亲朝电视机说,三更半夜醉醺醺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把新村邻居都吵闹了。石旗说,我想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这是我家。父亲说,三年前我回来,家里怎么没见你,孤魂野鬼一样,现在晓得是你家?石旗低头喝稀饭,后悔昨晚酒后冲动,奔波自找添堵,拿出手机订票,下午出发返程,不耽搁与乐队汇合。父亲放下酒杯,咂完嘴开始絮叨,二楼左边那家你冯叔叔,上个月心肌梗塞走了,就是你小时候在矿里摔破膝盖,抱你去卫生室缝针的那个财务科冯会计,新村解了封,情况好转了,大家松口气,他却走了。石旗发现父亲停不住嘴,如溢出来的酒缸,终于拧开缸底龙头,喷流止不住的话。父亲酒气四溅地叨咕,去年病毒厉害,别看新村搬来多年,过去五十年国营兰矿单位组织纪律性,还是很起作用,大家听号召听指挥,自觉封楼封门,六十岁以下的抽签出列,戴袖章搞志愿服务,挨家挨户帮忙送米买菜,全村就没感染一例,只走了三个年老多病的老伙计。
石旗只顾低头看票务,手机不断震动,点开繁花微信群,群里成员纷纷冒头,有问老大组织大家中午吃啥大菜,有问大旗你怎么不在房间。阿梵开了语音私聊,石旗离开饭桌,往阳台走。父亲视线紧跟他,嘴里像被木塞猛然堵住,一张一合,全是白沫,摸摸索索端酒杯,喝一大口,用劲咂嘴,丝音拉得老长。石旗眺望阳台下,大江像一条玻璃栈道,凝固而易碎,看不出流动痕迹。阿梵说,你昨晚上真回老家了?石旗说,今晚就回来,不耽误事,你安排大家先歇一天,就说我出去谈平台合作,明天我们就回Y省,继续磨乐队专辑,在网上推收费版本。阿梵说,有个事,等你,回来,再说吧。石旗说,有事说事,现在就说,莫吞吞吐吐。阿梵说,也可能没什么,晚上再说吧。阿梵又说,多说一句,你昨晚现场,最后不该砸琴。
江风呼啸,从五楼阳台望去,大江上有货船航行,岸左是江岸平原,初夏农田大片大片覆盖塑料膜,里面无数棉苗正在生长。十一年前大江截流,兰矿转产落空,矿工及家属分散搬迁,多地安置。包括石旗父母在内的兰矿机关两百多户,从峡江兰溪畔搬到这平原之地,当地棉纺厂打着横幅标语,欢迎大家入住务工。妈妈直到去世前,都对气候不习惯,天气一热她要不断给棉田打药,夏季最热时她要钻棉田摘棉桃,冬天平原没有大山遮蔽,风像狮吼一样日夜不息,她睡觉要穿毛线衣裤,盖三床棉被,家里离不得火炉火盆,过去在矿里拾拣不觉得,搬到这里才发现单买煤炭家用,都是一笔不小开销。
父亲听见石旗在阳台语音,忍耐不住,从屋里大声问,你这就要走?刚回家,住都不住一晚?搞什么名堂?石旗扭头看琴箱,它斜靠阳台转角,内腹空空荡荡,黑方酒瓶叠在底部,活像一个天生酒鬼。他回忆那把淡蓝琴在怀里的最后时光,长达五分多钟的噪音墙,从他剧烈拨动的琴弦,经过效果器,通过巨大音响,在数百观众脑子里炸开了一朵又一朵蓝色蘑菇云,厚重的层次感铺天盖地,抵达最密集最劲爆时刻,仿佛被一刀斩开,石旗静止一切动作,想让世界万籁俱寂,台下观众却依然沉浸其中,他们反复高唱繁花乐队歌词:大醉方醒的石先生,站在九十九层楼顶,举起望远镜,可怕的不是死亡,是你从没活过,可怕的是你活着,却从不曾活过……石旗感到释放后的空荡荡,在他头顶正前方,声音不断念叨,时候到了,时候到了,他紧握琴颈,高举琴体,将它砸向舞台前沿,琴身顿时断裂,蓝花飞溅,啸叫回荡。
玻璃碎裂声响,穿透门帘,石旗有些恼火,父亲改不掉多年醉酒习性,大概又在乱摔东西。他回到里屋,撩开门帘,果然家里红花玻璃杯又少了一个,被父亲摔碎在墙角,苞谷酒泼洒一地。让他惊讶的是,父亲像石旗小时候一样在抽泣,眼泪鼻涕流了满脸。
自制铁板门,厚达八公分,门框使用截断的废旧轨道,门板上方用食指粗铁条焊出带锁拉门菱形小窗。铁门一旦上锁,找不到钥匙,就算天王老子想尽办法也轰不开。五年前,为提防兰矿老同事们上门扯皮,石旗和魏涛找镇上农机厂相熟青工,给车间主任塞了两条红塔山,在车间里倒腾了三天,给肖魏两家做了两扇坚固大门,至少让两位妈妈少受些惊吓,能躲避度日。
现在,铁门被反锁,石旗只能干瞪眼,他肩背琴箱,衣裤蔫巴干,酒精味浓郁,父亲坐在桌前,自顾自看电视新闻。石旗说,钥匙拿来,我还有事,票都订了,必须走。父亲说,我不耽搁时间,我就讲两点,第一,去年新村上下一心,暂时封锁单元门之后,我就忘了家门钥匙放哪,后来解封也一直没出门,反锁了门蛮好,在家待起,既清静,又安全;第二,按照相关规定,你从外边回来,先要居家隔离。石旗说,你难道从去年就没出过门?钥匙一直忘记放哪,我昨晚怎么进门的?赶紧把钥匙拿出来。我出来巡演,两个多月,都是安全地方,健康码一直常绿,把门打开。
僵持片刻,父亲说到了睡午觉钟点,卧室门一关,把石旗晾在铁门前。石旗朝铁门踹一脚,坐木椅上揉脚趾。他翻箱倒柜找,没找到门钥匙。看屋里物件摆设,和自己五年前离开时几乎没有变化,比如码在双卡录音机旁的五十三盒磁带,书架上七十六本《音像世界》《音乐天堂》杂志,斜掛墙上那台积满尘网的暗绿色蝴蝶琴,还有一把破旧木吉他。除了厨房案板角落多了几件食品:塑料袋里五筒纸封面条,几颗蔫白菜,两瓶辣椒酱,长花的酱油瓶,大塑料壶里还剩差不多三分之一苞谷酒。打小记忆里,父亲生活自理能力弱,从不进厨房的大男主。石旗念初三那年春节,妈妈非要回江城看外婆,父亲却硬留石旗在兰矿过年。前三天被父亲带着到处喝酒吃肉,到县里镇上轮流拜年,县里镇上又轮流回拜,从餐馆到食堂,从食堂到餐馆,父亲酒桌上山呼海啸,县长局长镇长一通勾肩搭背,一回家就吐得昏天黑地,石旗摆弄家里脸盆脚盆水桶,紧跟父亲不停移动,从沙发到卫生间到床上,接纳他喷涌呕吐的腌臜物,还要不断跳跃避让父亲随手摔碎的玻璃器物。等到腊月二十九之后,地方单位拜年完毕,街上餐馆菜场歇业,父亲酒醒之后,每日三餐在家煮面、炒鸡蛋饭、炖隔夜饭,吃完他就躺床上睡觉,过年气氛荡然无存,石旗熬到正月初五,一直等到妈妈提前赶回。
自己离家这几年,不知道父亲怎样孤独度日,在外混吃混喝完全断了,靠他自己在家煮面炒饭,可以想见生活一塌糊涂。去年上半年,石旗想方设法给父亲寄了米面、酒精和口罩,大瓶消毒酒精快见底,两大包口罩不见踪影。父亲说他去年就再没出门,口罩怎么会用光?石旗看了看时间,现在就算打开铁门,也无法赶上今天最后一趟动车,只能多住一晚,改签明天最早车次。他拿笤帚扫墙角,收拾干净碎玻璃杯,再推父亲卧室门,里面上了插销,他说,我改签了车票,出来开了铁门,晚上出去打牙祭。卧室门还没开,大铁门被擂得山响。一口高亢女声喊,石总,听你在里面踢门,没事吧你,身体不舒服就赶紧开门,要买什么就直说,我从小窗递进来,别瞎折腾。石旗一听是打小的邻居李姨,年轻时兰矿职工文工团报幕员的声腔,他开口回应,没事,没事,李姨。嘴被冲出来的父亲紧捂,父亲将他推进厨房,迈过去拔开菱形小窗,连说,没事没事,你不要高声大嗓,我好得很!李姨哦哦几声,放低音量又问,我刚才是不是听见小旗这孩子声音,他回来了?我家魏涛呢?父亲答,没有没有,这家就我一个人,三年多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姨说,石总你可别打诳骗我,我耳朵好得很。父亲说,快回吧。石旗蹑手蹑脚踱步,眼见父亲抬手关上菱形小窗,门外传来李姨啜泣声,父亲对着铁门默立,好一会听见李姨下楼脚步声,父亲转身,坐旧沙发上,双手来回搓,一声不吭。石旗问,涛子走了快半年,李姨她不知道?父亲手往旧西服口袋伸,一紧张就习惯摸烟,摸了一会没摸着,又抬手薅头发,将打卷白头用力往后捋。石旗心里发慌,赶紧往里屋走。他目光依次扫过墙上绿蝴蝶琴、旧木吉他、双卡录音机和床头左下那张自己和魏涛十八岁合影,心里自责,不该贸然回来。石旗盯着阳台外,已是暮色四合,江涛寂寥,岸左平原上蝙蝠成群结队,棉田上低翔,划出怪异曲线。
妈妈在时,每天晚饭后,会和李姨走圈散步,这个习惯大概从她们年轻开始,从矿区走到新村,走了很多年。石旗从蹒跚学步到妈妈离世前,无数次跟在她们身后走。妈妈和李姨是同一批进兰矿的技术员,当时支援三线建设,妈妈和李姨从江城奔赴而来,抱定安家扎根的信念。石旗如今常回忆,矿里家属喜欢串门,爱飞流短长,妈妈和李姨除了两家走动,就是关起家门成一统,吃穿和兰矿另外三千多家也没什么不同,家里却总有生活在别处的氛围。想不通的是,后来无数拨返城机会,两位妈妈还是都选择留下,可是日常她们又让石旗和魏涛总对外边世界保持想象,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木吉他,牛仔裤,录音机,流行乐,诸如此类。不过,可能正是这种距离感,在兰矿卓然不群,让两位父亲从中受益,一路升迁,直到末任董事长、总经理的位置。
年轻时,妈妈和李姨是兰矿职工文工团的两朵花,妈妈演奏蝴蝶琴,李姨是歌手兼报幕员。那台积满尘网的暗绿色蝴蝶琴和破木吉他,是妈妈和李姨的爱物,那七十六本音乐杂志,妈妈也是一本一本都翻看过,她常对石旗念叨一句话,不知道从哪里读到的谚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打石旗小时候,妈妈就总对他说,要想不生苔生霉,长大走得越远越好。李姨对魏涛相对溺爱,这也导致魏涛和石旗不太一样,比如魏涛比较享受他父亲职位的荫泽,常常自诩为兰矿拐子(湘鄂方言,老大、狠人),喜欢惹事出头,心眼多,下手狠,从周边村镇到县城,四处横着走,挑事群殴。兰矿入驻兰溪畔挖矿建厂,已近五十年,矿区蔓延十余公里,近万名职工及家属自成生活体系,大矿自豪感延续几代人。热血青工一茬又一茬,因为各种理由干了无数场架,小到一个眼神、一件新夹克,大到露天电影争位置,往往成为兰矿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石旗趴在牡丹花旧床单上,瞪着那张十八岁的合影。外屋如长夜寂静,父亲呼吸声几不可闻,父亲在家里从来如此隐身。以前常年在外边,不是喝酒就是谈事,等回到家不是酊酩大醉,就是蒙头大睡。后来父亲和魏涛父亲一同出事,妈妈和李姨躲家里抱头痛哭,等石旗和魏涛回来,两个妈妈又装没事人,瞒了他们三个月之久。直到石旗十八岁生日,他和魏涛拍下这张合影,妈妈还笑着按下快门,第二天他和魏涛取下胶卷,去镇上冲洗照片,被十几个以前兰矿子弟堵在街角,逼他们掏钱抵账,骂他们老爹害苦大家。他们才知道父亲石代全和魏达浚因为涉嫌渎职贪腐,早已从公司办公室被带走。魏涛自小做惯兰矿子弟的拐子,哪受得起过去小弟骑在头上,拽着石旗一通乱打乱冲,反被逼进了街边网吧,子弟们冲进来,有人关了电源,拉黑了灯,双方拆了座椅混战,石旗落单被子弟们架到江边。魏涛亮出软剑救他时,他被五个子弟摁牢江水里,脸颊在滩底卵石上摩擦,江水灌涌口鼻耳目,胸口像被刀片反復刮割,肺就快爆掉。等那五个子弟松手,他抬头猛咳,好一会儿才看清,魏涛手持软剑砍伤两个子弟,对方五人像快进的录像带,一步一顿上岸飞遁。石旗喉咙发干,气粗如牛,趴在石滩上,捧几口江水入口,他看见江岸漂浮成堆白沫,好像成千上万条鱼在喘息。
石旗回家后,向妈妈问究竟,妈妈只顾手里忙活,不理睬他。下午出门找魏涛,才知道李姨已说实情,十一年前确定大江截流,兰矿获得过亿转产迁建经费,两位父亲喝酒出差频率更勤,在兰溪上游建水泥厂、化工厂,投产一年多,卫星发现大江中游出现一条乳白色支流,环保部门勒令其停工,更严令措施出台,水泥厂化工厂划入拆除范围,近万矿工及家属告别兰溪,分散搬迁,多地安置。李姨说,这两个酒麻木早晚要出事。魏涛拽着石旗赶去县城,想打听父亲消息,两人寻路无门,在县城网吧蹲坐一夜。这天晚上,被砍伤两名子弟的家人,带领大群兰矿老职工堵了石魏两家门。两位妈妈好说歹说,卖尽过去人情脸面,答应先赔付五千元医疗费,给这两个看着长大的子弟治伤。第二天早上,石旗和魏涛从县城回来,眼看情势不对,赶紧央求镇上青工,赶制两扇厚铁门。老职工们三天两头敲门,妈妈和李姨不由自主疏远。妈妈不再看书弹琴,渐渐愈加沉默,常常陷入思维停滞状态。石旗从那时开始,埋头苦练吉他,每天长达八小时,刻板封闭,沉溺其中。新村开始流言纷起,说是石代全交出了私藏账本,魏达浚惊恐不安,重病缠身。不久,魏家父亲病逝消息传来,楼下李姨撕心裂肺地哀哭,妈妈无法承受,晨雾里走入江中,从此失踪。
天黑定下来,楼下空地棚屋里,几个兰矿老人围在一起,唱卡拉OK。石旗隐约听见李姨熟悉的女中音,在唱一首老歌: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奔驰车窗的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楂树两旁……石旗胸口像堵了隔夜食,烧灼感渐渐浓烈,他迅速关上阳台门,习惯性掏出手机,手指飞快划动,屏幕上图文翻晃,繁花微信群里,乐队成员倒是安静。阿梵单独留了五遍言,问他晚上何时到。最后一遍留言说,昨晚演出现场,出了点事,不知道能不能摆平,你回来好商量。石旗想起此前阿梵吞吞吐吐,攥起手机连拨她号码,电话总是忙音。约莫半小时后,阿梵终于回信息,说石旗要是到了高铁站,就直接来市一医院。石旗更是惴惴不安,赶紧短信问原因。又过了十来分钟,阿梵回信息说,昨晚演出最后,石旗高举电吉他,砸向舞台前沿,琴身断裂飞溅,崩伤了台下一名观众,现在正在医院,被伤者家属围住,有说就划伤了脸颊,有说崩伤了眼睛,正在边安抚边道歉,商量赔偿金额。石旗从琴箱里摸出那瓶黑方,扭开瓶盖,对嘴猛灌两口,从喉咙到腹部像被剖开,热哄哄,透风漏气。石旗思来想去,想到阿梵加入团队不到三个月,他忽然想不起阿梵容貌,像江面夜雾升腾,巨大的水汽颗粒,让他堕入混沌。
三个月前,在羊城殡仪馆为魏涛办理寄存手续时,除了从机场匆匆赶来的自己,就剩阿梵一个人打把透明伞站雨里等,她戴了副黑框眼镜,说她不敢进馆,一直在等人来办理。石旗第一眼见她,感觉有些面熟,像兰溪畔芦苇丛里一只白鹳,孤零零立着,不定什么时候扑腾扑腾飞一圈。进城路上,石旗才问明白,阿梵曾经也是兰矿子弟,很小出来南方打工,和魏涛偶然相遇,魏涛将她从洗浴城捞出来,后来同居在一起。阿梵简单说了情况,魏涛是从十二楼和十三楼之间楼道窗户跳下去的,大概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左右,因为那天下午她没直播,出去转了转,在楼下超市买了瓶装水、散装饺子和卤藕,听见单元楼下一群爹爹婆婆嚷嚷,她还没走近,刚看清就瘫倒,饺子卤藕散一地,被警车救护车辗成乱泥。
阿梵说,他们住处附近有家湘菜馆,魏涛以前说有石旗家里饭菜味道,要不一道晚餐,算是送别魏涛。他们租住的小区较偏,出租车穿过主城,路上望见珠江,雨幕中船舶浮动,江水拍岸。石旗想着魏涛心思细,从窗口望出去,远处有支流水道,果然隐约有老家兰溪的模样。听阿梵说,他们在同一小区租了两处房,她住六栋十一楼,魏涛住七栋十二楼。阿梵自我介绍是音乐主播,魏涛总刷礼物,算是刷成了网红。石旗没接话,他是接到警方通知来办理后事,说是魏涛生前有留言,万一出了意外,就电话联系石旗。下车时,阿梵说魏涛还欠她二十万块,问石旗能不能转账给她。石旗说自己网银钱不够,先转她两万。阿梵盯着手机转账成功,两条长腿蹦跶进六栋门洞。南方雨水来去快,此时阳光闪烁,他跟在阿梵身后进了六栋十一楼房间,厅里摆着古筝、葫芦丝,一台暗黄蝴蝶琴,直播架,补光灯,炫色转椅。石旗问,你会弹蝴蝶琴?阿梵说,魏涛买来让学,网上有人看,有流量赚的。石旗摇头揉眼,想着五年前魏涛要是能和自己一道走,是不是就能活着。阿梵说,他总说起你,说他打小和你一起听歌,还想过组乐队,结果你撂下他出去闯荡了,成了一吉他手,有了一乐队,据说还想搞巡演,他还信誓旦旦说,你首轮巡演一定会带上他。
石旗在心里辩解,当初,没有撂下他,是上船过安检,他不声不响腰里别着那柄软剑。妈妈失踪后,石旗决意远行。魏涛倒是不在乎父辈纠葛,非要跟着石旗出去闯天下。软剑长九十八厘米,宽二点七厘米,剑锋双开刃,是还在兰矿时他们找二号井莫矿长,谋来一截上好弹簧钢,软磨硬缠车间高级锻工熊大红敲打出来。砍伤兰矿子弟后,被列为凶器,派出所多次前来搜要,都被李姨撒泼浪骂,搪塞拖延。结果在码头被查出,魏涛不肯交,两边一拉扯,时间耽搁了,李姨哭着赶过来,抱着魏涛一把鼻涕一把泪。船就要开了,石旗只能抢步登船,扶着船舷,江水越隔越宽,他们留在趸船上,越来越小。那柄软剑,救过石旗的命,他眼睁睁看着被魏涛扔进江里。后来,兰矿新村主业种棉花,子弟大多像被风吹散的枯草,流散四方,各谋生路。魏涛还是离开李姨,到北京找过石旗。那时石旗刚从迷笛音乐学校毕业,在树村租住土坯房,四个人挤七平方米,他每天在屋后皂角树下,弹琴八个小时,只吃得起一包快餐面。魏涛待了三天,说石旗才是干乐队的料,他自己熬不住,南下挣大钱去,等待石旗巡演时。
在阿梵推荐的那家菜馆,石旗印象最深的是剁椒鱼头、醪糟圆子,确实让他想起妈妈做饭的味道,从小两家邻居串门吃饭,口味都一样。阿梵连点了三扎鲜酿啤酒,喝得摇头晃脑。阿梵问,你知道魏涛为什么跳下去?石旗说,你多吃菜,少喝点。阿梵嘿嘿两声说,他们团伙把電梯给关了,一股从楼上冲下来,一股从楼下往上搜,他给堵在中间,翻出楼道窗户,直接下去了。石旗说,不说这些,人已经走了。阿梵说,知道为什么要堵他?石旗说,来之前接警方通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在幕后操控,他负责单线转账,他手里过钱像自来水,实在看不下去,截流款项做假账,被团伙发现。阿梵说,他那阵可真有钱,我直播时,帮我刷穿云箭宇宙之心,钞票成千上万,满屏礼炮焰火。石旗说,警方后来怎么处理?对你没影响?阿梵说,他留下两本账本,他总说网络不安全,都要白纸黑字,都是人名和数字,我照他以前交待,一旦出事就交警方,洗脱我干系。阿梵又说,积蓄没有了,收入没着落,房东催搬家,影响还是有。石旗问她以后作何打算?阿梵问,刚才你喝酒时说,后天你们乐队就开始首轮巡演?十个城市?石旗点头称是。阿梵说,魏涛走了,我帮他见证,可以跟你们乐队走一圈,打杂记账都行。石旗有些犹豫,阿梵说,魏涛常念叨,你们两家亏欠兰矿子弟,凡事看过去,就知怎么办。
石旗左手攥酒瓶,右手摁手机,反复拨打阿梵号码。夜色如墨,江面上水汽蒸腾,渐渐白茫茫一片,浓雾完全覆盖了大江,像舞台上的干冰。他从阿梵的红框眼镜,努力回想她的模样。雾中的鸟儿,湿漉漉,沉甸甸,晃动着划出一道弧线,不知归处。晚上十点多,阿梵终于接了手机,声音疲惫说,事情已经了结,你可以继续躲在老家,当缩头乌龟。石旗压住心头火,问她怎么了结。阿梵说,见到伤者了,真实情况是吉他碎片崩进对方唇齿,一颗门牙缺了大半,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谈定赔偿,转账了事。石旗追问,到底多少钱解决问题?阿梵说,除了巡演收入,哪还有别的钱。石旗感觉被整个酒瓶塞进咽喉,一时哽噎。十城辛苦巡演,收入二十来万,乐队贝斯张凡、鼓小司是当年迷笛学校一起熬出来的同门,键盘手老潘是自己费尽心思挖来的钢琴私教,他们都不比自己一人吃饱全家管够,搞音乐玩乐队也要养家糊口,对巡演收入,都有所指望。石旗天灵盖被猛擂,腌臜气从腹底直冲,撞碎酒瓶,喷腔而出。
父亲连连咳嗽,好像来自另外时空。石旗从朦胧中惊醒,黑方酒瓶在阳台碎裂一地,手机扔在他身旁牡丹花旧床单上,不断传出对方挂断的嘟嘟声。已是半夜,石旗感觉喉咙干哑,在梦里他被巨石碾压过,外屋传来嘶嘶声,一股新鲜酒精气味弥散,他缓慢起身走出,父亲正手持喷壶,对墙角消毒。石旗屏住呼吸,伸长脖颈望去,被置于酒精喷嘴下的,是一串绿锈斑斑的钥匙。父亲佝偻着背,站起身说,听你电话里吵了大半个小时,把自己灌醉了,不着急儿子,钥匙我找出来了,有些锈,消消毒,你开门快走,办事要紧。石旗眼前湿漉漉,进厨房猛灌凉白开,父亲过来拿笤帚,清扫阳台碎酒瓶。石旗问父亲,从去年就没出门?那寄回来两包口罩怎么光了?父亲低头将垃圾袋系紧,从铁门菱形小窗塞出去,说两包口罩递出去给李姨,让她和志愿老伙计们用,我回来后,很少出门,过去对不起兰矿,现在个人待着,好过些。
厨房窄窗外,新村三栋楼在平原上如三座碑,间或有落单蝙蝠穿行。石旗低头看手机,繁花微信群里寂静无声,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他试探着单独联系三位乐手,夜深暂时没有回应,阿梵头像已然变灰。石旗隐约听见外屋音乐声,仔细一听,正唱:大醉方醒的石先生,站在九十九层楼顶,举起望远镜,可怕的不是死亡,是你从没活过,可怕的是你活着,却从不曾活过……石旗循声走去,见父亲缩坐木椅上,用旧手机放乐队的歌。父亲问,你说歌里面,你唱的这个石先生,是谁。
责任编辑 丁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