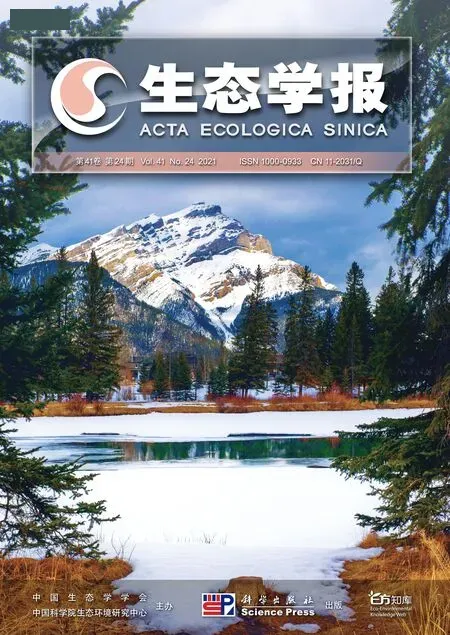广州市典型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特征
杜建会,方 政,林志斌
1 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2 广东省城市化与地理环境空间模拟重点实验室,广州 510275 3 广州海珠国家湿地科研宣传教育中心,广州 510305
城市化作为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最强烈的改造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城市地表环境的结构与功能[1-2],城市化过程中不透水面积急剧增加,显著改变了城市的自然水循环过程[3-4]。此外,随着气候变化,极端降雨的强度和频次均呈现出增加趋势,进而加剧了城市内涝灾害,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5-6]。绿地作为城市中心最重要的可透水层,其通过调蓄雨水、削减洪峰和雨污净化,有效推动了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在减缓城市洪涝灾害等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7-9]。因此,快速的土壤入渗就成为城市绿地建设的关键[10]。近三十年来,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对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性能提出了相关要求,确保新建和改建的区域地表径流量实现“零增长”。并通过建造雨水花园和下凹型绿地等,进一步提升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和蓄水性能,在减缓城市雨洪灾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1]。我国国务院办公厅也于2015年出台了《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通过海绵城市建设,确保70%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减少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城市绿地作为海绵城市系统的重要载体,其面积呈逐年增长趋势[12]。但已有的研究表明,绿地并未起到有效缓解城市内涝的作用[13-14]。许多学者通过室内和野外试验,对城市不同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进行了测定,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多个入渗模型对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过程进行拟合。结果发现,城市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相对较小,但不同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来源复杂,且植被类型多样,其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空间差异较大[15- 18]。首先,城市绿地土壤多来自于杂填土,无明显土壤结构,土壤含砂量普遍较低,且因其优先考虑绿地的旅游休闲功能,有机质归还量相对较低,土壤结构改善有限[17, 19]。其次,城市绿地作为市民重要的休憩地,一般表现为植被覆盖度越低,人为踩踏越多,土壤渗透性越差[19- 21]。此外,植被类型不同,土壤入渗速率也有所差异,乔灌草绿地的入渗性能好于乔草和灌草[22]。基于多个入渗模型的拟合表明,其均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过程,以Kostiakov模型或Horton模型最佳[16,21- 24]。近些年来,为了增加雨水蓄积及地表入渗,许多城市开展下凹式绿地建设[15],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蓄渗减洪的效果,也能对雨水及径流污染物起到削减作用,但随着蓄水次数的增多,其土壤容重增加,总孔隙度减小,绿地的入渗性能逐渐退化[25]。因此,如何维持绿地高效且可持续的水分下渗,就成为缓解城市内涝灾害的关键。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透水面积在广州市主城区不断增加,洪涝灾害也随之加剧。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简称海珠湿地)作为广州市主城区的两大生态屏障之一,被称为广州市的“南肾”,其良好的土壤水分入渗性能对于缓解广州市的洪涝灾害就显得尤为重要。海珠湿地于2012年建成开园,湿地一期经人工栽种园艺观赏植被,形成以乔草和灌草为主的绿地。但不同类型绿地的人流量、园林植物的根系分布和有机质归还能力等均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各功能区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空间变异较大,目前尚不清楚海珠湿地的入渗性能如何,无法为现有绿地管理及后续绿地的建设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对海珠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定量化研究,就成为准确评估其雨洪调蓄能力的关键。本文采用双环入渗仪,选择海珠湿地公园一期典型乔草和灌草绿地,对其土壤水分的入渗过程进行野外试验观测,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准确评估海珠湿地的雨洪调蓄能力,并为我国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提供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海珠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海珠区的东南部,包括万亩果园和海珠湖,是广州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湿地,总面积达1100 hm2。海珠湿地的前身是广州市万亩果园及与之相交的40条河涌,目前已完成三期建设。其中湿地一期位于石榴岗河北岸,属园内建成时间最早、园艺观赏植被景观最为集中的区域。考虑到城市绿地土壤的异质性较大,因此结合园区规划图,并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选择湿地一期的玉龙桥南岸以及花溪两处地势平坦,连续广泛,群系相似的新建人工绿地开展土壤水分入渗试验。两个样地的主要植物种具体如下:(1)玉龙桥样地(23°04′30″N,113°19′51″E),建群种为羊蹄甲(Bauhiniapurpurea),灌木层优势种为灰莉(Fagraeaceilanica),草本主要为结缕草(Zoysiajaponica)、蓝花草 (Ruelliasimplex)。(2)花溪样地(23°04′39″N,113°20′10″E),建群种为羊蹄甲(Bauhiniapurpurea),灌木层优势种为琴叶珊瑚(Jatrophaintegerrima),草本主要为结缕草(Zoysiajaponica)。
1.2 样品采集与测定
2018年11月11日—25日,在两处新建人工绿地选择乔草和灌草典型分布区作为样地。在土壤水分入渗试验开展之前,首先沿树干基部按120°间隔分三个不同方向,分别设置1 m×1 m的样方各1个,并对样方内的凋落物进行采集,共计12个。试验结束后,在入渗区域附近开挖土壤剖面,以10 cm为间隔,用环刀法逐层采集0—40 cm的原状土,并以土钻法采集对应层次的根系样品,每层各设置3个平行重复。所有样品带回实验室后,土壤样品使用激光粒度分析仪(Mastersize 2000,马尔文公司,英国)测定其粒径,并依据卡庆斯基土壤质地标准将绿地土壤划分为重壤土;参照《森林土壤分析方法》[26]测定土壤容重、毛管持水量和最大持水量,并依据相关公式计算得到绿地土壤的总孔隙度、毛管孔隙度和非毛管孔隙度等(表1)。凋落物样品采用手工清除其表面的土粒和混入的杂物,根系样品采用水洗法清洗干净,均放入烘箱中在70℃下烘干至恒重,并称取其干质量。

表1 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物理性质
1.3 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测定
在两处绿地各选择乔草和灌草样地1块,采用双环入渗仪(QT-IN12-W,渠道科学仪器有限公司,中国)对其土壤水分的入渗特征进行测定。该仪器内环直径30 cm、外环直径60 cm,可最大程度减少城市绿地土壤空间异质性的影响。试验前48 h内无降水或人工灌溉出现,其入渗过程受土壤前期水分影响不大。在尽量减少表土扰动的情况下,将待测样地的草本植物修剪至近似地表平整。双环插入土壤10 cm,使用10 L的马氏管向内环供水,人工加水至外环的泡沫板上,以防止水流冲刷土壤表层产生结皮。试验开始后水头稳定地控制在8 cm,记录马氏管每500 mL刻度下降的时间,至70 min后停止试验。入渗速率转化为水温为10 ℃下的土壤入渗速率。
土壤水分入渗参数的计算公式为:
(1)
式中,IT为一定温度下的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mm);Q为试验开始后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cm3);10为cm与mm间的转化系数;S2为双环内环的横截面积(cm2);T为某时段的平均水温(℃)。
(2)
式中,VT为一定温度下t时刻的土壤垂直入渗速率(mm/min);Qt为t时刻的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cm3);Qt-1为t-1时刻马氏管的累积供水量(cm3);S2为内环面积(cm3);10为cm与mm间的转化系数;Δt为观测间隔时间差(min);T为某时段的平均水温(℃)。
1.4 绿地土壤入渗过程的拟合
参照方政等[9]的研究结果,分别选用物理意义明确的Philip模型、半经验的Horton模型和经验性的Kostiakov模型对野外入渗量的实测数据进行拟合。相关数据分析在SPSS 13.0进行,作图采用Origin 9.0进行。
Philip模型:
(3)
式中,I(t)为累积入渗量(mm);S为吸渗率(mm/min1/2);A是与稳定入渗率(mm/min)有关的参数;t为时间(min)。
Horton模型:
I(t)=ift+(ii-if)(1-e-ct)/c
(4)
式中,ii为初始入渗率(mm/min);if为稳定入渗率(mm/min);c为常数;t为时间(min)。
Kostiakov模型:
I(t)=atn
(5)
式中,a和n为经验系数;t为时间(min)。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植被类型对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影响
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速率随时间变化的趋势总体较为一致,均表现为前期急剧下降、中期波动下降和后期逐渐稳定3个阶段。从不同样地来看,花溪样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下降较快,其中乔草绿地初始入渗速率为3.26 mm/min,稳定入渗速率为0.94 mm/min,而灌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为3.93 mm/min,稳定入渗速率为1.08 mm/min(图1);玉龙桥样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下降则较为平缓,其中乔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为4.14 mm/min,稳定入渗速率为1.37 mm/min,而灌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为5.25 mm/min,稳定入渗速率为1.80 mm/min(图1)。同一植被类型均表现为花溪样地的土壤水分初始入渗速率(乔草:P=0.012;灌草:P=0.002)和稳定入渗速率(乔草:P=0.000;灌草:P=0.000)显著小于玉龙桥样地。从不同植被类型来看,同一样地均表现为乔草绿地的初始入渗速率(花溪:P=0.239;玉龙桥:P=0.311)和稳定入渗速率(花溪:P=0.000;玉龙桥:P=0.000)小于灌草,其中乔草和灌草的稳定入渗速率差异达到了显著水平。
2.2 不同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的影响
不同样地土壤水分的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总体一致,均随着时间的延长渐趋平缓,但其单位时间的累积入渗量有所差异。花溪样地的乔草绿地和灌草绿地土壤70 min内的累积入渗量为分别为97 mm和123 mm,而玉龙桥样地的乔草绿地和灌草绿地土壤70 min内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155 mm和190 mm(图2),同一植被类型均表现为花溪样地单位时间的累积入渗量显著小于玉龙桥样地(P=0.000)。随着入渗时间的延长,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累积入渗量差异逐渐增大,且均表现为灌草绿地累积入渗量显著大于乔草绿地(P=0.000)。

图2 不同植被类型绿地土壤的累积入渗量变化特征Fig.2 Cumulative infiltration of soil water in different types of green spaces
2.3 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拟合
为进一步研究不同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影响,采用3个经典入渗模型对不同植被类型影响下的土壤入渗量拟合发现,与同一样地的乔草绿地相比,Philip模型中的灌草绿地S值(土壤的吸渗率)和A值(与稳定入渗率有关的参数) 均相对偏大,表明灌草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性能更佳。Horton模型和Kostiakov模型所对应的ii值,if值和a值也均表现为同一样地下,灌草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能力大于乔草型绿地,三个模型均很好地反映了不同植被类型绿地土壤水分的入渗差异。其次,Philip、Horton和Kostiakov模型的R2均值分别为0.998,0.998和0.999,RMSE均值分别为1.682、1.434、0.959 mm(表2)。综上所知,三个模型的相关参数均能很好地反映不同植被类型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差异,但与Philip、Horton模型相比,Kostiakov模型拟合的R2最高,RMSE最低,且其相对于其他两个模型能够更好地拟合研究区城市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过程。
本研究的野外绿地土壤入渗试验持续至70 min后结束,基于Kostiakov模型预测可知,玉龙桥乔草和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158 mm和191 mm(野外观测值分别为155 mm和190 mm),花溪乔草和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分别为96 mm和124 mm(野外观测值分别为97 mm和123 mm),与野外观测所得的累积入渗量差异较小。从不同植被类型绿地来看,参数a均表现为灌草绿地大于乔草绿地,这很好地反映了初始入渗阶段,灌草绿地的入渗速率显著大于乔草绿地。随着入渗过程的进行,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I(t)也在每一时段均大于乔草绿地,且二者的差异随着入渗时间的延长而逐渐增大。此外,Kostiakov模型为幂函数,其常数项0 表2 Philip、Horton、Kostiakov模型拟合参数结果 本文研究表明,海珠湿地的土壤稳定入渗速率为0.94—1.80 mm/min(1.57×10-5—3.00×10-5m/s),略大于北京(1.76×10-7—3.22×10-5m/s)和上海(3.0×10-6m/s)等城市的绿地土壤入渗速率[15,17]。按Yang等[27]提出的城市绿地入渗标准,其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属于中等至较快水平,这主要与海珠湿地的建成时间较短有关。从本文的采样来看,海珠湿地表层0—10 cm的土壤容重在1.19—1.41 g/cm3,基本符合绿化种植土壤容重小于1.35 g/cm3的技术规范,且远小于其他城市的绿地表层土壤容重[13,25],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其表层土壤的水分下渗。 但与自然土壤相比,海珠湿地的土壤水分入渗速率仍然偏低,这主要与城市土壤普遍存在压实有关。压实导致土壤颗粒遭受挤压,使得非毛管孔隙向毛管孔隙转变,堵塞了水分通过大孔隙向深层土壤快速运移的通道,进而影响到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13,28]。海珠湿地在建设过程中,大量地使用重型机械搬运客土和平整地表,造成了严重的机械压实。其次,海珠湿地在建成后,其作为广州市公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之一,人流量较为集中,频繁的人为踩踏导致绿地土壤容重增加,且远高于自然土壤的平均容重[19,29- 30]。绿地土壤的容重越大,其非毛管孔隙度越低,因而渗透性也随之越差[15- 16]。Wang 等[31]对长春市城市绿地土壤的入渗研究证实,城市不同类型绿地的土壤水分稳定入渗速率差异较大,乔灌草组合的绿地土壤入渗速率最高,而乔木下面只有裸地的区域土壤入渗速率较低,这一差异主要与后者所在的区域人流量较大,对地表不断的踩踏压实有关。Alizadehtazi等[32]对不同透水地表的入渗速率研究也表明,四周隔离的树池其入渗速率之间没有差异,而没有隔离的树池则差异较大,这一差异主要与未受隔离的树池土壤受到行人或机动车辆压实的频率高低有关。本研究也发现,同一样地均表现为乔草绿地土壤的累积入渗量显著小于灌草绿地,这可能与不同植被类型绿地对游客的可达性及吸引力差异有关[22,33]。乔木巨大的冠幅有助于户外遮阴等,可吸引游客的驻足休憩,因而加剧了乔草绿地的土壤压实,而灌木遭受人为踩踏较少。频繁的踩踏导致乔草绿地土壤容重偏高、而总孔隙度与非毛管孔隙度偏低,这也与本文的室内测定结果比较一致。因此,应大力种植灌木或乔灌木并植,促进城市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19]。未来仍需加强不同压实强度和频率下,各功能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研究,确定最佳的人为干扰程度,使得城市绿地在保持其旅游休闲功能的同时,也能兼顾雨洪蓄积的角色。 其次,海珠湿地土壤的入渗速率偏低也与其客土的来源有关[17- 18, 23]。客土来源不同,其土壤质地也有所差异,进而影响到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16]。海珠湿地的前身是万亩果园,果农为了追求挂果率,每年会采用沟渠底泥上基的方法来提升土壤肥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海珠湿地的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偏高[34]。室内分析表明,海珠湿地土壤的物理性黏粒含量在48.28%—52.53%之间。与自然土壤相比,其土粒比表面积更大,大孔隙含量更低[28],因而对下渗水分的吸持能力更强,单位水势梯度下的水分传导速率变小,湿润锋下移减缓。在下渗的过程中,土壤表面黏粒的散发和膨胀也会促进表土结皮的发育,使得土壤中未及时排出的空气被包被,进而抑制水分的持续下渗[23]。此外,土壤黏粒也会随着水分下渗堵塞在大孔隙中,使得毛管空隙增多而大孔隙进一步减少[16, 35]。大孔隙在土壤孔隙中的占比虽小,但其对于优先流的形成及土壤饱和导水率的变化起着主导作用[19]。因此,土壤物理性黏粒偏高会减缓水分在土壤有效通道中的运移,从而降低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速率[19]。李卓等[35]通过土柱模拟入渗试验也发现,土壤容重相近时,其90 min累积入渗量、稳定入渗速率与物理性黏粒含量分别呈指数负相关、幂函数负相关关系。这与本研究结果也比较一致,玉龙桥绿地的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小于花溪绿地,在同一植被类型下,70 min内的土壤累积入渗量和稳定入渗速率均表现为玉龙桥绿地大于花溪绿地。但土壤粒径过大,绿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又会减弱,同时也会影响其对污染物的净化功能。未来需要根据不同功能绿地的建设需求,选用合适的土壤改良材料,维持城市绿地高效且可持续的入渗性能[24]。 最后,万亩果园北侧毗邻龙潭村,该村作为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其城市废弃物早期因垃圾分类不当或管理不善而混入土壤,使得在此基础上建成的海珠湿地土壤结构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其土壤的水分下渗[15]。本研究野外土壤样品采集过程中发现,海珠湿地土壤中混入了混凝土块、砖块、塑料和布条等人为侵入体。方政等[9]研究表明,人为侵入体的出现会降低土壤总孔隙度,减少水分下渗的过水断面积,增加水分入渗通道的弯曲程度,进而抑制绿地的土壤水分下渗,以混凝土块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人为侵入体的类型、含量及分布的土壤层位不同,其对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的影响也有所差异,未来仍需加强不同人为侵入体影响下的绿地土壤水分入渗过程研究。 植物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根系穿插、分割和扩张等机械作用使得土壤产生孔隙和裂隙,增加土壤大孔隙的数量和连通程度,进而提高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性能[18,36]。根系在土壤中的分布特征不同,其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也有差异。本文研究发现,同一样地灌草绿地的累积入渗量均显著大于乔草绿地,这与杨倩等[33]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数量多、密度大的0.5—2 mm径级的根系是改善土壤入渗性能的关键,其通过增加优先流路径长度,进而促进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1,37- 38]。对研究区绿地植物的根系调查发现,灌草型绿地植物的根系主要集中分布于0—20 cm土层,该土层的平均根密度为2.19 mg/cm3,且径级小,密度大,增加了非毛管空隙的分布,减弱了入渗水流的阻力,使得单位水势梯度下的土壤水力传导度增大[23],有利于绿地表层土壤水分下渗。而乔草型绿地植物的根系主要分布于20 cm以下,0—20 cm土层的根密度仅为0.62 mg/cm3,且其根系粗大,密度小,降低了乔木根系与上层草本根系的连通程度,因而对绿地表层土壤水分入渗性能的改善有限。Rahman等[6]对刺槐(Robiniapseudoacacia)和欧洲椴(Tiliacordata)冠层下的土壤入渗速率研究也表明,前者的土壤入渗速率显著大于后者,主要在于前者的细根生物量密集分布于土壤表层,从而穿插形成非常多的小孔隙,有助于土壤水分下渗,而后者根系分布则相对较深,不利于林冠下土壤表层水分下渗。但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灌木根系对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则开始减弱,而乔木较深的根系则有助于土壤水分的进一步下渗,因此,未来需要对不同类型的园林植物进行优化配置,确保绿地土壤的不同层次均有根系分布,从而最大化城市绿地的水分入渗性能[1, 19]。 绿地植物也会通过枯枝落叶和根系凋亡向土壤归还有机质,提高绿地土壤的水分入渗性能[14,39- 40]。研究区灌草绿地的土壤容重小于乔草绿地,还可能与不同类型绿地的有机质归还能力存在差异有关。受树木冠层构型差异的影响,乔草绿地的凋落物更易于清扫,而灌草绿地受灌木丛状生长的影响,其凋落物常难以清扫而得以保存。这与海珠湿地的调查结果较为一致,两处样地的灌草绿地凋落物干重在92.38—95.34 g/m2之间,大于乔草绿地的凋落物干重(22.33—64.73 g/m2)。这有助于提高灌草绿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促进水稳性团聚体的形成,改善其土壤结构。且有机质中的腐殖质表面积巨大,富有亲水基团,能够增强绿地土壤对水分的吸持力[23],同时也能为土壤微生物和土壤动物活动提供必要条件,降低土壤容重,增加非毛管孔隙的比例。其次,凋落物的存在也会提高土壤表面的粗糙度,滞缓雨洪的汇流时间,增加绿地土壤水分的累积入渗量[16]。最后,根系在凋亡后,不仅会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还会进一步增加土壤大孔隙的比例[38]。其中细根的分解速率相对于粗根更快[12,41],使得根系与土体之间形成更大的优先流通道,进一步促进了绿地土壤的水分下渗。本文的研究也发现,同一样地灌草绿地的非毛管孔隙度总体大于乔草绿地,可能与灌草的细根系主要集中在土壤表层有关。不同类型绿地的有机质归还能力与其植被类型及人为干扰程度有关,未来需要研究不同有机质归还能力下,城市绿地土壤水分入渗速率的变化特征。 (1)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性能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但受机械和人为压实影响,其容重偏大,总孔隙率偏低。加上外来客土添加等的影响,其土壤物理性黏粒含量较高,且有部分人为侵入体混入,进一步抑制了绿地土壤水分入渗。 (2)植物生长可促进绿地土壤水分入渗,以灌草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性能的改善最为明显,这主要与其根系的分布近地表层有关。此外,凋落物和根系持续的归还土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地土壤水分入渗。 (3)Philip、Horton和Kostiakov模型均能够拟合不同植被类型的城市绿地土壤水分累积入渗量随时间的变化特征,但以Kostiakov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 后续绿地的建设过程中,应注重乔灌草相结合,并适当增加灌草比例,减少人为侵入体及物理性黏粒含量较高的客土如塘泥等混入。对已有绿地,应设置专用廊道及固定休憩区,减少绿地土壤的压实作用,并注重凋落物和根系的持续返还,增加绿地土壤表层的团聚体含量,兼顾城市绿地的旅游休闲和雨洪蓄积功能,促进海绵城市的高效建设。
3 讨论
3.1 土壤物理性质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
3.2 植被类型对绿地土壤水分入渗的影响
4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