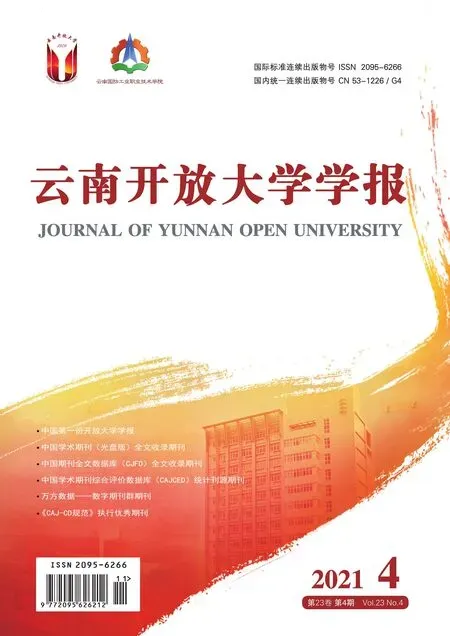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分析及税制模式选择研究
景 帅,高 玲
(云南开放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0)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是国家税收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通过立法,调节社会各阶层人员收入分配结构、缩小高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的一种有效手段。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
中国最早的个人所得税有关条例出现在中华民国时期,当时就薪给报酬所得、证券存款利息所得开征过个人所得税。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有关个人所得税的条例是1950年7月由政务院颁布《税政实施要则》,里面就列举名为“薪给报酬所得税”的对个人所得课税税种。但由于当时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工资水平也处在一个相对低位的水平线上,虽然有税收规则,但实际上并没有开征。
1980年9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自此走上了中国税收的历史舞台。同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施行细则》,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至此方始建立。1986年9月,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个人收入的不断提高,社会贫富差距逐渐显现,基尼系数有所上升的态势,为有效针对这一现象对社会成员收入水平差距进行调节,国务院发布了《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规定对本国公民的个人收入统一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连同之前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我国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制度日趋成熟。1993年10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的修正案,规定所有中国居民和有来源于中国所得的非居民,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来自境外的自然人,均应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同日发布了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这是对1980年税法的第一次修订。1999年8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这是第二次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这一次修订的最大亮点是把第四条第二款“储蓄存款利息”免征个人所得税项目删去。2005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再次审议《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免征额1600元于2006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第三次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第四次修订于2007年6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开征、减征、停征个人所得税及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随着经济发展需要,2008年再次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再次暂免征个人所得税。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满足当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切实保障当时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2007年12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人所得税免征额自2008年3月1日起由1600元提高到2000元,这是个人所得税法的第五次修订。2011年6月,在充分考虑物价等因素基础上,经过酝酿调研,本着保护中低收入人群,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人群的基本原则,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500元,同时,将个人所得税第1级税率由5%修改为3%,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3%和10%两个低档税率和45%最高档税率的适用范围等。该决定自2011年9月1日起实施。这是个人所得税法的第六次修订。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的腾飞发展,为了适应发展需要,个人所得税迎来了第七次修订,可谓是革命性的一次修订,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等四项所得合并成为综合所得计征个人所得税;二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减除费用),预扣预缴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汇算清缴减除费用直接设定为每年6万元;三是采取了先预扣预缴第二年再汇算清缴的方式;四是在原来专项扣除的基础上,增加了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专项附加扣除”,有效减除税收负担,其中包括: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五是进一步优化调整了税率结构,有效加大中低收入档次的纳税区间,与之前相比扩大3%、10%、20%三档低税率的级距,缩小25%税率的级距,30%、35%、45%三档较高税率级距不变。这些修订“亮点”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高收入,保护中低收入的作用,有效减少贫富差距,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上作出了贡献。第七次修订的《个人所得税法》于2019年1月1日起全面施行,这也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正式步入了从分类征收到混合征收的阶段。
二、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完善,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
(一)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的占比情况
见表1: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情况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表1 个人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情况表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近些年来各项税收收入数据中可以看出,2011年免征额提高以来至2018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收入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情况,但比重却一直在10%以内,可见个人所得税并非我国税收的主要来源。占比最高的年份是2018年,达到了8.87%,这正逢2019年新个人所得税法改革前,老的税法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年。个人所得税占比的不断提高,其实也侧面证明了从2011年以来老百姓绝对收入水平是不断提高的,但个人所得税由于免征额(减除费用),相关扣除政策没有明显改变,而致使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比重越来越高。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落地执行的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征收向混合征收改革,同时进一步提高了综合所得的免征额(减除费用),修订了各级税率档次的覆盖范围,增加了专项附加扣除,故而2019年的个人所得税税收水平有了明显下降,减税效果成效显著。[1]
(二)个人所得税的修订完善,切实体现了返利于民、调节各层次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目的
十八大以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就一直是党和政府致力奋斗的目标。2018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无论是从免征额(减除费用)的提高,还是从“专项附加扣除”这一新兴政策出台,都体现了党和国家切实为老百姓减负的决心和信心。据测算减除费用的提高,使得个人所得税纳税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由之前的44%下降至15%,“减税降费”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上效果明显。[2]专项附加扣除的引入,恰是符合中国老百姓生活最实际的6个方面的开支情况,这种亲民懂民的优惠政策落地,切实做到返利于民,造福于民。此外,将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的一套思路和机制引入到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计税上来,更体现了税收公平的根本原则,让老百姓都能分享到改革带来的红利。同时,综合所得3%-45%的7档超额累进税制也充分拓宽前三档的对应级距,彰显了新个人所得税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保护。经过两年多的实践来看,新个人所得税法的改革实施,对于各层次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效果的确好于过去,税收效率提高,彰显税收公平的效果更加明显。
三、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的分析研究
(一)参照国际个税经验,科学选择税制模式
纵观全球,各个国家个人所得税税制基本上是三大类:分类征收制、综合征收制和混合征收制。三种税制各具优点,也各有不足。[3]分类征收制相较而言征收管理难度较小,尤其是以个人为单位、以不同收入分类的分类征收制更加简单易行,然而却也是三种税制中对纳税人整体所得把握得最不全面,容易导致实际税负的不公平,可以说分类征收制是税制发展过程中最初级的一种直接、简单、粗暴的征税方式。综合征收制的难度大,需要全面收集足够充分的个人或家庭信息方可实现,对数据的要求极高,但却是极具人性化,可以较好地达到调节收入水平,确保税收公平目标的一种税制。所谓混合征收,即对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先分别按照不同的方式和差异化税率征税,然后将全年的各项所得进行汇总征税,它目的是有效整合前述两种税制,扬长避短,更加科学合理地选择税制模式,对于各项收入的特点来优化税制结构,提高征收效率,是经济社会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二)我国现行个税法关于综合所得的范围
当前个人所得税法的综合所得范围只在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种收入下开展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并且这四种收入的个人所得税征缴也是最全面最细致的,不难发现,这四项收入主要以劳动所得为主(这里的劳动所得是相比较财产利益所得而言),对于通过财产而获得的个人所得,目前个人所得税法的征管相对较简单直接,且很多财产转让、财产租赁等情况下的个人所得收入游离于个人所得税征管之外,由于征管难带来的个人所得税管理对于劳动所得的征收力度相对显得较强,征税呈现出“重劳动,轻财产”的厚此薄彼现象,对于税收的公平性是一种挑战。
(三)我国现行个税法关于减除费用的确定模式
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对于减除费用的规定仍然是以某一绝对数为准并保持一段时间,结合市场、物价、经济发展等因素若干年调整一次。但这种操作存在很大的弊病在于反应滞后,无法及时有效将通货膨胀相关因素考虑在内,往往出现物价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但减除费用依然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脱节现象。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11年至2018年,中国的CPI指数累计上涨了15.2%,而税法规定的减除费用却始终维持在3500元,减除费用没能及时根据市场、物价、经济发展水平及时提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节现象,税收调节效应降低,居民收入实质上出现了缩水,抑制消费,经济发展的内循环动力受到制约。
(四)我国现行个税法下关于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分析
居民个人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规定的,在2021年12月31日前,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12个月得到的数额,按月换算后单独计算纳税。由于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不采用超额累进制的,而是直接除以12找到月应纳税所得额所适用的税率,这就出现了纳税陷阱。[4]所谓纳税陷阱,就是在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时计算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时,奖金的应纳税所得额处在高一档税率的税后收入反而小于低一档税率的应纳税所得额的税后收入的异常现象。也就是出现在特定全年一次性奖金区间,全年一次性奖金发得多的人反而比全年一次性奖金发得少的人拿到手的还少的情况,从而出现了纳税陷阱问题,[5]比如,10%税率档中,发放金额在36001元-38566.66元时,要么选择小于36001元,要么选择大于38566.66元的发放金额,就可以避免“多拿一元钱,税多好几千”的现象产生。
年终一次性奖的纳税优惠虽然存在纳税陷阱的漏洞,但是对于一定范围内的综合所得群体,相比没有年终一次性奖纳税优惠而言,只要将一定比例的工薪收入中的部分作为年终一次性奖收入进行纳税,税收优惠的效果是存在的。[6]
四、对策和建议
(一)关于免征额(减除费用)的确定
免征额(减除费用)应该通过某些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变量进行关联计算,如将CPI指数等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货币价值的参量作为减除费用的因变量,采取更加合理的办法确定减除费用,每3-5年进行一次修正,这样确定的免征额才更为合理,更能体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税收调节的“共振”作用,切实保护低收入阶层,会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符合纳税人的社会期望,更加有效调节收入,维护社会稳定。
(二)关于专项附加扣除的标准进一步提高
现行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应该加大标准,打破一个子女教育1000元,赡养老人2000元等的标准,由于专项附加扣除测算需要的信息不单纯是某一个或某几个职能部门可以全部提供,就需要全社会各部门,例如住建、社保、教育等主管部门与税务机关协同合作,科学合理确定标准,方可实现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征管机制。与此同时,税务部门应当配合统计部门对于民生方面的数据加强联动,确保个人所得税的计征管理更加贴近百姓,更加“有温度、接地气”。
(三)对于年终一次性奖纳税的优惠
在年终一次性纳税优惠政策存续期间,很多中等收入人群还是可以通过年终一次性奖的纳税优惠实实在在获得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从减轻税负角度而言,对年终一次性奖的纳税优惠政策能够予以保留在现行税收体制下,不失为是“保护中等收入”的个税法根本目标和“减税降费”的阶段性目标。通过年终绩效考核后发放的奖金,应该算作单独的一个月收入单独计税,与现行的税收制度不冲突,可以在有这些收入的范围内继续推行年终一次性奖纳税优惠政策。
(四)加大对汇算清缴中逃税漏税的惩治力度
根据当前税收惩罚法律政策,对于偷税漏税行为的处罚经济层面上动辄3倍、5倍的惩罚力度已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最高是七年有期徒刑的限制自由措施稍显宽松,应当进一步加大对于这些“失信”人员的惩戒力度。例如从银行贷款等一系列与个人征信有关的层面加以限制,同时再加大对其直系亲属加以限制,不断提高惩治力度。随着新税法体质执行以来,对于已经出现的冒用他人身份虚报个人所得税问题等现象,阴阳合同,变相发放津补贴等情况的滋生,加大对新个人所得税法执行上的管控风险。对于新出现的情况加大约束力度,对于违法现象加大惩戒力度是迫在眉睫需要规范解决的,让纳税人感受到违法成本巨大,才会让他们真正做到“从不敢到不想”,切实净化税收社会风气。
(五)探索以家庭为单位的征收方式
既然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是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的个人所得,那么家庭因素是个人税收的重要影响因素,且家庭开支往往是个人成本支出的主要方面,按照现行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在考虑计税的时候并没有将家庭因素纳入考虑范围。而这样的税制无疑是削弱了税法在调节社会收入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调控能力。举个例子不难发现,假设A、B两个家庭年收入都是20万元,区别在于A家庭是一个成员收入20万元,另一个成员没有收入,B家庭是两个成员各10万元收入,通过计算不难发现,A家庭的税负明显高于B家庭的税负,也就是说同样是收入20万元的两个家庭,但是由于没有考虑家庭实际情况,同规模收入的两个家庭税负却差距甚远,难免出现了显失公平的问题。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达国家诸如美国、英国,都将家庭成员状况等因素考虑进纳税人纳税的环节中,最大可能实现量能纳税。有利于体现男女平等,提升社会对家庭劳动的认同度,同时这样的征收模式还能降低社会就业压力,维护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