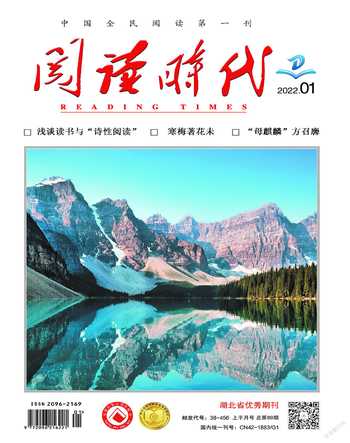仰韶文化是如何被发现的
秋兰菁
我们在阅读历史故事时,常常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面对现实中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古人们往往会一头扎进故纸堆中,从过去寻找答案。似乎越是生活在古老时代的人,越会拥有今人缺少的智慧、道德和信念。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徒劳的。因为经过历史长河不断淘洗,这些史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湮灭,少部分留存者也被后来的记述者删改、扭曲。对于后人来说,想要通过历史记录完整客观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原貌,似乎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任务。然而随着现代科学考古学的诞生,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出现了一丝曙光,人们终于可以不再完全依赖历史记述者的视角,近距离地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代接触。
安特生和仰韶遗址
中国现代考古学始于1921年秋,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
安特生本是瑞典人,1874年出生于谢斯塔,毕业于国际顶尖名校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获得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1914年,身为地质学家的安特生受北洋政府之邀前来中国,被聘为“农商部矿政司顾问”,与时任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丁文江一起组织地质调查,并训练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者。1916年由于袁世凯倒台,地质调查因经费短缺而停滞,安特生调整了工作重心,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边进行主业地质调查,一边满足自己的爱好——收集化石以及考古发掘。在这期间,安特生获得了许多足以载入史册的发现。
1918年,安特生在北京市郊的周口店鸡骨山进行过两次调查,并进行了试掘,但并无大的收获。
1921年,他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在龙骨山北坡找到了一处更大、更丰富的含化石地點,这就是闻名于世的周口店龙骨山遗址。安特生在此进行发掘后发现了两颗人类的牙齿化石,并在1926年向世界宣布了这两颗猿人牙齿,随后更多的北京猿人化石被发现,这些古老人类化石的发现,让全世界为之轰动。
而安特生最大的贡献,却来自一些不起眼的石器和碎陶片。
1920年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刘长山派往河南洛阳以西地区考察。12月,刘长山回到北京,带回600多件石斧、石刀和其他类型的石器,这些石器均来自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这引起了安特生的注意,并认为仰韶村可能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址。1921年4月18日,安特生来到仰韶村作地质调查,在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他在一个被流水冲刷露出的断面上发现了许多石器和彩色陶片,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并在未来的几天里不断扩大他的新发现。此后,安特生回到北京征得农商部及地质调查所同意之后,又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于10月27日正式开始对仰韶村进行发掘,这便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现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
随后安特生的调查又扩展至杨河村、西庄村、牛口峪、池沟寨等多座遗址,他通过对比出土的遗物,认为这些遗址都在一个大体相近的时间,由同一群人创造,因此他正式以最早发掘的仰韶村的名字,将在这些遗址中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在《中华远古文化》中提出仰韶文化是由中亚传播而来的假说,之后动身前往西北寻找史前文化遗址以证明其理论。安特生一行沿着黄河出发,用了一年多时间,途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调查和发掘了包括朱家寨、辛店、齐家坪、马家窑等众多遗址,这些遗址在后续的发掘中都成为补全中国史前历史的重要“拼图”。
这些遗址雄辩地证明,中国也存在着史前史,推翻了世界对中国无石器时代的刻板偏见,也为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古代文化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民国考古学的发展
自安特生发掘仰韶遗址以后,中国考古学也逐渐走向正轨。当时正值民国期间,虽国家仍风雨飘摇,但在广大爱国学者的努力下,考古学事业仍缓步前行。
1921年底,北京大学调整研究所结构,其中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和考古学研究室,成为较早的考古研究组织,但考古学研究室由于经费受限,未有实际的考古发掘,只收购一些古董商的古器物。1925年,清华国学会成立,清华正式开设“考古学”课。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即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之一,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国学研究院实现了本土考古学由“坐而言”终至“起而行”的转变。1926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的李济与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在山西运城夏县西阴村进行了三个月的考古发掘,这也成为中国学者自己主持发掘的第一处史前遗址。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研究部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任第一任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罗常培、李方桂、董作宾、梁思永、劳干、周法高、严耕望、石璋如、芮逸夫、全汉升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研究员。史语所集中了一大批英才,一时成为学术界瞩目的重镇,并在殷墟等处考古发掘、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研究、全国各省方言调查等多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果。
在1928年至1937年共10年中,由史语所组织进行了15次殷墟考古发掘工作。这些发掘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考古方法,在发掘之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重视地层的划分和遗迹间的相互关系,同时顾及各个遗址之间的有机联系。殷墟遗址的发掘,为中国考古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也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走向科学化。
这十年间,由吴金鼎主持对济南以东的东平陵以及城子崖进行了6次调查,发现了以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遗存,并在1930年由李济、董作宾、郭宝钧、吴金鼎等人对城子崖进行了一个月的发掘。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考古事业也走入低潮。随着中原地区成为沦陷区,殷墟考古发掘也被迫中断。史语所的田野考古工作逐渐转移到边疆地区,但再也没有恢复到“黄金十年”时的成就,抗战结束后的三年内战则完全陷入了停滞。而中国考古事业更大的辉煌要等待新中国成立后由新一代考古人来创造了。
新中国考古学与三大工程
新中国成立后,一度中断的考古工作又得以重启。由李济的学生夏鼐牵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1952年,苏秉琦主持成立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之后很多省份也纷纷成立各自的考古研究机构或文物管理局,其首要任务就是配合新中国轰轰烈烈的大建设,对受建设影响的古代遗迹进行抢救性发掘,中国的考古工作得以在比过去宽广得多的空间里开展起来。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丰厚的考古成果开始发酵,学术界已经不再满足于解读个别考古遗址,而是逐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原始国家诞生的机制和文明形成等问题,期间多种观点出现与碰撞,如由美国学者赛维斯提出的酋邦理论传入后,易建平、谢维扬、范毓周、王震中、陈淳、沈长云等学者曾围绕酋邦概念及中国早期社会如何与酋邦理论相结合进行过长期论战;也有学者结合世界考古理论与中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观点,如苏秉琦摈弃了传统的“中原中心论”,提出了中华文明“满天星斗”说、“古文化—古城—古国”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严文明提出了相似的“重瓣花朵式”模式;王巍则就中国实际,明确了中国地区文明和国家的定义,并指出文明和国家是不同范畴的概念。各种观点交織碰撞,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史前中国的认识。
随着国内各项考古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对探究中国历史真相和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有了新的要求,自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推出了多个大型考古工程项目。
1995年秋,国家科委(今科技部)主任宋健邀请在北京的部分学者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宋健提出并与大家讨论建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设想。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被启动。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开设了9个大课题,在这些课题之下设置了44个专题,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为研究中国5000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工程于2000年9月15日结题。
断代工程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是中国古史研究中第一次跨多学科进行的大型研究工程。虽然对最后得出的年表仍存在争议,但是断代工程的开创性是无可置疑的。而在此之后,学者们又在断代工程的基础上,开展了后续“中华文明探源”“考古中国”等工程,吸取了之前的经验和教训,为中国的考古事业开创了新的篇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至2004年间进行工程预研究,2004年夏季正式启动。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4期完成结项,2018年5月发布相关研究成果。
探源工程成果丰硕,首先是确定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三个阶段: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来,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然后是探源工程研究团队从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中心城市和强制性权力等方面,提出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的突出特征,最后是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了总体认识,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的总体特征。
探源工程取得的成果丰富且扎实,在此期间如良渚、石峁等大型史前文明遗迹一次次出圈也让探源工程被人熟知。
探源工程之后,国家文物局又立项“考古中国”,工程项目包括:“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下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海岱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夏文化研究”和新疆考古、西藏考古等重大考古项目,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之后还将有新的课题纳入工程。而早期中国文明的迷雾,也将在考古人共同的奋斗中逐渐被拨开。
责编:何建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