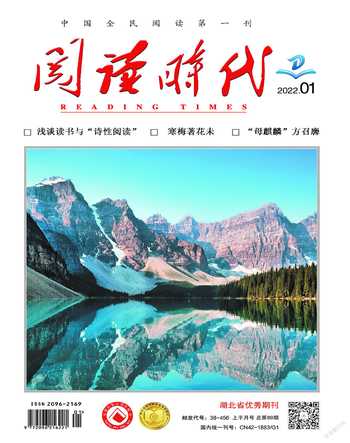佛教传入对汉语词汇之影响
黄大荣

在世界各地,宗教对人类文化产生的巨大影响,不言而喻。宗教信众甚广,不仅诗人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大量使用宗教词语、典故和特定句法,老百姓日常生活中,也有普遍运用和发挥。例如“伊甸园”“亚当”“夏娃”“上帝”“天堂”“天使”“忏悔”“祈祷”等字,便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方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古代中国亦不例外。虽然中国自古以来无一特定的国教,但儒教、佛教、道教,以至其他民间信仰(财神、关公、药王、茶圣等等),都不断促进着中国文字演变。当中,佛教属于外来宗教,它的经典绝大部份均译自梵文、巴利文、佉留文及多种胡语,所代表的文化是已高度发展的古印度文明,对中国本土的汉语语言冲击和影响很大。可以说,佛教的传入,直接导致了一次汉语词汇的大爆炸。几次语言大爆炸,第一次是在大约一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农耕时代,部落之间通婚和原始商品交换,促使语言极大的丰富起来。第二次,就是所谓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雄辩时期。第三次,就要算佛教的传入。第四次,晚清到民初,西风东渐,大量翻译西方各类著作。日本开放在先,我们借鉴了它的译著,科技词汇丰富了起来。第五次,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计算机和网络时代,社交媒体上,人们创造了无计其数的网络词汇。当然,这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淘汰鄙俗的、不合汉语规范的,留下精华。
首先是佛典翻译对汉语词汇之影响。一般认为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前,便已透过西域(今新疆一带)诸国传至已经拥有高度文明的东汉社会。为了在中土争取信徒,当时的佛教传播者就必须把梵文、巴利文或藏文写成的佛经翻译成汉语,以便人们受持读诵。因此,便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等高僧的译经壮举。
印度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当时已在宗教哲学上有很高的建树。正好弥补了我国哲学用语的不足,其中,多为中国所无。译经者介绍佛学概念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要临时创造一些新字新词,或把本有之汉字和词汇,加以引申,注入新意。这些字词涉及的范围甚广,从佛教专词,到哲学用语、成语以至日常用语,包罗万有,不胜枚举。略举数例,加以说明。
佛门专词:如“菩萨”,省略自“菩提萨埵”,梵语Bodhisattva之音译,意思为“觉有情”,指未曾成佛,但已解脱烦恼的智者,亦泛指一切修习大乘佛教之人。汉语中本无“萨”字,后因“菩”而造了一个带有“草”字头的“萨”字。又如“尼姑”,此词较为特别。原本在印度梵文中为Bhikchuni,在中土音译为“比丘尼”,即出家后受具足戒之女性佛教徒。其他如涅槃、般若、三昧、瑜伽、佛陀、和尚、僧伽、阿修罗以及忏悔、禅定、呗器、轮回等,也是汉语原本无有的佛教专用词。
哲学用词:“世界”,即宇宙。《楞严经》云:“何名为众生世界?世为迁流,界为方位。”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称“界”。中土本无明确的时空观念,所谓“天下”,亦仅止于古人可以到达的地方;直到佛教传入中国才有了比较抽象的时空观。“宇宙”一词出于中国战国时期思想家尸佼的《尸子》:“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古印度的世界观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自此产生了关联。又如“因缘”,此词汉语本有,解作机会、原因、缘故。《史记·田叔列传》:“(任安)求事为小吏,未有因缘也。”后来佛教用来作梵文Hetu-pratyaya的译名,指形成所有事物的原因和条件。“因缘”是译经者把新解释注入旧词语的一个例子。其他例子有唯心、实际、真如、法界、微尘、相对、绝对、意识等。
日常用语:如“解脱”原解释为开脱、免除一些罪名,《史记·酷吏传义纵》:“……为死罪解脱”。佛教译经者将原意扩充,指成佛后不受烦恼束缚、离苦得乐的境界为“解脱”。于是人们便以“解脱”形容痛苦完结后的一身轻的感觉。“刹那”,梵语Ksana的音译,极短的时间单位。《俱舍论》卷十二:“壮士一弹指,六十五刹那,如是名一刹那量。”京剧《霸王别姬》有唱词:“成败兴亡一刹那。”其他在日常生活被广泛使用的佛教用词有庄严、慧眼、如意、精进、众生、境界等。
成语:“水乳交融”,水和乳易于融合,比喻关系密切。《大般若涅槃经》上:“欢悦和谐,犹如水乳。”“飞蛾扑火”比喻自取灭亡。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如灯蛾投火,但贪明色,不知烧身。”“瞎子摸象”典出《涅槃经·狮子吼品》,原喻众生被愚痴所障,不解宇宙实相,后喻人局部地、片面地看问题,难以得悉事物真相。其他被普遍使用的成语有天花乱坠、顽石点头、天女散花、一丝不挂、恒河沙数、镜花水月、百尺竿头等。综上所说,印度佛教的传入,为汉语注入大量新词汇,已在宗教、艺术、建筑、社会学和哲学以及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紧密地融合到了本土汉语中,人们往往使用了佛门词汇而不自知。另外,佛经的翻译亦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语言学家王力说,“如果是意译,就更非复音不可。……至于吸收外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靠着主从仂语来对译单词。既然是仂语,至少要两个音节。”佛教所译的词汇,很多是古代中国所没有的概念,因此很难用一个单字确切地表达出来,加上佛典为了便于记诵,多讲求节拍,经常以四字为一句,两字为一节,于是便加速了汉语有使用双音节词的走向。这个走向,改变了以前以单音词为主的语言系统;同时,也避免出现过度创造新字,或一字多义的情况加剧。
佛教用词得以广泛流传,是有原因的。佛典主要译自以拼音为核心的梵文,这和以图像为基础的汉文截然不同,因此佛教词汇能够在文化深厚的中原植根,绝非偶然。一些学者,如葛兆光就指出原因之一,是宗教影响了文人。宗教作为信徒做人处事的最高准则,自然会使信徒抒发情怀时,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宗教词汇。在西方,基督教对人们谴词造句的影响极大;在中国,佛教也一样大大影响了人们的用字。我们可以看见不少中国诗人都受到佛教影响。例如王维(公元698至759)被称为“诗佛”,其字“摩诘”就是从《维摩诘经》而来,所作《鹿柴》有“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之句。苏轼(公元1037至1101)号东坡居士,所作《和子由渑池怀旧》也有“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之语。然而,这些诗人的诗句多不为底层民众所熟悉,因此,他们又往往刻意在写禅诗时不使用佛家语,如苏轼《题西林壁》的绝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底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此诗满布禅机而不露佛家痕迹,可见佛语对汉语的古诗词有影响,但不一定表现在文字层面。反而,受佛教影响的讲唱文学以及“非正统”的章回小说(古代文人以散文和诗词为登堂入室之正宗),对普罗大众用词的影响和改变更大。自南北朝以降,佛教便推行经典的唱导,优美地演唱佛经故事和义理,这就为后来出现的变文、宝卷、弹词、鼓词、戏曲等通俗文学提供了材料。这些说唱文学渗透了中国民间歌曲的元素,音乐性、故事性都很强,吸引不少大众欣赏。流行的章回小说又对佛教所说的神佛多有描述,《红楼梦》固然说尽人生情梦,但对儒道释的描述,极其精彩;也不回避受到佛家人生虛幻的色空观的深刻影响;而《封神演义》《西游记》又极言与天界众生的争斗,里面的佛教用词多不胜数。因此一般平民百姓即使不通佛理,口头亦多挂上了“十八层地狱、阿弥陀佛、前世、轮回、因果报应”等词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道教的神话故事同样被广泛流传,但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却远不及佛教显著,常见的只有“奇怪、丹田、蓬莱、画符”等。这一方面是由于道教溯源自先秦道家、巫术,同时又受到佛家很大影响,以至真正属于道教独创的用词不多。而佛家刻意运用较浅白的文字,也是一项不可忽視的原因。佛教重意不重文,甚至讲求“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因此翻译佛典时多用当时的口语,避免不必要的文字障碍,使人容易记忆、吟诵,令经典得以广泛流传。这与道教注重符箓经咒,用词夹杂古奥典故和生僻字词的做法大相径庭。
另外,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吸收外来词汇的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汉自张骞通西域后,由西域诸国传入的新词,如“石榴、酋长、琉璃、狮子”等;二是因佛教东渐而出现的词汇;三是明清以后,由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词语。而当中以佛教影响最深最广,近代学者丁福保所编的《佛学大辞典》便收入佛教词语近三万条,双方在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和借鉴的意义,可见一斑。文化犹如流水,由低往高流比由高往低流困难得多。汉语传至日本后成为日语的基石;满文在清代成为官方语言,却对汉语冲击甚微;现代中文在中国与外国频繁接触后,大量吸收了西方的科技词语,随便看看某一专业的技术辞典,就是厚厚的一大册。这些都说明了词汇交流的方向,与科学技术或文明的发展水平的高低不无关系。当时西域的文化水平较中土低,西域有而中国无的概念不多,因此所翻译的词语只以西域特有的物产为主,未能令中原人感到有使用西域词语的需要,加上这些词又多以音译,故未能在汉语词汇中击起多大涟漪。佛教传入时,印度古文明水平不比中国低,佛学代表了人类玄性思维的最高成就;它在宗教哲学上已经形成了自洽的逻辑体系,概念更比中国严谨得多;不少在印度经常运用的哲学词汇,在汉语中竟找不出相应的字来。所以当时的知识份子便大量吸收佛家的翻译词汇来弥补汉语之不足。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却能在汉土植根,表明中国古代智者具有吸取外来文化的胸襟和气魄。古印度佛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后来竟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在词汇上尤其如此。今天中国人脱口而出的大量语汇,不能忘记了其佛学渊源,这会让人忽略它对古代汉语词汇变革的重要性的认知。佛经的翻译不仅大大增加了汉语词汇的数量,并且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化的进程。可以说,不认识佛教,就不能认清中国文化;不认识佛教词汇,就不能认清汉语的演变历程。
(作者系本刊特约撰稿人)
责编:王晓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