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美学,时间与范畴
解芳
近读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引言里两句话颇有意思。他说,中国美学是指辛亥革命前的美学,只有把范围限制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规模冲撞和融合之前,才能从一个比较纯粹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美学。而西方美学却必须包括西方现代美学。只有包括西方现代文化,才能从一个全面的角度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
这个观点有些道理,但未必尽然。譬如五四以來的一些思想创见,作者显然把它们排除在外。这里也许有一种出于传统性的考虑,就是说他以为受到西学影响而产生的思想,偏离了中国两千年传承的文化,不再是纯粹而正统的。但事实上,五四一代兼有西学素养与国学传统,他们的思想创建往往以外化内、中西汇通而生新意。

王国维便是一例。王国维早年读书的志趣在西方哲学,他从德国唯意志论者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里受到启发,产生一种悲剧的人生观,里面既有对人生苦难的体验,亦有对国运衰亡的忧患。在这种人生观底下,王国维写了《〈红楼梦〉评论》,把文学和哲学结合起来,全面而系统地阐发了类似叔本华唯意志论的思想,以及他本身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譬如他分析人生本质,并以此阐释《红楼梦》的精神。以为人总是为了延续生命,而生命却在于欲望。这种写法,与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不同,更有一种理论的气势以及思辨和逻辑的成分。
从前,中国文人往往依靠一种相近阅读背景下的薰习,以臻相似的表达习惯、思维方法、感受联想,进而产生共鸣、理解以及共同的欣赏、判断标准。所以,中国传统的言说方式往往偏重直觉和经验体悟。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人不擅长西方科学推理的思维方式,而能够通过个别、具体的事物进行鉴赏、领悟,并传达作品中的精神和阅读中的体验。其弊端在近现代以来国别交流愈甚之时,显得愈发明显。另外,白话兴起替代了文言,也使这种仅仅依靠斟字酌句的领悟方式,显得过时而不讨好。由是,革新与拓展是必然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应算作一种尝试。他用西方批评思维的长处来弥补中国传统批评思维的短处,虽然对《红楼梦》本身略有误会,但其现实价值与意义却是显然的。
王国维的治学途径在后来发生转变。他从对西学悲剧人生观的耽溺,走向中国戏曲史、词史的研究。最后又钻研于古器物、古文字,好像乾嘉考据的传统,亦不乏西方实证的精神。这期间,王国维写了《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的说法。按照王国维的理解,西方美学上把美区别为两种,一曰优美,一曰宏壮。而古雅则是两者之间的另一个审美范畴,属于“低度之优美”和“低度之宏壮”,兼有两者的性质。因美学上尚未有人专论古雅,所以王国维于此一篇略述其性质及位置。这种说法,一面弥补了西方美学理论的不足,一面产生一种创见,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审美思想。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境界一说亦如是。境界一词古即有之,非王国维独创。然而古代文人对境界的讨论,常同于意境。所以,当王国维提出境界一说以后,便有人以为此论“一方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继承和终结,同时又是中国现代文艺的先声”。
由此看来,五四一代的文人学者常在社会变革与中西文化碰撞时候,推动中国思想演进,尤其在文学、美学一面,产生许多新意。这种新意,好比六朝佛学输入。六朝佛学输入极大地改变了汉以后儒家抱残守缺、思想凋敝的状况。然而当时,佛学属外来的新鲜物。唯其经过历史的涤荡,才真正融入中国文化精神,成为里面重要的,带有时代、流派特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今天中国人不会把佛学的价值与意义排除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外。所以,面对五四以来的融汇与变动,人们自然要把它视作中国文化精神传承的一部分。
这里,一面是自省的需要,一面是比较与对话的需要。现代叶维廉在《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中有一些观点,颇值得借鉴。他说,跨中西文化的比较,便是使读者看到两个文化的互照与互识。互照、互对、互比、互识就是要西方读者了解到世界上有很多作品的形成,可以完全不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美学假定出发,另有一套文学假定去支持它们;就是要中国读者了解到儒、道、佛的构架之外,还有与它们完全不同的观物感物程式及价值的判断。可见得,文化交流的真正意义,在于开拓更大的视野,相互调整、相互包容。人们在寻求共同的文学规律时候,必然从寻找“同”与“异”的认识过程,演化为跨文化的思想、美学精神的汇通。所以对于五四以后学者们的诸多尝试,应予以重视。因为正是从他们开始,中国人自觉地融入文化与文化开放式的对话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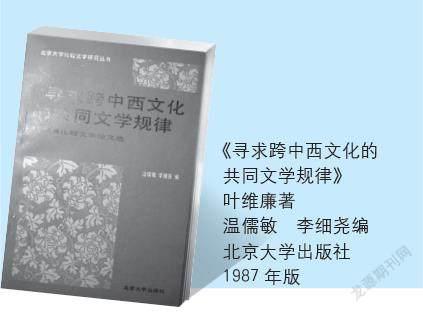
既然谈及时间,必然从历史的一面联想到未来事情。譬如《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和谐:中西文化理想追求的审美凝结”一章,便让人想到近几十年来,甚至往后许多年,人们都将争论不休的生态问题。虽然作者仅止于对中西美学里关于和谐观念不同走向的分析,以为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和谐模式未曾改变,而西方文化传统里的和谐模式则离奇曲折,不断走向荒诞。但于其他人而言,也许有些不同的看法。譬如中国文化传统里的“和”观念,未必都是中正平和。一些否定、不和谐、对立抗争的因素,自然不能忽视。尤其近代开始,在西人影响底下,国人对不和谐因素的追求愈发明显。又譬如,西人从和谐走向荒诞,近来又从荒诞复归和谐。这里有现代工业与科技危机的考虑,也有近代政治制度危机的考虑。在技术一面,每当一项新的发明产生,每当工业前进一步,自然就后退一步。自然成为不适于人生存的自然,人便失去了与自然的和谐。在制度一面,生产使工人成了卓别林《摩登时代》里麻木运转的机器,受到物的支配和控制。人本身失去了和谐,所以有了一种渴求复归和谐的生态审美追求。
由是,中西文化于此方面的比较与对话,好像有了汇流与新生。在中国,是一种对传统的“天人合一”之美的重新发现与重新提倡;在西方,譬如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里面,蕴含了将人与自然、心与物统一起来,相互依存的因素。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方面,尽管分属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历史局限,其发展好像走向一个共同的审美理想,同时又是敞开、变动不居的。
至于对和谐的议论,又能生出一些联想。在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里,和谐这个词(harmony)包含着“音响、自然、社会”等意义。毕达哥拉斯有一句名言,说“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在他面前,至美和谐的音乐底下,流淌着“数”的永恒定律。毕达哥拉斯以后,人们沿着他的思路,以为美的体验便是一种形式上的愉悦。譬如声音、形体、色彩,往往要体现一种整体、适度的规律。在亚里士多德的时候,发展成为有机整体的概念。也就是说,各部分的安排要见出大小、比例和秩序,要形成融贯的整体,才能见出和谐。不过,毕达哥拉斯亦因发现了“数”,而把人们引向终极体的追求。在他的理解中,“数”是宇宙万物的最高统治,唯其服从“数”,才能体现美。所以,由“数”开始,人们又以“自然”为终极。这时候,“自然”是先在之物,是美本身。人唯有竭力地模仿这种美,才能间接地领会它。“自然”以后,是中世纪的神学。上帝成为和谐之美的体现者。当时有名的奥古斯丁以为,所谓的整一与和谐,便是人在精神上和上帝接近。
但和谐之美不只是形式的构造,和对终极物的追求与模仿。它同时也深深地体现在社会层面,体现在人的道德和群体的关系之中。譬如苏格拉底,便是一个人生哲学家。他以为最紧要的是人生伦理问题,而非遥不可及的宇宙本体。所以他看重内容及以教化臻于和谐的作用。这种观点在后来被他的学生柏拉图继承,并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他说,“最高最美的思想智慧是用于齐家治国的,它的品质通常叫作中和与正义”。不过,文艺复兴以后,“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成为一种标志,理性得到彰显。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体的意义。至于那些自然终极、社会价值的思考,显然衰颓了。
与古希腊传承的文明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文言表述里,和谐这个词大抵是“和”“中和”“和合”。并且不同的时代和流派里,有不同的意思。当毕达哥拉斯出生于波光帆影的地中海沿岸时,孔子正遥遥相望地生活在阡陌纵横的黄河流域。孔子后来成为儒家的“至圣先师”。他在探讨“和”这样一种审美理想的时候以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一种折中而适度的表达。并且,《论语》里记载了孔子一句话,说的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理想的处世之道,在于从内心底下与人和睦相处,但不盲目苟同。
这里,“和”与“同”区别开来。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和”就好比包容多样性的精神,而“同”则是不加拣选地附和。显然,孔子是推崇“和”的。孔子以后,他的传人承其衣钵,进而阐述中和之说、中庸之道。事实上,中庸之道并不是庸俗一流,也不是违依两可的苟且折中,而是一种不偏不倚,求法乎上的,由综合、圆满臻于和谐的境界。儒家常常以此来实现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协调。
和孔子不同,庄子继承老子一派的思想,讲人与天、心与物的统一。在庄子看来,天不是希腊文明里那种具有超验意义的终极体,也不是先在和谐与美的范本。人应当与天融合,譬如“心斋”“坐忘”,游于两极之间,仿佛“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如此,方是一种和合状态,理想至极。庄子以后,大约到了汉代,董仲舒把孔子和庄子的观念糅合在一起,提炼出中和之说,既是社会的,亦是自然的。因之可以说是一种真正天人合一的观念。此观念,在后来流传甚广,渐渐生出一颗宽容之心。
生活在间隔着陆地与海洋的地球,人们总有一种热望,想要了解他人,了解那些遥遥相望的身影。然而,即使一些相似的审美追求,在跨文化的历史变迁里,也显得模糊而隐约。关于“和”的理想即如是。在这本《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里,作者把中华文明的“和”与希腊文明的“harmony”归结为“和諧”。他企图寻求共通点的愿望,自然毋庸置疑。可是,他忽略了一点,即一种动态的观察。譬如从单一文化本身来看,其话语范畴的意义指涉往往变动不居。它们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添赋新意。又譬如多文化对话,往往会有困扰。原因大抵在于,语言是思想栖居之所,又固执地烙印着自身文化的色彩。
当语言与语言传递彼此信息的时候,总也避免不了各自视域里的偏见与误会。就好比,中国人看到从“harmony”翻译而来的“和谐”,往往想起孔子的中庸之道,想起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同样地,当西方人看到从汉字“和”翻译过去的“harmony”时,亦会想起毕达哥拉斯,想起苏格拉底,想起亚里士多德。
这样的例子亦可再举出一些。譬如“崇高”(sublime)。西人谈及崇高,往往把它作为对和谐的反抗。从郎加纳斯到康德,再到黑格尔,“崇高”这个词大体说的是对立与冲突,一种突破了静穆和自身圆满的痛感。而在中国,这种痛感与渺小感似乎无法以“崇高”表现。现代曹顺庆曾把西人的“崇高”与国人的“雄浑”,放在一处比较,似乎略显合理。毕竟单以古书里偶然提到的“高”或“大”作释,显然不足以把中西方不同的思维与理解统摄于一“崇高”。
跨文化比较,是一种同中求异、异中求同的过程。这里,往往有交织、交错的一面,又往往有分隔、独立的一面。人们感到惶恐,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目光不再中立;他们绞尽脑汁,终于发现一种圆桌会议式的包容、开放和谦恭,可以让他们得到欣慰。在这种圆桌会议上,所有因历史传承而相异的理想追求、内在困境、超越意识和自由精神,都静静地绽放着花朵,闪耀着无比灿烂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