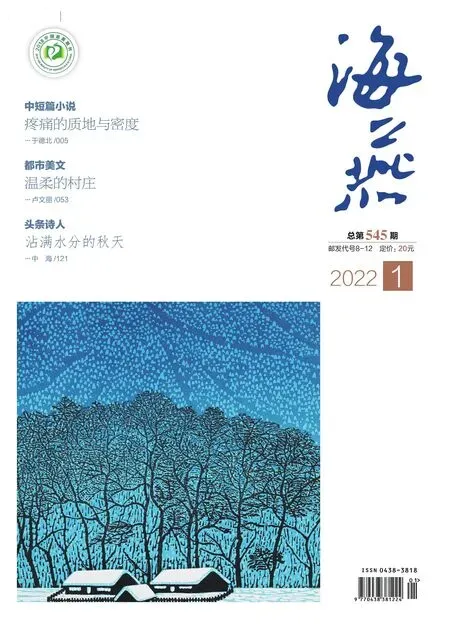火车开往哪里去
文 谢 伦
一
我大姐的婆家在兴隆镇黄家寨,离我们村有30里地。我母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和父亲怄气。说太远了,说大丫头脑筋呆,眼睛不好使,小时害过眼病,要来不得来,要去不得去的,够不到,不放心。我父亲却说好。我父亲说她将来的老婆子(婆婆)是她的姑妈哩——父亲的一个远房姐,亲上加亲的,还能亏待了她?我从没见这个姑妈到过我们家,姑父来过一次,也是前不久为了托人说这门亲才来的,跟媒人一起,拄着拐杖,穿黑色的长袍子,瞎一只眼,很怕人。话倒是说得好听,说他们那里有桃园、梅园,还有一个叫520的工厂,还有火车,火车成天昂昂地打村前的油菜地里跑过去跑过来。我就记住了火车。
大姐出嫁的那天母亲在柴房里哭死过去,我姨慌慌地掐她人中,掐得我姨自己也哭起来,弟弟妹妹也跟着哭起来。大姐就在一片哭声中被前来迎亲的人接走了。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没有通往兴隆镇黄家寨的沙石大道,我母亲醒过来追到村子后面,只见一条白茬小路空无一人地漫过高冈去,她喊了一声大丫头,就又哭过去了。
想不起那一天我父亲在哪里,还有我大哥、二哥,他们都在做什么呢?多年后我想努力地回忆起,可记忆到那儿就像是断裂了,那一天,还有后来那么多的日子,都成了恍惚的时光碎片,如瓦砾,锋利、尖硬,扎在我的生活里,遍地疼痛。就常常在睡梦很深的时候,听到了一个人呼唤的声音,极微弱的,缥缈在遥远的地方。
记得接大姐回门(三天后回娘家)时,是凤姐姐和我大哥,我赖着也要去。母亲不让,大哥也不让。大哥很恼烦的样子说,你跟着干什么呢,绊脚啰嗦的。我眼泪就出来了。还是凤姐姐打圆场,说要去就去吧,三兄娃儿能走得动的。凤姐姐叫谢伦凤,是我堂姐,大伯的二丫头,按乡俗接回门是要娘家屋里去一个闺女才好,我母亲就叫凤姐姐去。
我说我要去看火车。大哥白我一眼,一脸不屑。
去黄家寨的路真难走,全是翻黄土冈,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黄土冈,翻过了一条又有一条,少有村庄,虽然是春天了,但给人的感觉仍然是很荒凉。走到大半晌的时候,遇到一道像河一样又宽又深的大沟,不过沟里没水,我们下到沟底,就看到了两条锃亮的伸向远方的铁轨。大哥说,这就是火车路。因为大哥不乐意我跟来,一路上脸色难看,我就很小心,走路腿走疼了也不敢吱声儿,是怕他生气。但一听他说这两条铁轨就是火车路时,我着实吃惊不小,一时没管住嘴巴,失口道:“咦,原来火车是在大沟里跑的呀!”没想到还是惹得大哥生气,他劈头盖脸地训斥我:“不懂胡说个啥,丢人现眼!”
看到了火车路,没见火车,我就站在铁路上磨叽着不想走。我瞪着一对大眼睛,把头偏过来偏过去地朝铁轨两边的尽头望,可尽头空空茫茫,啥也没有。这时凤姐姐和大哥已经上到对面沟坎上了。就听到喊:“三兄娃儿,三兄娃儿!”我以为是凤姐姐叫我,不是的,是我大姐。我大姐说她一早就在火车路边等我们了,等很久了,我猜你们就该到了。她从坡沿儿上走下来,牵住我的手。我问她火车呢?咋没见火车?大姐说,这会儿没火车了,已经过了,回家吃晌午饭吧,以后会有你看的。
黄家寨是个大村庄,但我大姐家却是单门独户地住在村子外面,三间旧茅屋带个小偏厦,歪斜在一面土坡上,四面不靠,显得孤零零的,极矮,进门时得弯腰低下头。凤姐姐皱着眉在屋里转了一圈就出来站到场子里了,她说她在屋里憋闷得慌,透不过气;她说,把大姐嫁到这样一个鬼都不下仔儿的人家,我小爹(我父亲)他也狠得下心!
我姐夫慌忙搬出椅子让凤姐姐坐,凤姐姐不理他。
二
母亲生病很突然。我记得刚刚过完春节,母亲去锄春麦地,就晕倒在麦地里了。卫生所医生说是心脏病,做活累的。母亲却说不是。母亲说,做活哪能累得成病?是操大丫头的心操的。那一年我读小学二年级。开学了,我没去。没谁说不让我上学,我父亲没说,母亲也没说。母亲说,这兄弟几个,就小三儿和我亲近。还真是这样儿。我一听到母亲难受的呻吟声,就挪不动脚了。有几回我已背着书包走出院子门了,还是退回来。我想我要是走了,母亲躺在床上连个叫嘴的人也没有,连口水都喝不上。那时候大哥好像已经参军走了吧,二哥读初中,也不怎么上课,但成天个儿跟着老师们不是学工学农,就是上街开批判会、游行,不落屋;父亲起早摸黑儿下地做活,弟弟妹妹还太小指不上,就剩下我了。母亲问我,咋不上学去?我说不上了。母亲也没再坚持,只是叹一声气,说,要是大丫头不嫁那么远就好了。
大姐怀云举时我成了母亲的通信员。一天早上,母亲叫我到夏店子喊我二姨家的四老表,是要他和我一起到大姐那儿给还没出生的小外甥送尿布。母亲说,你大姐快生了。就把我们兄弟几个穿的烂得不能再穿的旧衣服,都用剪子剪开,裁成了一块块破布片儿,要我下河里用棒槌捶洗干净,晾干,再烧开水烫一遍,再晾干,就成尿布了。包了一大包。
我说我记得路,我一人去就行。

插图:齐 鑫
母亲不干,说那么远,荒冈野洼的,怕碰上毛狗(野兽),还是喊个伴儿她心里要踏实些。四老表比我大两岁,长得壮壮实实,但个子反而比我矮,上学跟我读一个年级。开始他有点不愿意。后来我突然说,还能看到跑火车。他一高兴,就跟我去了。
我不知道那会儿我是怎么想起火车的。其实,这些日子我只顾照顾母亲,火车,这个被我想象过无数次的无比威武的大家伙,我已经忘记很久了。路上四老表问了许多关于火车的问题,比如说,它长的是什么样子,有嘴巴耳朵吗?是不是真像传说的龙一样长,风一样快,是不是真跟蜈蚣似的有数不清的脚?我一样也答不出来。但我不想掉面子,不想跟他说我上回只看到了铁轨,而没看到火车。就说,走快点,马上看到了你不就晓得了嘛!
其实我是铁了心的,这回,哪怕等再晚,就是等到天黑了,也一定要看上。
快到我上次翻过的那个“大沟”时,远远的,我指给四老表看,说那沟底下就是铁轨。这时已经到正午了,太阳顶着脑门儿晒。我肚子饿了,四老表的肚子也饿了,饿得腿脚发软,但都没说出来,还坚持走。是不是决心下大了,反而得来容易?甚至没让我们好好地等一下,准备一下,火车就冲过来了。先是听见它震耳欲聋的昂叫声,轰隆声,接着就看到了从那个“大沟”里冒出的滚滚白烟。可这时候我们离“大沟”还有好几百米的距离,而“大沟”又太深了,只看见白烟冒出。不见火车,我俩就拼命地朝沟沿儿上跑,我们分明已经感受到了车轮滚动时给脚下的路带来了震颤,但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只看了个火车尾巴。我恨自己背了包袱,没跑快。四老表倒是显得特别激动,站那里望着早已没了踪影的火车,大发感慨:“哎呀呀,不得了,光个尾巴就那么长啊!”
三
父亲早晨起来去灶屋煮稀饭,然后喂猪,扫院子。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是给母亲熬草药,把草药和水装进药罐里,用手指比一下(水要漫出草药二指高),泡一会儿,就抱来剥过皮麻的白麻杆,开始熬。中午热一次,晚上热一次,倒掉。倒药渣儿有讲究,要在天色黑定之后倒在村前的十字路口,倒时不能让人看见。说不清为什么。母亲的病终于有好转,天气好的时候,能起床坐屋檐下晒晒太阳了。姐夫来家报喜,说老娘您得了外孙子呀!母亲喜极而泣。没想到我这个通信员更难当了。
母亲淌着泪说,不晓得大丫头这会儿是咋儿在过,她老婆子睁眼瞎(患严重白内障),我又病在床上,合该她命苦,坐月子也没人帮。姐夫赶忙宽慰母亲,说不咋的,有我哩。
但姐夫走后,第二天母亲还是叫我去了黄家寨,一是带半斤红糖(家里只有半斤了),捉只老母鸡补大姐身体;二是让我代她看看大姐到底好不好。我回来就说好。母亲问哪儿好?吃得下饭吗?娃儿呢?是胖还是瘦?我低头不语。我心想,这些姐夫来报喜的时候不都告诉你了吗,怎么还要问?母亲就生气,骂我:“指不上的东西!”
大姐在生病,脸白得像张纸,连和我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小外甥饿得哇哇叫,姐夫使土方子给大姐发奶,可是越急奶越不下来。但这些我都不能说,姐夫、大姐都不让我说。
我猜母亲一定是看出了名堂才生气骂我,因为她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这是第一次。辛辛苦苦跑路还挨骂,我心里委屈,就耍横顶撞母亲:“有本事你自己跑去黄家寨看。”
我自然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有多重。一个还不懂岁月风尘和人生多艰的孩子,一下子把母亲气得说不出话,她虚弱地坐在病床上,抬手指了指我,脸色发白,浑身打颤。
这可把我吓坏了,却不知该如何做才好,急得直喊妈、妈、妈……扯着母亲的衣袖哭起来。
四
黄家寨的春天多雾,却也不特别浓。没风的时候,这些雾就像是生了根,一缕一缕从地里长起来,二尺来高,缭缭绕绕。地里是麦子,是油菜。麦子也才长到二尺高,油菜要高些,有半人高。油菜花都开了。清晨起来开开门,扑面而来的全是花香。
姐夫说,屋子孤零有孤零的好处,周围都是庄稼地,清静。不像他们(寨子里的人)住在大村里,那么多人都挤在一坨坨儿,臭烘烘的,还三天两头不是你的鼻子就是我的眼睛。来黄家寨时候多了,住时间长了,经常听到村人骂仗,对姐夫的话逐渐认同。
我以往来黄家寨最多住一天,自打有了云举,母亲就交代我要帮大姐做点事,别急着回。一住三五天是经常的。但我在大姐家除了照看一下云举,却也没有多少事要做。反而每每担心母亲,抽空跑回家看,母亲还好好的。母亲说,只要你大姐那儿好,我就好。
大姐的屋子东边有20多棵梅子树,都在结指头蛋大的青梅了。这就是几年前我姑父(大姐的公公)到我家提亲时所说的梅园吧!但他所说的桃园我没见到过;520工厂在村北半里地,我时常背着云举到厂里面去看外国人,外国人大鼻子凹眼的看多了也没啥意思了,就去村南头。村南头有明清时期残留下来的黄家寨的古寨墙,墙外一片金色的油菜田,稍远是铁轨。只是寨墙已经没有了墙的轮廓了,落一截一截长长的土堆,土堆下摆放着几排蜂箱。在天气又好,又没有火车过的时候,天地安静,坐那里看蜜蜂们嗡嗡融进阳光,恍惚身在别处。我那时尚在少年,并不知这就是寂寞、孤独,或者伤感所至,总感到心里很空,总想哭。
云举极听话,不吵不闹,我若想自己出去逛一下,不想抱他的时候,就把他放在门前的场子里,对他说,别动啊。他就不动。我走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我回来他还是坐在那里。印象中那时的云举只有一岁多点吧?往往大姐在做活的间隙回家发现我不在,便大声喊:“三兄娃儿,三兄娃儿!”而我一定是坐在寨墙头、或别的什么地方发呆。
那段时间,我最盼望的就是我二姨家的四老表来。我母亲也怪,我要是来黄家寨一晃就回去,她就说我怕给大姐做事,偷懒;若要是住的日子稍长,她又操心大姐这里会不会有别的啥事儿,就会派四老表来察看。好在四老表说他喜欢到黄家寨来,不用上学,还能看火车。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和四老表都对火车表现出了特别的迷恋。已经看过无数回了,还是迷恋。不管是拉人的还是拉货的。我们远远地坐在沟坎上,数火车的节数。拉货的火车总要长些,最长一回我们数到过78节;而拉人的就少多了,一般就12节、13节。我们喜欢火车开过来的那种压倒一切的威猛无比的力量,喜欢它咆哮时掀起的无形的冲击浪,喜欢它刺耳的歇斯底里的尖叫和迅疾的飞驰速度。火车一过,我俩立刻就跳到铁路上去,跟着火车跑一阵,直到火车跑远了,什么也看不见了,才停下来,喘粗气,望着两条溜光锃亮的铁轨,空寂地伸向远方。火车要开往哪里去啊?有时四老表会很无助地问我。其实,他更像是自己问自己。我说,哪儿远它就开往哪儿吧?哪儿远有多远呢?我们无从知道。但朦朦胧胧的,那时候,它成了一个巨大的诱惑,我们心中的永远的疑问。跑累了,我和四老表就坐在铁轨上歇一会儿。偶尔还碰到一个穿工作服的铁路工,背一个帆布挎包,拿一个铁锤子,在铁轨的这边敲敲,那边敲敲。其实我们经常碰到的是另一个人,是个中年男人,穿一身破旧的黄衣裳,黑色脸,头发乱蓬蓬的。他缺了一条腿,拄着双拐,一动不动地站在铁路边上的一个三岔路口处。我们发现他每回都是站在那一个地方,一动不动,眼光迷离。有一次,我和四老表沿着铁路走,捡到几大坨煤块(后来知道那是焦炭);又一次捡到了20多个大苹果。苹果多得抱也抱不下,不晓得如何才好。四老表就脱了裤子当布袋,只穿个裤衩走回来。我姐夫说,你俩的胆子可真大。你们晓得那个缺腿的人是谁吗?我问是谁?姐夫说,是白湾儿那边的一个飞车贼,专门扒火车偷东西的。
这东西是他偷的吗?四老表担忧地问。
姐夫说,不是他偷的,可也算是他的。他的腿那年被火车轧了,不能再飞车了。但他们有一伙子人。公安局天天逮,逮了好几个坐监去了,还没逮完。这苹果,还有上回你们捡拾回来的焦炭,都是他们夜里扒车时落下的。
原来我只在说书匠那里听说过飞车贼,感到他们都是武功非凡的人,很神奇,佩服得五体投地;可真的碰上了,又叶公好龙地害怕起来,吓得好几天没敢再到铁路上去。
五
大姐常常在夜里哭泣,声音很小很小,早晨起来好好的,像啥事都没发生过。大姐和姐夫吵架不让我看到。听说有几次吵得厉害,还动了手脚。大姐眼神不好,有回我见她左边脸肿得青一块紫一块,问她,她说是夜里起来上茅厕摔的。我也没怀疑。是住在同村的姐夫的妹妹李光珍知道了来找姐夫,说哥,你不能对嫂子那样!姐夫黑着脸,一声不吭。
当春天的脚步一天一天走向纵深的时候,油菜花开始凋谢,田垄上一同开始调谢的还有其他许许多多我不知名的小花朵,它们都成了火车奔驰途中的匆匆过客。火车在夜间的吼叫声特别瘆人,巨大的铁轮撞击钢轨的声音比白天要响过几倍。我开始睡不好。
我床铺铺在堂间里,屋子进深浅,我头对门,脚就抵着了砌在北墙的鸡舍了。老鼠一点不怕人,半夜跳上我床头,打我被子上沓沓沓跑到床尾,再钻进鸡舍里。老鼠不敢吃鸡,但鸡们以为是黄鼠狼,惊慌得咯咯一阵乱叫。我用被子把头捂起来。
第二天大姐给云举喂奶时,我对大姐说,我想回家去。
她抬脸看看我,又看看怀里的云举,半天不说话。我发现大姐眼里有泪光。
我的心就软了,就说,我不回了,也行。可大姐又说,还是回去好,眼不见心不烦。只是这两天天还有点冷,再等等,等天气暖和了你把云举带到他姥姥身边去。
可没过多久,就听说那个缺腿的飞车贼被火车轧死了。是后半晌,村里那么多的人涌过去看热闹,把铁路都阻断。大姐嘱咐我,三兄娃儿带着云举,可不敢去。我就没去。据回来的人讲,那个飞车贼是自杀。的确是自杀,还是在那个三岔路口,有人亲眼看见火车开过来了,他扔掉双拐,一只腿弹跳起,像只大鸟一样飞进火车的轮子里。等火车停下来,他的头在铁路的那一边,身子在铁路的这一边。也有人说他并不是有意去自杀,他成天站在那里,是在等一个叫江红梅的姑娘。说那是个有一对长辫子的漂亮姑娘,他的相好,几年前被一辆到北京的火车卷了衣裳,碾死了。从此他成天就站在那里,眼都不眨一下地朝铁路上看,这不,眼睛看花了,把火车看成是江红梅姑娘了,便不顾一切地扑过去。
这真是一个让人忧伤的噩梦。一连多少天,黄家寨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我心里越发不安定。那颗乱蓬蓬的头,那双迷离的眼神,那只被风甩动的空裤腿,总是闪现在我眼前。姐夫喜欢上了喝酒,没醉的时候谁也不在他眼里,醉后见着谁都笑。有一天又喝得摇摇晃晃回来,大姐去灶房舀一碗酸白菜水给他醒酒。他却歪坐在堂间的椅子上,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看着我笑,突然就冒了一句:“火车路的三岔口,就是一个死人的地儿!”
说得我身上的汗毛直竖,头皮发麻。
那天大姐屋里屋外忙,姐夫坐那儿自言自语,直到我上床睡觉了也没停下。
六
等我带着云举回到吴店,已是初夏了,云举的到来,给母亲带来安慰。我重新上学去。这一年是1970年。如果我没记错,1968年、1969年、1970年,这三年应该是我去黄家寨最勤、也是滞留时间最长的三年。后来大姐生云五时,母亲就没再叫我去黄家寨了;再后来大姐又有了云川、老四儿、小五、小红,我去黄家寨越来越少,以至于终于止步。认真回忆一下,我对黄家寨最早、最多的记忆,也就是我的大姐。
还记得云举才来吴店的头两年,大姐每次回老家来看父母和云举,走时都是我送她。我每次送她都要送到一里外的板头井;而每次她上到板头井的井坡上,总还要回头呼唤我:“三兄娃儿、三兄娃儿,还要来黄家寨呀,还要去看火车!”我觉得我已经不小了,她还当我小,还当我是那么迷恋火车的小时候。记得有一次大姐站在板头井的井坡上大声地呼喊我,后面的话没喊出口,就弯下腰哭泣。大姐口里的“三兄娃儿”,已不止是指我这个小弟弟,而是她这些年孤独远离的整个家。那种无奈的心底苍凉,也是我多年后才渐渐明白的。
在过去的40多年里,我父亲去世,母亲去世,二哥去世,后来大姐也去世了。大姐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但都成家立业在别处,黄家寨的日子,他们是回不去了。
何止是他们。2007年冬,我出差从武汉回襄阳,走316国道,经过兴隆镇时,心头忽然一酸,已经是黄昏了,我让司机把车子往岔道上拐一拐,拐过520工厂,到黄家寨村外停下,我一人摸进去。我轻手轻脚,左顾右盼,就像个不小心掉了东西又回来寻找的人。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一阵仔细寻觅之后,才发现我要找的东西早没有了,找不见了。村庄已不是原来的村庄了,原来的村庄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很紧凑,现在是东一户西一户的散乱;道路也改变了;最让我怀念的是爬上去过多次的黄家寨的古寨墙,不知何时也被夷为平地,上面建了好几幢二层的小楼房;我大姐的那座老屋自然是没有了,好不易找到原来的房基处,那里现在是摇曳着一片枯草的黄土坡……我曾经来过这里,在这里生活过,而生活过的一切,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这里从来就是一片黄土坡。
“三兄娃儿,还要来黄家寨呀,还要去看火车!”
记忆里那天晚上风很大,黄家寨冬日的老北风,夹杂着大姐带哭腔的呼唤,吹进我的耳朵,我的骨头。但我看不到那列火车了,我站在村前的铁路上,铁路依旧,那列载着我大姐的黄家寨,也载着我昔日在黄家寨那段生活的火车,开走了。
最后来说说我喜爱的一位诗人吧,他叫邰筐,可我们并不相识。有一个时期,我特别迷恋他的文字,充满困惑、孤独、挣扎,就像是一把把粗糙的刀子,扎进时间深处。他写过一首《猜火车》的诗,我一直记得。我是在网上读到这首诗的,竟以为是专门为我写的,只不过读过几年之后,又一个几年之后,就当它真是我写给我自己的了——
一列火车开走了
它从未知之地来
开到乌有之乡去
车次不明,速度不定
恍如一条
细长的影子
从我身体的针孔中穿过。可是
我的身体是时光里那一座荒凉的小站
我骨骼的道轨
我身体的枕木,至今
依然还承载着
曾经的每一次颤栗、轰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