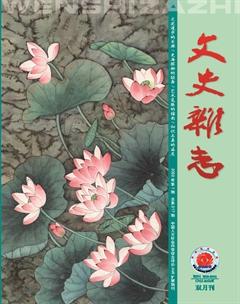“忙儿”指代牧童考
梅强
摘 要:宋代以来的典籍中有“忙儿”一词,一般认为有“牧童”之义。其实,“芒儿(忙儿)”在宋以来的文献中原本作为“句芒神”即春神的代称。“芒儿”(牧童)是人们对“句芒神”的人格化。
关键词:芒儿;句芒神;牧童
宋代以来的典籍中有“忙儿”一词,宋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卷四《宋太师彦筠奉佛》:“(宋彦筠)为小校时,欲立奇功,每见阵敌,于兜牟上阔为双髻,故军中目之为‘宋忙儿’。后虽贵为节将,远近皆谓之‘宋忙儿’。”宋陶岳《五代史补》卷四《李知损轻薄》:“(李知损)对曰:‘下官平素好为诗,其格致大抵如罗隐,故人为号。’彦筠曰:‘不然,盖谓足下轻薄如罗隐耳。’知损大怒,厉声曰:‘只如令公,人皆谓之“宋忙儿”,未必便能放牛。’”《近代汉语词典》对此解释说:“忙儿,同芒儿。”“芒儿,牧童。”[1]这些解释是不错的,其实宋人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六十四《谈谐戏谑·语嘲》:“胡秘监旦文学冠一时,而轻躁喜玩人。其在西掖也,尝草《江仲甫升使额告词》云:‘归马华山之阳,朕虽无愧,放牛桃林之野,尔实有功。’盖江小字忙儿,俚语谓牧童为忙儿也。”宋彦筠的绰号、江仲甫的小名,都与此义有关。“忙儿”又作“芒儿”,上引胡旦戏江仲甫事,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谈谑》作“芒儿”。又如金谭处端《长思仙》词:“芒儿归,牛儿随,明月高空照古堤。”亦是此义。直到今天,兰银官话仍然称呼牧童为“芒儿”,李鼎超《陇右方言·释亲属》:“俗呼春牛牧童为芒儿。”[2]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忙儿(芒儿)”一词有着牧童之义?学者们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分歧。潘荣生《俚语以“牧童”为“芒儿”小考》认为“芒儿”指泥塑的土芒神,因其为偶人形,故有此戏呼。不过阚绪良《“芒儿”义是“村民”》则认为潘氏所举的例证中,“芒儿(忙儿)”并非“牧童”义,而是“村民”义。姚永铭同意阚说,并考“芒”本字为“甿”,称潘荣生“认为源于‘句芒神’,恐不确。”[3]可是,“忙”“甿”虽然音近,但“甿”在文献中并未有见到义为牧童的,牧童义的“忙儿”和“氓”“甿”并不是一回事。丁喜霞也提出了一种观点:“‘芒’本指草或稻麦的芒刺,牧童的常见发式是总角,即束发为两结,向上分开,形状如角,故称牧童为‘芒儿’或‘芒郎’,概得名于其头上有总角。”[4]按说凡孩童皆束发为总角,但为何“芒儿”独称牧童?丁说似乎也有些牵强。
其实上述阚、姚、丁几家说法均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芒儿(忙儿)”除了指牧童,还可以作为“句芒神”的代称。在这一点上潘荣生的说法更接近真相,不过仍有补充的必要。宋以来的文献中,“芒儿(忙儿)”常常指代春神即句芒神,如宋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四十九《杂着》引何耕《录二叟语》:“将春前一日,有司具旗旄、金鼓、俳优、侏儒、百伎之戏,迎所谓芒儿、土牛,以献于二使者。”此处所迎的“芒儿”即句芒神。又如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建炎改元冬,予闲居扬州里庐,因阅《太平广记》,每遇予兄子章家夜集,谈《记》中异事……因言顷闻一异事云:元符末年,渭州潘原县民方耕田,有民自地间涌出。耕者见之,惊怛弃犁而走。则斥逐击之不得走,执耕者及县……见县令马敦古,又殴令,令亦走。俄而仆于庭,奄然一土偶人也。视之,则岁所尝奉土牛傍,所谓勾芒神者。于是共舁出之……未几复有至者,其事皆同,日十数至,不能御。官吏惶恐,令不敢复视事。居若干日,有物人類,蓬首黑而矬肥,降令舍。莫知其所从来,令罔测。乃曰:‘尔无庸恐,我为尔尽食芒儿矣,尔恭事我。’”阚绪良指出潘荣生引用此例不当,认为“我为尔尽食芒儿矣”中“芒儿”指村民。其实通读原文,“芒儿”指的应是“奉土牛傍,所谓勾(句)芒神者”。再如宋刘克庄《汉宫春·赏红梅》词之四:“且祝东风小缓,沥酒芒儿,道伊解冻,甚潘郎、鬓雪难吹。”明王廷《吏部考功郎中西原薛先生行状》:“先生自幼颖异,始生三月,偶见芒神,连呼曰‘芒儿芒儿’。”“芒儿”皆是“句芒神”的异称。
而“芒儿(忙儿)”引申指牧童,应源于人们对句芒神人格化形象的联想。原本“鸟身人面”(《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的句芒神到了宋以后有一个世俗化和人格化的过程。在不少民俗材料中,句芒神都是以童子形象出现的。如宋杨万里《观小儿戏打春牛》诗:“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绿蓑笠青箬。”周汝昌认为诗中“牧童”即土塑的芒神像。[5]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前面彩亭里头,一个塑的小童子,叫做芒儿,牌上写着‘句芒神’,手拿结线鞭,头戴耳掩或提在手里,立地赶牛。”明汪懋麟《东风第一枝·迎春》词:“芒儿斜绾双鬟,土牛半弯两角。”这些“芒儿”(芒神)均作牧童形象。另外我国传统民俗绘画中“芒神”常常是小牧童形象,比如清代山西、山东、陕西等地年画《春牛图》。
一般认为图中赶牛的牧童就是“句芒神”,清周广业《过夏杂录》卷二:“今印卖《春牛图》,一人驱牛曰勾芒神,双髻如牧童。”今天我国浙江、福建、广东、四川、云南不少市、县,如什邡、广州、杭州、开远等地立春时举行“迎春”礼还会扎制或者泥塑牧童模样的芒神。这些都是牧童形象的芒神在民俗事象中的具体反映。
朱大可认为句芒的牧童形象来自印度神话中作为司春之神的英俊少男kama。[6]其实与其说前者是后者的余影,不如说是两个民族某种共通的民俗心理,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未必非得是因袭。“句芒神”代表春天,寓意欣欣向荣,按照传统民俗心理很容易将它具象化为生机勃勃、象征希望的童子。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一“立春”条:“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着帽则春暖,否则春寒。”给“勾芒”取名“拗春童”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心理。同时“句芒神”作为春耕之神,又与春耕、耕牛密切相关,童子也就顺理成章成了牧童。有了这些认识,说“芒儿(忙儿)”指牧童源于“句芒神”不为无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形式上来说,“芒儿(忙儿)”是“句芒神”一词缩略加小称“儿”构成的;从语义上来说,“芒儿(忙儿)”指牧童是一种引申义,是人们对句芒神的人格化。
注释:
[1]《近代汉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2]李鼎超:《陇右方言·释亲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3]姚永铭:《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4]丁喜霞:《〈洛阳缙绅旧闻记〉词语考释》,《励耘学刊(语言卷)》2012年第2期。
[5]参见周汝昌选注《杨万里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6]参见朱大可:《华夏上古神系》,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
——牧童逮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