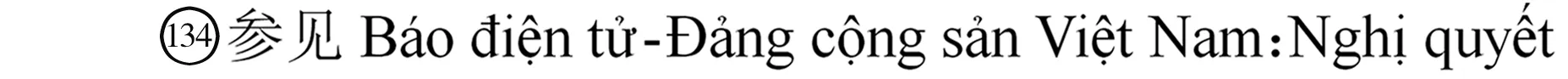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合作的进展、动因及影响
王传剑 黄诗敬 王居正
(1.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2.广西民族大学 东盟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一、引言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久,奥巴马时期的“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战略“正式死亡”①,“印太战略”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新的指导方针。2017年11月,特朗普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正式提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概念②;同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攻击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地区权力平衡”“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并据此将中国界定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提出美国应进一步强化“印太同盟体系”,加强与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合作伙伴的经济、安全合作,以此回应来自中国的“挑战”③。2018年1月,时任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签发《国防战略概要》,重申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所谓“修正主义国家”的表述,指出“大国战略竞争已取代恐怖主义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强调美国应通过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吸引新的战略合作伙伴等手段赢得“大国战略竞争”④。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做好准备、加强伙伴关系和促进区域网络化》,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印太战略”的基本内涵、战略目标和行动方略,并再次强调了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开展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进一步突出了越南在“印太战略”中的关键地位,提出美国政府应向越南进行更多的安全援助以提升其国防实力,具体措施包括提供武器装备、组织联合训练、提供技术援助等多种形式⑤。2019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又发布了《自由开放的印太:推进共同愿景》报告,该报告在指责中国“破坏了印太地区稳定和繁荣的环境”的同时,声称包括越南在内的湄公河地区国家对于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美国将致力于从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地区安全等方面出发加强与越南等国的全方位合作关系⑥。
作为中国的邻国之一,越南在冷战后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中一直被赋予极其重要的地位。早在2001年,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就曾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与亚洲:迈向新的战略和力量态势》的研究报告,声称越南在南中国海战略博弈中有着重要的地缘价值,美越两国在“防止中国谋求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存在着军事合作潜力,这将“使两个昔日对手团结起来”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战略界开始明显提升对于美越安全合作前景的预期,并通过一系列外交和军事举措拉近了美越双边关系,试图将越南打造为美国重返亚太的关键合作伙伴。2010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宣称美国将寻求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发展新的战略关系,以解决反恐、缉毒、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地区共同问题⑧。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将“深化与该地区的重要合作伙伴,如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的防务关系”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部署的重要一环⑨。与此同时,越南也积极配合美国主导的亚太战略,并主动寻求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双方陆续达成了一系列防务合作协议。比如2011年,两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备忘录》;2013年,又高调宣布建立“全面伙伴关系”⑩;2015年,双方签署了《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2017年,又正式达成了《防务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特别是近几年来,为增加在南海争端中的政治筹码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维权行动,越南还积极鼓动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在内的域外国家公然介入,蓄意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和国际化,对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中越关系的发展大局造成了明显的消极影响。尤其是在“印太战略”加快实施的大背景下,美越两国在安全领域的互动越来越被赋予了特殊含义,双方安全合作的不断强化无疑会对南海地区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进而损及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和对外政策选择。
为此,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均对美越安全合作的进程特别是“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关系的发展表现出极大关注,很多专家学者也已就此开展了一些较有价值的探讨。就目前的情况看,国外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述:一是从越南的战略需求出发,认为开展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是越南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对冲”中国实力优势的一个可行之策;二是从美国的战略需求出发,认为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应成为美国推进印太战略部署进而掌握中美战略竞争优势的一个必要选项;三是针对“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安全合作的前景以及取向,认为持续推进双方的安全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共识”。相比之下,国内学界的研究虽然更多集中于回顾和梳理美越安全合作的历程,但大多数学者均强调中国崛起是推动两国加强安全合作的最根本原因,而南海问题则构成了双方安全关系得以维系和发展的最重要利益交汇点。他们进而认为,美越之间的安全合作将会对中国维护海洋权益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并将妨碍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损及地区局势的安全稳定,不过在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之下,双方的合作又仅仅属于一种各取所需、相互利用的关系,因此难以朝着实质性同盟的方向发展。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的相关论述已经基本涉及了美越安全合作的动因、趋势以及限度等内容,这些分析对于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不过由于时效性等方面的原因,现有研究鲜有涉及“印太战略”背景下美越安全合作的最新进展,也难以体现“印太战略”对于双方安全关系发展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因此,本文将在系统梳理近年来美越安全合作中的标志性事件和实证性材料的基础上,对两国安全关系的发展进程展开一种长时段、多维度的阐释和分析,进而就其变化趋势、具体动因以及影响维度作出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期能够对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较有价值的参考。
二、冷战结束后美越安全合作的启动与发展
1975年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对越南实施了包括贸易禁运、经济封锁、武器禁售、旅行禁令等在内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两国关系因而长期处于停滞和相互隔离的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格局的终结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双方关系的调整与转圜提供了一个重大历史机遇。1995年7月,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越南政府总理武文杰(Vo Van Kiet)共同宣布了美越关系的正常化与外交关系的建立,这为此后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特别是由于南海地区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安全议题在美越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开始显现,双方高层均表达出推进双边安全合作的意愿,两国间的安全关系也随之朝着逐渐深入的方向发展。虽然受制于历史问题、意识形态、南海局势以及中美关系等因素的影响,美越之间的安全合作在双边关系正常化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取得重大进展,且一些合作项目的象征意义也明显大于实际意义,但是却为“印太战略”出台后双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作了重要铺垫。具体来看,双边关系正常化后美越两国之间开展的安全合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高层互访为纽带,安全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开始显现
2000年3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威廉·科恩(William S.Cohen)访问越南,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到访越南的美国国防部长。同年11月,克林顿也对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从而实现了越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对越南的首访。2003年11月,越南时任国防部长范文茶(Pham Van Tra)访问美国,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美的越南国防部长。2005年6月,越南时任总理潘文凯(Phan Van Khai)也访问美国,成为越战结束后到访美国的最高级别越南官员。上述一系列“首访”释放出两国高层致力于打破制约双边关系发展的历史桎梏的强烈信号,也为双方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创造了良好氛围。此后,通过密集的高层互访,美越两国领导人逐渐形成了推进双边安全合作的共识,安全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权重和地位也开始显现。比如2006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H.Rumsfeld)到访越南,并与越南方面探讨了加强两国防务合作的可能性。同年11月,美国时任总统布什出席了在河内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并到访越南。2009年12月,越南时任国防部长冯光青(Phung Quang Thanh)到访美国,双方围绕深化两军合作、扩大军售范围、南海争端与中国崛起等问题进行了交流。2010年10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借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之机到访越南,并与越方就加强两国安全合作、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等达成了一致。在该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Diane Rodham Clinton)先后两度访问越南,向越方表达了提升两国关系层次的意愿。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Leon Edward Panetta)到访越南军港金兰湾,成为越战结束后首位访问金兰湾的美国国防部长,此访也被视为美越军事合作全面升温的前奏。同年7月,希拉里再次到访越南,实现了其国务卿任内的第三次访越,进一步凸显了越南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2013年7月,越南时任国家主席张晋创(Truong Tan Sang)到访美国,与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共同表达了加强两国国防安全合作、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发展面向未来的双边关系的愿景,此访标志着两国“全面伙伴关系”的正式建立,也为此后的美越关系发展及双边合作提供了总体框架。2013年1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Forbes Kerry)到访越南,表达了对南海局势及中国在南海开展维权行动的“关切”,得到越方的积极回应。2014年8月,美国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Edward Dempsey)到访越南,实现了自1971年以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对越南的首访,双方不仅增加了对中国崛起与南海局势的关注,还寻求将海上安全合作打造为美越安全合作的重要领域。2015年5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访问越南,并与越方共同签署了《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从而使两国安全合作再次取得了较大突破。2016年5月,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亦到访越南,并与越南时任国家主席陈大光(Tran Dai Quang)等越方政要共同表达了推进美越国防安全合作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意愿。
(二)以军舰外交为主线,两国逐步开展了一系列的军事交流活动
2003年11月,美国海军“范德格里夫特”号导弹护卫舰抵达胡志明市,实现了越战结束后美国军舰对越南的首访。此后,美国海军舰只频繁到访越南港口,两国间军事互动水平也随之明显提升。2004年7月,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到访岘港,成为越战结束后美国军舰对岘港的首访。2005年3月,美国海军“加里”号导弹护卫舰到访胡志明市,“爱国者”号扫雷舰、“救援”号深海打捞与拯救舰则于2006年7月同时到访该市。2007年7月,美国海军“金熊”号训练舰到访了位于越南北部的海防港,两艘美国水雷战舰“爱国者”号和“保护者”号亦于同年11月到访该港。2008年10月,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到访越南。此后在2009年和2010年,越南军政官员先后受邀考察了停靠于越南外海的美国海军“约翰·斯坦尼斯”号和“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并观摩了上述两舰在南海的行动。2010年8月,在“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抵达越南外海的同时,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以“纪念美越关系正常化15周年”为名到访岘港,并与越南海军开展了所谓“非战斗演练”。2011年7月,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钟云”号、“普雷贝尔”号导弹驱逐舰及“哨兵”号救助船到访岘港,并与越南海军举行了交流活动。2012年4月,第七舰队旗舰“蓝岭”号、驱逐舰“查飞”号、救助船“哨兵”号到访岘港。2013年4月,“钟云”号导弹驱逐舰、“救援”号救援船到访岘港。2014年4月,“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哨兵”号救援船到访岘港,并与越南海军扫雷舰举行了搜救演习。2015年4月,“菲茨杰拉德”号导弹驱逐舰和“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到访岘港。2016年9月,“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再次到访岘港,并于同年10月与“弗兰克·凯布尔”号潜艇补给舰共同访问了金兰湾。在频繁开展军舰外交的同时,美越双方还通过各类多边军事演习加强了军事交流。比如2002年,越南首次作为观察员参加了美泰新“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2007和2008年,越南又连续两年派出观察员参加了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组织的海上合作战备和训练演习(Cooperation Afloat Readiness and Training, CARAT)。2012和2016年,越南还先后两次派出观察员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
(三)以武器禁运政策的解除为契机,两国开启了军武合作的进程
2006年12月,布什政府宣布取消对越南出售非杀伤性军用物资的禁令,意味着美国长期执行的对越武器禁运政策出现了松动迹象。2007年,美国又进而修改了武器贸易条例,允许视情况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性武器,标志着美越之间的军事互信得以初步建立。2014年10月,正值越南时任外长范平明(Pham Binh Minh)访美之际,美国宣布部分解除已经对越南实施数十年之久的武器销售禁令,“以帮助越南提高保障海上安全的能力”。2016年5月,奥巴马在访问越南期间正式宣布,美国将在武器出口“逐笔审议”的前提下全面解除对越南的武器销售禁令,这被视为美越安全关系发展历程当中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两国的军事互信水平和防务合作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武器禁运政策的解除,美国逐渐开启了对越军售、军事援助和军事技术合作的进程,而越南则出于改善本国防务状况的考量对美国的相关举措展现出积极态度,并同美方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军武合作。比如2008年4月,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越南邮政电信集团(VNPT)制造的通信卫星“越卫1号”(VINASAT-1)成功发射;2012年5月,该公司为越方制造的第二颗通信卫星“越卫2号”(VINASAT-2)亦发射成功。上述两颗卫星构成了越南卫星发展与应用体系的重要一环,对于维护其国家安全特别是军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2010年9月,美国国防部还表示将划拨专款,帮助越南升级一批老式的UH-1“休伊”直升机。2013年12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在访越期间进而宣布,美国将向越南提供1800万美元的援助,以“加强本区域的海事安全以及确保航行自由”。
(四)以双边和多边机制为依托,两国开展了安全政策协调和对话
在美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之间不仅建立起了双边安全政策协调和对话机制,还寻求利用各种多边平台讨论彼此关心的安全议题,为双方安全合作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制度支撑。就前者而言,早在2008年10月,美越两国即建立起部长级年度政治、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截至2016年8月,双方已利用该机制进行了8次对话;2010年8月,两国继而建立了副部长级年度国防政策对话机制,截至2016年10月,双方已利用该机制进行了7次对话。就后者而言,美越两国不仅致力于通过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东盟机制加强彼此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协调,而且积极寻求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等多边机制框架下开展政策对话。值得注意的是,伴随南海地区局势的逐渐升温和中国崛起进程的持续加快,特别是针对中国南海维权行动和岛礁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涉及中国崛起和南海局势的相关议题开始逐渐成为美越两国利用双边或多边机制协调彼此安全政策时的重点关切。比如在2010年7月举行的第17届东盟地区论坛上,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越南就曾竭力推动将南海问题纳入论坛议程,而与会的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借机针对该问题表达了立场,声称“与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在航行自由问题、对亚洲海洋公域的准入、在南海地区尊重国际法等方面拥有国家利益”。此外在2010年8月举行的首次国防政策对话会上,美越双方也专门围绕所谓“中国军事现代化问题”交换了意见。而在2013年10月举行的第4次国防政策对话会上,双方进而表达了“在尊重国际法原则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东亚和东南亚各国之间海上领土主权争端”的共同立场,并表示希望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尽快签署“南海行为准则”。2016年8月,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不久举行的第8次政治、安全与防务对话上,美越双方又继续针对南海局势、《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及其相关条文的适用性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三、特朗普政府时期美越安全合作的新进展
以美越双边关系正常化后逐步开展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为基础,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伊始,越南即表现出进一步强化美越安全关系、深化两国防务合作的政策意愿。2017年5月,越南时任政府总理阮春福(Nguyen Xuan Phuc)访问美国,成为特朗普上任总统后首位访美的东盟国家领导人;同年8月,越南时任国防部长吴春历(Ngo Xuan Lich)也正式访问了美国。这些访问释放出越南希望深化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积极参与美国对外战略布局的信号,也为美越安全关系的继续深入发展创造了条件。伴随“印太战略”的出台,美国领导人多次到访越南或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东盟防长扩大会议等国际场合与越方领导人会晤,向越南方面宣传、解释“印太战略”的具体内涵与核心概念,并就“印太战略”下美越开展安全合作的具体事项深入交换意见,得到了越南领导层的积极响应。在此背景下,美越两国愈益重视并加快推动双方在军事和安全合作领域取得更大的实质性进展,开始将美国航母访问越南、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等重要事项提上了双方关系的议程,使得美越安全关系实现了诸多历史性的突破。具体而言,特朗普政府时期美越之间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在以下几方面呈现一些突出的进展:
(一)在频繁的高层互动中愈发凸显安全合作议题
在2017年5月阮春福访美时与美方发布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共同表达了在2011年《防务合作备忘录》、2015年《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防务合作的意愿,越南希望从美国获得包括“汉密尔顿”级海岸警卫队巡逻舰在内的更多武器装备,以增强其国防实力和海上执法能力,同时双方还探讨了美国航母访问越南港口的可能性以及深化美越海军合作的相关事宜,并强调两国将在南海问题上加强协调与合作。在2017年8月吴春历访美时,亦与马蒂斯共同表达了加强美越国防合作特别是海上安全合作的愿望,进一步明确美国航母会在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访问越南,并再次重申两国将就南海“航行自由”加强合作。特别是在2017年11月特朗普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后与越南时任国家主席陈大光的会晤中,双方又进一步商定了旨在加强两国防务关系的《防务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从而为今后的美越安全合作确立了更为清晰的框架。2018年1月,马蒂斯正式访问越南,除高调宣布“卡尔·文森”号航母将于同年3月访问越南岘港外,还重点向越南政要介绍了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概要》的相关内容以及该报告对于越南的战略定位。2018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首访越南,这成为其东南亚之行的第一站。2018年10月,马蒂斯再次对越南进行了工作访问,这也是美国国防部长一年内对越南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在美越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前所未有,很大程度上凸显了越南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2019年11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 Esper)亦首访越南,与越方领导人共同探讨了美越安全合作的现状,并再次呼吁双方持续推进《防务合作备忘录》《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防务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的各项防务合作内容。2020年5月,阮春福与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对于美越两国在政治、外交、国防安全、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的合作进展表示肯定,并一致同意以建交2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国的全面合作关系。2020年10月,蓬佩奥以“纪念越美建交25周年”为名再次到访越南,并分别与阮春福、范平明等举行了会谈。2020年11月,美国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到访越南,在与阮春福、范平明、吴春历等越方政要举行会谈后,奥布莱恩宣称“越美关系‘非常牢固’,并且今后‘只会更加牢固’”。可见,在特朗普政府高调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下,美越关系不仅通过密集的高层互动实现了迅速升温,而且进一步凸显了双边安全合作的重要地位。
(二)显著加大了对越武器销售和军事援助的力度
基于加快推进“印太战略”实施的政策考量,在奥巴马政府全面解除对越武器禁运的基础上,特朗普政府显著加大了对越军售和军援的力度,并积极通过直接商业销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s, DCS)和外国军事融资计划(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 FMF)等渠道为越南的国防建设提供武器装备和资金支持。来自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示,在2015~2019财年间,美国国务院授权通过直接商业销售方式向越南出售了价值达5286万美元的军事装备;与此同时,在2016~2019财年间,越南还通过美国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获得了后者提供的超过1.5亿美元的各类安全援助。2017年5月,美国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将退役的“汉密尔顿”级海岸警卫队巡逻舰“摩根索”号无偿移交给越南,该巡逻舰已经成为当前越南海岸警卫队编制中吨位最大的执法船。2019年11月,埃斯珀在访问越南时又宣布,美国将把第二艘“汉密尔顿”级巡逻舰移交越南,以“增强越南的海上执法和搜救能力”。此外,美国还通过外国军事融资计划出资采购了24艘“金属鲨鱼”型快速巡逻艇,其中18艘已于2019年4月前交付越南,最后6艘也于2020年5月正式交付。2019年5月,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向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四国出售总价值达4793万美元的34架“扫描鹰”(Scan Eagle)无人机,越南将获得其中的6架。除不断加大对越军售力度外,近年来特朗普政府还通过其他一些形式为越南的国防力量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样来自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数据显示,在2016~2020财年间,越南方面通过美国东南亚海事安全倡议(SAMSI)下属的外国军事融资账户获得了2000万美元的资金,美国国防部还通过印度洋-太平洋海事安全倡议向越南提供了约1000万美元的额外援助,以帮助越南增强所谓的“海域态势感知能力”。
(三)积极致力于开展各类实质性的军事交流活动
在近年来的美越安全关系发展进程中,以军事外交和联合军演为主要形式的实质性军事交流活动的重要性迅速上升,使得美越两国的安全合作取得了堪称历史性的突破。在军事外交层面,由美国海军“科罗纳多”号濒海战斗舰、“救援”号救援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于2017年7月实现了对金兰湾的访问。不过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下,双方显然已经不再满足于以美国海军驱逐舰、护卫舰等访问越南港口为主要形式的“军舰外交”,而是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美国航母访问越南的计划。在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下,由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尚普兰湖”号导弹巡洋舰、“韦恩·梅耶”号导弹驱逐舰组成的舰艇编队于2018年3月5日抵达岘港,对越南进行了为期4天的访问。由于此次交流是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首次访问越南,因此对于美越安全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而且在2020年3月5日,美国海军“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邦克山”号导弹巡洋舰又再次到访了越南岘港。与此同时,美越双方还积极借助环太平洋军事演习、“海猫”多国联合军事演习、东盟-美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ASEAN-U.S.Maritime Exercise, AUMX)等开展了一系列实质性的军事交流活动。比如在先后两次派出观察员进行观摩之后,越南于2018年首次受邀参加了环太平洋军事演习,这成为美越安全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历史性突破。2019年8月,越南还受邀参加了由美国主导的“海猫”多国联合军演,美方则派出了海军第7驱逐舰中队、P-8A 反潜巡逻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参加了此次演习。2019年9月,东盟-美国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在泰国湾海域举行,作为双方开展的首次联合军演,包括越南在内的所有东盟国家均参与其中。
(四)充分利用各种机制加强安全对话和政策协调
越南驻美大使何金玉(Ha Kim Ngoc)认为,越美两国的防务合作不仅限于双边合作,而且包括多边合作,双方应在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美国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香格里拉对话会议等多边机制中保持协调配合。在“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下,近年来美越双方均充分利用了此前建立起的部长级年度政治、安全与防务对话机制和副部长级年度国防政策对话机制,进一步加强了彼此间的安全对话和政策协调。比如在2017年的国防政策对话会上,双方一致同意将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作为推进两国安全合作的切入点。而在2018年的国防政策对话会上,又进一步明确了两国在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联合国维和行动、灾难救助等方面的防务合作计划,并同意在2020年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继续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协调配合。在2019年的政治、安全与防务对话会上,双方也一致肯定两国关系及现有合作的进展,并进一步加强了在南海问题、防务合作、解决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等方面的立场协调。而在2020年以视频形式召开的国防政策对话会上,双方继而一致同意继续加强两国的防务及海事安全合作。与此同时,两国还充分利用了各种多边机制和对话平台加强彼此在防务和安全领域的政策协调。比如在2017年第16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马蒂斯利用南海问题攻击中国,其污蔑中国为“南海国际规范和亚太地区秩序的威胁”的论调得到越南方面的积极支持,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越南代表团团长、越南国防部国防战略研究院院长阮德海中将表示,美国与东盟各国已就地区安全重要问题达成共识,东盟高度评价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在2018年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吴春历又专门与马蒂斯举行了会谈,进一步明确两国将加大在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合作力度。而在2019年第18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吴春历还与时任美国代理国防部长帕特里克·沙纳汉(Patrick Shanahan)举行了会谈,并就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中的相关重要事项达成了广泛共识。除此之外,近年来两国还充分利用东盟国防部长扩大会议、美国与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多边平台加强安全对话,从而推进了双方安全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特别是在2020年9月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上,蓬佩奥不仅利用南海问题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还敦促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此举得到越南方面的积极回应,声称“东南亚国家希望美国在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中发挥作用”。
四、印太战略下美越加强安全合作动因解析
如前所述,自双边关系正常化以来,美越两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处于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之中。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进“印太战略”的背景之下,美国希望将越南打造为其战略布局中的关键合作伙伴,越南则对此表现出积极的欢迎态度,并主动寻求与美国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合作。总的来看,美越安全关系的质量与水平在“印太战略”出台后的短时间内已经实现了显著提升,两国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所开展的相关合作项目也较以往更加富有实质性。如果从当前国际战略形势的突出变化、美国“印太战略”文件的相关表述以及美越两国对海上安全合作的高度重视等多个视角进行分析的话,不难发现对于中国崛起的共同关切以及在南海争端中的利益契合,构成了双方进一步加强军事和安全合作的根本驱动因素。换句话说,对于中国崛起的共同忧虑为美越安全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因,而南海问题又成为其中重要的利益契合点,正是这两大因素的相互叠加,使得美越安全合作不断深入发展。
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曾经借助“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揭示了中美两国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并认为这种因国家实力变动导致的矛盾将会成为中美冲突的根源。同样,对于“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关系发展变化的分析,也应当根植于中美结构性矛盾的理解和把握,因为对于美国而言,正是中国的崛起挑战了它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在它看来,伴随中国实力的持续累积,亚太地区秩序将有可能不再为美国所主导,因此必然会对中国的崛起持抵制态度,也必然会采取各种手段阻止中国的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印太战略”无非是特朗普政府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下所推出的旨在遏制中国的一个战略。正如其《印太战略报告》所宣称的,美国将通过做好准备(preparedness)、加强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和促进区域网络化(promotion of a networked region),全面整合印太地区战略资源,不断深化与越南等国的安全关系,持续推进南海“航行自由”行动(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以达到联合相关国家共同遏制中国的目的。
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同,越南对于中国崛起所表现出来的担忧,主要是集中在南海问题上。长期以来,越南借助地缘优势侵占了大量南海岛礁,成为在南海争端当中侵占岛礁与海域最多的国家。除非法占据了29个南沙岛礁之外,越南还对整个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提出了所谓“主权诉求”,并以此为基础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为本国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虽然由于海上行动能力的局限,中国曾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无法有效制止越南在南海地区的扩张行径,但是随着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目前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力量和执法力量都得到了显著增强,海上维权的力度也正处于持续加大之中,这就使得越南长期所奉行的南海扩张策略已经难以为继。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近年来越南进行了相关政策的调整,一方面积极谋求美、日、印等域外国家的介入,以此增加本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政治筹码,另一方面则主动寻求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以此提升国防实力,缓解本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军事压力。
关于美国强化与越南安全关系的战略意图,一些美国学者主要是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量,将美越关系视为东南亚战略的理想切入点,认为美国可将“印太战略”的基本原则与越南在南海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联系起来,通过强化双方的安全合作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实际上在“印太战略”之下,美国政府之所以选择将越南作为理想的合作伙伴,不断加强和提升与越南的安全关系,除了上述遏制中国崛起的根本考量之外,还是对中越关系发展现状、东南亚地缘战略形势以及越南经济社会需求等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的结果。
首先,冷战后中越两国关系发展并不顺畅,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矛盾重重。熟悉中越关系史的人们都知道,早在1988年时,两国就曾因为南海问题爆发过“3·14”海战(又称南沙海战、赤瓜礁海战)。到了2014年5月初,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所属的“海洋石油981”深水钻井平台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开展钻探作业时,遭到越南方面的强力阻挠,期间越南政府还纵容其国内发生的反华游行示威,导致数千名不法分子对中国企业进行了严重的打砸抢烧,使得在越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遭受严重威胁。而在2019年下半年,双方船只又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发生了激烈对峙,使得中越两国关系再度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作为南海扩张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越南长期获益于非法开发南海海洋资源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因此面对近年来中国逐步加强在南海地区开展岛礁建设、资源开发和海上维权行动,越南表现出了强硬对抗的姿态,除直接与中方船只进行海上对峙外,还频频借助“南海问题国际化策略”弥补本国在海上力量方面的相对弱势。对于美国而言,在中越南海争端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利用中越关系矛盾加强美越安全合作便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其次,借“南海仲裁案”搅乱南海局势的企图未果,美国希望以越南取而代之。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上台后,基本放弃了阿基诺三世(Benigno Simeon Cojuangco Aquino III)政府时期“联美抗华”的对外政策,通过主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中美之间开展了近乎平衡的“等距离外交”。上台伊始,杜特尔特便明确否定了借助“南海仲裁案”对华施压的可能性,甚至表示执行该仲裁决定“可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任外交部长小佩尔费克多·亚赛(Perfecto Yasay Jr.)也曾明确表示,不论“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如何,菲律宾政府都不会发表挑衅性的声明。在此基础上,杜特尔特政府坚持“不在东盟讨论仲裁裁决”的立场,实际上是将“仲裁案”移出了菲律宾的对外政策议程,这就使得美国希望借此搅乱南海局势的企图已然无法实现。特别是在双边关系层面,虽然杜特尔特政府对于1998年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从2020年2月“威胁终止”经历了三次“暂停终止”后最终还是于2021年7月确认“放弃终止”,但围绕该协议所产生的龃龉毕竟对美菲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并且对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部署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短期内菲律宾显然已经难以成为美国搅动南海局势的有力帮手,而加强和提升与越南的安全关系则因此成为了一个最佳替代之选。
最后,加强与越南之间的安全合作,能够为美国带来极为可观的军火收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生产的武器装备出现质量下降甚至“供不应求”的状况,因此越南开始积极拓展武器进口的渠道,并逐步加大了从美国购买武器装备的力度。实际上,近年来越南之所以主动寻求与美国开展安全合作,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希望从美国获取更多的军事装备,以增强本国的国防能力和海上行动能力,增加在南海争端中与中国对抗的资本。2016年5月,奥巴马宣布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销售禁令的决定得到越方政要的热烈欢迎,而阮春福在2017年5月访美时,也向美方领导人表达了采购更多美国武器装备的意愿。就近几年的情况看,特朗普政府已经通过直接商业销售和外国军事融资计划等多种渠道,为越南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显然,对于积极推进“印太战略”的美国而言,不断强化与越南之间的安全合作,无疑会为美国的军火生产商创造更多来自越南的采购订单,而且两国的武器交易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也将会帮助美国军火商在东南亚地区占领更为庞大的军火市场。
对于越南选择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会是奇怪和不解,因为当年美国发动的战争毕竟是给越南造成了巨大的创伤。时至今日,那场战争依然是许多越南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越南社会也依然遭受着各种战争遗留问题的折磨。但是,近年来越南却在着力开展与昔日敌人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并积极寻求在美国“印太战略”实施中进一步提升两国安全合作的水平。就目前的情况看,在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联动效应”之下,越南之所以选择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主要是与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考量密切相关:
其一,维护在南海地区所获取的现实利益,是越南寻求加强美越安全合作的首要动机。多年以来,除非法占据大量南海岛礁外,越南还不顾中国反对,广泛招揽外国石油公司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据统计,越南在南海开展的这种“盗油抢气”行为已成为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支柱,“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0%,不仅使其赚取了大笔外汇,也支撑着其每年7%的GDP增长”,其中在2006~2015年间,仅越南国家油气集团(PVN)便为其国家财政提供了20%~25%的年均贡献率。特别是近几年来,由于其近海区块的油气资源呈现枯竭趋势,越南又进而加大了在“九段线”以内海域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的力度。但是随着中国军事力量和海上执法力量的增强,越南长期所奉行的凭借有利地理位置抢先占领南海岛礁、抢先开采南海资源的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其在南海地区的所谓地缘优势也正在逐渐消失。特别是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概念和“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目标之后,中国积极开启了践行“海洋强国战略”的步伐,并且进一步加强了海上执法力量建设和岛礁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综合国力、军事实力处于弱势地位的越南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其国内甚至出现了“一旦中国的实力足够强大,必然会以军事手段一一收回被越南非法侵占的南海岛礁”的广泛忧虑。在此背景下,维持对南海相关岛礁的非法占据,延续对南海海洋资源的非法开发,显然成为越南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特别是在美国大力推进“印太战略”的新形势下,作为“安全寻求者”(Security Seeker)的越南有着充分的理由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以求增强本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政治筹码和对抗实力。
其二,通过强化美越安全关系,试图弥补东盟各国在南海争端中“共同立场”的缺乏。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各声索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原本应在双边外交的框架下协商解决,但是包括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往往倾向于将东盟作为本国在南海争端中的“保护伞”,并热衷于推动东盟成员国形成关于南海问题的所谓“共同立场”。不过,并非所有的东盟成员国都与中国存在海洋争端,它们对于南海问题的是非曲直也不可能持有完全相同的立场,更何况这些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也有着“远近亲疏”的差异。在2012年7月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上,主办国柬埔寨就曾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致使此次会议最终没有发表联合声明,这在东盟历史上尚属首次。尽管在此次会议后,被视为东盟“领头羊”和“天然领导者”的印度尼西亚在各成员国间展开了积极的“穿梭外交”,并通过指导东盟解决南海问题的“六点原则”缓解了东盟国家间的立场分歧,但这一事件的发生毕竟已经凸显出南海问题当事方与非当事方达成所谓“共同立场”的难点之所在。另外,在杜特尔特政府成立后,原本在南海争端中持激进立场的菲律宾也进行了对华政策调整,因“南海仲裁案”而陷入低谷的中菲关系逐渐得到改善,两国已于2017年5月正式建立起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标志着中菲之间的南海争议又回到了双边磋商的轨道。特别是近些年以来,秉持“亲、诚、惠、容”理念的中国周边外交正在迅速推进,坚持“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加快落实,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已经得到了显著提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中,包括南海声索国在内的东盟国家相较以往更愿意倾听中国的声音,东盟各国就南海问题形成所谓“共同立场”的可能性也在更趋减小。在这种情况之下,越南显然更希望借助美越安全关系的强化,弥补东盟在南海争端中“共同立场”的缺乏。
其三,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还可以换取美方对于战争遗留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在越南战争中,美军曾广泛使用落叶剂等化学武器,由此造成的二恶英污染使大批越南民众深受其害,不少人一直饱受遗传病的折磨,此外战争遗留的未爆炸弹药也持续困扰着越南社会。据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越南人被美军投放的二恶英橙剂毒害,数十万越南民众因战争遗留的爆炸物而伤亡。但是,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相关治理项目的施工周期也都比较长,比如仅对越南岘港国际机场32.4公顷的落叶剂污染土地进行的综合治理,即已耗时6年、耗资1.1亿美元;而越南边和机场二恶英污染治理工程(一期)项目,则预计需要耗时10年、耗资3.9亿美元。在此情形下,财政状况不佳、技术力量有限的越南希望通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提高它对越南战争遗留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解决力度,促使它为受害者提供更多的战争补偿,这也构成了其选择强化与美国安全关系的原因之一。
五、美越安全合作持续强化的影响及其评估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印太战略”下的美越安全关系主要是一种围绕东亚地缘政治形势变化而形成的相互利用关系,还远未达到军事同盟关系的标准或者程度。除了《防务合作备忘录》《防务关系联合愿景声明》《防务合作行动计划(2018-2020)》等具体的防务合作指导性文件外,美越两国至今并未签署任何带有同盟条约性质的政治文件。而在国防部出台的《印太战略报告》中,美国也仅是将越南定位为“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伙伴”,并没有表现出要将美越关系提升为双边军事同盟关系的意愿。另外根据2019年越南《国防白皮书》的表述,迄今越南依然坚持不参加军事联盟、不允许外国在越建立军事基地的原则,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美越安全关系未来发展的限度。不过,在“印太战略”加快实施的大背景下,美越之间的安全合作毕竟已经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必然会对南海地区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冲击,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和对外政策选择。具体而言,“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合作的持续强化至少会对中国产生以下几方面的负面影响:
(一)不利于“南海行为准则”的最终达成
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同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明确了在各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制定“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目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坚持将DOC精神作为管控南海争端的可行之道,在坚定维护本国海洋权益的同时,努力维持地区局势的和平稳定,并通过持续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域内国家的政治互信水平,致力于“把南海建设成为造福地区各国的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南海地区局势已经实现了总体稳定,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相继建立起海上问题双边磋商机制,与文莱之间也就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达成了重要共识。特别是COC谈判现已取得关键进展,“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的第一轮审读已经提前完成,这就为南海问题的疏解和管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伴随“印太战略”的加速推进,美国更加重视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争端,不仅继续强化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而且显著增加了在南海海域进行所谓“航行自由”行动的次数。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全面加强了与越南在武器援助、军舰外交、联合军演、安全对话等方面的防务合作,不断鼓动越南在南海挑起针对中国的单边行动,支持越南以强硬手段对抗中国的海洋维权与海上执法。越南则展现出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姿态,除两度邀请美国航母访问本国港口外,还公开通过外交渠道表达了对美国在南海海域开展“航行自由”行动的欢迎。可以预见,美越安全关系的发展必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南海问题磋商和谈判进程产生严重干扰,而且在这种“示范作用”影响之下,也不排除在南海声索国之间形成所谓的“连锁效应”,为“南海行为准则”的最终达成设置一些新的障碍。
(二)不利于我国南海海洋权益的有效维护
2018年10月召开的越共十二届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至2030年越南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及2045年展望”的36-NQ/TW号决议,强调越南不仅要继续“坚决、坚持不懈地捍卫国家主权和海上合法权益”,还要在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文化培育、海洋生态保护、海洋污染治理等多个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以确保其能够通过海洋强国战略成为“靠海致富、可持续发展、繁荣和安全的国家”。以此为指导,越南国家油气集团进而制定了在2019年和2020年各增加1500万吨石油储量的计划。鉴于近年来越南近海的油气资源已出现枯竭势头,因此完成相关石油增产计划的关键,就是要在“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寻找更多可供长期开采的油气田。不过这种做法必定会损及中越关系的大局,妨害两国既有的合作进程,更何况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海空军事力量和海上执法力量,越南的谋求也将很难有效落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关系的不断强化,美国为越南“撑腰打气”的做法又无疑会刺激越南在南海争端中的战略野心和对决心态,而且极容易使其出现战略误判,进而在南海地区采取更为激进的对抗行动。在2019年下半年发生的万安滩事件中,越南方面就已展现出强硬对抗的姿态,除广泛调集船只与中国对峙外,还高调宣布延长在万安滩海域部署的“白龙5号”(Hakuryu-5)钻井平台的工作时间。甚至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亦就此公开表态,“凡是涉及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事情,我们决不能做任何让步”。与此同时,越南官方还鼓励本国渔民挑战中方制定的“南海伏季休渔制度”,并公开支持他们进入“九段线”以内海域进行捕捞作业。可以想见,伴随美越安全关系的强化,今后越南将有可能会在“九段线”以内海域冒险推动相关的资源开发计划,并继续通过海军、海警、海上民兵、武装渔船等阻挠中国的海上维权行动;另外越南也极有可能会对中国在相关海域的油气勘探和渔业活动进行阻挠,并不惜再次与中国发生舰船对峙和海上冲突。在此情势下,中国在南海开展维权行动的难度和成本肯定会明显提高,南海海洋权益甚至可能再次面临被进一步侵蚀的风险。
(三)不利于南海地区局势的长期和平稳定
毋庸讳言,“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合作的持续强化,已经向外界释放出了以下五种非常明确的信号:其一,美国坚持将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战略抓手”,因此当前南海局势的“降温”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二,美国致力于寻求将越南打造为加快实施“印太战略”的“新帮手”以及它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的“代理人”;其三,美国将持续加大以军事力量介入南海争端的力度,并充分利用美越双边安全合作以及在南海海域的“航行自由”行动为越南站台,试图在该地区挑起中越两国的矛盾和冲突;其四,越南无意在DOC框架下以双边谈判的形式和平解决南海问题,也并不乐见COC的最终达成,相反它更倾向于在南海争端中“联美制华”,并热衷于借助域外大国的支持采取单边行动谋取现实利益;其五,未来美国将越发借重与越南的安全合作,加快在该地区军事渗透的步伐,而且极有可能会寻机提出在越设置军事设施、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向,美军重返金兰湾的问题也可能再次被提上美越两国关系的议程。显然,上述这些信号不仅会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和地缘政治风险,也将在根本上不利于南海地区局势的长期和平稳定。
六、结语
在美国的强力推动和越南的积极配合下,近年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双方谋求在南海问题上共同牵制中国的互动模式也已然初步成型,这就使得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一种新的严峻考验。特别是在“印太战略”加快实施的背景下,美越两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呈现持续加强的态势,双方安全关系的不断深化无疑会对南海地区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2020年是美越关系正常化25周年,而且正值越南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年份,这既为美越双边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契机,也在客观上为美越两国共同针对中国发起某种直接而且重大的挑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在2020年6月越南以轮值主席国身份组织召开的第36届东盟峰会的主席声明中,涉及南海问题的相关内容不出意外占据了相当篇幅,其中不仅继续表达了对于中国在南海开展的岛礁建设活动的所谓“关切”,而且进一步强调了“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体现出与美国“印太战略”理念较高的契合度。2020年7月,美国国务院发布题为《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海事索求的立场》的声明,公然宣称中国“对南中国海大多数地区离岸资源的索求完全不合法,与其为控制这些资源采取的霸道行为如出一辙”,而美国将“支持我们的东南亚盟国和伙伴保护各自对离岸资源拥有的主权,尊重他们根据国际法拥有的权利和义务”“支持国际社会捍卫海上自由和尊重主权,拒不接受在南中国海或更广泛的地区推行‘强权即公理’的任何行为”。针对上述声明,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公开回应,“越方欢迎各国在东海问题上符合国际法的立场”,并“希望各国为维护东海和平、稳定与合作,根据国际法通过对话和其他和平措施解决争端作出努力和贡献”。这些措辞不仅反映出美越两国利用南海问题共同针对中国的政治图谋,也在客观上为继续推进美越安全合作提供了新的话语体系。
必须承认,“印太战略”下美越安全关系的发展是双方“互取战略所需”的结果,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国对于中国崛起的共同关切乃至联合应对。可以想见,在中国崛起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之下,美越之间的安全合作也将朝着更加“常态化”的方向发展,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将不得不需要统筹应对来自美越两国的共同挑战。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尽管拜登上任之后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南中国海政策尚未完全明晰,但它显然并未改变对华战略竞争的既有方向,也未放弃以“印太架构”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路径。实际上,从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2021年4月通过所谓《战略竞争法案》以及商业、科学和运输委员会2021年5月通过所谓《无尽前沿法案》等一系列动作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态势极有可能会不断延续甚至进一步拓展。与此相适应,在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久,越南政府副总理范平明便于2021年2月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通电话,双方共同表达了在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推进两国全方位务实合作的意愿。考虑到特朗普政府竭力推进“印太战略”而造成的强大“惯性”,今后美越两国进一步加强安全合作肯定会成为大势所趋,特别是在中美关系仍旧缺乏转圜迹象的情势下,美越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对抗中国的可能性也将有增无减,这毫无疑问会对该地区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注释:
①参见:《美国助理国务卿: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结束》(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7_03_15_398864.shtml)。
②参见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APEC CEO Summit/Da Nang,Vietnam(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apec-ceo-summit-da-nang-vietnam/)。
③参见The White House: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④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⑤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preparedness,partnerships,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⑥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1/Free-and-Open-Indo-Pacif-ic-4Nov2019.pdf)。
⑦参见The RAND Corporat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Asia:toward a new U.S.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https://www.rand.org/pubs/monograph_reports/MR1315.html#download)。
⑧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2010(https://archive.defense.gov/qdr/QDR%20as%20of%2029JAN10%201600.pdf)。
⑨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2014(https://archive.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⑩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U.S.Relations with Vietnam(http://www.state.gov/u-s-relations-with-vietn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