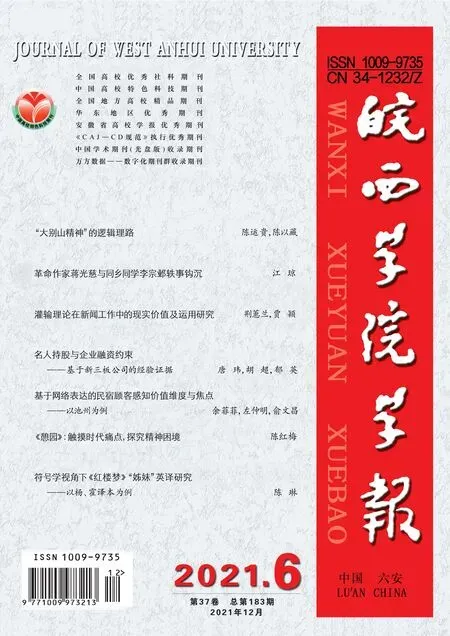明代以来皖西地区的健讼风习与应对
关传友
(皖西学院 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安徽 六安 237012)
健讼风习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皖西地区亦不例外。由于长期遭受南北方政权争战的影响,皖西地区在明代以后,此风习才逐渐出现并形成,成为皖西地方社会问题。学者对此关注不够,仅陈业新先生对明清皖北地区的健讼风习进行了探讨,涉及皖西地区的寿州及霍邱县[1]。故作者在前人时贤基础上对此问题进行考察。
一、皖西地区健讼风习的历程
历经元末战争摧残之后明代前期的皖西社会,处于一个相对较为稳定发展的环境和状态。“其民淳朴,安于稼穑”“民力耕桑,士敦礼义”[2](P513)“土地沃饶,稻粱价贱,乡闾无游堕之民,邻里有周卹之义”[3](P13)这种士事诗书而敦礼义、民安稼穑的淳质简约社会,则正是明朝统治者所“刻意追求的‘国治民安’的理想而和谐的社会发展模式”[4]。
自明代中期始,皖西地区健讼之风兴起。据地方志记载皖西地方健讼始于明弘治年间。霍邱县为古蓼城之地,“界颍寿之间,为中都钜邑,夙号殷富”[5](P439)。到弘治年间,“霍民性好讼”[5](P435)。隆庆间,出现了“民瘠且偷,称难治焉”“俗好讼讦,吏缘为奸”[5](P439)。至万历后期,“霍讼充栋,上下缘为利孔,以故逮系旁午,黑衣载道,城野骚然,霍邑大蠹也。”[5](P445)可见霍邱县民在弘治时期就好讼成性。明中期以前,六安州人耻于角讼。明隆庆五年(1571)任合肥邑令胡时化所云:“庐之风俗视昔悬殊。昔以淳朴,今以浮靡;昔以务本,今以逐末;昔以力学,今以嚣讼。”[2](P513)当时六安州属庐州府,说明此时六安州健讼风习已经出现。到万历年间,“六僻在山陬,民蠢而尚气,蠢则听人唆使,尚气则惯兴鼠雀。”[6](卷二,P410)明正德八年(1513),福建莆田人林僖知寿州,“禁戢凶轨及健讼无赖者,善类以安。”[3](P90)明万历年间,霍山县已是“健讼成业”[7](卷三,P46)由上所引可见,明中后期皖西地区各州县已经盛行健讼之风。
清代则健讼之风更为日炽。康熙时六安就有“六民骄惰浮靡,往往健讼”之说[6](卷二,P331)。清初,舒城县“南山民富而尚气,片语不合,辄兴讼。”[8](卷十四,P7)虽经数代官员教化,乾隆时霍邱县仍有“霍俗素以多讼称刁”之称[9](P117)。清康熙时舒城知县沈以栻曾发布息讼以正风俗告示,同治时六安州知州李峻发布《劝民息讼示》,当是应对健讼而采取的举措。
民国时期皖西地区健讼风习丝毫未息,民国十一年(1922)舒城县知事鲍庚在给安徽省省长呈文称健讼是舒城县的“三害”之一,“舒邑西南好讼,东北乡讼案亦在不少。乡愚无知者多,不识字者尤多,一朝之忿,争讼遂起,而理解既未了然,讼词尤难执笔。于是附近讼师,乃为之多方划策,词状未递之前,必预筹数十金,乃至数百金之费用。盖讼师之作词有费,膳宿有费,车马有费,酬应有费。讼而胜,则报酬有费;讼而败,则上诉又有费。一案之起,中人之家,即缘之以倾,且有典宅、鬻妻子,以靳最后之胜利者。法庭之上,两造身后,有怀挟证据,交头接耳,其影憧憧者,皆此类也。问官见其情节较轻,婉言劝息讼,两造必皆商承于讼师而后可。有两造均愿息讼,而讼师不可者;且有两造拖累既久,泥首讼师之前,求和而不得者。舒城一邑,每年倾家于讼师之手者,不知若干。”[10](P653)霍邱县人好讼在淮河南北地区独占第一位,“据以前凤阳高等法院统计,该院经办案件,其中百分七十以上属于霍邱。如霍邱县城简陋荒凉,只及江南一小镇,而城内旅馆,且有七八间,此皆为乡农入城打官司而设。”[11](P13)
二、皖西地区健讼的主要内容
皖西地方社会争讼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土地争讼
历史上皖西地方社会的争讼大多是因田土山场之争而引发的。
霍邱县南一百里有罗汉寺,分东西两廊,西廊僧不守清规被驱逐。生员裴潜修等因所施寺田讦控,乾隆十八年(1753)经知县张海讯明,将生员裴潜修施田二十二石、监生刘世杰施田二十四石,并胡宗孟占田十六石,勘清界址,归寺香火,详宪批允,勒石立案[5](P72)。
寿州城外尉升湖(又名西湖)是清代寿州驻军与凤台县民樵牧之地,因界址不清,兵民常因争牧地而“频年结讼”。自嘉庆十一年(1806)后,兵民互争牧地之讼连年不断,屡行禀控于上台[12](P43)。最后经两江总督派员实地勘察划界后才结束讼案。清咸同年间因抗击太平军、捻军对霍山地方的袭扰,西乡保绅组织团练自卫,为抚恤阵亡乡勇,经朝廷批准西乡九保佃农拥有“永不转庄”的永佃权。民国十一年(1922)霍山县西乡九保(今属金寨县燕子河、长岭等乡镇)佃农因地主转庄夺佃、加租加贷而引起争讼,霍山县知事陈判定九保农民拥有永佃权[13](P792)。
皖西山区众多山场也时常引起争讼。明季六安州齐头山下有古刹水晶庵(今属金寨县麻埠镇所辖),是宝志公香火地。庵有四僧“居之以好讼为能,因羡贡生周姓者山多而利广与之邻,遂掘残碑指皆宝志遗业,往投桐之吴绅奉为山主。致书当道,判归僧有。僧亦不善其终,传之徒嗣借梵宫为垄断。方春茶盛,估客盈门,赀获无算。吴绅之裔日来需索,与髠讼。山寺之可鄙者莫若此也。”[6](卷二,P450)很明显是寺僧为贪山场之利,借端构讼。民国六年(1917),英山县段翰卿等段氏族人以“天下名胜寺宇类多供奉先贤,先贤之后裔皆可认为私产”①为名,通过时任北京国民政府督办边防事务处督办段祺瑞向安徽省政府构讼,欲占有响山寺的田地山场。经六安县知事李楚铭与原、被告两造及地方士绅现场勘查后,判定田地山场为响山寺所有②。
(二)水利争讼
水利纷争是皖西地方社会争讼的主要内容之一。明嘉靖《寿州志》载:“芍陂,州南六十里安丰故县。楚相孙叔敖所作,溉田四百余顷。明正统以来,六有奸民辄截上流利己,陂流遂淤。成化间,巡按御史魏章得其状惩之,委任指挥戈都董治尽逐侵者。未几代去,顽民董玄等复占如故,后知州刘概指挥戈都奏行勘问,令同知董豫修复、巡按都御史李昂,檄指挥胡、六安指挥陈钊会勘,参考古典,指点旧迹,众皆输服。凡朱灰塘埧五道开其三,李子湾埧四道开其二,案存各司。惜乎自是以后,典守日疏,法制日弛,顽民占种日增,于前民益告病。”[3](P18)是上游截水引发的水利争讼。嘉庆间的六安南乡《韩陈堰使水碑记》则称:“自乾隆四年,派夫出费重修。凡有水分之家,印册存案,并赤契注明韩陈堰使水字样。其堰上流不得打坝,无水分者,不准使水,历年无异。突今四月,有朱谋贤、许明乐、蒋启盛并无水分,恃强打坝,经堰头秦隆山、周维其具禀差押毁坝,谋贤等屡抗不遵,复经乡地原差具禀移送军主讯究,谋贤自知情亏,愿具永不打坝切结,恳免究惩。”[6](卷一,P106)是因干旱争水而引起的水事诉讼纠纷。筑堤防洪也引发诉讼。据金陵大学森林系教授、美国人罗德民所称,淠河下游寿县距六安县五十里处(约在今寿县隐贤集至迎河集间)有一新岔河,系民国三年(1914)大水所决口,“淹没农田计约一百八十英方里”。至民国七年(1918),受灾农民倡议修补决口,遭到对岸及下游农民的反对,认为淠河在此处当有一新岔河入淮,如“填补决口,违逆水性,则对岸必遭大灾,而下游河堤亦有溃决之虞。两方之争执久而未决,乃向省中起诉,请省长公决此事。结果主修堤之农民失败,勒令将修补之处着即毁去,但受灾之农民始终未从命令,最后调停办法,将修补之处挖掘一缺口。”[14](P211)此讼案方告结束。根据作者的考察,皖西地区历史上的水利争讼主要有用水使水、筑坝截水、占垦塘堰、蓄水排水等类型[15]。
(三)讹财争讼
明代以来,皖西地方还出现了地痞无赖等黑恶势力群体,横行于较为繁华的市镇及人口稠密的乡村,需索讹诈财物,影响到地方社会秩序。清雍正时,安徽巡抚程元章于雍正八年(1730)五月奏疏称,霍邱县无赖光棍陈天爵为首的“控首”纠合“棍徒”蒋正等人,“以首告欺隐为名,沿门吓诈”财物。他们以欺隐田亩为名,挨户向有田产的数十百户人家索要钱财,“肯助盘费者即去其名,无论有欺隐无欺隐,俱要诈财”。若不依从个,“定要列姓名词状,拉到江宁、安庆,拖累到二三年”。民众因惧于诉讼,纷纷如数襄助盘费,先后讹诈得数十家米稻银钱[16](P334)。清代六安州扛夫乘民间棺柩出殡霸留,任意勒索抬钱,多次引起争讼[6](卷二,P585)。同治年间六安州白洋铺下保乡地袁洪道、潘五璜等人飞散鱼苗讹索乡民财物,引起争讼,受到知州的严厉禁止[6](卷二,P591)。
皖西众多河流的船渡时常被一些地痞无赖之徒把持渡口,讹索行人,引起争讼。清同治九年(1870),六安州小刘集下保窑冈嘴渡口,有吴姓渡船遇有乡民卖米,“每石米索取钱四十文”,被过渡者告讼,经六安直隶州知州王峻审理,出示《禁渡夫讹索示》,约束禁止渡夫讹索行人钱财[6](卷二,P590)。
(四)坟山争讼
坟山是家族死者的埋葬地,其主要由坟地和坟树构成,是中国人鬼神崇拜、祖先崇拜、风水观念的体现。皖西地区历史上因坟山引发的争讼较多。清乾隆九年(1744),六安州西山方家坪(今属金寨县)有邹姓人“误伐坟树数株,碑记坟台击毁,以致江姓具控,州主审断,身赔江姓树价银肆两正。又同乡长、乡地、公亲踩验清立界址。”于乾隆十二年(1747)立坟界契约③,是因误伐坟山树引起的。嘉庆间署理六安州事的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中曾记载其审断二宗坟地纠纷案。
(五)其他争讼
皖西地区历史上的争讼内容很多,除上述所举外,还涉及其他方面。舒城县《龙舒李氏宗谱》载,雍正八年(1730)三河镇南居民朱德章“缘为城隍庙建戏台,嫌地窄小,侵占寺地”,生员李振藻、吏员李先文等控县,“街邻劝施于庙无异施于寺也。着朱德章立借字求息。”④是因寺产引起纠纷,经街坊邻居调解立借据而息讼。民国三十四年(1945),六安城内晁、关、江、杨、张等六姓因慈善团体广惠局的房产引发争讼⑤。二例是属房产争讼。清嘉庆十四年(1809),在六安州经商的徽州商人于州治东北儒林岗下六安儒学之左创建新安会馆,引发州城内士绅的不满,认为其妨碍了儒学的风水,贡生李若桂、举人杨恢曾、生员熊可举、监生熊步芳等闻知,于三月初五日“以违例创建叩赏示禁以全学校事”为名,禀告到六安知州处,引发了六安州城内的绅商互控案。前后历时将近两年,官司历经州到两江总督四级衙门才结案[17]。是因风水原因引起的争讼。霍山县西乡西界岭保(今金寨县长岭乡界岭村)与英山县交界之处设有厘卡征收税费,清光绪年间“滋因厘卡舞弊,移累地方,迭次争讼”⑥,则是因厘卡征税引起的争讼。霍邱东乡《刘氏宗谱》所录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霍邱县正堂张知县谕令,就是一起冒认宗支案的处理结果⑦。其文曰:
嘉庆二十三年卫籍乱宗堂谕
霍邱县正堂张讯得刘燕宾等控刘南川受贿冒认刘鸣皋为本族乱宗一案,今经讯明,据刘鸣皋供称实系颍上县籍卫人,于四十年间逃荒在霍,微积钱文。诚恐卫人拉害,贿通刘南川私将刘鸣皋祖名填入二门祖先牌上,以致紊乱宗支。本应究治,姑念到案供明,宽免重究。着将刘鸣皋掌责,并将牌上刘明珠等名抹去,一干省释,并取具各遵结,送案查备。此谕
三、皖西地方的应对
通过对历史上皖西地区健讼风习的考察,其争讼的对象主要涉及军民、商绅、僧俗、官民、宗族、主佃之间的争讼。因此,皖西地方社会积极应对健讼风习。
(一)官方应对
就皖西地方健讼案件而言,大多数州县官出于职责所在,都积极应对予以及时审断。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如明宣德间任舒城县令的刘显,“刚廉得民隐,听讼讲学,士民环听,实惠在民。”[18](P567)万历二十二年(1594)由部郎中降六安州同知的王金星,“发奸擿伏如神,久之,不施鞭扑,几至无讼。”[6](卷一,P328)清康熙时,出任六安知州的王所善“决事如神,案无停谳。”[6](卷二,P393)雍正时,六安知州朱衣,“深知讼狱为民累,署六安十九日审断积案三百余件,阳示严明,阴寓慈惠。”[6](卷一,P330)清嘉庆十年(1805)前后,署理六安州事的高廷瑶在《宦游纪略》卷上称:其“忝牧斯土十阅月矣,检词讼簿经断结者,凡千三百有六十余宗,虽皆酌理准情决。”有兄讼析产不均者、有族人谋夺寡妇田产者、有偷诬良善为盗者、有持六博骰子证诬某国子生博者、有子死婆卖媳者、有胞弟杀其兄而兄子泣请雪冤者、有谋夺坟地盗葬者,等等,还有奸夫雇杀本夫并杀雇者灭口者的刑案,平均每月要审断一百多件。清初,霍邱县“有大害曰镟讼,罡盟虎翼实繁,有徒瞷里之良且懦者,群起而螫之,百人一喙,即起张释之包,希仁为理鲜不投杼矣”,知县庞禔“痛之而力为禁。”[5](P452)雍正时霍邱县知县张鹫“判事剖决如流,案无停积。”[5](P178)道光中,寿州知州王恩植“讼辄面质数语可了,胥吏不得为奸”,一到任,“于落膝初,供必反覆研诘,此时既有把握,而串牵之余犯,拖带之邻证,核稿时一删辄二三十人以此归。”[12](P211)乾隆时,霍山知县陈瑺“事精勤有为,讼至立决。”[19](P120)嘉庆初年任霍山知县孙菖生“到官,清积案数百卷,邑无冤民。”[19](P120)道光年间的霍山知县许道藩“性严重,廉明有威,剪除健讼,良民赖以安息。”[19](P121)道光末,霍山知县成福“折狱剖决如神,虽老吏不能及,百日内囹圄几为一空。”[19](P121)同治间,任霍山知县的彭广钟“视事之初既严束其下,而壹驭之以法。其于讼之来也,必先诘控者之情词得实,方允右情;虚及事已细者,则反覆劝导,或破其诈,或醒其迷,控者往往理屈气平,卷舌而退。批准之状非紧要人证,率一笔勾之。其应传质者,立签差而严其限,两造既备,及时庭鞠。愚懦者偿假以辞色,不轻为威,怒亦不遽,以才辩折人,务仕得其情而服其心。判既定,每细询讼之时日及旅费之多寡,仍恐其畏役而不尽吐,则又从而阴察之,虽有蠹役得遂,其诈索者鲜矣。至案须勘验,率轻骑至乡,于事主毫无所累,何论邻右。霍人感其化,不忍以琐事劳公,或数月不控一纸,古所谓讼庭草满者,于兹犹信。然讼之累民,讼者受,不讼者犹可脱也。”[19](P124)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舒城知县海柱“决狱明允,四民钦服,遇命案绝无株连。”[18](P572)乾隆五十六年(1791)任舒城知县周濂“政尚明察,案无留狱,苞苴不行。”[18](P573)道光二十年(1840)任舒城县令刘丙“居官廉明勤干,简车从,清讼狱”[18](P573)道光二十八年(1848)任舒城知县余国卿“初下车,有告訐者,面诘之,数语即折服,胥吏不敢受一钱,决狱平允。”[18](P573)同治十二年(1873)任舒城县令周岩“判事折狱,聪察如神,莫敢欺者。”[18](P574)
一些州县官针对此现象,积极劝谕民众息讼。清同治九年(1870),六安知州王峻发布《息讼狱以正人心示》告示,称:
照得六安风俗旧称安靖,向善者多。乃近来日渐变更,兢务兴讼。夫讼之兴也,起于人心好争,争之起也由于人心好利。好利者不顾礼义,并不顾至亲,遂致宗族之间不思敦睦,每以细故而抅讼端;乡党亲戚不相体恤,每以一言而入官府;以致妇女好讼不以见官,对吏为羞卑贱,敢讼不以犯上受刑为惧;此皆人心不趋于正,遂致渐染恶风,大可虑也,深可惜也。本州下车以来,审理词讼,惟知秉公持正,以天理为权衡。其不公不正者,必予严惩;其公正有天理者,亦必当堂嘉奖。忝居民上必时时存仁义之心,必时时教民以仁义之道。切望好利者自知其过,背义者自悟其非,人皆知慕公正仁义为至美之名,则不敢为不公不正、不仁不义之事。庶几,讼风渐变,人心归正,地方日渐清平,年岁益登丰稔,贼盗化为善良,岂不共享太平之乐哉。为此示谕,恺切劝导,自示之后,尔民人等其各深思,勿再因争小利,至不顾礼义,不顾乡党亲戚,轻入官府,自蹈罪愆。本州洞见民隐,一有欺弊,立施重刑,断不稍宽贷也。其各凛遵毋违。特示[6](卷二,591)。
王知州恩威并重,要求居民息讼。第二年新任知州的李蔚也发布了《劝民息讼示》告示,用较为浅俗的大众语言劝谕居民息讼,不要因一些蝇头小利而轻易争讼,劳民伤财[6](卷二,P587-589)。
然而并非所有州县官员都是尽心尽力按律办案审案,也有不少州县官疲玩失责,甚至收受贿赂,大事需索。如清嘉庆朝寿州发生了武举张大复毒杀三条人命的重案,但知州郑泰极端不作为,不质讯明确、据实详报,而是辄行包庇蒙混结案,引发了震惊朝野的各级官员舞弊大案,案件反复多次,经嘉庆皇帝数次谕批后,才得以完全查清,凶案主使人得到正法,多名朝廷命官被革职并法办。
(二)民间应对
1.士绅
绅乃一邑之望。因此,士绅在地方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深受普通民众的敬重。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一个农民从出生到死,都得与绅士发生关系。这就是在满月酒、结婚酒以及丧事酒中,都得有绅士在场,他们指挥着仪式的进行,要如此才不致发生失礼和错乱。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坐着首席,得接受主人家的特殊款待。”[20](P120)正是对士绅声望的高度概括。
传统社会里普遍存在“诉讼入官为耻”的观念,邻里社会常因一些事情发生争执,如买卖纠纷、打架伤人、田界屋址、用水纷争等,理所当然的请士绅来调解。作为士绅也乐意从事于这类事情的调解。地方志书对此记载较多,但较为简略,基本上反映了士绅调解地方社会纠纷的史实。六安州文生耆儒魏奠芳“里有纷争,必就质,辄因一言而解。”[6](卷一,P587)乾隆间曾任无为州千总护理庐州营都司职的沈镗晚年居乡,“里有争执者,得镗一言,讼端多息。”[6](卷一,P623)监生方冠儒见“里有纷争,招至家,释以杯酒,人感其意亦遂释。”[6](卷一,P633)监生邵星华自守诚信,乡邻有争,片言排解,靡不悦服[6](卷一,P634)。监生江希德见“乡有争兢,力为排解,虽倾资不吝,亦不使人知。终其身,里无涉讼者。”[6](卷一,P635)庠生吴震亨“处乡里风裁峻整,古道照人。邻有纷争,招之来剀切规劝,务使冰释而后已。”[6](卷一,P637)
2.宗族
宗族是皖西地方社会非官方基层组织,对地方治理和维护基层社会秩序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皖西地方各族在其制订的族训、族规,对族人的各种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要求宗族成员遵守国家法令。其中常将“息讼”作为对宗族成员的要求、训诫,禁止族人有争讼行为的发生。清乾隆年间,舒城县西乡姚河梯子岭(今属岳西县)朱(孙)氏宗族十一世朱公璋在纂修宗谱时所立的家训,有“禁争讼”条训诫子孙。其云:
家人戾离,多生于争兢,争而兴讼,乃奸险之徒恃其口舌便捷,以三尺为不足畏,以身家为不足惜,专一生机讦告,间由小隙,遂构大讼。此而不禁,则刁风日滋,而醇厚者变而浇漓矣。自今事有不得其平者,投鸣宗长,务集祠内,议论事情真实,从公分剖,但以曲直分胜负,不以尊卑论是非。若有强梁执梗,不肯输服者,就将实情送县惩治⑨。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安关氏宗族制订的“家规惩恶十二条”中有“戒争讼”条,禁止族人兴讼,并对此行为进行了约束和规范,如果违犯就要受到惩处。
是非有定论,何必到公廷。不管输,不管赢,银钱虚费先忧闷。忍了暂时气,免得破家门。若凭健讼以为能,结仇种怨多遗恨。
凡我族人,有好为兴讼、出入公廷者,乃健讼之徒。若与本族构讼,凭户长分别责惩。其与外人争讼,除万不得已外,依恃刀笔代人作词者,户长指名,送官究治⑩。
从上述家训、族规的规条可看出,诉讼会损害家庭及宗族的尊严,有损“族望”。诉讼不仅破财积怨结仇,甚至引发输者报复等不可控结果。所以禁止族人兴讼、构讼,违者责罚。若是宗族内部人员的纷争则族长和户长自然就成了宗族内的主要裁决或调停的主持者,当事者不服裁决才可告官处置。
四、结语
综上所述,自明代中期至民国结束,皖西地区历史上健讼风习持续近达五百年历史之久。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利益的纷争,经济利益是其争讼基本动因,地方官员的不作为和胥吏需索自肥则是争讼的外因。清固始县人蒋湘南对此评曰:“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阍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1]限于篇幅不再详述。皖西地方民众围绕各自利益而展开的涉及多方面的争讼,给地方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和负面影响,许多参与争讼对象为之付出了很大代价。前述清嘉庆年间六安州士绅与徽州商人因建新安会馆引发争讼官司历经两年,使得署理六安州知州沈南春为之革职,徽商建会馆购置材料被损毁,需重新选购,经济损失较大[22]。这些都是社会风习窳下的反映,更是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也是本地区社会经济和社会文明发展的结果。因此,皖西地方社会积极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地方官员及时审断讼案,并通过教化宣传劝民息讼;士绅、宗族参与邻里社会和宗族内部纠纷的调解和裁决,节约了诉讼成本,减轻了纠纷者的经济负担,起到了和谐乡党、和谐社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的矛盾。在今天的社会里,仍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 《具禀》碑,嵌金寨县响山寺院内山墙。
② 遵令勒石》碑,嵌金寨县响山寺院内山墙。
③ 金寨县九修《江氏宗谱》卷一“良卿公坟境”,2008年印。
④ 舒城《龙舒李氏宗谱》谱末 “朱德章立借字”,2005年印。
⑤ 六安五届《晁氏续修宗谱》卷二“广惠局记”。
⑥ 《復禁碑》,碑存金寨县长岭乡界岭村诸佛庵庙前广场。
⑦ 霍邱《刘氏宗谱》卷首上,民国八年刊本。
⑧ 金寨县九修《江氏宗谱》卷一“简传”,2008年印。
⑨ 《家训碑》,碑存岳西县姚河乡梯子岭孙氏宗祠。
⑩ 六安《关氏宗谱》卷一“家规惩恶十二条”,1987年石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