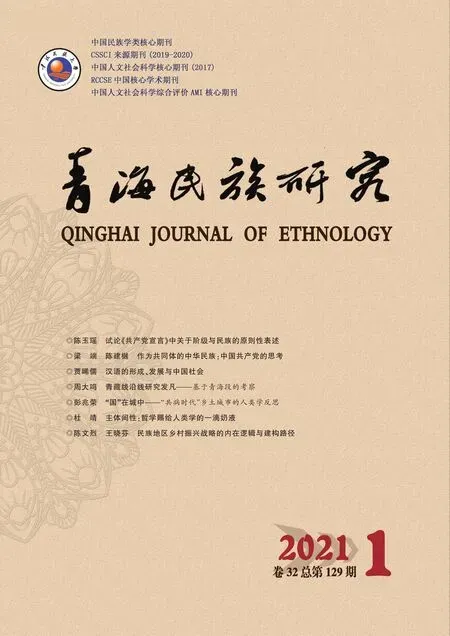晚清循化厅藏族“重案” 审理的理念与成因
张 蓉
(兰州大学,甘肃 兰州 730020)
清朝司法制度中“重案”包括命盗、抢劫、犯奸、谋反、叛乱等,属于严重威胁政治统治与社会秩序稳定的案件。 “重案”历来为王朝国家关注之重点,故《周礼·秋官司寇》云:“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1]。在以《大清律例》为主干的法律规章体系中,对“重案”的审理及其处置,实施层级明晰、严密审慎的逐层审转覆核制[2],将“生杀之柄”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3],以实现高效的社会控制[4]。 但具有统一性的理想的司法图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存在因时因地的变通[5],造就了“天理、人情和国法各有疆域而又贯通一气,事实、规则和信仰彼此有别却又打成一片,形成特定地域人群的法律生活与人文空间”[6]的法律文化景观。光绪五年(1879年)循化厅起台沟古勒庄冬至保上控纠众抢杀人命一案(以下简称“冬至保”案)及其最终解决方式,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区域社会的丰富内涵与多维度纠纷治理场域。
一、“冬至保”案及其审断特色
古勒庄,又称古雷庄,即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道帏藏族自治乡古雷村,位于起台沟内。 据光绪二十九年循化厅同知长赟调查:“起台沟番民五寨,计七百七十户,头目拉郎昂锁。 古雷寺一座,番僧二百二十名,有佛僧加仓,距厅城六十里。 哈家寺一座,番僧二十五名,距厅城八十里。 ”[7]起台沟五寨,又合称为道帏部落,由道帏昂锁总管。 同其他藏族聚居区一样,道帏部落深受藏传佛教影响,“沟沟是佛寺,村村有经堂”[8]。 古雷寺为道帏部落的主寺,寺主为加仓活佛,寺内设法台一名主持教务,“除江协寺外,上下禅院、寺院都是它的属寺”,香火部落除道帏五部外还包括隆务河下游的麻巴部落。[9]与汉传佛教寺院的集体财产所有制不同,藏传佛教寺院僧人经济来源除可分得少许香火部落的布施外,主要依赖家庭的供养和平时为他人诵经所得。
现实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古雷寺僧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进而发展成为暴力冲突。 光绪三年古雷寺僧官去乎与赞追各树党羽, 为争夺诵经权互相冲突。 光绪五年二月初九,在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中,同寺僧人桑果旁观械斗,不幸被飞石击中,越月于闰三月间身亡。 其各种情形,正如其后参与调解的乡老调查后所言:
缘冬至保向系河州朱麻滩汉民,早年间在起台沟番地傭工,招娶古雷庄番妇,生有三子,长子桑果为僧,其二子为俗耕种为业。 前年间,古雷寺番僧官去乎与同寺僧人赞追等两不相睦,各树党羽,事事争胜。 于三年三月二十间,在古雷俗庄念经起衅打架,互相受伤。而官去乎之党僧人刀周,伤重身死。官去乎遂以师傅名目,控告到案。 获恩饬差缉获到案,严加惩办,罚服了结。 而官去乎以讼事获捷,自是骄纵,多为不法。该寺法台心中不善,于今年正月间传集寺僧,言官去乎与赞追一般凶徒耳,而赞追已逐出寺,惟官去乎仍居寺院,尤不安分,恐非沙门之福,可将他逐去。 而官去乎恃强不服,亦不改行,致令起台沟番众心抱不平,于今年二月初九日起而攻逐。时官去乎弟兄三人约集十四家僧人帮助拒斗,彼此拾石乱打。 不意冬至保之子桑果闻声出视,忽被飞石中伤,越月身死。[10]
四月间,桑果之父冬至保径赴西宁办事大臣衙门控诉起台沟藏民却群(档案中又称为却郡)、花洛、拉隆等纠众抢杀人命。 此案情节看似简单,但背后牵涉因素甚广,是研究晚清循化厅藏族命盗重案审断理念,解读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法律文化景观的一起典型案例。
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西宁办事大臣喜昌札饬西宁府办理“冬至保”案。 西宁府遂移转循化厅,并派差前往协查。 五月初一日,循化厅在接管后,随即按照规程介入调查,但审断无法进行:“敝厅当即添派妥役协同来差前往勒提几次,该被告等均以愚番畏法推诿不敢到案,以致来差空累往返,而敝厅亦无从批解。 甚至该原告冬至保原被番僧官去乎因与寺众不合,欲捏其词上控以为帮讼之计。 现在该被证又屡提不到,不惟官去乎主唆愈力,即冬至保更可得其键讼。 是非被证到案,莫可分其泾渭。 ”[11]
两造与人证均拒不到案,又缺乏进行研判的必要证据,审断难以为继。 延及九月,冬至保给循化厅上“悔呈”,以“气忿谬控”“恳祈电准转详销案”:
时,小的子桑果与官去乎比邻而居,忽闻人声鼎沸,去门看视,恰被飞石打伤胸膛,调治不痊,于闰三月间因伤身死。当斯之时,实不知伤出谁手。小的痛子身死,又因一时气忿,前赴西宁青海大人辕下,以纠众杀命等情告案。 奉准批府宪差提之下,小的伏念子系石伤并非枪死,不合一朝之忿起葛藤之狱。 ……今蒙河镇右旗马参将路过说和:事因官去乎起衅,又系官去乎唆告,罚官去乎与小的付银二十两,以作诵经超度之费。 小的心服气消,情愿具悔,永不反复。[12]
十月间,“河镇右旗治下马占鳌、 商民马三顺、张哈工头目马八十、马四麻恒、韩且令等为讼己处息,恳祈电准转详销案”[13]。循化厅同知虽知“此案关系上控要件,无论谁之虚实,自应一并批解,听候到案审办,原不能听其和息”[14],但面临审断之困难,案情之纷杂,再加原告与诸位乡老皆恳请息讼的实际情况,决定就此结案:根据乡老“治下等得悉细情,公议事因官去乎而起,讼由官去乎而致,罚官去乎出银二十两给付冬至保之手。 以十两作为念经之费,十两为冬至保歇店之需”[15];循化厅判定官去乎“系念经首僧,不以清静无为为事,而以搬是非为法,固宜驱逐出寺,无容置喙”[16]。
“冬至保”案的诉讼程序与处理方式,具有晚清循化厅藏族命盗重案审断的典型特色, 无论是受理、初审乃至结案,皆与清代一般内地州县衙门的司法实践存在着明显出入。
首先,就受理程序而言,根据《大清律例》,冬至保存在“越诉”行为。 《大清律例》规定,州县衙门负责命盗重案的第一重管辖,“军民人等遇有冤抑之事,应先赴州县衙门具控”,“如审断不公,再赴该上司呈明”。[17]如原告不向州县首告而径赴上级衙门,即可视为“越诉”。[18]冬至保首告于青海大臣衙门:“小的痛子身死,有因一时气忿,前赴西宁青海大人辕下,以纠众杀命等情告案。 ”[19]经循化厅查报,“冬至保并未在敝厅报过人命”[20],并不存在拒不受理或处置不当等特殊情形。 依照《大清律例》,冬至保的行为已构成“越诉”,不仅不应当理,还要受笞杖惩儆。 然此案如循化厅报告所言:
为详情转详事。 本年五月初一日,案准堂台移开:“光绪五年四月十九日,蒙钦宪喜宪札:案呈,据循化厅古勒庄番民冬只卜呈控恶番纠众抢杀人命,恳请讯究等情一案。 除原呈有案邀免不录外,尾开烦照来文及奉宪札原词内事理,希将此案原被人证照依单开姓名,逐一勒提齐全,同厅卷限五日内一并添差批解过府,以凭讯详。 案关奉宪饬审要件,勿稍庇护,有干未便。切速等因。”到厅准批,敝厅当即添派妥役,协同来差前往勒提几次。[21]
西宁办事大臣喜昌接到诉状后,于四月十九日札饬西宁府五日内将原被人证及厅卷批解到府进行审理。 换言之,西宁府成为了“冬至保”案审断的主体,循化厅则处于协查地位。
其次,就审理程序而言,根据《大清律例》规定,“冬至保”案存在现实障碍。 州县衙门在辖区内发生命盗重案时, 亲民之官须亲赴现场查核,“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前往相验”[22]。 随即通传两造,或强行缉捕当事人对簿公堂,进行审讯并取得供词,“凭伤定供,凭供定罪”[23],提出书面判决意见,称之为“看语”或“拟律”,至此初审告一段落。 然而“冬至保”案在政府介入时,已距案发之时将近2 月,且“当系此之时,乱石如雨,亦不知石出于谁之手,伤自何人。冬至保果有仇众之心, 势必留尸待质, 何自遽尔焚化,甘心灭迹,亦知命无可偿,伤无从究也”[24]。 可以说, 一桩人命案件所必须具备的关键因素皆不够清晰。 原被两造及人证皆不愿意到官,导致此案在履行勘验、通传以及审断等程序方面难以为继。
再次,就处理方案而言,此案的实际解决方案与各类律例的相关惩处出入较大。 其一,表现为对官去乎唆讼行为的姑息。 官去乎原为光绪三年古雷庄念经起衅案的主要肇事者, 惟因其方僧人刀周身死而控。 彼时循化厅未按律惩处,不过“罚服了结”。 光绪五年,官去乎公然对抗法台驱逐出寺的决定,再次酿成武装冲突, 以致同寺僧人桑果丧命,“事因官去乎起衅,又系官去乎唆告”[25],企图“借他人之事泄自己宿恨”[26]。政府并未追究官去乎两次纠众械斗,以致误伤人命之责。 再者,根据《大清律例》对健讼的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最轻者亦须笞杖惩儆。[27]但此案最终对官去乎并未依律严断,只是将其驱逐出寺,罚服银两。
其二,表现为对冬至保诬告行为的忽视。 冬至保在诉状中攀扯循化厅衙门差役杨、郭两人贪赃枉法:“至于小的控告杨总爷、 郭总爷吃银三百两,实因与起台沟番子相识,小的心中疑惑,想是他们受贿偏袒,其实并无亲见。 ”[28]《大清律例》规定:“凡词状止许一告一诉,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倘波及无辜者,一概不准,仍从重治罪。”[29]虽冬至保承认控告杨、郭二人并无真凭实据,仅为自己的疑虑。 众乡老也对差役受贿一事予以否认:“至于差役杨、郭两人吃银三百两,明是听人嘱唆,不知是有不准状之语,以故捏饰虚言耸动上听。 ”[30]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始终未对冬至保有任何惩戒。
其三,表现为未深究寺院内部的恶斗及其参与人员。 依据《大清律例》,“凡斗殴,以手足殴人,不成伤者,笞二十”[31],“及因斗殴而误杀伤旁人者,各以斗杀伤论,死者,并绞;伤者,验轻重坐罪”。[32]“冬至保”案由一场有预谋的斗殴引发,且致人身死,原谋官去乎被驱逐,“对聚众为首之却郡等三人”仅仅“堂查训责,以示薄惩”[33]。
其四,表现为命盗重案经民间调解和息。 “冬至保”案为典型的人命官司,深为各级官府重视,且须经历严密的逐层审转程序。 清朝规定:“若将命盗案内紧要情节及重大事件滥批乡地查覆, 降三级调用。 ”[34]循化厅虽知规章制度,且“关系上控要件,无论谁之虚实,自应一并批解听候到案审办,原不能听其和息”,但“伏念番民无知,事出愚弄,兹既自相调和,各知后悔,是可稍施姑息,以顺舆情”。[35]
由“冬至保”案可见,循化厅在处理藏族命盗重案时,受到重重掣肘,以致于律例规程往往难以与复杂多变的现实严丝合缝:命盗重案虽“越诉”在前,但由西宁办事大臣督办,西宁府限期提审;而地方政府对藏族民众的权威性明显不足,难以有效地提解原被人证,又受制于“重案”限期完结。 再者,从光绪三年古雷庄念经起衅案来看,是一起典型的聚众斗殴而致人命的重案,其结果不过是“严加惩办,罚服了结”而已,处处透露出循化厅审理藏族命盗案件的特殊性。
二、土俗民情与特殊律例
清朝因循前代, 构建了层次分明又立体交叉、因地制宜的多民族管理制度体系。 在法律制度方面“逐渐形成一个由律、条例、事例、则例、成案、章程、禁约、告示等不同法律体系,而专门针对蒙、藏、回等民族聚居和杂居地区的规定往往不同于内地,体现了‘因俗而治’的传统”[36]。循化厅自设置之初至光绪年间,处理各类社会纠纷基本形成了以《大清律例》与《理藩院则例》为宏观制度基础,以《蒙古律例》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为具体指导规章的框架结构。 《大清律例汇辑便揽》“化外人有犯”之条明文规定:“凡化外人来降,犯罪者并依律拟断,隶理藩院者仍照原定蒙古例。 ”[37]其中,《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系西宁办事大臣达鼐于雍正十一年(1733 年)奉命于《蒙古律例》内挑选出与藏族密切相关的条款编纂。 大学士鄂尔泰等奏请:“该番子等之颁发律书,应照玉树、纳克书番子之例颁发。 惟律书甚多,有番子等处不用之杂款,应交付达鼐等,将蒙古律内可用于番子地方之重要条款摘录送来。 到时,译成唐古特文颁给之。 ”[38]次年颁发,简称《番例》,共68 条。 在此法律文化背景下,隐藏着以“冬至保”案为代表的甘青藏区蒙藏命盗重案从诉讼程序、审断依据乃至结案方式所具特色的密码。
首先,“冬至保” 案的特殊审理程序背后是循化厅行政隶属的复杂的层级关系。 循化厅又名“抚番分府”,清楚地表明循化厅同知兼具一般亲民之官和民族事务之官的双重身份。 循化厅成立之初隶于甘肃省临洮府。 后临洮府改为兰州府,乃改隶于兰州府。乾隆五十六年(1791 年),经陕甘总督勒保、西宁办事大臣奎舒奏请,“将蒙古等近边就近贵德、循化两处等处番子,亦令西宁办事大臣兼管”[39]。循化厅境内,“以南番二十一寨、西番上龙布十八寨、合儿五寨、阿巴拉八寨共五十二寨为生番;西番边都沟七寨、下龙布六寨、起台沟五寨、保安四屯共二十二屯寨为熟番,统归青海衙门管辖”[40]。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清朝又定:“嗣后贵德、循化等处,遇有盗贼案件,着地方文武官员听办事大臣指示办理, 如有观望掣肘即行参奏。 ”[41]嘉庆十年(1805 年),西宁办事大臣贡楚克扎布奏准:“西宁文员自道府以下、 武员自镇协以下俱归该大臣兼辖节制。 ”[42]道光三年(1823 年),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准,循化厅改隶于西宁府。
西宁办事大臣设立于雍正三年(1725 年),初名“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 又因驻地西宁,称西宁办事大臣,“直属于理藩院,管辖青海蒙古和硕特、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喀尔喀诸部,及青海各藏族部落,主持青海各旗盟会,并节制西宁镇、西宁道文武官员,掌青海之军政大计”[43]。 至“西宁所属番子,隶驻扎西宁办事大臣兼管”[44],循化厅在“行政组织上隶属甘肃省承宣布政使司西宁府;族群管理与民族纠纷方面归西宁办事大臣管辖”[45]。因而,循化厅所辖藏族百姓前往青海衙门首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由于往来查处不便,西宁办事大臣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札饬西宁道、西宁府审断,并由相关厅、县协助详查。
其次,“冬至保”案暴露出循化厅地方社会中特殊的权力结构,地方政府因权威性不足而缺乏彻底肃清纠纷与深度干预的能力。 起台沟五寨地处循化厅通往河州、兰州的要道,与撒拉族、汉族、回族等毗邻而居,因而被划入“熟番”。 但从根本上讲,起台沟五寨仍处在部落制度之下,并被笼罩上了浓厚的藏传佛教色彩。 这就使得:道帏昂锁在部落事务,特别是在部落内部的纠纷中,具有传统权威性;在部落道德驱动下的集体责任制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个体冲突易演变为群体冲突;藏传佛教上层在地方社会中成为魅力型权威。 光绪三年古雷庄念经起衅案因发生于古雷寺僧团之间, 道帏昂锁并未介入。当时官去乎上诉至循化厅,并获得罚服,看似赢得了官司。 不过造成的结果则是:循化厅虽对赞追罚服,驱逐出寺,但造成冲突的肇因并未清除;另一方面,从藏传佛教内部而言,官去乎告官,显然是未遵从寺院内部调解的结果, 挑战了寺院法台的权威。法台,藏语中称“赤巴”“堪布”等,“总管全寺宗教、行政事务,类似汉传佛教寺院的方丈。 一般从佛教知识渊博、获得‘格西’学位、在宗教界享有声誉并具有经济实力的活介(应为活佛,译者注)中选任”[46]。 在光绪三年那起古雷庄念经起衅案中,官去乎借助循化厅官方审断,成功抵制了法台的权威后,愈加骄横。因而,在光绪五年遭到法台驱逐后,他企图再次利用自己积累的诉讼经验,借助官府资源,抵制法台的命令,因而唆使冬至保径赴西宁告状。 这既体现出循化厅藏族部落内反传统性的萌生,也为清朝改变地方社会权力结构提供了契机,只不过彼时清朝未能意识到并加以利用罢了。 地方政府作为王朝国家的代表,在区域社会中的权威性依然受到限制。
地方政府权威的有限性, 使其在地方社会命盗重案以及相关讼诉问题的处理上, 常常偏离律例的规范。 如在内地州县,“遇有地棍讹诈, 讼师播弄之案,彻底根究一二”[47]、“捏空造虚,起祸诬人,我为杜之。聚众当恶,主谋唆讼,我为殄之”[48],是地方官一贯的态度。 故西宁道曾令循化厅,“有奸徒暗行唆使,从中图利,尤为可恨”,“如棍徒敢充讼师,身后挑唆,于中取利,一经本道访闻,定即查拿,严行惩办”。[49]然而,熟悉地方社情的循化厅同知,无论是对官去乎还是冬至保均未追究唆讼及诬告之责。 特别是冬至保诬告循化厅衙役杨、郭两人贪赃枉法,证据确凿。 清代地方官的经验总结中强调,“差役剥民, 固是惯技,然敢于上控差役者大抵刁徒什九,而良懦无什一”[50],因此惩治较重。 《大清律例》规定,“倘波及无辜者,一概不准,仍从重治罪”[51];《蒙古则例》中,雍正二年议准,“蒙古人告状必列姓名,方与准理,若诬告者,原告及见证皆罚三九”[52];《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对诬告行为并无涉及。 循化厅对冬至保的诬告不究,既有对“无谎不成状”司空见惯的原因,更有非冬至保本意的判断。 寺院内斗导致其子不幸身亡,经人唆使提起诉讼又需要耗费不少钱财,冬至保本人才是整个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的受害者。
再次,“冬至保”案采用民间调解和息也是循化厅特别是藏族部落土俗民情与司法文化互为交织的结果。 无论是光绪三年古雷庄念经起衅案,还是“冬至保”案,均可看到《西宁青海番夷成例》中“番民自相殴杀”条“番民殴死番民,追九九罚服”[53]相关规定的影子。 不过,这个判决并未严格按照“九九罚服”,实则既有法不责众的考量,也有涉藏地方“尚武之风”与“集体责任”以及“赔命价”传统的影响。“赔命价”是藏族民众在佛教精神影响下的特殊罚服制度。 根据著名藏学家李安宅的调查,藏族民众认为:
“杀一个人已经够坏了”,他们将说,“为什么要以处罚方式杀另一个人呢? ”所以,藏地通行的办法是“赔命价”,以补偿受害一方的损失。 实际上,杀人的人或强盗,杀了人就被认为种下罪根,要在来生得到报偿,谁能逃避劫数呢? 自做的,必要自赎。 这就是他们的理论。[54]
因而藏族民众对斗殴流血乃至杀伤人命案件,惯以赔命价的方式了结,必要时附加相关的惩罚即可。 此案冬至保告状的目的,纵然有官去乎等唆使的因素,但也不能排除本人想要借助官司为自己争取补偿的动机。 最终案件经过民间调解,原告愿望已经达成,始作俑者官去乎被驱逐出寺,并接受“罚服”,被告中“聚众为首”之人被官府训责,是百姓比较认可的处理结果,即“以顺舆情”。
由是,“冬至保”的处理方案与律例规章既有符合,也有差距,是循化厅同知在充分综合衡量土俗民情与朝廷一贯司法理念等因素后酌情处置的结果。 追根溯源,此案的症结乃古雷寺内斗,但循化厅没有能力从古雷寺内部进行寻根究底,也没有能力对斗殴参与者逐一摸排查清,更不能保证律例所规定的各项惩处方案可以贯彻实施。 再者,律法之刚并非是最实用的处理手段,很有可能会再次激化更深的矛盾,就如官去却乎首告的结果仅为官方粗浅的干预那样,难除痼疾。 司法之本意在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如果依律严断,有可能引起基层社会秩序的混乱失调,与官府审断初衷相违背,那么一定程度的退而求其次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三、羁縻为政下的法律实践
“冬至保” 案特殊的诉讼程序与处理方案充分说明,对像循化厅这样兼具边疆性与民族地方双重特点的基层政府而言,就法论事、缘法而判在绝大多数时刻只是执法过程中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 每一起案件的解决,都需要权衡具体情形做出决断,更多的时候必须妥协于各种现实因素, 即遵循实用主义的审理理念。 乾隆年间龚景瀚对此做过一番概述:
新附番人虽云归地方官管辖,不过输粮纳赋羁縻而已,非能入内地民人整齐,而梳栉之也。 转徙无常,非有保甲邻佑可稽查其出没往来,即其父兄不能知子弟在外所为何事,而谓地方官能禁约而钤束之哉? 至蒙番接界,又皆深山旷野,非有汛防可以踪迹。 而贪利嗜杀,又番夷情性之常报仇泄忿,互相抢劫,此皆无足怪者……故响之都统及各镇管总起大纲而不责其细目,盖大员则轻重操纵可以自如。[55]
直至晚清此种情形仍然没有得以彻底改善,这既根植于晚清国家在边疆民族地区实施社会治理的实况,也包括清代循化厅特殊的土俗民情与地方文化权力网络。
从朝廷在甘青藏区的司法理念来讲, 始终充满了“不深治”的羁縻色彩。 对藏族寻常命盗重案不按律究拟严惩,而以民间调解的“罚服”结案,是清代在甘青涉藏地方一以贯之的司法理念。 雍正十一年(1733 年),经大学士鄂尔泰等会议,令西宁办事大臣达鼐于“蒙古例”内摘选藏族人易犯条款,纂成“番例”颁发遵行,作为甘青藏区各类社会纠纷的处断依据。乾隆元年(1736 年)六月初四,署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刘于义以“番民归服未久,处在僻远,虽圣化霑濡,渐知天朝威德,而番野之性究未尽除。 若遽以法律相绳,诚恐各怀疑惧,转生事端”,奏请“准其宽限五年,暂停律拟,姑照番例完结……如五年之后,再有干犯, 执法拿究, 庶恩威可以并济, 番愚共荷矜全”。[56]乾隆四年(1739 年),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包括又奏请:“五年限满后, 除番民杀死汉人或盗劫汉人财物者照律审拟外,其番民杀死番民,或番民盗劫番民财物,其被害之家不愿罚服者,听其赴省告理,依律科断。 至若番民盗杀番民,而被害之家情愿得受罚服者,仍照番例完结。 ”[57]嘉庆十三年(1808 年),西宁办事大臣文孚奏准“嗣准刑部议覆,番民僻处要荒,各因其俗,于一切律例素不通晓,未便全以内地之法绳之。不如以夷治番,觉于夷情妥协。嗣后,自戕杀命盗等案,仍照番例罚服完结,毋庸再请展限”[58]。自此,藏族寻常命盗重案按照“番例”进行罚服完结成为定例。 甚至光绪年间循化厅内卡加寺江洛千户与岁仓捏力哇等屡次仇杀,“其互伤人命九命, 以及焚掠房屋、牲畜、财物”的大案,也照旧“均由汉番乡老循照番规查抵清楚”。[59]诸如此类的案例解决在整个清代的循化厅乃是一种常态,“惟番夷风教攸殊, 难概绳以律法,拟请循照番规,兼仿厅办成案,从权完结。 庶于恩威怀畏之余,仍收控驭羁縻之益”[60]。由此可知清代朝廷与各级政府处理各类甘青藏区社会纠纷的普遍态度。
从政府履行司法职能的角度来讲,“冬至保”案的处置模式深刻地反映出清朝在边疆民族区域实践的诸多问题。 首先,清朝的政策法规对基层社会尤其是边疆民族区域的渗透非常有限。 清朝以“因俗而治”为原则,针对甘青涉藏地方制定了《西宁青海番夷成例》。 然而,《西宁青海番夷成例》终究不过为摘自《蒙古律例》,不仅有水土不服之嫌,且仅有68 条,难以覆盖复杂的社会纠纷问题。《西宁青海番夷成例》原为针对甘青特殊的社会情形制定的具有过渡性的特殊律例。 正如甘肃按察使司按察使包括所言:“是法律原以惩凶,而行之番地,则转因而滋事;抵偿原以平怨,而施之番族,则转因而结仇。 是必渐之以仁,摩之以义,型之以礼让,讲之以律令,庶几可销其桀骜之气,闲于礼法之中。 此固非可责效于数年也。”[61]随着嘉庆朝成为定例,所谓期许“教化”之后再推行《大清律例》就成为了镜中黄花:无法给州县官断案提供严丝合缝的依据,给予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的全面指导。 “法律是地图,成文的法律是制图学意义上的地图,而习惯法、非正式法则是意境地图”[62],清代循化厅审理词讼清册反映出来的诸多“重案”案例,既没有严格依据《大清律例》进行判决, 也并未完全遵照各民族习惯法予以处置。这些都是经过“冬至保”案反映出来的一般情形。 其次,封建专制王朝权力高度集中的原则,极大影响着基层政府对命盗重案的办理效率。 严密的逐级审转覆核制规定,州县级官员们必须在朝廷的各项规章制度、各级上司衙门的三令五申所限制的极为狭窄的范围内履行职责,“他们始终受到琐细的规章条例的制约”[63]。这种制度会间接促使基层地方官员以应付上司为办案宗旨,从而将完成命令置于事实真相之上, 加上极为粗陋低级的刑侦破案技术,追求事实真相非常困难,面对“重案”提出一个“互利互赢”的解决方案,是颇为务实的做法。
从循化厅地方社会的运行逻辑来讲,杜赞奇所提出的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在晚清循化厅的基层社会中同样存在,甚至表现得更为强大。 这一网络功能复杂且富有弹性, 使生活其中的任何个人和集团都必须主动或被动遵守约定俗成的是非标准与行为规范:“在组织结构方面, 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 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之中, 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 领导体系得以形成。”[64]在“冬至保”案处置过程中,循化厅地方社会的“权力的网络”悄然浮现。 参与该案调解乡老的身份构成颇为耐人寻味,国家官吏、商人与地方头目构成了一支十分特殊的调解团队。 穆斯林商人作为甘青涉藏地方的调解人既有其特殊性, 也与其在商业经营中建立起来的范围广大的熟人网络有必然联系,“穆斯林尤其擅长商贸……依靠他们身处交界地等地理优势,以及容易抵达交界地方的便利条件,为自己提供了充当中间人的独特优势”[65]。正因如此,循化厅上报西宁府与青海衙门称:“伏念番民无知, 事出愚弄,兹既自相调和,各知后悔,是可稍施姑息,以顺舆情。”[66]所谓“舆情”,正是当地“权力的文化网络”的反映:国家政权在晚清循化厅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对文化网络领导权威的争夺, 却又要妥协于长期形成的地方运行规则和非正规的地方领袖们。
在“冬至保”案中,作为地方社会权威的古雷寺活佛加仓、法台等因涉及寺院本身,并未参与调解。实际上,在地方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日常运行中,古雷寺加仓活佛与道帏昂锁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权威角色。 如,光绪二十七年的“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一案”,则是由佛僧、昂锁、军功、歇役、差役、番目组成了一支调解团队,照依“番规”罚服了结。
遵查此次起台番众杀毙立加八乙一案起衅之由,军功等询诸前乡老佛僧、昂锁声称,立加八乙前控番民七家捏设帐债、霸去田地、磨房等情,前议令两造吃咒完案。 议明若原告吃咒,则七家如数赔还;若七家吃咒,则与原告一概免让。 乃该被告七家自知情虚,不能吃咒,不但不赔霸业,歹敢聚众逞凶滋事,此原告立加八乙被杀之由来也等语。 军功等询悉前情,随即协同歇役、原差、番目人等,邀集两造,仍照番规在下开导理处。[67]
可见,“有许多乡规、俗例和流行的惯习完全不为官府承认和支持, 但它们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结果不但官府屡禁不止,而且它们往往迫使各地官府在有关场合作出妥协。”[68]又如,“边都沟番民还卡加具告你尕才浪等投毒谋害”案,经过循化厅“屡次勒差血比,据边都沟番目多已先等恳禀前来,缘该犯你尕才浪等畏罪逃入野番不敢赴案,番目等照番规在下处息,敝厅复查属实,于初二日取结完案”[69]。同样也说明了官府对地方文化网络的一种让步。
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王朝国家的政权建设水平、边疆民族地区的土俗民情、地方官自身的态度与长期形成的地方文化网络等,都会成为解决一起案件应当拿捏尺度的考量,尤其是“民间秩序中的规范性内容越丰富, 官员进行审判的依据也就越多,官府的作用是建立在民间秩序基础上的”[70]。
四、检讨与总结
王朝国家“高专制权力与低基层渗透权力”[71]在晚清循化厅,尤其是在藏族聚居区,体现得尤其明显。政府的司法权威因其所处的社会伦理环境总是缺乏应有的强制力,理想的司法架构与具体的司法实践,实则与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意图及真实地方社会的运行逻辑相表里。 即便是一件普通的命盗重案,循化厅同知亦需要把握好社会现实与国家司法制度间复杂而又微妙的平衡: 既不能排斥民间权威等介入与按照“番规”罚服结案,审讯过程也需要兼以情理和民俗予以裁断,而非履行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职责。 而基层社会的不流动性造成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致使官方法庭虽设置良久, 依然必须依赖传统的仲裁手段。 当然,这仅限于普通的发生在蒙藏聚居区内部的命盗重案, 清朝对有可能威胁边疆稳定与统治秩序者并不手软:“夷民等如敢纠约多人肆出劫掠,或竞扰及内地边氓, 情同叛逆, 以及肆意抢掠蒙古牲畜,凶恶显著,关系边疆大局之案,自应慑以兵威,严拿首从,随时奏明,请旨办理,以彰国典。 ”[72]
清朝在边疆民族地区司法实践中的实用主义理念,也带来许多问题。 其一,过于迁就民间力量而使大量案件无法正本清源, 官府难以树立权威,甚至可能引发更深层更多维的治理难题。 如“冬至保”案中的官去乎,在被驱逐后,先后辗转于河南蒙旗、拉卜楞寺一带,投机钻营,播弄是非,引发了一场更大风波,导致数十人死亡。[73]其二,无法保障法律固有的确定与权威,就无法利用法律重器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若归内地地方官办理,则必以内地之法治之,过于认真,所谓束缚之,驰骤之,急则败矣,颟顸了事又启番民轻视中国之渐。”[74]其三,正如洪堡曾言“既防范外敌又防范内部冲突,维护安全,必须是国家的目的,必须是它发挥作用的领域”[75],然而清朝的治理既未曾改变以循化厅为代表的边疆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也未能改变其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权力的文化网络”:“部落与部落之间不断械斗,为藏民生活痛苦者一大原因。 盖各部落间, 缺乏统一有力之组织, 为之解决各项纠纷。 ”[76]当然,这些问题并不能粗浅地认为是司法规程的不合理所导致,实乃由政治体制、权力结构、施政理念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特点等共同导致,因此其根本性改变,也就绝非朝夕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