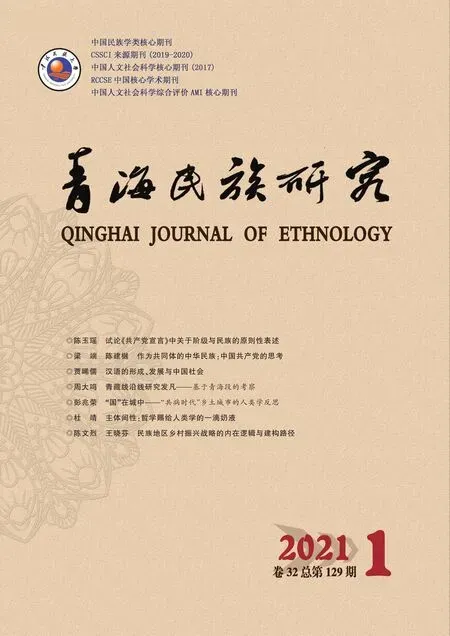夏尔巴人的宗教实践、 社会结构与精神气质
——对《通过仪式认识夏尔巴人》的讨论
央 卓
(中山大学,广东 广州 510275)
谢丽·奥特纳(Sherry B. Ortner)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犹太家庭,曾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茅尔学院后师从格尔茨学习人类学。
在芝加哥大学期间,奥特纳开始关注和研究尼泊尔夏尔巴人,最终完成博士论文《思想之粮:一个夏尔巴文化的关键象征》, 及以这次田野资料为基础的完成了她的另一部夏尔巴人民族志《通过仪式认识夏尔巴人》一书。 之后,奥特纳又多次前往夏尔巴人村庄进行田野调查, 聚焦夏尔巴社会的政治、宗教、仪式和20 世纪50 年代“登山运动”对夏尔巴社会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对于夏尔巴人和其社会的一系列研究成为奥特纳的代表作,主要包括《通过仪式认识夏尔巴人》《高原宗教:一部夏尔巴佛教的文化与政治史》《珠穆朗玛峰上的生与死:夏尔巴人与喜马拉雅登山运动》 三本民族志以及发表在《美国人类学家》等杂志和论文集上的一系列论文,如《论关键象征》《夏尔巴人的洁净观》《神体、神食:一个夏尔巴仪式的符号分析》①。
一、“浪漫”的夏尔巴人
夏尔巴人是一个居住在喜马拉雅云端上的民族。 珠穆朗玛峰滋养着夏尔巴人,也赋予了夏尔巴人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夏尔巴人生活在尼泊尔、印度、不丹和中国西藏交界处的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印度大吉岭、锡金邦、尼泊尔境内的索卢(Solu)和昆布(Khumbu)地区以及中国西藏自治区境内。其田野点在尼泊尔西北部索卢和昆布地区的夏尔巴聚居区,位于尼泊尔与中国西藏定日交界处囊巴山口要道上。
在《通过仪式认识夏尔巴人》第二章对生活在索卢-昆布地区(Solu-Khumbu)的夏尔巴人和其社会进行了全观性的文化素描,包括历史、经济、社会组织、宗教等方面。 夏尔巴社会实行外婚制,血缘以父系计。 诸氏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制度划分,其中拉马氏族(Lama)的地位最高,廓尔扎氏族(Gordza)的身份最为低贱。 夏尔巴人讲藏语,主要信奉藏传佛教宁玛派。 在日常生活中,多数夏尔巴人通常以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劳作,互惠行为多发生在同一个村落当中。 农业是核心家庭的重要经济来源,主要种植小麦、大麦、玉米和土豆。 畜牧业饲养的牲畜主要包括牦牛、犏牛、绵羊等。 随着1953 年尼泊尔开放边境, 西方登山者和旅游者开始涌入索卢-昆布地区,夏尔巴人登山的天赋被西方登山者发现并深受其赞赏, 于是夏尔巴人开始作为登山者的向导、背夫、厨师,这成为他们的另一条收入来源,改善了他们的生活境遇。
奥特纳认为夏尔巴人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人群之一。 然而,通过对夏尔巴人的三个仪式的分析,夏尔巴人在这些宗教仪式中所展现出的内在精神气质并非“浪漫”,夏尔巴人的仪式与其社会结构紧密相关。通过对夏尔巴人仪式的研究展现出夏尔巴人的宗教实践、社会结构与精神气质之间的复杂张力。
二、 通过仪式认识夏尔巴人
(一)赎罪仪式(Nyungne)
每年的赎罪仪式是佛教中常见的年度仪式,它通过强调某种特殊规则来获得功德并得到救赎。 夏尔巴人的赎罪仪式历时四天,仪式参与者是自愿参加。 整个仪式的目的是让参与者接近并经历一种禁欲式的生活, 他们在仪式期间 “就像是僧侣”(like monks)。 夏尔巴人认为,通过赎罪仪式所获得的功德是最大和最有效的。 虽然赎罪仪式是面向所有人,但参与者主要是老年人,奥特纳认为其背后的社会学原因与夏尔巴人强调核心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婚姻相关。
家庭是夏尔巴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单位。 每个核心家庭有自己单独的房子,拥有自己的和家畜。 核心家庭的成员作为一个团队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农产品除满足自给自足的生活外,剩余部分用来履行与村庄成员的互助义务。 在夏尔巴社会中,核心家庭是作为面对外面世界的“避难所”,家庭成员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甘共苦,共同抵御外界攻击。 因此,夏尔巴人的核心家庭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成员之间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并且高度独立与封闭。 然而,夏尔巴人这种核心家庭的理想状态会在孩子进入婚姻生活后被打破,孩子的婚姻为父母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并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威胁。
首先,孩子的婚姻打破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精神纽带,尤其是打破了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所以,夏尔巴人的母亲们喜欢她们的儿子当僧人,这样就不需要打破母子关系,也不需要把儿子交给另一个女人。 “当一位僧侣被问其母亲是否为他出家感到高兴,他的回答是‘是的,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娶了老婆,她会和我的母亲吵架,我的母亲会嫉妒年轻的妻子,还会批评她的工作等等’”[1]。
其次,孩子的婚姻分裂了夏尔巴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单位。 孩子一旦结婚,他就没有责任和义务再为父母的财产劳动,而是为了自己的个人财产。 同时也意味着家庭财产的破裂,除了幼子会继承父母的房子外,父母应该要为每一个儿子准备一所房子。 当儿子结婚时要得到他应得的那份家产,包括土地和房子,女儿出嫁时要给予大量的现金、珠宝和器皿作为嫁妆,这些东西远远超过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能力, 甚至可能会因此造成经济困难。 所以大多数父母会在表面上做出渴望子女进入婚姻状态,但实际上父母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家庭利益而有意延宕孩子的婚期。 父母的自私在夏尔巴社会的传统里也得到了支持,夏尔巴人的婚礼通常分为六个阶段,各种各样的婚礼活动极其繁琐而昂贵,父母的拖延便被合理地解释为他们没有能力为子女举办婚礼,而在拖延的这段时间里丈夫和妻子一般会继续住在他们各自的父母家庭,从而能够继续为父母的财产劳动。
第三, 孩子的婚姻使父母遭遇社会危机。 根据夏尔巴人的继承规则,理论上由幼子继承父母的房子,并由他赡养父母。 但事实上,年老的父母在儿子的房子里几乎变成仆人,婆婆与儿媳之间也会有摩擦。 年老的父母也意识到这些问题,所以他们或保留一小块土地盖一所小房子或是买一所小房子自食其力,尽可能地保持独立。 所以夏尔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多或少地会被子女遗弃,至少会被忽视或被冷漠地对待。 在夏尔巴社会中,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拥有的东西,家庭和财产不仅是生存的源泉,也是一个人自我的基础,一个人一生的意义和价值与家庭的事业是一致的。 夏尔巴文化中,孩子的婚姻危机和自身的老龄化危机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个人生存危机,也是在社会方面的个人身份危机。
孩子的婚姻所带来的危机是基于夏尔巴人以核心家庭作为最基本社会单位的社会结构,所以父母尽可能长时间地阻止自身核心家庭的瓦解,但同时孩子也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家庭而在父母的晚年背叛父母,最终父母被孩子抛弃。 在夏尔巴人的婚姻中完美展现的夏尔巴人的精神气质也决定了夏尔巴社会一种贪婪、吝啬和封闭的个体及核心家庭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单位。
夏尔巴人步入老年后, 不仅生命力量在下降,而且社会地位也在下降,面对死亡的临近和对社会生活的无力感最终使得夏尔巴人在年老时向佛教寻求精神慰藉。 他们对孩子不抱幻想,而是希求于神灵,努力实现自身的个体救赎。 赎罪仪式也加强了夏尔巴人的封闭性,只有当一个人逐渐衰老时才会意识到做功德的重要性,才会关注自己死后的命运,“一旦一个人失去了他的家庭,或者在其他方面发现家庭对他的支持不够充分,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除了宗教,他没有其他的‘避难所’”[2],“赎罪仪式的目的是产生真正的佛教个体, 与社会分离,不期望从他人身上得到任何东西,也不给予他人任何东西”[3]。
赎罪仪式也为即将要面临孩子婚姻的父母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避难所”。 对于夏尔巴人的年轻人而言,婚姻的利益和僧侣的禁欲理想生活之间充满矛盾与对立,但是对于父母而言,个人利益和宗教理想实际上是紧密相连的,父母延宕甚至反对子女结婚的行为与宗教的救赎规范不谋而合。 因此赎罪仪式使父母从与子女在婚姻上的矛盾与冲突中解脱出来,即使不是完全的脱离也至少帮助他们与冲突保持一定距离。 赎罪仪式以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把父母从对孩子的依赖中解放出来,转而关注自身的个体救赎并倾向于宗教。 最终,宗教在解决人生危机时战胜了社会。
(二)供养仪式(Offering rituals)
供养仪式并不是一个专门的年度性仪式,而是在很多年度性仪式中都会出现的特定环节。 供养仪式有一个基本的仪式结构。 仪式总是以净化仪式开始,通过向地方神供奉祭品来净化仪式地点和仪式参与者,之后伴随着诵经声,神灵被邀请前来参加仪式,喧闹的音乐声、缭绕的香烟和撒向天空的粮食、啤酒都是为了吸引神灵的注意力,神灵被邀请附着在用青稞面团捏制而成的朵玛上。 代表神灵的朵玛被放置在寺院或房子外面的四个方向以保护地方的边界, 代表恶魔的朵玛是作为恶魔的食物,通过暂时满足他们贪婪的欲望来引诱它们进入寺院。 当诵经声和音乐达到高潮时,代表恶魔的朵玛会被狠狠地扔掉,意味着恶魔已被驱逐出去,神灵开始尽情享用整个祭坛的供品,喇嘛们为神灵诵念颂词。 村落的代表在祭坛前磕头,既表示对过去过错的歉意也请求神灵能够帮助人们净化罪恶。 仪式总是以tso 宴席结束, 这些供品是已经做好的或是能即食的食物,陈列在祭坛底部的长凳上,这些食物在供奉完神灵后会分给在场的所有人并当场吃完,实现人与神灵之间的共食。 喇嘛们的诵经声愈来愈低,暗示着神灵的离开。 最后,祭坛被拆卸,酥油灯待其燃尽,喇嘛们带走生的粮食,朵玛被孩子带回家送给生病和年老的人或者喂给村庄里的狗。
供养仪式的期望是祈求神灵能够继续保护村民并帮助村民战胜恶魔,仪式的实现手段是使神灵变成人类。 先是通过朵玛的象征意义给予身体,朵玛最主要的意义是作为神灵临时的“身体”,每一个神灵都有一个规定的朵玛,每一个朵玛都有来自它所代表的神灵的名字和身份,因此当神灵的名字被召唤时,他就会前来附着在朵玛上,接受人们的敬意并倾听人们的祈求,然后通过祭坛摆放的其他供品的象征意义给予神灵以感官和思考等“六识”,再进一步通过“八供”给予神灵各种感官享受以刺激和唤醒神灵, 最后通过tso 宴席实现人与神灵之间的共食。 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神灵快乐,“现在,他任由崇拜者处理了”,“神灵已经变成了人, 被困在身体里,充满了感官的欲望”[4]。 这一过程展现了在身体方面的矛盾,因为神灵本身是无形的,没有感官上的欲望,更不需要任何东西,然而在仪式中神灵不仅被给予身体,还被供奉供品。 在宗教的观点中,身体此时被消极地看待,身体成为了感官享受的代表,从而引导人性进入罪恶。 然而,除非人们积极地通过供品和神灵保持联系,否则神灵将会退出与恶魔的斗争,任由恶魔摆布人类。 “根据一位村民在谈论家庭要进行季节性供养仪式时说道,‘如果你不进行这些仪式,伟大的神灵将会离开’,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在喇嘛诵经的指定时刻,房屋的主人要反复呼喊,意思是‘祈求神灵不要离开’”[5]。
因此,供养仪式的重点不在于战胜恶魔,而是要获取神灵作为人类盟友的支持,也就是激发神灵的积极的愤怒。 给予神灵身体和各种感官享受,甚至是污染性的供品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激怒神灵的企图,以唤起他们强烈的反应,使他们愿意帮助人类参与到与恶魔的斗争中。 这是仪式在情绪上的双重性过程, 人们既要使神灵快乐又要使神灵愤怒,而神灵的情绪转变是仪式的核心与动力,最终的结果也具有双重性即达到神灵对恶魔的愤怒和对人性的积极性的仁慈,情绪的转变在仪式中主要是通过朵玛表现出来。 对于朵玛的不同处理方式也表现出神灵的愤怒和恶魔的愤怒之间的不同,神灵被邀请附着在朵玛上并给予一系列的感官享受以唤起神灵的积极的愤怒,而恶魔的朵玛不仅被狠狠地扔掉,还要被打碎。
但是,使神灵变成人的过程仍然不完整。 虽然神灵已经被赋予了身体与人性,但是他们仍然缺乏人性的最后一个关键维度,即社会性,这一赋予由tso 宴席完成。 宴席作为仪式的结束,神灵正是在宴席中被象征性地给予人类的肉体和感官享受,在这里神灵享用的是真正的人类的食物, 而不是朵玛、香这些神性食物。 因此,朵玛在供养仪式中的象征意义最初是作为神灵的身体, 但是随着仪式的进行,朵玛作为食物的象征意义占据主导地位,神灵对人类食物的享用代表着神性的堕落,并在宴席中真正实现了人与神灵的共食。 “换句话说,在tso 宴席中,通过最明显的社会好客(聚会)的形式,神灵最终成为社会的盟友。 至此,他们才真正地被人性化。 只有在tso 宴席,当神灵被尽可能地完全‘人性化’时,他们也才能宣称是‘快乐的’”[6]。 宴席总是愉快的,它所表现的是神灵最终转变为积极的、仁慈的、愉快的心情,最终与人们结成联盟并渴望帮助人类战胜恶魔。 这一过程再次展现出身体方面的矛盾,也展现出宗教理想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宗教理想贬低身体并强烈反对任何不利于救赎的感官享受,社会的实用主义则认为感官享受不仅满足了个人的愉悦还是社会的一种建构机制,这种建构正是表现在夏尔巴人的好客(Hospitality)中。
好客是夏尔巴人处理社会事务的重要手段,好客使夏尔巴人获得社会合作和互助,因此在供养仪式中,世俗视角最为盛行,“它可以被看作是最彻底地把系统拉向世俗利益和体验的方向。 在其他仪式中,运动是朝向反社会的、超越社会的立场,在这里的运动是相反的方向,把神灵和宗教与社会过程联系起来, 并通过在文化中最标准的社交模式来实现。 ”[7]事实上,整个仪式都是好客的社交方式,从仪式的开始到结束,村民们一直是作为主人,神灵是被邀请的客人。 夏尔巴人在仪式中通过一系列行为使神灵“成为人类”,“我已经为你供奉了供品,现在你必须做我要求的任何事情”[8],强迫神灵“帮忙”。然而,从宗教的观点看,围绕着供养仪式的好客是不道德的,比如在宴席上一位喝醉的父亲会试图强迫他的僧侣儿子喝啤酒, 它挑战了宗教的禁欲伦理,因为仪式是通过一系列反宗教的感官诱惑和污染使神变成人。
可以看出,整个仪式展现出夏尔巴人道德水平的低下甚至是没有道德水平。 他们对于救赎几乎没有渴望,但他们又是佛教徒,这其中的矛盾便是通过仪式来弥合,“通过确实人性化神灵,同时通过将它们作为集体道德斗争的工具,神圣化看似反宗教和邪恶的社会形式”[9],夏尔巴人通过朵玛强制性地把神灵变为可操纵的对象, 从而获得自身的福报,使夏尔巴人让宗教服务于他们而不是与他们作对。如果说,赎罪仪式是宗教战胜了社会,人们变得像僧侣一样,人类最终认同了神灵,供养仪式则完全反转过来,神灵变得像人一样,神灵最终认同了人类。
(三)驱魔仪式(Exorcisms)
介于赎罪仪式和供养仪式之间的是驱魔仪式。驱魔仪式总是与葬礼相连,死亡被夏尔巴人认为是最大的污染之一。 因此,驱魔仪式被看作是有关净化的仪式,“为了清洁所有的脏东西”,“为了清洁所有坏的味道”[10],驱魔仪式也必须要作为葬礼的结束仪式。 和供养仪式类似,驱魔仪式的目的也是为了驱逐恶魔,但是驱逐手段有所区别。 夏尔巴人将供养仪式和驱魔仪式统称为kurim:前者,人们可以召集所有的神灵,通过供奉祭品请求神灵加入人类一起战胜恶魔,当恶魔意识到人类与神灵的联盟的强大后,它们会感到害怕并自行离开;后者,人们被要求为恶魔供奉能够满足它们的供品,恶魔在得到满足后会自行离开。 所以,供养仪式的重点在于动员神灵,并不会直接面对恶魔,而在驱魔仪式中,动员神灵虽然同样重要,但重点在于要直接面对恶魔。
一般的葬礼都以一个单独的仪式do dzongup结束。 在仪式中,人们会用泥巴和青稞面团捏制成一个老虎的形状,老虎以站着或跨步的姿势立在一块木板上。 在老虎的周围还有三个用青稞面团捏制成的人形:一个人在老虎的前面引导,一个人跨骑在老虎身上,一个人在老虎的后面赶虎出城。 写着疾病和恶魔的名字的纸条被插入虎的背部或人形里。 在场的每个人会拿着一小块青稞面团,绕着自己的身体一圈后,在手中捏制以留下手指和手掌的痕迹,然后放置在木板上。 这些面团叫作pak,代表转移走身体里所有的“坏气味”,并会跟随着老虎一起被赶走。 老虎被放置在葬礼房间的中心,并面对着门。 一些青少年穿着破烂的衣服扮演peshangba,或是拿着刀叉,或挥舞着棍棒。 喇嘛们开始念经,恶魔通过念咒被召唤进来,少年们向着门的方向激烈地跳舞, 看起来就像是想冲出门但是却不能的样子。 随着经声和音乐达到高潮,其中一个peshangba敲响铙钹,另一个peshangba 拿起老虎,整个队伍跳着舞出了门。 到达村庄入口的佛殿时,虎形会被扔掉,并被peshangba 砍成碎块。 砍完之后,peshangba脱下衣服,继续边唱边跳,沿路返回。 因此,在驱虎仪式中, 老虎是放置恶魔的容器,peshangba 像是战士,他们要护送老虎出城,出城的过程是驱逐恶魔的过程,砍虎的过程是毁灭恶魔的过程,也就是说,人们将老虎视为恶魔,并认为他们能够通过武力或暴力杀死恶魔。 但是,一位喇嘛对此说道,“他们太无知了……你杀不死恶魔,只能怜悯它们,给予它们想要的,满足它们所有的需求”[11],恶魔是杀不死的,它们只能通过喂养和贿赂来控制,这样它们就会自行离开,所以还要举行第二个驱魔仪式,富裕或虔诚的家庭还会举行gyepshi 仪式。
举行gyepshi 仪式之前要先建造祭坛。 建造一个完整的gyepshi 祭坛是很复杂的, 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整个祭坛被放置在一个巨大的图像即佛陀打开的手掌上。 祭坛的中心是一个巨大的朵玛称为lut,它象征着主人自己也就是主人的替罪羊。 为了能够生动地代表人,lut 的面部会用宝石装饰, 穿着华丽的衣服,还有一张咒文,喇嘛在一面写上主人的名字、出生日期和其它内容,另一面是印好的要求恶魔离开主人的咒文。 围绕着lut 的是四类同轴的环形祭品,分别是100 个微型的用泥土做成的神殿、100 个仪式食物、100 个酥油灯以及100 个微型lut。 每一类祭品的供奉对象都是特定的恶魔。gyepshi 仪式驱逐的恶魔是一个群体, 称为“four Dü”,象征“four Dü”的朵玛被放置在佛陀的手的四个指头处,有时也放在祭坛的四个角上。 佛陀的神像被放置在手腕处。 祭坛一建好就可以进行仪式。喇嘛们开始念经以建立起与神灵的联盟,并向恶魔展示供奉给它的祭品, 要求恶魔在满足后自行离开。 参加仪式的人们向祭坛抛洒花瓣和粮食。 在仪式的结尾,所有的东西排成一列,最大的主人朵玛排在队头, 排在后面的人们用篮子装着其它祭品,每一个篮子上面都放着象征恶魔的朵玛。 象征恶魔的朵玛连同它们的祭品会被粗暴地对待,但不会像驱虎仪式那样被砍成碎块, 而是恶魔们被告知如果它们不接受供品从而平静下来, 并试图回来制造麻烦的话,喇嘛们将会把它们砍成碎片。 之后,代表主人的lut 被小心地放置在村庄的佛殿里,喇嘛们穿着佛衣围着它跳舞,以表达人们已经摆脱恶魔的幸福。最后,要把佛陀的神像放置在lut 曾经放置的地方。
“恶魔是极其贪婪的、恶毒的、掠夺成性的生物, 他们漫步在世界上只会导致各种麻烦——疾病、死亡、使人堕落和破坏”[12],暴力和贪婪是恶魔最显著的特征,它们对于食物贪得无厌,贪求各种物质性财富以及感官上的愉悦和满足。 夏尔巴人认为,恶魔生来是贪婪的,人类也是如此,贪婪被认为是人类基本的人性,而人们也意识到这些恶魔其实是人的心理投射,所以这些恶魔是杀不死的,人们只能将象征自己的朵玛喂食给恶魔,使它满足欲望后离开。 正如主人将代表自己的替罪羊朵玛lut 精心装扮后供奉给恶魔, 比起驱虎仪式的暴力,gyepshi 仪式强调的是人们通过为恶魔供奉精心制作的、美丽的祭品来喂养和贿赂恶魔,满足恶魔的要求,这样恶魔就会自行离开,不会打扰他们。 “仪式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把佛陀的神像放在lut 曾经放过的位置,而lut 已经被喂给了恶魔,因此,在最后时刻,人们已经超越了对肉体和物质的依恋,现在‘成为了’神灵”[13],人们在将朵玛喂食给恶魔时就已经抛弃了对肉身的执着和对感官享受的贪恋,以达到一种纯粹的精神状态,超越对死亡和世俗财富的关注,最终还是宗教取得了胜利。
三、夏尔巴人的宗教实践、社会结构与精神气质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奥特纳对于夏尔巴人的仪式的分析始终与其社会结构相关并形成复杂的张力。 赎罪仪式展现的是与夏尔巴人强调核心家庭的社会结构以及婚姻之间的张力;供养仪式展现的是与夏尔巴人的社会性好客之间的张力;驱魔仪式虽然表现了宗教战胜恶魔的主题,但是奥特纳未能在夏尔巴人的现实生活中找到合理的对应。 因此,夏尔巴人的宗教仪式并非只是单纯地处理人与神灵之间的问题,更多的是用来处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张力。 奥特纳认为,尽管夏尔巴人所信奉的是社会性更加强烈的、 更富有同情心的大乘佛教,但是,“夏尔巴人的佛教在很多方面很难被认为是正统的,但是它保留了佛教的核心倾向,即孤立和分散个人,贬低社会纽带和社会互惠”[14]。 为了突出夏尔巴人的特质,奥特纳将生活在大乘佛教影响下的夏尔巴人与谭拜亚(Tambiah)讨论的生活在小乘佛教影响下的泰国人进行了比较。
功德是小乘佛教中最重要的观念。 根据功德的因果报应和转世的观念,个人通过供奉寺院和僧侣积累功德,从而在下一辈子得到好的转世。 因此,在泰国东北部的村庄里,寺院通常建于村庄内,村民与僧侣有着紧密的日常接触和联系,村民们把供养僧侣作为日常。 相比之下,夏尔巴人的寺院一般建在高处或难以到达的地方, 村民们缺乏布施的热情,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供养寺院,村民们只会在一些主要的节日前往寺院,僧侣几乎远离村民的视线与思想,僧侣仅仅是为了葬礼被邀请前往村庄或是为了一些特殊的诵经, 而后者很罕见并且昂贵,僧侣在这两种情况中也仅仅是受到个别家庭的邀请。 事实上,夏尔巴人的大部分僧侣是由其家庭供养,很少受到村民的供养,这就意味着这些僧侣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禁止从事体力劳动,这使夏尔巴人认为僧侣更懒惰、更贪婪,僧侣寻求的也只是自身的救赎,并不在意俗人的需求。 在谭拜亚的描述中,“佛教仪式中的和尚被喻为‘功德的田野’,上至国王下到平民都期望通过在这块‘田地’中撒下功德的种子, 确保此世和来世的福祉”,“和尚成为俗人获取功德的媒介”[15],村民和僧侣有着互惠关系,村民们日常供养僧侣,反过来这些僧侣会为村民们定期且频繁地进行功德仪式。 而对于夏尔巴人而言,虽然他们承认做功德是一件好事,但是他们对做功德的行为并不具有普遍性的关注。 总之,夏尔巴人对于宗教和僧侣是一种怨恨的态度,但是他们仍然身为佛教徒,宗教仪式便成为夏尔巴人获取福报的主要媒介。 因此,不同于泰国的佛教靠着大众的布施生存,佛教与社会之间形成紧密的嵌合关系,夏尔巴人的佛教并没有与社会之间形成紧密的嵌合关系,因而他们保留了佛教自身对自我救赎的个体主义追求,并通过宗教仪式获得个体救赎。
而且,夏尔巴人的佛教体系与卫藏的社会明显不同。 塞缪尔(Geoffrey Samuel)认为,“西藏是一个无国家社会,格鲁派所主导的政治只在卫藏有限的区域内行使政权,而更大规模的西藏社会是靠着教派组织的发展来维系的, 在这个教派网络之下,存在着大量的部落社会”[16]。 塞缪尔也认为,在卫藏区域, 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权力体系无所不在,行使专制权力的组织是喇嘛教会,真正的部落社会大多仍旧存在于西藏的边缘地带。 卫藏地区在佛教后弘期的前200 年左右的时间里,寺院在宗教、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同时取得了决定性的地位,几乎完全掩盖了王权和贵族的影响,不同教派之间的纷争也导致政教合一无从实现,直至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才终于完成统一,并将其置于个人的最高权威之下,西藏自此形成了一个以喇嘛为首的统一的神权体系。 “当我们将轴心时代的眼光引入到西藏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西藏实际上是一个格外有趣的地方, 因为世界上所有进入了轴心文明的社会,只有西藏的喇嘛教会最终几乎完全战胜了世俗贵族,教会制度的过度发育反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东方专制主义形态,世界上绝少有哪个教会组织能够像西藏的格鲁派教会这样全部垄断土地、历史书写和救赎财”[17]。所以,在卫藏的社会中,教会几乎完全整合了王权和贵族体系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而夏尔巴人的教会体系不发达,使得佛教体系无法完成对社会的整合,只能成为夏尔巴人存在的两个方面即社会的与宗教的层面,并始终与社会之间保持了复杂的张力。 因此,夏尔巴人的仪式体系更多的是用来协调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与夏尔巴人保留个体主义追求相关的是夏尔巴人自身的精神气质。 正是通过这些仪式使我们得以认识夏尔巴人的内在精神结构,即格尔茨所讲的“精神气质”(ethos),“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是格调、性格及生活质量,是它的道德风格、审美风格及情绪,它是对他们自己及生活所反映的世界的潜在态度”。[18]这些仪式充分地表明了夏尔巴人的个体主义, 因为参加这些仪式的夏尔巴人都是作为个体,并非作为某个社会群体或社会分类的代表,他们所寻求的是个体救赎,他们并不关注集体救赎。 这些仪式也表明了夏尔巴人贪婪的人性,他们对人性是持批评的态度, 他们认为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私的、贪婪的、吝啬的、利己主义的。 夏尔巴人的道德水平也是低下的,他们对于救赎并没有渴望,但他们依然是佛教徒,依然渴求个人的福报。 那么,夏尔巴人本身贪婪的人性、对福报的渴求与佛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如何弥合,夏尔巴人的解决方法正是这些宗教仪式。 格尔茨认为,宗教的意义只能“储存”在象征中,这些宗教象征又在仪式中得到生动的表现。 在夏尔巴人的仪式中,最重要的宗教象征就是用青稞面团捏制成的朵玛。 在供养仪式中,人们通过朵玛将不可见的神灵在身体的维度上变为可见的、可操纵的对象强迫神灵接受人们的祈求战胜恶魔。 在驱魔仪式中,人们是将象征自己贪婪的人性的朵玛喂食给恶魔,使恶魔在满足食欲后自行离开。
同时,夏尔巴人自身的精神气质与夏尔巴人以封闭、吝啬的核心家庭作为最基本社会单位的社会结构是契合的。 所以,父母不愿在婚姻中放弃他们的子女, 即使最终会有新的婚姻和家庭的成立,父母依然会尽可能地阻碍或延长给予他们孩子经济上的独立性和婚姻上的独立性。 在实践中也被证实,夏尔巴社会的个体往往是自私的,在社会结构上鼓励封闭的、自主的、基于私有财产的核心家庭,整个社会也没有必要的社会组织形态。 因此,夏尔巴人的精神气质和社会结构为夏尔巴人在宗教理想上对自我救赎的个体主义追求奠定了社会基础。
奥特纳对于夏尔巴人仪式与象征的关注有着丰富的学术肌理和学术背景,尤其也体现出奥特纳对于实践这一概念的关注, 这一点在奥特纳10 年后发表的《20 世纪下半叶的欧美人类学理论》(又译为《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一文中流露出来。 奥特纳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表明在人类学中一种新形式的理论取向正在诞生即实践(practice),为此奥特纳梳理了20 世纪60 至80 年代欧美人类学的理论发展,包括60 年代兴起的象征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和结构主义,70 年代兴起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派以及80 年代兴起的实践论。 其中,能够明显地看到以奥特纳的导师格尔茨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其研究具有深远影响。 格尔茨认为,“文化不是以概念的形式存在于人脑之中,而是公共象征体系的具体化,即文化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意义模式, 社会成员借助它来交流,表达世界观、价值取向、道德气质及生活态度,代代相传”[19]。芝加哥学派关注的是象征如何塑造社会行动者的世界观,进而格尔茨倾向于探讨和分析文化的“精神气质”而非“世界观”,倾向于情感的分析而非对认知的理解。 格尔茨也坚持从“行动者”的角度看待文化,“必须置身于文化所建构的情境中。 文化不是空洞的制度,而有实在的逻辑(或特殊符号的连贯性)。 这套逻辑即文化要素之间的关系准则,是以人的行动为基础的符号配置,人的行动是有秩序的,循此才能作出与其所处环境相符的解释”[20]。 这些理论和学术倾向在奥特纳对夏尔巴人的仪式研究中都得到了较清晰的阐述、应用以及延伸。
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奥特纳在夏尔巴人的仪式研究中所流露出的对实践这一概念的潜在关注。 奥特纳将以索绪尔、帕森斯为代表的实践论和以布迪厄、萨林斯等人为代表的实践论区分为旧实践论和新实践论。 “新实践论承认系统(社会与文化)对人类学行为和事件过程的影响是强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新实践论寻求的是解释人类行动及其与系统(社会或文化)相互适应的关系”[21]。这套系统并非是单纯地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化单位和社会单位等这些要素组成, 而是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新实践论并不想人为地把系统分割成这些组成要素,进而讨论谁决定谁或是谁引出谁,它的分析重点是用实践来沟通整个系统。 对应于夏尔巴人,实践就是奥特纳所分析的三个宗教仪式,这种实践特性与夏尔巴人的社会结构、佛教体系、精神气质这一套系统紧密相关,并在彼此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张力。 最终,夏尔巴人通过宗教实践实现了自我救赎的个体主义追求,协调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弥合了精神气质与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
四、结 论
夏尔巴人虽然信奉社会性更强的大乘佛教,但是不同于信奉小乘佛教的泰国人将佛教相对成功地转变为一种社会性的、交流的、共同的、保持团结的宗教,夏尔巴人的佛教是一种反社会的、不交流的、私人的、个人主义的宗教。 夏尔巴的佛教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教会系统不发育,宗教组织内部的权力系统不足以压制个体主义,而夏尔巴人佛教所保留的个体主义是以夏尔巴社会的社会结构为基础。 通过上文的讨论,夏尔巴社会本身是原子化和个体化的。 在个体的层面上,夏尔巴人的精神气质是自私的、贪婪的、吝啬的、利己主义的;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上,拥有私有财产的核心家庭是夏尔巴社会最基本的社会单位,而且夏尔巴社会通过一系列文化手段和社会实践既反映了也再生,加强了作为单位的家庭的封闭性和独立性,核心家庭也对社会交换和社会关系保持一种相对封闭和谨慎的态度。因此,虽然事实上夏尔巴社会围绕每个核心家庭会形成长期的互助集团,但是互助关系的范围是有限的,互助关系是通过一对一的核心家庭之间的直接互动来运作,村庄的边界有效地标示了个体互助关系的界限,互助关系也不能延伸到其他的关系中。
奥特纳通过整本书的讨论,证实了夏尔巴人的个体主义和夏尔巴社会的原子化,但是她对夏尔巴社会的家屋继承制度之间的横向关联性(也就是村落的措哇制度)没有进行充分的研究。 事实上通过夏尔巴人的代际关系也能看到村落的组织确实不发达,而且整个夏尔巴社会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威体系,村落的政治结构是高度无组织的,没有人拥有任何真正的权力, 也没有必要的社会组织形态,连内部秩序的维护方式和力量也十分脆弱和混乱,这才使得夏尔巴人的佛教和社会之间的嵌合不深, 佛教本身成为一个和社会相互紧张的因素,两者之间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张力和矛盾,佛教无法完成对社会的整合,最终身为佛教徒的夏尔巴人在世俗生活中以宗教仪式为主要媒介实现宗教理想上的个人救赎,并用来协调佛教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大乘佛教和密宗佛教更关心社会,社会性更加强烈,关注集体的救赎,呈现出一种整体主义。 然而夏尔巴人的佛教作为大乘佛教传统的一部分却保留了佛教自身的个体救赎,而小乘佛教的传统是更严格地关注个人的救赎,呈现出一种个体主义。 然而泰国的佛教却是靠着大众的布施生存,佛教被实践为一种为人们所共享的社会化宗教,这正是奥特纳通过夏尔巴人和泰国人的对比所要强调的,即佛教所呈现的个体主义或是整体主义更多取决于社会本身的气质和结构, 而不是宗教本身的教义,也就是探求佛教的个体化趋势和藏传佛教组织的整体化趋势与村落组织之间的关系。
注释:
①具体内容参见刘志扬:《谢丽·奥特纳与 〈珠穆朗玛峰上的生与死:夏尔巴人与喜马拉雅登山运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