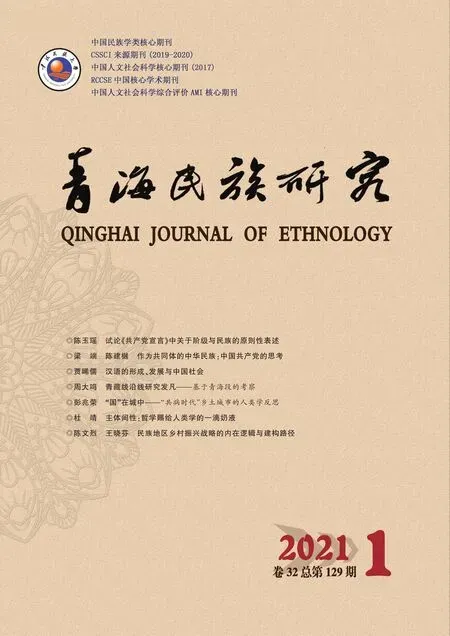主体间性: 哲学赐给人类学的一滴奶液
杜 靖
(青岛大学,山东 青岛 266071)
现代人类学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存在。假定没有人类学者与其研究对象之间达成的主体间性,现代人类学怕是难以成长起来。 但长时间以来,科学主义民族志作品没有展现出主体间性的魅力,或是它们始终不肯承认存在主体间性。 直到后现代实验民族志觉醒,并努力在表述中呈现出来,主体间性才摆脱了被无视的地位,被推向了前台。
主体间性首先是针对主体性这个概念来的。 在社会与文化的形成上(包括人的生成),持有主体性信念的学者认为,世界是基于人的意识或意志而形成的,因而在学术研究中努力展现被研究对象的主体性。 显然,这样的理解只是突出了个体的主体能力和价值,没有追问主体或主体性的由来问题。 那么,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原因在于主体间存在相互作用,具备某种统一性。 我们研究文化、研究社会、研究世界,不只是到个体的主体那里去寻找答案,更应该到一个主体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间的互相作用和关系中去寻觅。 这样一个思路,就给现代性的单纯主体性理路致命一击。 具体而言,是把康德的唯智主义和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受此影响的研究 (自我中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主体论)放倒在地。
A·莱西在《哲学辞典》中将“主体间性”定义为:“一个事物是主体间的, 如果对于它有达于一致的途径,纵使这途径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 ……主体间性通常是与主观性而不是客观性相对比,它可以包括在客观性的范围中。 ”①这里表明,主体间性概念并未完全抛弃主体性,实际上是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但不允许停留在主体性这个平台上。 也就是说,思考的逻辑起点不同了。 “人是意识的存在”。如果说这句话的逻辑思考起点是个体的主体性,那么,当用主体间性思考问题时便是从个体的主体性所组成的集成块或结构链起步,再也不是原子式的思维了。
其次,主体间性涉及理解(understand)问题,即一个人对他人意图的推测与判定。 如果不关涉理解,那么何来“主体”? 主体是理解的主人。 所以,得先有个主体,且不止一个,才能谈论到“主体间”,有了“主体间”才能理解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的那种状态。什么状态?达成统一意见或彼此理解的状态。这就是“主体间”的“性”或“性状”。 具体到人类学来说,就是在做田野工作时作为人类学家这个主体必须理解被研究的主体,而被考察的对象也必须理解人类学家。 如果双方不能沟通、交流、理解,人类学家将何以向世界去呈现或表述人家? 当然,也包括表述人类学家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交往、互动及结构化的关系。
但是,必须意识到:主体间和主体间性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主体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它并非我们想象出来的一个空间,尽管有时难免想象。
一、人类学研究中常见的三类互为主体性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能够“互为主体”,即意味着在心意上能互相意会和了解。 如果心意不能相同或沟通,那么,人类学家便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无法达成互为主体间性,民族志资料的提取将是非常困难的。
就一个指示性陈述而言,比如在一场谈话和交流中,会涉及发话者、受话者和它的指谓(陈述谈论的东西)。 发话者被这个陈述安放并暴露在“知者”的位置上, 受话者被置于表明同意或反对的境地,指谓也被指示性陈述以特有的方式当成是某种要求得到正确认同或表达的东西。[1]显然,在谈话和交流开始之前,两个主体都对对方作出了可以沟通或理解的判断,以及期待。
就人类学研究而言,若从与人类学家互动的对象和互动的时间性来考虑,可将主体间性分成同生性主体间性和错时性主体间性,以及人与人搭建的主体间性、人与文本之间的主体间性等两组类型。
人与人通过交往或互动而搭建的主体间性可分为同生性主体间性和错时性主体间性。 同生性主体间性是指互动的主体都身处当代或当下,二者要面对面。 具体到人类学来说,则是作为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建立的互为主体性。 这是一种活人与活人之间的心灵交会模式,更是人类学向来所惯用的常态或主流形式。
这种模式下的“互为主体”交流始自现代文化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他帮助我们确立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研究规范。 当年,他在考察西太平洋航海者时通过参与观察和访谈获取信息。[2]具体来说,就是人类学家跑到田野里去,与被调查对象在一起,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在活动中观察、交流和体悟。 这是人类学家获取信息的三种手段中最基本的一种形式。
观察、交流和体悟的关键媒介是语言。 注意,这里的“语言”是一个宽泛概念,它既包括与被调查对象的言语交流,也包括各种体语、神情、仪式、行为及人类的各种制造物里所蕴含的符号意义。 当然,也包括各种自然自在之物,因为各种自然自在物早已以概念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意识里,并在大自然中存在,当我们目光触及的刹那便用早已储存好的概念去感知和理解。 就各种符号的制造者或传递者而言, 任何制造物都浸润着人类的心意和情感,制造或表达过程中是一个符码编织过程。 在观察者而言,观察是一种视觉的捕获。 一切在我们面前,但不是一切自动送入我们的眼睛,而是我们的目光伸出去将其摄入我们的视觉神经系统,然后传入大脑中的意义处理系统进行解码。 所以,观察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意义活动,这是一个既向外又向内的双重感知过程。
语言交流 (这里专指通过声音传递的形式)是一种听觉的收取活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语言是组织在声音物质中的思想。[3]言说者与闻听者一来一往,同样存在如上述的语义编码与解码的过程。 对于言说者而言,他有主动送入的意图;但对于闻听者来说,听觉不能像视觉系统那样将“触觉”伸出去而主动获取,听觉是被动的,但在交流中闻听者有一种待听的心理期待。 但无论言说者还是闻听者皆是以双方能听得懂的语言进行交流。 语言的交流是最容易建立互为主体性的。 语言交流同时也伴随着观察,除非一方或双方是盲人。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 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一方面肯定这一看法,而另一方面又并不完全赞成这种庸常的见解。 他说:“事实上,只有非常小的部分语言得以外化, 即由我们之口说出,或者如果我们是在使用手语, 就是用手完成的表达。……绝大部分的语言都是内在的;外在的语言只有一小部分,外在的语言中真正用于交际的所占比例就更小。”[4]那么,语言大部分用途是干什么呢?乔姆斯基说:“很有可能其99.9%的用途都是内在于心智的。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跟自己言语,要做到不跟自己交谈需要强大的意志。 自我交谈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使用完整句子。 很明显,我们一直在大脑中使用语言,不过,是以同时存在的碎片、片段等形式在使用。 ”[5]
体悟与直觉,就是乔姆斯基这里讨论的内在于心智的语言活动。 它往往是个体瞬间在没有跟他人互动的情形下独立完成的。 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中大量使用领悟与直觉去领悟对方的内心。[6]
第一种互为主体性是发生在当下的事情。 从语言时态论,人类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共处于现在进行时状态中。 但第二种互为主体性即错时性主体间性则发生在口述史采录过程中,我们与口述史中的人物之间的互为主体性是通过口述报道人来建立的。 从语法时态上论,口述史中的人、物、事相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处在过去时或完成时状态,不论口述人是讲述自己的过去还是他人的过去。
人类学家与口述报道人之间的互为主体性建立是很容易理解的,在本质上与第一种无异。 因为口述报道人在回忆,人类学家在倾听,二者工作的媒介是语言,他们共处同一场景中,且同处现在时或现在进行时中。 复杂的是,人类学家要准确地理解或走进口述史材料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即与之建立互为主体性, 恐怕只有通过口述者的语言来完成。 这时,人类学家必须确保口述材料的准确性,否则就难以借助口述史料去重构历史。 当然,退一步讲,不论口述人的报道是正确的,还是歪曲或错误的,都不要紧,因为人类学家有时想弄清的事情并不在过去,而是思考口述人为何这样讲或为何那样讲。 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清醒:口述材料是口述人“达志”的一种手段。 所以,讲对与讲错都值得研究。那么, 这样的研究就又退回成了上述第一种类型了。
历史人类学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已经远逝的古人。 人类学家既不能与他们坐在一起互相交流与观察,也不能通过口述史来捕捉到他们。 只能通过他们留下来的文献资料 (大部分以文字形态表现出来)理解他们:与古人会心,或神交古人。 这就是本文所言的第三种人与文本间的互为主体性。 在这种交流活动中,古人隐藏在文献中来到身处现代的我们的面前,我们通过视觉及大脑中的语义处理系统而走进古人内心世界。
依赖于语音学, 西方现代语言学得以建立起来。 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看来,文字是语音的附属产物,语音是语言的符号。 这种见解完全是基于表音系统的语言实践经验而获得的,未必就适于表意系统的文字体系。为此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建立了“文字学”,意图使关于文字的学说从一般语言学中独立出来。 他主张,一种活生生的东西必须具有从原语境抽离而进入其他境遇的能力,文字的特点和优点恰恰在于能够切断与原语境的关联, 自由的“意义撒播”。 历史事件的解释如果完全偏向“口头语言”和谈话,或许就失去了这一本真的意义经验。[7]德里达文字学理论确立了文字具有独立分析的价值和地位。 德里达为一切依赖文字的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为文字文本或文献可以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
那么, 身处现代的我们为什么可以直通古人?在一篇前不久刊印出来的文章里我作出了分析,这里略加引述。 我认为,现代人与古人拥有一套共享的理解范畴和认知方式。 祖先们一代代对我们进行语言训练, 往我们脑子里安装了一套语言符号系统,借着这套符号系统去读懂古人和他人。 尽管随着时代与社会场景的变迁而不断产生出一些新的语词,但我们可以明白古老词汇的意义,而且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也还在使用。 至于语法、文法之类的东西,同样如此。 这就意味着,作为现代的我们身体里本就含有古代的东西。 比如,来自祖先的感觉及感觉世界的方式,也包括感觉和呈现自我的方式。 我们本身就与古代不曾割裂,与祖先是一个绵续体,且一直就在历史之中,在精神和情感上与古人共处一个语义场中。 所以,作为现代的我们可以与古人互为主体或达成主体间性。[8]
需要说明,读者与文字的作者和文本达成主体间性,有时需要借助与另外的文字作者和文本达成的主体间性。 比如,我们读《诗经》,有时看不懂,就需要借助前人的笺注或分析。 这样,首先必须理解前人的笺注和分析,而理解前人的笺注和分析势必与前人达成主体间性。 可见,读者与文字文本及其作者间的主体性达成往往需要多级台阶,层层剥笋而入。
我们还可以从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一些话来理解:“话语通常要说出来, 而且总已经是(有人)说出过的。 话语即语言。 而在说出过的东西里向已有领会和解释。 语言作为说出过的东西包含有一种对此在之领会的解释方式。 解释方式像语言一样殊非仅止现成的东西;它的存在总是此在式的存在。 ”[9]而在说出过的东西背后已有一种领会,因为“说出过的东西”保存着“对他人的共同此在的领会以及对向来是本己的‘在之中’的领会”。[10]另外,“说出来的话语即传达。 其存在所趋向的目标是:使听者参与向着话语所谈及的东西展开而存在”。[11]
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在谈论主体间性的时候是以“先验主体”作为前提的(详见下文)。 我上述语言学的理解或语言模塑论的解释与之相反。 我认为,一代代的语言训练使得我们能与祖先或古人互为主体, 由此诞生出主体间性,即主体是后天被语言模塑出来的。 在此,语言是媒介,是桥梁。 在某种意义上,共主体间性,即共语言性。 语言应该成为未来人类学思考的聚焦点。
马凌诺斯基确立的现代人类学研究范式是关于当代或当下的一种学术实践。 在当代或当下,即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共处或同在时是可以达成互为主体而理解的。 这是一种关于“活人”及其所创造的社会与文化的考察。 但这样的思路能不能用于回到古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 我们能不能与已逝的古人达成互为主体性理解? 马凌诺斯基及其追随者没有交代, 处于后现代民族志反思前沿的保罗·拉比诺(Paul Labinow)和约翰尼斯·费边(Johannes Fabian)等也没有讨论过。
德里达和马凌诺斯基以及部分口述史学者的主张是互斥的。 而同生性(这一概念可见下一部分)的历史民族志是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所没有的,而为人类学的历史人类学所独享或包容。
我们必须清楚,人类学田野过程中涉及的主体间性, 不仅仅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还有被研究的对象或人群内部的主体间性。 每个人类学家在做田野时都会遇到,即我们不可能总是遇到一个人且只研究一个人, 而是要研究很多人、一群人。 这些人可能在一起做仪式,也可能在一起讨论问题或从事生产, 甚至打斗之类的活动,他们首先必须达成主体间性,如果没有主体间性就无法在一起互动。 我是指同一文化里也需要主体间性,同一文化正是因主体间性才得以存立,才有社区聚落,才有共同体等。 因而,在做田野工作时,我们首先必须弄明白他们之间如何达成了主体间性以及达成了什么样的主体间性。 这个理解过程同样涉及多级主体间性工作。 首先被研究对象之间的主体间性, 其次是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 而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总体达成主体间性之前,研究者首先必须与被研究人群的单个主体间形成主体间性,实际上共涉及三个认知层面。 总之,一句话,用研究者参与的主体间性去解读并呈现被研究人群的主体间性。
建立在主客认知模式基础上的科学的人类学以客观地描述或呈现被研究对象为目的,往往把人类学家与“土著”间的互为主体性在最后生产的人类学文本中隐藏起来。 持此信念的人类学家相信,对象是可以被观察、描述和呈现的。 据此撰写出来的民族志作品,我们通常称为科学民族志。 在这类作品中,作者大多使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即使使用第一人称,也多用复数形式“我们”。 科学民族志的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着清晰的边界和距离。
这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所确立的一种理性思维方式: 认知的主体和客体有着明确的边界,彼此不具备互生关系。 笛卡尔的思想造成了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分离以及主客观的对立,在这种认知模式中,主体极具膨胀性。
但到了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尤其是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后,伴随着西方知识界对主体性的重视,一部分人类学家开始反思并试图在民族志作品中反映或呈现出这种主体性以及由此搭建的主体间性。 设计或实践出来的这类民族志作品习惯上被称为后现代民族志或实验民族志。[12]典型的方式就是对话文本或类戏剧文本的产生。 但较早思考主体间性的人是英国的人类学约翰尼斯·费边和美国的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 一位是通过纯理论的批评来达成对历史的清算;一位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进行思考。
二、人类学对主体间性的觉醒之一:约翰尼斯·费边的思考
费边于1960 年代末至1970 年代末十年间构思并完成了《时间与他者》一书。 那么,作为一位先驱者,费边当时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发现了这个问题呢?
人类学家所栖存的社会与被调查的社会共处于一个全球时空之中,且人类学家本人与被研究的人群也同时共处同一个田野之中,而人类学家最后在民族志中生产出来的、关于被研究者的形象却是异于自己的形象? 为什么田野考察时是同生性的研究, 而在文本表述中却采用异时性的诠释方式,故意拉开时间的距离? 约翰尼斯·费边发现,人类学的研究原来是一项关涉价值的研究,是一个讲究区隔的认识论工具,目的在于建构他者,属于一种书写的制造。 即在文明-野蛮、现代-传统的叙事结构中,将被研究的社会与文化处理为“过去时”,被研究的人群代表着野蛮、落后和传统,而作者及作者所身处的社会则代表着先进的另一端,里面蕴含着知识生产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费边斥责这种民族志书写行为是对同时性或“同生性的抵赖”,批评现代民族志处理时间的方式为“生殖分裂性时间方式”,他为此提出了一种基于互为主体性的民族志构想。[13]
具体而言,他说:
拆解人类学的帝国主义的计划必须以民族志的实证主义概念作为替代方案。 我提倡向语言和一种民族志客观性概念的转变,这种客观性是作为交流对话、互为主体性的客观性(intersubjective objectivity)。 可能我没能说得更清楚,我要求将语言和交流当作一种实践来理解,通过这种实践,认识者不能将宣称对被认识者拥有支配权。[14]
尽管费边强调互为主体性,但是他仍以客观性为追求的根本目标。 这不是说他的研究是主观的,而是他想努力在民族志作品中展现互为主体性。 在以往的研究中,尤其是科学民族志中人类学家是隐身的, 费边倡导民族志必须勾勒出人类学家的形象,展现人类学家与被研究对象间的互动。 其次,他的这种民族志设计推崇语言交流,或者说是建立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语言交流或沟通基础上的。 他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应该是一种语言为基础的沟通性行动。 试想,假定人类学家与被研究者没有语言交流,或者不通过语言交流,那么,如何能够“互为主体”?
费边强调这两者重要还不是关键,而更为关键在于他主张客观性有赖于“互为主体性”才能实现:
第一,在人类学的调查中,客观性既不在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也不在于资料的给定性,而是应该植根于人类互为主体性的基础上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intersubjectivity)。
第二,人类学调查中客观性的获得是藉着进入沟通互动的场景(context)而实现的,而要建立或呈现这种场景,就必须借助一种媒介,这种媒介就是语言。[15]
在当时,费边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受了若干学者思想的启发。 主要有:以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为代表的德国实证主义思想、 语言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互为主体性认识论”(intersubjective epistemology)、语言人类学家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16]的“言谈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或“沟通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概念[17],还有现象学思想家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关于主体间性时间的分析[18]。 而在人类学里边, 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从意义的角度理解时间(《巴厘岛的人、时间与行为》)也对费边发生了影响(其实,格尔茨也是受惠于舒茨的启发)。[19-20]
费边的讨论实际涉及一个对等性或平等性问题。 他隐含着一种观点:观察者一方不能把自己的文化和栖身的社会价值观念凌驾于被观察的社会文化之上,以高高在上的态度俯视全球。 费边态度实际上秉承了博厄斯(Franz Boas)[21]和赫斯科维茨(Melville J·Herskovits)[22]以来的文化相对论精神。费边之后, 法国人类学家阿兰·李比雄 (Alain Le Pichon) 提出了 “互观人类学”(reciprocal anthropology)。 这一理论主张,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主体性。 因而,不同文化之间也会构成主体间性。 “互观人类学”意在使交流双方都为对方的文化建立一套人类学叙事。 赵汀阳认为,李比雄致力于推动一种具有“跨主体性”的跨文化——不同于所谓的文化交流,并非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发现各自的本地知识和文化特产,而是试图以不同文化为出发点来共同创造一种新文化。[23]即,不同的文化之间都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眼光和地位,然后互观,并最终在民族志文本中呈现出来。
这种平等的互观体现在与费边同时代的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民族志田野工作中。
三、人类学对主体间性的觉醒之二:保罗·拉比诺的思考
1968 年和1969 年,保罗·拉比诺遵照其导师克利福德·格尔茨的安排前往摩洛哥开展田野调查,五年后出版了以田野工作为审视对象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这项工作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拉比诺与被研究人群之间建立的“主体间性”。 可以说,他是直接把二者共同搭建的主体间性作为民族志文本的聚焦与呈现的对象。
首先,让我们来看他对“主体”的界定。 保罗·拉比诺用的词汇是“自我”。 但这个“自我”并非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一个文化的存在物,一个集体意义上的个体。 这一点费边没有明确指出,而李比雄的不同文化间的互观人类学理论也漂浮着,没有在细部上落实到位。 拉比诺说:
按照保罗·利科的说法,我把解释学(hermeneutics,希腊语,相当于英语中的“interpretation”)的问题界定为“通过对他者的理解,绕道来理解自我”。尽管本书某些段落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色彩,但绝不是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 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讨论的自我完全是公共意义上的,它既不是笛卡尔信徒们的纯粹脑的思考,也不是弗洛伊德门徒的深层心理学自我。 毋宁说它是通过文化中介、具有历史定位的自我,在持续变化的意义世界里发现自身。[24]
这是一个文化的主体性。 拉比诺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文化性主体。 作为一个厌倦了自身社会的美国大学生,他知道美国社会正被深刻的结构性问题所困扰。 而现有的知识界和政治体制也无法提供答案。 在对自己的文化失望之后,抱着朝圣的精神,在导师格尔茨安排下前往摩洛哥做田野,希望在异文化里寻找到解决美国社会的智慧。[25]可以说,拉比诺是西方社会和文化里一类人的一个代表。
在通往摩洛哥的塞夫鲁乡村的路途上以及呆在田野中的时候,拉比诺接触到了该社会中的形形色色的个体,他们是他的线人或资讯人,拉比诺与他们建构了不同的交往模式,即不同层次上的主体间性。
作者一到摩洛哥, 接触的第一个线人是开旅店的法国失意商人理查德,他处在摩洛哥社会的最外层。 理查德虽然身在摩洛哥,但却是摩洛哥文化的局外人,当然,也是法国社会的边缘人。 第二个线人,即阿拉伯语教师易卜拉欣,他是一名摩洛哥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文化掮客。 他同样是个摩洛哥的边缘人,但他是一个融合了社会科学家所说的传统与现代的人。 他作为欧洲社区和摩洛哥社区之间的中间人,他是商品和服务的包装者、传输者、中间人、政府信息的官方翻译者。 他愿意将拉比诺引向摩洛哥社区的边缘,引向摩洛哥文化的新城区,但却深深抵制任何更进一步的渗入。 拉比诺视易卜拉欣为朋友, 但易卜拉欣把拉比诺视作一种个人生存资源。[26]第三个人是来自西迪·拉赫森村的塞夫鲁居民阿里, 他是当地城市社会与乡村社区之间的中介,是局内的局外人。 拉比诺由他引荐而进入当地人村庄。 第四个线人是阿卜杜拉·马里克·本·拉赫本,他是拉比诺在西迪·拉赫森期间的线人。 拉比诺雇佣他是通过合同来实现的,因而,二人之间是契约关系,而非友谊,这与拉比诺与阿里之间自由轻松、相对随意的互动模式不一样。 拉比诺和马里克的交往更为严肃,这种关系状态是由马里克导向的。 自此以后,在社区里拉比诺都身不由己,接受村里人对他的各种安排,忍受村里人对他的种种利用。 但正因如此,他才有机会得到圣人后裔做线人,洞悉了村庄里的社会脉络。 最后的报道人是一个名叫本·默罕默德的大学生。 他抱着寻找宗教智慧和力量的目的回家度假,希望做文化的复兴工作。 默罕默德与拉比诺存在分歧又彼此尊重,因而成了好友。 分歧的原因:各自都是自己文化里的存在,都不想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历史意识;同时,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传统中存在深刻的危机,但依然要回溯传统以期复兴或是寻求慰藉。 正是在与默罕默德的交往中,拉比诺认识到:就本质而言,世界上不存在他者,大家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 因而又都是对方了解自我的他者。[27]拉比诺与这些线人达成了不同的主体间性。拉比诺与他们遭遇或互动的过程实际上是拉比诺身上所携带的美国文化与摩洛哥不同文化层次间的邂逅与阅读。
可以说,拉比诺文本的全部目标就是展现与这些线人的互动、理解以及再互动、再理解。 按通常的道理, 一个调查者是通过线人的合作获得情报,然后撰写民族志作品,去呈现那个异文化的他者。 但现在拉比诺却把与线人的打交道端上了民族志的前台。 这在之前,却是以人类学家田野日记的方式公布于世的。 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笔记》、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弗里曼的《玛格丽特·米德与萨摩亚》和奈杰尔·巴利的《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日记》等作品。②可以说,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 在人类学民族志著述上是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具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双重价值。
主体间性究竟怎么生成出来的? 保罗·拉比诺在机理上有着非常清晰的认识。 拉比诺是格尔茨的学生,自然懂得“意义”对于理解人和文化的重要性,因为格尔茨格外关注“意义”,尤其欣赏马克斯·韦伯的“人是悬挂在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的那句名言。 人是在内心里感觉到某种意义才开始行动的。 拉比诺当然清楚,他毫无疑问地接受了“文化事实是阐释,而且是多重阐释”的精神。[28]
借助于利科的哲学思想,他阐明了主体间性的生成机制:对于他(利科)来说,现象学是一种描述,他描述“一种运动,在此运动中,每一个文化角色是在其之后的而不是它之前的运动中发现自己的意义:意识产生于其自身和它之前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步消失后又被保留在下一步里。 ”[29]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主体的意识以及意义的产生是后发的,两个主体基于这样的后发心理实现了连续性互动,进而搭建起主体间性空间。 他摒弃了教授们谆谆告诫他的问题导向式的、人类学家可控的研究[30],转而追求“随遇而安”的种种际遇,且以这种际遇作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 其实,科学民族志作者大多情况下也不能把控自己,未必就按照自己的学术预期或研究计划而开展田野工作。
进一步,拉比诺提出了一种“田野作业的辩证法”思想。 这种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共建或互构。
拉比诺认为, 田野作业是反映与直观的辩证法,二者都是文化建构。 在具体的田野工作中,我们不可能时时处处按照学科规范、朝着既定目标去开展田野调查,因为日常生活或互动是一个不断变动且富戏剧性变化的世界,人类学家和被访谈或观察对象处于不断变动、调整与适应状态中。
我们以拉比诺在研究线人阿里的治疗术时的情景来说明。 当拉比诺第一次看见这种活动时全神贯注,整个意识都被吸引和控制了,但随着田野作业的继续, 又复连见证了几次类似的治疗过程,拉比诺就不再以为然了,因为它很快成了拉比诺知识的一部分,甚至是他的世界里的一部分。 同样,当作者按照欧洲医学和人类学的知识观察和询问阿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阿里平常的治疗思维方式,使他被迫持续地反思自己的行为,并对其作客观化审视。 结果,阿里结合了某些欧洲经验和智慧来实施治疗,并将自己的世界按照拉比诺可以理解的方式向拉比诺呈现。 这是一个局内人向局外人将自己的文化转述给局外人的过程。[31]在这个经验基础上, 人类学者拉比诺进行了理论的抽象和概括:“与阿里在一起, 出现了双方对经验和理解的共建过程,一个相当脆弱的常识领域:常常会断裂,又随时续上,然后再检验;开始是这儿,接着是那儿。 ”[32]显然,这里的“理解”(understanding)指涉的是对“意义”的把握。
拉比诺笔下的主体是具有反思认识能力的。 在摩洛哥柏柏尔人眼里,拉比诺的线人马里克既不富裕也不贫穷,看起来代表一种“中等”状态。 这既是他的认识,也是他所在社会里对他的定位。 但当拉比诺为研究摩洛哥人的财产且选择了马里克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将其财产一项项登记出来,并予以对象化,马里克开始认识到他的自我形象暨他们自己的文化里头的身份归类与拉比诺给出的分类有所不同,这令马里克难安。[33]这个询问和登记财富的过程, 实际上训练土著将自己的生活世界对象化,而不是他们原来的那样的对象化和自我反省。 正是通过田野作业的互动,使马里克滋生了一种意识的双重性,马里克被迫以一种新的方式看待自己。
由此,拉比诺意识到他收集的材料再也不是单纯地客观对象, 已经被调查者所携带的价值观念、文化方式等给模塑了。 他说,首先,我们自身是通过我们提出的问题和我们寻找理解与经验这个世界的方式而历史地存在的;其次,我们从资讯人那里得到的解释也是以历史和文化为媒介的。 因此,我们收集的数据是被双重调节出来的,首先由我们自己的存在,然后是我们向资讯人要求的第二层的自我反省。[34]在另一处,拉比诺阐述道:“人类学家和他的资讯人都生活在一个经文化调适过的世界,陷于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35]在此,拉比诺清晰地意识到了材料是通过主体间性收集起来的,那个预期的客观对象消失了。
至此,他给出了田野工作,实际上也就是主体间性一个明确的界定:
田野工作,是一个交流的阈限模式的主体间建构的过程。 互为主体,字面上理解,不止一个主体。但其所处的背景既不完全在这, 也不完全在那,所涉及的主体没有共同的假设、经历和传统。 他们的建构是公共的过程。 本书的大部分都在关注我和那些摩洛哥朋友们为了交流,而逐渐建立起来的这些对象。 一个中心主题就是,交流常常是艰苦而局部的。 另一个同等重要的主题则是:它并不完全是模糊不清的。 它是这些极点之间的辩证过程,总是被重复,却从不完全一样。 而这正是田野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36]
我们看到,拉比诺与费边不谋而合。 我在《知识人类学何以成为一种可能? 》一文中称这种对主体介入的研究行为的研究为“在象研究”。[37]拉比诺有这样的思想, 与他受到的哲学训练有密切关系,包括他的人生成长期间的哲学氛围。
早在中学时代,保罗·拉比诺就对哲学感兴趣。1960 年代早期,作为一名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保罗·拉比诺就一度沉迷于哲学史。 他的哲学导师理查德·麦基翁(Richard McKeon)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教哲学, 认为哲学是镶嵌在实践和世界之中的知识。 当然,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ierce)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也关心经验话题。 不过,相比来说,法国哲学更加关注对经验和实践的思考。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他同时也是一名人类学家)等人分别把经验理解为意识、行动和政治,对经验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 同时,法国人类学家卢西恩·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对普遍理性的思考、莫里斯·林哈特(Maurice Leenhardt)对宗教体验的关注、乔吉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对性欲、异国情调和主体性的讨论都吸引了拉比诺的兴趣。 罗伯特·贝拉(Robert N.Bellah)是一位宗教学家, 同时也是解释社会科学的领袖。1975 到1976 年拉比诺参加内拉举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讨会。 在贝拉的哲学探讨会上,他结识了威廉·沙利文(William Sollivan)、休伯特·德赖弗斯(Hubert Drefus)这样的优秀哲学家。 德赖弗斯把海德格尔的哲学传给了拉比诺,接着海德格尔又教给他大量欧洲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 1978 年,正当拉比诺在与德赖弗斯热烈的讨论期间, 米歇尔·福柯正访问斯坦福大学,德赖弗斯和拉比诺乘机邀请福柯介入到他们俩的争论与对话之中。[38]哲学家讨论经验和实践问题显然不是通过经验研究去思考,而兼具哲学训练和人类学修养的拉比诺肯定想在人类学的学科范式内去思考哲学家的问题。 当然,也包括去思考上述哲学家讨论的意识、行动、政治、宗教体验、主体性等内容。 所以在给中译本做的序言里,拉比诺借用了皮埃尔·布迪厄的智慧,将“哲学地反思田野作业”作为序言题目。
就拉比诺关心主体间性这个概念而言,除了与上面所述学者有关外,还当与现象学家舒茨(Schutz Alfred)有关,因为我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的文后参考文献里发现了他参考了舒茨1970 年出版“On Phenomennology and Spcial Relations” 一书[39]。在这一点上,他与费边共享过舒茨的现象学智慧。
费边和拉比诺之后,在理论反思方面,才有萨义德的《东方学》[40]、马尔库斯和费彻尔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41]等著述问世以及写文化学派[42]的诞生。 这些都多多少少受了费边和拉比诺的影响,或与二人共同分享智慧来源。 而在民族志方面,则出现了青安娜(Anna Tsing)的《在钻石女王的国度》这样的优秀作品,展示了人类学自我与民族志他者之间互为主体性的同生性问题。[43]正如马蒂·本泽(Matti Bunzl)在评价费边的影响时所云:“如今人类学知识的呈现成为特定情境下人类学家与报告人之间对话性互动的产品。 进而,更广泛的表达形式是作为作者的‘我’更加显著。 民族志的互为主体性成为构成性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典型的现在式呈现出来。 它具有作为人类学的同生性和反思性实践基本载体的作用。”[44]至于影从拉比诺的人类学民族志著述同样不在少数,在此不再赘言。
接下来,我们将系统地梳理和考察西方哲学家关于主体间性的思考。 希望寻找到费边、拉比诺以及受他们影响下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和写文化学派的智慧来源。
四、主体间性在哲学史上的思考
在西方哲学史上,讨论主体间性的学者主要有胡塞尔、海德格尔、舒茨、伽达默尔等人。
现象学大师胡塞尔首先提出了 “主体间性”问题,其目的在于让“他者”成为“自我”的本质构成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给予他者“对话性”的地位。[45]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由三个层次组成:
第一,每个人多方面变化着的意识自发性活动的综合体与此世界相关。 这是他所处的世界,并同时是他的周围环境。 人,属于他周围世界的每一种对象或事物。 这个综合体由以下诸项组成:研究考察,说明和概念描述,比较和区分,收集和计数,假定和推理。 简言之,具有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理论化意识。 另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情绪和意志的行为和状态。 比如,喜欢与不喜欢,喜悦与悲伤,渴望与逃避,希望与恐惧,决断与行动。 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笛卡尔的用语cogito(我思)中了,它包括单纯的自我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每个人以自发的注意和把握来意识到这个直接在身边的世界。 虽然每个人生活于这个自然生活中,但他的生活不断采取一切“实显”生活的基本形式,不论他是否陈述这个“我思”,不论他是否“反思地”朝向自我和诸我思(cogitare)。
第二,对自己适用的上述种种,也对“我”在我周围世界中发现的其他人有效。 在把他们当作为人来经验时,每个人把他们中的每一个都理解作和承认作一个像自己一样的自我主体,并把他们理解作与周围自然界相关。 但当这样理解时,是把他们的周围世界和“我”的周围世界都客观地当作同一个世界,对此大家都能意识到,虽然方式各有不同。
第三,我们与我们的邻人相互理解并共同假定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时空现实,一个我们本身也属于其中的、事实上存在着的周围世界。[46]
尽管胡塞尔说“所有这一切都包含在一个笛卡尔的用语cogito(我思)中了”,但胡塞尔谈论的认知主体仍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理性主体,那是一个经过现象学“还原”技术加工后的自然之“我”,一种“自发的注意和把握”。 这个“我”不是后天的社会或文化训练出来的,更不是在现代学术体制中成长起来的形象,那是一种自自然然的认知“裸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主张的主体间性也是通过现象学的“还原”或剥离技术而得。 当他把所有的人都还原成一类人,即自然之我的时候,主体间性便由此构建起来。
海德格尔沿着其老师胡塞尔的足迹往前思考。其“他人的共同此在”概念就是为“主体间性”概念而设计的。 首先他认为,“他人”并不等于我之外的全体余数,而我也不是从全部余数中兀然特立出来的“我”;“他人”是那些多半与我们无别、且我们也在其中的那些人。 至于“共同”,则是一直此在(Dasein)式的共同。[47]海德格尔在阐述完这层意思后,接着论述道:“由于这种有沟通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 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 ‘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 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48]请注意这里的“沟通性”和“分有”两词汇,它们意味着“我”和“他人”的“共同世界”是建立在“沟通性”基础上的,且能彼此分有;共同世界是我和他人建构出来的,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先验地存在着的。 那么,何以沟通、分享和共在?借助话语活动。在海德格尔看来,像发言、协商、说情、演讲、陈述主张、赞许、呵责、请求、警告等等皆是话语;话语总是关于某种东西的话语,关涉言和听,一端是表达或传达,一端是领会和理解;在话语中,共在以形诸言词的范式被分享着,分享的不仅是“话语所及的东西”,也包括“表达方式”或“理解方式”。[49]需要说明,这里的“话语”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霸权话语”(Gramsci·Antonio),也非一般讨论的“话语权”里的“话语”。
另外,必须在此交代上文里的“此在”概念。 可以说,“此在” 与 “在”(Sein,or being) 和 “在者”(Seiende)等概念占据着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地位。“在”,即存在物的显现或在场,它思考的是:事物何以在起来? 不是一个静态的状态,而是攸关事物的生成,或某个观念的澄明与实现。 “在者”,显示出其存在的现实以及仅仅是观念中的事物与现象。 “此在”,即“人”,他是追问在者的独特的在者,作为在的意义的发问者和追究者的人的存在。[50]可以说,在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此在” 这个概念相当重要,因为“此在”既是人类学家也是其被研究的对象——人群或个体,是面对彼此才生成的互为主体。
海德格尔在另一处说:“人从来就不是简单地或原初地作为具体主体与世界并列,无论人是单个或群体,都是如此。 他原则上不是或不是一种其本质存在于主体-客体关系中的意向地指向客体的(认识论的)主体。 相反,人在本质上是首先存在于存在的开放性中,这种开放性是一片旷野,它包括了主-客体关系能呈现于其中的‘中间’地带。 ”[51]海德格尔实际上是说, 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主-客体关系中而指向于客体的,而是存在于主体到主体或主体与主体中而相互指向的关系。[52]海德格尔的这个观点表明了他理解的“主体”不再是胡塞尔现象学框架中的“主体”或“我”。 胡塞尔的“主体”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人,而海德格尔的“主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视野中的人了,并且这个主体具有自身参与生成的意味。 原本的“主-客”关系,经海德格尔的努力就转变成了“主-主”关系,且主-主关系构成了分析的基础或起步。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在人类的认知情景和内在自觉状态中来理解时间。 现象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舒茨则考察了时间在交流中的角色。 他在《一起制作音乐》中说:“显然所有可能的交流皆基于一个假设,即交流基于交流者和信息接收者相互之间的调和关系。 这样的关系基于内在时间之中有关他者经验流变的互惠共享,建基于一种共同的生动的现在,建基于这样的共同性是‘我们’的共同经验。 ”[53-54]这种“共享时间”即“主体间性时间”,亦即费边所言的“同生性”。 舒茨的研究受到过胡塞尔的表扬,尽管舒茨从未成为胡塞尔的入室弟子。 结合前面的论述我们看到,拉比诺只是把舒茨的“调和”换成“调适”和“调节”;至于舒茨的“交流”“共享”“共同经验”等词在费边和拉比诺那里都格外重视。
海德格尔解决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互为主体性问题。 由于每个人都具有主体,因而理解他们之间的互为主体性并不是一个难点。 但是,当一个人面对一个文本的时候,是否能达成主体间性呢? 要知道,文本不能像人那样在现实里与阅读者进行具有物理声音的说话,尤其反复地询问、辩难等。 海德格尔稍微向我们闪现了这方面的智慧。 比如,他说:“只有我们不去企图把事物硬塞进我们为其制造的观念的框框中去时,它才能向我们显现自己。 ”[55]什么意思?海氏是说,事物自己可以陈述自己。这为客体向主体转变打开了大门,因为客体获得了自由。
伽达默尔的主体间性思想主要体现在“视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这个概念里边。 简单说来,“视域融合”意指理解过程中文本作者的原初视域和解释者现有视域的交织融合状态。 尽管理解的过程受到“前见”(vorurteil)或“前结构”(历史和传统方面的,vorstruktur) 的影响, 但经双方互动出来的“视域融合”是个新视界,根本不同于文本和读者的各自原有视野,超出了双方原有主体性的预设。 这种新视界建立在理解的多次循环基础上。[56]海德格尔提出了事实性的或有关此在的解释学理论,伽达默尔受其影响。 在《真理与方法》的第二版序言里说:“我认为海德格尔对人类此在的(Dasein)时间性分析已经令人信服地表明: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本身的方式。 本书的‘诠释学’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57]
“视域融合”发生在多种场景里。 比如,“谈话”“文本(text)阅读”和“翻译”。最简单而且也是最经常的“谈话”和“文本(text)阅读”往往发生在两个“个体”之间。 谈话涉及交流的双方,构成说者与听者的关系,语言是媒介。 文本阅读涉及文本作者和读者,文本构成二者交流的媒介。 但是“翻译”活动要稍稍复杂些,如果是文本翻译,那涉及到文本、作者和翻译者;如果是现场翻译,则涉及到言说者、听者和同期声翻译这些角色,中间是指谓。 这些活动无一不表明:彼此沟通是需要主体间性的。 伽达默尔分别讨论了这几种情形[58],它们皆属语言的活动。
就在讨论“文本(text)阅读”的时候(当然,也包括文本的翻译),伽达默尔使文本获得了“主体”地位。 进一步,文本中的对象人物也成为了对话中的一员,由此摆脱了受制于自我主体的客体性而成为获得自主独立性的主体。 在伽达默尔的眼里,文本不再作为客体而出现,而是像另外一个“参加者”一样的主体。[59]也就是说,阅读者与文本之间构成了主体间性关系。
其实,萨特(Jean Paul Sartre)、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杜夫海纳(Mikel Dufrenne)等人也认为由文字构成的作品是相当于自我主体的“人”或“类主体”的。[60]这与伽达默尔有着一致的思想抱负。
从上述简要梳理中可以看出,有关主体间性的见解是非常多元的。 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是从认识论角度入手, 海德格尔是从生成的本体论角度讨论,伽达默尔则从理解或解释的角度审视 (带有前意识)。 此外,舒茨紧紧步随胡塞尔。 造成诸家见解不一的关键原因是对“主体”定义的千差万别。 胡塞尔的“主体”是一个还原出来的、自然的、未经现代学术体制训练的人;海德格尔的“主体”是一个经自我参与而生成出来的人,不是一个现成的此在;伽达默尔的“主体”即可以是人,也可以为文本,人有前见,但又有创造力。 两相比较,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之主体有自我制造与生成的意思。
我们看到, 在过往的主客关系认知模式中,认知的主体是主动的,客体是被动的。 即前者主动去观察、去认知,后者等着被观察、被认知,主客有着清晰边界。 但互为主体性的认知模式,实际上是把客体提高到主体地位,即客体不再是被等着观察与认知的对象,客体也有思考能力,对主体形成了认知和判断,由此积极介入了思考活动。 难道不是吗?人类学家在观察时被调查对象不也是观察人类学家吗? 为什么人类学家只在最后的作品中呈现出了自己对他人的观察与认知,却没有呈现被观察的对象对人类学家的观察与认知? 思考到这一步,那么,客体就不能再叫做客体,应该叫做主体。 知识的获得实际上是两个交流的主体互动的结果。
上述哲学家的成果, 特别是现象学的智慧,为人类学家探索互为主体性民族志提供了哲学基础。正如费边所言:“……就是在这样的脉络中,主体间性以及共享时间的问题成为现象学哲学的洞见,并持续地影响了人类学、社会学及语言学。 ”[61]
就历史人类学实践倾向而言, 伽达默尔的见解,特别是关于“文本也是一种主体”的看法,为历史学的历史人类学提供了认识论基础。 这是特别需要指出的。 可惜,中国的历史学中的历史人类学家从来就没有试图去寻找这种哲学的依据作为知识探索行动的出发点。[62]
五、总结与讨论
从田野调查到文献梳理和阅读,最后到书斋中的民族志撰写,主体间性是每一个人类学家都离不开的认知平台。 可以说,人类学的工作就是植根或搭建于主体间性基础上的, 这是我们的工作机制。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笛卡尔主客认知模式的影响,人类学家只在民族志作品中呈现自己的观察与认知,却没有允许被观察者对观察者的观察与认知露面, 没有呈现受观察者影响所感受到的被观察者,更没有展现自己影响的被研究人群在人类学家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映像。 人类学家在此任意恣肆自己的观察与书写霸权。 只到费边和拉比诺出来,才改变了主体间性长期被默杀的地位。 之后,有许多人类学家跟进,遂形成了一股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和写文化学派思潮。 在这个人类学知识谱系脉络里,费边和拉比诺处在这一学术流派的先驱位置。 但是,他们的智慧之根却又植于哲学之中(包括语言学),尤其是现象学,是哲学思想给了他们以启迪。
费边和拉比诺的成功,以及两位开启下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学派和写文化学派席卷业界的现实启发我们:今后必须跳出学科藩篱,借鉴哲学等学科的智慧,才能实现中国人类学的弯道超车,并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可是,目前业内的形势不容乐观,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类学工作者缺乏哲学修养、深度和问题意识,我们培养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大纲里也无哲学课程,原因在于我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人类学作品阅读上,且在人类学问题意识及脉络中徘徊,由此造成了中国人类学作品的集体复制与模仿。 到田野中去做哲学问题,应该是未来中国人类学的新生之路。
在我个人看来,主体间性是人类学家开展田野工作的一项技巧或技术,是人类学家获取民族志资料的一个平台。 通过这个技巧或平台,人类学家可以撰写两种民族志: 一种仍然是传统的科学民族志,即将研究对象客观化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将人类学家与土著的关系或互动作为学术考察对象的研究。 即皮埃尔·布迪厄所讲的“参与客化法”(participant objectivation)或“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 我想,即使拉比诺本人也没完全否定客观性研究,因为他依然任自己的《象征的支配:摩洛哥的文化形态和历史变迁》一书在世上传阅与流行。 要知道《象征的支配》是在同一个地点同一时段(1968-1969)做的田野成果,先于《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即于1973 年出版。[63]否则,他会做一个郑重的声明,废弃前书。 他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一书中也只是笼统地批评从前的精致的科学民族志或客观民族志,也没有拿自己的以往作品作靶子。 但后人似乎有意凸显他的反思精神而忘记格尔茨意义上的研究。
通过与被调查对象搭建起共同的主体间性去获取田野资料, 最后回到书斋撰写科学的民族志,仍然是一条可行路径。 正是两者之间存在共主体性,人类学家才能理解被研究对象,由此去描写他们,刻画他们。 就像拉比诺在与最后一位线人默罕默德的交往中理解的那样,如果各自撇去自己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其实人是一样的,即没有他者。既然如此,怎么不可以实现客观观察?
是让主体间性沉潜在民族志文本背后? 还是让主体间性直接跳出来,走向前台,成为民族志文本的聚焦对象?我认为,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民族志作者有权选择自己撰写什么和不撰写什么。 同时,任何撰写活动都要面对读者和社会的需求,不是任由人类学家自己说了算。
费边和拉比诺是同时段进行思考问题的,并不存在先后问题。 他们问题意识的趋同应该归于相同的哲学背景和学术兴趣。 是时间的拐点到来了,只不过有幸选择了这两位,让他们作为人类学界的代表去陈述集体的心声。 事实证明,他们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而存在的。
就主体间性这个概念而言,人类学还没有完全释放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能量。 无论费边还是拉比诺,抑或后面跟上来的后现代实验民族志与写文化流派,都只是参考了哲学里面的一或至多两家的学说。 通过上面考察我们看见,还有好几家的学说没有被使用和开发,人类学应该把更多的空间开放给哲学。 这一点远不像本体论回归的人类学那样宣称的,它们已经走到了尽头。 事实上,本体论回归的人类学也离不开主体间性这个平台。 否则,他们无法讲出被研究对象的故事。
主体间性,是费边、拉比诺和后现代反思民族志及写文化学派的核心概念和逻辑基石。 本体论回归的人类学若想超越它,首先必须解构或敲碎这一基石。 可是, 本体论回归的人类学没有这么做,相反,自己还不得不仰赖这一机制。 所以,本体论回归的人类学对它的否思是不成立的。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你无法阻止人们把与调查对象之间的互动作为人类学的考察对象。 只要有人感兴趣,且愿意这么做,后现代反思民族志和写文化学派就有存活的理由。 难道不是吗?③
最后需要说明,主体间性仅仅是社会人类学家或文化人类学家与其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这一概念并不适宜于体质人类学家,因为体质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生物性,而生物性是不存在主体意识问题的。 但是,研究体质人类学史则要用到这一概念, 因为体质人类学家之间会达成某种主体间性。 特定历史时期,体质人类学家间达成的主体间性往往影响了体质人类学学术实践和学科发展。
注释:
①A·莱西这个定义见诸A.R Lacy 主编的《哲学辞典》(A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第二版,该书由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 (Londen: macmillan press) 于1986 年问世, 具体见第113页。A·莱西只是谈出了主体间性的部分内涵,而非全部。事实上,哲学史上,诸家见解并不一致。 具体详见本文第四部分。
②国内学者庄孔韶近几十年来不断倡导“不浪费的人类学”。 其实,拉比诺等实践的这类后现代实验民族志和过往人类学家的田野日志可归属庄先生的“不浪费的人类学”概念之范围。 除了这类作品外,“不浪费的人类学”概念里还包含民族志电影和绘画等形式。
③近年来以朱炳祥等为核心的一批人类学家在《民族研究》上发表了一系列倡导“互为主体民族志”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类学家的向前探索精神。 如,朱炳祥的《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见《民族研究》2011 年第3 期)、《再论“主体民族志”:民族范式的转换及其“自明性基础”的探求》(见《民族研究》2013 年第3 期)、《三论“主体民族志”:走出“表述的危机”》(见《民族研究》2014 年第2 期)、《事·叙事·元叙事:“主体民族志”叙事的本体论考察》(见《民族研究》2018 年第2 期)和朱炳祥,刘海涛:《“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一个白族人宗教信仰的“裸呈”及其解读和反思》(见民族研究》2015 年第1 期)、朱炳祥、徐杰舜:《主体民族志与民族志范式变迁——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七十九》(《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 期)和刘海涛:《主体民族志与当代民族志的走向》(见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4 期)等。 这些作品声称超越了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设计蓝图,但就主体间性而言,两者实为共享。 我的意思是说,在根本的工作机制和原理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都离不开主体间性。 如想超越主体间性,或许应该求助后现代主义大师拉康 (Lacan,Jacaueo) 的 “我在我不思之处”。 只有在这个智慧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超越了后现代实验民族志的牢笼和藩篱。 世界,至少有一部分世界是落在“主体间性”或“互为主体性”之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