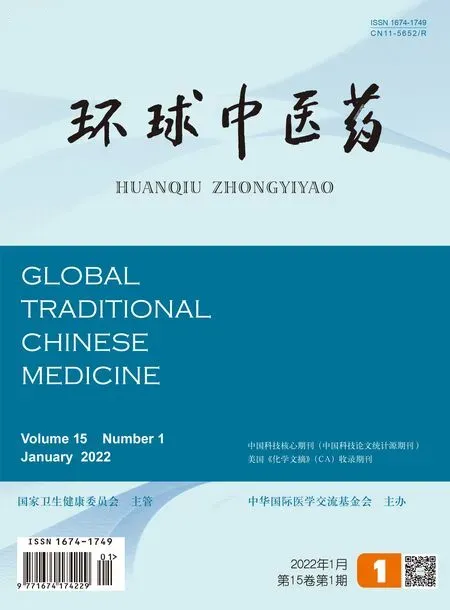壮医药特色名词术语英译刍议
蒋基昌 扶应钦 岑思园 林辰
自“一带一路”国家级合作倡议发布以来,中国民族医药对外发展的速度不断加快,并受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欢迎,这与中医药疗法独特、成本低廉、疗效显著的优势密不可分。壮医药作为目前传承发展程度较高的民族医药之一,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壮瑶医药振兴计划(2011~2020年)》等政策及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等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的带动下,壮医药的对外交流与推广需求激增,但壮语文规范形成较晚,无疑阻碍了壮医药国际化发展的进程[1-3]。英语作为国际社会通用度较高的语言,可应用于壮医药的对外交流,而壮医药英译工作的开展须以相关术语的规范英译作为基础保障。
壮医药名词术语是在壮医药领域用于表达相关概念的称谓集合,是对壮医药的理论和文化的集中展示,而壮医药名词术语中的特色术语则呈现出壮医药文化的精髓部分,其准确性不仅是译者对术语内涵正确理解的反映和体现,更能向世界传播壮医药承载千年历史的壮民族文化。
壮医药特色名词术语可按其描述属性分为具体术语、抽象术语和混合术语三类,不同属性的术语固然应遵循不同的英译原则进行翻译,但如何将术语背后所蕴涵的民族文化进行有效的信息输出是壮医药特色名词术语英译的重点和难点,下文将通过这三类术语的相关实例对此进行探讨和分析。
1 壮医药具象术语英译难点解析
具体术语是确指客观存在对象的术语,如“九龙藤”“壮医药线点灸”等。由于其真实存在的属性,在英文中基本都能找到对应的意思,故此类术语的英译一般遵循同一概念的术语尽可能只用同一对应词的“同一性”原则进行英译。当“具象化”术语与相似领域术语存在通用译名的情况下,其文化特色通过何种方式呈现是该类术语英译工作的重心。下文以药物和技法两类术语为例进行分析。
1.1 药物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壮药药材是中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绝大部分壮药已为历代诸家本草著作所载,并经后世实践得以考证并冠以拉丁名进行译名规范。为凸显该类术语的壮民族特色,可在参考中药术语“汉语拼音+拉丁药名”英译标准的基础上,将已行规范的壮文药名加入译文,如广西道地药材“鸟不企”可译为“Niaobuqi (AraliaeDecaisneanaeRadix, Doenghha)”,“一匹绸”可译为“Yipichou (ArgyreiaeAcuteHerba, Gaeudahau)”等。
其次,在早期以口口相授为教学模式的用药实践中,部分壮药存在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的情况。如冬青科植物“岗梅根”(RadixIlicisAsprellae,Laekcaengh)又称“金包银” “土甘草”。其中,“金包银”也是毛茛科植物铁线莲(ClematisFlorida, Raglingzsien)的别称,而“土甘草”在《广西中药志》又为玄参科“冰糖草”(ScopariaeDulcidiisHerba, Gamcaujdoz)的别名[4-6];又如,“白花九里明”在《壮族民间用药选编》《全国中草药汇编》《广西民族药简编》《广西本草选编(下册)》《广西中药资源名录》等文献中的基源为“东风草”(BlumeaMegacephala,Go’ngaihvenh),而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编写的《中华本草》中则将该药的基源标示为“假东风草”(BlumeaRiparia, Gonzya),二者属近缘种,虽均来源于菊科艾纳香属植物, 但在形态特征、地域分布、临证功效等方面仍存在区别[6-7]。这种命名的混乱极易造成壮药辨识的混乱,从而影响壮药的使用和推广,因此,对壮药译名实行“汉语拼音+拉丁药名+壮文”的翻译标准不仅是壮民族特征的体现,也能避免因“同物异名”或“同名异物”情况而导致药物在临床的混淆和误用。
此外,因早期缺乏统一文字,少数通过生产生活实践发现的药材未得以及时记录,以致相关信息甚少或缺如。如著名的解毒壮药“陈家白药”和“甘家白药”分别源于苍梧(今为广西梧州)和龚州(今为广西平南),因旧时为陈姓和甘氏家族所用,故以姓氏冠名。据《本草拾遗》记载,陈家白药“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毒……蔓及根并似土瓜……叶如钱,根似防己”,而甘家白药“味苦,大寒,小有毒。主解诸药毒,与陈家白药功用相似……叶似车前……根形如半夏”。虽因历史资料鲜少而尚未得到现代药学研究证实,但经现有文献考究,相关学者认为“陈家白药”与防己科头花千金藤相似,故可考虑借用“头花千金藤”的拉丁译名,并结合壮语读音拼写将“陈家白药”译为“Chenjiabaiyao (Chen′sStephanlaeCepharanthaeRadix; Cinz Maengzbaegmbouj)”[8]。而对尚未得以考证的“甘家白药”,虽与“陈家白药”在植物形态、毒副作用上有别,但在性味与功效上却大体一致,故可参照“陈家白药”将其拉丁名译为“Gan′sStephanlaeCepharanthaeRadix”;壮文名也予借译为“Ganh Maengzbaegmbouj”,故“甘家白药”译名应为“Ganjiabaiyao(Gan′sStephanlaeCepharanthaeRadix;Ganh Maengzbaegmbouj)”。虽然,这类借译造词法能暂时解决翻译中目的术语语义空缺的困境,但受众群体对此接受度和推广度的高低尚须通过长期翻译实践来验证,故在使用时应予斟酌考虑。
1.2 技法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壮医技法类术语名称基本能较为直观地反映出各类疗法的具体内容,通常是以“治疗部位”或“材料器具”或“操作方法”联合中心词“法”或“疗法”的形式进行命名:如以治疗部位命名的有“耳针疗法”,可对应译为“auricular needle therapy”;如以治疗器具命名的有“火功疗法”,可译为“fire therapy”;又如以操作方法命名的有“灼法”“刮法”等,对应译为“burning therapy”“scraping therapy”等。又如“拔罐疗法”(cupping)“针刺疗法”(acupuncture)“熏蒸疗法”(fumigation)等英译本身即为疗法称谓的,在英译时可省略“therapy”,避免赘译。
在众多壮医医技中,壮医灸法又因其“简、便、廉、效”得以高频应用和推广,并衍生出一系列烙印着壮族生活实践足迹的灸法术语。灸法术语在壮医技法类术语中占据了较大比例,故其英译成为了壮医技法类术语英译中的重点和难点。在处理此类术语的英译时,首先,应厘清“灸”的含义,辨明此“灸”非彼“灸”。壮医灸法中并非所有的“灸”都指代使用艾绒、艾炷或艾条的传统灸法,而在临床技法中以“燃烧”这一操作多见,故在翻译含“灸”字的非传统灸法术语时应以“burning”代替混淆概念的“moxibustion”,如“麻黄花穗灸疗法”和“药棉烧灼灸疗法”是将麻黄花穗、蘸吸壮药酒的棉球点燃后按压或烧灼于穴位或患处,故可分别译为“ephedra flower-burning therapy”和“medicated cotton-burning therapy”。其次,有些术语名虽无“灸”而实为“灸”,故在英译时应将重点放在中英内涵的对应与否而非简单停留在文字的对应上。如“鲜花叶透穴疗法”是将点燃的鲜花或叶片放置于穴位上进行隔灸操作,以期通过花叶之芳香达到治疗的目的,如仅按字面意思译为“flower-leaf acupoint penetration therapy”会让目标读者产生该疗法是“使用鲜花或叶片进行类似针灸透刺”的困惑,且没有体现出该疗法“灸”的特点,而译文“isolated flower-leaf burning therapy”中的“burning”不仅能体现该疗法使用烧灼或熏烤的操作方法,而且“isolated”能反映出“隔物灸”的操作特性。
2 壮医药抽象术语英译难点解析
抽象术语和具体术语概念相对,是指表达观念、概念或性质的术语,如“阴阳”“三道两路”“嘘”等术语。这类术语并非真实存在,而是需要通过联系到具体关联事物时才具有一定意义[9]。因此,这类术语的英译一般遵循使译文意思尽可能与中文术语内涵相对应的“对应性”原则进行英译。当抽象术语概念在出现多层含义甚或无英文对应词的情况下,如何最大程度地兼顾词义完整与文化内涵是该类术语英译工作的重心。下文以基础概念和病因两类术语为例。
2.1 基础概念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壮医药基础概念类术语是壮医药规律形成和发展的基石,是壮医药理论体系架构精髓的体现,因此基础概念类术语的英译在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这类术语大多是通过壮族先民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在头脑里形成的概念性认知,虽能在英文中找到对应词,但因壮汉文化表达有别使得源术语对应英文所表达与中文内涵存在差异,故其英译难点在于对术语内涵的准确辨析及其英译的准确把握。
如“三道”和“两路”是壮医特有的概念术语,因此,“道”“路”不能与现代汉语释义混为一谈。“三道”是与人体外界联系的通道:“气道”(包括咪钵等)为外界自然之气与人体之气的交换通道,“水道”(包括咪腰、咪小肚等)是水液代谢的通道,“谷道”(包括咪胴、咪隆、咪叠等)为食物消化与吸收的通道,而气体交换、水液代谢和食物消化与吸收都是升降出入的双向过程,故“三道”是沟通人体内外的双向通路[10]。“两路”是维持人体生理机能和反映疾病动态的两条内封闭通路:“龙路”为体内输送血液营养的路径,“火路”是信息传感的路径,而无论是血液循环抑或是神经传导,都是具有单一且不可逆的过程,故“两路”是连接人体各部而形成的定向路径。“道”主要强调“通”的特性,而“路”则强调定向属性。“passage”释义中有“a long narrow hole or tube in your body,which air or liquid can pass along”的意思,能对应上“道”的术语内涵,而“route”有regular”“particular direction”等单一指向性的定义特征,符合“路”的术语含义。其中,“两路”以比类取象的手法分别命名为“龙路”和“火路”:壮族文化认为龙能兴云生雨,滋润万物,以此譬喻濡养人体的血液循环,同时,壮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火势猛烈,便以此比喻神经传导之速。如“异化”译为“dragon route”和“fire route”,可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回译性,保留术语语源文化,但在西方文化中,“dragon”是邪恶之征,“fire”则显危险之象,故直译或会使译文不易于目标读者接受;若采用“归化”译法,在了解术语内涵的基础上意译成“blood route”和“sense route”,相较前者使译文更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壮医文化输出的损失。因此,可考虑以“异化”先行,“归化”为辅的形式英译为“dragon route (blood route)”和“fire route (sense route)”,不仅能重现壮医文化原貌,还能准确传递术语信息。
2.2 病因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处于南方亚热带的壮区山林茂密、气候湿热,又有使用“蛊毒”的悠长历史文化,因此,“毒”“瘴”“蛊”等是壮乡特有的致病因素,这也是有别与中医药及其他民族医药的特色术语。对这类包含多层内涵的特色术语,在英译时应注意把各层含义对应译出后根据术语所处语境斟酌选用,如出现因文化导致术语理解偏差情况的,应予择优处理。
如“毒”原指有毒植物,后为壮医引申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是痧、瘴、蛊等所有病因的总称,而狭义则指对人体产生毒性作用的物质总称,可对应分别译为“pathogen”和“toxin”,因二者英译含义不对等,不能等同互用,故在实际应用中须根据该术语所处语境斟酌选用[10]。又如,“蛊”是兼具壮医文化和医学内涵的一类致病因素,从文化层面的角度看,即广义的“蛊”,是指壮族民间流传的一种以有毒媒介物作用于机体,从而使之产生心理上的变化,甚或通过心理变化对生理产生进一步的影响,轻则患病,重则致死[10]。因此,其英文可对应理解为“witchcraft”(巫术)或“poison-seduction”(毒物魅惑);而从医学内涵的角度看,即狭义的“蛊”,特指使人致病的毒素,对应可译为“toxin”。但“witchcraft”的英译有混淆医巫之嫌,易造成壮医宗教化的理解偏差,且“蛊”的操作是人为将“蛊”制成品投放于饮食或器物中而作用于人体的被动过程,与“seduction”所阐述的主动致毒行为不一致。此外,如简单将其理解为“毒素”而译为“toxin”的话,在实际应用时又易与“毒”的概念混淆。
综上,该术语上述含义的对应英译均不尽如人意,在不造成误译和漏译的前提下,考虑在最大程度上同时保留该术语的医学和文化内涵,故予音译为“Gu”。虽然“音译法”可在一定情况下避免直译或意译时出现的词不达意、表述累赘或语义误解的弊病,但因为拼音本无任何含义,倘若单独应用于翻译实操会给目标读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困难,而适当予以文内注释或增译的形式能让目标读者更清楚准确地理解术语所表达的信息,若音译通过长期翻译实践检验后形成“约定俗成”,可无须在文中另行加释。当然,不能因过分强调保持术语特色而滥用音译,而须在实际操作中根据术语含义和所处语境对其翻译策略作出适当的调整。
3 壮医药混合术语英译难点解析
混合术语是介于具体术语和抽象术语之间的概念,既可用作表达具体事物,又能用于表达抽象概念[9]。如“咪心头”既指心脏实体,又是一个与身体各部有着密切关系的抽象概念;又如壮医的穴位,虽然可在体表找寻定位,但实际是气血输注汇聚之处,无法通过现代科学进行明晰的解剖定义。因此,这类术语的英译可在上述二者英译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英译。下文以内脏和穴位两类术语为例。
3.1 内脏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壮医的内脏概念不同于中医有“脏”“腑”明确之分,更没有五行生克理传遍模式[10]。在广西壮区发现的医学史上首张人体解剖绘图《欧希范五脏图》表明,壮医在早期已通过人体解剖对脏器生理、病理有一定的认识,并将位于人体体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均称之为内脏,如“咪心头”“咪隆”等。如仅考虑保持术语的民族特色进行音译,会导致过度造词,给翻译实践带来不必要的负担。虽然这些术语名称看似新颖陌生,但实际上是以壮语对其进行称谓,如“咪心头”有脏腑之首之意,指“心”,“咪隆”意为“被遗忘的器官”,故对应“脾”等。
考虑到壮医在脏腑生理、病理观点上的阐述和中医相似相通,如“咪心头”为主宰、主温运,生“勒”、行“勒”、主“神志”;“咪隆”喜燥恶湿,主运化、主统“勒”、主升清等,因此,在英译时可参考目前已行的中医药术语英译标准对应译为“heart”“spleen”等,而壮医内脏是关联多个功能的有机整体的概念,其远远大于脏器的实体含义,即便“heart”“spleen”等英译未能完全涵盖源语义,但仍可根据术语英译的约定俗成原则考虑继续沿用。
3.2 穴位类术语的英译解析
壮医穴位包括环穴、络央穴和经验穴三类,其中环穴是以体表标志或肢体部位为中心环周取穴,并按特定方位或方向进行命名,如“腹环穴”;络央穴多是以四肢骨节或关节横纹之间连线的中点取穴命名,如“内三肩穴”;而经验穴则是以自然万物、人体部位方位、取类比象、穴位功能等取穴命名,如“月亮穴”“猫爪尖穴”“土坡穴”等[11]。
由此可见,壮医穴位不同于中医的循经取穴,因此在英译时,不可按中医“所属经络的英文字母缩写+数字代码”的方式进行英译。此外,对于“侧下下桩”“手心三环12穴”等名称过长的穴位,若用拼音全写翻译也会稍显冗长,有悖合术语的简明原则。蒙洁琼等[12]认为,壮医穴位的英译可按穴位含义进行直译或意译,或采用“编码+拼音+意译/直译”的三联译法。但此种英译方法仅适用于个别中英文有明确对应且译名不会产生任何误解情况下的穴位名称英译中,如“莲花穴”可译为“lotus acupoints”“鼻通穴”译为“nose-opening acupoint”等。又如,“内三肩穴”是位于手臂内侧在腋前纹头与肘横纹连线上的穴位群,共含3穴,若参照上述译法译为“three acupoints of inside of the arm”则表达过于冗长;再如,“外中桩”是位于小腿膝关节外侧下缘中点沿小腿外侧中线至外踝最高点连线的中点的穴位,按上述译法直译为“middle acupoint of the lateral calf”不仅显累赘,且也没能体现壮医穴位以“桩”称谓小腿络央穴的命名特点。
为方便记忆,同时让穴位术语英译更具明确识别和定位功能,在保留不违背壮医对穴位命名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壮医穴位从上(人部)至下(地部)的命名规律,用“‘天、地、人’汉语拼音的首字母大写(T、R、D)+穴位名称拼音首字母缩写(第一个字母大写)”对壮医穴位进行英译。如在头额两侧部发际线处的“山前门穴”,可译为“TSqm”,即将穴位所在的“天部”的“天”字拼音首字母大写“T”和“山前门”拼音首字母“Sqm”(穴位第一个字母大写)结合。又如位于“人部”以脐周为中心的“腹环穴”,可对应译为“RFh”,而“腹环穴”又根据脐周半径的不同分为腹一环穴、腹二环穴和腹三环穴,故可根据命名中的数字进行加译,即可分别对应译为“RFh1”“RFh2”和“RFh3”。又如“足背一环穴”是位于“地部”的穴位,可译为“DZbh1”,而该穴按时钟的12个刻度等分为12个穴位,分别命名为足背一环1穴、足背一环2穴、足背一环3穴等,故可以连字符号“-”按顺时针刻度数字进行加译,即可分别对应译为“DZbh1-1”“DZbh1-2”“DZbh1-3”……依此类推。此种译法融合了音译和编码两种方法,能让目标读者仅从拼音首字母就辨别出穴位的大致分布。但考虑到音译全拼更便于口述,故对壮医穴位名称可予以“音译全拼+拼音缩写”的形式进行英译,如“Shanqianmen (TSqm)”“Fuyihuan (RFh1)”等,既书写简明,又无碍于口述表达。
综上,笔者认为在壮医药特色名词术语英译时应根据术语属性类别进行英译策略的调整。一般而言,当处理在客观现实中能找到对应译入文本的具体术语英译时,应遵循“同一性”原则进行“一义一译”的对应英译;在处理通过感观连接客观事实的抽象术语时,应遵循“对应性”原则在客观现实与感性认知中找到“共情”的平衡点,尽可能地将术语涵义进行趋完整化的表达;而在处理介于以上二者属性之间的混合术语的英译时,应具体根据术语本身内涵及实际应用情况进行斟酌翻译,基于上述各类特色术语英译原则指导的基础上,在翻译时多采用壮文增译、归化和异化相结合、借译、音译等英译方法。
随着广西国际壮医医院的建立,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等国际交流的开展以及汉、英、壮三语等壮医药系列专著的出版,壮医药名词术语的英译实践获得了践行平台和诸多实践机会。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壮医药名词术语英译标准化建设工作仍旧任重道远,也必将在向世界弘扬和传承壮医药文化的道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