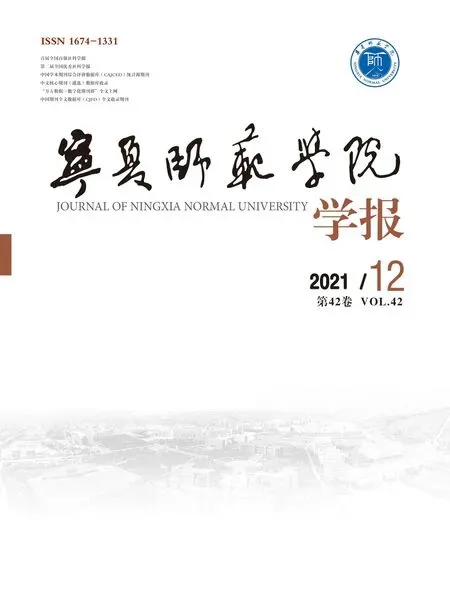存在之思与生命体验
——论张存学长篇小说《白色庄窠》
焦玉琴,李生滨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精神世界的贫瘠与荒芜成为当下社会普遍的现象,世俗的颓废、低级趣味充斥日常生活,生命体验在现代化进程的裹挟下反而不再那么容易被感知。张存学的小说氤氲着挥之不去的生命的沉重感,关乎作者生命本身的困境体验。对故土的怀恋、精神家园的寻找和生存困境的书写等成为他小说创作的重要方面。鲁迅或存在主义哲学生发的现实观照,具有形而上的求索,小说人物命运与时代交错的深处是审美批判的存在之思。作者对生命本真的存在体验来自陇原深处、黄河岸边的乡土农耕文化,但长期生活工作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深厚体验更具有历史反思的文化自觉。如果说《温柔之手》多角度书写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近代苦难和荒诞年代的血腥疯狂,笔底蕴藉故乡寻根和历史批判的双重悲伤,那么《白色庄窠》就是关于命运无法超越时代力量的存在之思,且多了生命体验超越人物故事而考量灵魂的玄思色彩。
一、精致内敛的小说叙事
长篇小说《白色庄窠》是一部内涵深厚的优秀作品。小说通过卢里讲述了庄窠里每个人的生存遭遇和心灵困境,也展示了德鲁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现代文明对原有文化生态的侵蚀,甚或淹没。主人公“我”——卢里,通过内省的叙述方式还原加告街、德鲁小镇近百年历史流变的情景。小说自始至终以一种忧伤的叙事基调讲述白色庄窠的灾变以及家族成员在时空变迁中的悲情往事。姥爷周顺昌在“文革”中被迫致死,舅舅周特背负愧疚与自责远离德鲁、客死他乡,“我”的父亲卢振威——曾经的桥梁工程师,在突如其来的升迁之后发疯而死。“我”母亲、阿哥卡尔罗、阿姐周雪芹以及卢雅和“我”等诸多活着的人,一直摆脱不了白色庄窠灾变的阴影。在失去亲人的悲痛和生存的焦虑中活着,出走又返回,似乎每个人都有一种宿命的未来。压死骆驼的不是最后一根稻草,生命在一次又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打击下愈显脆弱。在一系列灾变面前,个体的力量始终是微小的,始终面临“被侵害”“被摧残”的恐惧。就像狂人翻开历史陈年的流水簿子,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到的唯有“吃人”。“有时候,历史是以‘重现’的方式来呈现自己的足印的。”[1]小说低沉压抑的叙事情调,在边地风情的冷静透视里,既有内在连续性,又显现了外在开放性。
故事既是小说的主体,又是文本时间呈现的侧面。小说中人物、事件始终围绕白色庄窠展开。白色庄窠就是为了躲避世事颓废、寻求生活安定而建的家,自然也成了周王氏为主心骨的家族生活的主要空间——每个人内心深处情感皈依的所在。世事纷扰流变,这个家里有藏族、汉族、藏汉血统交融的人,也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人。在这身份复杂、语言多样、信仰各异的大家庭里,每个人却真诚善良,彼此牵挂,相互关爱。因而,庄窠灾变的发生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白色庄窠注定要被侵害和被摧残。侵害和摧残的力量是无形的。加告街只是一个缩影,迷乱的缩影。无形的力量来自更远、更强大的地方,或者,它来自历史的深处和人心的深处。”(1)张存学:《白色庄窠》,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下文未注引文皆出自此书。白色庄窠、德鲁小镇在迷乱气息的扩散中,走向衰落,人心的慌乱伸向草原,生命个体在成长中恐惧不安却又无处可去。“生活在德鲁的人从来都没有把德鲁当作自己真正的故乡,自己的故乡永远在远处,或者在虚无之中。”小说再次凸显“故乡”在个人成长中的不可缺失,以及“异乡人”对“故乡”的寻找。在时代无形力量的波动中,《白色庄窠》的人一次又一次出门远行,离开庄窠,他们把受难当作一种修行。远行是对不可抗拒命运的苦苦挣扎,修行则是每个人坚守信念和自强的精神彰显。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讲述了白色庄窠的兴盛和衰落,以及与它相关的每一个个体生存者的现实困境与多舛命运。在冷静、思辨的回忆描述中,叙述不仅没有限制文本的语言张力,张弛有度的人物布局反而在打破故事完整性的交叉描述里,充满描摹生活真实的独特魅力。“我”——故事主人公卢里,成了白色庄窠历史的见证者,他人命运的“看客”,见证和目睹家族亲人共同演绎的庄窠的兴衰。此外,作家以白色庄窠为缩影,透视德鲁小镇和外来经济、政治和文化对原有生活状态的冲击和改造,直至草原日常伦理生活秩序的某种溃败。因此,白色庄窠在时代力量的冲击下没有了昔日的安详平静,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不可触碰的伤痛,“白色庄窠的人互相只要瞅一眼就知道对方心里的这种陷落”,“白色庄窠人共同生活的基石被抽去了,每个人活着的理由被拿走了”。在这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下,个体选择生活的同时也在被命运所选择,如舅舅周特的远走、阿姐周雪芹的婚姻选择、“我”漂浮不定的生存境况等。“时间是联接时间的主轴,事件与事件之间在时间上常表现为一种连续的线性运动,尤其是离别与归来,人世的兴衰,追寻的历程等主题。”[2]在大历史、大时代背景下,白色庄窠和德鲁代表的地域文化,不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心灵与精神的寄托,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深层参照。
鲁迅鲁镇系列、沈从文湘西系列、老舍北京系列、贾平凹商州系列、莫言高密系列等地域文化的特别书写,除了展现地方独有的自然环境、生活风貌外,形形色色个体生命的精神世界也是地域文化投射历史变迁的抽象抒情。换言之,“艺术须有自己的某种框架,以此述说从现象世界中抽取的东西”。[3]《白色庄窠》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视角展现了历史文化、地域文化背景下一座庄窠三代人,还有一个边地小镇的历史变迁,以小见大,呈现多民族、多文化交融中无数个体生存的悲剧遭遇。
二、触及心灵的苦难书写
20世纪20年代,鲁迅以“表现的深切,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作家。时至今日,他依然是中国的鲁迅,更是东亚和世界的鲁迅。鲁迅先生怀着大众启蒙的悲悯,触及心灵,绘写了孔乙己、华老栓、阿Q、祥林嫂等无数在现实生活里挣扎的苦难者。张存学通过循环往复的独特叙述方式,以简劲的笔调呈现了一幅藏地文化背景下“白色庄窠”人物命运的悲情画卷,内敛的叙述背后有冷峻的思索与体悟,揭示了生命无法承受的历史沉重感。
在德鲁,加告街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地方,文明、道德、制度、信仰等伴随日常生活的文化气息在这里交织,异乡人相聚,建造共同的家园,“但那个家似乎遥远而缥缈”。姥姥周王氏是来自草原的藏族人,草原文化滋养了她勤劳善良、虔诚真挚的美好品性,为了远离加告街“乌烟瘴气”的杂乱环境,在一片荒草地上她主导建成了白色庄窠,以逃避的方式去抵抗外在力量的精神侵蚀和直接伤害。但时代发展的力量过于强大,“二十多年前的灾变让白色庄窠的每一个人都惊悸并惶恐。小说一开始为整部作品奠定了低沉、压抑、慌乱的基调,却又不失叙事的现实意义和悲剧魅力。“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无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4]白色庄窠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生命的也是历史的沉重感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却显渺茫,心灵的无所归依压抑着每一个人。为了家族和亲人避免更大更多的灾难,不惜以“自己带着灾难离去,不再归来”的决绝相继离开白色庄窠、离开德鲁。舅舅周特个性倔强、内心藏着无法言说又不愿吐露的重重心事,在他高大形象的背后是个体生存的不屈与自我寻找,离开德鲁后,客死他乡,以灵识的方式回归。这种性格悲剧的背后,恰恰是时代的悲剧和心灵的苦难。一切外来的压力和伤害变成白色庄窠每个人心灵的地狱,老一代人经受的时代灾难留下烙印,内心的惊悸无法消除,因而阿姐周雪芹婚姻的不幸又一次打击善良、本分和隐忍的“我们”。不仅仅是舅舅一个人,包括阿哥卡尔罗、父亲卢振威以及卢雅,还有漂泊的“我”。卢雅虽然离开白色庄窠,前往美国了,但“白色庄窠的空茫是在每一个人心里的,包括在卢雅的心里。”“我”在兰州的一个出版社工作,“我是一个被聘任的编辑,我想我一直处在生活和世事的流程中,我被不断驱使,不断被裹挟着向前。”此外,卢加尼、肖连、李五十三等诸多与白色庄窠有关的人都在经受苦难,在一个道义和礼乐山崩溃的时代,他们善良的灵魂无处安放,时而妥协、时而抗争、时而寻找。“艺术的任务在忠实地表现人生,不在对人生加以评价。”[5]我相信,作家张存学在写作过程中,与他小说中每一个人物的心灵是贴近的,经受着他们的喜怒哀乐、迷惘彷徨。面对一系列灾变,他并没有用夸张的词汇抑或场面描写告诉读者,苦难究竟是怎样折磨这里的每个人,甚至没有用一个感叹句或反问句来描述人生境遇的压抑和痛苦。这种平静如水的叙事语言的背后,蕴藏着作者个人生命深切而真挚的反思。时光流逝,并没有抹去灾难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影子,也没有消除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对灾难的恐惧,心灵的恐惧。埋藏在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并没有随着成长而纾解,而是生根发芽般撕裂、侵蚀着每一个灵魂,“白色庄窠已经成为他们心里永远的乡愁,即使靠近,也无从抵达。”[6]
自然的灾难可以抗拒,但面对各种无形的人为的灾难,“白色庄窠”每个人都无法逃脱。他们虽然在距离上远离了白色庄窠,在时间上放逐了自己,但心灵深处的恐惧,生命始终漂泊的无力感,以及出离与回归永远无从抵达的迷惘,吞噬、解构着个体存在的价值与尊严。“语言,在这个时候变得轻而又轻了”,存在之思,我们其实无法直面惨淡的人生,更怕正视淋漓的鲜血。这也许就是《白色庄窠》揭示命运悲剧和心灵苦难的哲学主旨。
三、宿命悲剧的深层意蕴
张存学祖籍白银,出生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农耕文化、藏地生活以及现代人文思想滋养了他注重生命体验的精神品格,特别藏民族自然的、朴实的、崇尚信念的生命观也在无形中影响、塑造、成就了他的内心情感,使他将个体精神的成长以及对人物命运的历史观照,上升为小说叙事的主要追求。“所谓宿命论就是承认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承认在人的意志之外有一种超然的不可避免的力量操纵着人的命运。”[7]这种悲剧的宿命论不完全是消极的,恰恰深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力量。这与嘉绒阿来的自然的人文主义书写,与安多梅卓的神性的浪漫主义书写,形成鲜明的对照。
白色庄窠和德鲁小镇日益被外来势力冲击,原有生活的常态遭受挑战,生存个体在这种不可逆的变化中,心灵无处安放,没有了家园的安稳和踏实。小说中,卢里“我”回到白色庄窠后,与遇见的每一个亲人、朋友沟通交流,但更多的并不是语言的交流而是相对无言的沉默。一种心灵感伤的沉默默契,代替了语言上的空洞和无力。整部作品中,仿佛总有一双无形的大手控制着白色庄窠,操控着每个人的选择和命运。可以说,正是不可名状的厄运逼迫着白色庄窠一代又一代人的离去,他们最后要么死于他乡,要么无奈返乡,要么永远离乡。舅舅周特是最早离开的,他“在旷野中踽踽而行,他的眉宇间凝成的是承受一切的决绝和坚定的神色。这也是把受难当作是修行的神色”,但这种修行并没有带给白色庄窠希望和光亮,自己却死在青海。他这种性格悲剧的充分观照,无疑带给我们更多关于自我与生存的深思。阿姐周雪芹漂亮美丽,像白色庄窠的太阳。“她的笑声和她的眼睛让白色庄窠充满了阳光。”是的,在卢里“我”的回忆里,阿姐是快乐的女神,带给庄窠一种光明与温暖。然而花季少女在遭受婚姻的变故以后,从此成了沉默的人,“现在她更像一条孤独的鱼。鱼有眼睛却流不出眼泪,鱼有嘴却发不出哭声。”阿姐在世事中失去了欢笑纯真,不再有期待与梦想。“心冷一次岁数自然要长一次。人就是以这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长大的,心同样也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死掉的。这和年月反而没有什么关系了。”[8]“我”父亲卢振威曾经是桥梁工程师,在乖张的世事纷扰中发疯,迷失在弘克草原并死在那里。“德鲁或者草原隐含着根性的、久远的力量,这些力量他无法看到,也无法感觉到。”生活的苦难和命运的打击在庄窠里时隐时现,让人想起了《活着》里面福贵老汉在大时代背景下经历了自己人生和家庭苦难后,仅剩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无法言说的时代悲苦。“我”母亲在“我”继父死去后,搬回了白色庄窠,继承了姥姥周王氏对白色庄窠的领导与管理,“母亲试图重复周王氏姥姥的生活道路,试图像周王氏姥姥那样能挺住一切”。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卢雅去了美国,“我”将要继续前往兰州,未来亦然是漂泊的宿命。
在一系列时代和命运不幸的背景上,灾难缠绕着每一个与白色庄窠相关的人物。而这种灾难又杂草般蔓延开来,侵蚀心灵,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慌乱、陷落与探寻在时间里变得更深远渺茫。作者通过心理的细致描写,实现了情感的升华,“命运的沉重感落在悬浮的白色庄窠中,里面的人,不可承受,唯有忍耐或逃离。而这种不可承受性,在看似受制于一种神秘力量操控下的同时,也铸造着里面那一个个悬浮、挣扎、不断撕裂的灵魂。他们在‘看不透的’不可承受之中,逃避着命运的不可捉摸的沉重。”[9]这是许多批评者阅读的共同感受。
“魂兮归来”,“白色庄窠的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迷乱的印记”,这好似命中注定的生命存在状态,不管是灾难的来临、还是迷乱气息的肆意滋长,没有人能够逃离,除了按生命既定的轨迹前行。“悲剧是最上乘的艺术,就因为它能教人‘退让’,能把人生最黑暗的方面投到焦点上,使人看到一切空虚而废然思返。”[10]无论是白色庄窠里个体的磨难,还是德鲁小镇草原文化的现代性蜕变,作品里形形色色的人在努力过后选择一种坦然的直面。这种明白命运博弈的无望却还要努力去改变的执着与坚守,是个体生存必然的一种精神状态,也是对生命本身的歌唱与赞颂。长期耕耘西部文学的批评者刘晓林教授,从生命体验的感悟中剖析说:“关于苦难的体验与记忆之于一个以文学写作为志职的人而言,其重要性在于通过对不幸根源的追索认知世间的真相、透视难以预测的命运的秘密,包含着对慈悲、拯救与关怀等人类情感的真切体认,提供了测试生命韧度和人性温度的标尺。”[11]同样,读张存学《白色庄窠》等小说,除了感受到生命在苦难面前的弱小无助以外,令人震撼的是,“逃离”与“沉沦”,个体在经受不幸的磨砺后,依然以生的意志在命运中走向未知、完成自我——即是不惜以死亡的魂归方式抵达现实中无法抵达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