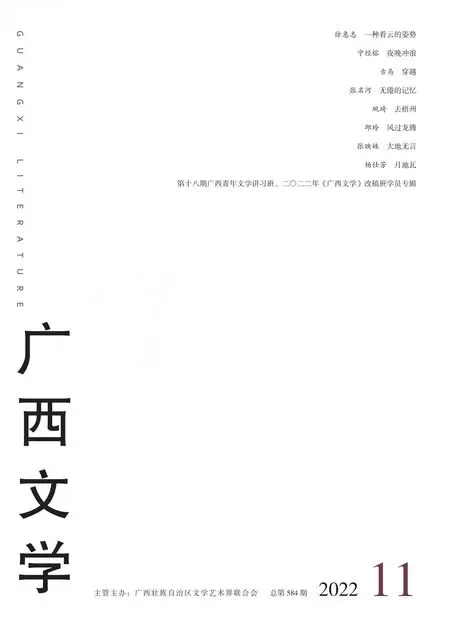门前的撒哈拉
梅赞峰
避风港新来的租客是一名设计师。
他没有挨着我们住,而是租下了海堤岸边上一间单独的杂物房。晚饭后,我靠近向里头瞟了一眼,瘦削的黄木拼凑成的两个书架、笔记本电脑、折叠的小沙发、风扇。门前一个大扁头的孩子,指甲缝里黑乎乎的,四岁的模样还穿着开裆裤,腹股沟长有些许小湿疹。他不停地将沙子装进小货车,随后又倒了出来。
我弯下腰问,老板呢?孩子起身提了提开裆裤,小手指了指避风港里一个瘦男人,此时他正双手握着数码相机对准落日。西边的远海金红一片,起伏的水波像在沸腾,一阵阵闷热的海风裹着咸鱼味飘来。我喊了一声老板,他移开相机看了我一眼后又端了起来。等等,等我拍完,他说。我转过身,蹲下来与孩子玩起沙,他抓住小货车往后压了压,随即冲向我便翻了车,方才装满的沙子撒了一地。
呜呜呜。
男孩哭了起来,设计师循声爬上岸。我尴尬地指了指翻倒的小货车,一时说不上什么。设计师张着一口黄牙连说没事,就抱起男孩回到了屋内。我随他进门,狭窄的空间被他在南墙上挂起了幕布,黑的、红的、蓝的。我说,你这可以拍证件照?他点了点头后又抚摸起男孩的后背。我在小沙发上稍稍坐了下来,双手搓着膝盖环顾四周,饮水机被贴上奥特曼和猪猪侠的贴纸,书架底下摆满了父子俩的鞋,闷热的屋子把鞋臭味烘得更浓。倒数第二层则用几个收纳箱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玩具,一只塑料骆驼歪着头。
天热,喝点水。
谢谢。
我接过设计师的纸杯,上面居然还印着“避风港设计室”六个字。我说,准备上大学,想拍一组照片,蓝底和白底,一寸和二寸的都要。毛毛下来吧,他说。毛毛自觉地顺着设计师的毛腿滑了下来,离开前还在脚背上调皮地蹭了蹭,随后又提了提开裆裤跑到门前,将沙子重新铲进货车里。设计师将蓝布挂到了第一层,我就着门后的一张小镜子扣完了纽扣,狗啃的刘海尽量地拨到侧边。
来,一、二、三,笑。
可以了,他说。我这才活动一下脖子。他跟我说,后天来吧,我帮你精修。我谢过后和他说,不急,我就住前面。他没有理会,从电脑桌下搬出电磁炉放在一张小木桌上,晾在房子外西边的一口小锅就着水龙头冲了冲。毛毛继续摆弄着小货车,蹲累了就坐在门槛上,一对蛋蛋微微显露出来。
我沿着避风港绕了一圈,回来时已是深夜。平静的水面上没有浪潮,休渔期的船只一艘挨着一艘,船上的渔灯似乎要与两岸的灯火争个高下,灯火通明得连成一片。一个系着长辫子的女人跨船串门,没多久就回到自己的船上。闷热的深夜里,一些男人光着膀子在船上喝酒。岸上的路灯暗淡了许多,一个戴着眼镜佝偻着背的男人在堤岸上抽着烟。我认得出是那个设计师,我走上去问,那么晚还不睡吗?他摇了摇头,推了推眼镜后抽了一口烟。我借着路灯瞧见他青黑色的眼窝更深了,牙齿也更黄了,仔细一嗅似乎还有烟味和菜味。
我继续走着,瞥见屋子里笔记本电脑上精修着的是一个年轻的美女,单眼皮,高鼻梁,小巧的嘴。沙发展开成了一张小床,毛毛继续穿着开裆裤酣睡着,一块应该裹肚子的小被子被他蹬到了地上,地面还散落着一些小米粒。黑黢黢的路面,我无意踩到了小货车,毛毛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动了动身子,我连忙跑回了家中拴起了门。
躺在老宅的鸳鸯床上,我关了灯,不断思索着为何设计师此时一个人站在堤岸上抽着闷烟,电脑上精修的对象不是自己。银色的月光透过木窗淌了进来,像一堆绵密细软的白沙子。没多久,避风港传来久违的孩子哭闹声。自从高考完回到老家居住,已经许久没听过孩子的哭闹声,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喊,我不禁爬到窗前看起四周,微弱的路灯也没有消减那间杂物房传来的动静。过了一会儿,设计师抱起毛毛走出来用力拍打着,毛毛双手抱紧他的腰身,手里的小货车摔在地上。
别打了,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了!
我特地压低了声,向外吼道。当设计师正要看过来时,我压低了头屏住呼吸。次日,当我经过杂物房时,又瞥见设计师在修着那个美女。毛毛说,你踩到我的骆驼了。我这才意识到,踉跄了几步。设计师转头瞥了一眼,我低下头灰溜溜地离开。
后天一早,我来到他门前徘徊许久。“吱呀”一声,设计师缓缓地推开了门。我说,你好,今天来拿相片。他戴上眼镜推了推,一边抽着烟一边在电脑上输入一串密码。我半坐在沙发上,毛毛侧身睡着,嘟着小嘴,怀里抱着那辆小货车。我说,真不好意思,这么早打扰你。没事,他说。他将打印出来的相片放到闸刀下,手指有点颤抖。我凑近一瞧,发现十二宫格的相片里有个女人混在其中。我认得出是那个被精修过的女人。他抬头问,少收你一列的钱,可以吗?我想了想便答应他。他将那张肖像夹进了钱包里,另一侧放着一张沙漠图。
我说,去吃早饭吗,我没吃。他愣了一下后笑了笑,说,行。毛毛仍在熟睡,设计师锁上了铁门后将烟头扔进海里。海面上金灿灿的初升太阳被烟头砸碎,大小的涟漪像是涌动的沙丘。我们决定爬上避风港里一艘小船,那是专卖小吃的。船尾浮动几下后平静了下来,一张小木桌油腻腻的,酱油、北海辣椒酱、柠檬酱、沙蟹酱摆在中央。我要了一份三拼的越南卷粉,设计师则要一碗蟹仔粉和一个鸡蛋。他娴熟地拿来一对味碟,舀出一勺辣椒酱后滴了三滴酱油。这样就甜,他说。我笑了笑。他看向东边的海岸线又抽起一根烟来,又转过半个身子瞧了瞧身后的杂物房。我说,要不要带毛毛出来?他转回来推了推眼镜说,不用。
三拼的卷粉端上来,我刮了刮木筷的毛刺,再夹上一条用力浸了浸醋汤。木耳肉末流了出来,我说,你吃点吗?他夹起烟摇了摇头,说,某使(不用),我常吃。我笑了笑,小心地嗦起卷粉。他说,你倒是蘸点辣椒酱呀。我顺势点了点,继续嗦着。他又抽了一口扭过头呼出烟来,随即瞥了我一眼说,你是本地人某(吗)?我常被别人质疑,今天又碰到了这个话题,随即一口咽下。我说,是的,本地人,只不过高考完才回老房子这里住。
你住哪?
我本想精准地指向那幢爬满三角梅的老宅,但一想起前晚的动静就怯了下来。我抬头向岸上皱了皱眉,喏,那就是。我埋头又吃起另一条胡萝卜肉丝卷粉,不锈钢碗里的肉末变得更多了。你想读么嘢(什么)专业?他说。说完,他舀上一勺满满的蟹黄嘬了一口。我说,还没想好,无论什么专业,可能出来都不一定干本行。我蘸了蘸辣椒酱,似乎这样底气更足。那你想做滴么嘢(干点什么)?他看着我说。写作、旅游,我说。他继续说,是挺文艺的。说完,他哈哈笑了出来,黄牙上还残留着方才的蟹黄。我说,我喜欢去旅游,想看看外面的世界,首先是首都,然后是国内的新疆、青海、西藏、四川和云南,出国第一站是越南、泰国、俄罗斯,还有撒哈拉大沙漠!他听完后没有接话,埋头一口气嗦完了一整碗蟹仔粉。
上岸时,我看着水面上的那个男人脸色暗沉了下来,与水一样青黑,热风持续刮着。毛毛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归来,设计师进门后抱起他,还塞了鸡蛋。毛毛从书架上拖出一箱的玩具,我帮他捡起落在地上的骆驼。我在一旁臭椿树下的网床上躺了下来,热风吹着树冠僵硬地摇摆,毛毛在烈日下一边擦着汗一边继续用小货车运送沙子。我说,嘿,毛毛,来树下玩,这里不晒。
他瞪了我一眼说:“撒哈拉沙漠没有一棵树!”
我耸了耸肩,把左腿搭到右腿上独自晃动网床,眯着眼幻想起自己毕业后会是一个自由职业者,背着一个相机走天下。可能在新疆有一场艳遇,和心爱的她同居一段时间后就一直南下到丽江。她的肚子大了起来,却总是嚷着要出国,我带她吃起正宗的越南卷粉、泰国的冬阴功汤,还有路边的飞天空心菜,最后一定要去撒哈拉大沙漠走一走。
爸爸,没有沙子了。
我这才睁开眼,以为梦里的孩子已经长大。毛毛指了指远处的一幢新楼房,工人已将沙子清掉。设计师走出门,右手拿起小货车稍稍掩起烈日径直走去,我从网床上坐了起来向毛毛招了招手。他慢慢地扭着屁股走来,挠了挠潮红的腹股沟,里面爬满了湿疹。我说,毛毛,你妈妈呢?毛毛又抓起大扁头的那撮毛说,在大沙漠里。我说,她不回来吗?毛毛回头看了看远去的设计师爸爸,转回头摇了摇。我随后侧身看起避风港,一只大黄狗叼着狗仔越过了几艘船,狗仔不小心坠入了海里大力扑腾着。
毛毛想要走下海堤,设计师一手抓住了他的小胳膊。设计师在烈日下又像前晚扇起毛毛的屁股,毛毛哭闹几声后安静地咬住小嘴唇,眼珠子直勾勾地瞅着我。我似乎有些惭愧,又无可奈何。设计师鼓着腮帮子继续用力打着。我像泄了气的气球,瘫在网床上。毛毛的单眼皮微泛着泪珠,小门牙紧紧咬住莲藕般的小胳膊。
设计师回到屋里工作,我把老宅的香炉倒出一些干净的白沙,细细的,绵密的。我装了一小袋来到臭椿树下,毛毛看了一眼后,嘴角耷拉着挠了挠腹股沟。我起身望了望屋里忙着的设计师,便向毛毛招了招手,小声唤着,毛毛。说完,我还捧起手中的塑料袋掂了掂。毛毛似乎明白了我的心意,两眼冒起金光,伸出小脑袋看了看屋里便蹑手蹑脚地来到我跟前。他咧起嘴,伸出的双手像是讨要糖果。我抓了少许放到他掌心,他那对单眼皮似乎要被撑开来,于是我又特地加了一些。他流着口水说了一声谢谢,随后双手合上扭着小屁股回到了门前,将白沙与地面上的黄沙混合搅拌几下后,用小货车装起沙子从门前运到了屋里。
我说了多少遍,别带沙子进屋里。
屋里传出这一声嘶吼,我连忙躲到臭椿树后观望。几个响亮的巴掌后,毛毛连忙跑出来一边揪起开裆裤,一边揉着单眼皮呜咽着,小小的身子不停地抽着。随后,他张开小胳膊喊着,爸爸,不要。设计师穿着人字拖大步走了出来,一脚将沙子尽可能地都踢了出去,黄牙还啐了一口。我像做了贼,心里扑通扑通地狂跳,脸颊像被烈日烫伤,火辣辣地疼。热风袭来,船上的彩旗微微扬起,树冠抖着,海面上的沙子终于一声不吭地沉了下去。
从学校领回录取通知书,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家人,骑着自行车驶回坑洼的石子路上,心情与避风港的海面一样异常地平静。毛毛又蹲在门前玩沙子,我停下车一看,有海沙、金沙、银沙,还有我前段时间送他的一些细软的白沙。我说,哟呵,毛毛又有那么多沙子了。毛毛起身提了提开裆裤,抓了一把走上前来给我。我趁着设计师不注意捏了捏他的小脸蛋,整个人被晒得像黑炭,只有那口牙还算白净,不黑也不黄。我将自行车停在树旁,叩了叩门。哎,你怎么来了,设计师转头推了推眼镜说。我说,给你看样东西。说完,我从书包里掏出金灿灿的通知书递到他面前。他抖着小腿,开心地露出大黄牙,说,哟,咱们还是校友呢!
校友?
对,我也是医学院毕业的。
平静的我稍稍荡起一层涟漪,重新打量起这个有点吊儿郎当的设计师,想不到他竟是医学院毕业的,还是自己的校友。我说,校友,真的?他起身让我坐下,主动地拿过我的通知书小心地翻了又翻,嘴里说着,真是我学校。随后还小声地念着通知书的内容,念完又抽出印着字样的纸杯递上了水。我简单地抿了一口,不禁用手扇起风来,设计师尴尬地说着,是有点热。说完,他特地将电风扇对准了我。
你和家里人说了吗?
还没。
快说,他们会很开心的。
家人并不喜欢我学医。
设计师没有说话,跷起了二郎腿,腿毛似乎在淌着汗。我说,师兄。他愣了一下后笑出了声,电脑椅都在摇动着。我说,师兄,我请你喝杯奶茶。不不不,他摆了摆手。接着他又说,应该是我请你,是你考上了大学。毛毛见状,趴在门上探出大扁头瞧了瞧设计师,说,爸爸还没请我呢,今天是我的生日。设计师笑得飞出两三滴唾液,缓了过来说,今日也是毛毛的生日,要不你今晚来我这做客吧。我握着通知书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不信你问毛毛,毛毛,是不?毛毛抱着小货车点完头后,又跑到门前装起了沙子。设计师起身来到门槛上,看着阳光下认真玩沙子的毛毛,低声说:“真是双喜临门呀。”
我将家里后院的一些油柴都搬来了树下,设计师摸着堤墙来到浅海找来几块还算平整的砖石。我接过手,简单地围了起来。设计师掰断几根小树枝放在一旁,毛毛用小货车运来少许的沙子。设计师将晾在屋外的砧板冲了冲水后直接放在堤岸上,我们在码头买来一些花蟹、弹虾、生蚝和扇贝。我说,今晚是海鲜宴了。毛毛听后,赤着脚跑过来瞧了瞧花蟹,随后伸出小手指被蟹钳猛地钳住,毛毛痛叫了起来,小胳膊挥舞着。设计师拧断了蟹钳,一些汁水溅到了毛毛的嘴边,于是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后冲着我笑。
天逐渐暗了下来,设计师从屋里拉出一条插排,小小的白炽灯没多久就引来几只大水蚁。毛毛坐在中间只吃扇贝,我在味碟上挤了几个小青橘。毛毛继续蘸着味碟,设计师在一旁沉默地切起番茄,凉拌着吃。我先夹了一片后猛地啐了一口,说,嘿,这可不是糖,这是沙,白沙。设计师推了推眼镜一看,果然是白沙。毛毛的单眼皮扫了一眼,伸出小脚悄悄地将小货车踢进了木桌下。
设计师将切好的番茄倒掉后,重新切片凉拌,放白糖前还特地尝了尝。我说,师兄,坐下来吃吧。快了,快了,他说。说完,他掀了掀锅盖,一股热腾腾的水汽直接淹没了眼镜。“砰”,没等他拿稳,整个高锑桶倒了下来,里头的生蚝滚出了不少,我连忙上前扶起来,瞧见他的小腿立马生出几个大水泡。我拧开水龙头让水直流冲刷,设计师整个身子倚着我,大黄牙咬紧嘴唇,嘴边还有“嘶嘶”的声响。
爸爸。
哎。
爸爸,疼吗?
不疼。
毛毛握着一个裹满了沙子的生蚝,单眼皮眯得更小了,淌出了两行泪。设计师说,毛毛,你哭什么呢,今天是你的生日,也是哥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好日子。毛毛放下手中的生蚝,提了提开裆裤跑过来,双手接住了一些水继续给设计师的腿上浇着,“哗啦啦”。设计师拧上了水龙头,暴躁地说着,够了,够了,节约用水。说完,他让我们都回到座位上,拿出一个小碟端起方才掉在地上的生蚝重新冲了一遍。微弱的灯光反而把他佝偻的背照得愈发嶙峋,肿起的一块富贵包也更加突兀。他顺着水流,小声地说,冲冲就好。
毛毛吃得最快,我与设计师一直吃到了深夜,小木桌上都是成堆的壳。毛毛伸出小手拿走一块贝壳,又从桌底下拿回那辆小货车。设计师推了推眼镜盯着毛毛,毛毛扭着小屁股迅速地跑到门前。过了许久,设计师猛地拍了头,说,丢,我忘记了一件大事!我不敢再抽烟,一瓶啤酒也悬在手中,我说,么嘢供(什么事那么)紧张?设计师叼着烟跑到门前抱起了毛毛,毛毛被憋红了脸,手里的一枚贝壳颤抖着。我走过去拍了拍设计师的肩膀,他说,我忙这忙那的,就是忘记给毛毛准备蛋糕了。蛋糕,蛋糕,门前的毛毛学着设计师重复着说。我看了看前后,说,我们这的避风港就海鲜多,蛋糕店需要上坡直走再拐个弯,不过生日蛋糕似乎需要预定。设计师沉默了一会儿,和毛毛说,毛毛,你想吃蛋糕吗?
不想。
毛毛看了看设计师小腿上的大水泡就低下了头。我说,某关系(没关系),想吃,哥哥就去买。毛毛耷拉起小嘴说,不要。设计师推了推眼镜,拿起毛毛手里的贝壳一点点地收拢起沙子,还倒上一些水堆成了一座小山,最后再用贝壳一点点地砌成了一个蛋糕模样。毛毛起身提了提开裆裤后又蹲下来,指了指问,蜡烛呢?于是我折断了一小根细枝,设计师就着打起了火机,“啪”的一声,整个门前都亮了起来,小火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细烟引诱着邻居围了过来。
这是爸爸给我做的撒哈拉沙漠蛋糕。
毛毛又挠起了腹股沟,设计师把他的小手拉开,说,没有礼貌。毛毛嘟起小嘴,眼珠子湿湿的。我说,毛毛,快许个愿吧。毛毛这才眨了眨单眼皮,眯着一条细缝双手合十地许起愿来。我说,不能偷看,偷看就不灵了。
我将蛋糕拍了下来,连同录取通知书发了朋友圈。
去学校的前一周,接连几天不见毛毛的身影,杂物房门前的沙子被设计师扫到了树下。半夜里,我躺在鸳鸯床上睡不着,甚至渴望能再听见毛毛的哭闹声。我爬到窗边借着微弱的路灯观察那间杂物房,树下的沙子所剩不多,网床随风摆动着。窗外的天一亮,总会听见熟悉的铁门声,我爬到窗前眯眼看见设计师早早地出了门,左手还怀揣着那台笔记本电脑。随后,他来到那艘船上要了两份卷粉和一枚鸡蛋,上岸后快步远去。
我趁着人少,偷偷摸摸地来到那间杂物房前,“避风港设计室”的塑料招牌掉了色,隔着铁门可以瞧见小沙发上的小枕头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小货车和骆驼被装进了收纳箱里。我来到树下在网床上睡了下来,右脚将地面上的散沙踢了又踢。有别于往日里的闷热,一股凉风吹过,整个手臂的汗毛立了起来,我似乎有种不好的预感,但又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抚平了汗毛,长舒一口气后来到避风港的那艘小吃船上。
“靓仔,吃点么嘢(什么)?”
“刚才那个男的是要卷粉吗?”
“是的,两袋卷粉和一个鸡蛋。”
“那我要一份卷粉就好。”
“还吃点什么吗?”
“不用了,我还想和他一起吃早餐呢。”
“谁?”
“就刚刚那个男的。”
“哦,他呀,一直帮衬我的生意。”
“你知道他的小孩去哪了吗?”
“住院了。”
我“哦”了一声,在船尾坐了下来。海风似乎又将岸上仅剩的沙子全都吹了下来,浸到醋汤中,我一粒粒地撇出来,再嚼上一口卷粉似乎吃不出以前的味道了。我最后没有吃完就上了岸,向前走着,心想订一个生日蛋糕等毛毛回来可以直接吃上。我将零花钱重新盘算,最后攥住手机快步直走,来到十字路口后拐了弯。
“你好,欢迎光临。”
“我想订制生日蛋糕。”
“可以的,请问您想要什么样的呢?”
“撒哈拉沙漠蛋糕。”
“这……我们没听说过。”
“是的,是别人原创的。”
“请问,有照片可以给到我们参考吗?”
我打开手机相册,终于找出那晚无意拍下的一张照片,沙子砌成了圆柱形,一根细枝丫插在其中,火焰独自燃烧。店员皱着眉,似懂非懂地答应了。当我回来时,看见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停在了杂物房前,我快步走去,设计师把书架搬了出来当场拆掉,饮水机也搬上了车。他拿出那包印着标签的纸杯递给了我,说,你要某(吗)?我接过后没有谢他,走进屋里看见小屋一夜之间变了模样,三张幕布捆绑了起来,相机与玩具放进了收纳箱里,旁边的收纳箱叠在了一起,笔记本电脑的桌面是撒哈拉大沙漠,路由器和电线窝在角落里,被子和枕头堆在了沙发上。
你要搬家?
设计师点了点头,还带我来到屋外挂着锅和铲的西墙前。上面喷了一个大红字,“拆”。我凑近一瞧,黏糊糊的,喷漆似乎未干,一股臭味让人恶心。他还将一张通知单递到了我手上,我读后颤颤地归还给了他。我说,那毛毛呢?他说,在医院。我说,你打算搬去哪?南宁吧,那里有大医院,他说。
我点了点头,与他一同来到海堤边上抽起烟来。我说,我订了蛋糕,今晚让毛毛出来吃吧。他吐出一口烟,手指弹了弹烟灰。
夜沉下来后,撒哈拉沙漠蛋糕摆在了堤岸上,通体土黄,表面上还有模仿沙子的粗糙感,一根仙女棒插在正中央。我说,毛毛,这回许愿要闭紧眼,这样才会灵验。他点了点头快速地皱着眉头,挤出了三道小小的抬头纹。临近九月的夜风仍是闷热,我们沁着大汗大口吃了起来。次日,天蒙蒙亮,我站在窗前看设计师收拾完行李后背着毛毛离开,背影愈来愈小。
半个小时后,一台挖掘机铲平了那间杂物房。我走近一看,那只塑料骆驼伫立在废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