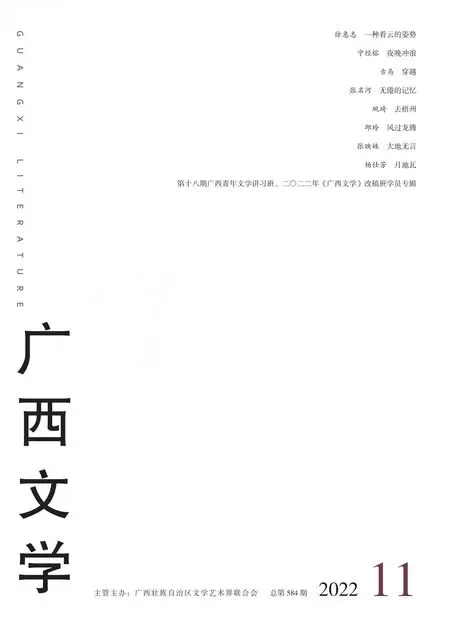夜晚冲浪
宁经榕
一
盐场就在我面前,分割成一块块方形盐田向海里延伸,盐田里水面平静,火烧云在上面燃烧着。空气中有一股咸腥味。达仔打着赤膊,从盐场与海岸公路之间的那片荒滩跑过来,他的背和手臂晒成了黄铜色,胸膛稍微浅一些,大概是经常背向太阳干活的缘故。头发天生鬈,他跟我讲过,这都是遗传的,他父亲也是个鬈发。这样没什么不好,连烫发的钱都省了。因为这两样,大家都喊他印度佬,他不在意,都是笑笑应了,他觉得他们并没有恶意。盐场里的人大多都有外号,比印度佬难听的大把有,诸如鱼头、烂虾、八爪鱼、水母之类。
现在出发?他跨过了公路的栏杆,一屁股坐在上面说。我看盐场那边还有不少人在干活,说,现在走得了吗?他说,走得,我那几块田都搞定了,剩下的高哥弄。他说完从栏杆站起来,向盐场小跑去。他有点外八,跑起来一颠一晃的,像只鸭子。我们约着去找冲浪点。盐场这一带浪不大,礁石又多,不适合冲浪。我们打算沿着海岸公路一直往南边找,据说那里有几处浪特别大,底下全是沙的野海。
我们认识有两年多了。三年前我被分配到沿海小镇食药所,工作不算太忙,难度也不大,日子还过得去。只是这边一个熟人也没有。刚来那时候,下班无事可做,一个人待在出租屋里玩游戏打发时间。办公室几位同事刚开始还叫我去喝酒,我拒绝几次后,他们再也没叫我。这也没什么,我天生就喝不来酒,一喝多就容易上头,大学的时候跟一个师兄拼酒,拼输了不服,喊着要跟师兄决斗。几个同学把我按住,一路押回宿舍,即便被绑到床上,我还是大呼那师兄的名字。第二天醒来什么也不记得,问舍友才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我去给那师兄道了歉。师兄大人有大量,说没事没事,醉酒的事别当真。但那以后那帮人就没叫过我喝酒。我也有自知之明,从此就不再敢喝多了。
第二年我买了辆雅马哈摩托车,一有时间就往海边溜达。我住的地方离海边有十多公里,骑摩托车十来分钟能到。这里是个半岛,在北回归线以南,夏季无比漫长,阳光亮得让人发慌,所以我几乎傍晚才出去。海岸线从东边往南,有几十公里,沿着海岸公路就可以走完。有一天傍晚,我去南端的一片野海吹了一阵海风,回到盐场附近摩托车熄火了,怎么打也打不着。我把车立在路边,正想着怎么找附近哪里有修车的,达仔从盐场上来,从我面前经过。我问他兄弟知道附近哪里有修车的吗,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边上的摩托车,说,镇上有。我看着他的样子,鬈发赤膊,吊儿郎当的像个混混,我说,我当然知道镇上有,我是问你这附近有没有。他倒没计较,问我你车怎么了。我说,不知道。他走到摩托车边上,一骗腿骑了上去,说,钥匙拿来。我把钥匙抛给他,他便开始打火,捣鼓了一阵,下来拔出火花塞说,烧了。我凑过去看,火花塞一头变黑了,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回去,想着叫一辆拖车过来吧。打了几个电话问同事,都没有拖车的号码。达仔问我,住哪。我说住镇上。他说,你别叫拖车了,我拖你回去。说完跑回去,不久骑着一辆嘉陵摩托过来,停到我摩托车前面。嘉陵看起来有些年代了,油箱的油漆掉了不少,不过保养得不错,车身和轮子都没生锈。达仔从后箱里拿出一根拇指粗的绳子,一头绑到嘉陵后架,一头系在我的车头。就这样,他把我拖到镇上,到修理店天已经黑下来,我要请他吃饭,他说今天不行,然后转身开摩托车走了。
几天后的周末,我骑车去盐场找达仔,他正在盐田里装盐,用铲子把盐铲到两轮斗车里,装满后他在前面拉,一个约莫五十岁的男人在后面推。我问他需要帮忙吗,他让我在那里等他。海风从远处吹来,穿过脖子,痒痒的。我往他们推车的方向看去,料场上堆着一堆堆盐,像下雪天路边铲堆起来的雪。他们把斗车里的盐倒进盐堆,转推回来,放到我旁边的盐田边上。达仔向我介绍,这是高哥。高哥也是打赤膊,皮肤比达仔黑一些,肌肉块很大,但表皮已经发皱。高哥看着我说,中午一起吃饭。我说,我本来是过来请你们吃饭的,上次帮我拖车回去还没谢过。达仔大概也把这件事给高哥讲过了,高哥笑了笑说,下次再请,今天有深海鱼。中午我就在他们住的地方吃饭,那是一间当地人的自建房,一楼开海鲜大排档,二楼以上出租。高哥和达仔住二楼,是间单间,二十来平方米,厨房和住房用一堵墙隔开。一张铁板床,高哥睡下面,达仔睡上面。床底下有一块冲浪板,我问达仔,是不是在玩冲浪。达仔告诉我,干完活他经常去附近的海里冲浪。不久后,我便和达仔熟了起来,两人经常骑着摩托车沿着海岸公路兜风。我也跟着他一起学了冲浪。
二
摩托车沿着海岸线往南开,达仔有时在我前面,有时在我后面,有时我们并排走。海岸公路两边长满了热带植物,葱葱郁郁,棕榈树、香蕉树、椰子树,以及很多不知名的热带植物。达仔说高哥以前刚来的时候很不适应,这里的树似乎总是在疯狂生长,各种颜色鲜艳的花,在冬天也不谢。高哥老家是东北的,在那边完全想象不到存在这些东西。潮湿闷热的风吹着我们的耳根,摩托车的声音一浪一浪的,像是被这天气烤急了性子。不远就有一个斜坡,得退到一挡加大油门才能上去,斜坡顶上是个海军训练营地,那里视野很好,可以看到一片宽敞的海域。各种各样的鸟藏在树林里叫喊着,乱成一团。虽然路边立牌上有一些候鸟的相片,据说是从西伯利亚飞来过冬的,可我们从来没见过。
我和达仔一路向南,在几个海滩停下来,下去看后都不满意。不是太脏就是礁石太多,或者背风,浪很小。累了就立起摩托车,脚架在把手上,头枕着后箱,闭目养神。最终在海军营地附近的一个偏僻处,我们发现了一个海湾。那里偏离海岸公路有五六百米,周边都是松树,松树下长满了带刺的植物。我们下去后才发现这里是个墓地,那些土丘堆成的墓就分布在松树底下,带刺的植物长在墓与墓的间隙间。我们快速通过松林,到海滩时光线刺眼,一片细软的沙滩就在我们面前,沙滩上没有脚印,显然这里没人来。几十米外,浪一波一波的从远处奔袭过来。海湾呈一个环形,开向东南,东南风从风口吹进来,所以浪很大。底下也没礁石,都是沙。不用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最佳冲浪点。我们拿起冲浪板,往海里冲去。整个下午,我们都在海里度过,傍晚的时候,我们冲累了,便躺在海滩上休息。
你觉得怎样,达仔问我。他闭着眼睛,跷着腿,身上都是细沙。我说,这是我见过最适合冲浪的海滩。他说,那定时间吧。我打开手机看日历,今天是初七,下周日是十五,是涨潮时间,但第二天要上班。我说,下周星期六怎么样。他说,行,我提前跟高哥讲,上午多干些,下午就能来早点。
我们约的是晚上冲浪。最初是因为看了一些极限冲浪运动片,看着他们在海啸中冲浪很是刺激,还有的在毛里求斯的海底瀑布上面冲浪,像是随时都可能坠下去一样。这些离我们太远,我们不可能做到。达仔跟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试试晚上冲浪,也许更好耍。我试着想象晚上冲浪的样子,四周漆黑一片,只能听到海浪的声音,由远到近向我们袭来。我说,那样行吗?达仔说,不试试怎么知道。我说,那也行,但是要保证安全,我们得穿着救生衣,再买一个荧光手环戴在手上,好互相知道位置,毕竟夜里视线不好。达仔答应了。
我网购了救生衣和荧光手环,物流显示三天到。我一边等一边在市场和饮食店里奔波。几位顾客吃了海鲜粉后食物中毒,送去卫生院治了两天,出来后向我们投诉。我们去海鲜粉店里取样检验,样本并没问题,怀疑是顾客先前吃了跟海鲜过敏类似的东西。顾客那边不服气,坚称海鲜粉肯定有问题,最后把事情捅到上面。县里下文,要两天之内,进行一次全面大排查。第一天结束累得腰酸腿胀,晚上十点下班后,瘫到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干,连澡都懒得洗。我妈打电话来,问我最近状况,我知道她想问什么,她想问我有没有处对象,她一直盼着抱孙儿。我假装听不懂,说挺好的,附和几句便挂了。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们去市场搞突击,抓了三辆外地车,都是卖青头鸭的。两辆微型车,一辆摩托车。让他们登记后,便赶他们回去。微型车走了,摩托车却没动,人站在边上愣着。我过去问他怎么了,他指着旁边的熟食摊说,能不能先把鸭子放这里,我去趟海边再回来拉走。我心里掂量,他是不是想让熟食摊老板帮卖,但看他样子挺老实,就说,行吧。他把鸭笼从摩托车后架拿下来,跟熟食摊老板说几句话,转头跨上摩托车骑走了。我们收队回去,那笼鸭子还在那里。
下班时,我从办公室下楼梯,正要回去。办公室就在市场边头,在走廊就可以看见市场。有人喊喂,我转头,他向我跑过来,手里提着一个小塑料袋。他过来就把手里的塑料袋递给我,说,这是沙虫,就当是我感谢你。我摆手说,你留着吃。他的手僵在空中,没收回去。
我把他手推回去,说,你去海边就是为了这个?他说,我堂弟给的。他从兜里掏出根烟递给我,我自己点上。他继续说,我堂弟在盐场干活,他那海货多。我瞄了一眼他摩托车,后面只见一个笼子,里面的鸭没了。我说,行啊你。他抓着后脑勺,憨憨地笑着。我说,你这是要回去了吗。他说,准备回了。我问他住哪里,他说在北边山区那,骑摩托车半个小时就到。夏至将近,白日漫长,六点天还亮得很。我说,喝杯茶再回去吧,反正也还早。他开始还不太敢,以为我要跟他算鸭子的账。后面我跟他说,下班不讲工作,他才同意了。
他上身穿着一件篮球服,印着23号,下身穿着牛仔裤,身上有一股鸭毛味。端起茶杯,我发现他的手指很粗,手掌厚实,便问他除了卖鸭子还干些什么活。他说,砌房子啊。他有一个五个人的工队,专门给人砌房子,但现在活少了,村里面该建的也建得差不多了。没活干就贩鸭子卖。谈到他去海边的事,他叹了口气说,不瞒你说,我去海边就是为了想让我堂弟回去一趟。
三
他叫邱盛业,他堂弟叫邱盛强,他跟他堂弟同一个阿婆,他爸排行第十,堂弟他爸排行第十一。他十一叔有三个孩子,堂弟最大,下面还有两个妹妹,叫二妹三妹。三妹出生那年,十一叔因为械斗被判了八年刑,出狱两三年后因白血病去世了。十一嫂想留下来带大三个孩子,阿婆把她赶走了,她于是带着三妹回到她娘家贵州,从此没了音讯。一年多后堂弟离家出走,也一直联系不到。直到去年,二妹嫁到贵州,打听到她妈的下落,她妈改嫁好多年了,又有了两个男孩,大的已经五岁多了。她妈问二妹堂弟的情况,二妹说堂弟出走就没回来过,她妈就哭了,她说她想见堂弟一面。二妹就打电话回去跟他讲了,他去告诉阿婆,阿婆就让他去找。他一边贩鸭一边找,找了一年,在盐场那找到了堂弟,然后他跟堂弟讲已经知道他妈下落,他妈想见他一面,他堂弟没有置话。走的时候,堂弟送给他一袋沙虫,让他拿回去吃。
我们一直聊到天色发暗,他说他该回去了,我也没留他吃饭。出了门,他骑上摩托车往北而去。街面上人都散完了,街道显得宽大冷清。我一个人懒得煮饭,泡了包泡面充饥。半夜饿醒来,又吃了一包,结果腻得想吐,狂喝水。这样一折腾,睡意全无,打开电脑想玩游戏,又觉得无聊。手闲不小心点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还有和前女友小蟋蟀拍的照片,那是一个湖,我们站在湖边,笑得傻不拉叽的。还有几张她站在重庆的江边,烟雾弥漫,身后是一条空中轨道。她是重庆的,前一阵子刚结婚,请了我的几个大学舍友去喝喜酒。这样没什么不好,总不能盼望着人家一直单着。我看了几遍,把相片全拖入回收站,又东点西点,一直弄到五点多才上床躺着。隔天上班,昏昏沉沉,一直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着,像是要随时猝死一样。
周四快递来了,拆开把救生衣洗了一遍,晾了一天便干了,打算周五拿去给达仔,顺便请他跟高哥吃饭。周五早上请了下午假,午睡醒来后便往盐场去。到那他们还在盐田里。高哥看见我,说来了啊。我说,今天来请你们吃饭。高哥一听,放下手里的耙过来低声说,你是铁了心要请我们吃饭?我说是啊,都拖了两年多了,在你这白吃白喝的。高哥说,行,你把钱转我,我去买菜。钱转过去后,高哥推出他的嘉陵摩托车立马出去。剩下我跟达仔,他在盐田里,我在盐田边上。我跟他说,救生衣和手环到了。他嗯一声,头没抬起来,耙着海水,海水里已经有盐结晶出来了。我说,海水就是这样变成盐的吗?他抬起头,指着海的方向说,从那边引入海水,一层一层过滤,到这就变成盐了。他带我到最低的盐田,海水已经全蒸发掉了,田里都是盐,像一田雪。
我们聊了半个小时左右,高哥回来了,买了石螺、虾、八爪鱼和大蚝,说都是刚捞上来的,保证新鲜。他问我会做菜吗,我说马马虎虎,他哈哈大笑,转头走进厨房里。我跟了过去,帮他打下手。整好四五个菜,高哥下到一楼搬上来一箱冰啤酒,一盘冻饺子,还从角落里搜出几根红肠,问我吃过这东西吗,东北老家寄过来的。我说我吃过热狗,两个都笑。饺子加热后,高哥打电话叫达仔回来吃饭。
三个人围着一张小桌子,高哥把几瓶啤酒放上来,我们一人一支。喝了两瓶,我跟高哥说,我不敢喝太多,喝多会发酒疯。高哥说怕啥,喝个酒都不能痛快喝,做什么人啊。他这么一说,我只能继续喝下去了。喝了三瓶多,我有点晕,高哥问我,结婚了吗?我说还没结。我便把家里催婚的事和小蟋蟀结婚的事讲了出来。高哥说,这算啥事啊,以后好女孩儿多的是。高哥也喝了不少,说起了他的事。他说他二十多年前就到这来了,父母那时候说,你去吧,那边暖和,你从小就怕冷。他在这边成了家,也有了两个孩子,大儿子在广州读书,毕业后就留在那工作了。小儿子现在还在南宁读大学。这些年他想把父母接过来住,他们不肯,说这把年纪,就别瞎折腾了。高哥拿起半瓶酒,一饮而尽,说,我就想啊,人啊怎么过都是过,在东北是过,在这也是过,关键是过得痛快就行了嘛。我觉得高哥说得有道理,又敬了他几杯。达仔话很少,几乎都是喝酒。不久我们都迷糊了,高哥执意让我睡他的床,我问他睡哪,他说你别管,大老爷们还怕没地方睡觉。达仔爬到上铺,我也实在是晕了,躺下来就睡。
做了一些混乱的梦,醒来后发现脖子和额头都是汗,看了一下时间,凌晨三点半。又眯了一下眼,但毫无睡意,干脆就起来了。墙壁上的风扇缺润滑油,咔咔转着,外面路灯光从窗帘的缝隙泄到地板上,高哥侧着身子,两条腿叠在一起,躺在凉席上呼呼睡着。我有点想吐,踮着脚走出门,外面正下着大雨。下了一楼,拧开小门,雨一下子扑面而来。好久没见这么大的雨了。虽然想吐,但脑子却异常清醒,喝了这么多年酒第一次这样。这让我担心是否身体某些器官出了问题,前段时间在宿舍洗头,一抓下来手里都是头发,以为是用力过猛,试着轻轻抓,头发也一样被抓下来。对着卫生间里的镜子照,笑起来眼角有两道很深的沟,突然感到一阵恐惧。我贴着墙壁,顺着路往外面走去。雨水落到地面,从高处往低处汇集,疯狂往下水道冲去,到处是水的流动声。路灯上一群飞蚁盘旋着,有些断了翅膀掉下来,在湿漉漉的路面爬。夜幕被一道闪电劈开,接着传来轰隆的声音,前面已经能听到海浪的声音,但雨实在太大,我钻进路对面的一个公车亭,靠着广告牌掏出一根烟,发现火机好像落在房间里了。也不想放回去,就把烟叼在嘴里。很多以前的事情被大水从角落里冲出来。好多个这样的夜晚,我跟小蟋蟀在出租房的窗前,她爬上窗台,把细长的腿伸出防盗网外,让大雨淋她的脚。我背靠着窗台,一直抽烟。窗外是一条铁路,隔半个小时,火车呜呜驶过,远处是嘉陵江,很多船停在江边,船舱里亮着昏黄的光。有次她伸手出去抓了一把雨水,甩到我的脖子上。有次我把一根烟插到她嘴里,把打火机藏起来,不给她点火。她急得从窗台下来,在我身上摸了个遍,最后把烟插回我嘴里。她那会刚学抽烟,经常换各种姿势问我,烟是这样抽吗。我说,你想怎么抽就怎么抽。我们分开后,有一天她发信息跟我讲,她学会抽烟了。那天我正在赶着去考事业单位,考完天就下雨了。这里也是很多雨。后来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贵州出差,在高速公路上下起了暴雨,前方一片模糊,我右拐进应急车道打双闪停车。雨刮开到最大挡位,在密密的雨中,我模糊看到右前方的路牌,上面写着“重庆”两个大字,我按下车窗,探出头去呕吐不已。吐完雨把中控台全浇湿了。
四
雨中,有脚步声传来,达仔也出来了。他跑过来坐到候车椅上,脱下短袖去擦身子和头发。他说,你是不是出来吐了。我说,还没有。他说,我先吐。说完蹲到旁边,面向绿化带开始吐。雨水大力敲击着公车站的遮雨棚,落下来的雨滴弹到我的小腿上。你带火机出来了吗?我说。他背着一只手,把火机递给我。我点燃烟,把火机放进兜里。他说,火机呢?我说,你不是在吐吗?他说,妈的,一个月被你顺了多少个火机了。他转过身来,还是蹲着,我把火机递给他,他也点上一根烟。有些事情跟你讲。我说,讲。他说,昨天我堂哥过来。我说,我猜到了。他说,噢,你还见过他?我于是把那天遇到邱盛业的事情讲了。达仔说,我一直没告诉你,我真名叫邱盛强。顿了一下说,他叫我回去一趟。我说,然后呢?他说,他说找到我妈了,在贵州,她想见我。他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树枝,伸到雨水中胡乱划着。我不搭话,继续抽我的烟。他继续说,我妈那时候走前说写信给我和二妹,我每天都去小学门口等邮差来,每天都没有我的信。后来邮差说,别来了,有信我拿上去给你。我等了一年多,就不等了,出去跟一帮小混混到处晃荡,天天找架打。有一次我们中一个人被打了,我们纠集几个人去给他出头,在一个小巷里被人家拿砍刀埋伏,我溜得快,一路狂飙,最后跑到盐场躲。被高哥撞见,高哥一看我这狼狈样,就问我小伙子跑啥,见鬼了呢。我说是,他说过来我这儿,我看哪个鬼敢来。后来那帮人没追来,我也没地方去,就留在盐场了。妈的火机怎么打不着了。达仔烟被雨溅到熄灭了,正要点,怎么也打不着打火机。我把烟递给他,他对着火星点着,浓浓吸了一口。我爸被劳改那些日子,大家都叫我劳改犯,我全都回击,说你他妈全家才是劳改犯。等我爸出狱,我一直想问他到底是不是劳改犯。那天早上天还没亮,他用摩托车送我去学校,天很冷,但我不抱他,我把手放在车后架上。一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摩托车穿过了很多村子和铁路桥,两边山影模糊,我想着到学校门口就问他。等到了学校门口,我下了车,在原地站了几十秒,最终什么也没问,就进学校去了。不久后他就死了。二妹前阵子打电话来跟我说,妈那时候有寄信,隔一段时间她就把信放到街道的邮筒里。她一直没收到回信,以为我埋怨她,不给她回信。一年多后发现那个邮筒是废弃的,早就没人来收信了。她还说,你也别怪阿婆,她要是不把妈赶走,妈怎么养我们三个孩子。
雨越下越大,偶尔闪电把夜空照亮,旋即又暗了,像谁关了灯一样。有个井盖被冲开,水从下面喷涌上来,一下子路上的水全变黄了。我手靠在公车站柱子上,那是一根不锈钢柱子,很凉快,敲起来哐哐响。我面向着海边的方向,达仔面向着岸上的方向。我们就这样对话。我说,你现在打算怎么样,要回去吗?很久都没有回音。一声响雷之后,他说,不回了,回去又能怎样。
后来雨小了一些,我们都不说话了,我敲着公车站柱子玩,他也拿起那棍子敲,我敲一声他敲一声。声音消失的间隙,我们听到了海浪的声音。一直待到雨停,我们才回去睡觉。出租房里,高哥翻了个身,继续打着呼噜。
醒来发现太阳晒到我的脖子上,高哥不在了,凉席卷起来挨在墙边,爬上去看,达仔也不在上铺,他们什么时候起来我都不知道。起来用冷水洗了把脸,拿上救生衣便出去。他们都在盐田里了,我把鞋子脱掉,扔到很远的沙地上,也进去盐田里帮忙。高哥问我吃早餐没有,我说我不饿。我是真的一点都不饿。
下午五点多吃了东西我们就出发了。达仔骑着高哥的老嘉陵,我骑着我的雅马哈,我们沿着海岸公路一路往南。想来是大雨刚停的缘故,海里和山上有一层薄雾,我们穿过一层,前面又有一层。柏油路很潮湿,路边的热带植被刚喝饱了水,叶子比平时都肥。蝉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层层叠叠,笼罩着海和雨林。
穿过松树林,墓地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到了海边,风开始吹起来,太阳隐在浅灰色的云层后面。浪很大,白花花在海面上翻卷着。我们把摩托车停在海滩上,各自靠着自己的摩托车,等夜晚降临。我们没有讲话。但我们都知道,今天是个适合冲浪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