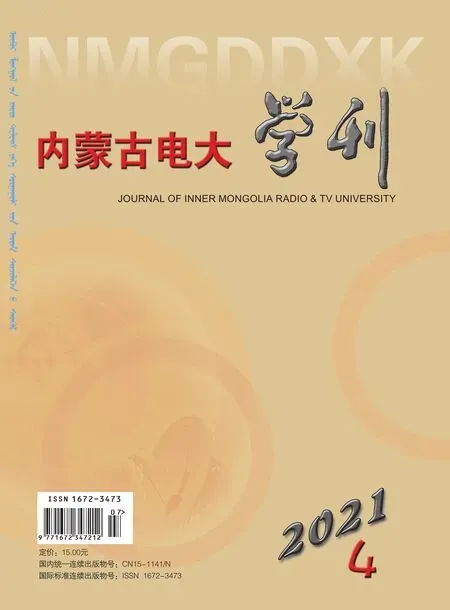由“同义”而“相利”:墨子君民关系思想探析
华 宇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0)
墨子学说是中国先秦时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被韩非子誉为世之显学, 秦汉以后,由于思想统一的现实统治需要,墨子学说虽坠入历史洪流,一度沦为绝学,但是墨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却不可忽视。历代统治者虽未对墨学引起重视,但在学界和民间,对墨子思想的学习与研究从未中断。近代,梁启超曾疾呼:“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1]P6胡适、鲁迅等现代大家也对墨子及其学说有极高的认可。显然,虽然经历了历史的考验和岁月的沉浮,墨子思想依旧在整个中国思想史发展进程中散发着璀璨的光辉。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与实践中,君民关系一直是一个关键性的议题,作为判别政权统治有效性和合法性的重要标准,也一直为官员和学者所重视。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荀子的载舟覆舟理论,都体现了儒家对这一问题的观念和立场。然从中国古代的政治实践来看,先秦儒家所倡导的这一观念和立场并未发生实效,在“尊君”和“重民”的选择上,历代统治集团的旨向显然更偏向于前者,这也是牟宗三先生评价中国古代政治历史“只有治道,而无政道”的根本原因之一。作为先秦政治思想中主要反映下层人民和小生产者利益诉求的墨子思想,被诸多学者称为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代表,其关于君民关系的阐析无疑应当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以此,对墨子君民关系之思想致思理路加以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墨家思想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也使我们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系统特性,从而获得新知的重要线索。
一、墨子义利观概述
关于墨子思想的基本内涵,自先秦以来就有诸多的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兼爱、非攻为墨子思想之核心;亦有人称节制克己为墨学之精髓;还有观点认为墨家之本在于专制、上同。以上虽各有根据,但墨子思想中的要意何在?仍有待研讨和商榷。关于墨子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墨子·鲁问》中有明确记载,“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2]P503墨子将其政治思想概括为十条论纲,亦称为墨子十论,即尚同、尚贤、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这十论体现了墨子思想的基本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3]P33墨子十论分别从国之局势、经济、风气、制度、交往五个方面对应性地论述了何以治国,从一定层面来说,可以将其理解为墨子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或策略。然纵观墨子全书,其所论之重中之重无外乎“义”和“利”两点。
墨家从政治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义者,善政也”[2]P225的观点,“义”在此成为治政之核心与基本原则,前述十论皆为善政之具体措施方略,从“义”而出,由“义”统领。如果说“义”为治国之准则和出发点,那么,墨子思想要实现的终极目标或政治理想则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此句作为墨子陈述其思想的结语在《墨子》中出现达十余次之多,足见其在墨子观点中的重要地位。亦有学者提出墨子的思想核心,并不是“兼爱”“非攻”,而是“交相利”。[4]在此可察,“义”说可以说是墨子对儒家“仁”学的重新改造,这种改造集中表现为以“义”释“善”,以“义”释“利”,比较于儒家的纯情“仁爱”道德具备坚实的“利益”内核,无疑是更能为普通民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5]综上,可以有以下的解读,墨子以“十论”作策,以“义”为本,以“利”而终,义利统一构成了墨子政治思想的整体体系和完整方案。虽然墨子义利统一说在当时具有空想的性质,但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辩证的色彩。[5]
二、“天”—“君”—“民”的政治关系体系
以“义”和“利”作为墨子学说的要旨来分析其君民关系思想,有几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分析。第一,“义”从何起,即墨家之“义”之来源和合理性的问题;第二,君与民,权力的主体与客体,国家与社会之间因何 “同义”?如何 “同义”?第三,如果“同义”构建起了良好的君民关系基本体系,如何达到兴利除害的基本目的。
(一)“天志”——“义”之源来
中国自夏商周以来就有比较明显的天命论和上天崇拜论的特点,亦有诸多典籍对此有所记载,诸如“有夏服天命”“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等。这首先源自从远古时代开始,人们对赋予生命及生存的自然资源的上天的敬畏,对“自然之天”的一种简单而直接的原始崇拜。及自国家诞生,又将这种原始崇拜与政治权力结合起来,赋予政治权力无可争议和撼动的神圣地位,也把世间政治关系和社会安排归于天的意志。这种带有神秘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论说无疑是那个时代的必然选择,也成为诸子百家学说的重要依据和起点,墨子思想也不例外。
关于“义”的源来,墨子的解释是:“曰:义者,善政也。何以知义之为善政也?曰: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是以知义之为善政也。夫愚且贱者,不得为政乎贵且知者;然后得为政乎愚且贱者。此吾所以知义之不从愚且贱者出,而必自贵且知者出也。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然则义果自天出矣。”[2]P226(《墨子·天志中》)墨子将天志作为义政的源来与出处,天的意志就是善政,善政即为义。志者,士之心也,在这里,墨子将天塑造成为一个有心有欲、富于理想的人格神,给“义”建构了无可争议的终极依据,确保了义政来源的正确性与神圣性。
“义”既为天出,在政治关系体系中就具有至高无上的意蕴和地位。“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贵于天子也。是故义者,不自愚且贱者出,必自贵且知者出。曰:谁为知?天为知。然则义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为义者,则不可不顺天之意矣!”[2]P238(《墨子·天志下》)在此,墨子强调了天志的无上权威性,同时确立了“义”在整个政治理论中绝对精神价值并作为其政治思想的准则和出发点。在政治关系体系中,“天”被置于独一的、最高的地位,虽然在现实政治关系体系中,“君”为上位,“民”为下位,但在无上的“天”面前,“君”与“民”两者无疑都位于“天下”这个相同的层面,两者皆需按“天”之意,受“天”所约,而不会因“君”与“民”位阶差距而有所区别,在“天志”之前,两者所受之“约”是平等一致的。
(二)天人关系——“义”之路径
作为“义”之所出,神圣之“天”在墨子思想中无疑是一个威严而慈爱的存在,其高高在上,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触摸与感知的。敬天事天,天必福之;逆天而为,天必祸之。作为至高神圣的存在,天不能直接参与人间事务的仲裁,因此,需要有一个天人之间的媒介。因此,墨子在构建其天人关系时,加入了“鬼神”之概念,并且清晰地表达为“明鬼”,不但需要不能模糊地、选择性地认识和使用“鬼神”之说,而且必须明确“鬼神”之存在及其在天人关系中的作用:作为天义之仲裁者和赏罚的执行者。“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想恶,交相贼,必得罚。”[2]P223(《墨子·天志上》)墨家将这种不同的后果引向了天降的灾异,可看作汉代盛行的天人感应论的先声。[7]
“天”“鬼”合一,构成了墨子义说的源头与保障。“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2]P106(《墨子·尚同中》)“天”“鬼”之下,便是立“君”,作为“义”在人间的倡导者和执行者,“君”之作用与价值便在于“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自此,墨子更进一步完善和构建起其“天”“鬼”—“君”—“民”的天人关系,也为“义”之精神的普及和实施构建了完整的渠道。
在墨子的天人关系中,以“义”为线索,“天”“鬼”—“君”—“民”为完整的政治关系体系。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政治关系体系中,墨子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特点是需要注意的。其一,这一体系中的前提是尊天事鬼,对天、鬼的认同与敬畏是必要的,不可置疑的。其次,民对君之所事亦应当是绝对服从的,无可争议的。这种自上而下、位阶分明的政治关系体系是天下同“义”,一以贯之,保证“义”能够顺利施行的基本条件和最优路径。其二,这一体系中,所有主体也应当是平等的,“义”之要旨在于“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义”也是一种通约和规则,“义”既已出,“天”“鬼”“君”“民”之间总体上就成为互通互爱、相利相赢的命运共同体。在本文看来“天”“鬼”同源,“明鬼”之说应当可以放置于“天志”之下,为其补充,故在本文关于墨子相关思想论述中只强调“天”—“君”—“民”之政治体系。
三、君民互约与君民互利
在明确了完整的政治关系体系链条之后,回归于人的现实政治关系,对现实政治中的君民关系进行梳理成为墨子思想的重要任务。在礼坏乐崩、诸侯相倾的战国时代,如何具体构建和谐有序的君民关系无疑具有巨大的挑战性,通过对墨子思想的进一步解读,以下就君民互约和君民互利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君民何以互约——“同义”
自然状态下,现实生活中人的欲求、意志和价值是有差异性的、主观性的、充满变化甚至是区别对立的。人们的价值和意志既有善意的,也有不善至恶甚至威胁全体利益的,即便上升到了所谓群体意志,亦存不同群体、共同体,乃至民族、种族、国家之间之差异。国中之君主、家庭中的父母皆为长上,但其中仍不可避免有德行不端,即使品性良善之人也可能因为客观原因由善而恶,始乱终弃。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在墨子看来,其根源在于对“义”理解和认识的差异,如墨子所言,“一人一义……百人百义……”天下治,百姓利的关键在于“义”的同一,在墨子看来现实政治体系中,就是君民按照天志通约同义。
《墨子·经上》:“君臣萌,通约也。” 孙诒让间诂:“谓尊卑上下,等差不一,通而约之,不过此三名。”[2]P224也就是说,虽然权力有高低之分,阶位有上下之序,但君与臣民之间是互为通约的。在墨家思想里,“君”就是顺天同义、扶困救难的 “工具”,此所谓“天下器”。君主、三公、正长、里长的职责是“举公义,辟私怨”。以“义”为旨去治理天下,那便是顺天之意而治,是“兴利除害”之大义。
那么关于君民如何互约呢?从“民”对“君”的限约来看,对君主的要求首先是“自节”。墨子提出:“节于身,诲于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2]P59(《墨子·辞过》)如何理解“节”呢?墨子此处提出的“节”虽有一般意义上的“节约”或“节省”,但更应当是“君”的俭谨和自律,具备与儒家“修身正己”异曲同工的蕴涵,是一种出自严格的自我修养和领悟天志后的辟私为公、保民利民的道德修为与有效作为。“节”是立君之本,为君之道,亦只有通过 “节”才能获得“民”的认可,才能诲民同义。
从“君”约“民”的角度来看,除了勤、俭、备、富这些为民的基本要素之外。墨子反复明言:“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墨子·尚同中》)“君”所认可的事情,“民”也须得全盘认可;“君”所否认的事情,“民”也须得全面抵制。从“君”之事,习“君”之为。“君”为上天所选,受上天之托,作为上同与天的天志解读者和代言人,“君”在君民二元关系中具有相对较高的位阶也应当具有绝对话语权和权威性,“民”对其必须要保证绝对的信任和服从,从言行上认可、学习、效法并与之一致。
当然,这种一致的前提是保证“君”能上同于天,举天之义。“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2]P109(《墨子·尚同中》)墨子天志之下,以“义”为旨的君民互约体系之中,为君者,需上同于天,举天之义,俭谨自律,方才能够使天下臣民信服;为民者,需以君为榜样,为君是从,与君共同除害兴利。
(二)君民何以互利——“同义”而“交相利”
在墨子眼中,君民互约的基本原因是两者的相互依赖:“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2]P53(《墨子·七患》)以粮食为例,没有充足的粮食,就无法供给整个以君为首的国家机器;没有充足的粮食,作为普通老百姓也无法生存,更无法从事再生产的活动。因此,两者的“利”在此是具有一致性的,利民便是利君,利君亦是利民,二者相互依存,彼此不可分割。
从天志和同义的角度来说,君民互利亦是体系之利,“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2]P50(《墨子·法仪》)因此,天志之“义”在于君民之间的互爱互利,上天之义的达成也在于君民之间“兼相爱而交相利”。为君需要能够谙合天之义,谨言慎行,精心考虑,去求索天下。以此上奉于天,以此下施于万民,天即享用其德,确保其权位和统治;万民即蒙受其利,方能心悦诚服,为君为国。天义之下的君民互约、君民互利构成完整和谐的政治关系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以“义”为旨,以“利”而终,“天”是发起者、“君”是倡导者、“民”是践行者,“天”“君”“民”同义而交相利,以此,天下大治方可实现。
——Revisiting the Problem of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betwee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