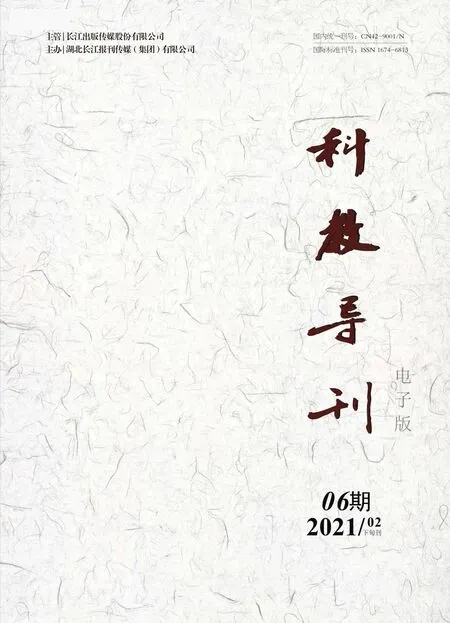《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叙事及审美价值探析
张嘉容 卢 敏 肖 雯 宋佳静
(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044)
艾丽丝·门罗(Alice Munro)是享誉国际的当代短篇小说大师,1968年出版发表首部短篇小说集,获得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其后四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也佳作频出,于2013年成为加拿大首位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门罗的视线多聚焦于小地方普通人特别是女性隐含悲剧的平常生活,以细腻透彻又波澜不惊的话语,着力描绘她们对周围世界、生活中的男人的自省式反应,洞见了人性的幽微处。门罗遵循传统叙事风格,同时又大量借鉴了现代叙事技巧,这使得其小说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艺术。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艾丽丝·门罗作品的研究,国外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现已形成清晰的研究发展脉络,相较,国内学界对门罗作品研究起步较晚,在近十余年中呈蓬勃发展之势,主要聚焦于叙事学、女性主义等角度,对小说主题、写作风格、女性形象、文本叙事特点进行研究。周怡(2014)探讨了门罗作为短篇小说家的身份以及门罗作品中重要的叙述表现手段,进而阐释门罗的短篇小说艺术;陈思(2015)运用苏珊兰瑟的空间、心理、时间及语言视角探讨了门罗作品中的女性声音,揭示门罗作品的女性主题;傅琼(2016)将语用学理论成果用于分析检验门罗短篇小说中的女性书写主题。尽管学界对门罗及其作品的研究已有较丰硕的成果,但研究成果距离她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国际影响力尚相差甚远,并且对门罗作品的某一艺术特点进行孤立的研究为主流,缺乏多维度、综合性研究。
于197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合集《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是艾丽丝·门罗创作的第三部小说作品,被认为是门罗尝试长篇写作后的成功转身,从此门罗只创作短篇小说。小说集同名作品《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随着主人公记忆的展演,拼接回忆片段,揭示两男两女间的情感纠葛,以及深埋心中数十年的秘密。此篇小说就问世以来,学界对其研究仅聚焦于文本叙事特点及小说主题。陈英红(2018)探讨门罗于此篇小说中记忆书写、意识流手法、多视角叙述等非线性叙述技巧的运用,进而揭示门罗对现实主义创作的传承和突破。张磊(2014)对小说主题,女主人公心理特征进行剖析,指出门罗于此篇小说中展示了病态的权力与控制欲望在家庭生活中复杂而又残酷的运作过程。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作品主题内容的解读和文本形式的剖析上,论题较为集中。本文拟从叙事和审美双维度,突破现有研究的局限性,以德国康斯坦茨学派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为理论观照点,通过探讨该小说中的叙事艺术,分析作者在小说中通过拼贴式非线性叙事以及叙述视角的转换,如何为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接受、审美空间,进而召唤读者进行填补和再创造,实现文本本身丰富的艺术魅力。
1 伊瑟尔的接受美学
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是德国接受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从事文学的接受研究的先锋人物,强调了读者在文学批评和鉴赏中的地位与作用。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是在文本与读者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得以实现的动力和条件,强调文本的意义存在于阅读活动中读者的创造性的集合之中。
根据沃夫尔冈·伊瑟尔(1991)于《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文本与读者互动交流的理念论述,文学文本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召唤结构”,而“作品的未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从而赋予他参与作品意义构成的权利”。“空白”作为文学文本和读者相互作用的驱动力因素,构成了文学本文的召唤结构,不仅实现了读者与文本两者交流的可能性,而且激发读者更积极地参与文学文本的再创造。另一方面,读者需要通过“游移视点”响应文本。根据沃夫尔冈·伊瑟尔(1991)于《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的论述,游移视点是“描述读者在本文中得以表现的方式的手段”,并且“游移视点不断地在本文的视角之间转换,每一转换都表现了一个清晰连接的阅读瞬间”。由于读者的“每个阅读瞬间都是延伸与记忆的辩证运动,并且与正在不断消退的视野一道构成或唤起一个未来视野”,因此,随着阅读不断向前推进以及文本叙述视点的不断转换,读者需要通过游移视点适应文本,“穿越文本而演进”,不断对阅读所获材料进行联结、转换、修改、综合,即“一致性构筑”,从而在光度与深度上扩充文本,形成相互作用、彼此构建的关系。而读者在对文本积极和主动的接受与构建过程中,正实现了审美对象的呈现以及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
2 拼贴式非线性叙事及其审美价值
2.1 作者叙事——拼贴式非线性叙事模式
根据申丹(2010)所引用的亚里士多德于《诗学》中“叙事有机完整性”的论述:“所谓完整,指事有头,有身,有尾。所谓‘头’,指事之不必然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的发生者;所有‘尾’,恰与此相反,指事之按照必然律或可然律上承某事发生,但是他不引起后事的发生;‘身’即上承某事,也下启某事发生。”,情节结构完整,时间序列在起因、发展和结局过程中有因果关系和有机联系,单线且前后有序即“线性叙事”,由此,打破“线性叙事”单线、有序模式的叙事,即为“非线性叙事”。艾丽丝·门罗在叙事手法上突破传统叙事模式,叙事艺术灵巧精妙,常采用多线条的叙事模式、碎片化的叙事时序、灵活多变的叙事节奏、交替转换的聚焦模式等,使读者从其短篇小说简单故事背后感受到深邃的审美体验。短篇小说《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正突破了传统的单线有序线性叙事模式。小说的叙述时间随着恩特记忆的展演不断变换,形成故事叙述时序的错乱,而呈现断裂且零碎的叙事,构成颇具张力的拼贴式结构,即“多个叙事模块,包括不同叙事文本或不同叙事情境的模块拼贴在一起的叙事结构”(罗美娇,2016)。小说叙事话语如下展开:
主要人物及基本关系:
恩特;
莎尔:恩特的姐姐;
布莱基:莎尔的初恋;
亚瑟:恩特的高中历史老师,莎尔的丈夫。
叙事话语:
事件A:恩特和莎尔谈及刚刚返乡的布莱基(此时莎尔“头发灰白”)。
事件B:恩特跟布莱基观光团出游,布莱基对女游客献媚(“就在前一天”)。
事件C:亚瑟身体抱恙在家休养,布莱基、恩特、莎尔陪伴游戏(“那个夏天”莎尔亚瑟已婚多年)。
事件D:恩特时隔30年街上偶遇布莱基。
*恩特回忆:莎尔的美、弟弟的死、认识布莱基、旅馆的改变。
事件E:莎尔和布莱基的恋情(1918年的夏天)。
事件F:布莱基结婚,莎尔服毒未遂。
事件G:恩特照顾亚瑟,发现橱柜毒药,随后每次到他们家均检查是否使用(亚瑟身体抱恙在家休养)。
事件H:亚瑟爱上莎尔,两人婚后生活不合,恩特时常拜访。
事件I:布莱基短暂离开小镇,恩特向亚瑟、莎尔谎称布莱基勾搭上有钱女人。
事件J:恩特担忧谎言识破,与亚瑟共同生活(莎尔已去世)。
事件K:毒药瓶消失,莎尔去世。
事件L:恩特一直没有告诉亚瑟真相,两人共同生活,直到终老。
小说开篇以恩特跟姐姐莎尔谈及布莱基开始,紧接着转换到回忆随布莱基出游的行程中,恩特无心观光,仅对布莱基对女游客的献媚进行观察,并不由自主想到亚瑟,随之新人物的闪现入场制造出新的悬念。随后叙事时间自由穿梭,以恩特的回忆对莎尔进行介绍,并交待人物之间的关系,为后续情节的发展奠定基础。接着,叙述时间倒回莎尔为布莱基服毒未遂事件的回忆后,随即拼接恩特于莎尔和亚瑟家中发现毒药的记忆片段,制造出悬疑效果。而后,叙事回到莎尔服毒未遂事件后收获亚瑟的爱,其间插叙恩特对亚瑟作为其历史老师的回忆,描述莎尔对亚瑟冷漠的态度以及两人婚姻不合的状况。最后,叙事转向恩特难以释怀的、一直没有告诉亚瑟的,关于莎尔自杀的秘密。《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全篇通过回忆片段的拼接,叙述时间的跳跃转换,基于记忆的非线性叙述使得剧情扑朔迷离、情节波澜起伏。门罗通过其独特的叙事艺术,使四位主人公的人物关系以及情感纠葛,随着记忆片段的叙述逐渐浮出水面。
2.2 读者审美——空白
由于文学文本不仅需要作者的构建,更需要读者的主动参与,以实现小说情节的积极意义,而接受美学正阐释了文本与读者之间存在的互相作用彼此建构的关系。因此,根据沃夫尔冈·伊瑟尔(1991)于《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中文本与读者互动交流的理念论述“一部作品所包含的不定性与意义空白越多,读者就越能深入参与作品潜在意义的现实化”。通过上文对叙事话语的分析,可知《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的非线性叙事模式,打乱现实时间中故事发生的顺序,以在小说中营造出时间错乱的场景,构成了叙事时间的张力与不定性。并且,在非线性叙事下,拼贴式结构的采用“使短篇小说拥有更多的叙事角度和叙事空间”(罗美娇,2016)。门罗有意使叙事话语呈现断裂且零碎,以回忆片段的拼接和叙述时间的跳跃处处留下“空白”,给读者提供了诸多参与空间与审美空间,诱导读者进行填补和再创作。根据伊格尔顿(2007)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的阐释“空白向读者发出邀请,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连接种种断裂,填补种种空白,进行种种推断,验证种种预感”。当读者阅读完整篇短篇小说后,会发现原本零散的部件其实都是叙事结构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各个叙事模块之间虽是独立,实则相联系,以此召唤了读者的构建行为,使读者深入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实现和作品艺术的再创造。
再读《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读者会发现小说开篇从接近尾声的部分开始,着眼于恩特和莎尔的对话以及布莱基形象的构建,而事件B以一个问句戛然而止,“毫无疑问,莎尔是见过他这种表情的。但她是否知道,他是何等随意地将这一表情送给每一个他遇到的女人?”此处,读者无从得知莎尔与布莱基的关系。而叙述者笔锋一转,时间跳跃到“那个夏天”,即事件C,莎尔和亚瑟策划的旅行因亚瑟身体不适去不成,布莱基前来拜访玩游戏。此时故事人物均出场,但人物间令人困惑的关系仍没有得到解答,故事线索又再次中断,造成意义的空白,读者只能通过想象力、猜测与推断去填补空白,直到阅读到事件E与事件H,即对1918年的夏天莎尔和布莱基的恋情以及亚瑟爱与莎尔间感情的介绍后,读者才得以重构故事顺序,对文本结构进行思考、判断与连接。小说的后部,恩特发现毒药瓶、恩特撒谎、莎尔自杀、恩特与亚瑟共同生活,这几个事件发生时序被打乱成零散部件,相互交错,导致读者不断处于交叉点中,游移于几个部件之间。叙述中断引起的空白又不断诱导读者通过游移视点,逐步填补牵连起现实时间的过去与现在,网络人物间关系,重新整理构建起故事话语。最终读者对文本的建构如下:
故事话语:E—F—H—D—B—A—C—G—I—K—J—L。
故事话语对事件现实时间事件发生顺序的重组,呈现出叙事话语中时间上的交织与拼贴。门罗通过拼贴式非线性模式的叙事安排,使作品呈现出时空的分散与跳跃,为读者留下空白,设置接受与审美空间。同时,对传统单线有序叙事模式的打破,使读者习惯阅读模式受阻,“当习惯动作收到困境阻碍的时候,就会产生审美态度”(阿米斯,2015)。因此,读者在曲折性阅读过程中,会主动积极地通过游移视点,填补文本意义空白,重建时空的逻辑性,聚拢文本细节,对文本进行意义重构。根据阿米斯(2015)在《小说美学》所述,“在这些景象面前,出现了另一种实际上是由读者掌握的东西。由这些东西也就增加了戏剧的价值”,同时,读者在参与作品审美潜能的实现和作品艺术的再创造过程中得到了审美体验。
3 叙述视角转换及其审美价值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采用高度自由的第三人称叙事角度,其中涉及全知视角向固定人物有限视角的切换。根据申丹(2010)在《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所述,“在全知模式中,会经常出现规约许可的内部视角转换”,并指出,“这种转换可产生短暂的悬念,增加作品的戏剧性。”视角变化是作者设计调整读者观察方式的一种方法,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向第一人称限知视角转换,可以让人物在亲身经历中向读者讲故事,这就使得叙述的范围因叙述者的眼界而逐渐变小,最终与人物的视角一致,读者的视点从全知全能叙述下的客观事实,游移到小说人物的内心活动中,有了亲身体验的代入感。同时,视角变换推动了读者对文本进行一致性构筑,“建立审美对象最终个性化的综合”(伊瑟尔,2010),从中获得审美体验。
在事件I,即恩特编造谎言,向亚瑟和莎尔谎称布莱基重蹈覆辙勾搭上了有钱女人因此离开小镇的场景,叙述者站在全知全能视角下,通过对恩特与亚瑟的对话,三人状态变化的细微描写,客观叙述事件、描绘情景同时塑造人物,此时读者的所知所感大于人物视野。转而,叙述片段以莎尔走进房间弹起的琴声中断,切换到事件J,转入人物限知视角,即恩特的视角,叙述时间也通过视角的转化实现了跳跃。此时已是多年之后,恩特已与姐夫亚瑟生活在一起。在事件中,恩特充当叙述者,通过有限视角来叙述自己对谎言是否会被识破的担忧,同时反思自己撒谎行为。此时,读者此时只知恩特视角下,其自身对撒谎的愧疚与纠结,以及在失去莎尔后,恩特与亚瑟共同生活的日常。在此,文本视角转换,读者所知所感等于人物视野,而亚瑟的心理状态,以及亚瑟对布莱基离开和莎尔自杀的想法我们不得而知,留下了空白,形成召唤结构,诱导读者进行想象与填补。并且,恩特此时纠结的心情与视角转换前恩特毒舌的性格,以及不假思索的撒谎形成鲜明对照,留下悬念。而此悬念在随着视角转换而倒退的叙述时间中才得以解答。当恩特的回忆跳跃回莎尔突然去世的那天,即事件K,恩特发现毒药瓶消失,揭露出恩特的愧疚在于她认为莎尔是由于自己谎言而选择了自杀,而此秘密恩特一直藏于心中,并与姐夫一起生活直到终老。此时,读者通过游移视点,不断调动相应视野下已经实现了的过去视野,重新整理构建文本,完成情节逻辑联结。
在此,全知视角向固定人物有限视角的切换,使读者视野转向与人物的视角一致,一方面,使得故事有了亲身体验的代入感,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所感所知缩小留下空白,进而召唤读者进行想象与推测填补文本之外的空白。同时,由于视点的转换,叙述时间的跳跃,读者需通过游移视点,展开对相互联系的各视点的整合,通过全知视角下恩特与亚瑟的话语和状态以及情节的展开,对固定人物有限视角下恩特的心理以及人物形象进行修正与整合。如此一来,两个视角便相互交错穿透,相互调节影响,读者阅读过程中不断进行信息的加工与整理,依照伊瑟尔(2010)的论述,“这种观点和关系的不断变换推动了读者去建立审美对象最终个性化的综合”。此时读者对作品的主动参与互动过程,对本文意义进行了重构,从而实现了文本意义,获得了独特的审美体验。
4 结论
《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中非线性叙事模式以及拼贴式结构的采用,使得文本的演进呈动态发展,而全知视角向固定人物有限视角的转换,使得文本的视野交错穿透。恰恰是这种空白多,具有极大跳跃性、随意性和不连贯性的阅读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诱导读者通过游移视点加以合成处理,主动对故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进行填充、修正衔接、更新期待视域,使得文本各个间隔的成分组成连贯而有意义的单元,连续构建进而使得文本具体化,成为有生命的艺术形象。艾丽丝·门罗独特灵巧的叙事艺术,引导读者对文本积极和主动的接受与构建,赋予了《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事》非凡的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