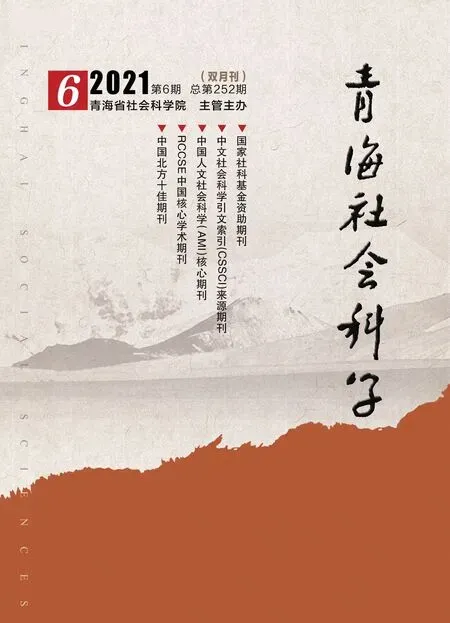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效应及其治理
◇吴 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页。互联网时代,网络社群存在诸多思想舆论形态,那些非理性的“群体极化”对意识形态或许会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网络群体极化”是互联网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亲和力的基本背景,依照美国社会学家桑斯坦的观点:“群体极化的定义极其简单: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网络对许多人而言,正是极端主义的温床,因为志同道合的人可以在网上轻易而且频繁地沟通,听不到不同的看法,持续暴露于极端的立场中,听取这些人的意见,会让人逐渐相信这个立场。”①[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网络群体极化”的反映形式,它们对意识形态的效应及相应的治理路径是有必要的论题。
一、网络群体极化的“非理性”困境及其成因
我国学界对“群体极化”的研究大多围绕桑斯坦的上述定义展开。有论者对桑斯坦的观点进行了如下的简化:“网络群体极化就是指网络群体成员在网上就某一问题进行反复讨论后出现的意见和观点的分化、移动、集中并达到对立或相反的一种网络现象。”②王邈 、蒋一斌:《网络群体极化及其心战功能》,《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7页。也有论者认为:“群体极化似乎是个不带有感情色彩的中性词。因为群体极化的方向可能是保守,也可能是冒险……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群体极化现象已经愈加走向消极的方向。”③袁慧、李锦珍:《网络群体极化表现及其特征》,《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第140页。这些研究指出了“群体极化”的结构在于“成员-形成群体-固定论题与反复讨论-观点形成-观点集中”,单纯就其形式来看“网络群体极化”并不必然导向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但因诸多不可控因素,则极易导向非理性而造成负面影响。
(一)“身份理性”的悬搁与成员的匿名化:去具身化与行动恣意性
首先就“成员”来看,互联网为其成员的社会身份提供了较好的掩饰,意味着一个人兼具“公民”和“网民”两重身份,前者对应这个人的现实的职业工作,后者则与前者没有必然关系,我们将之称为“去具身化”,意味着在现实社会之中的基于身份的理性尺度的悬搁。一些论者将这种情况称为“身体的不在场”,认为:“身体的不在场性和不可见性除了使得网络极端情感的发生可以克服冲突性紧张的阻碍之外,还使得网络极端情感的后果不可见,从而大大减轻了道德负担……一方面使得个体能够克服阻碍极端话语和极端情感发生的冲突性紧张,另一方面还使得个体对其恶劣言行后果产生心理盲视,道德自抑机制因此失效。换言之,身体的不在场性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极端情感的‘发生’扫平障碍,也能够有效地控制极端情感的恶劣 ‘后果’对极端情感发出者所造成的心理和道德负担。”④田林楠:《网络情感是如何极化的? ——一个情感社会学的视角》,《天府新论》2017年第2期,第136页。在本文看来“身体的不在场”的深意在于“具体身份”的不在场。在互联网营造的虚拟世界之中,现实社会的身份不再有效,这一方面体现为在现实生活之中的人的身份和伴随的社会阶层在互联网之中消解;另一方面,“去具身化”也意味着那些以身份为符号的社会规范在网络世界之中被悬搁,这既体现为用社会身份来进行网络活动会遭致匿名他者的背反,也体现为前引所述的依照“身份”背后的“职业伦理”“行业规范”进行道德自律和自制的理性活动有可能在“去具身化”的情况下被替换成不受自我规制的纯粹的感性宣泄。概言之,在“公民”之中存在的社会阶层在“网民”之中可能不再有效,“社会身份”带来的理性自律也可能随着“去具身化”而丧失。
在这种情况下,与“去具身化”相伴随的就是“行动恣意性”。当然,并不排除即使在互联网领域内仍然坚持自律自制的人的存在,但是“恣意”至少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有论者认为:“在互联网空间,人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匿名化的缺场交往,这种人的‘身体缺场’和‘符号化’交往方式极大地张扬了人的生存自由,使普罗大众获得了选择与表达的权利,他们可以凭借‘面具’的遮掩以虚拟身份游弋于网络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就其所关注的网络议题随心所欲地发出自己的声音。”⑤秦程节:《网络群体极化:风险、成因及其治理》,《电子政务》2017年第4期,第50页。也有论者指出:“网络世界虚拟的身份与匿名的形式让人们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等感与安全感。正是这种平等感与安全感增加了人们对自我意志的认同,并激发了人们表达与表现的欲望。于是,人们开始选择在网上畅所欲言、无所顾忌。在网络把关人允许的范围里,网络可以宽容任何人的任何惊世骇俗的见解。可见,由网民虚拟身份所带来的网络舆论的开放性、自由性是传统舆论形式无法比拟的。”①相喜伟、王秋菊:《网络舆论传播中群体极化的成因与对策》,《新闻界》2009年第5期,第93页。这也就意味着,在允诺了平等、交往、表达权、宽容和开放的互联网空间中,成员的行动自由在缺乏“自律”的情况下,必然转向“恣意”,既体现为作为网民个体的舆论表达和评判的自由,也体现为作为网民个体与其他个体之间进行群体性交往的自由。
因此在互联网之中的“极化”也就变成了:首先,由于社会现实身份的去除,“网民”依照身份和职业的现实社会阶层被打破,身份和职业的规制也被悬搁。其次,网络空间本身的包容、平等的表现形式使不同现实身份的网民在遇到“共同兴趣”的情况下自由地形成“网民群体”,并且依靠兴趣话题恣意讨论。桑斯坦将这种情况称为“回音室”效应,认为这种恣意的群聚讨论的后果往往变成“归入自己的回音室”,持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个体不断组成群体,对同质化的信息进行不断的讨论和发酵,最终让自身陷入只有一种声音且反复被听觉的“回音室”之中。②[美]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
(二)“制度理性”的悬搁与观点的极端化:去权威化和群体激进性
再从“论题和观点”来看,“成员”的社会身份以及相伴随的社会伦理和自律可能由于“匿名”的自由而转为“恣意”,在选择维系共同群体的话题上也就相对恣意。这首先表现为“去权威化”的效果,即本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态,法律的权威很难成为如同在现实社会之中的“铁律”一般的行为尺度,“制度理性”也被悬搁了。有论者认为:“在网络虚拟这种特殊的社会情境中,生存于同一社会阶层或具有相同生活感受、体验或经历的人们,往往更容易因相互理解、沟通而产生共鸣。特别是对某个人、某件事件持有相同观点或立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时,这种观点和立场往往会得到彼此间的强化,最终突破道德伦理、规章制度的藩篱而走向极端。激进观点或不满的情绪,逐渐演化得更偏执更极端。”③胡明辉、蒋红艳:《构建网络群体极化与约束机制》,《学术交流》2015年第6期,第209页。上述的论断体现了“去权威化”的两个面向:一是维系一个极化群体的不再是法律或制度的权威,而在根本上是“论题”“观点”抑或是“事件”,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法律”还是“政策”都不再是规范而是可能的“共同论题”之一。另一个面向则是,在论题和观点的选择之前与论题与观点发酵的过程之中“法律”或“政策”的权威性有被忽视的可能。互联网之中“兴趣”“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可能要比法律和政策的“制度内容”更具吸引力。情感共鸣、兴趣共通,以至于有悖于法律与一般性的社会伦理的兴趣爱好都可能让“群体”凝聚起来,而在成员之间反复而成的对观点的切磋之中,本着“去权威化”的法不责众的心态导致的错误言论和非理性情绪也就自然而生,论题本身也会趋于极端和激进,甚至成为“信念”。
这种“去权威化”并不意味着“论题”与“观念”在群体形成前选择就一定是任意率性的,但是如果在桑斯坦指出的“回音室”已经形成的情况下,群体内的成员希望发出不同的声音来质疑群体的意见反而会受到来自多方的攻讦,以及被打上“背叛”的烙印,遭受“群起而攻之”的激进化对待。“激进化”并不是再造一个“权威”出来,因为以“论题”和“观点”维系的社群之中没有什么权威存在。对于反复讨论和反复交流的论题和观点的盲目信任,对于共同爱好的一致盲从,让个体反而在群体之中消灭了。在固定且反复的“论题”出现前,在“观念”成为“信念”之前,个体之间或许还能保持“退场”的自由,但是一旦这个“群体”形成,那么个体再行退出就至少要面对两个困难,一是来自既有的“网友”的唾弃与愤怒,二是来自既有群体的“背叛”的评价。在极端化的论题与观念形成之后,个体要么已经被抹平棱角而变得无法控制自身的情感,并且把原本的论题和观念视为“教条”来对他人进行评价,或者虽然对“极端化”已经有所认知,但是由于畏惧公意而不得不把自己真正的观点隐藏起来。在实践中的“饭圈文化”就是这样的情况,本着对一个艺人的外貌、谈吐或艺术水平的喜爱,逐渐成为对这个艺人的拥趸,以至于在“信念”形成后,“饭圈”不仅对其他“饭圈”进行极端的指控,也可能对那些希望“理性追星”的成员进行攻讦,即使这些成员希望“出圈”也必须被已经形成的极端化群体做出消极的道德评价。
桑斯坦把这种情况称为“信息茧房”与“群体盲信”。前者指的是人有选择地信任自身喜欢的观点和论题而排斥其他的哪怕更加合理的论题与观念,甚至是更为权威的法律与政策,仿佛成了一个“蚕茧”,把自己和群体的成员包裹成一个密不透风的小圈子。①[美]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02页。后者则指在“回音室”和“信息茧房”之中,最终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的极端性”,既表现为一个“圈子”对其他“圈子”的敌视,更体现为“茧房之中”的人由于惧怕群体的激进言论与极端评价而不敢走出茧房。
(三)“交往理性”的悬搁与群体的多元化:去核心化与多群体中心性
“群体极化”必然由于它的“成员匿名性”和“论题观念极端化”导致出现不同的“极化群体”,处于“回音室”之中熏陶渐染的人就不自觉地“作茧自缚”而成为“茧房”之中的一员。他们依靠“匿名性”可以抹平社会身份差异的条件与可以淡化制度权威的网络空间,把相互排斥的“极化群体”置于网络之中,在这种“去核心化”之中把原本网络应有的“交往理性”也悬搁了。有论者指出,在互联网极化群体之中,“社会上的思想认知、价值概念也不再由极少数知识分子和道德精英来进行塑造,似乎人人都可以主宰自我,掌握命运。”②赵宬斐、赖乐涵:《网络空间公共话语表达范式转向》,《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0期,第106页。反映为“在学理外衣、文艺外衣包装下的错误言论在专业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大肆传播,一些不明真相的网民长期受其蛊惑,引起一定的思想混乱,尤其是消解了广大青年网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③肖唤元、郑晶晶:《新时代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内在逻辑及实践指向》,《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1期,第10页。所谓的“去核心化”就是在“极化群体”内部与“极化群体”之间,专业人士的涉及专业问题的“核心话语权”被偏执和极端的“极化群体”共同地无视或抵制,而如果专业人士对某个“极化群体”有所贴近而成为群体的成员,那么他也未必在这个群体之中享有既有的核心话语权,反而或是由于“回音室”之中的反复争论而越陷越深,或是由于走出“茧房”将受到“极化群体”内部的指责。同样常见的,不参与也不赞同“群体极化”并且对其非理性有所认知的专业人士,以个人的力量既不能把成员从“越陷越深”之中拯救出来,更不能把“极端”和“激进”的情绪化的“茧房”从外部打破。甚至对于“极化群体”本身来说,一个知名学者对其反复讨论趋于极端的论题和话题发出的声音根本传不到他们的耳中。反而是迎合这类群体的,打着“科学”的旗号或“科学普及”的旗号传递错误知识,打着“艺术活动”或“文艺作品”的旗号暗中迎合这类群体以获取流量资本的伪学者、伪艺术家更具市场。
在专业知识与文化缺失的情况下“去核心化”必然导致“多中心”的“网络极化群体”境况。这些群体之间成员不一致,共同的“论题”与“观念”也不尽相同,造成了每个“极化群体”都可能成立一种“自我中心”的心态,形成宏观的“多中心”样态。各个“自我中心”的“极化群体”的非理性体现为在判断方式上只有“正确/错误”,其依据并不来自法律、制度或专业知识,更不来自社会的一般伦理规范,而仅仅来自这些群体“常听常说”和“反复确信”的观念与兴趣。争论乃至攻讦源自对“自我中心”的认信和保护,源自通过在舆论场上争个胜负来扩大“自我中心”的领地,源自通过让这个“自我中心”的利益得以保存和延续的非理性的激情。
哈贝马斯一度将“交往”视为其理论的核心概念,亦指出在“极化群体”之间乃至其内部都不可能出现“交往”,“主导它们的是一些规范的直觉观念,这些直觉观念超越了间接要求的‘理性它者’身上所能容纳的范围……不管是把现代性描述为异化的生活关系,还是描述为可以用技术控制的生活关系,或是描述为权威化和同质化的生活关系。”①[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81页。而“交往”正是桑斯坦认可的破除“回音室”“茧房”与“盲信”的工具②桑斯坦的原话是:“身为公民,他们的责任是‘与人见面’和‘商量’,有时通过面对面的讨论,如果无法这么做,那也要考虑一下不同想法的人的观点。 这不是说多数人该将多数时间投入在政治上,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人们有一堆事可做。公民和民意代表依不同的情况和经验基础行事,并且都能从异质社会中获益,其实就符合了宪法设计的最高理想。”见[美]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黄维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去核心化”后的“多中心性”的极化群体,根本不能进行“理性商谈”,因为它无法达到“包容他者”的理性高度而仅仅有出于自我的“规范直觉”。
二、非理性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效应
“非理性”的“网络群体极化”的反映与成因,概言之就是由于在“身份理性”悬搁后成员的“匿名性”—“去具身化”导致的“恣意性”的群体组成和言论抒发,由于“制度理性”的悬搁而在“论题和信念”方面允许“极端性”的话题并且在话题讨论中“去权威化”导致的“激进性”的群体行动,还有在“交往理性”悬搁后群体之间拒斥“核心”性的专业人士而以“自我中心”组成的纷争状态。而上述的问题对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必是负面的,网络之中“去具身化”的匿名成员会让意识形态的宣传难以做到“人对人”的亲和性,对某种自我信念的坚持以及对这种坚持的兴趣会稀释意识形态在网络传播之中的深刻性,在“多中心”的群体之间的纠纷瓜葛以及“去核心”的态度也会导致意识形态的独一性损害。
(一)网络群体极化的“匿名性”削弱意识形态的亲和性
网络极化群体之中的“匿名性”对于意识形态的亲和力有所阻隔。在传统的线下意识形态宣传过程之中围绕基层党组织、街道和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熟人社会”进行“挨家挨户”“通知到人”的宣传方式在互联网空间之中显然不再合适。因为就目前而言,“网民”已经悬搁了社会之中的身份造成了意识形态传递对象的“混沌”与“不明确”状态,所以那种由上到下的,精准到人的意识形态精神传达模式无法在匿名的网络社群之中有所针对地传播,而只能采取“广播”(例如新媒体技术和自媒体平台)的形式进行一般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
这既意味着意识形态无法打破“回音室”而亲和于匿名的群体 ,也意味着在网络极化群体之中的“匿名性”在阻隔现实社会之中具有“亲和力”的人对人、点对点的意识形态传播模式。首先,由于各类新技术的涌现,人们利用这类技术去掩盖“身份”而消散为“匿名的网民”更为容易,以至于有论者认为“就其对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言,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正在加速网络空间的去意识形态化。”③杨嵘均、吴悠:《论网络虚拟公共领域去意识形态化的风险及其调适》,《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0页。新技术在助力意识形态内容传播的同时,也同样可以被视为匿名人对意识形态的阻隔方式,被视为匿名网民摆脱来自社会与职业方面的伦理要求的“技术支持”。其次,“匿名性”的网民也让意识形态宣传面对可能在网络之中有“多重匿名身份”的人,即使有意亲和,也找不到对象,表现为意识形态对那些游走于各个网络平台之中,游走于各类“极化群体”之间的“匿名的人”在宣传亲和上有所乏力。这是由于“以这些感性意识和感性活动表现出来反映不同主体客观需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具有无序性、瞬时性、非逻辑性和不可言说性,由此决定了它无法用理性的方式来衡量和把握。”④任春华:《网络空间中的感性意识形态:基本特征与传播机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3期,第49页。这就指明了意识形态无法通过那种稳定和理性的方式去对“匿名群体”的无序、多边和非逻辑性质进行点对点的引导。最后,人们通过网络空间而“匿名化”也有逃避现实的因素。意识形态本身的严肃性和严格性可能被视为不符合网络空间的轻松特质,不符合“极化群体”在论题选择方面的恣意,特别是那些不希望现实生活之中身份责任在网络空间被复制的群体一般不欢迎严肃的意识形态介入,因此在各种网络平台之中充斥着大量“更接地气”的内容。例如有论者指出:“为加强用户的感官实现注意力吸引,短视频类产品通过对用户进行视听感官的强烈刺激,通过模仿、段子等大量娱乐化信息,在短视频内聚集流量,实现商业价值。大量娱乐化、低俗化的内容充斥了网络内容空间,挤占了网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影响了网民的政治参与。”①谢新洲、杜燕:《政治与经济:网络内容治理的价值矛盾》,《新闻与写作》2020年第9期,第75页。这些打着“轻松”“娱乐”的旗号的网络内容,可能更符合部分匿名化的网民群体在“卸下身份”后的兴趣爱好。因此,就“匿名性”对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区隔来说,我们应当注意到匿名群体用新技术搭建的防御意识形态规制的壁垒,注意到复杂多样的匿名性群体的无序性、瞬时性造成的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把握的困难,也要注意到在“身份理性”被悬置和职业道德被“卸除”的情况下稍显严格的意识形态内容可能在互联网市场之中缺乏相对于其他内容的“竞争力”。无论上述的哪一种情况,都意味着“意识形态”面对着“匿名群体”的“进不去”或“高高在上”,都会导致意识形态的亲和力的阙如。
(二)网络群体极化的“极端性”冲淡意识形态的严肃性
在可能的论题选择方面,互联网空间的极端化特别是“极化群体”经由“回音室”效应形成的“信息茧房”会与“群体盲信”效应结合去稀释意识形态的深刻性。在“群体极化”的可能性之中,存在在最终的论题选取与观念认信上看似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极化群体”,也存在在论题选取和观念认信上看似中立而无涉政治的“极化群体”,还存在在论题选取上先天错误或是在最终观念认信上与意识形态要求背道而驰的“极化群体”。这三类群体都存在对于意识形态的稀释效应,因为它们的共性都在于“极端化”,意味着这些“极化群体”之中被反复讨论的论题是“越说越窄”的,在最终的信念形成上是“偏听偏信”的。
所以,“意识形态”被“网络极化群体”的稀释,不是说意识形态本身以及涉及意识形态话题的内容不会被讨论,也不是说这些讨论都完全符合或不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而是说“极化群体”的“极端化”会导致意识形态在群体之内被分割,而无法从整全的和系统的角度将之进行科学的认信。首先,即使在那些论题选择正确的“极化社群”之中,由于“信息茧房”和“群体盲信”效应的存在,可能出现对国家的过于“疼爱”与偏激的和片面的“热爱”而导致的幼稚化和简单化的感性认知。其次,在看似“无涉政治”的“极化群体”之中同样存在极端化倾向。其论题或许关于消费、娱乐、追星等兴趣爱好,有论者将之称为“泛娱乐化”现象,指出:“‘泛娱乐化’是相对于‘娱乐化’现象而言,指认价值观念产生变化的某种泛的概念,主要表现有娱乐明星崇拜、偶像崇拜、戏说历史、色情暴力等。”②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 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探索》2020年第5期,第182页。很显然在互联网领域购物消费,声援喜爱的人物,学习获取历史以及其他知识,乃至于借助互联网平台相亲恋爱等并非不合理,但是一旦这种“购物消费”转变成了“极端化的消费主义”,“声援支持”转变为“饭圈互撕”,“历史学习”变成了“戏说歪解”,“相亲恋爱”打着“色情暴力”的擦边球,也即这些群体走向了“极端化”乃至具有网络暴力倾向的时候,那些本来看似和意识形态无关的内容一旦充斥在网络之中“爆炸”,甚至在流量经济之下利用大众的从众猎奇心态被“定时引爆”,则必然会导致那些符合意识形态的网络内容的“网络生存空间”被挤压。例如经常有明星的花边新闻由于“粉丝打榜”而占据一些网络平台的“头条”,反而让涉及政治民生的重要内容被“挤压下去”。最后,如果由于匿名和恣意,且在根本的论题选择和在反复和重复之中形成了信念根本错误,那么弥散开的“极化群体”势必在对立的方面对意识形态有所损害。有论者指出:“网络空间中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终结论’甚嚣尘上,新自由主义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等接踵而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恶意攻击、诋毁和消解。”③秦程节:《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6页。这些错误的论题和极端的“社群”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之中的对手,而由于这些群体的偏激和执拗,意识形态在改变这些群体的思想方面势必分身乏术。因此就“极端化”对意识形态的稀释来看,存在三种不同的“稀释”表现,一是那些在论题和观点方面贴近与认信主流意识系统的“极化群体”出现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仅仅把他们感兴趣的意识形态内容作为论题进行讨论,这稀释了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二是看似中立,但极有可能由于“群体盲信”而极端化的“极化群体”由于关注的问题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在舆论发酵之后会抢夺意识形态在网络之中的主导地位而稀释意识形态的关注度;三是根本上立场错误和论题悖谬的“极化群体”由于责任主体匿名、群体数量繁多,让意识形态在处理这些错误的情况下分身乏术而只能转为防御的事后追责问责,进而稀释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之中的主导性和能动性。
(三)网络群体极化的“多元性”影响意识形态的独一性
“网络群体极化”带来的“去核心”且在“极化群体”内部与之间存在对交往的排斥,意识形态的独一性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主流文化的“独一性”难以确立。现实生活中也存在“极化群体”,但是出现纠纷时可以由专业人士进行调解与促进和解,要么由政府行政执法和行政调解部门等代表意识形态的行政机关让这些群体的成员和代表明晰孰对孰错以及如何补偿,要么启动司法程序以“原/被告”的身份让双方在法庭上进行论辩并以有意识形态背书的法律权威负责执行终局裁判。“调解”“执法”“庭审”等活动是通过某个核心的强力让争议双方走到一起,坐下来把问题说清楚,解决明白,但针对网络极化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群体之内的非理性行为,却没有一个“核心”具有这种强力,这种愈演愈烈的“多元化”使得意识形态及其表现出的主流文化成为“多”中“之一”。
“多元化”且拒绝交流的“网络极化群体”对意识形态的独一性至少在以下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首先,网络“极化群体”的对立与排外,让涉及意识形态的内容难以在保证严肃性、整全性特别是“非极化”的理性立场下统合互联网领域,意识形态工作者一旦走入这个空间就可能遭到类似的“非此即彼”的待遇。有论者认为:“近年来,互联网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存在感不断遭到稀释。主因在于,非主流意识形态恣意反弹,迅速占据网络空间,频繁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弈,竭力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①杨章文:《网络泛娱乐化: 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遮蔽”及其“解蔽“》,《探索》2020年第5期,第184页。一旦意识形态通过专业人士或专业媒体参与到与这些“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辩之中,则既不必然打破这些“极化群体”的茧房,也极有可能导致本来就已经壁垒林立的“极化群体”对专业人士的敌视,他们可能会无差别地以“非对即错”的自我中心主义把这些意识形态工作者同样视为“对手”。其次,多元化的“极化群体”在根本上反对独一的话语权存在,但是却不排斥把政治问题当作论题、把法律制度当作话题的情况,而在没有意识形态的“一锤定音”的解释权的情况下,长此以往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也会遭到负面影响。有论者指出:“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舆论场中失语或旁落,那么必然危及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②秦程节:《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流失与重构》,《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6页。多元的“极化群体”之间的相互攻讦的乱象,不仅不利于互联网环境本身的健康发展,更会导致关于政治话题、法律制度的伪科学、伪知识在非理性“极化群体”之中蔓延,并且让一些非理性的“极化群体”用以作为攻讦他者的工具,这对意识形态的形象是有极大损害的。最后,多元化的“极化群体”可能导致各种社会思潮的蔓延而侵害意识形态安全。有论者指出:“多数西方国家的民众从未到过中国,对中国国情缺乏客观公正的了解,而西方媒体便利用舆论将中国妖魔化……致使西方民众曲解中国,进而对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排斥和敌意。尽管原因不尽相同,但这些西方社会思潮的共同目的都是要消弭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理论体系,这不可不谓威胁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外部因素。”③朱文婷、陈锡喜:《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中的社会思潮辨析与引领》,《湖北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22页。外部的颠覆性思潮通过互联网极有可能传播到国内,并且通过迎合各种不同的非理性的“极化群体”而让这些群体在彼此攻讦之外,也对一些社会事件和政治决定有极端的错误判断。因此非理性的极化群体“侵蚀”意识形态的独一性的面向必须被重视起来,既表现为“极化群体”以“自我中心”的运作逻辑对意识形态工作者进行相似的敌视导致的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困难,也表现为对意识形态知识的歪曲解释被利用到相互攻讦之中而导致的意识形态形象受损与话语权旁落,更体现为极端化的极化群体在境外势力的煽动下对意识形态的多方攻击而带来的对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三、网络群体极化的意识形态治理路径
出于辩证的方法,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在互联网的“极化群体”之外的互联网空间之中仍然存在理性化的可能?是否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到在既有的“极化群体”之中可能存在理性化的倾向呢?是否应当出于联系的眼光看到“极化群体”可能成为与“理性”关联的“理性极化群体”呢?这些问题都指向了“群体极化”有可能通过“群体理性化”而实现转型,也即首先要恢复“群体之间”的交往理性,这个思想治理的任务要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来实现;其次再让“极化群体”之中的人敢于破圈、乐于探索圈外的世界,这就要求互联网平台加强自我治理与监督,纠正极端的思想,强化平台治理;最后要通过“制度理性”的介入,让观念错误或者以“匿名性”为挡箭牌的不法和违法的人无处遁形,健全网络法治,从“教育”“市场”“制度”三个方面推动“理性化”,让“群体极化”之中的理性化因素盖过非理性因素,巩固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环境之中的应有地位。
(一)交往理性的介入: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强化思想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要理直气壮开好思政课,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9页。发展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意味着在广义的“思政课”意义上,对思想本身进行治理,建构最起码的交往理性。有论者指出:“社会思潮的治理仅仅依靠党和政府是无法实现善治的,为此,我们要构建一元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思潮协同治理格局。”②秦在东、靳思远:《错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及其治理》,《思想教育研究》2019年第1期,第84页。面对“网络群体极化”的现象,需要把“思想政治教育”搬到网络之“中”,也要扎实网络之“外”,通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等意识形态的反映,奠定“交往理性”的合乎意识形态的良好基础。
第一,开展“在网络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一般性的政治知识普及、意识形态教育,让意识形态知识和政治素养作为“在网络之中”的存在而持留。有论者指出:“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第一位的是坚持正确方向导向,要始终绷紧导向这根弦,讲导向不含糊,抓导向不放松;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确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③李丽、戴湘竹:《完善坚持正确导向的舆论引导工作机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6期,第108~109页。一方面,“在网络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初步目的是在“群体极化”的壁垒之间建构其最起码的“合理性”共识,即要诉诸例如法律、政策等反映意识形态要求的规范性文本去解决问题,通过其把“意识形态”作为解决纠纷、制止争论的终局性和核心性地位树立起来。要让“极化群体”以及其中的个体意识到,当其他的“极化群体”造成了对自身的名誉、人格的损害,乃至有以“网络暴力”“人肉搜索”等侵犯隐私权的非理性且非法的情况时,法律与政策才是真正能够保证个体或群体利益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网络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目标,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反映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的精神与伦理去对“交往”的规准有所强调,要让非理性的“极化群体”意识到全社会的成员在交往之中以道德为准、以德性为据的基本现实,让这些群体在纠纷出现时意识到相互谩骂、诋毁的彼此攻讦只能受到来自全社会的“负面评价”。
第二,要巩固“在网络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意识到“网民”也是“公民”,“网络”也是和“现实”关联的构境,网络中的“非理性”与现实生活中的“非理性”是有联系的,现实生活中能够具有“交往的理性”并且开展“理性的交往”,有助于破除互联网之中的“壁垒森严”。一方面,“在网络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巩固现实生活中的教育成果。如果在现实中就形成依照意识形态的理性商谈习惯,形成对意识形态的尊重与遵守的基本理性态度,形成对各种极端思想和思潮的辨别能力,能够“针对多维的环境层次、丰富的环境要素、普遍的主体交往、变化的媒介形态等网络环境特性,正确处理虚拟性与现实性、技术性与人文性、知识性与价值性、开放性与封闭性、主导性与自主性、社会性与个人性、继承性与创新性等矛盾关系”①张瑜:《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观的演进与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5期,第193页。,那么这种风气就可能被引入到互联网环境之中。另一方面,在“网络之外”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站在“网络之外”,通过举例子、讲道理的方式指出“极化群体”带来的负面社会效应,指出非理性的攻讦和“壁垒森严”地否定一切核心的错误,让在网络之外的人对这些现象有正确的认识,让大众擅于运用意识形态知识、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对这些极化情况进行认识与批判,最终以内外的教育合力破除“极化群体”的“自我中心”式的森严壁垒,树立意识形态在互联网领域的终局决定的功能与交往基础的作用,使其“独一性”得以强化。
(二)制度理性的回返:完善网络平台监管机制,引入平台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握大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坚持导向为魂、移动为先、内容为王、创新为要……立足形势发展,坚定不移推动媒体深度融合。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不是取代关系,而是迭代关系;不是谁主谁次,而是此长彼长;不是谁强谁弱,而是优势互补。”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1版,第317页。在消解非理性的“网络极化”对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的过程中,互联网平台特别是新兴媒体平台要担负起治理责任。如果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之中”与“网络之外”都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中心性的“交往理性”基础,实现了遵纪守法、明理修德的思想共识,那么就要求通过互联网平台的治理特别是自我监管,在源头上对那些“极端化”的倾向“早发现、早区别、早引导、早治理”,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者和网络执法者请进来。
第一,网络平台要进行积极的自我监管,在自身领域内对极端化话题以及话题发酵进行合乎制度要求的“议题设计”,保证自身监管合乎制度理性的要求。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要避免“流量为王”而要以“内容”为王,要在“优质内容”的基础上“引流”。有论者指出:“流量的地位相对于内容,就只能是‘王后’了。‘王后’的影响取决于‘王’的势力,但是也可以辅佐‘王’,提醒‘王’,让‘王’更加成功。”③喻文益:《“流量为王”的“善”与“恶”——“质量为王”才是真正的“王道”》,《人民论坛》2019年第6期,第126页。互联网平台需要盈利,因此对市场的规律要进行把握,适度地“引流”是它们生存下去的需要,但是要把那些合乎意识形态的先进事迹、理论主张、优质内容作为“引流”的对象,而不是通过对“极化群体”的刻意迎合去毫无底线地“收割流量”。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要避免“娱乐至死”的陋俗。有论者指出:“网络舆情群体极化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一种积极向上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观点得到极化,这无疑是有益的,并且网络舆情在极化后能够反映到现实社会中,形成多数人受益的效果。但同时,网络舆情群体极化更具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当一种不健康的、非理性的或者被误导的观点得到极化后,则会带来很大的不利影响,从而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进步。”④史波:《网络舆情群体极化的动力机制与调控策略研究》,《情报杂志》2010年第7期,第51页。这就指出互联网平台在“引流”的过程中,完全有可能可以让那些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舆情群体极化”产生,在“议题设计”方面完全可以有来自平台的善意诱导。例如在抗击疫情时期的“最美逆行者”“硬核防控”等话题都和政治问题息息相关,这些话题既是“流量”的增长点,也是有助于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认同的价值增长点。相反,当网络平台坚持“娱乐至死”,置国家大事、群众生活、经济要闻、先进文化于不顾,而仅仅关注明星绯闻、段子八卦、伪科学与伪知识的时候,“极化群体”势必由于这种“议题设计”而走向背离于意识形态的非理性之中。因此互联网平台必须在“盈利”和“监管”之间做好平衡,在议题选择和观念摘选方面避免极端性。
第二,互联网平台必须允许那些代表着“制度理性”的成员进驻,在网络环境之中建立制度性权威。一方面,互联网平台要为网络监督特别是技术监督部门提供进入渠道,对来自网络监督部门的整改意见要及时反馈。有论者认为“新兴互联网技术背景下,舆论传播与意识形态深度关联,技术将意识形态的幽深之处提要出来,使其在舆论传播中得以映现……关注舆情舆论与意识形态的叠合之处,讨论主流思想与公众表达的交接地带,目标是通过挖掘技术张力凝聚社会动能。”①冉华:《势归于理,建基于实——重大舆情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价值遵循》,《理论月刊》2020年第11期,第112页。互联网平台既是舆论传播平台,也是“技术引流”主体,必须接受法律监督。“互联网非法外之地”不仅指互联网中匿名的个人要受到法律约束,更意味着互联网平台的技术操作和商业引流技术手段要受到代表了意识形态要求的法律监督部门和行政监管部门的调整,后者则要在保证互联网平台的正常盈利措施不被干扰的情况下,对那些非理性的极化议题进行根源上的消除。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也要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进入提供专门的渠道,深刻认识其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普及意识形态知识的政治任务,在完成账号注册、实名制认证等基本流程后,绝对不能对这些入驻平台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分配“引流”的商业任务,而且应当通过跨平台交际等方式,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极化群体的交往理性养成之外,鼓励不同平台的优秀内容创造者和“意见领袖”进行线上线下的交流。依照制度安排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跨领域、跨平台的更为深入的,能够促进网民“多听多看”的内容创作,在兼顾制度要求、商业运作和思想道德形塑的基础上形成破除“茧房”、破除盲信的治理效能。
(三)身份理性的塑造:健全立法追责激励机制,引导正确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作为基本任务,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核心价值追求,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为根本目标,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积极深化改革,加强和改进政法工作,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7页。互联网对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作用。“群体极化”的一个根本表现就是“身份”的约束缺失导致的匿名主体的恣意言论,而在“匿名性”的“保护伞”下网民群体极有可能出现网络生活和现实生活的行为反差,这也构成了“极化”的成员要素。因此对互联网领域进行立法,从源头整饬恣意的网络行为,破除“匿名性”屏障同样是对意识形态权威性和严肃性的保证。
第一,加强互联网立法,明确互联网中“匿名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要通过立法明示保护互联网主体的基本言论自由、隐私权和信息安全,明示参与到互联网生活之中的匿名个体的基本义务与言论边界。例如有论者认为,“在网络立法方面,除对网络中法律自然人以及法人进行明确界定外,还应对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违法进行明确规定,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责任划分和对利用网络侵犯隐私权如何追惩也应有明确体现。国家应制定更加符合网络行业特点的相关法律,让网络管理者有法可依,也让网民更加了解网络应有的话语尺度。”③相喜伟、王秋菊:《网络舆论传播中群体极化的成因与对策》,《新闻界》2009年第5期,第95页。这就是说,无论是互联网的“匿名参与者”、处于互联网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还是“互联网平台”乃至于在“互联网平台”之中代表国家进行监督的“监督执法者”,必须在法律明示的范围之内进行活动,用法律作为互联网活动的行为指南。既要让那些发布错误言论、宣泄不良情绪的匿名主体受到法律的规范,也要让互联网平台依照法律要求进行合法经营与商业博弈,还要让“网络执法”部门依照法律进行合规合法的治理活动。既不能堵塞有真实证据的揭露现实问题的报道与有理论依据的改善社会环境的建议的传播,也不能任由那些宣扬消费主义、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匿名主体”为所欲为。也即通过网络立法,把“社会现实身份”与“网络虚拟身份”纳入同一个“权利义务”框架中来。明确的立法规范有助于让意识形态成为互联网之中的枢轴,并且提升各方对意识形态的公正性的尊重与亲和。
第二,通过政策激励的方式,让一些“匿名”的个体走到“显现”之中,尤其是要发现符合意识形态要求的既有网络话语权威和培养新的网络话语权威,让他们能够在话题引领方面具有“引导者”的身份。正如有论者指出:“应着力培养一支具有公益精神和良好法律道德底线意识,并认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意见领袖群体,通过意见领袖搭建与网民沟通合作的桥梁,引导网民理性表达和正确发声,特别是借助‘意见领袖’群体来转移或稀释受众对焦点话题的关注度,最大限度地消除民众的负面情绪及其带来的舆论风暴,避免网络群体极化,促进网络舆情的良性发展。”①秦程节:《网络群体极化:风险、成因及其治理》,《电子政务》2017年第4期,第55页。由于网络空间的“匿名性”,个别的“话语权威”在带动匿名群体的情绪与倾向上具有一定的能力,这种“话语权威”身份的获得并不必然与社会身份相关,但是也能够吸引和粘连大量的受众,通过对这些“引导者”的政策激励可以更大地发挥他们舆情反馈、政策传递和舆论疏导的能力,以他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带动周边网友的意识形态归属感。一方面,“引导者”来自“网民”之中,他们对于网民最初的寻求公正和改变社会作风的心态有所掌握,正如有论者指出:“群体极化现象源于社会分化造成矛盾,群体极化本身表现了民众寻求社会公平、试图改正社会不良风气的美好愿景。但在讨论的过程中,由于道德价值的迷失、网络环境的复杂、群体心理的免责性、政府监管的弱力度等多方面原因,群体极化多数走向负面。”②袁慧、李锦珍:《网络群体极化表现及其特征》,《现代传播》2016年第9期,第142页。“引导者”一方面由于来自“网民”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受到政策的激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依照意识形态要求,在立法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保证极化的“身份理性”。有论者指出:“在全球化及网络化时代,各种社会思潮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在意识形态领域,更应该采取疏导开流的方式,不断采取措施,提高公众的知情权、参与度、思辨力。‘谣言止于智者’,只要公众的认知素质提高了,各种负面社会思潮的假面具也会无处遁形。”③王平:《当前社会思潮的主要形态、渗透逻辑及其应对策略》,《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6期,第89页。政策激励的“引导者”也应当是“智者”并且是能够分辨是非的对网民负责的代表,要发挥他们在区分“真正的舆情”与“刻意的渗透”方面的能力。产生于网民之中并且由政策激励的睿智的“意见引导者”既能保证忠于意识形态,也能保证对网民的负责,通过他的联动,意识形态和网民的距离将会拉近,网民会对意识形态产生亲近感。
结 语
交往理性的回返意味着通过对意识形态知识的基本思想政治教育,基于意识形态这一“核心”的交往和纠纷解决能够形成;制度理性的回返意味着围绕意识形态的治理和监管顺畅开展;身份理性的回返意味着互联网空间中匿名主体的权利义务也被明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由意识形态支持和政策激励的“意见领袖”。在这一意义上,“群体极化”之中的非理性成分也就会削弱。理性化的群体极化将围绕意识形态这一基本枢轴;舆情表达和反馈的机制将更加畅通;“极化”但理性的网民将在权利义务明确、知识教育充分、平台有序联动的情况之中,经由网民群体和“引导者”的配合来实现网民积极参与政治事务、政府积极反馈舆情解决状况、司法机关公正裁判纠纷、平台高质量产出兼具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作品的良好互联网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