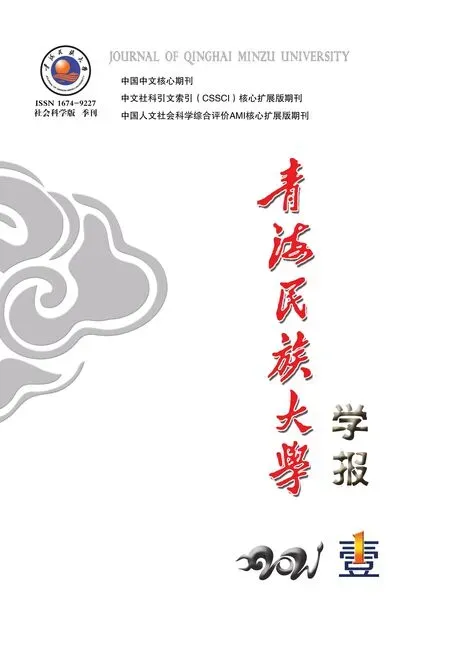口述史之难:品读祁进玉《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
——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胡鸿保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北京大学马戎老师认为, 对于20 世纪50 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族群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专题。 趁有些“民族识别”亲历者依然在世,抓紧开展带有“抢救性质”的口述史调查工作是他的心愿。[1]基于这样的认识框架,自2000 年以来,马老师指导他的几位学生陆续写出了几部这方面的论著。①其中,祁进玉博士的《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是分量最重的一部。 拜读之后,笔者拟谈谈学习体会,与专家切磋。
首先, 笔者注意到有关祁博士论著题目用字先后的一些细小变化: 从《20 世纪50 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2009 年,祁进玉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到《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20 世纪50 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2012 年,马戎在有关论文中介绍祁进玉此项研究时提及的题目), 再到《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15年,最终公开出版著作的书名)。 由数年之间题目的变化,结合阅读专著《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2015 年)来看,似能察觉祁进玉研究重心的调整,即,对口述历史的弱化。
笔者无缘一睹当年的出站报告, 但按直觉揣摩,祁进玉仅凭实地调查能够获取的访谈资料,想来写一部60 万字的与出站报告同名的专著,恐怕很难成功。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大部头著作,算得优秀,关键还是得益于他前后开拓,广征博引,充分利用历史古籍、中外近人论著、民俗调查所获以及考古发掘资料和体质人类学研究成果,等等,展开了视野更为开阔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其实,粗看一下, 祁进玉亲自访谈所得且被引用于此书中的口述材料,恐怕不足全书10%。 所以,尽管题目的改动使得“名”“实”之间更加相符,却也无奈偏离了导师的最初设计框架。
书中前后几处措辞, 透露了研究过程中思路调整的行迹。 比如“绪论”里写道,“本书的写作正是基于如上的考虑, 希望用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视角, 对20 世纪50 年代的民族识别的理论与实践重新加以考察……这才是本书研究的缘由和写作的目的”(第6 页)。第八章开头说,“本书的研究主旨是通过对20 世纪50 年代初的土族民族识别与社会历史调查来反观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本身, 审视土族民族识别的过程与相关理论支撑以及确定族源来源过程中……”(第449 页)。第八章最后一段, 也是全书的最后一段, 作者再次点出“本书所要研究的主旨”, 申述了与绪论里及本章开头类似的话语。 最后,话锋转移,表明作者之深意还在于“借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视角精心审视所谓的‘真实’的土族民族历史是如何被编纂与书写的, 这种族源研究与争论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宏大架构’‘话语’与‘权力’以及更经典的‘知识生产’体系”(第 497 页)。
祁进玉还采访了不少亲历20 世纪50 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老人,既有平民百姓,也有干部、专家学者、民族上层人士,包括董思源(第217-219页)、祁成寿、祁生海、叶爷(第 229-232 页)、夏吾才朗(第248-256 页)、吴屯下寺上师和寺院总管(第 269-271 页)、芈一之(第 326-327 页、487-493页)、 麻宝珠、 乔志良、 史成刚(第 334-346 页、434-435 页)、祁明荣(第 450-452 页)、祁占才(第453-455 页)、马元彪(第 473-475 页)、谢生才(第478-480 页),等等。 书中讨论各种问题时对口述材料多加援引。②
祁进玉意识到,口述史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其所传递的内容随着岁月的流逝也会逐渐发生变异(第219 页)。 历史学家们也一致认为,历史文献、档案、口述等证据的互勘是绝对有必要的。 在这方面,祁进玉充分运用了不同资料的互勘互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但是,祁著理应区分当年的识别情况(历史场景)还原以及土族被识别并确认为单一民族之后,族群认同意识的变化及带来的社会效应, 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追根溯源,导师马戎此项研究设计的初衷,其实含有一定的学术偏差。
笔者认为,若要紧扣“20 世纪50 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这样的题目进行研究,就应该选定一两则标志性历史事件并以此为界,如1954 年土族自治县(区)成立,和/或时间上比较相近的1959 年(是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刊印《土族简史简志合编》), 区别对待事件前后不同时代的材料并加以比较,由此展开讨论。
通观全书可知,第五章“从土人到土族:土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历程” 第二节中的第二部分,即“(二)‘互助土族自治县’ 设置始末”(第305-329页),运用口述与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写得比较成功的。 作者在此引用了不少互助县档案馆馆藏资料,有一些当时的会议发言记录,是可以视为口述史料的。如《互助县四届三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总结报告》 中记录了一些与会代表对于成立“土族自治区”的意见及反应,十分生动。
代表马友业(汉族)说:“我们民族之间的不团结,看不起少数民族,都是蒋马匪帮统治阶级给我们造成的。 ……”
有的干部说土民人数少,识字的人也少,没有汉民干部就干不成事,这也是错误的。
……
有土民说, 成立土民自治区后, 怕汉民不答应。 (这说明土民在反动阶级统治下受的压迫最大。 )有的土民说,成立自治区后怕不会办事。
……
代表发言(汉族):昨天听了张部长的报告,过去反动统治时期把少数民族压的喘不过气来,把土民没有当成少数民族,所以把(土民)文化也毁掉了。 ……
代表发言(土族):当了这个代表,成立土民自治区,自己十分高兴。 ……
(第 318-319 页)
比起21 世纪初的现场采访所获口述材料,档案里记录的口述,尽管有的仅是只言片语,但对了解20 世纪50 年代土族民族识别具有更高的史料价值。祁进玉指出,还原该原始文本并加以深入分析, 能够让我们很好地把握成立互助土族自治区之初, 各族各界群众复杂的思想状况及当时综合的社会情况, 有利于准确地认识20 世纪50 年代初民族识别工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同时,祁进玉还运用了自己对事件亲历者、老学者芈一之的访谈材料(第326-327 页、487-493页),前后印证。 1925 年出生的芈一之先生当年作为汉族干部参加了撒拉族的调查, 情况与土族有相似之处。 2012 年接受祁进玉访谈时芈先生说:1952 到1954 年是民族认定, 民族认定主要是座谈会的形式,还不是社会调查。③
以全书着墨最多的土族源流讨论为例, 认为祁进玉不恰当地使用了大量后起的、20 世纪50年代初民族识别历史场景中不存在的材料。比如,访谈《中国土族》主编解生才(第478-480 页)。 这样一来势必会导致“因果”混乱,或者至少是“只能体现”目前书名定位的主题,而它已经重心偏移、远远超出了最初题目《20 世纪50 年代土族“民族识别”的口述史研究》框定的研究时段。
美国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P.Geary)在《作为记忆的历史》一文中讲过一段话,对我们正确处理口述材料具有启发,值得引述如下:
记忆是一个当下的创造性行为。 ……记忆中的当下因素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也是它与历史的最大不同之处。……将过去与当下混为一谈,抹平彼时与此时的重要差异,是记忆的精髓,也是与历史的对立面。[2]
受访者的陈述,是需要口述研究者仔细辨析、谨慎运用的。 我们既应该警觉受访者讲述的早年生活必然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 也不能过于强调“当下性”、轻言“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④
在进行历史研究、 面对不同口述材料的选择使用时,笔者以为,首先要考虑的并非是获自一手(研究者亲自调查)还是二手(利用他人采集),而是这份口述访谈时间与被讲述事件发生时间两者的年代间隔。一般说来,距离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愈近,口述或回忆录参杂进事后的影响相对较小。所以,前人记录的口述史料,只要他操作规范,即使已经变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死文献”,也是弥足珍贵的,毕竟“时不再来”,自己的访谈实践只可能晚于前人。
对于20 世纪50 年代民族识别, 民族工作者们非常关注“族源”这个要素,经过事后总结,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中国人不墨守苏联成规的创新之举。 祁著用了极大篇幅讨论土族族源, 对于一项“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而言,自有其合理性。 但若聚焦“50 年代土族识别”,考量的重点则当有所不同。我觉得,可以从中选出三种材料来思考其间发生的变化。 一是1959 年《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第三次修订稿、 第四次修订稿) 主张“蒙古说”;二是《土族简史简志合编》(第五次修订稿、第六次修订稿)观点有所改变;三是1982 年公开出版的《土族简史》 主张“吐谷浑说”(第204-215 页)。
民族历史演变的规律总是分分合合, 交流交融, 因此, 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多元的一体”,不可能只有一个来源。 20 世纪50 年代初认定土族为单一民族时,“吐谷浑说”“蒙古说” 都早已存在。 问题的紧要处在于:主张族源“蒙古说”,但同时确认了土族是一个单一民族, 而不是蒙古族的支系。 费孝通等先生在不同场合介绍民族识别工作成就时, 大多会举出达斡尔族与穿青人作为例子,前者被识别为单一民族,而后者则属于汉族的一个支系、并非单一民族。 族源和历史,对于识别问题的解决,就是那么关键。 至于后来“吐谷浑说”转而占了上风,甚至有“定于一尊”之势(第346-347 页,以及第 220、491 等页),那也无法穿越时间隧道,回头影响到“50 年代土族识别”问题的讨论。 况且,各族《简史简志》的编写,乃是在认定或者识别确定若干单一民族之后, 方才启动的“工程”,即,为每一个少数民族编写一部“简史”,也就是所谓“分族写史”的做法。
进行20 世纪50 年代民族识别口述史研究,困难肯定不少。不过,研究者一般总是特别重视抓紧时间去进行“抢救式”访谈,而疏于关注史学研究的通则和处理资料的具体方法。 后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
注释:
①目前已见公开出版的有三部: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 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再版),祁进玉《历史记忆与认同重构——土族民族识别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学苑出版社,2015年,以下引用此书仅随文夹注页码,不另起脚注),卢露《从桂省到壮乡: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②顺便指出, 作者展示的口述记录有明显不够规范的地方。如多数访谈并没有注明准确日期、地点,受访者年龄;如此一来,读者便无法推知当事人在1950 年代初经历土族识别时的年纪。此外,同一个人名(祁成寿)却有两个不同的年龄,这种情况可能是不同年份两次访谈所致(第229 页、231 页)。还有的访谈没有用答问者,而是误写成翻译者的称谓(第269 页)。 可惜互联网上只能够查到名人的生卒年份, 权将查得的几位受访者记录于此,以备参考。 芈一之(1925-2020), 祁明荣(1927-2017), 马元彪(1934-2014)。
③祁进玉在书中分两处记下了访问芈先生的时间和地点:访谈时间,2012 年6 月(第496 页);访谈地点,青海民族大学家属院(第326 页)。 读者据此无法肯定他是否只进行过一次访谈。
④此语是菅志翔在借助口述材料讨论保安族历史时说的。“以下两位受访者的话反映了一种现实的心理逻辑: ……任何历史都是现代史。 在分析保安族的历史表达的时候,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对应了民族历史的同构。 ”菅志翔:《族群归属的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关于保安族的一项专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330 页。 笔者认为,作者的有些推断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 容日后另文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