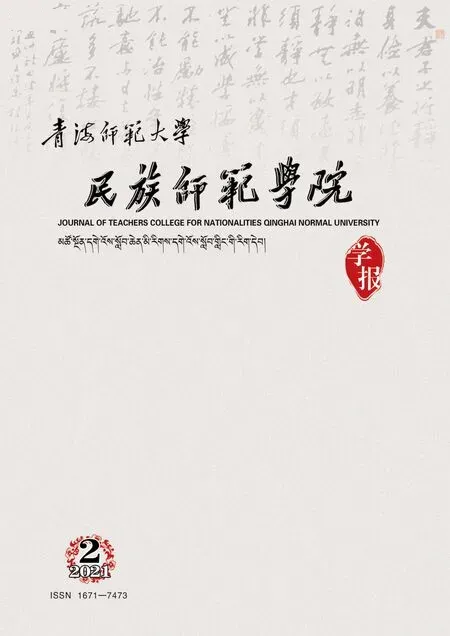论体验意境的三种方式
孔祥睿
(青海师范大学文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0)
在我们的文化源头就已经出现审美体验的说法。例如在《易经》中有“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说法,老子提出“心斋”“坐忘”“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王弼提出“得意忘象”等,这一系列观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表现出一种体验的思维方式。究其根本,都是以“道”作为基础,而“道”最本质的特点是在形式上的混沌造成我们难以分辨,因此我们也就无法清楚地认知“道”,所以我们不能妄想靠事物的外在形象去分辨而是需要用心去体验,其实这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体验性很强。意境也是如此,体验意境的三种方式:从“观”到“味”到“悟”的整个过程不是简单的转变而是表现为从感官到内心的深入。先由感官“观象”传送到内在感受的“味”,从“味”再传送到内在思维的“悟”,最终由意象构成的意境就在“悟”中被体悟。
一、观——观象体验
在《说文·见部》中曰:“观,谛视也。”[1]实指有目的的、仔细察地看。可见“观”是带有主观性的、带有选择性的看,而且所看的对象一定是有价值的、值得看的东西。最早在《易传》中有提到有关“观”的说法:观象于天,观法于地。在其中已经非常明显地突出了主体的“观”与客体的“象”之间的关系,随之是概括性的“观物取象”概念的提出。由此可见,观是人们在感知外在世界的第一感官要素,在连接外在客体与内在主体之间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观”不仅仅是对于外在“象”的一种认识过程,同时也是新事物创造的过程。因此观与象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形式上的认识,还应该是对于象本身的内在本质的理解。这也就要求主体对于世间万物要有全方位的把握。而正是因为需要全方位的把握,观不再是环顾四周的简单看,而是要将自己深入“象”中用心去体悟和感受并再进行下一步的抽象和提炼。这一过程其实是完成了从自然物到象再到“取象”,以“观象”为基础的意境的体验也是如此,将自然物转化为“象”,再将自然物象凝练进一步转变成“象”达到体验意境中“观”的最终目的。
“观”是一种有目的性、有选择性的认识过程。更是在这样的认识过程中外在“象”与内在的心灵产生了默契的碰撞,进而产生了心灵的体验。就像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2]由此可见,在意境创造的过程当中“观”的体验方式是在感知了外在事物的同时与自己心灵发生的一种对接,可以说“意境”的营造更是“观”的另一种高级的表现形式。整个过程不外乎是由“观”去摄取作家想要表达的物象,通过心灵的加工提炼将自然物象转化成意象,许许多多的意象再组合成意象群,最终通过“味”和“悟”将意象转化成意境。意境是意与象的结合,意境的产生离不开意象,意象的产生离不开“观物取象”。换种方式讲,作家在营造意境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融入进“象”之中转化为“意象”,最终由“意象”构成产生“意境”。由此可见在一系列的转换中“意境”产生的基础是“观”,是体验意境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审美体验层次。“观”作为体验意境最初的感官感受,也是艺术意境体验的基础。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一个问题:不是每一次的“观”都会收集到自己想要的信息,只有在“观”时,某一个信息点触发了创作者的灵感并将信息保存在下一次创作中得以使用,“观”才真正地发挥作用。然而不同的创作者因为他们的“观”的角度和方式不同,由于他们文化程度和艺术修养程度的不同,又因为他们“观”的不是具有同一性的事物,因此这个时候创造的意境就带有一定的差异性。那么这时高雅而不落俗套的意境就会出现在具有高层次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深厚的创作者的作品之中。
二、味——心象体验
如果说“观”只是处于体验意境过程中最初级的阶段,那么“味”就是在“观”接收到外在的“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所接收到的“象”通过思考、揣摩、体会等过程,外在信息转化为内在的主观感受和体验,我们用郑板桥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来比喻从“观”到“味”这个过程再合适不过了,这不仅仅是在取象之后人们对于对象的一种理解和把握,更是一种在深度认识之后,对对象融进了自己主观的感知和领悟。
在《说文·口部》中曰:“味,滋味也。”[3]先秦时期,老子提出“五味”之说,刚开始的“五味”就是指五种味道,后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逐渐“味”开始泛指一切味道。从老子在十二章提出“五音、五色、五味”到“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味”不再单单是感官上的物质满足而是转向精神上的探寻,“味无味”中味带有了动词体味的含义,这也是“味”在含义上的质的突破。到魏晋时期,“味”逐渐从哲学范畴转变为审美范畴,比如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许多和“味”相关的词:“余味”“道味”等等,还有钟嵘提出的“滋味说”,这显然带有以味论艺的传统特点。这时的“味”呈现出三种主要内涵:首先是人的嗅觉、味觉、触觉所感受到的酸甜苦辣等感官感受;其次是在感官体验下经过人的感受而体会到的“味”;最后是人对于世间万物的整体把握,不仅仅是感官上的还延伸到人的内在心理深层次的体验。
这时我们不难发现“味”所具有的两方面的含义了:首先是“味”作为名词时指本身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味道;其次是“味”作为动词时,含义上升到具有体味、领悟内涵的心理体验活动。正因如此,“味”也就成为了体验意境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钟嵘的《诗品》中曰:“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弘斯三义,酌而用之,幹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4]这其中的“味”就已经明显上升到心灵精神的深层次体验上。从“味”概念的发展来看,“味”相对于“观”来说特殊之处在于“味”具有内感性,与人的内在心灵、感悟、情感相联系,这也是“味”能够成为体验意境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的原因。
体验意境同样需要从感官感受到精神探寻这样的过程。关于“味”和体验意境的关系,我们将“味”作为动词放在体验意境中进行探讨。最早将“味”纳入到艺术理论中的是宗炳,比如在他的《画山水序》中提到“澄怀味象”即指审美主体要有纯洁无瑕的心胸和淡泊宁静的心境来体味审美对象,而这里的“象”指的是审美对象内部显示出来的深厚意蕴和精神。是一种在摆脱了利欲熏心之后去体味、感受审美对象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畅快与愉悦。宗炳所提到的“味”不仅解释了在体验意境过程中体验主体与体验客体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于“味”作为体验意境的重要方式的心理内涵作了详细的解释。自宗炳之后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将“味”作为意境的体验方式中重要的一环,明代的陆时雍在《诗境总论》中说道:“少陵七言律,蕴藉最深。有余地,有余情。情中有景,景外含情。一咏三讽,味之不尽。”[5]其中“味之不尽”的“味”就是在对于“象”的体验转化为意象之后,同时带有对于意象无限回味的意味。
在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味”这个概念刚开始是和艺术创造和体验没有任何关系的,然而经过上面的梳理,会发现“味”从最开始的感官动词到后来的动词性的审美特质,以及“味”所带有的独特的内感性都决定了“味”一直会存在于“观”和“悟”之间,在体验意境的过程当中起到的是桥梁的作用,“味”在意境体验的过程中是“悟”的先导,没有“味”的积淀不会有后面“悟”的升华作用的产生,“悟”才是在意境体验过程中的最终理想价值。
三、悟——神境体验
体验意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到达超然的精神境界,表达主体的主观感受,所以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就需要体验的主体从“观象”深化到“味象”,意象构成意境形成最终一个过程“悟”达到精神的升华。可见“悟”是意境体验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存在的,也是中国人最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最清楚提出“悟”的应当是严羽,他在《沧浪诗话》中提到的“妙悟”这个命题,具体是指“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这里的“妙悟”是指对审美过程的一种领悟,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的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只是需要对于自然物的外在形象的捕捉进行“观”,随后将其放入心灵世界进行“味”,最终在冥冥之中心领神会,进入精神的最高境界去领悟。
其实,体验意境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作为审美体验的过程中的一种方式。在意象基础上生成的意境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物质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人生感悟。所以,这个时候“悟”意境显然成为了一种主观体验,在意境体验的过程中是无法被取代的。钱锺书认为,“悟”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方式,只有博采众通、工夫不断,才能真正达到“悟”的境界: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6]这段话显然是在说明“悟”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一定会进入到意境体验的“悟”的最高境界。经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关于意境的体验方式是一种循序渐进式的,是从感性关照,到感性体味,最终精神体悟以至韵味无穷的过程。
意境是在意象的基础之上所建构起来的一种精神创造活动,那么在“观象”“味象”的基础上最终产生了“悟境”,由此,可以说体验意境的过程包含着三种方式:观、味、悟。三种主观体验方式构成了意境从“象”到“境”的转变过程,同时也完成了从“观”到“味”再到“悟”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完整体现了中国独有的意境理论以及特有的体验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