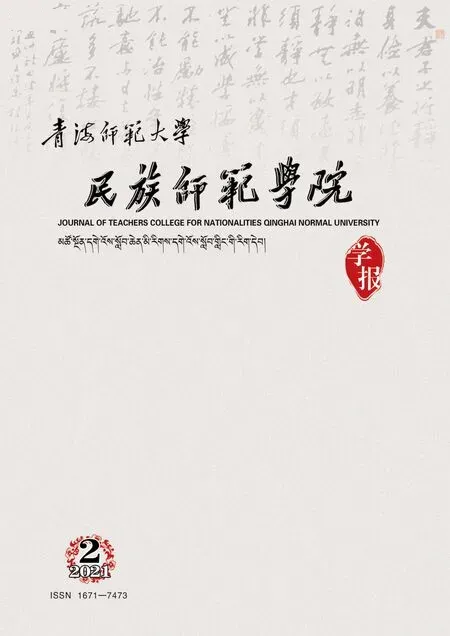浅析《左传》所见“亡人”语义
董雨康
(青海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青海西宁 810008)
《左传》所载“亡人”多指出奔逃亡的贵族,“亡人”一词共出现12次,所记“亡人”出奔之事较多。有学者认为,在独立国家意识尚未形成且各国为了招徕人才或政治投机而对“亡人”来者不拒的情况下,出逃的“亡人”往往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对于春秋时期的贵族阶级来说是无毁于荣誉的,不过是生活方式的变更。[1]事实上,从“亡人”一词表现出的语义看,前贤论见稍有偏颇之处,《左传》所见“亡人”一词含有贬损或自嘲之义,是当时历史语境下的特殊产物,值得进一步研探。
一、“亡人”的语义
《左传》多使用“奔”“出居”“亡”等词汇来表述人的出奔逃亡。“亡”一词在《左传》里有多种含义,可指国家、家族的衰败覆亡,也可表达具体的某人或某几个人逃亡。宋元公和华多僚的对话就有:“司马以吾故,亡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2]第一处“亡其良子”和第三处“再亡之”,应释为使之逃亡,第二处的“死亡”则分别指死亡和逃亡两种状态。也就是说,“亡”字可以表达“使之逃亡”和“逃亡的状态”两种含义,而“亡人”可释为逃亡的人。在宋元公看来,让华貙“亡”对不起和他有生死之交的华费,而华多僚则认为,“亡”不过是比“死”轻一些的惩罚方式。这足以说明,“亡”一字在使用时,多是带有贬损意味的。有学者称,出奔逃亡是一种有准备有选择有退路的政治出行[3],但从宋元公对于华貙“亡”的犹豫态度之中,可以看出这种逃亡并非从容之举。当“亡”字以“亡人”一词的方式连用,“亡人”一词也带有了贬损之意。
“亡人”一词可分别用于自称或他称两种情况。首先,“亡人”一词作为自称时含有贬义。《左传》中卫灵公就曾数次以“亡人”自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4]其意为自己是无能的“亡人”,丢失了自己的国家,落魄于草莽之中。在这里,卫灵公以“亡人”自称,实际上是一种自嘲,承认自己的无能和无奈,感叹自己的落魄。同时,又有“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意思是说,“亡人”的忧患,不能落到客人的身上,杂草丛中的人,不足以劳驾随从。卫灵公以“亡人”一词自称时,总是将之和“草莽”一词相提并论。对贵为国公者而言,“草莽”指涉其失势的落魄状态,含有自贬之义,自称“亡人”者当然也有同样的语义。
与卫灵公一样,出奔逃亡之中的鲁昭公也自称为“亡人”。荀跞以晋定公的名义安慰逃亡中的鲁昭公:“寡君使跞以君命讨于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鲁昭公云:“君惠顾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将使归粪除宗祧以事君,则不能见夫人。己所能见夫人者,有如河!”[5]鲁昭公在自称“亡人”时,是面对晋定公使臣的一种谦称,在这一句中,鲁昭公自称“亡人”以示卑下,然后想办法提出自己的一个不情之请,其实也说明,“亡人”一词表达出的仍是自谦、自贬之义。显然,“亡人”作为自称时表现出一种窘迫难堪的状态,其使用时的语境自然是谦卑或者自卑的。
其次,“亡人”一词用作他称时同样也有贬义。“亡人”一词在《左传》中用于臣子控告或者诬陷别的臣子,声称其他臣子招纳“亡人”,以此激怒君王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除前文中提到的华多僚向宋元公诬陷华貙时用“亡人”一词外,宋平公时期,寺人柳也用了同样的方法来陷害敌人华合比,声称“合比将纳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6]。宋国寺人柳受到宋平公的宠信,太子佐讨厌他,华合比“欲杀之”,寺人柳知道此事后,就伪造盟书,诬陷华合比,宋平公因此驱逐了后者。从这里可以看出,接纳逃亡的“亡人”在君主眼里是一种等同于反叛的罪行,惩罚方法无外乎驱逐或处死,说明臣下不可接触或招纳“亡人”,因为此乃一种触怒君主的行为,是一种僭越和叛逆。
晋怀公对“亡人”亦并非宽容,虽其父晋惠公曾经是“之人”。《左传》载:“九月,晋惠公卒。怀公立,命无从亡人,期,期而不至,无赦。”[7]晋怀公下令不得跟从“亡人”,按时归国者可得到赦免,不按时归国的则不会赦免。一方面,“赦”一词所针对的对象必须是有罪的罪人;另一方面,针对国君而言,“亡人”是有罪的,所以对有罪之人才需要用赦免来展现国君的宽容态度,而不服从赦免的“亡人”是可以且应该被惩罚的。晋怀公此举看上去不够宽大,但在当时已是一种善举。不过,从当时的语境看,国君对于“亡人”的态度总体上是不友好的。
综上所述,从《左传》所见“亡人”的自称和他称看,“亡人”一词都带有贬义,或是自贱自谦之称,或是对逃亡之人的贬称,“亡人”一词反映出的社会行为并非无毁于荣誉,相反带有明显的贬损之意。
二、“亡人”语义形成的原因
“亡人”语义的形成,首先与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尽管春秋时期出现礼乐崩坏现象,不仅流亡者众多,且有诸多如晋公子重耳携大量从亡者的出奔者,社会影响力很大[8]。但是,礼乐宗法制度对人们的行为仍有较强的约束力,尤其是从与“亡人”对立的政治集团或个人角度看,“亡人”脱离了宗法制度的约束,游离于政治体制之外,本身就是有罪的。《左传·昭公三年》:“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9]《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书曰‘出奔’,罪高止也。”[10]从这两处记载看,在春秋时人的观念里,出奔逃亡本身就是一种有罪的表现,作为出奔逃亡之人的代称,“亡人”一词本身就指有罪之人。
楚灵王即位后,“为章华之宫,纳亡人以实之”,无宇的守门人逃到章华宫里,无宇要抓他,管理宫室的官员不肯,抓住无宇而进见楚灵王,无宇申辩说:“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仆区之法,曰:‘盗所隐器,与盗同罪’,所以封汝也。若从有司,是无所执逃臣也。逃而舍之,是无陪台也。王事无乃阙乎?”[11]楚灵王无奈,只好赦免无宇。楚国有“仆区之法”,专门惩罚背主逃亡之人,按楚国法律,藏匿“亡人”也是犯罪[12]。可见“亡人”不仅仅指逃亡他国的贵族,背叛主子出逃的平民甚至奴隶也可称为“亡人”,而称其为“亡人”是因为逃亡本身就是犯法。
另一方面,“亡人”往往对统治阶级造成威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华多僚诬陷华貙的事件中,其结局是:“张丐不胜其怒,遂与子皮、臼任、郑翩杀多僚,劫司马以叛,而召亡人。”[13]张丐因为得知华多僚陷害华貙之后非常愤怒,于是便伙同华貙一起将华多僚杀死,劫持司马发动叛乱,并且召集逃亡者加入了他们的叛乱。可见,对于统治者而言,“亡人”是可能加入叛乱的潜在敌人。此外,回归本国的“亡人”本身就可能是叛乱的主谋。齐国的庆封曾经“使诸亡人得贼者,以告而反之,故反卢蒲癸”[14]。因告发贼人有功,卢蒲癸返回了齐国。庆封允许“亡人”归国无疑是一种有宽恕意味的态度,是对“亡人”的赦免。然而,卢蒲癸却与王何“卜攻庆氏”。卢蒲癸返回齐国后一年之内发动对庆封的进攻,成功击败庆氏,使其流亡国外。这足以说明有些“亡人”归国后,有可能会组织叛乱、威胁国家安定。
显然,大多数“亡人”并非良善之辈,招纳“亡人”自然就会遭到抨击。在这种背景之下,不仅臣下招纳“亡人”的行为会被国君视作叛乱而加以严惩,哪怕是国君本人行包庇、纳“亡人”之事,也会被劝谏或者批评,甚至引发国君和臣子之间的冲突,无宇就批评楚灵王:“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君王始求诸侯而则纣,无乃不可乎?”[15]无宇将楚灵王的行为与商纣王相提并论,认为楚灵王招纳“亡人”的行为是商纣暴行再现,所用言辞极为激烈。贵族“亡人”出逃多为政治竞争失败之举,平民乃至奴隶“亡人”出逃,多数是想摆脱主子控制,或谋得更好差事。他们的行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破坏了既有秩序,使原本稳固有序的人际关系遭到破坏,因此才会招致反感、谴责。
总之,《左传》所见“亡人”一词多有贬视、轻贱之义,用“亡人”一词表达的鄙夷和以“亡人”的自轻自贱,是春秋时期人们使用“亡人”一词的常态语境。“亡人”之所以常有贬损之意,其主要原因在于三点:其一,从伦理道德上来说,“亡人”属于出奔逃亡者,出奔者对于宗法制度的维护者和支持者来说,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有“罪”。其二,从统治现实来说,“亡人”是一种不稳定因素,随时可能威胁到他们的权力和人身安全。其三,在其他方面,接纳“亡人”,会破坏人际的关系,形成与逃亡者原主人之间,乃至君臣之间的冲突。因之,接纳“亡人”是一种被道德所不容的昏聩之举,臣子招纳亡人等同谋反,会受到君主的严厉惩戒,有些国家还专门制定法律,禁止招纳“亡人”,贵为君主,一旦包庇“亡人”也会受到臣子的强烈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