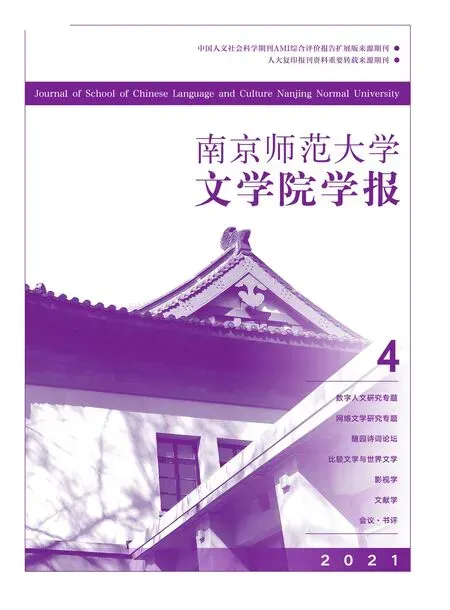约翰·班维尔小说中的“视-触觉”与真实
张荆芳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继科学与艺术三部曲之后,爱尔兰当代小说家班维尔(John Banville,1946—)在本世纪初又创作了《日食》(Eclipse,2000)与《裹尸布》(Shroud,2002)这两部内容上形成相互嵌合的“双生小说”,而从其表现的死亡与哀悼主题来看,又与其布克奖之作《海》(TheSea,2005)构成了又一个三部曲。[1](P62)它们仍着眼于班维尔一贯以来的对自我真实的探索,以及对重现过去记忆的理解。通过将自己置于虚构与真实的边界地带,班维尔“证明了当代小说中存在着一种远离摹仿现实主义的运动”。[2](P29)此外,对于摒弃小说现实性(realistic)而崇尚小说艺术性(artistic)范式的班维尔来说,绘画艺术充当的是一种“脚手架”功能,因此班维尔小说还常被国外学者称作“如画”(Ekphrasis)文学。[3](P137)一直以来奉行卡夫卡的“艺术家无话可说”座右铭的班维尔,与那些反映政治喧嚣的作家不同,他更喜欢静下来营构一种沉默的绘画美学,并“使用艺术的最新隐喻来讽刺和取悦旁观者”。[4](P79)由此路径解读班维尔的研究现已甚多,约翰·肯尼(John Kenny)即认为,班维尔的小说“这种对直接可见的图像和隐喻的强调是班维尔现象学现实主义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如画’中存在着对现实主义的强烈的决心”。[5](P56)又如朗西埃所言:“对于奥尔巴赫来说,小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成为两个过程的结合体:一个是把任何事件纳入到社会过程的整体中,一个是把任何一个卑微的个体,变成了小说中的‘严肃’主体,一个能够表现出最强烈而复杂的感情的人物。”[6](P6-7)而在虚构的现代性冒险中,这些“残缺的雕像、跳蚤式的孩子或嬉戏的小丑创造了一种新的美。”[6](P11-12)这正是班维尔此三部曲中那些主体形象的共同特征:人物身份的流动性、自我本身的虚假性。其实,小说的“如画性”除了表现在大量绘画作品的嵌入,或以诗性语言来厚描如画场景外,绘画本身与主体的看视问题也尤为重要,班维尔小说中的关键画作俨然成了主体的“精神生命”,或者一面返照自我的面容之镜。现在问题在于,单是视觉层面上的看与被看是否足以解释主体的多维?或者还存在着其他感官的联合作用?由此小说的“真实性”基于何处?质言之,小说是如何从单一的视觉幻象转换为一种视-触觉式(Haptic)的感性现实,以及由此呈现出的主体存在姿态。
一、 面具、裹尸布、肖像与视觉幻象
人物身份的真实与虚假、自我之原本与副件的并立等问题被糅合进班维尔许多小说里,营造出一种因其欺骗性的外观而呈现的不透明世界。如赫达·弗里伯格(Hedda Friberg)所说,班维尔被喻为“明喻和隐喻大师,他是狡猾的记忆模糊水域的探索者,是人类状况不确定性的不懈探索者”。[7](P1)其中贝克特式的独白者占班维尔小说的绝大多数,如《裹尸布》中的自我哀怜、自我忏悔者同时是自我欺骗者形象范德、《日食》中自我放逐于幽魂之屋的演员阿历克斯·克利夫,《海》中追忆逝去岁月与爱人的垂垂老者马克斯·莫登,他们都将自己絮絮叨叨的述说裹挟进了这些逝者幽灵的重重环绕之中,将他们从其尘封的记忆废墟中,搬演至读者眼前。
“面孔”及其衍生之物面具、裹尸布、肖像画等作为一种重要的视觉元素,在为小说建构多重化主体的意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国著名艺术史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认为,人们对“脸”这一观念的理解有“肉身化”(Inkarnation)(即由表情制造的表情面具)与“去肉身化”(Exkarnation)之分,“脸”的德语词为“Gesicht”,脸(Ge-sicht)即为被观看者看见的那种东西,而古希腊词源中的“pros-opon”,既表示脸也表示面具。[8](P23)脸的这种双重性特征也与主体的降格问题有关,面具化的主体常常表现虚假和可替换的特征。在不同侧面目光的凝视作用下,“肉身化”的脸常常被面具、裹尸布一类“去肉身化”的物质性产物所替代,因而主体每一次揭开面具的动作,都是一种远离本真自我的过程。班维尔所塑造的范德跛脚、半盲,穿行于古老欧洲城市的大街小巷,凝视着目之所及的一张张陌生面庞。此时他并非通过直接的语言与他者交流,更多的是凭借对他者与自我“面孔/面具”的描画来呈现主体的多重样态,从而建构了一个永远无法达至真实之自我的虚假主体。从小说变幻多端的用词表达中可以看出,“脸”的诸多变体大致有四个层次:一是对最普遍陌生人脸的特写式描绘,具体表现为小说中大量出现的“我的脸”(my face),“她的脸” (her face),“他的脸”(his face)等脸部细节静态描述,尤其是借范德之眼随机扫视的路人脸;二是由脸产生的丰富多样的动态的面部表情(look)细绘,范德仿佛将自己所穿行的意大利城市街道当作真正的戏剧舞台,以特写镜头的方式凝视他人面孔的细微末节变化;三是一种由脸延伸出来的“物质化”形象,即“面具”(mask)、“裹尸布”(shroud)、肖像画(portrait)甚至是“物体表面”(surface)等一系列面孔生成的副本;最后是其否定意义的变体——“无脸化”(faceless)或“无脸”(no face)的一种抽象的自我存在状态。
《裹尸布》中的这位在大浩劫中冒用朋友名字而幸存的知识分子“范德”,在接到一位意大利的陌生女子的威胁信后,随即乘车来与她会面。在此之前,范德用肉体征服了这位名叫卡斯·克利夫的女子,但在随后的相处中发现自己逐渐爱上了她,于是向她娓娓诉说了自己虚假身份的由来。小说以“裹尸布”为名,实际上蕴含了两种维度的意义,“裹尸布”(shroud)作名词时意为耶稣裹尸布,其实就相当于远古初民所使用的“死亡面具”(death mask),这是人在临死之前被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张面容,小说多次将裹尸布与范德的脸做比较,意为范德面具般多重的脸最终将会像裹尸布一样消蚀成一种被人们遗忘的“无脸”(faceless)样态;而作动词时“shroud”又有“掩盖”“隐藏”之意,小说的整个行文结构恰恰是借范德这样一个自我建构并同时自我解构的人物,一面表述其是如何掩盖其真实身份,即通过多重面孔的形构来经营其新身份的;一面又通过叙事进程的展开讲述其是如何被逐步揭示出来的过程。
作为一位具有极强反刍意识与极度自恋的老学者,这位身份的变身者和复制者、欧洲大浩劫时的犹太人与外邦人,在盗用他人名字的同时也逐渐失去了其本真自我,陷入了自我认知的迷雾之中。于是他们便以面具、裹尸布或肖像画等一系列替代物来建构自我的副本。无论一生中拥有了多少副人脸面具,他最终发现,其实脸与面具早已合二而一,面具在这里成了虚假的拟像式存在,整个小说世界都变为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的虚幻世界。具体来说,范德这一虚假主体的建立主要来源于大理石面、镜子、耶稣肖像画或眼睛瞳孔等反射所产生的视觉幻象。从正面视角来看,在蒙着水汽的浴室落地镜里,老范德看到自己的映像“赫然耸立:面无血色,凝神盯视”。[9](P27)同样,阿历克斯·克利夫也喜欢时常揽镜自照,将自己看作是潜伏在某处的陌生人,与范德一样是无法触及真实自我的空心人。同时,范德还在凝视大理石反光产生的模糊映像时,立刻将其叠印在之前看过的安德烈亚·曼特尼亚的殉难基督肖像画《死去的基督》(1)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安德烈亚·曼特尼亚(Andrea Mantegna,1431-1506)的油画名作《死去的基督》(The Dead Christ),约作于1480年,又称《哀悼基督》(Lamentation of Christ),现藏于米兰布雷拉美术馆,在这幅图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耶稣双脚上的伤口,有人认为这幅画头部和脚部的比例不协调,但其实这是用一只眼睛观察的视线所致,这也许也是班维尔将同样以单眼观看的范德与耶稣的这幅画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上,这一阴冷如青铜雕塑的色调与此时从浴缸出来的范德形象相比:“(范德)先是双脚,再是小腿、膝盖,悬荡着的生殖器,肚子,宽阔的胸膛,最上面是一团乱糟糟的头发和一张正在俯视的平庸的脸。”[9](P28)
正如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艺术史学者克劳斯·克吕格(Klaus Krüger)所说,“这幅图上的基督看起来很近,但又很远,是可触摸的,却又是不可理解的,这确实是一个适应图像要求的呈现结果。只有在视觉决定的图像真实中,基督的外表才能成为旁观者眼中的具体真实”。[10](P247)耶稣头部与脚部比例看起来的不协调,实际上是作画者采取单眼视角所致。正如范德表现其自我哀怜的情形类似,从置入画中的哀悼的旁观者来看,他们似乎溢出画框的哀伤使得观者在观看过程中意识到自己的感知对象,这与同样作为作为观者的范德亦如是。代表“人子”的耶稣作为那“不可见的可见者”上帝的显现,是其在人间的替代,而这里的肖像画就像作为其始源的耶稣“裹尸布”一样,代表的是对上帝的第二重替代。如南希所说,“每一幅肖像画都是向着独一性画出上帝——他的退隐和他的诱惑,那不可能的肖像。”[11](P57)同时,肖像画与裹尸布在这里都成了范德面具的指代。这种相似性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唤起某种值得敬佩的生者记忆,它并非充当纪念碑的作用,而是为了“向着主体自身来唤起主体,为了实现它向自身的无限返回。”(同上)裹尸布既是一种重要的“死亡面具”,又是一种唤起废墟记忆的盲者“自画像”。
最后,这种主体印象的形成还来自于“他者肉眼”的反射。对自我面孔的凝视是为了对建立自身的神圣性,树立一种受难形象,从而合理化对他者的暴力。虚伪的范德在凝视他人面孔时极尽扭曲和漠视:当穿行于意大利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他看见路边一位衰老丑陋的卖花女郎,不禁有了自己肉身已然衰弛的危机。他想象着通过瞎眼的卖花女郎瞳孔反射出自己的面容模样,“一个奇形怪状的撒拉弗,如此庞大,这般赤裸,何等苍老。”[9](P27)而参加聚会时,他仿佛看不到眼前已然垂危形容枯槁的前情人克里斯蒂娜·科瓦奇,却只是又在顾影自怜,这个从欧洲那场浩劫里幸存下来的有血有肉的人,“宛如弗兰肯斯坦的怪物蹒跚着走出熊熊燃烧的磨坊”。[9](P44)范德这一形象其实与班维尔在之前艺术三部曲中所塑造的典型“反英雄”形象一脉相承,他们都是有道德瑕疵的自欺者与自恋者。而范德的自我之真实性悖论就在于,他渴望生活于当下的时刻,将自己从那段特殊的历史及民族遗产中摆脱出来,但从他挪用他人之名的那一刻开始,他便成了一个无名的怪物形象,一个自始自终虚假的自我。“这就是班维尔的怪物,一种恶魔化了的主体,即便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虚幻本质,他仍努力实现他为自己设定的重要的愿望。”[12](P549)于是他将自己与赝品作比,通过此种自嘲的方式自我忏悔,因为这赝品本就映照了他的虚假本质。
从面孔到面具、肖像画与裹尸布,主体之脸经历了一种“去肉身化”的过程,但比“去肉身化”更深层的自我异化是“去脸化”,就如耶稣的脸在人们的记忆中被“消蚀”(eclipsed)一样,这也更像是在隐喻世界上那些被遗忘的饱受离散命运之苦的民族(如犹太人、阿卡迪人等)。对于范德来说,他的犹太民族血统决定了他命定的流亡,而其模棱两可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自我的流亡,这种主动的流亡便是对民族历史与自我的双重弃绝。在他被劈开(cleaved)的内心深处,他一面作为那一民族的受害者自居,但一面又鄙视自己的那部分血统。当他讲述那些阿卡迪人时,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们是一种没有任何地域与心灵皈依的“空气人”,与他现在所定居的美国类似,同样“是一片虚无。在我的脑海里,美国无论在哪儿都见不到人影,唯有巨大、荒凉、寂静的高楼,熠熠生辉的机器和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荒芜地带。就连这个国家的名字也像是个临时捏造的词,或是一个无解的字谜游戏:这个单词的元音太多了。”[9](P208)当作为“旧世界”之副本的新大陆人故地重游于那旧世界的中心意大利都灵时,新世界的虚假本质就如同那永远回不到脸上的面具一样,已经昭然若揭。
如班维尔研究者马克·奥康奈尔(Mark O’Connell)所言,“《裹尸布》中最核心的哲学问题便是关于自我存在与否的问题,这个问题定义了范德的整个学术生涯。”[13](P109)自我之真实问题被种种视觉幻象所掩盖,小说在揭开这些面具的同时,也使人窥探出了那主体中心的虚无之境。“班维尔被掩盖(shrouded)的虚构领地——其文本世界的中心可能是虚无(nothingness)——这呈现了一个尼采的世界,在其中真实与现实的观念受到质疑,人性‘游离于无限的虚无之中’。”[7](P1)班维尔用精雕细琢的语言魔术为读者设下层层厚重的面纱,在阅读过程的荆棘密林中,面纱被逐渐卸下,而正如范德的小丑式表演面具一样,一层面纱之下仍然是面纱,始终不可见的是面纱背后实乃空无的本真自我。那么,如何才能触及面具背后的本真自我?怎样才能抵达那被主体所忽视的他者的隐藏之域?班维尔在其艺术巅峰之作《海》中,以对逝者更浓烈的情感态度,试图再造一个皮格马利翁式的可见与可触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者不再是被漠视的存在,不再具有范德或克利夫之类的虚假性与多重性,而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凝结了视-触觉等多维感官性的浮雕般的主体形象。
二、从肖像到浮雕:眼睛“触摸”真实
班维尔最富盛名的《海》于2005年打败朱利安·巴恩斯与石黑一雄夺得曼布克奖,虽然他的作品被普遍认为有乔伊斯、贝克特和纳博科夫的影子,但却很少有人谈论将他们综合起更接近的普鲁斯特。在他们高度诗意化的文字里,那些死去的恋人如阿尔贝蒂娜们、克罗伊们成了古希腊神庙中的雕塑女神,雕塑作为一种通过触摸的方式重现某一生命真实瞬间的艺术形式,使人们更能从中体验到自我生命的真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触觉可以增加视觉现实的真实感,让眼睛变成“盲人的手杖”,既发挥眼睛的功能又具有手触摸的效果,比如同时具有视觉性与触觉性的浮雕。就像在那副《死去的基督》画中所呈现那样,其身体真实性的证明就在于耶稣双足上那“炫示性”的伤疤,无论观者处于哪个角度,这个代表哀悼的痕迹都逃不出视线之外,或者这就是通向两种世界之共鸣的缺口,它促使观者将自己自动代入其中,由此凝视者与被凝视对象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眼睛沿着这些衣褶边缘,冷峻的线条,仿佛能直接用手指触摸它们。
如果依赖所呈现的单一视觉功能来看,小说主要表现为多种视觉幻象建构一种虚假的主体,同时,在与他者的关系中,界限分明地呈现出看与被看的主次关系,而如果将其作品视为一种综合的感官维度的“视-触”空间,那么主体便如同隐没于人群中的芸芸众生,形象与背景之间的界限在一种模糊的错觉中,浅浮雕便显现了出来。对于从视觉到触觉的延伸,德里达认为:“当视觉不再倾向于区分自己与所见或可见的事物,就好像眼睛接触到了事物本身——或者说……就好像眼睛让自己被它所接触摸。”[14](P123)这种看与被看、触与被触的肉身性主体的折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小说中的镜子,它的魔力在于“把事物变成场景,把场景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15](P43)而“触摸自己,看到自己,就是获得这种镜面的自我的提取。”[14](P214)同时,触摸还消弭了视觉与触觉、背景与图形,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就触摸对于主体的建构意义方面来说,对他者的触摸仍是一种“自我触摸”,因为他者成了自我的肉身之镜与心灵之镜。
《裹尸布》中的范德对他人的触感是冷漠的,他生命中具有深刻肉体记忆的女人们,在他眼里仿佛成了莫迪里阿尼画中有目无珠的少女,内心拒绝他人触及。他已经去世的妻子玛格达被形容为“俨然一块花岗岩,一抹单调的灰色”[9](P42)之类的肉体质感,他们结合的很大原因是相似的生存境遇使其几乎成了精神上的“双生子”,玛格达逃离死亡集中营是因为她的名字被错误地从名单中删除,与范德偶然盗用名字如出一辙。与《日食》中的亚历山大类似,玛格达是范德内在自我的翻版,在与范德相处的人生里,同样经常以假面示人,保持一副不可窥探的内心,如同艾可和那喀索斯一样成为彼此的心灵镜像。而范德生命中另一重要女人卡斯·克利夫因患有曼德尔鲍姆综合症,经常处于精神分裂状态,沉浸于自己封闭的个人世界,使她在其他人看来像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在这种情况下,卡斯成了范德世界中反射自我的肉身之镜。范德打量着自己永远无法探触内心的卡斯,他并非是享受年轻身体的欢愉,而是为了从这种肉身关系中证实自我的真实。而这位神秘女人在溺水身亡后,无论对于范德还是父亲而言,她都以一种幽魂似的幻影姿态现身于两位叙述者的回忆之中,成了他们永远触不可及的追忆对象。无论是肉身之镜还是心灵之镜,她们在小说中的呈现都得益于范德肉眼的触感式再塑作用,作为回声女神(玛格达)和复仇女神(卡斯),一个在范德的叙述中已经身死一个即将死去,就如梅洛-庞蒂所说那样,所有的视觉中都有一种根本的自恋主义:“因为看者被摄入了被他看之物中,所以他看到的仍是他自己”。[16](P172)她们都是通往自我本真的镜像。
而卡斯的主观视角同样体现了这种自反性。在她短暂的人生中,范德与父亲都具有自己的多重人生和多重自我,一方面,卡斯对范德的了解主要通过三种方式:一是从其所著的哲学著作中了解到了范德之名及其重要思想,其次是与范德之间保持的肉体关系,最后正是通过一张印错名字的简报照片发现范德的身世之谜。当携带范德秘密的卡斯·克利夫只身前来意大利时,她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这位具有复杂面向的人,等到他们真正碰面时,她开始将之前照片里的面庞连同在书架上看到的他的名字融合起来,这一次“她想通过手触摸来辨别”。[9](P87)另一方面,这种想象性的触摸其实来自对父亲的触感记忆,她喜欢注视着父亲说话时的嘴部动作以及父亲的胡茬,喜欢摸它们时留下的针刺感。这一切想象感觉的来源始终作为小说的不可知力量与不可能性而存在,在父亲回忆的尾声,卡斯的幽魂形象光明正大地闯了进来,被“复活”成为一个具有真实感的浮雕之躯:
她看起来多么真实,一个化身前来迎接我,而另一个她,桦树女神,留在外面,给她的箭包上鞘,解开她镀金的弓。 卡斯! 那闪闪发光的眉毛,那黄褐色的头发的光环,那带着苹果斑点的精致鼻子,那双属于我的灰绿色的眼睛,那长长的、苍白的颈柱。 我感到一阵剧痛,伸出一只颤抖的手去触摸她,我说出了她的名字,她似乎停顿了一下,颤抖着,仿佛真的听到了我的声音。[17](P211)
而到了《海》中,他者与主体之间不可通达的界限通过克罗伊关键性的一吻被打破,一种“与幽灵共舞”的方式将这两重断裂的世界重新焊接了起来。以马克斯与童年女友克罗伊的亲吻为标志,他们相互走向对方世界的界桩之内。这段描写极易使人联想到普鲁斯特笔下马赛尔与阿尔贝蒂娜的经典一吻,与深不可测的阿尔贝蒂娜相比,克罗伊在某些方面的神秘性有过之而无不及。已逝的故人们像《裹尸布》《日食》中的幽灵一般重现于眼前,而这一吻将哀悼情绪推到了高潮。马克斯亲吻之后感觉自身发生了变化:“我是我,同时又非我,我成了别的什么人,一个彻底的新人。我们朝着海滨咖啡馆的方向走着,在人群中我跟在她的身后,用指尖轻轻碰了碰自己的嘴唇,那副刚刚吻过她的唇,希望能发现它有什么细微但重大的变化。”[18](P99)相比起马赛尔亲吻阿尔贝蒂娜时:“当我的嘴唇凑近她的脸颊时,刹那间,我看见了十个阿尔贝蒂娜,仿佛要把一个女人在同我们多次约会中向我们呈现的丰富多彩的姿态和色彩以神奇的速度在几秒钟以内全部展现出来……”[19](P353)这惊奇的一吻像是打开废墟的阀门,将灰尘中的幽灵以倍速的生动方式呈现了出来。此时,主体不再倨傲于肖像画的绝对中心,而是将潜隐的陪衬或绘画中的背景搬到了前景同一高度,“背景”与“图形”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形成了一种浅浮雕的效果,在可能与不可能的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对于小说书写死亡而言,其实是去触及那不可能性的存在,去触摸不可触及之处,如南希所说,“触摸就是触摸到一个极限,是一个表面、一个边界、一个轮廓。”[14](P103)在那个“视-触”的空间领域内,生者与死者、主体与他者交织在一起,甚至还可以将一种单纯生理性触摸延伸至书写与阅读领域,共同纽结于“死亡”这一不可能性的命题之中。
与单纯视觉所带来的真实所不同的地方在于,此时由文字的“视-触”空间所呈现的是一种基于身体性的“感官现实”。视觉理性的经验告诉我们,班维尔小说中的主体形象像小丑哈利奎恩一样,始终无法掩饰内里实际中虚无的事实。但除此之外还有另一种方式帮助我们理解班维尔世界所呈现的真实,它以一些不起眼的细节残存于文字之中:那便是大海的某一次寻常的涌动、受难耶稣画像身上的伤疤与皮肤褶皱、父亲下巴上呈针刺感的胡茬、还有因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卡斯经常会闻到的并不存在的气味……它是视觉的、触觉的、味觉的或者声音的交织,却不总是视觉的。当主体目光所及之处无不被蒙上了视觉幻象的阴影时,视界成了一个充满了复制品的赛珞铬世界,从名字到面孔都体现一种虚假性。但其真实的生命就存在于与那些无法触及的幽灵相触所产生的自我的新变化,如班维尔在《雅典娜》中所说那样,主体需要这些感觉来确认自我的真实性存在,在对逝者的感官性重塑中:“我却依然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如此鲜活生动过,如此富有生命力,对事物的感知如此敏锐,我的整个身心都全然暴露于世界火热沸腾的粒子涌动中,就像剥离了皮肤上那层精巧的保护膜。雨水静静地穿过我的躯体,宛如接受一片微子的洗礼。”[20](P7)在对这些逝去生命及虚假自我的反思中,主体强化了对于生命本真的认识。朗西埃继承奥尔巴赫的余脉,成为所谓的感性现实建构的开拓者:“没有感觉表象的真理。只有在它没有使任何东西出现的地方,只有在它只是一种噪音、一种冲击、一种与任何约定意义无关的味道、一种只指向另一种感觉的地方,才有可感性的真理。”[6](P6-7)然而,这种真实却是以文字的幻象建构出来,它永远不能达至真实,只能最大程度地靠近真实。从班维尔小说的现实主义立场来看: “对于一个宣称自己属于‘准现实主义学派’(quasi-realist school)的作家来说,悖论是表现真理的唯一方式,真理被定义为‘引导人们穿越哲学的困惑,尽管经过了三千年的艰难思考,人类仍然深陷其中’,可以说,班维尔的作品深深地扎根于这个泥潭之中,正如我们在他错综复杂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就像莲花一样,他的风格从这个泥潭中长出来,将它的花朵举到某个明亮的世界。”[21](P129)
这种真实来源于文字的独有创造力量,尽管这些都像是文字所创造的产物,但正如庞大固埃再造的“口中世界”一样,这是一个充溢着肉身体验的,具有生命原初本真力量的感性世界,这个世界犹如与现实世界平行的“乌托邦”——一个与现实“概念”世界平行的肉身式世界。
三、“视-触”式感性真实
班维尔在创作上极力推崇小说艺术性的同时,又不断探索小说虚构的边界与新的可能,但“求真”始终是其一贯的诉求,他所希冀的小说艺术是一种处于新的综合体的门槛上:“是一种足够诚实到绝望然后继续的艺术; 严谨和控制,冷静而热情,没有错觉,意识到自己的可能性和自己的局限性; 一种知道真相是任意的,现实是多样的,语言不是一个清晰的镜头的艺术。”[22](P17)小说语言不再仅具有现代主义的建构性或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性,而是成了与他所探索的模糊水域相似的混沌所在。或许是由于爱尔兰作家对英语书写的一贯的疏离,他使用了并非爱尔兰特色文化的绘画艺术,来表现其世界性与国际化的愿想。
具有“如画”文学特征的班维尔小说无疑深受视觉媒介的重要影响。在W.J.T.米切尔那里,如画(ekphrastic)是指“对视觉再现的语言再现”(the verbal representation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这个希腊词英译为“speak out”,在此意味着用画来表达诗,强调两种艺术之间的相通。[23](P151)在班维尔以“画框”(Frames有画框与框架之意)为名的“框架三部曲”《幽灵》《证词》《雅典娜》中,绘画主题成了小说的重要架构:在内容上绘画成了映照主人公人性复多面向的镜子;而形式上,小说的书写抹掉了画框的边界,使读者在凝视小说所嵌套的绘画作品的过程中,感受一种虚与实交织的幻境。而在以死亡主题连接起来的《裹尸布》《日食》与《海》又一三部曲中,虚实与真幻问题同样蕴含其中。然而,与寻常的“如画”小说刻意营构一种单一视觉再现所不同的是,班维尔通过对绘画艺术更深刻的运用,在融合生与死之界域中创造出了一种可见与不可见、可触与不可触相互交织的双重世界。
《日食》(Eclipse)与《裹尸布》(Shroud)作为表现“戏如人生”、建构分裂主体的双生小说,从书名来看也相得益彰:第一部小说中的‘日食’(eclipse)被遮盖(shrouded),第二部小说中的‘裹尸布’(shroud)被消蚀(eclipsed)。[21](P122)无论是内容上(标题的名词义)还是形式上(标题的动词义),他们都成了相互耦合相互阐释对方的副本,名字近似的“双生子”阿历克斯·克利夫(Alex Cleave)和阿克塞尔·范德(Axel Vander)在人物特征上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无论是演员阿历克斯还是老学者范德,都因享有多重人生而具有了多面向的人格特征,以致最终都认识到自我的空虚本质。他们姓氏与名字的意义在对方身上同样适用:“vander”在荷兰语中类似于英语中“of the”,表示有归属但没有起源之意;而亚历克斯·克利夫之姓氏“cleave”有分裂、劈开之意,在演绎无数人生的过程中,克利夫找不到自我的归属。[21](P116)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阿历克斯的女儿或阿克塞尔的情人卡斯·克利夫(Cass Cleave),“Alex”的孩子是卡斯,而她怀了“Axel”的孩子后溺水身亡。两部小说在形式上也似衔尾蛇结构——卡斯将自己生前手稿交予父亲,阿历克斯的书写(即《日食》)便以卡斯身亡、动手编辑阿克塞尔的生活而告终,而艾克塞尔·范德一开始也是伴随着脑海中卡斯幽灵声音的推动下开始叙述《裹尸布》。做了多年演员的阿历克斯“无法找到那个独特的本质的自我,那个我来到这里要寻找的自我,它一定藏在某个地方,藏在一堆废弃的面具之下。”[17](P50)而《裹尸布》中的范德正是一位以面具、裹尸布、肖像等脸的延伸之物所形成的寓多重身份与虚假自我于一体的复杂形象。就如同小说标题上的画外音一样:“日食”世界作为日照世界的例外形式,表现的是一种暂时被遮蔽的不可见的视觉假象,而“裹尸布”作为神圣耶稣面容的副本,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消蚀为面具性的假面。这些虚假形象毕生所不竭追求的便是一种本真性的自我,他们都如班维尔许多小说主人公所追寻的孪生兄弟一样,被拦截在两个世界之间无法通约,一边是由主体的视觉虚幻外壳建立的可见世界,而另一边是主体所悼亡的始终无法触摸的不可见的他者世界。
其实,无论是通过视觉还是触觉呈现一种现实,其真实性的程度主要在于读者层面的感知能力,说到底,究竟是视觉还是触觉能复现更真的现实,其实源自不同时代的观者对于“看”这一词思维范式的转变,尤其对于以视觉文字符号为基本元素的文学作品来说,人们几乎很少关注到阅读中存在的其他感知维度问题。班维尔小说最善于使用与主体建构密切相关的绘画元素,而其所呈现的模棱两可的看视问题又不能单从视觉层面来理解。传统意义上的视觉并非单指一种生物性感官能力,而是在习以为常的思维中被赋予了双重性功能(兰波描述为“超视觉”),即“存在‘心灵的看’和‘眼睛的看’”,[15](P55)但长久以来文学阅读都停留在“心灵的看”而鲜少涉及纯粹肉眼的观看。对此,以梅洛-庞蒂肉身现象学中的“可逆性”思想或可为这种非此即彼的单一看视问题找到新的理解思路:一方面,他主张文学作品的“看”应参照塞尚式绘画艺术的“看”,将“看”这一件事变为一种姿势(可触摸)。另一方面,与心眼之“看”所不同的是,肉身之眼使得“我的身体同时是观看者和被看者”[15](P34),看视问题也就变为了一种结合视与触的、主体与客体的双重问题。德勒兹关于讨论培根绘画的例子便是这种“视-触”(haptic)问题的直接展示,在德勒兹那里,这位生于爱尔兰的肖像画画家培根(Francis Bacon)在反对古典再现范式中的触觉与视觉的对立性中,“发展出了一种触觉色彩主义,将形象、底色和轮廓的所有力都作为色彩的力。”[24](P177),更多是一种回归古埃及艺术的“触觉般的视觉”(haptic),这是一种结合了光的视觉(optical)和手的触觉(tactile)的一种感受。[25](P155)他所呈现的变形的人物面孔具有很明显的浮雕感,既包含视觉的平面性,又具有手的触感,为观者提供了具有看与触双重作用的第三只眼/手。
在表现悼亡主题的《海》(TheSea)中,班维尔同样以一种“视-触觉”式双重再现来追忆逝去的方式,打破了这两重世界的界限。叙述者马克斯·莫登,一个缺乏天赋和野心的艺术史家,在妻子因癌症病故后,回到载满沉重苦痛记忆的童年海滨小镇,在这里他不仅要面对失去妻子的忧伤,更要面对的是童年爱人克罗伊的突然溺亡,悲伤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真实与虚构等双重世界的界限。沉浸在伤痛的记忆洪流之时,语言多次表现出了再现感伤时的无力,小说描述了童年与老年马克斯对所见所触之事物的虚幻感受,此时感官性现实取代了视觉理性的幻象,营造出了最真实的人性所发出的强大冲击力。于是,从这三部小来看,班维尔的书写呈现了一种由虚假向着真实性探索逐渐迈进的路径:如果说《裹尸布》以一系列视觉幻象的方式再现了主体的虚假与空无这一维度,那么从《日食》开始,叙述者便在尝试着与过去和解,在与幽灵共舞的过程中以求获得罪愆的消解;而罪感最轻的《海》中的主人公马克斯,饱含着一种皮格马利翁式的忧伤,重塑了逝去爱人的倩影,竭力去触及那无法触及的生命真实。
四、结语
班维尔式“如画”文学在其“死亡三部曲”中更多是以一种视觉的虚构力量,来建构一系列虚假的肖像式主体;而与一般如画文学所不同的是,小说还以触觉这种更具伦理性、向他者敞开的感官融合作用,在对幽灵他者的认识上,重塑了一种更具本真性的“浮雕式”主体,由此为文本建构了一个感官性的现实世界。就像梅洛-庞蒂所说的,画家通过把自己的肉身“提供”给世界,才把世界变成了绘画。文学的感性书写遵循同样的道理,通过文字和话语的方式为世界赋予肉身形式。朗西埃在在奥尔巴赫所梳理出的“感性书写”暗流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可感性真理”(sensible truth),而在梅洛-庞蒂看来,“可感世界是由于内在的意义和结构才比思想的世界“更老”,因为可感世界是可见的和可延续的,而思想的世界是不可见的和断裂的,初看起来不能构成一个整体,其真理必须依靠它者的标准结构。[16](P22-23)班维尔小说所追寻的,正是这最为基础的“可见的”,这种对于所有人来说可以通约的、可以在情感和肉体体验中显现的世界,比概念世界所建构的现实更为真实,因为那些概念之所以被我们所理解,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直接通过我们的外表、姿态与他者世界相互接触与交流。与概念世界的固着化、层级化相对的,是生命体验世界中的流动性、开放性,这些作为概念的生成基质便以一种潜藏的方式存在于一种感性的真实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