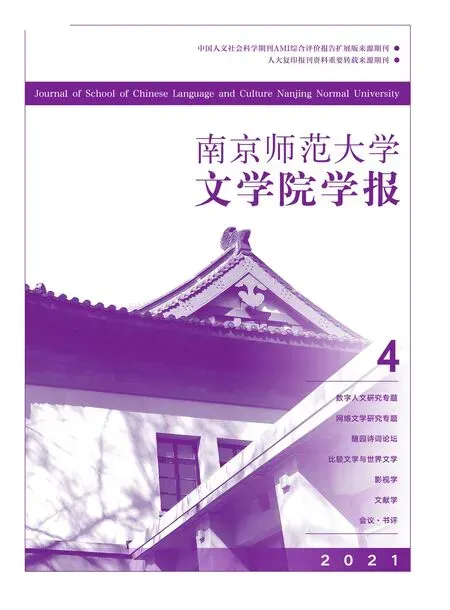世界文学里的资本语境与侨易空间
—— 以文学世界表现的家族史为中心
叶 隽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一、世界文学及其作为资本语境的“诗性载体”
世界文学不仅可以作为一种理想,而且同时可被视为一种事实,即由各类文学文本所构成的一种超越性的“文学类型”。我们最耳熟能详的自然是歌德那句话:“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德文原文为:“Nationalliteratur will jetzt nicht viel sagen, die Epoche der Weltliteratur ist an der Zeit, und jeder muβjetzt dazu wirken, diese Epoche zu beschleunigen.”Mittwoch, den 31. Januar 1827. in 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歌德谈话录——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年头).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198. 中译文见[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第113页,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这个判断因其过于著名而广为流传,但如果细加推敲的话,我们会意识到,这个概念并不自歌德而始。其实维兰德(Wieland, Christoph Martin, 1733-1813)此前就已经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他认为:“罗马在其最美好的时代颇有首善之都的风格,这种风格可以用文雅 ( Urbanität) 一词来概括,文雅指的是博学多才、世界知识和世界文学以及成熟的性格培养和良好品行的高雅趣味(diese feine Tinktur von Weltkenntnis u. Weltliteratur so wie von reifer Charakterbildung u.Wohlbetragen) ,这种高雅趣味是通过阅读最优秀的作家的杰作和与这个有教养的时代最文明和最杰出的人物的交往而不知不觉地形成的。”但这并不妨碍是歌德,而非维兰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成为最重要的界定者,因为前者为世人所熟知与发生影响,后者则是后来才被挖掘出来的尘封史实[1]。
在现时代更因为全球化的一体态势,“世界文学”引起学者们的特别关注。譬如美国学者丹穆若什(Damrosch, David)就撰专书讨论《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发覆更为详尽,一方面他认为歌德提出的“这个词语融汇了一种文学视角和一种崭新的文化意识,令人初识正在兴起中的全球现代性”[2],另一方面则要提出自己的理念:
在恰当的理解下,世界文学根本不会命里注定似地沦为不同民族传统在相互冲突中变成的大杂烩;另一方面,它也不一定非得让简妮·阿布-鲁戈浩(Janet Abu-Lughod)称为“全球杂音”(global babble)的白色噪音(white noise)给吞没了。我认为,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无边无际、让人无从把握的经典系列,而是一种流通和阅读的模式,这个模式既适用于单独的作品,也适用于物质实体,可同样服务于经典名著和新发现作品的阅读。本书旨在探寻这种流通模式,也旨在厘清阅读世界文学作品的最佳方式。而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是,正如从来没有单单一套被公认的世界文学经典,也没有单单一种阅读方式可以适用于所有文本,或不同时代中的同一个文本。变异性是世界文学作品的基本构成特征之一——当作品被完美地呈现和阅读时,这是它最强大的力量;而一旦被误用或挪用,这也就成了它的致命伤。
他的论点也就相对清晰,即:(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椭圆式折射;(2)世界文学是通过翻译而广泛流通的所有作品;(3)世界文学不是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即超越地接触自体时空之外的世界[3]。而比科洛福特(Beecroft, Alexander)则将文本集合称作文学的生态(An Ec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他认为既有的文学及其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环境”之间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里穿过时空来考察世界文学的过去和当今则构成了6种文学生态格局,即:1. 非常狭小区域内的文学(epichoric,very local),或当地文学,包括古代的和现代的,属于一种只限于部落内交流、部落外无人能懂的文本。比如,美国或澳大利亚的部落文学,希腊早期城邦文学等;2. 跨区域文学(panchoric,translocal),因为政治和行政区域的设置而跨越了非常狭小的区域。主要是古代的,比如,古希腊文学,玛雅城邦文学,中国战国时期文学等;3.“四海为家”之“世界文学”(cosmopolitan),包括流散文学;4. 当地文学,区域文学,或方言文学(Vernacular);5. 民族文学(National);6. 全球文学(Global)[4]。
这些思路无疑都是卓有见地而启人深思的,关于世界文学的具体内涵我们还可以有各种立场和讨论,但在理论阐释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一个基本事实,按照豪泽尔(Hauser, Arnold, 1892-1978)的说法就是:“在‘世界文学’这个词作为一个概念出现之前,欧洲早就已经有了‘世界文学运动’。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学,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的作品,还有英国的洛克、法国赫尔维提乌斯等人的作品,都已经是严格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了。早在18世纪上半叶,欧洲范围内就已经掀起了一场跨国度的对话,源自不同文化的国家、民族都参与到这场盛况空前的文化对话中。”[5]这一判断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强调了在欧洲范围的诸家并起、列国争雄的客观历史场景。引入到全球史盛行的现时代,它显然也是适用的。
我在这里则想将其进一步和广阔的全球史、资本语境相联系,使得仿佛遗世独立的文学更立体地还原到其文明体结构中的客观位置,因为说到底“权力是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权力一方面是文学得以兴盛的原因,因为文学构成了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另一方面又是它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因为伴随着它在表征领域里位置的急剧下降,文学被挤压到权力的边缘。”[6]在这样一种复杂的交互关系中,文学、资本、权力或能更清楚地意识到彼此的位置。当然,按照华勒斯坦(Wallerstein, Immanuel)的说法,“世界史根本是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反面;它毋宁是文化差异化的趋势,或文化精巧化、文化复杂化的趋势”,则更为深刻地接近了其中可能涉及的陷阱与无奈。
当然,马克思早以其锐利而智慧的目光将这两个仿佛遥远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即“世界文学”与“世界市场”,他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编者注中指出,这里的“文学”(Literatur)的概念乃是指包括了科学、艺术、哲学等等方面的书面著作,所以“世界文学”在这里是个拓展性的概念,可以看作是人类精神产品的指称,但这里的德文概念“Weltliteratur”是与歌德使用的同一个词汇,所以我倾向于将其翻译为“世界文学”,而非“世界的文学”。在这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相互依存、难分彼此的关系,我们当然也就有理由进一步通过“世界文学”的镜射反观“世界市场”的形成。
二、文学世界里表现的家族史
无论是世界的文学,还是“世界文学”,乃至仅仅是经典文学作品,都是非常宏大的概念和宏阔的领域,仅是要熟悉文本就不是一件易事,这里试图缩小范围,将关注点主要聚焦在“家族史”上。本文试图在个体与宏观之间,找到可以凭借支持的某种“介观”通道,能够上通下达,既见树木,亦见森林。家族(甚至是家庭)得到关注不够,其实却颇能反映出社会结构性的某种梯度。从具体的个体出发,好处是特别容易把握落实;但如果将家族作为一个观照的点,则可以联系起更为广泛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某种脉络和管道,既接近于中观维度,又不失其小,不会虚无缥缈、难以把握。当然还必须进一步开掘家族史涉及到的方方面面,譬如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结构构成,他们的生存状况和经济来源,他们的文化品味和闲暇安排……虽然是一个小家族,但也必然通过细微琐事和日常生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大背景发生关联。当然在家族这个概念下,还必须开掘出一系列的子概念,譬如家庭、支系、名人等相互关联、连接、支撑的关键词,这样就能构建出一个完整的家族体系来,其在社会中作为一个极为强有力的细胞单位是不容忽视的。
在这里,我们聚焦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反映的家族现象。文学作为一种诗性资源,尤其值得挖掘;其提供的广阔空间不仅可以让我们回溯历史(诗史互证),而且更可能聚焦典型(经典再现)。我们可以列举出文学世界的诸多声势显赫的家族,譬如《红楼梦》里的贾、王、史、薛四大封建家族、《源氏物语》里的源氏家族等,就是文学世界里的“家族符号”,是必须要关注的。就西欧资本语境的形成来说,英、法、德各有其经济道路和制度建构过程不同,文学世界里也得到印证。法国文学史这点表现得比较明显,譬如巴尔扎克、左拉都是大家式的人物,构建出一个极为庞大的文学世界,完全可自给自足。相比较《人间喜剧》涉及到多个家族、区域、行业,过于百科全书,那么《卢贡—马卡尔家族》作为左拉的标志性著作(包括20部长篇小说),体量虽可谓庞大,但聚焦尤为明显。尽管如此,这部副题为《第二帝国时期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Histoirenaturelleetsocialed’unefamillesousleSecondEmpire)》(1868-1869的冬天开始构思,1893年完成)在历时二十五年的时间里才大功告成。英国则有狄更斯 《双城记》里的埃弗瑞蒙特家族(Marquis St. Evremonde)值得关注。《双城记》描写埃弗瑞蒙特侯爵及其家族成员的生活特征,诸如贪婪、骄奢与跋扈等,显示出反动贵族的阶级性。譬如埃弗瑞蒙特兄弟的马车压死小孩,只觉得“一点讨厌的震撼”,抛一个金币就认为足够抵偿。有人扔回金币,他们就扬言“要把你们从世界上统统消灭”。
我这里举三个文本来看德国文学史上的“家族叙述”,只是窥斑见豹。冯塔纳可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他以少有的“长河小说”的气象与规模建构出一个19世纪柏林社会的众生相来。这里说他那部与《安娜·卡列宁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包法利夫人》(MadameBovary)并列为欧洲三大女性长篇小说的《艾菲·布里斯特》(EffiBriest)。小说内容很简单,就是讲殷士台顿(Innstetten)与艾菲(Effi)的婚姻问题与悲剧故事。作为男方的殷士台顿,不但有男爵的头衔,还是海滨城市凯辛(Kessin)的县长,算得是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作为女方的艾菲,其父亲布里斯特家族乃是容克贵族。这种配对,算得是“门当户对”,当然刻薄的话则是“名门攀旧户,乌龟爱王八”(牧师尼迈尔妻子语)[7]。可如果对一下年龄,就知道不匹配了,殷君年近不惑,而艾菲则年方二八(17岁);更糟糕的是,艾菲的母亲路易丝(Luise)竟是殷君的昔日恋人,而当初之所以弃殷他嫁,也是“不为情郎单为财”。可怜的是,艾菲的路子竟然是重复了母亲的老路,但她却没有妈妈这样的幸福。因为,在这里,她遭遇了爱情。艾菲与殷君朋友克拉姆巴斯(Crampas)发生爱情,克君为了艾菲“提枪应战”而在决斗中被殷君所杀。艾菲不被原谅,不但远离夫、女独居,而且不为母家所接纳。这里从家族史角度切入,艾菲的父亲布里斯特家族乃是容克贵族,按说也是有一定地位和身份的家世,但在这件事情上却是寒蝉不敢言一字,不敢保护自己的女儿。为什么?在其时的历史语境中,容克(Junker)乃是混杂贵族、官僚、军人等多种身份于一端的一种普鲁士特殊阶层,是一种上层阶级的简称,譬如俾斯麦的出身就是容克。所以,艾菲与殷士台顿的关系虽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但却并不反映典型的金钱式的资本主义关系。不过,这也正反映出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式资本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里,资产阶级的出现确实有其必然性,甚至还不仅仅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因为以资本为立身之本者并非前无古人,商人更是贯穿人类历史。但之所以商人(资本家)在现代社会里凸显出一种极为特殊的地位,乃在于资产阶级能应时所需,别出手眼,起到其他阶级、阶层无法替代的主导型功用,应当注意到:“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又是相当不同的,这当然与德国的所谓“特殊道路”有关,因为德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是非常不完备、不充分的。所以在这个故事中,传统社会的封建价值观占了上风,像“秩序”(Ordnung)以一种非常沉重而具体的方式出现在每个个体的正常生活中;其中“荣誉”(Ruhm)则是普鲁士价值的核心观念之一,对于殷士台顿这样的人物来说,他是高官,与俾斯麦等高层有着颇密切的关系,也有着很明朗的仕途前景,但他却不惜一战,以生命为代价,为的是捍卫自己的荣誉。这表现出传统社会的价值标准是有着强大势力的,在无声无息地统治着整个社会,家族势力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必须遵循这些基本价值观,否则就会被社会所淘汰。最后结尾时艾菲父母在其墓前自怨自艾,想是否是自己的“教育过错”。
而托马斯·曼(Mann, Thomas, 1875-1955)则相对更精英些,我颇为情有独钟的,是《布登勃洛克一家》中表现出的布登勃洛克-哈根施特罗姆的两大家族结构,通过对两个家族在时代转折点上的此消彼长,反映出哈根施特罗姆(Hagenström)家族失之于道德却胜之于商场的历史,即对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的胜出[8]。布氏家族乃是德国北方城市吕贝克的望族,尤其是商业世家。虽然在时间跨度上不过四十年,但曼氏却以如椽巨笔描绘了四代人,由老约翰-小约翰-托马斯-汉诺,如果掐头去尾,即开头作为背景的旧式商人老约翰(Johann)与结尾少年早殇的艺术家气质的市民汉诺(Hanno),则首末两代人只是陪衬,实际上在本书中作为主角的是约翰(Johann)与托马斯(Thomas)两代人。以1855年约翰突发心脏病死去为界限,实际上托马斯代表的才是俾斯麦时代的商人景观。在作者浓墨重彩描绘的第三代人中,也是以群像出场的。即不仅是作为掌家的有古风的托马斯,还有浪荡公子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虚荣靓女的安东妮(Antonie)、小妹妹克拉拉(Clara)等,他们构成了布氏家族的第三代主体。作为19世纪德国商人,托马斯是商人中的英雄,他体现了德国社会中传统商业伦理观的代表人物形象。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资产阶级上升期,他秉承讲究信誉、良知的理念,甚是难得。这种理念在老约翰那代人一点都不稀奇,在小约翰那里也是正常的,因为老人要求下一代的就是:“白日精心于事务,但勿作有愧于良心之事,俾夜间能坦然就寝。”(Sey mit Lust bey den Geschaeften am Tage, aber mache nur solche, dass wir bey Nacht ruhig schlafen koennen! )[9](P158)可到了第三代,且是对生意不甚感兴趣的托马斯,他仍然坚持了源自祖父那代人的理念,那就相当不容易了。如果再考虑到,其时社会风气的裹挟之力,那么托马斯所表现出来的,就应该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商人品格:
由于他足迹广、见识多,也由于兴趣广泛,托马斯·布登勃洛克在他的周围一群人中头脑最不受小市民思想的限制,无疑是头一个感觉到他的活动范围狭小局限的人。但是在这个城市外面,在他祖国的辽阔的地域上,紧随着革命年代给社会生活带来的一阵繁盛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个萎靡不振、死气沉沉的倒退的时代,过于荒芜空洞,一个活跃的思想找不到可以依存寄附的东西。然而托马斯·布登勃洛克非常聪明,他把人类一切活动只具有象征的意义这句格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并且把他所有的意志、才能、热情和主动的精力都用在他的小小的社会事业上,用在他继承来的名誉和公司上。他在本市从事市政建设的一群人中已经成为名列前茅的人物;他野心勃勃,想在这个小世界做出伟大的事业,取得权力,但是他很聪明,他既懂得认真地看待他的野心,也懂得对它加以嘲笑。
从这段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托马斯所受到的时代语境之制约和影响。作家很明确地在这里点明了大时代背景,就是革命年代与倒退时代的交相承继。在塑造以托马斯为代表的传统商人形象的同时,作家也逐步呈现出作为对立面的新兴资本家形象,这就是哈根斯特雷姆的崛起。哈氏家族是如何发迹的呢?虽然远不如布氏家族那么辉煌,但却也算是“盗亦有道”。作者这样叙述道:
毫无疑问,亥尔曼·哈根斯特雷姆有自己的一群拥护者和崇拜者。他热心公众事业,施特伦克和哈根施特罗姆公司腾达发展的惊人速度,参议本人的奢华的生活方式,他的豪华住宅,他早餐吃的鹅肝馅饼,凡此种种,对他的声势都不无助长之功。这位商人身材伟岸,略有一些肥胖,浅红色的络腮胡子剪得短短的,鼻子稍有一些扁平地贴在上嘴唇上。他的祖父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祖父的生平。他的父亲由于娶了一个富有的、然而身分可疑的女人在社交界几乎还没有立足之地,然而他自己却仰仗着和胡诺斯家、和摩仑多尔夫家攀了亲,挤到本城五六家名门望族的行列里。他的姓氏居然能和这些高贵的门第并列,他自己也无可争辩地成了一个令人起敬的显赫人物。他性格中新奇的地方,同时也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自由和宽容的本性。也正是这一点使他和一般人不同,使他在许多人心目中居于领导地位。他那种轻易大方的赚钱和挥霍的方式,和他的一些同僚商人的勤俭谨慎、循规蹈矩的工作方法很不相同。他有自己的立脚点,不受传统梏约束,也不懂得尊奉旧习……如果说哈根斯特雷姆参议也遵奉什么传统,那就是从他的父亲,老亨利希·哈根斯特雷姆那里继承下来的自由、进步、善于容忍和没有成见的思想方法,人们对他的崇拜也正建筑在这上面。
这段叙述很重要,因为这里交代了哈氏成功的奥妙所在,他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迅速跻身望族,同时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我们再一次看到,联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提升通道,这个祖父一代还是默默无闻之辈的哈根施特罗姆,通过父辈与富家婚姻而获得经济资本,接着又通过与名门联姻而获得社会地位。再加之个体生性的长袖善舞,使得他在大变局的时代脱颖而出,能够与时俱进地成为新时代资本家的代表。我们不应忽略,所谓“自由、进步、善于容忍和没有成见的思想方法”,正是启蒙思脉以来占据文化场域主流的话语模式,同时它也进一步渗透到政治、经济与社会诸领域。很难说哈根施特罗姆究竟对这些理念有多少深刻的认知,但他无疑属于那种政治正确的资本家,也就难怪,他将来会在这样一种背靠整体场域的商业角逐中轻松胜出。
鲁格(Ruge, Eugen, 1954-)的小型家族史叙述,无疑独具匠心,而且营构细腻,处处见出智慧。《光芒渐逝的年代》通过乌姆尼策家族四代命运流变的叙述,威廉(1899-)-库尔特(约在1920年代)-亚历山大(1954-)-马库斯(1979-)这四代人的延续过程,不仅是生命史的世代承续,更反映了历史的线性演进,反映出20世纪德国的一部另类兴亡史。作者选择了2001年作开篇,亦即21世纪的第一年,作为回首往事的一个出发点,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年份。更重要的是,作者设置了一组以1989年为中心的对峙年份,即“十二年”(Zwölf Jahre),“十二年到底有多重?”(Was wogen zwölf Jahre?)“他觉得易帜前的十二年比易帜后的十二年长多了。1977——悠长得像永恒!1989——一下子滑走了,好比出门乘了一趟有轨电车。”(Klar, dass die zwölf Jahre danach. 1977 - das war eine Ewigkeit! 1989 dagegen - ein Rutsch, eine Straβenbahnfahrt.)[10]作为第三代人的亚历山大似乎并没有太沉重的历史负担,他其实素来就有一种玩世不恭而又看破红尘的念头,按照作者的描述:“无所谓喽。都是身外之物,亚历山大想……不就是身外之物嘛。自己死了,对后人来说,无非是一堆垃圾而已。”如此心理的亚历山大,居然也是子承父业的历史学家。“欧根·鲁格的家族小说折射出民主德国的历史。他成功地将四代人五十多年的经验压缩在一个编排巧妙的布局中。他的书讲述的是社会主义乌托邦、其要求个人为之付出的代价以及它的逐渐熄灭。他的小说表现出极大的娱乐性和强烈的谐谑感”(德国图书奖颁奖词)。
这三部顺时演进的小说,反映出的是什么呢?“婚姻悲剧”-“商战兴衰”-“理想之灭”, 每一种叙述都离不开个体,离不开家庭,甚至有更大的家族在存在,发生二元交错关系,出现代沟冲突与变异,但都离不开生存其中的社会生活、时代背景,但最后具有强力意义的仍是隐在背后驱动的资本语境。《光芒渐逝的年代》或许最好地表明了某种象征符号,按照华勒斯坦(Wallerstein, Immanuel, 1930-)的说法:“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资本主义是一剂危险的麻醉药,在整个历史上,大多数的文明,尤其是中国文明,一直在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在最为虚弱的时刻对它屈服了。我们从此都在承受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11]这是一种相当有水准和高度的表态,是对资本主义一针见血的否定,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随着时代的演进,资本力量的作用仿佛无往而不利,华勒斯坦可能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衰落同样都是必然的,其实即便是标榜着“资本主义精神”的知识人也多少意识到其背后的奥义所在呢?在这里要提出“资本域”的概念,就是说资本的发展进入到一种超出人力主控和主导的时代,进入某种集体无意识状态的“器物自运作”阶段,即形成了它自己内在生存、发展与维系的系统性功能;而舍却资本规定的一种系统考量,其实很难理解人类现代社会运作的某些根本特性。
三、资本语境的器物符号与侨易空间的成立——在民族文学、家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之间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德国资本语境的若干基本叙事模式,当然我们也有观察这些语境的特殊视角,不一定都是从情节结构、主题思想、社会生活考察,也可以就从具体的空间符号入手,也许同样可以得到别出心裁的观察角度。空间是文明结构的基本元素之一,这里仅就地理空间而言,除了可以被切分为大家都认可的不同文化体之外,也可以有进一步的单元意义区分。这里仅就和资本相关的一些概念稍作划分,譬如:
商业交易场所的名称:商铺、商店、百货商店、超市、大型购物中心。
住房:廉租房、平房、楼房、别墅。
机构:证券所、银行、法院。
休闲场所:公园、俱乐部、咖啡馆、茶馆。
路径:拱廊街、林荫路、马路、道路。
商品分类:男装、女装、老年用品、婴儿用品。
当然还有消费社会,还有交通分类,诸如:公路、铁路、海运、空运等。它们对于海外殖民、资本社会的连接、全球市场的形成起着最为关键的大动脉作用。当这些资本语境里的空间符号被确认出来之后,侨易观念就自然发生作用了,因为正是在这些具有标志性的空间符号之间,发生着不间断的、各种类型、形式各异的侨易过程。
二战前的美国曾有一句经典之言:“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的,而共和党是属于洛克菲勒家族的……”其实尚缺一句,“而洛克菲勒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被巴尔扎克改名换姓放进作品,称为纽沁根男爵,这就是鼎鼎有名的人间喜剧中的一部《纽沁根银行》,相关的一部前史则是《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皮罗托本是乡下人,其第一重侨易过程,就是从乡土到都市,这里是到了巴黎,帝国之都。这种二元地域的变化过程,只是大的方面;具体言之,则是进入了商铺。
赛查十四岁上便能读能写会算。他口袋里装着一个金路易,徒步去巴黎闯荡。图尔一家药房的老板介绍他进了拉贡夫妇的花粉店,当了一名打杂的学徒。那时候,赛查的全部家当是:一双铁钉掌底鞋子,一条扎脚裤,几双蓝袜子,一件花背心,一件乡下人穿的外套,三件厚实的土布衬衣,外加打狗棒一根。他剪了一个唱诗班式童花头,腰板十分结实,不愧是个都兰仔;他虽受过家乡懒散风气的影响,但发财致富的愿望把这个缺点弥补了;若说他缺少智慧和教育,却从母亲那里继承了正直的天性和办事认真的优点,因为按都兰人的说法,他母亲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赛查的一日三餐由店里供给,每月有六个法郎工钱,在阁楼上支一张破床,紧挨着厨娘的卧室。伙计们教他打包,送货,打扫街道和店堂。他们边教他干活,边拿他取笑。小商店都有这样的风气:师兄们传授技艺时,戏谑调笑是一门主课。拉贡夫妇像使唤小狗似的将他呼来喝去。小学徒在街上奔波了一天,累得双脚肿痛,肩膀像裂开似的,就是没有一个人体恤他的苦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信条,在各国京城被运用得如同金科玉律,使赛查深感巴黎生活的艰辛。晚上,他想起都兰便暗自流泪。在那里,农人种起地来怡然自得,泥瓦匠慢悠悠地砌上一块砖头,懒散和劳作结合得浑然一体。
在这里虽然有都市-乡村比较的清淡一笔,但核心仍在于花粉店成了赛查的安身立命之地,他由学徒而店员,而出纳、领班,最后甚至盘下东家的铺子,自己当老板,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变,也就完成了都市侨易的最终过程。这样一种精神质变并不仅是简单的抽象的观念变化,而更接近于所谓“精神的经济政治社会史”,正是在具体语境的变化、涵濡、养成过程中,赛查完成了一个乡下小子到城市商人的转变,其梦想不过挣大家业、嫁出女儿,出盘商铺,进而衣锦还乡,回老家买一座小农庄。这种传统,在中国也有,所谓“致仕还乡”也。但幸与不幸,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之中,其侨易过程仍在持续发生。在赛查,波旁王朝的复辟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因年轻时卷入保王党暴乱而被当了副区长。人总是利欲熏心的,赛查于是不安心他的小商铺,而想往大生意。结果卷入商海的尔虞我诈和残酷商战之中,被银行家蒂耶、公证人罗甘设局捕获,破产败灭。这时,小农庄的意象转换为豪宅舞会,但旋即因债主纷至而烟消云散。当然,如果仅仅如此简单,也低估了巴尔扎克的大手笔。作者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更深层的理念层次,为了“还清债务,恢复信誉”,赛查一家打拼不息,靠打工苦干奋斗三年,终于还清债务,取得“复权”资格(在法律上正式恢复市民的各项权利)。因为“在巴黎的正派商人看来,诚信为本永远是事业成功的前提,也是一个商人的尊严、荣誉和价值所在”,这就塑造出了一个相当有深度的老派商人形象(有点像布氏家族),但在我们看来,则是相当有意味的“复杂侨易”过程,这其中既有直接的从乡村到都市的地理侨易,也有物境符域的虚拟侨易,譬如从小商铺到大事业,从花粉商到地产商,到大资产阶级的向往。这其中有有形的物境标志,譬如说商店、豪宅等等,也还有无形的“情义无价”,譬如在困境中哥哥弗朗索瓦·皮罗托寄来的1000法郎和那封信:
亲爱的赛查,在你悲伤的时候别忘了:人生犹如过眼云烟,且充满了考验。为了上帝的圣名,为了神圣的教会,为了遵守福音书上的箴言,因积德而受苦受难,将来都会得到报偿;否则,世上一切事物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之所以重复这些箴言,是因为知道你虔敬上帝,心地善良。有些人像你这样遭受人间的风暴,卷入利益的惊涛骇浪而痛不欲生时,往往会说出亵渎神明的话。你可别诅咒伤害你的人,也不能诅咒有心在你的生活中洒下苦酒的上帝。不要总是望着尘世,要举目遥望苍天:对弱者的安慰会从天而降;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恐怖,也都在天上……
这么一番人生道理,当然是和他的牧师职业有关,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实在是有振聋发聩之效,尤其是对于像赛查这些奔波逐利于资本语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者。这也对我们理解巴翁的神妙之笔有很大的助益,因为在如此精雕细刻般的巧匠之功后,显然他时刻未忘更大的关怀,让人们知道在现世的红尘滚滚和利益追逐之外还有更高的精神生活和身后世界。
那么,我们要继续追问的是,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侨易空间”的概念?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文学世界里的时空变化过程,如何可以一种较为有趣而轻松的方式来观察文本现象。这里提几点思路:
一是相关侨易概念的直接运用; 譬如我们可以观察到非常典型的物质位移现象,譬如从南方到北方(盖斯凯尔夫人的《北方与南方》),从本土到异国(《印度之行》),从乡村到城市(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都很有代表性。譬如这里看到的皮罗托从希农的乡村到大都市巴黎;还有像韦小宝从扬州到北京,不仅是大环境的变化,即城市风土之南北迁移,更是小环境的质变,从“妓院”到“皇宫”。
二是物境拟符空间的考察,正是在这样一种空间侨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更清晰地展现出资本语境得以具体型构的若干环节,使之得以“节点化”(Nodes)。这有些类似于坐标轴的功用,使得资本语境立体化和具象化,譬如下面这段简短描述提及的歌剧院休息室、交易所、纽沁根银行等,其实就是这些“势境节点”。这是我所谓的“筑势”,其关键在于“势境”的形成,这里可理解成资本语境作为一种整体强势的构境成型。“资本势境”是经由不同的管道建构而达成的,譬如网链六度(参考六度分割,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的概念就有意味,在《赛查·皮罗托盛衰记》中,那个原本不过小伙计的蒂耶就通过人际网络的营构以及“移仿高桥”的变易过程,实现了他的野心:
做金融投机生意好比走钢丝,杜·蒂耶竟把平衡杆玩得稳稳当当。他把自己这副空壳子打扮得衣冠楚楚,俨然一个富家子弟。他一朝买进了自备小马车,就一直坐下去。上流社会的人惯于在寻欢作乐中做买卖,歌剧院的休息室成了交易所的分号,那儿的人一个个都成了现代的杜卡莱;杜·蒂耶在这个圈子里居然站住了脚。在皮罗托家,他认识了罗甘太太,靠她的帮助,很快就结交上一帮金融巨子。至此,杜·蒂耶想发迹,已不是吹牛撒谎摆空架子了。靠罗甘的引荐,他和纽沁根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又很快跟凯勒兄弟和银行界高层搭上了关系。这年轻人从哪儿一次次调度到巨额资金,至今无人知晓,人们还以为他的成功靠的是聪明和诚实。
如果在这段叙述基础上加以复原细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过程:先是“移变”,本来不过一家花粉店伙计的蒂耶敢于当于连,野心勃勃,厚颜无耻,不但贪污挪用款项,而且居然安然离开;其次是“仿变”,蒂耶可以通过自己的乔装打扮、易容变身,将自己伪装成一个富家子;而这就无形中给了他象征资本,让其能够在社交场合出入自如,不说是“往来无白丁”,至少是“谈笑有富人”,这就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高变”;但最关键的则 “桥变”的过程,正是通过在社交网络中的勾连建桥,蒂耶将所以这些本来在社交场里很是常见的人物编织到自己的“象征资本链”中,开始“空手套白狼”。具体的案例,就是他如何精心营构,借助这帮夹带人物完成了对皮罗托的“设套兑现”,让一个成功的商人破产,斩获他的财产。当然如果更深入分析,我们会有更深刻和复杂的图景可以描绘出来,但仅就此段稍作延展,就已可展现无限风光。所以就蒂耶-皮罗托的主仆过招而言,整个的过程也不妨看作蒂耶一连串的颇为完整的“侨变”学。
当然“资本势境”可以是上面说到的抽象的银行、交易所等,也可表现得更具体一些,是一些地名:“冬天的夜晚,圣奥诺雷街的嘈杂声只有片刻的休止;从戏院或跳舞会出来的车马刚过去,前往中央菜市场赶早市的菜贩又闹腾起来。这片刻的宁静在巴黎喧嚣的大交响乐中好比一个休止符,出现在凌晨一点左右。此刻,旺多姆广场附近开花粉店的赛查·皮罗托的太太刚被一个噩梦惊醒。”作为开篇首段,一个个地名的出现,其实也是筑境的符号确认,诸如圣奥诺雷街、中央菜市场、旺多姆广场各自都有着特定的内涵,各有意味却又统一在巴黎这座城市之中;而一个个场所意象的呈现,则意味着其特定的语境功能,像戏院、跳舞会、花粉店也相互配合,似乎想要呈现某种特殊的话语含义。正是在这种环境中衬托出赛查夫妇的悲剧命运,其实也是对结局故事的预兆和预告。所谓“草蛇灰线”,所谓“事事有征”,都在这里了。
三是侨易观念的元思维运用,这将更有助于我们将问题链接到一个更为开阔的大背景和大语境中,譬如立体结构、交叉系统、混沌构序等等,当然最核心的还是二元三维。譬如我们讨论世界市场问题,就不仅需要就经济来论市场,而且也需将其放置在文明体结构中。在现实世界里,我们提出一个与文明结构三层次相呼应的概念,即:世界市场、世界治场、世界知场。在最初级的器物层面,对应于经济社会的是世界市场,这个场域的形成乃是由利益为关键,尤其是经济利益和收入来作为基本驱动力和原则的人类生活空间;在中级层面的制度层面,世界治场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相当于打通了的政府联合体,即构建一个世界的治理模式和制度架构,或者所谓的“全球治理”或“世界制度”概念是可以相互交集的;在高端的文化层面,则是世界知场的构建,即人类的知识场域应该形成一个相通、相连、相融的整体性场域,这个层面相对于前两者来说,其实是最容易也最难建构的。就人类求知而言,当然具有普适性,不管你使用的语言如何,你所在民族国家为何,如果承认知识的客观规律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大家公认的世界知场的存在。所以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趋一是绝对不可回避的大势,但在具体的进程中,则知识精英与普罗大众其实都可以找到相对一致的愿景,不管这种驱动力是来自理想情怀还是现实利益需求,但问题的关键将停留在中端层面,即权力精英的决策、观念和现实考量,他们的作为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通过对政治权力,尤其是民族国家政治权力(暴力机器)的掌握,他们有直接发言权。但政治精英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可改变的,虽然他们在短期内握有直接权力,但从长远看来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观念的作用,所以一个纯粹以求知、真理、寻道为目标的世界知场的良性建构十分重要,它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象牙塔。但如何通过制度驱动来实现这三者之间,即世界市场-世界治场-世界知场的结构成型,则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这里无法展开,可强调几点,通过二元三维的思维模式,我们会意识到,市场、治场、知场是整体结构,即便我们关注世界市场,但不能孤立思考之。
这段话或许更深刻地提醒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民族文学空间的建成是和民族的政治空间紧密相连的,这些民族文学空间反过来有助于政治空间的建立。但是在最具禀赋的文学空间里,资本的资历——必须以其崇高、威望、规模、世界上的认可为前提——将会带领整个空间逐步走向独立。”[12]这里当然不仅有资本、政治和文学的关系,也还涉及到本土、他者和世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德国虽是最早提出“世界文学”的民族,但其文学实践情况则是,“没有‘他者’,就不会有德意志文学的产生,源自古日耳曼异教传统的格言诗和英雄史诗早在中世纪便已失传,而来自地中海沿岸晚期的基督教传统塑造了德意志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部分。德意志文学从宗教型到诗意型的转变要归功于法国启蒙运动,归功于它偶然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在其他国家,文学很早便以令人深刻的方式促成了文化的进步,如果没有这些国家令人嫉妒的先例,德国知识界在法律或科学之外的语言表达便要局限于宗教惭悔,而不会有文学语言的产生。尽管奥皮茨和戈特舍德推荐的法国文学模式并不适合德国,无法终结德国文学落后的状态,他们还是成功地使德国人注意到了文学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并激起了德国人的效仿之心。德国人只需找到更适合德国的榜样,博德默尔和莱辛发现了英国文学。对于18世纪的德国文学而言,没有一位德国作家的影响力可与莎士比亚、弥尔顿、杨恩和斯特恩相媲美。歌德嗅到了同时代文学作品(他自己也不例外)中的虔诚气味,并为此感到难堪,于是作为某种意义的祛魅者,他改拜外国作家为师,从荷马到拜伦都成为他的榜样。如果存在一种德国文学,那它应该不仅仅是德国的文学。”[13]正是因为善于借镜,能从“他山美人”反思“镜中之我”,也才有创造人类现代精神高地的德意志文化的成就。
我这里则还想提及“家族史”的纽带和线索意义,正如39岁的皮罗托给妻子解释其冒险房地产业的雄心壮志的说法:“我交上了好运,有着锦绣前程,总得再闯一闯。只要谨慎小心,我可以在巴黎市民中开创一个光荣的门第。这样的先例已经很多了,像凯勒、于勒·德马雷、罗甘、科香、纪尧姆、勒巴、纽沁根、萨亚、包比诺、玛蒂法,等等。他们在自己的地区里,有的早已出了名,有的正在出名。我皮罗托也能使这个姓氏成为名门望族的!别担心啦!这桩买卖肯定会像金子一样靠得住,否则……”在这里,不仅皮罗托的悲剧肇因于此;更重要的是,光荣门第,名门望族似乎成为一般市民阶层的价值标准,是一种理想梦,我们看到了社会的价值标准所在。而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家庭与家族,我们可以看到市场是如何逐渐成型的,最后如何由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最后连接出一个世界市场。要知道,“资本主义并不限于某一国,而是存在于世界体系之中;既为世界体系,自然是超越国界的。假定此过程仅在某一个国家里发生,那么就无法避免国家权力的所有者侵占剩余价值,从而剥夺(至少是极大地削弱)企业家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市场里完全没有国家,就无法形成准垄断。只有当资本家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世界经济’,即有多个国家参与的经济时,企业家才有可能追逐无止境的资本积累。”[14]正是鉴于资本主义与资本语境型构的这种明显跨国性、国际性和流动性,运用侨易学的视域观察之,或许可以提供相当有趣的角度。而文学世界所提供的那种在“诗与真”之间的模糊地带,或许有多少沾染上可能第三维的“介观”特质,而家族史的承上启下、内外勾连、时间延续等方面的优势,或许正可为我们打开“世界文学与资本语境”的侨易空间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