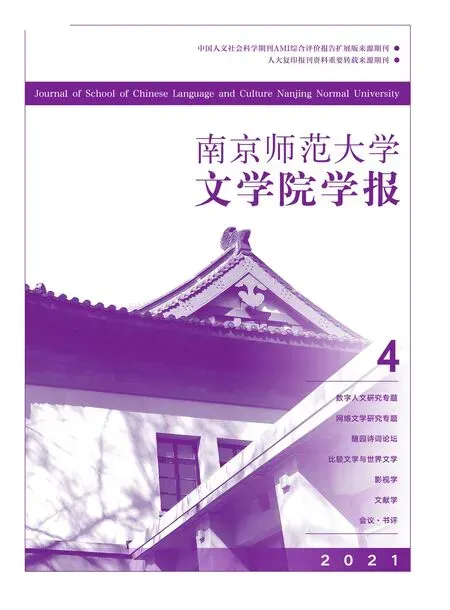游戏之作的创造性与局限性
—— 三组唐代唱和诗的比较研究
肖瑞峰 杨珏沁
(浙江工业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4;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27)
一、 三组唐代唱和诗概述
在中唐诗人刘禹锡与白居易、元稹的唱和诗中,还有一组值得注意的作品,那就是《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这组唱和诗的作年是大和二年(828),即诗人重回长安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期间。佐证是,白居易大和二年作《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中云:“微之又以近作四十三首寄来,命仆继和,其间瘀絮四百字、车斜二十篇者流,皆韵剧辞殚,瑰奇怪谲……今足下果用所长,过蒙见窘,然敌则气作,急则计生,四十二章麾扫并毕,不知大敌以为如何?”所谓“车斜二十篇者”,即指元稹所作《深春二十首》。宋王得臣《麈史》记云:“唐元微之《何处春深好》二十篇,用家花车斜韵,梦得亦和焉,余亦和之。”可知元稹原唱南宋时尚存,王得臣曾经追和;亦知其用韵与白居易所述完全一致。
但元稹这组原唱今已佚失。或以为原诗即《元氏长庆集》中的《生春二十首》,显然不妥。理由有四:第一,据诗人题下自注,这组诗乃元和十一年(816)丁酉所作,距大和二年已有十二年。第二,《生春二十首》以“中风融丛”为韵,与刘白唱和诗韵部有别。对此,陶敏、陶红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已作辨析。第三,刘白的和诗分别以“何处深春好”和“何处春深好”领起,仅有一字之差,可以理解为唱和时间在后的刘禹锡故意错落一字以求变化;元诗则以“何处生春早”领起,不仅两字有异,而且意蕴全然不同。第四,刘白和诗均致力于描写何处“春深”,分别着笔于“万乘家”“阿母家”“执政家”“大镇家”以及“富贵家”“贫贱家”“方镇家”“刺史家”,即以人物为中心,写照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元诗则致力于描写何处“春早,”先后落墨于“云色中”“漫雪中”“霁色中”“曙火中”“冰岸中”“柳眼中”,即以景物为中心,刻画早春景色在不同处所的多样呈现。因此,刘禹锡的《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不可能是今存的元稹《生春二十首》的和作。
自然,我们不能笼统地将唱和诗一概视为游戏之作,唱和诗中的精品佳什层出不穷。以刘禹锡而言,他的《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酬元九侍御壁州鞭长句》就分别是与白居易、元稹唱和的作品,但它们都寄寓了真切的人生感喟与感悟,思想深刻,语言工巧,可在最为脍炙人口的唐诗作品之列,“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且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因此将唱和诗与游戏之作划等号的做法是荒诞的、罔顾事实的。但刘、白、元这三组咏春的唱和诗,由于其创作目的主要不在抒写怀抱,而在娱情遣兴,又有共同遵守的创作规则,这本身就滑近游戏的边缘了。
从总体上看,这类旨在逞才竞技的唱和组诗,绑定同一体裁、围绕同一主题、拘囿同一韵脚,叠相赓和,联类无穷,明显带有游戏性质。刘禹锡于题下自注:“同用家车花邪四韵”。这一限定犹如自我禁锢,迫使他们带着镣铐跳舞。不过,有赖于身段灵活、内力充沛、舞技高超,他们的舞姿还算回旋有方、舒展自如。换言之,他们在画地为牢的有限空间内,将腾挪翻转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这就叫“因难见巧”。这也就是说,作为中唐诗坛上独树一帜的名家,他们在为“游戏”而作时,也不忘开拓创新,在遏制创造力激荡的框架下表现出一定的创造性。当然,游戏之作固有的局限性,他们也未能避免,只不过表现程度略有不同而已。
二、 元稹《生春二十首》寻绎
兹录元稹《生春二十首》前五首与后二首于下:
一
何处生春早,春生云色中。
笼葱闲著水,晻淡欲随风。
度晓分霞态,馀光庇雪融。
晚来低漠漠,浑欲泥幽丛。
二
何处生春早,春生漫雪中。
浑无到地片,唯逐入楼风。
屋上些些薄,池心旋旋融。
自悲销散尽,谁假入兰丛。
三
何处生春早,春生霁色中。
远林横返照,高树亚东风。
水冻霜威庇,泥新地气融。
渐知残雪薄,杪近最怜丛。
四
何处生春早,春生曙火中。
星围分暗陌,烟气满晴风。
宫树栖鸦乱,城楼带雪融。
竞排阊阖侧,珂伞自相丛。
五
何处生春早,春生晓禁中。
殿阶龙旆日,漏阁宝筝风。
药树香烟重,天颜瑞气融。
柳梅浑未觉,青紫已丛丛。
十九
何处生春早,春生客思中。
旅魂惊北雁,乡信是东风。
纵有心灰动,无由鬓雪融。
未知开眼日,空绕未开丛。
二十
何处生春早,春生濛雨中。
裛尘微有气,拂面细如风。
柳误啼珠密,梅惊粉汗融。
满空愁淡淡,应豫忆芳丛[1](P173)。
春回人间,东风骀荡,万物复苏。这让刚由江陵奉召回京,席不暇暖,便又贬任通州司马的元稹看到了生机和希望,精神为之一振,忍不住要向诗友传达春的消息。在诗人笔下,无处不生春,无物不逢春,春天的脚步已悄然跨入人世间及自然界的每个角落,带来许多细微的改变。诗人抓住初春时节特有的症候,谱写了一组舒缓悠扬的“早春圆舞曲”。如第二首写“春生漫雪中”:漫天飞舞的雪花在空中就融化了,没有一片完好地降落到地面,这就点出了春雪与冬雪的区别,昭示了气温向暖、严寒不再。第十一首写“春生鸟思中”:鸟类在春天的怀抱中各得其所,无比自在——喜鹊欢天喜地地构筑了向阳的新巢,飞鸢在吹面不寒的春风中展翅高翔,栖息到沙滩上的鸿雁惊讶地发现沙子变得暖融融的,鸳鸯也更爱戏水,因为一江春水已经无复凛冽。第十七首写“春生绮户中”:细碎的阳光穿过精致的窗栊洒进屋内,轻灵的春风掀动着光影斑驳的罗幔,倚窗张望的佳人腰肢像新绽的柳条一样柔软纤细,而梅花的幽香不仅弥漫在空气中,还沁入人的心田。诸如此类,都紧扣诗题来驰骋想象、安排笔墨,以生动而又富于张力的画面,解答了“何处生春早”的自我设问。
就中,第十八首“春生老病中”和第十九首“春生客思中”尤堪寻味,因为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糅入了诗人的身世之感。“似觉肌肤展,潜知血气融。”意谓和熙的春风使他顿觉全身的肌肤都舒展了开来,潜意识中血气融和,活力大增。这实际上是说,自己已经“春心”萌动,开始作脱离谪籍的非分之想。“旅魂惊北雁,乡信是东风。”托出诗人喜忧参半的矛盾心态。与春天一同归来的大雁,使处于羁旅中的诗人魂魄为之悸动:自己什么时候才像大雁一样开启归程、重返京都呢?东风给自己带来了春归的信息,这是令人欣喜的。可是,自己政治上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乡信”,本指来自家乡或家人的信息。刘长卿《同诸公登楼》一诗有云:“北望无乡信,东游滞客行。”这里借指春天的信息。“纵有心灰动,无由鬓雪融。”进一步倾诉纠结不已的心曲。本以为连遭两次贬逐后已经心如死灰,谁知正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样,春回大地之际,他内心也死灰复燃、不无期盼。然而,两鬓如雪,老病见迫,时不我待。想到这,他又不免悲从中来。这就跳脱出了纯客观写景的立场,而跃迁至情景“妙合无垠”的更高站位。
然而,这组作品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景物描写缺少变化,因而各首之间的区分度不大,给人雷同之感。尤其是遣词造句,重复率已高到与诗坛名家身份不相称的地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韵脚通押“中风融丛”的缘故。能与这四个字搭配的词组及构建的句式十分有限,又不能颠倒其序、错落其位,有时就只能生拼硬凑,难以做到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以“融”而言,“泥新地气融”“天颜瑞气融”“梅惊粉汗融”等句尚可玩赏,至少还文通字顺;“波神玉貌融”“先添酒思融”“抬神便恐融”等句,强自凑泊的痕迹就很明显了。“丛”字句的情况就更糟糕了:“空绕未开丛”“偏在最深丛”“衰白转成丛”等句虽不够精粹,也还清通;“杪近最怜丛”“珂伞自相丛”“缘未有诸丛”等句就殊不成语了。另外,“谁假入兰丛”“飞入小梅丛”“挑得小莺丛”等句相似度既高,又了无余蕴,纯属为了敷衍成篇。
三、 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考释
限于篇幅,仅录白居易《和春深二十首》前三首和后二首如下:
一
何处春深好,春深富贵家。
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
罗绮驱论队,金银用断车。
眼前何所苦,唯苦日西斜。
二
何处春深好,春深贫贱家。
荒凉三径草,冷落四邻花。
奴困归佣力,妻愁出赁车。
途穷平路险,举足剧褒斜。
三
何处春深好,春深执政家。
凤池添砚水,鸡树落衣花。
诏借当衢宅,恩容上殿车。
延英开对久,门与日西斜。
十九
何处春深好,春深娶妇家。
两行笼里烛,一树扇间花。
宾拜登华席,亲迎障幰车。
催妆诗未了,星斗渐倾斜。
二十
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
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
兰麝熏行被,金铜钉坐车。
杭州苏小小,人道最夭斜[2](P2072)。
尽管视角与取径与元稹所作不同——事实上,白居易所奉和的也不是元稹的这组作品,不应该把它们放在同一层面上加以比较,但或许因为创作时间推后了十二年,状物写景、谋篇布局及抒怀寄意的艺术技巧理所当然地更见成熟,所以,白居易的这组诗要比元稹的《生春二十首》体察入微、细密尽情。为诗人烛幽显微的镜头所摄录的二十户人家分别为“富贵家”“贫贱家”“执政家”“方镇家”“刺史家”“学士家”“女学家”“御史家”“迁客家”“经业家”“隐士家”“渔父家”“潮户家”“痛饮家”“上巳家”“寒食家”“博弈家”“嫁女家”“娶妇家”“妓女家”,可以说涵盖了三教九流,亦即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在诗人举重若轻的笔下,他们不仅身份、地位有别,而且面目、姿态各异。春深时节的景物,各处大同小异;春深时节的人物活动却是千差万别。诗人将他们一一驱遣上舞台,在春深时节汇演成一幕幕活色生香的人间悲喜剧:“富贵家”罗绮成群,成日在豪宅中观赏轻歌曼舞,金银珠宝可用车载斗量。唯一憾恨的是人生短暂、夕阳西斜。“贫贱家”门前冷落、庭院荒凉,妻子满脸愁容,时兴日暮途穷之感,足履“平路”也充满风险。“学士家”以起草诏书为业、青灯黄卷为伴,偶蒙圣上赏赐便深以为幸。平日谨言慎行,低调为人,路遇同僚都不敢招呼。“潮户家”不畏惊涛骇浪,弄潮于钱塘江上,在滚滚江潮犹如千马奔腾、万车竞逐之际,手把红旗,胜似闲庭信步。“痛饮家”嗜酒如命,所爱惟有杯中物,三杯入肚,眼前便花开五色,无复他求,糟瓮下亦可酣眠。“妓女家”自恃美色,眉毛比杨柳叶还要纤巧,衣裙比石榴花还要鲜艳,为了招徕“檀郎”,兰麝熏被是其日常生活方式,而她出行的香车也镶铜嵌金,不失华贵。诗人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捕捉不同人物的行为特征,为他们逐一传神写照,用笔细腻而又精准。
不过,白居易同样受限于韵字,而不得不“以辞害意”。通读这组作品,偶亦见语言乖格、别扭之处,如“饱识浴堂花”“恩容上殿车”“收萤志慕车”“举足剧褒斜”等,完全有失大家水准。还有,对所描写的二十种人物的分类也有些前后含混:“富贵家”“贫贱家”“刺史家”“学士家”等是按人物身份来划分的;但“上巳家”“寒食家”又是按时令节日来划分了。至于“嫁女家”“娶妇家”,则既并不是按身份划分,也不是按节令划分,而是按生活事件来划分了。前后分类标准的不一致,暴露了诗人逻辑思维上一时的淆乱,也见出他在急于酬答之际素材之不足与思力之不逮。此外,“痛饮家”作为一种人物身份的标识,似乎不太符合传统的语言表达习惯,如果直白一点或可改为“酒徒家”,含蓄一点则可改为“杜康家”。
值得称道的是,这组作品虽是娱情遣兴的游戏之作,却没有脱离或粉饰社会现实,而在诗人认为适当的地方楔入了一些讽喻之辞。比如,描写朝中的学士们“相逢不敢揖,彼此帽低斜”,就揭示了当时政治氛围的严酷:朝官唯恐罹祸,一个个噤若寒蝉,与同僚形同陌路。再如描写权贵们的骄奢生活说“马为中路鸟,妓作后庭花。”将“后庭花”这一亡国之音标举为歌姬们演唱的曲目,自然寓有讥讽权贵们醉生梦死、不恤国事之意。同时,我们还不难发现,在诗人对“迁客家”和“隐士家”的刻划中,分明渗透着他自己对现实人生的真切感受和深刻感悟——“迁客”生活是他过去曾经历的。 “一杯寒食酒,万里故园花。”刻划出迁客生活的孤寂、清寒,一方面只能借酒浇愁,在日复一日的麻醉中求得心灵痛苦的暂时消解,另一方面格外怀念故乡的鸟语花香,渴望能早日回到故乡的春天的怀抱。“炎瘴蒸如火,光阴走似车”。点出迁客们寄身的蛮乡瘴地气候条件极其恶劣,让他们既有度日如年之感,又痛感时光流逝、壮志成空。“为忧鵩鸟至,只恐日光斜。”用贾谊《鵩鸟赋》,代迁客们寄恨抒愤。贾谊谪居长沙时作《鵩鸟赋》,借与鵩鸟的问答曲尽其致抒发了自己忧愤不平的情绪,并试图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思想求得自我解脱。笔力劲健,一气呵成。忧鵩鸟将至,即担心年寿不永、盛时难再,机遇错失、功业无成。这正是诗人贬任江州司马期间心头挥之不去的隐忧,而且迄今还让他不堪回首。
“隐士”生活则是他现在所欣羡的。尽管他不愿放弃眼下这优裕而又相对自由的“中隐”生活状态,但内心深处对完全摆脱了官场羁绊和世俗纷扰的隐士生活还是不胜向往的。“野衣裁薜叶,山饭晒松花。”以“薜叶”为衣、“松花”为饭,不仅可免冻馁之苦、衣食之虞,而且充满野趣和泥土气息,更加贴近自然、回归本真。“兰索纫幽佩,蒲轮驻软车。”隐士的生活自在而又惬意,可以安步当车,也可以自驾“蒲轮”;至于佩饰,那手编的“兰索”既具雅人高致,又自带幽香,沁人心脾。“林间箕踞坐,白眼向人斜。”这是诗人最为企慕的。中隐者尚必须遵守朝廷礼法,顾及自身公众形象,不得肆意妄为。隐士则徜徉于密林深处,可以不管不顾地箕踞而坐,用“白眼”傲视人世间白云苍狗的变化。这才是诗人内心最深的渴望!当然,也是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但由这类作品,我们却可以触摸到诗人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了解隐匿在其“优哉游哉”的表象背后的感情潜流。
四、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发微
兹一视同仁,亦录刘禹锡《同乐天和微之深春二十首》前三首和后二首于下:
一
何处深春好,春深万乘家。
宫门皆映柳,辇路尽穿花。
池色连天汉,城形象帝车。
旌旗暖风里,猎猎向西斜。
二
何处深春好,春深阿母家。
瑶池长不夜,珠树正开花。
桥峻通星渚,楼暄近日车。
层城十二阙,相对日西斜。
三
何处深春好,春深执政家。
恩光贪捧日,贵重不看花
玉馔堂交印,沙堤柱碍车。
多门一已闭,直道更无斜。
十九
何处深春好,春深种莳家。
分畦十字水,接树两般花。
栉比栽篱槿,咿哑转井车。
可怜高处望,棋布不曾斜。
二十
何处深春好,春深稚子家。
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
笑击羊皮鼓,行牵犊颔车。
中庭贪夜戏,不觉玉绳斜[3](P477)。
以“后出而转精”来评价刘禹锡的这组唱和诗,在我们看来是合适的。同样选择二十类人物来描写其深春时节各不相肖的生活形态,除了“执政家”“刺史家”与创作在前的白居易诗名目相同外,其余都属于另立名目者。当然,“大镇家”之于“方镇家”、“小隐家”之于“隐士家”,只是更易一字,人物身份没有明显差异,也可以看作同一描写对象。描写对象的重复,并不意味着艺术创造力的匮乏,而是由于题材及体裁的规定性。之所以重复,是因为这几类人物在“深春众生相”中是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将他们舍去,人物形象的长廊中就会出现空白或断裂。给相同的描写对象赋予不同的造型、留下不同的剪影、抹上不同的色彩,这恰恰是需要不随人作计的艺术独创能力的。
在没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既要在元稹的原唱外另辟蹊径,又要在白居易的和作外别开生面,可以说,刘禹锡的这组唱和诗在起笔时就面临着两头回避、双重超越的要求。而诗人同样受到用韵和取材的严格限制。这也就是说,除了既定的镣铐一副未减外,他的舞步还被压缩到更逼仄的空间,其翩然起舞的难度要超过了元、白。但他的舞姿却比元、白更为动人,至少一点也不逊色。如果把每一首都视为一个舞蹈单元,那么,几乎每一首都无意炫技,而自有引人瞩目、令人惊叹之处。
在分类上,刘禹锡的唱和诗吸取白居易的前车之鉴,摈弃了或按人物身份或按时令节序的多种标准,统一按人物的社会身份来划分。而且,他把笔触擢升至最高端,把白氏未敢触及的“万乘家”也纳入了刻划的范围,同时,为“少妇家”“稚子家”“幼女家”也专辟一席之地。这样,其所涉及的人物角色就更加纷纭复杂,其行为举止也就更加丰富多彩。
无论笔下的人物角色如何变换,作为其活动背景的“深春”是始终不变的。当然,不变的是“深春”这一时令,而不是“深春”的具体景色。如果景色也一成不变,笔力就过于孱弱了。事实上,诗人在描写深春景色时,极注意移步换形,在山重水复中,不断转出柳暗花明的新境界。第一首描写“万乘家”时,着力刻划的是“柳”“花”“暖风”,这些无疑都是深春时令的代表性意象。在以后的各首中必然还将多次出现,不可能用别的意象来完全取代它们。否则,就难以做到“春”意盎然了。同时,“花”又是必须采用的韵字,每首中都出现它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同样是“柳”与“花”,在不同的场境中亮相,可以呈现出迥不相犹的形态,焕发出别样的风采。要达成这一效果,除了每次都要对“柳”与“花”重新梳妆打扮外,还要精心设计其出场亮相的方式,为其配置新的背景板、聚光灯以及联袂登场的伴郎或伴娘。以“花”而言,第一首中是“辇路尽穿花”,第二首中是“株树正开花”第五首中是“庭树有名花”,第六首中是“绶结虎头花”,第七首中是“马色醉桃花”,第八首中是“雨甚亦寻花”,第九首中是“杏树满山花”,第十首中是“撼树去狂花”,第十二首中是“贵买色深花”,第十五首中是“自剪入时花”,第十七首中是“养蜜近梨花”,第十八首中是“高架引藤花”。或者花的种类有别,或者花的造型有别,或者养花的环境有别,或者赏花的人物有别,竭尽变化生新之能事。
诗人在描写过程中,既不脱“深春”二字,又始终紧扣人物的特定身份,以独有的、与其身份相对应的景物或行为加以显现,无不丝丝入扣,惟妙惟肖。如第一首描写“万乘家”:“宫门”映柳,“辇路”穿花,已显示出独一无二的皇家气象,而“池色连天汉,城形象帝车”,这种浩瀚无垠、吞吐帝都的气势只能属于天子。第二首描写“阿母家”:“瑶池”长明,“珠树”开花,一望便知是神仙世界专属的景象。着一“瑶池”,西王母的身份已隐然可见。而接下来的“通星渚”“近日车”更揭示了其宅第与星、日相伴的特殊地理位置,令人想见其超凡脱俗的“阿母”身份。尾联补曰“层城十二阙”,渲染其宫阙之巍峨远过于人间皇室,让读者确认其为仙家无疑。第五首描写“贵戚家”:“贵戚”,指皇帝的内外亲族。他们“枥”有无价之马,“庭”有名贵之花,享受着皇亲国戚的荣华富贵生活。“欲进宫人食,先薰命妇车。”他们还经常得到“入宫赐食”的恩宠。每当此时,他们总是先把享有“朝廷封诰”的女眷的香车熏染一遍,以更宜人的气息沐浴皇恩。仅此一笔,人物的特殊身份和特定性格便呼之欲出。“晚归长带酒,冠盖任倾斜”。宴罢归去时,他们习惯于带走几瓶御酒,用作骄人的资本,而其自身已是烂醉如泥,一任冠盖倾斜、斯文扫地。这也深得其仿佛。第十五首描写“少妇家”:这位时尚少妇能“偷”得最新的宫中乐曲,“剪”成最入时的各种花样,总是得风气之先。与同伴出游时,最喜爱的话题是评论豪车的价格。而其发型,不喜梳成“堕马髻”,而故作随意地任其偏斜,更添几分风韵。其追逐潮流、爱慕虚荣之心尽显字里行间。第十九首描写“种莳家”:“种莳”,指菜农。诗人笔下的菜农,精通所有的农活,“分畦十字水,接树两般花”,从灌溉到嫁接,无不得心应手。菜园的篱笆用槿枝编成,其整齐密集的程度犹如篦齿一般;井上的辘轳不停地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这就彰显出菜农的勤劳与心灵手巧。“可怜高处望,棋布不曾斜。”“可怜”,在这里是值得羡慕的意思。从高处望去,菜畦好似棋盘一样横平竖直,不见丝毫歪斜。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其身份的底色,凸显了“种莳家”的环境特征。
刘禹锡胸罗万卷,习于化用典故或前人诗文入诗。他曾在不少诗中自注用字来历和用典出处,以示并非自己的生造。据韦绚《韦宾客嘉话录》载,他还曾告诫后学:“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后辈业诗,若非有据,不可率尔造也。”这组唱和诗遣词造句也多有所本,显现出诗人对浩如烟海的典故及前人诗文的精熟及锻炼改造功夫。如第九首描写“羽客家”,看似寻常语,了无深奥处,其实大多有其出典:“芝田绕舍色,杏树满山花。”“芝”,指芝草,为传说中的仙草,本于《十洲记》:“东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生琼田中,或名为养神芝”。“杏树”,用董奉事:据《神仙传》载,董奉居庐山,不事田耕,每日为人治病,亦不取诊费,唯要求愈后病重者栽杏五株、病轻者栽杏一株。如此数年,累计得杏树十万余株,郁然成林。“云是淮王宅,风为列子车。”“淮王”,指西汉淮南王刘安。其人笃好神仙黄老之术,宾客甚众,其中苏飞、李尚、左吴、田由等八人被称为“八公”。八公聚其门下炼丹,炼成后,刘安吞服丹药与八公携手升天,鸡犬啄食余药亦随之飞升,遂留下“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神话传说。事见《水经注·江水》等。“列子”,指列御寇,为庄子寓言中的人物。《庄子·逍遥游》有云:“列子御风而行,泠然而善者也。”[4](P14)刘安、列子是“羽客”的标志性人物,以之入诗,题意不言自明,而又源自典籍,底蕴丰饶。又如第十首描写“小隐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处,但主要词句都有其源头:“醉酒一千日,贮书三十车。”明白如话,却有案可稽。上句语本干宝《搜神记》卷十九:“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5](P235)下句语本《晋书·张华传》:“雅爱书籍,尝徙居,载书三十乘。”[6](P1074)即使是“狂花”“有馀斜”这样浅白的词语,也渊源有自:“狂花”,指不结果实或早谢的花。《荀子·君道》云:“狂生者,不胥时而落。”[7](P235)庾信《小园赋》有“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句。“有馀斜”,谓斜而有余。典出《列女传》卷二:“鲁黔娄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见先生之尸在牖下……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焉。’妻曰‘斜而有馀,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有这般丰富的内容蕴蓄于其中,“有馀斜”三字貌似平常,实则乃苦思冥索而后得之。另外,诗人除了化用典故及前人诗文外,对时人诗句亦不吝点化。如第十二首描写“豪士家”,其中“贵买色深花”句便是点化奉和对象白居易《买花》的结句“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刘禹锡这组唱和诗对人物与景物的描写既是谨严的,力图有所依托的,同时也往往是生动的,不失活泼之趣的。诗人遗貌取神,摄录最能揭示人物性格、传写人物精神的生活片段,以出神入化之笔加以刻画,所选用的字词往往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如第三首描写“执政家”有句:“恩光贪捧日,贵重不看花”。一个“贪”字活画出手握重柄的“执政”迷恋权位、媚颜事君、贪心不足的形象。第四首描写“大镇家”,颔联云“前旌光照日,后骑蹙成花。”颈联云“节院收衙队,球场簇看车。”“蹙”字与“簇”字前后勾连、相互支撑,精准而又灵动地映现出物态人情。第二十首描写“稚子家”用笔更见生动:“争骑一竿竹,偷折四邻花。笑击羊皮鼓,行牵犊颔车。”“争骑”“偷折”“笑击”“行牵”云云,都十分传神,把稚子们活泼好动、顽皮成性、喜欢出风头、偶尔还恶作剧的天真模样表现得活灵活现。
由于此时的刘禹锡身居庙堂之中,虽然宦况清冷,升迁无望,处境终究比辗转流徙于巴山楚水时有了很大改善,同时,为了避免与白居易重复,在描写对象中,他已经剔除了“迁客”“学士”等敏感人物,因此,在这组唱和诗中较难觅得身世之感和怀旧之情。不过,某些篇章还是融入了他自己的生活体验的。如第八首描写“刺史家”说:“夜阑犹命乐,雨甚亦寻花。傲客多凭酒,新姬苦上车。”夜深时分还在聆曲听歌,那是因为心有慊慊,难以安眠,只好藉由“广陵散”之类的天籁之音来消磨光阴。大雨滂沱之际,依然外出寻芳,那是出于强烈的惜春爱花之心,担忧自己的政治前程也和春花一样被“雨打风吹去”。在客人面前负酒使气,一醉方休,那是想借助酒力来消释胸中块垒,麻醉痛苦的心灵。新来的歌姬献艺方罢,便又登车而去,那是不耐遐荒生活之清寒,反衬出刺史境况之难堪。类似这样的写真笔墨,若无长期的亲身体验,是很难描写到位的。
然而,依韵唱和之作固有的弊端在刘禹锡这组诗中同样未能绝迹。为了撑足二十首的篇幅,不得不强自敷衍,凑泊成篇。“贵戚家”“贵胄家”“富室家”“豪士家”“恩泽家”等名目不同,内涵却十分相近。虽然诗人在分别描写时煞费苦心地显示其差异,措辞及画面也的确没有雷同之处,但区分过细,必然带来实质性内容的交叉,使本该非此莫属的描写趋于宽泛化。说得更直接些,将“贵胄家”与“富室家”的内容互换,一点也不会影响其艺术效果。这就意味着,有些篇章本来是可以合并的,之所以拆分恐怕是要凑足篇幅的缘故。与此相应,在韵字的使用上,则和元、白一样存在削足适履的情况。诸如“婴孩锦缚车”“身轻不占车”“不敢径由斜”“村落逐原斜”之类,大概都属于扭曲其意、伧俗其辞以就其韵。当然,这方面的弊病似较元、白为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