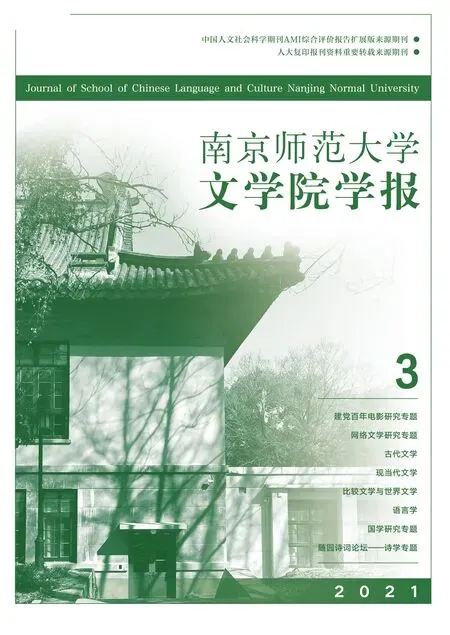论文化艺术通才李渔
沈新林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
明末清初的文化巨子李渔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文化艺术通才。他聪明博学,淹贯百家,学富五车,却命运不济,科举之路崎岖坎坷;又身处明清易代之际,传统而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教育堵绝了他改换门庭的道路,于是,他只能选择“卖赋糊口”的道路。由于受时代风气的熏染,他“少不宜男”,不断娶妾添丁,家庭人口众多,生齿日繁,仅仅靠“卖赋”(写文章)尚不足以“糊口”,于是他闯荡江湖,独辟蹊径,寻找突破,不断创新,千方百计向其他领域进军,涉及到园林建筑、编辑出版、巡回演戏、琴棋书画、烹调美食、休闲养生、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古人云:时势造英雄,逆境出人才。这样的历练,使他不仅成为古代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专业作家,而且锻造成为一代卓绝的文化艺术通才。
一
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有所建树,是必须的,也是能够实现的,大多数人可以做到;如果要在几个方面同时有所建树,那就不太轻松,实属不易,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到;而要成为一位文化艺术通才,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唐代的山水田园诗人王维,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而且精通音乐、绘画。宋代的苏东坡,诗词文俱为大家;还精通音乐、绘画,又是书法巨擘,可以称之为文艺通才。明代的徐渭是一代怪才,善书画、工诗文,精戏曲,自称“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其书法、绘画的造诣登峰造极,空前绝后;又擅长杂剧创作,其杂剧作品“为明曲之第一”;难能可贵的是,他又有研究南戏的理论专著《南词叙录》;他还能谋阵布局,带兵打仗,常常出奇制胜,谙熟军事文化,称之为文化通才,名副其实。晚清的刘鹗,少精数学,后学医术,再业商贾,又擅长治水;不仅创作小说,而且精通音律以及诗、书、音乐;对于金石文物考据颇有造诣。……比较而言,清初的李渔才是一个文化史上十分难得的集大成的通才。
通才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辞海》释义:“谓通晓一切,其才足普遍适应者。”并引宋之问诗“试剧仰通才”。窃以为,一个人对某一领域所有的分支,基本能够掌握,或者至少掌握大部分,并且都能取得不俗的成就,才可谓之通才。李渔说:“才兼六艺称通儒”[1](P53);六艺,《周礼》谓指礼、乐、射、御、书、数;《史记》则指易、礼、乐、诗、书、春秋;这里“六艺”显然是泛指多种技艺。李渔还在《耐歌词》自序中说“凡士有不能诗者,则为通才所鄙”[1](P377),这可以说明,诗才是通才的必要条件。
汪裕雄《艺境无涯》云:“宗白华以睿智的目光巡视整个艺苑,论及的艺术门类包括诗歌、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剧、园林、建筑和工艺美术,他不仅能对每一门艺术发表深刻独到的见解,而且能够发掘各门类艺术间的相通之处,进而揭示艺术理想的文化哲学底蕴,在20世纪中国美学界,能作此通观者,唯宗白华一人而已。”[2]仔细揣摩这一段文字,我们惊奇地发现,美学家宗白华所论及的诸多艺术门类,基本无不为李渔所染指。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巧合吗?显然不是。宗白华(1897-1986)是现代著名美学家、作家,祖籍江苏常熟虞山,出生于安徽安庆,八岁起在南京生活学习,后毕业于同济大学;1920年赴德国留学,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学习哲学、美学等课程,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他学贯中西,主要著作有《宗白华全集》,美学著作有《意境》、《美学散步》等,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将中国体验美学推向了极致。
这实际上包含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也是令人深思的课题。早在四百年前的李渔,不仅是文化艺术通才,而且高瞻远瞩,眼光独到,看到了艺术门类之间的联系,能宏观地把握艺术哲学。这一现象无疑可以说明,明末清初的李渔与三百年后的宗白华对于艺术门类的划分,见解基本是一致的,其美学观点惊人相似。宗白华和李渔有共同的文化背景、知识积累和生活体验,宗白华的原籍常熟与李渔出生且生活过二十多年的如皋仅一江之隔,分别处于长江下游入海口的南北两岸,隔江相望,二人都是饮长江水长大的,从小既感受到滔滔江水的温柔多姿,仪态万方,又领略到东方气象万千的海洋壮观:巨浪的奔腾飞溅,波涛的汹涌澎湃。那里的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容易接受外来信息。二人又都有在十朝古都南京的多年生活经历。相同的自然景观、文化背景、人文信息给他们共同的启示。当然,李渔不仅是美学家,而且是文化巨人。他的事业超越了纯粹的艺术领域,应该属于文化范畴。但艺术又是文化的最重要的支柱,仍然属于李渔所从事的主要文化产业门类。
二
李渔从事的主要是文化艺术产业,包括艺术和文化的诸多领域,其门类繁多,现简要分析如次:
李渔的文学创作,作品繁富,门类齐全,以小说、戏曲成就为最高;而诗歌则是他最早创作的文体。其诗文主要见于《李笠翁一家言》,广义的诗歌包括诗、词、曲,乃至戏曲。古人称词为诗余,曲为词余,戏曲为曲,其源盖出于此。李渔最早创作的诗歌曾刻于早年在如皋亲手种下的梧桐树树干上:《续刻梧桐诗》可视为他最早创作的作品。明季的李渔以诗闻名。他一生创作诗歌一千多首,填词三百余阕。其他还有戏曲十种,见于《笠翁十种曲》。其诗词大多为应酬赠答的游戏之作,但也有少量反映改朝换代的现实,记录艰难时事的好作品。如七言律诗《吊书四首》,其一云:
将军偶宿校书台,怒取缣缃入灶煨。国事尽由章句误,功名不自揣摩来。
三杯暖就千编绝,一饭炊成万卷灰。犹幸管城能殉汝,生同几案死同堆。[1](P161)
反映战争毁灭文化,动乱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再如,面对清朝的剃发令,他赋七言绝句《薙发二首》,其一云:
晓起初闻茉莉香,指拈几朵缀芬芳。遍觅无复簪花处,一笑揉残委道旁。[1](P325)
幽默诙谐的诗句中包含了微妙的感情,其中的爱国思想、民族意识隐约可见。如此等等,可窥一斑。
他的散文,包括赋、序、记、传、赞、书等三十多种应用文体。李渔主张写作要随物赋形,内容决定形式,所以,他是古代运用文体最多的作家。《一家言释义》(自序)云:“凡余所为诗文杂著,未经绳墨,不中体裁,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为一家,云所欲云而止。”[3](P4)作者声明《一家言》是独出心裁、有感而发的个性化的文字,诚如他自己声称的“不佞半世操觚,不攘他人一字”。现代文化大师林语堂云:“笠翁才思超逸,事事自发机杼,《一家言》无一句抄袭人家,故写出必是个人笔调,而因此笠翁之文,至今无一篇不读得”。(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见《语堂文集》下)。
李渔的戏曲创作有《十种曲》传世,以喜剧居多,他是专擅喜剧创作的戏曲家,以《风筝误》为代表作。其友人石鲸《柬李笠翁》书云:“《怜香》《风筝》诸大刻,弟坐卧其中旬日矣。丹铅密匝,评赞如鳞,每食必借以下酒。昨者偶失提防,竟为贪人攫去,不啻婴儿失乳。敢向左右再乞数册,以塞无厌之求。”[4](P28)清代戏曲家黄周星云:“近日如《李笠翁十种曲》情文俱妙,允称当行。”(黄周星《制曲枝语》)清乾隆时期的文人李调元说:“李笠翁渔工词,所著《十种曲》如景星卿云,争先睹之为快。余家有歌伶,皆令搬演。”(李调元《雨村诗话》)光绪时期曲论家杨恩寿云:“《笠翁十种曲》意在通俗,故命意遣词,力求浅显。究其位置角色之工,开合排场之妙,科白打诨之宛转入神,不独时贤罕于颉颃,即元、明人亦所不及,宜其享重名也。”(杨恩寿《词余丛话》)而《清朝野史大观》则评说道:“笠翁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不欲摹而摩不出之情,绘人不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摛句,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陈者出之为新,腐者经之而艳,平者遇之而险,板者触之而活。不独此也,结构离奇,变化令人莫测。事之真者能变之使伪,伪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贴服而归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能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故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近代戏曲大师吴梅认为:“清人戏曲大抵顺康之间以骏公(吴伟业)、西堂(尤侗)、又陵(徐石麒)、红友(万树)为能,而最著者厥推笠翁。翁所撰述,虽涉俳谐,而排场生动,实为一朝之冠。继之者唯有云亭(孔尚任)、昉思(洪升)而已”[5](P176);他又说:“翁作便取梨园,本非案头清供。科白之清脆,排场之变幻,人情世态摹写无遗,此则翁独有千古耳。”[5](P191)。他将李渔戏曲与《桃花扇》、《长生殿》相提并论,颇有见地。李渔戏曲的创造性、艺术性得到准确的评价、充分的认可和高度的赞扬。
李渔的戏曲创作实践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完善了古代戏曲文体概念的内涵,针对前人戏曲创作重曲轻戏的倾向,他力求戏曲并重,加重了戏的分量。具体说就是重视宾白的创作。卢冀野《中国戏曲概论》云:“以前的作家是偏重曲的,他却偏重戏字。”这一发现举重若轻,极富见地,有振聋发聩之功。其实,李渔是通过创作实践纠正了过去重曲轻戏的偏向,看上去似乎偏重戏的成分多了,其实他的主张是戏与曲两者并重。绵延数百年重曲轻戏的偏向得到了纠偏,也带来古代戏曲的黄金时代,出现了古代戏曲的高峰性作品。可惜学术界对此的评价不到位。其后的洪升《长生殿》、孔尚任《桃花扇》与李渔《风筝误》堪称古代戏曲的巅峰性作品。日本学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云:“故《十种曲》之书遍行坊间,即流入我邦者亦多,德川时代之人,苟言及中国戏曲,无有不立举湖上笠翁者。”[6]。李渔的戏曲早在清乾隆朝就流传到海外,走向了世界,赢得了美誉。
李渔的小说创作有白话短篇小说集《十二楼》《无声戏》(《连城璧》),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十二楼》包含十二个中短篇小说,每篇都有一座楼,皆以楼命名。《无声戏》(一名《连城璧》),包含十八个短篇。其短篇小说的特点是故事新颖,情节曲折离奇,趣味性强。其友人李一贞《柬李笠翁》书云:“焚香啜茗,拂几静閲《无声戏》,大则惊雷走电,细亦绘月描风,总人间世未抽之秘,不啻駭目荡心已也。昔人云,施耐庵《水浒》成,子嗣三代皆喑。仆甚为足下危之。虽然旁引曲喻提醒痴顽,有裨风教不浅,岂破空捣虚辈可同日语也。国门纸贵,信然信然。”[4](P29)小说研究大家孙楷第说:“笠翁毕竟有才,毕竟有创造的能力。在笠翁小说,是篇篇有他的新生命的。”[7](P346)“我们看他的小说,真觉得篇篇有篇篇的境界风趣,说到清朝的短篇小说,除了笠翁外,真的是没有第二人了。”[7](P370)“求短篇小说于清代,除笠翁外,亦更无人。”[7](P374)。
李渔的绘画艺术成就首推《芥子园画谱》(亦称《芥子园画传》)。他晚年构思酝酿,主持倡导编写,身后出版的《芥子园画谱》,是一部供学画者自学的范本性技法教科书,是学习绘画的启蒙读物。《画谱》初集,包括卷一树谱、卷二山石谱、卷三人物屋宇谱、卷四名家山水画谱;二集以竹、兰、梅、菊各自编为一卷,共四卷;三集以草虫花卉、翎毛花卉、模仿诸家花卉翎毛编成四卷。全书十二卷,共设有画图浅说九种,基本技法二十一种、七十三式。举凡人类社会、大自然典型事物,均委曲周详,无体不备。还详细介绍了王维、米芾、苏东坡、马远、黄公望、李唐、王蒙、吴镇、朱彝等近百名历代书画名家的技法特色。《画谱》面世之后,作为绘画教材,取得了广泛的效益,得到社会高度的美誉。齐白石、潘天寿、陆俨少等许多著名画家均得益于《芥子园画谱》,后来其成就才攀上艺术高峰。清代画家余椿赞誉《画谱》“如暗室一灯,……真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8](P227)李渔则称《画谱》为“不可磨灭之奇书”,良有以也。
李渔本人也有绘画作品,他在《芥子园画谱》序言中曾说“余生平爱山水,但能观人画,而不能自为画。”这包含有自谦的成分,但他的画作确实流传不多。笔者经眼的有:一是《沧浪濯缨图》,立轴,画面有大山、树木、山谷、野草、流水、瀑布,并自题七绝一首,后两句“莫笑野人生计少,濯缨随处有沧浪”,含蓄地点明了画作旨趣;盖有两方小型印章。诗书画珠联璧合,相映生辉。可惜该题画诗未见于《笠翁诗集》。二是《墨梅图》,南京艺兰斋美术馆收藏。立轴,上诗下画;画面古拙简朴,老树新花,一枝独秀,超然物外。诗为草书五律,尾联“色连千嶂月,香散一帘风”。钤有两方印章“李渔”“笠翁道人”,落款是:“甲寅春日李渔”。字体飘逸老到,书画相映成趣。该题画诗亦未见于《笠翁诗集》。三是《山居读经图》,立轴,画面群山起伏连绵,悬崖怪石,松树苍劲,树下有一陋室,室中有人正襟危坐,专心读书。画右上方题“康熙十八年晚秋,李渔”。钤有“笠翁”印。四是《山水人物图》,立轴,画面有山水、树木、亭台、人物。山上有亭,亭中有人对弈赏景。山下道路蜿蜒曲折,道旁行人相互拱手问候,亲切交谈。画右上方题“癸卯秋九月写似芝麓大宗伯玄粲,湖上笠翁题”。钤有“笠翁”印、“湖上笠翁藏”印、“灵岩山人秘籍”印。五是《李渔山水人物四段卷》上海博物馆收藏,是近几年发现李渔的作品。包含四幅山水人物画,为写意画。其一《扬帆载月图》,其二《拍蝶图》,其三《蕙兰图》,其四《山水图》。画面立意高远,情趣古雅,生活气息浓郁,画面配有楷书题诗,诗书画相互发明,含蓄雅致。考其内涵意蕴,当为晚年所作。画作一经发现,便被誉为极为难得的佳作。可见李渔画作虽然不多,皆可称为传世精品。
李渔的书法功力深厚,行、草、隶皆有佳作。其隶书有《芥子园画传序》、《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言》。篇幅较长,布局美观,字迹工整、运笔有力、笔画匀称、炉火纯青。方家称其“整齐秀美,浑厚清丽”[9](P98),李渔被书画界誉为“笔法圆浑,浇淳散朴,是个隶书造诣极高的书家”(赵文卿《李渔研究麟鳞集》)。前几年新发现的竹刻对联“江湖归白发,诗画醉红颜”笔力遒劲,古色古香,拙中见雅。有行书“湖上笠翁李渔”的落款,上下联各有两枚印章,分别是“老桂山房” 、“系结陇西”、“湖上老鱼”、“笠翁”。现藏浙江兰溪市芥子园国际李渔研究中心。其草书,笔者经眼的作品一幅为立轴,上有李渔题款,下方有三方小型印章,左下角有李渔签名。用笔粗犷有力,率性随意,如天马行空,笔走龙蛇,漫不经心,亦如行云流水。字与字相对独立,互不连属,既富有独立的个体美;又显示出整体的和谐美。另一草书作品则为扇面书法,字体古拙,后有“李渔”落款署名。其他还有行书,曾有《李渔手札》一通寓目,小楷行书,写在竖行专用信笺上,挥洒自如,削瘦美观,柔中见刚,颇见骨气,极为养眼。书札提到“昆山二太史”“野老入都”云云,符合李渔口吻。此书札未见于《李笠翁一家言全集》,恐为遗珠一枚。
关于金石印章篆刻,李渔有专著《芥子园图章会纂》。原手稿分文字、图章两部分,文字35页,图章52页。其专论亦收录于《李渔全集》卷十八,分为三部分:一是述古印说,包括印学、章法、笔法、刀法、印的名称、篆刻秘诀等。二是续纂印论,包括论章法、论印体、论纂病、论印病、论刀法,以及刀法总论。三是附录理涂八法:研朱、揉文、取油、配合、加金、盥涂、盖印和藏护。《芥子园图章会纂》兼采诸家之长,并有所取舍选择,不仅系统地阐述了篆刻理论,而且表现了李渔治印的方法、经验及其审美追求。内容丰富,分类明细,言简意赅,说明到位,可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刘聪泉《东皋印学》评云:“可以说,这是中国篆刻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性著作,对其后几个世纪中国篆刻艺术的影响不言而喻。”[10](P363)
李渔设计制作的工艺美术品,有芥子园锦笺、韵事笺,等等。李渔经营芥子园书铺期间,精心制作的芥子园锦笺,深受市民喜爱,誉满金陵。“已经制就的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韵事者何?题石、题轴、便面、书卷、剖竹、雪蕉、卷子、册子是也。锦纹十种,尽仿回文织锦之义,满幅皆锦,止留瀫纹缺处代人作书。书成之后,与织就之回文无异。十种回文各异,作书之地亦不雷同。”[11](P210)针对当时的盗版现象,李渔宣称:“唯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不许他人翻梓。”[11](P210)这是李渔独创设计的工艺美术品,美观而实用,当时畅销全国各地。
李渔的音乐舞蹈,戏曲活动。李渔在康熙初叶以乔、王二姬为骨干,组建了家庭戏班,周游全国十多个省分,巡回演出,以戏会友,获取演出报酬,或者争取达官贵胄的资助,解决全家的生计。他家班演出的剧目,不仅有他本人创作的戏曲,还有传统戏剧名篇的片断,而且也有歌舞表演。他的七律诗《舟泊清江,……是夕外演杂剧,内度清歌》,就是明证。李渔本人集戏曲的编导于一身,又是戏曲活动家,家班剧团巡回演出范围很广,地点遍及长江、黄河流域的十多个省分,北至京都,南至两广福建,西到甘肃西部。
李渔的园林建筑:他自己先行先试,早年在原籍兰溪营构伊园,小试牛刀,粗具规模;中年时期构建的金陵芥子园,北京半亩园,则大显身手,其事业如日中天,最为辉煌。晚年营造的杭州层园则是夕阳晚照,落日余晖。营建园林居室的艺术实践贯穿其一生,成为熠熠生辉的闪光点,其中以芥子园为代表。芥子园最大的特色就是小、巧、雅;芥子意为芥子纳须弥,谓小中见大。“芥子园之地不及三亩,而屋居其一,石居其一,乃榴之大者复有四五株。”[11](P249)“后有小山一座,高不逾丈,宽止及寻,而其中则有丹崖碧水,茂林修竹,鸣禽响瀑,茅屋板桥,凡山居所有之物,无一不备。”[11](P158)还有一尊神气宛然的笠翁手执纶竿,端坐石矶,临水垂钓的塑像,为芥子园平添无限生机和诗情画意。他晚年在杭州西湖边营构的层园也自出手眼,别有洞天。后人评云“筑芥子园(应为层园)于铁冶岭上,凡门扇、窗牖、匾额、对联,皆独出新意。即起居服用之物,亦多异寻常。其制度备载《闲情偶寄》中。”(陈景钟《清波三志》)。其他,还有代人设计建筑的园林作品,如北京半亩园、惠园等传世。鳞庆《鸿雪因缘图记》云:“半亩园在京都紫禁城外,东北隅弓弦胡同内,延禧观对过。园本贾胶侯中丞宅。李笠翁客贾幕时为葺是园,垒石成山,引水作沼,平台曲室,奥如旷如。易主后,道光辛丑,始归于余。”[12](P333)钱泳《履园丛话》云:“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 “忆昔嘉庆辛未(1811年)余曾小饮南城芥子园(在韩家潭)中,园主章翁言,石为笠翁点缀。当国初鼎盛时,王侯邸第连云,竞侈缔造,争延翁为座上客,以叠石名于时。内城有半亩园二,皆出翁手。”[12](P332)。南城芥子园就是京都芥子园,加上一所惠园、二所半亩园,可见李渔在京师的园林作品至少有四、五座之多;他的园林创作实践有许多已不可考索。总之,李渔的园林创作虽然遗存不算多,如吉光片羽,但在中国园林建筑史上仍然享有一席之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一家言居室器玩部》“识语”云:“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笠翁乃欲于规矩之外,更与人巧。”现代建筑大师童隽《江南园林志》称李渔为“真通其技之人”[12](P349)。
三
从文化角度看,李渔的建树在文学艺术之外,其他方面还有不少,论述如次。
首先,理论研究是李渔一生文化事业的重大建树。《闲情偶寄》是生活艺术的百科全书,该书理论价值最高的部分首推其中的戏剧创作论和戏曲导演论。戏剧创作论的贡献在于:重视创作构思,提出“结构(即构思)第一”的观点,注重戏曲真实,在戏曲审美方面提出“奇”的审美标准,主张戏曲语言尖新、浅显、机趣,对戏曲音律提出具体要求,具有完整的体系,堪称古代戏曲创作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戏曲导演论包含选择剧本,导演构思,物色演员、口授身导等几方面,具有实践性、系统性、创造性,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演学著作。此外,还有史论,他著有《论古》一书,称《笠翁别集》,收入《李笠翁一家言全集》。内有史论一百三十余则,一事一议,篇幅短小,多有新见。其特点是,古为今用,举一反三;标新立异,自出机杼;予夺前人,曲直往事,敢于疑君疑古,善于知人论世;见微知著,富有文学色彩。其史论富有超出常人的瑰丽色彩。王仕云叙《笠翁论古》云:“有笠翁之论断,可以持国是,可以正人心,可以誉千秋而权万古。”[13](P306)当然,其历史观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李渔平生擅长理论总结,其他还有词论、印论、文学评点等传世。
其次,李渔的编辑出版事业成就斐然。李渔在康熙初期首创的芥子园书铺,几易其主,到道光年间还在出书,延续了二百多年历史,成为清代为数不多的老字号书坊。其经营特点鲜明,一是出版通俗文学为主;二是坚持质量第一的出版宗旨;三是注意经济适用,读者至上;四是运用广告宣传,扩大销路。芥子园曾经出版过“明代四大奇书”、《西厢记》、《芥子园画谱》等一批名著。芥子园出版的书都能注意迎合读者口味,多有创新,曾设计出版了便于携带的袖珍本、图文并茂的插图本。黄摩西《小说小话》载,曾见芥子园“四大奇书”原刊本,纸墨精良,尚其余事。每回作一图,卷首人物如生,细入毫发,远出近时点石斋石印画报之上,而服饰、器具尚见汉家制度云云。(见《小说林》第二期)现在海内外各大图书馆都把芥子园书铺出版的书籍作为珍稀版本和善本书收藏。
再次,旅游文化有所成就。因为一生经济拮据,李渔基本没有主动的旅游,但李渔毕竟是高雅的文化人,善于欣赏山水古迹。他经常接受朋友邀请出游,或者在巡回演出途中,经过一些旅游景点,他带领家班顺便旅游,是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他前往兰州途中,经过华山,便携家姬攀登华山探险揽胜,在半山腰的青柯坪上搭台演戏,并赋诗留念,成为古今天下奇事美谈。仅从他的诗词、对联可以看出,扬州瘦西湖、平山堂、二十四桥,金陵的夫子庙、石头城、观音阁、关帝庙、莫愁湖、燕子矶,北京的著名景观,西岳华山的莲花峰、玉女峰,形势险要的潼关,桂林山水,钱塘江潮,高邮露筋祠,激流险峻的十八滩、分水龙王庙,大庾岭,会稽大禹陵、越望亭,武昌的黄鹤楼、晴川阁,汉阳的吴王庙,九江的陶白二公祠、庐山胜境,杭州西子湖,苏州拙政园,虎丘剑池、千人石、寒山寺,金华仙霞岭、五显岭庙、宝婺观,镇江的金山寺,长江中的大、小孤山,富春江上的严陵钓台,等等,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以及诗篇、墨宝。他饱览胜迹,浮想联翩,文思泉涌,诗兴大发,遂操觚染翰,挥笔成章。他的许多诗、词、文赋、对联等作品,赞颂了祖国千姿百态的壮丽山河、名胜古迹,弘扬了绚烂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大大丰富了古代旅游文化的内涵。
复次,家庭教育卓有成效。李渔擅长教育,他的儿子、女儿、女婿,都由他一手教育成才。李渔在康熙己未仲冬题于吴山层园的《千古奇闻序》云“予课儿之暇,即以课女。”这可以说明,李渔的子女是自己亲手教育的。李渔五男三女,大多由自己手把手教育成人。他在家庭教育方面用力最多的是对长婿沈因伯的培养。沈因伯聪明伶俐,幼年失怙,与祖父相依为命,慕李渔之名,拜李渔为师,后来登堂入室,成为李渔的乘龙快婿,长期帮助李渔代司家政,并成长为李渔的唯一传人。有材料表明,李渔转让芥子园之后,沈因伯还帮助芥子园书铺继续出版过《芥子园画谱》等书籍,并自称“芥子园甥馆主人”,成为芥子园书铺的主持人。[13](P157)至少在编辑出版方面,他成为李渔名副其实的传人。此外,李渔对乔、王二姬的教育,用力尤勤。乔、王均于十三岁先后进入李渔家门,经过悉心调教,两个普通民女成长为著名的昆曲表演艺术家,成为李渔家班的主要角色。乔、王二姬的天赋和勤奋自不待言,李渔的教育培训也功不可没。可以说,李渔对于她两的人生角色转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乔、王二姬先后在十九岁上夭折的弥留之际,一个焚香告天,谓得侍才人,死可无憾,但惜未能偕老,愿以来生续之;一个声称“生卧李家床,死葬李家土,此头可断,此身不可去也”。[14](P99)这似乎令人匪夷所思。“推其本念,究竟出于怜才”。[14](P100)可以说,艺术家之间的心灵相通,就是她俩对李渔的爱情生死不渝、无以复加的根本原因。李渔主张“优师”必须“明理”,懂得教书育人的规律;他善于把握教学的重点与难点,要言不烦,简明扼要,“不数言而辄了”。教学方法灵活多样,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常常通过诗词唱和、校点编订、携同出游、个别指授、函授批阅、评点著作等方式,培养人才。李渔不能算是教育家,但他在生活实际中注意教育后生,他的教育方法多种多样,并不拘泥于一般的教授识字作文,改变了简单的师徒结对教学的古板模式。这在古代教育史上是值得加以总结的现象。
又次,烹调美食经验丰富。李渔不相信“君子远庖厨”的古训,他不仅善于写作,妙笔生花,而且精于烹调艺术,制作八珍面、五香面、花露饭等,美味可口,闻名遐迩,为世人津津乐道。《闲情偶寄 饮馔部》有详细论说,他论饮食,先蔬后肉,“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其出发点一是节俭,二是复古。他总结了古人的饮食规律和养生之道。吃什么?“食之养人,全在五谷。”怎么吃?蔬菜讲究味道鲜美;竹笋凉拌最佳;吃螃蟹要自任其劳,旋剥旋食才有味,等等。如何烹调美味食品?首先,择菜洗菜,“摘之务鲜,洗之务净”;其次,烹调有法,做饭的关键在加水和火候,“粥水忌增,饭水忌减”;制作糕点的秘诀“糕贵乎松,饼利于薄”;面条制作“拌宜极匀,扞宜极薄,切宜极细,然后以滚水下之”。烹调菜肴要掌握要领,“煮冬瓜、丝瓜忌太生,煮王(黄)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酱醋而不宜盐,煮芋不可无物伴之。”“鱼则必须活养,候客至而旋烹”;“煮鱼之水忌多”;“更有制鱼良法,则莫妙于蒸”,等等,都来自于烹饪实践,具有可操作性(本节引文均见《闲情偶寄 · 饮馔部》)。他还对《左传 庄公十年》“曹刿论战”中的名句“肉食者鄙”提出新见:“食肉之人之不善谋者,以肥腻之精液,结而为脂,蔽障胸臆,犹之茅塞其心,使之不复有窍也。”[11](P226)并以老虎食肉,只能直行,不食小儿,头脑简单等为例,加以说明,似乎不无道理。这可以证明“穷而后工”,“逆境出人才”的哲理性。此外,他终身不食牛犬,只由于牛能耕田,犬能守户,有功于人类。这在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亦属难能可贵。由此可见,李渔的饮食文化内涵丰富,具有强烈的个性色彩。
最后,休闲养生,初见成效。他出生于医药之家,伯父是医生,父亲从事中药销售,因此他粗通医药之道。他更明白防重于治的道理,重视休闲养生。历史上把休闲养生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来看待的,首推李渔。李渔一生闯荡江湖,奔波劳碌,不得休闲,却很注重休闲,向往休闲。古人云:“忙世人之所闲者,方能闲世人之所忙者”;“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他对休闲文化颇多研究,帮助别人休闲,乐此不疲,并进行深入思考,以之为产业。他主张休闲先要闲心;休闲的方法因人而异,且应该因时间、地点不同而灵活选择。他的休闲方法可以梳理为数端:在注重物质享受,享受美食的基础上,首先讲究精神享受,鼓吹男欢女爱;其次凭借五官接受信息,通过观花、赏月、听鸟等以愉悦身心;又次身任微劳,节其劳逸,修身养性,如琴棋书画、栽花种草、把玩古董、放风筝、垂钓、读书写作、清谈、游戏、旅游观光、居家独处,等等。不同的人可以做不同的选择,这是科学的休闲之道。
其他,李渔还有发明创造。李渔是一个业余发明家,他津津乐道的梅窗,就是他把枯槁梅树的天然树干分成两半而进行设计创造,而加工制作出来的窗户,五香面加五种佐料、八珍面加八种美味、花露饭有桂花的幽香、笠翁椅冬天可以取暖、借景法能够移步换形,等等。这些小发明,虽然属于雕虫小技,但即使在今天也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此外,还有古董把玩、服装剪裁、美容化妆等方面的发现,相对次要,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李渔在文艺领域,是名符其实的通才。不仅如此,在艺术之外的文化领域,他也颇多建树,可以称为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杰出通才。如果把历史文化名人的终身成就分门别类,进行分析评分,再加以累计,那么,李渔肯定得分最高。
四
为什么一个杰出的文化艺术通才出现在明末清初?一个经天纬地的文化艺术通才又是如何打造出来的?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我以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可缺一,中国历史上最卓绝的文化艺术通才只能是出生于明末,成就于清初;只能是闯荡江湖,纵横天下,又主要活动于长江流域、吴越之间的落第秀才李渔。
首先,天时。对于博雅素养的空前推重,盖起源于明代中后期下层知识分子学风的转变。宋元以降,程朱理学被定于一尊,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到了明代中期,终于受到以李贽“童心说”为代表的进步思潮的挑战。知识界掀起一股声势浩大的博学之风,形成了强大的思想潮流。其实,博识、博物的核心内涵就是通识、通才。要求知识阶层博物洽闻,学识渊博,学以致用。追本溯源,博学本是儒家标举的价值观之一。到明代中后期,拟话本小说《三言》、《二拍》,人情小说《金瓶梅》、浪漫抒情戏曲《牡丹亭》等等重要作品的相继出现,通俗文学的各种文体才算发展完备,从而臻于成熟。通才,顾名思义,首先要熟悉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所以,清代之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主要文体还没有充分成熟和完善,那也就不可能出现名副其实的真正通才。因为各种艺术门类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存在着共同的艺术规律,才使得文艺通才的横空出世成为可能。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到清初,古代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才臻于健全和成熟。艺术种类本来繁多,五花八门,但其中具有共同的内在规律。比如,诗、词、曲同源,都属于诗歌艺术,都讲究音韵、格律、含蓄、雅洁,都可以吟唱,具有较多共同的美学特征,所以古人视诗余为词,词余为曲,故词又称为诗余;曲又称为词余。小说和戏曲两种文体也是同源异派,大同小异,相互影响。李渔直接把他的小说集取名为“无声戏”,他认为,小说是无声的戏剧,戏剧是有声的小说。此论虽不完全正确,但也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的观点。再说诗、画之间,苏东坡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志林》),他的眼中,诗画具有相同的美学元素,诗画交融,诗情画意,难解难分。他还有诗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苏东坡诗《韩干马》)。为何苏东坡乐此不疲,反复宣讲诗画之间的联系呢?因为只有苏东坡等这类诗画兼通的文化人才能看出诗画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是宋代的文化艺术通才,具有艺术家的眼光,这是他的天然秉赋与艺术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技能。
其次,地利。清代学者阮元说过:“孔门之学,首在于博。”[15](P3)近代学者刘师培也说:“孔门之论学也,不外博、约二端。”[16](P16)其次序是先博而后约,由博返约。而程朱理学却舍博言约,造成束书不观的陋习和流弊,制约了士子的成长和成就;势必遭到抨击和扬弃。明代博学风气之盛又以经济发达,文化积淀深厚,交通便捷的吴中地区知识分子群体最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台湾学者龚鹏程《晚明思潮》第十章云:“明代学者自有博雅一派,……若胡应麟、王世贞、杨升庵等,皆其人也。而苏州地饶多贤,俗好博雅,尤为当时之特色。……吴中学者往往兼治经史子集,旁及小说、释老,与当时复古派如李梦阳等不读唐以后书途辙固殊;与理学家之好谈性理,束书不观者,亦复异趣。”[17](P291-292)可见知识分子博览群书是晚明时代的潮流和风气。
另一方面,李渔长期居住、生活在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如皋、杭州、金陵等地,这些地方是鱼米之乡,人文荟萃,文化繁荣,文化古迹众多,文化积淀深厚,图书资料丰富,文化产业门类齐全,交通四通八达,往来便捷,这些地缘因素也为李渔提供了有利条件。恰逢其时的李渔虽然出身于商人家庭,但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成年之后,又长期在金华、杭州、金陵等大都市谋生,时常与许多文化名流交往,包括号称“江左三大家”的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以及王士祯、周亮工、杜于皇,余怀、尤侗、施润章等著名文化名人,其中不少人就是活动在金陵、松江、苏州、杭州一带,他与吴中地区读书人直接和间接的交往甚多,龚鹏程在《晚明思潮》中隆重推出的明代博雅派大儒胡应麟,就是李渔的原籍浙西兰溪人。他中年时期在金华当幕僚,企望博取异路功名;又在兰溪隐居三年多,希图走终南捷径。虽然两次都没有成功,但他对社会本质加深了认识,肯定受到了时代风气的熏染。此外,李渔中年以后,带领家班女戏巡回演出,以戏会友,以戏谋生,时间长达六七年之久,海内之地,涉足大半,北至北京,南至两广;西至甘肃,不仅领略到少数民族文化和风情,而且也与各地文化人聚会论文,唱和诗词,展开交流切磋,相互取长补短,受获良多。这对于他成长为通才,多有助益,十分有利。
复次,人和。李渔得到历史悠久的如皋古代文化的熏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刻苦读书,早有“神童之誉”,他善于动脑筋,思维敏捷,又勤于动手,具有良好的基本功和文学艺术多方面的天赋以及求新求变的创造性。“乳发未燥,即辨四声”。精通音律,置造园亭是他津津乐道的两大技能。这直接影响到他置办家班女戏,多次帮助达官贵人营造私家园林,成为一段时期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他自己对戏曲艺术情有独钟,能编能导能演。他开动脑筋,运用自己的特长,自谋生计。以家姬为主要成员,组建了家庭剧班。巡演足迹几遍中国。西到甘肃,北至京师,南到两广福建,难得一个家庭戏班有如此高雅的兴趣。李渔交游广泛,平生友人人数众多,他们均有一技之长,李渔从此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和影响,人脉资源显然是李渔成功的关键之一。李渔交游有八百多人,大多为文人、官员、技艺百工,尤其是与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毛先舒、丁澎、周亮工、余怀、尤侗、方文、徐釚、杜于皇、王士祯、施润章等历史著名文化人交游,不但扩大了眼界,而且通过交流,可以相得益彰。李渔出于各方面原因,善于虚心求教,学人之长,这也大大推动了他的全面发展。
又次, 除了李渔的博学多闻,勤奋刻苦,富有开拓创新精神,还有其特殊原因。他家口众多,又喜欢张扬人性,追求生活享受,经常造成经济拮据,而急于谋取经济利益的必然要求。创造和生活是李渔人生的两大追求[18](P40),他不断添丁,家口太多,最多时有一妻数妾,五男三女,全家主仆四十余口。而生活来源仅靠他一个人的一双手,一支笔、一张口,这就迫使他要使出浑身的解数,养活全家。那就必须不断创造,不断创新,不断创业,以求得经济回报,来维持全家的基本生活。压力必然转化为动力。然而,更要命的是,他又不肯节衣縮食,按照最低标准将就度日;而受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濡染,并不考虑收入,还不合时宜地过度追求享受。比如,他喜欢吃螃蟹,每年应时而食,肯定需要超常开支;他喜爱花草,四季不同,“予有四命,各司一时,春以水仙、兰花为命,夏以莲为命,秋以秋海棠为命,冬以腊梅为命。”[11](P262)就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性嗜花竹,而购之无资,则令妻孥忍饥数日,或耐寒一冬省口体之奉,以娱耳目。人则笑之,而我怡然自得也。”[11](P144)他曾经要求妻妾拔下头上的装饰品换钱来买花。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还主张超前消费,借贷消费。要消费就需要真金白银,就必须艰苦创业,而要创业就必须掌握知识技巧,就必须学习。还要善于未雨绸缪,走一步看三步。因此。李渔比一般人更勤奋刻苦,在旅行途中,舟车之内,夜以继日,辛勤笔耕,读书学习。他是古代最早的专业作家,也是运用文体最多的作家,他的作品数量多,门类全;出手快,修改少;喜剧意味强,主张浅处见才;他有知识产权意识,主动自觉捍卫著作权。这些都渊源有自。在文学创作不足以糊口的关头,他不能束手待毙。求生的本能,家长的责任,驱使他左冲右突,闯荡江湖,见缝插针,于是,他再经营书铺,自办剧团;又帮人整理古董、设计园林、烹饪美食、服装设计、美容化妆,代写寿序、祭文、对联,等等,甚至应邀与人谈天说地,提供名目繁多的有偿文化服务。他日夜兼程,马不停蹄,从事一切力所能及的文化产业,凡能够换取一点生活资料的事情,无所不为,以解燃眉之急。即便如此,还常常捉襟见肘,借贷度日,逋累满身。他的多才多艺,与他的生活困境休戚相关。其实他十分无奈,心力交瘁,苦不堪言,甚至痛不欲生,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倒不完的苦水。说到底,确实是时势造英雄,英雄本不想成名,是他所处的境况迫使他别无选择,不得不将自己造就成英雄;否则面临的就是灭顶之灾。英雄其实是逼出来的,通才也是形势逼出来的。民间成语、俗语说得好:“穷则思变”、“穷而后工”,“置之死地而后生”、“天无绝人之路”、“逆境出人才”,等等,异曲同工,都是讲的这个道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通才的背后,竟然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时代大悲剧。事实就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末期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与市民阶层迅速增长的人口数量,以及日益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求之间的尖锐矛盾。那是封建社会回光返照,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典型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文化大师林语堂说过:“他(李渔)极富创作思想,对每一件东西都有新颖的议论。他所创作的器具中,有许多至今为人所乐用。……因为他是一个戏剧作家、音乐家、享乐家、服装设计家、美容专家兼业余发明家,真所谓多才多艺。”(林语堂《生活与艺术》,1937年版)是的,他的概括很有道理,但还远远不充分,不周延,不严密,更不全面。其实,一个通才,不仅具有美学的眼光,而且擅长哲理的思维,他与思想家的距离最短。李渔的不少思想观念尽管当时看来不可思议,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观念具有前瞻性,比如,他站在以人为本的思想高度,轻物重人,把生活和创造作为人生的两大追求;主张充分享受生活,虽然负债累累,却选择超前消费、借贷消费,等等。不料到四百年后的今天,居然成为时尚潮流。唯此,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他作为思想家的历史地位。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这个古代卓绝的文化艺术通才不是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也不是一掷千金的富家子弟;他不可能出现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只能出炉于清初这个封建王朝趋于衰亡,资产阶级思想潜滋暗长的艰难时刻。这个人只能是既不能为官作宰,又不愿意务农经商,而乐于“卖赋糊口”,终身从事文化产业的市井文化人李渔。其中的道理发人深省。简而言之,的确是时代造就了杰出的文化艺术通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成就了文化巨匠李渔。鉴此,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再去讨论,这对于李渔的人生,到底算是悲剧,还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