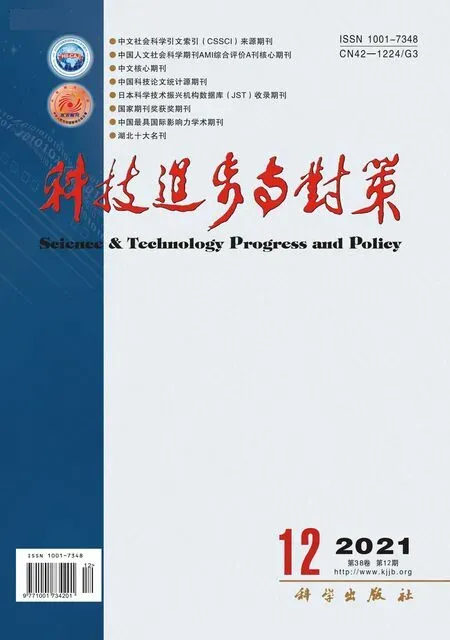非共识研究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陈良雨
(电子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0 引言
伴随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嵌入程度加深,创新驱动力愈发成为科研活动注意力配置焦点,诸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都依赖于创新的支撑作用。高校作为科研活动“重镇”,更是离不开创新精神、创新意识的推动,尤其是良好的创新环境,其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际比较看,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高校创新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原始创新能力是指通过原始创新活动创造出此前没有的发明、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及研发出重大突破性技术的能力[1]。对于高校而言,其原始创新能力是高校在科研成果上创造前所未有的发明、取得重大科学发现与重大突破性新技术的能力。然而,从高校科研创新现状看,我国虽然在科研创新上取得一定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面临诸多不足,尤其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更是饱受各级人大代表诟病。如有代表指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亟待“解套”,并要清楚认识高校科技创新痛点[2];有代表通过对比中美科技竞争局面,指出“卡脖子”关键技术买不来,只能够靠自力更生、自主创新[3]。针对这一问题,教育部与科技部联合发文,要求加强高校“从0到1”的基础研究,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以充分发挥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4]。由此可见,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已经成为高校创新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
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涉及诸多方面,但科学研究场域无疑是驱动创新的重要支柱。在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研究议题往往具有争议或分歧,并导致科学研究评价不一,这就涉及到高校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非共识研究。从哲学学术评价角度看,非共识研究应该倡导包容、鼓励探索与创新[5],坚持非共识研究存在孕育创新成果的可能。事实上,正是由于非共识研究的争议与分歧,导致该类研究往往在投票评价模式下面临困境,如非共识性项目一旦遭遇多数票反对,则进入淘汰环节。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被否决的非共识研究就一定没有创新价值?非共识研究被否决是否也会存在误判?更值得进一步探寻的是,非共识研究是否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制约因素?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紧密联系?
从有关高校原始创新的研究现状看,有的研究侧重于高校原始创新指标设计,如邢纪红和龚惠群[1]基于某市的实证研究,建立了包含资源水平、创新氛围、管理水平和产出水平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李玉琼等[6]设计了由原始创新基础支撑能力、原始创新投入能力、原始创新产出能力和原始创新管理能力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有的研究关注到我国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现实问题,如汪寅和黄翠瑶[7]指出我国高校基础研究水平低、创造教育发展滞后、潜科学研究衰落等现状;王章豹和汪立超[8]认为,缺乏重大原创性成果、知识产权创新能力弱等制约了我国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有的研究聚焦于原始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如陈劲和汪欢吉[9]从个人、团队、制度层面对影响高校原始创新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褚怡春等[10]分析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影响。还有研究探讨了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策略,如汪立超等[11]从生态位维度、生态位宽度以及原始创新生态系统协同进化等方面提出应对策略;王冬梅[12]针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出强化基础研究、加强产学研一体化以及创新环境建设等建议。
学者们从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应对策略等不同层面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进行探讨,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然而,已有文献却鲜有从研究项目角度思考高校原始创新能力问题,如非共识研究。作为具有颠覆性、争议性的非共识研究,是促进还是制约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如果存在制约关系,应该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本文针对上述问题,探索非共识研究何以支持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剖析非共识研究视角下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制约因素及其应对措施,以期为我国高校创新发展提供思考方向。
1 非共识研究内涵
关于非共识研究,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界定。由于项目、课题等是从事非共识研究活动的主要支撑,非共识研究需要通过相应的课题、项目呈现和反映,因此非共识项目的界定可为理解非共识研究提供一定依据。例如,杨列勋等[13]认为,如果评审专家在某一研究项目的评价上高度一致,即使存在极少数异议,那么该研究项目就不是非共识研究项目,如果评审专家在某一研究项目的评价上正反意见近乎各占一半,正反方具有可靠的论述和论据,那么该研究项目就是非共识研究项目;郝凤霞和陈忠[14]认为,当一项技术开发活动在最初阶段前景不够明朗,兼具风险和不确定性,且评审专家对其难以评价时,该项研究就具有非共识性;刘文波和钮晓鸣[15]指出,非共识研究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既面临风险又存在希望,同时,非共识研究项目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与创新性,在其初期难以达成一致认识;西桂权[16]认为,非共识项目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超出一般认知水平,从而导致小同行无法进行评判,或大同行评价时评审专家对项目看法不一致;曾敏[17]将非共识研究项目定义为没有得到公认,甚至可能有悖于权威论断,但又具有创新性的项目课题。
综上所述,非共识项目是一种既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又具有颠覆性和创新性,并在初期难以得到同行评审一致认识的项目。非共识研究则可以理解为从事兼具不确定性和创新性且在初期评审专家难以对项目达成一致意见的研究行为或活动。非共识研究通过非共识项目呈现,其项目的非共识性决定该研究活动的非共识性。非共识研究一方面表现出研究活动的风险性,即充满不确定和不可预知;另一方面又具有高度创新性和颠覆性,研究成果一旦产生,将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在评价层面,非共识研究在初期往往使评审专家陷入困境,难以达成高度一致的意见,甚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挑战权威论断,从而导致专家评审充满异议与分歧。因此,非共识研究就是一种体验机遇与风险的科学研究行为或活动。
2 非共识研究何以促进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虽然非共识研究在初期充满不确定性与争议性,但其较强的创新性却不容忽视。高校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非共识研究能否促进其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从实践状况看,非共识研究在以下方面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可能。
首先,开辟新的理论疆域。非共识研究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高度创新,尽管其在初期饱受争议,但其创新性特征为高校科学研究中新的理论疆域开辟提供了可能。由于非共识研究涉及到的颠覆性技术会对传统主流技术产生根本性影响,是一种“独辟蹊径”的技术[18]。因此,一旦非共识研究最终获得成功,将会在原有研究、学科基础上打开新的理论空间。以色列理工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丹尼尔·谢德曼(Daniel Shechtman)的准晶体研究发现就体现了非共识研究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贡献。当丹尼尔·谢德曼提出准晶体概念时,极具争议性,传统化学理论遭遇颠覆性挑战,其研究团队被标签为“羞耻”,诺贝尔奖得主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甚至公开质疑,认为世界上没有准晶体[19]。然而,经过不懈努力,丹尼尔·谢德曼最终成功占领准晶体研究领域,改变了科学家们对物质本质的思考,即晶体内的原子结构从不重复,并且这一发现也使准晶体成为物理学、材料学、数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20]。由此可见,丹尼尔·谢德曼的这项非共识研究一方面为高校科研开辟准晶体研究新领域打开新的空间,为相关领域科学家、研究人员、学者等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该研究还创生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为交叉学科创造了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为一流学科的创新发展提供动力。因此,从事非共识研究,也是高校孕育颠覆性发明和重大创新发现的重要前提之一,可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驱动力。
其次,推动原创成果生产。高校原创成果生产状况是衡量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而非共识研究在实践中为加速高校原创成果供给提供了可能,从而从原创成果产出角度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支撑。事实上,国内高校也存在研究人员从事非共识研究并最终取得丰硕成果的案例。以中科院院士田禾的非共识项目申请为例,虽然其项目评审过程遭遇曲折,但最后仍然取得重大突破。2004年,田禾申请一项与分子梭研究有关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由于该领域国内尚无研究人员涉足,评审结果也未取得专家一致赞同,随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采取非共识项目方式对其进行资助。在基金资助下,该团队获得中国发明专利12项,在影响因子大于6的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4项,产生4篇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1]。正是由于该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创新支持,才使得田禾及其团队在项目执行期间获得诸如专利、论文、奖励等方面的产出,而这些产出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具有直接关联。取得专利本身就意味着对新发明或新发现的认同、许可;科研论文作为科学研究的文字呈现,也是原创成果的重要表现;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体现了该研究在相关领域获得的认同,同时博士论文产出也建立在原始创新基础上。因此,非共识研究取得的多元化创新成果,不仅仅体现在对研究成果的呈现上,也从更深层次反映高校科研团队与科研人才的创新能力和水平,这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再次,营造包容型创新环境。学术环境状况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优化学术环境能够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从而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22]。因此,良好的创新环境也能激发高校原始创新活力。非共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营造一种更加包容、容错的创新氛围,尤其对于高校而言,容许、支持非共识研究,本身就是在营造一种包容型的创新环境,这也是高校原始创新的软实力所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从1993年开始,留出30万元风险基金用于资助思想、概念、方法等方面的原创性研究,以包容、保护非共识项目的进行,从而营造一种宽容的创新环境,在科学思想碰撞中迸发创新火花[23]。对于高校而言,鼓励非共识研究,创新非共识研究支持机制,也是在营造高校科研创新环境,体现高校对非共识研究活动的包容,更是彰显对创新活动中不确定性的容纳。虽然非共识项目具有较高的风险性,但其发现探索性与创新思想性同样较高[24],高校支持、鼓励非共识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鼓励和支持探索发现、思想创新行为与活动,更凸显出对非共识项目风险性的包容。因此,高校支持非共识研究活动,实际上也是为高校自身科研活动创造相对宽松、包容的氛围与环境,从而吸引、培养更多优秀创新人才,这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方面。
3 非共识研究视角下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制约因素
尽管非共识研究具有较强的创新性,但由于其争议性、不确定性等特征,也使非共识研究在实践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尤其在评价环境、干预行为、学术司法、多元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制约着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首先,观念转型滞后阻碍高校原始创新生产力。从一般流行观点看,一致好评或一致通过的研究项目往往意味着好的预期,而具有价值争议或观念冲突的研究项目往往被搁置。这就涉及到一个观念转型的问题,而观念转型是一个更加复杂、困难的过程,且本身包含着各种新旧价值观念冲突[25]。如果在评审活动中难以转变对具有争议性、颠覆性研究项目的包容观念,在评审活动中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项目自然容易被搁置,尤其是非共识研究项目。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匡迪指出,新想法、新技术冒尖之初,难以得到大多数人认可,评审专家投票,其结果往往是把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项目投没了[26]。具有创新性的科研项目被埋没,反映出一些专家对具有争议性的学术观点、技术等多有排斥,往往让争议性小的科研项目通过,这种求稳的观念反而抹杀了冒尖的新想法。同时,中科院院士徐冠华指出,争议项目往往被习惯性拒绝支持,没有国外先例的研究也往往被排斥[27]。习惯性拒绝同样反映出对待较高原创性想法的保守姿态,这种只能接受符合自己学术观点与技术,或基于已有研究的观念,本身就与原始创新的内涵互斥。因此,这种观念转型滞后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非共识研究项目减少,扼杀非共识研究活动或行动,非共识研究项目中创新性、颠覆性思想得到彰显的机会更加渺茫。然而,非共识研究活动本身就是高校原始创新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非共识研究项目受到限制,也就意味着高校产生颠覆性研究思想或技术的概率降低,进而影响高校原始创新生产力。正如有学者戏言,原创价值高的项目还需要到未通过的非共识项目中寻找。尽管这一说法带有讽刺性,但确实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对待非共识研究亟待转变观念。
其次,保守干预模式制约高校科研创新治理水平。高校科研创新治理状况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重要观测点。高校获得创新成果的质量高低与高校教师对创新事物的兴趣及参与紧密相关,高校应该通过有效的管理激发教师创新活力[28]。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到科研创新活动中,就是科研创新的治理形态。要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除教师自身科研创新外,还离不开必要的积极干预行为。然而,从当前非共识研究的干预状况看,主要表现为一种保守干预模式,即相关管理者、领导或团队负责人在相关项目交流、探讨过程中,对具有创新性的项目进行干预,对创新内容持保守态度。一项涉及非共识研究的问题调查显示,超过70%的科研人员存在项目被干预的情况,而对于一些科研力量相对较弱的地方院校而言,开展非共识研究更被视为一种“赌博”;一些教师提及,当自己展开创新性想法或观点的讨论时,甚至还被认为“异想天开”[29]。在国家项目申报过程中,对于存在争议的非共识项目,绝大部分领导、科研团队负责人能够带着善意为科研人员提供建议,帮助其修改完善,以提升通过率,但也存在项目争议内容修改后,原创性大打折扣的问题。非共识项目中的创新与颠覆能反映科研人员的兴趣和发现,而对科研人员创新发现进行保守干预则会阻碍科研人员的创新参与,这直接影响高校原创成果产出,更会影响高校内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非共识项目的创新治理水平。因此,保守干预会制约高校科研创新治理水平,也会阻碍高校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
再次,学术司法缺陷影响高校科研成果的创新生产。专利、项目等研究成果体现了高校科研成果生产状况,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之一[1]。高校科研成果生产效率越高,其原始创新能力就越强,创新生产过程、途径、渠道等也会更加通畅,从而增加高校科研成果的原始积累,这也是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关注的焦点之一。然而,从实际情况看,非共识研究面临的学术司法缺陷会对高校科研成果的创新生产造成直接影响。学术司法是对有学术争议的科研项目进行带有司法特征处理方式的一种描述,如项目申请中的复审。尽管在项目申请中可以提出复审请求,但这种复审却是一种有限复审,即不能针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提出复审。这对非共识研究而言是一种司法缺陷,也是广受学者批判之处。因非共识的评价结论而被错判、误判的例子客观存在,尤其在前沿、交叉领域,相关知识可能超出评审专家的理解和认知范围,更可能产生错判和误判问题。为什么不能针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提出复审呢[30]?这一反问表明,在创新性较强的领域,评审专家也会陷入知识盲区。难道复审环节就不能为挑战专家知识权威开一扇窗?非共识研究本身蕴含着后续预期创新成果的生产,但由于学术司法中拒绝针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提出复审,一些可能具有较好创新预期成果的非共识项目也就被拒之门外。综上可知,由于存在争议且创新性较强的项目难以对评审专家的学术判断进行挑战,其预期科研成果的创新生产途径也自然受阻,从而导致可能的创新成果原始积累减少,进而对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最后,多元参与不足削弱高校对原始创新的支持效应。高校的非共识研究活动除自身和国家相关基金资助外,还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其作用在于为非共识研究活动提供相应保障。由此,非共识研究活动便获得更多发生条件。当非共识研究因学术见解不同而不能通过专家评审,却能够得到多元主体支持时,非共识研究的创新火种将获得一线生机。这种多主体参与的支持模式,可为高校在多种场景中彰显其颠覆性、创新性观点与技术提供实践保障。但从当前非共识研究实践看,尚面临多元力量参与不足的问题。虽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从2011年起设立了重大非共识项目,但受益面较小,仍有大量非共识研究项目被拒之门外。同时,政府在非共识研究上普遍采取保守的财政支持政策[31],部、省、市等立项机构也缺乏非共识研究项目资助的特定渠道。此外,对于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主体如何支持非共识研究项目,并激发高校非共识研究活力,当前也没有一套成熟稳定的运作模式。由此,非共识研究缺乏多元主体的创新支持行动,原本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研究项目可能由于支持渠道缺乏而被搁置,这对高校原始创新实践无疑是较大的损失。正如有学者指出,由于非共识研究新颖度高,往往会因评审专家对创新认识不足而被否定,因而更应该探索非共识研究的系统性支持方式[32]。因此,非共识研究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不足,导致非共识研究项目难以获得多渠道创新支持,同时也会影响高校在科研活动中生产创新思想和技术的途径。
4 非共识研究视角下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策略
非共识研究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但非共识研究面临的现实困境,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因此,针对上述问题,非共识研究视角下的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可以通过以下方面进行尝试:
(1)塑造包容的评价制度。当前科研项目评价环境对非共识研究仍然缺乏包容性,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原本具有创新潜质的研究生长点消失,从而影响高校原始创新实践。因此,可以尝试通过评价制度的塑造应对观念转型滞后问题。首先,从制度层面,针对非共识研究存在的问题,制定专门审核与保护具有颠覆性、创新性研究思想和技术的系统性方案、政策,创新性设计非共识研究项目评审方式、评审内容等,从而形成一套与其它项目相比,具有差异性的评价模式,以此从制度层面引导非共识研究项目评审活动,同时也提高对非共识研究的重视程度。其次,从机制拉动层面促进评价机制变革。可以通过机制创新,如增加非共识研究申请比例,或采取例外手段专门评审涉及跨学科的项目抑或冷门但又具有重大前景的基础研究项目。以美国为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强调支持变革性研究,专门征集和鼓励能够挑战现有研究范式的研究项目申请,支持具有风险性和挑战性的想法;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针对交叉学科、跨学科等领域的研究项目,专门设立特别评审机制,以弥补常规评审的不足[33]。因此,我国在非共识研究上应当通过创新制度与机制设计,进一步扭转当前对待非共识研究的滞后观念,为非共识研究活动开展提供包容的制度环境。
(2)构建科学的干预模式。对非共识项目进行干预属于高校内部科研治理的范畴,体现为领导者、团队负责人等与项目负责人的沟通与交流。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角度看,这种沟通与交流应当体现为对非共识研究中颠覆性和创新性观点、思想、方法、内容等方面的支持或凸显,而非刻意抹杀,否则干预后的非共识项目在创新性上将大打折扣,反而产生较差的科研创新治理效果,进而导致项目原始创新水平降低。当前,高校在非共识研究项目中存在或强或弱的干预行为,尽管出发点是为了获得认可与资助,但要提高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就必须构建科学的干预模式。一方面,高校领导者、团队负责人应当鼓励和支持具有创新性、颠覆性的非共识研究;另一方面,高校领导者、团队负责人应当与项目研究者一道,在坚持非共识研究的前提下,尽可能完善相关研究内容与方法,进一步提高非共识研究项目的成熟度。与此同时,高校领导者、团队负责人还应当为具有重大创新发现潜质的非共识研究提供更多交流与展示的机会、平台,并在与其它研究相互吸收借鉴的同时,获取更多支持与认同。这种互动模式能够为高校内部科研创新治理水平提升奠定基础,同时也有利于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
(3)建立开放的申诉程序。尽管当前存在与非共识研究相应的申诉程序,但仍相对封闭,尤其是在学术判断方面,并未给非共识项目研究者留出足够申诉空间。建立开放的申诉程序,就是要为非共识研究提供更多机会,让更多非共识项目获得资助,从而促进更多优秀原创成果生产,最终弥补高校原始创新成果不足的问题。一方面,由于非共识研究涉及的思想、观点、方法等具有较高的创新度,难免超出评审专家的研究领域。因此,应该进一步开放非共识研究项目复审空间,使学术判断也能成为非共识研究申请者进行申诉的理由。这不仅体现出对知识的尊重,还体现出对原始创新的保护。另一方面,还可以尝试进一步开放其它申诉渠道,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非共识项目申诉中规定,未获得资助人员如果对评审结果持有异议,可以向NSF助理主任提出申诉,甚至重新组织评审,如果对NSF助理主任的解释不满意,还可以向NSF副主任提出申诉请求[34]。从保护非共识研究原创成果的角度看,我国也可以尝试开辟更多申诉渠道,为具有较高创新潜质的非共识研究提供良好保障。
(4)拓展多元支持体系。拓展多元支持体系旨在弥补当前非共识研究过程中支持渠道不足的问题,增强政府、社会力量对高校非共识研究的支持力度,从而发挥多元主体在推动非共识研究过程中的协同效应,促进更多原创成果产出,进而提升高校原始创新能力。多元化支持体系不仅包括各级各类基金会的支持,还包括政府、企业及其它各类社会组织的支持,如政府可加大对非共识研究的财政支持力度,企业和社会组织可以对未通过专家评审的非共识项目进行后续资助等,以此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支持体系,其目的就在于为具有潜质的创新项目服务。当前,广东、浙江等地方政府和企业已经开始尝试拓展经费资助渠道[35],这对于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是一种有益探索。在多元支持体系下,非共识研究活动将会获得更多保障,高校原始创新实践也将在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下取得更大进展。
5 结语
非共识研究为高校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了探究空间,但从实践看,要通过非共识研究促进高校原始创新活动,还需要从多个方面进一步展开研究。尤其是在本土创新文化建设和原始创新国际比较方面,更需要加强研究。如应该塑造怎样的创新文化才能促进对非共识研究的包容?这直接涉及到当前科研创新项目评审活动中的观念转型。又如,从国际层面看,原始创新能力较强的发达国家是如何看待非共识研究的?其又是采取何种措施保护非共识研究中颠覆性思想或技术的?这也是未来在该领域研究中需要从比较角度进一步探索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