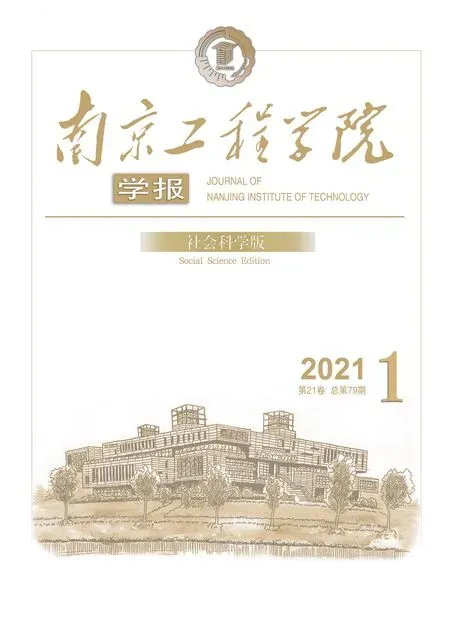从签名管窥藤田嗣治画风嬗变
袁悠然,徐泳霞
(1.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江苏 南京,210046;2.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日本没有人会否认藤田嗣治是获得世界承认的唯一的日本画家。他是人们公认的20世纪法国和日本最杰出的画家之一。他本人倾向于将自己的一切包括对他作品的评价交给时间来处理,事实上,由于他传奇的行为和生活,加上其作品很少展览,至今他仍然处于人们视线的边缘,大家对他的认识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而有关他的争论却仍未停止。
藤田嗣治1886年出生于东京,13岁时就立下了当画家的志向。1900年,年仅14岁的藤田便有一幅作品入选巴黎万国博览会的日本展区展览。随后,他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1913年,27岁的藤田来到巴黎,此后,除了20世纪40年代短暂返回日本外,他几乎所有的艺术生涯都与巴黎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藤田在画作上的签名具有时段性。当他刚到巴黎时,在1914年创作的《立体主义静物画》《巴黎城门》上,他签下的是“T﹒Foujita”(T代表Tsuguharu,即“嗣治”的意思,Foujita是“藤田”的意思)和“Foujita”;在1918年的《礼拜》《基督》《基督诞生》等作品上,他在“T﹒Foujita”的上方增添了竖写的四个字“藤田嗣治”;1921年,从一张《自画像》开始,他的签名由竖写的“嗣治”和横写的“Foujita”组成,这个签名方式一直沿用到20世纪40年代,他代表性的画作几乎都完成于这一阶段。
毫无疑问,“嗣治”这两个方块字表征的是日本身份,而字母组成的“Foujita”则有着鲜明的法国特征。这貌似不经意的签名实则与画家本人思想的变迁、画风的变革都有紧密联系,也包含了他对巴黎的情感以及巴黎对他的影响。一个东方人,想要在巴黎出人头地,在“嗣治”和“Foujita”的身份转换与认证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迷惑与困顿、孤独与彷徨,又有着怎样的纠结与挣扎、努力与拼搏、转折与蜕变?我们只有把画家的个性、生活与作品连缀起来,才能更好地剖析这个问题。
一、初入巴黎(“T.Foujita”):渴望融入
20世纪初期的法国巴黎是自由而前卫的艺术之都,而位于其西南的蒙帕纳斯更是诗人、画家及各种社会边缘人的聚集之地。1913年8月,藤田嗣治初到法国,第一站便是蒙帕纳斯,他迫不及待地跑到艺术家的聚集地圆顶咖啡屋去瞧个究竟,第二天就到毕加索的洗衣船画室中观看立体派的作品,精神上受到极大冲击,感受到绘画的自由抒发,想主动地融入巴黎的艺术圈。不久,他又与莫迪利阿尼相识,后者于1906年来到巴黎,其艺术上的探索深深启发了藤田。在藤田早期的画作中,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各种尝试。在1914年的《立体主义静物画》中,他把瓶瓶罐罐、沙发、书籍等分解成各种几何形体,加以平面组合,采用的是毕加索分析立体主义的手法。1917年,藤田所作的《幻想风景》《巴黎城门》有亨利·卢梭的超现实和荒凉感。在《赤发妇人》《三个妇人》中,有意拉长的脸庞和手指、细眯的杏仁眼、冷漠的表情、抽象的背景,又令人一下就联想到了莫迪里阿尼的画风。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藤田滞留法国,家中的供给中断,他在贫困中坚持学习,把卢浮宫等博物馆作为学习的课堂。他精研古希腊的优秀传统,感受古埃及的异域风情。他研究毕加索和莫迪里阿尼的画风时注意到了他们对非洲艺术、东方艺术的借鉴与引用,也关注到了莫氏画中意大利人的端庄清丽以及浓浓的波希米亚风情。他已经意识到,要想在巴黎竞争,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须创造自己的风格。
初到巴黎,藤田画了300多幅立体风格的作品,此时,他使用“T﹒Foujita”或“Foujita”带有明显西方特征的签名,也许是想尽早融入法国社会,获得巴黎艺术界的承认;或许是他想消弭日本学院派的影响,像巴黎的艺术家一样,用更自由的方式表达自己。而当他与莫迪利阿尼走近,思想上又起了变化,在绘画中运用线条和平涂的色彩,他模糊地意识到这种画风与东方绘画有契合之处,所以,从1917年开始,他的签名中有了不少的“T﹒Foujita”与上方竖写的 “藤田嗣治”的组合,试探性地表征自己的东方特征。
二、在巴黎竞争(“嗣治”加“Foujita”): 重现自我
1920年前后,藤田完成了一次华美的转身。1919年,他提交的6幅作品全部入选巴黎的秋季沙龙展;1921年,他提交的3件作品则更是造成了轰动。很快,他便成为各大艺术展览会特别是秋季沙龙展的宠儿,1925年还获得了荣誉勋章。他对自己是东方人的肯定开始复苏。他画中最为人称道和欢呼的一是墨线,一是“伟大的乳白色”,这两个明显具有东方印记的特征使他与同时代的画家拉开了距离。
线条的运用固然受到莫迪里阿尼、古希腊陶罐上的装饰画、埃及的壁画艺术的启发,但藤田走得更远。他把自己的绘画艺术探索建立在日本艺术与西方前卫艺术的对比的基础上,在油画中用中国墨来勾形,即用墨线描绘出主体的轮廓,勾勒出复杂的细节,使形象“内在的动作被合理的节奏表达出来”[1]。在传统的水墨画中,线条本身就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这也是中国线描和书法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然而,油画中用墨线,必须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在技法上墨与油画颜料是否兼容。在正常情况下,水溶性颜料很难固着在油彩材料上,藤田经过无数次试验,最终获得成功。由于藤田的语焉不详,至今这一技术还未能被完全揭示,他只是说:“经日本水彩颜料稀释的烟灰墨就像油上漂浮的水,我倒更多的油为了留住水分”。二是在审美上墨线在油画中是否能相得益彰。事实上,当时,马蒂斯与莫迪利阿尼都已经试图在自己的油画上用线来驾驭体面关系。不过藤田的墨线更细腻、敏感和柔和,且因为材料的选用而更具东方特色。在藤田作于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的一系列画作中,从人物到背景,线条信手拈来,随意环绕,在1923年的《有挂毯的妇人》中,人物左侧从手肘到脚趾一根线条贯彻始终,光滑而和谐,这线条甫一面世,在沙龙展上便被识别出来,引起称赞。
一旦他用上了东方的线条,他就会对同样源于东方的平面装饰性感兴趣。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的画家专注于日本的浮世绘,藤田同样也从中获取灵感,尤其是想用喜多川歌磨、铃木春信等大师留白的手法画人物的肌肤。但把这种手法用于油画创作中难度很大,“把一个空白的背景变成丰富的肌理是困难的。每一次失败都是一种经验,一次进展。这样我最终得到理想的称之为‘白色肌理’的方法。”[2]189他在画布上均匀地涂出白、粉、灰色交织的层次,用这种看似湿润的珍珠色直接表现裸露的肌肤,让画布的质感与肌肤细滑透亮的质感相同。在他看来,技巧是绘画的精髓,人们欣赏画应该“用眼睛去触摸和爱抚画幅的表层,可以完全忽视旧时期的价值,如阴影,比例,透视等”[2]193,也就是说,在他的画中,画布本身就是妇女的皮肤,他并不关注逼真的三维空间,只是关心画面的最表层。对自己独创的技术他非常自信:“我确实是第一个认识到人类的皮肤及其本质的人,这也是我的裸体画与众不同的原因。正是这一点,捕获了观众的注意力。”
为对比衬托这光滑的肌肤,他又在背景上仔细推敲,他吸收了野兽派战将马蒂斯对室内尤其是装饰窗帘描写的手法,又受到象征主义大师莫罗描绘女性服饰的启发,在画面中,有时用柔软的画布,有时采用温和的灰色阴影,或纯黑的背景,让作品更富有现代感和简约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他创作的精髓和招牌特征。在1923年的《有挂毯的妇人》中,床单及枕头的褶皱、猫皮毛的质感、窗帘的针脚细致却对比度低,处理柔和。在1922年《裸卧的吉吉》中,背景或环境相对抽象,因为他知道它们并不比人物本身重要。
在创作题材上,他也适时调整。他发现法国人与保守的日本人不同,他们毫不掩饰地追求感官快感,因此,他也可以不顾忌观者想象空间,大胆自由地创作裸体画,呈现出自己对欧洲的印象。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创作了一系列的人体画,包括《五个妇人》《有挂毯的妇人》《沙滩上的妇人》《两个朋友》《我的梦》等等。他认为通过叙事的方式吸引观众是一种胆怯的表现,应该将绘画与文学分离,把绘画的真实与客观的真实划开来。与莫迪利阿尼笔下的那些女子一样,藤田笔下的女子也脱离了古典人体的“寓意”,她们典雅、平静,有时还显得冷漠。在《五个妇人》中,几个女子似乎以拼贴的方式呈现在画面中,彼此无论在肢体还是在情感上都没有关联和呼应。
事实上,藤田技法和题材上突破的尝试在1918年便初露端倪。这一年,他创作了《持花少女》,恰恰在这幅画上,他签下了清晰而又端庄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标签——“嗣治”加“Foujita”,“嗣治”在上,以东方的方式竖写,“Foujita”在下,以西方的方式横排,不再避讳自己的东方人身份。在他1910年所作的《自画像》中,画者是一个身着西装的现代青年形象,运用了印象派的手法,而1921年的《自画像》则完全是一个传统的日本人的打扮:蘑菇头,圆眼镜,上嘴唇的横须,长袍烟斗,刻意强化“异乡人”特征。此后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的所有的自画像均是这个形象。在1923年所作的《妻子与我在室内》中,藤田与妻子端坐桌前,桌上排列着水墨画创作所用的碟子,旁边的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藤田手上也紧握一支毛笔,标准的东方人握笔的姿态。在1926年的《画室中的自画像》中,他盘腿坐在地上,以日本人标准的坐姿呈现在观众面前。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刻意强调自己的“东方”特色,以特立独行引起世人关注,他知道,这种独特正是西方所缺失和需要的,这也是立足巴黎的根本。在一次访谈中,他曾说:“我不了解为什么很多前人企图学成归国后,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再和欧洲画家一较高下;不过我决心在欧洲大陆抗争,在真正的战场上竞赛。”在当时的法国画坛,“异域风情”是来自世界各地画家们注入巴黎的新鲜血液,也是他们快速获得巴黎承认的有效途径。莫迪里阿尼以其独具的波希米亚风情令人瞩目,夏加尔的作品中则有很多的斯拉夫式幻想,柴姆·苏丁画中流露的是犹太民族的美与丑的纠缠,而藤田也有他独特的东方传统风貌。
从1931年开始的近两年的南美洲之旅再一次改变了藤田的艺术风格,南美绘画中亮丽的色彩、民族的特征让他找到了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也更坚定了自己的创作道路。首先强化色彩的平面装饰性,其次他开始对风俗和风土的人和物感兴趣。他画日本的传统,创作了《街头艺人》《郊区的艺妓》《相扑选手》等一系列民间文化作品,一块布、一盏灯、一个闹钟都会成为他精心刻画的对象。他还为自己设计、建造纯和风的房屋,里面摆放着古旧家具,他坚信传统具有合理性,而并非已经西化的日本人所谓的坏品味。
与初入巴黎不同,这一时期,他的签名由竖写的“嗣治”和横写的“Foujita”组成,或者有时干脆就签“嗣治”二字,此时,他已经知道了巴黎艺术界的游戏规则,创新出奇是生存的法则,他的画风受到了巴黎的认可。既然大家对他的东方风格感兴趣,那他就不必遮遮掩掩,去趋同西方,而是大胆亮相,创作出“由日本固有文化当中渗透而出的作品”[3]。从自画像到签名,都表达出他对东方艺术的重新认识和自我肯定。
三、结语
诚然,“签名更替”并不能作为藤田嗣治更改画风的动机,而是画家思想变迁与画风蜕变而产生的附带结果。然而通过研究藤田嗣治的签名,我们仿佛理清了关于藤田嗣治的一根艺术线,一条时间轴,这使我们可以注意到画家创作的阶段性,更清晰地看到他的艺术历程,对画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巴黎给了藤田嗣治开阔的舞台,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去学习,去创作,去坚持,藤田饱含东方意蕴的艺术语言使他的作品成为“日本的巴黎派画家奉献给巴黎的最好礼物”[4]。另一位同样享誉世界的日本艺术家村上隆总结自己和藤田成功的原因时得出的结论是:“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将之视为创作动机”“将日本独特的文化体系植入欧美美术史的脉络,这样就能与西方艺术世界产生决定性的接触点。”[3]熟悉西方艺术的游戏规则,用东方的方式去突围,才成就了巴黎画派中的藤田嗣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