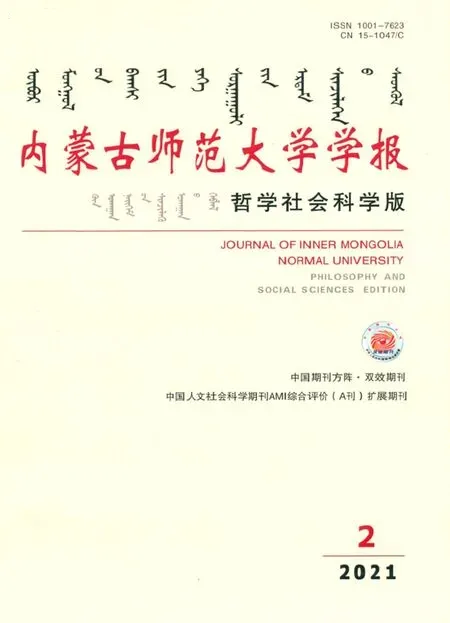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思想与理论研究
石丽荣
(中央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 北京100081)
阳明学作为中国儒家哲学的代表在东亚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界的研究也主要围绕阳明学在东亚的传播和影响展开。但是,随着中国儒家哲学在海外的传播及海外汉学研究日益成熟,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也引起了西方学界的重视。其中,最受关注的研究主要是对阳明学的译介与思想研究。与此同时,在传统译介和思想研究的基础上,阳明学的研究视角也发生了重要转变。从当前学界对阳明学与西方学术的关联性研究来看,一方面,主要是围绕阳明学在美国的传播作为研究线索探讨其学术思想之流变[1]198;另一方面,从通识译介、学术繁荣、多元化研究三个阶段系统性梳理了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过程[2]121-127。虽然这些研究提高了西方关于阳明学传播史的研究水平,但是仍然囿于传统通史性的材料梳理。因此,为了摆脱传统纵向史料堆积的影响,笔者拟从译介传播、哲学思想、理论研究三个层面梳理阳明学在西方学界的传播轨迹,以期明确英语语言文化语境下对阳明学的理解和认识。
一、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传播
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的传播主要是围绕孔孟以来先秦哲学展开的,因此,强调哲学史的西方学者鲜有触及中国先秦哲学以外的思想。关于阳明学的译介滥觞于20世纪初,美国传教士、学者弗雷德里克·古德里奇·亨克(Frederick G.Henke)首先将阳明学的代表著述《传习录》英译为ThePhilosophyofWangYang-ming(《王阳明的哲学》)。于是,亨克的英译版《传习录》,开辟了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传播。
如上所述,亨克敏锐地察觉到西方关于中国哲学思想研究中的问题,他指出:“就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趋势而言,孔孟之后很少有详细的资料提供给哲学研究史的欧洲学者。这其中的原因就是,流行的观点是除了《四书》和《道德经》之外,中国人没有提供多少有价值的思想。”[3]9在这一问题意识的基础上,亨克参考上海书店出版的《王文成公全书》的同时,将其年谱、《传习录》和部分书信翻译成英文。其中,年谱部分涵盖了从“出生及祖上来历”(Ancestry and Birth)到“死后追谥”(Posthumous Honors);《传习录》(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feⅠ,Ⅱ,Ⅲ)为徐爱、陆澄、薛佩编辑的《王阳明语录》、陈九川编辑《王阳明语录》(RecordofDiscourses),以及《大学问》(InquiryReadingtheGreatLearning);书信为《王阳明的书信》(LettersWrittenbyWangYang-ming)和《王阳明书信(续)》(LettersWrittenbyWangYang-ming〈Continued〉)。由于亨克的传教士身份,他在译文中将“天”翻译为 “上帝”(Shang-ti)、“天堂”(Heaven),将“道”翻译为“教义”(Doctrine),从亨克的这些翻译可以看出,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传播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换句话说,西方学界是从宗教的出发点理解和认识阳明学的。
然而,西方对阳明学的这种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很快在美籍华人学者陈荣捷(Wing tsit Chan)的翻译中得到改善。陈荣捷在海外汉学研究界声名斐然,他被誉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者”和“把东方哲学文化思想最为完备地介绍到西方的中国大儒”[2]123,他将《传习录》重新翻译为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vingandotherNeo-ConfucianWritingsbyWangYang-ming。其中,关于《答陆原静书》中“不然,则如来书所云三关、七返、九还之属,尚有无穷可疑者也”一段[4]70,陈荣捷翻译为:
Otherwise there will be an infinite number of things in doubt, such as the Taoist formulas to prolong life called the “three gates”, the “seven return”, and the “nine returns”, mentioned in your letter[5]133.
在这段翻译之外,陈荣捷还加入了补译,他将“三关”翻译为“The three gates were the mouth, hands, and feet, considered as the gates of heaven, man, and earth”;“七返”翻译为“the seven returns were the return of the soul after seven periods”;“九还”翻译为“the nine return, the return of the soul after a complete cycle”[5]133。“三关”“七返”“九还”本为道家修行秘术,而陈荣捷在《传习录》的翻译中,详细地诠释了这些术语的翻译,可见他不仅重视原文的本义,而且通过补译的方式,对原文中晦涩难解的部分做了进一步的诠释。这种译介传播方式既让阳明学的意蕴以一种开放的形态进入英语语言文化的语境,又使得西方学者得以进入阳明学的思想范畴。在亨克、陈荣捷的翻译基础上,海外汉学学者秦家懿(Julia Ching)从王阳明的书信中选取了67封辑录,并翻译为ThePhilosophicalLettersofWangYangming(《王阳明的哲学书信》)。秦家懿的翻译涉及王阳明关于人性论、义理内涵等传统儒家哲学范畴,这为西方学者进一步深入理解阳明学拓宽了研究思路。
但是,在阳明学的译介传播中,不少学者对亨克、陈荣捷、秦家懿的翻译提出了质疑。关于《传习录》书名的翻译,倪德卫(David S. Nivison)不同意亨克与陈荣捷将《传习录》分别翻译为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fe和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ving,他认为翻译成RecordofTransmissionandPractice更为妥帖;施友忠(Vincent Y. C. Shih)则将《传习录》翻译为RecordofInstructionsforMoralCultivation;王昌祉(Wang Tch’ang-tche)翻译为CollectedLessonsoftheMaster;卜德(Derk Bodde)翻译为RecordofInstruction;张君劢翻译为RecordsofInstructionsandPractices;艾文贺(Philip J.Ivanhoe)译为ARecordforPractice[6]154-161。此外,倪德卫还指出《大学问》不应像陈荣捷一样翻译成AnInquiryontheGreatLearning,而应该译为QuestionsaskedbysomeoneabouttheGreatLearning。涉及阳明学的具体概念,陈荣捷将“致良知”的“致”翻译为“To extend”,施友忠则认为应将“致”译为“To realize”或“To apply”。在陈荣捷的翻译中,他还把“良知”翻译为“innate or original knowledge”,把“格物”翻译为“the investigation of things”,“致知”被翻译为“the extension of knowledge”,而秦家懿主张把“良知”“心”“格物”“致知”等哲学概念直接音译。在阳明学向西方的译介传播过程中,英语语言文化的通约性成为翻译、理解和认识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争论也恰恰说明阳明学作为儒家哲学在思辨中的张力。
综上所述,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传播主要围绕《传习录》展开,一方面表现为亨克等西方学者从西方宗教思想的角度理解和认识阳明学;另一方面也显示阳明学自身的内在张力,通过陈荣捷、秦家懿等海外汉学学者的翻译,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形态为西方学者所理解。
二、阳明学与西方的哲学思想研究
阳明学既是中国儒家的重要哲学思想,也是中国近代思想转折的萌芽。从阳明学的哲学思想研究来看,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等日本学者重点强调了其在中国思想史中的近代思维意义[7]1-43。它不仅对泰州学派、李卓吾等学者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还影响到日本幕末的维新志士[8]111。但是,西方关于哲学思想视域下的阳明学研究则显得比较迟缓。
从目前关于阳明学在美国的传播研究来看,按照传播和研究来说,主要划分为1910-1979年、1980-至今的两个阶段[9]28-30与通识译介(1960年以前)、学术繁荣(1960-1980年)、多元化研究(1980年至今)三个阶段[2]121-125。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也大致符合上述时间的发展,但是笔者尝试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阳明学在西方的传播是一个连续的动态发展过程。因此,从西方哲学视域下审视阳明学的传播研究,可以引发我们对儒家哲学在海外传播问题上的诸多思考。
阳明学在西方的哲学思想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致良知”课题。约瑟夫·周(Joseph Kuang-su Chow)在探讨超然(Detachment)与介入(attachment)、存在、知识、无私、爱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道教、禅宗“无”的智慧对王阳明思想的影响,认为阳明学的“致良知”属于超然之道[10]。在柯雄文看来,“良知”是阳明学的道德教育[11]。瑞士汉学家、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把阳明学的“良知”解释为“心理—素质概念”“道德—批判概念”“宗教—神性概念”,实质上概括为本原能力、本原意识、本原实现,“将现象学、汉学、阳明学的研究推向更高水平,对于沟通中西思想文化,增进相互理解,推动共同的学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12]。艾文贺指出,“良知”(pure knowing)和“良能”(pure ability)是“理”的外在表现,生而具有,非孟子所谓后天培养,不过是“致良知”(to extend pure knowing)[13]46。就目前学界研究而言,关于阳明学“致良知”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DasWichtigsteimLeben:WangYangmingundseineNachfolgerüberdie‘VerwirklichungdesursprünglichenWisssens’ )。
此外,为了能更好地理解阳明学的“良知”意蕴,不少学者还将阳明学与西方哲学进行了比较。彼得·张(Peter T.C. Chang)通过比较巴特勒与王阳明的道德观和良心观,指出二者的相似点在于以终生的道德修养为实现作为人类最高道德规范的“良知”;不同点是巴特勒主张“警醒”以达到“基督徒”的目标,而王阳明则是以“静思”成为“君子”[14]。
除了上文提及的亨克以外,法国汉学学者王昌祉围绕阳明心学展开对王阳明良知的学理性研究,并撰写法语论著:LaPhilosophieMoraledeWangYangming(《王阳明的道德哲学》)。德国汉学学者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通过德文专著GeschichteDerNeueyenChinesisechenPhilosophie(《中国近代哲学史》)论及王阳明的心学与朱熹、陆象山的思想关联。不过,较之王昌祉与阿尔弗雷德·佛尔克对阳明心学的重视,亨克则从“心即理”“知行合一”“万物一体之心”三个方面对阳明进行了系统性探讨。他指出阳明学中对“本心”的论述表明人是一切事物的衡量标准,进而引发每个人需要将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义务,从而衍生出自由平等的观点[3]13-14。而西方学界对阳明学关注的另一重点是“知行合一”。
关于“知行合一”的研究,柯雄文在《知行合一:王阳明的道德哲学研究》中,从伦理学角度重新诠释阳明学知行合一的内涵和意义[11]。沃伦·弗里西纳(Warren G.Frisina)从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展开对阳明学“知行合一”概念的讨论,并将其翻译为“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知识与行动的统一)[15]。伊莱瑞(Larry Israel)在《合一的边缘:王阳明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帝国、暴乱和伦理(1472-1529)》(DoingGoodandRiddingEvilinMingChina:ThePoliticalCareerofWangYangming)中从心学与兵学的内在关联探讨了其哲学与军事思想的关系[16]3。虽然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对“知行合一”概念的诠释,但是整体来看,这些研究都在尝试通过以一种西方式的思维打开阳明学“知行合一”内涵的大门,进而能够以一种西方的话语重新阐释其内在意义。
无论是“致良知”还是“知行合一”,西方关于阳明学哲学意义的诠释显示了其思辨的活力与温度,阳明学的研究不是历史堆积的结果,而是不断被认识、理解的哲学范畴。在英语乃至其他西方语言的体系下,阳明学在译介传播的基础上能够不断深入地展开哲学讨论,充分体现出其在西方哲学领域的延伸和张力。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不少理解仍然没能超出西方哲学思维的界限。但是,不少学者能在文献译介的前提下进行进一步的诠释,这是阳明学在西方连续性、动态化发展的标志。与此同时,西方关于阳明学的研究也显示出百花齐放的趋势。
三、阳明学与西方的理论视角
随着西方学界对阳明学的关注,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了阳明学的研究中。于是,就形成了不同理论视角对阳明学思想的审视和诠释。这也是近年来阳明学研究的新态势。
在这些西方研究阳明学的新态势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视角是比较哲学研究。秦家懿通过论文《真实的自我:王阳明与海德格尔》(“AuthenticSelfhood”:WangYang-mingandHeidegger)比较分析了王阳明的“心”(mind)和海德格尔的存在(Dasein)。沃伦·弗里西纳在《知行合一:走向知识的非表象理论》(TheUnityofKnowledgeandAction:TowardaNonrepresentationalTheoryofKnowledge)中利用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非表象理论比较了王阳明与美国实用主义学者杜威、“过程哲学”学者怀海德的实践哲学。杨庆球(Jason Yeung)在《成圣与自由:王阳明与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比较》(SanctificationandFreedom:AComparativeStudyontheThoughtofWangYang-mingandChristianity)围绕“成圣”与主体性自觉,比较了王阳明与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祈克果(Soren A. Kierkegaard)的思想。围绕人性、“恶”,以及对激进人类的定义等问题,金洽荣(Heup Young Kim)在《王阳明与卡尔·巴特:一场儒家和基督教的对话》(WangYang-mingandKarlBarth:AConfucian-ChristianDialogue)中比较分析了王阳明与卡尔·巴特思想的相似点。德国奥尔登堡大学哲学博士大卫·巴拓识(David Bartosch)从比较哲学的视角在传统思想语境中系统分析了德国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库萨·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与王阳明的思想,并出版《“不知之知”抑或“良知”?——库萨·尼古拉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WissendesNichtwissen”oder“GutesWissen”?ZumphilosophischenDenkenvonNicolausCusanusundWangYang-ming)。姚新中比较了王阳明与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思想,指出二者虽然代表了中西方的学习文化,但却存在本质性的不同,前者是“道德的、主观的、直觉的方法”,而后者则是“科学的、客观的、积极的方法”[17]433。诺曼·何(Norman P Ho)在围绕阳明学探讨中国自然法的同时,对西方早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等的思想与阳明学进行了比较,认为阳明学是“连续性的自然法理论”[18]1。从比较哲学的理论视角来看,西方学界关于阳明学的研究既包括同质性的普遍性思想研究,也存在异质性的特殊性思辨,显示出人类哲学在发展历史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同时,这种或同质或异质的研究体现了阳明学作为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共通性与延展性。
不过,在西方研究阳明学的理论视角中,最具有转折性意义的是前文提到的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他通过现象学解释阳明心学,开辟了西方阳明学研究的新理论视角,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积极意义。卢盈华不仅继承了耿宁的现象学研究思路,还结合比较哲学的理论视角比较分析了王阳明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的价值、情感等概念[19]197-211;与此同时进一步以现象学作为研究理论,探讨了王阳明思想中关于道德的判断、知识、经验等问题[20]309-323。从这个角度来说,耿宁所开创的现象学视野下的阳明学研究是一种范式上的重大转折,他不同于过去简单地围绕某两种或某几种人物、思想的比较,而是真正从西方哲学开辟阳明学研究的领域。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王庆节所言,耿宁对阳明学的研究“是在西方的现象学传统中首创了一条现象学的阳明学领域,而且更可以说是在中国以及东亚的阳明学研究中开辟了一条阳明学的现象学解释新路”[21]11-12。
与此同时,历史学学者也不断推进关于王阳明传记研究的进程。杜维明(Tu Weiming)针对其生平与思想形成之间的关联,指出阳明之于儒学,毫不逊色于马丁·路德之于基督教[22]。之后,白安理(Bresciani Umberto)说道:“当我意识到西方还没有完整的王阳明传记时,我就在现有的传记基础上着手书写,虽然说不上是个大部头、不能无所不包,但足够让我们了解王阳明其人其事,”[23]3他根据王阳明成长的过程完整地记录了其思想的发展过程。而关于王阳明及其思想,历史学家这样给予评价:“明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王阳明,他在接受儒家道德思想的基础上,主张能够通过静思和经验发掘人人所拥有的、天生的道德知识,而不是仅仅依靠学习儒家经典。他认为普通人也可以理解儒家美德,鼓励学者与普通人互动联系。儒学者们为了掌握和发展儒家传统,造成对王阳明思想一个多世纪的激烈争论”[24]483-484。由此可见,历史学界不仅从王阳明的个人成长历程挖掘其思想的变化与转变,还将阳明学置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评价。
从比较哲学到现象学,再到历史学,西方关于阳明学的研究视角在不断切换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入地思考阳明学的成因及思想特质。在此基础上所引发的对世界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的探讨,显然更能引发西方学界的共鸣。这也说明西方学界对阳明学的认识愈加成熟,成为可以融入西方哲学体系的重要课题。
结语
中国儒家哲学中,阳明学因其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这种影响也扩展至东亚。关于阳明学的研究在东亚学界较为普遍,但是阳明学在西方的研究却一直未能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重点。在这一问题的基础上,阳明学在西方学界是如何译介传播的,是怎么诠释阳明学的哲学内涵的,是用怎样的理论视角研究阳明学的,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国际汉学乃至世界哲学的重要课题。
根据上述论述可知,在译介传播方面,宗教思想对阳明学在西方的译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恰恰是宗教语言的影响以至于阳明学在具体术语的翻译上呈现出多元化的理解和认识,造成西方对其思想的误读。在哲学思想研究方面,“致良知”“知行合一”等概念的诠释也是在译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翻译所造成的误读也很容易引起诠释上的误解。不过,在西方学人特别是华裔汉学家的不断努力下,阳明学所折射出的普遍性意义与西方哲学具有共通性。这也为西方对阳明学的理论视角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理论视角方面,比较哲学最先针对阳明学与西方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发问,比较分析了王阳明与海德格尔、马丁·路德、祈克果、卡尔·巴特等哲学家思想上的异同。一直待到现象学开辟了研究阳明学的新范式,顺利地让比较上升到具有公开性讨论的可能。随着西方对阳明学的重视,历史学也逐渐开始结合王阳明的成长经历思考其思想形成动因。这些研究都为阳明学在西方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多维的立体视野。同时,这也体现了阳明学作为中华传统思想在西方哲学中的张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