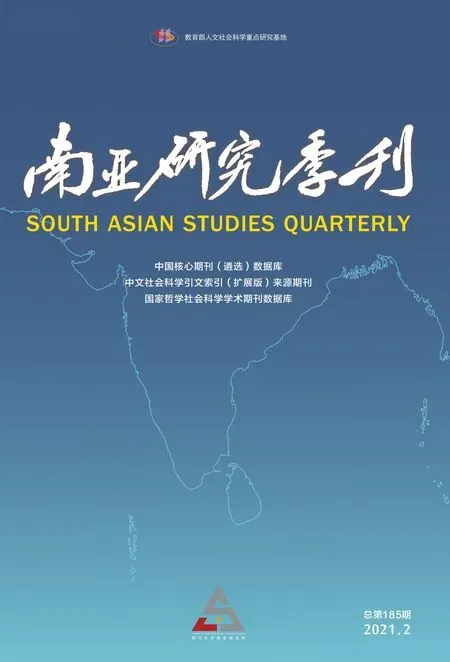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与中国应对 *
杨翠柏 张雪娇*
【内容提要】 近年来,印度不断制定、修改其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以促进外商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改善印度营商环境。实际上,由于对国家利益的过度强调,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已背离了其改革初衷,偏向性地强调国家管制权而忽视了对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究其本质,系激进的“国家中心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制度外化,导致印度扩大解释和滥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对投资者采取武断性的不利措施,并对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采取日益保守甚至排除的态度。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也对中国投资者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加上印度出于中印特殊地缘政治考量,为中国投资者“量身定制”的针对性、歧视性制度,导致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面临结构性难题。对此,我国必须保持对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变化的敏感性、警惕性,积极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作为发展中大国,印度对外国投资需求迫切并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国投资的举措,如自2010年起发布《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Consolidated FDI Policy)并及时进行修订和更新,以促进投资自由化和合理化。(1)印度历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参见:https:∥dipp.gov.in/policies-rules-and-acts/press-notes-fdi-circular.(2021-3-19)2020年初印度政府还计划设立投资法庭,以期加速国际投资争端在印度国内得到解决,促进外商投资、提振国内经济。(2)Aditi Shah,Aftab Ahmed.Exclusive:India plans new law to protect foreign investment—sources.https:∥in.reuters.com/article/india-investment-law-idINKBN1ZF0FG.(2020-1-16)印度政府的计划包括任命调解员、设立投资争端解决的“快速通道法庭”、在高级法院设立投资法庭等。当然,印度政府的另一目的是缓解印度所面临的国际投资仲裁压力,试图通过新法律给外国投资者带来信心,将投资争端留在印度国内解决,并弥合与部分国家间双边投资协定缺失问题。不过印度国内法显然很难取代双边投资协议和国际投资仲裁,合同的执行仍是在印投资者最担心的问题之一。然而,从近年来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包括国内层面印度FDI法律制度和政策,以及国际层面投资条约制度)的变化和实践角度分析,印度的做法又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吸引和鼓励外商投资的初衷相背离,尤其是泛化后的国家利益考量在其投资法律制度中的比重显著上升,政治问题向经济领域渗透融合,致使印度国内投资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印度履行、谈判、签署国际投资协定中的保护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在印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对我国投资者而言,印度的投资法律制度是限制性、歧视性的,显著增加了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的阻力和风险。面向未来,印度激进的国家利益保护理念已然深刻扎根于其投资法律制度之中,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重塑印度投资法律框架这一基本面只会加强而难以弱化。鉴于此,本文以近年来印度国内与国际层面的投资法律制度走向为研究对象,分析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变化的新趋势,以及根植于政策背后的强化国家利益(3)国家利益,是指以维护国家和政府利益为目的一整套价值和制度体系,在投资政策中,包含“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和“国家利益”等抽象概念以及围绕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广泛而模糊的制度规范。国家利益既包括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等传统安全利益,也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利益。的政治逻辑,并提出中国应对。
一、国内层面: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立法与政策变化
(一)制度框架与制度变更
所谓印度投资法律制度,泛指适用于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投资的国际条约、国内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具体制度,以及印度司法机关的判决和印度外商投资主管部门的相关决定。国内层面的立法以印度1999年《外汇管理法》(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1999)及相关规则为基础框架,包括2002年《竞争法》(Competition Act,2002)等反垄断立法和1951年《工业(发展和管制)法》[Industries (Development & Regulation) Act,1951]等特定行业立法。在外商投资主管机构和权力划分上,根据1999年《外汇管理法》规定,印度中央政府所属部门负责制定外商投资制度,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of Indian,RBI)则制定有关证券发行或转让、外汇管制规则,这导致两部门在规则制定和外商投资监管上长期存在权力重叠、权限不清和冲突的现象(印度储备银行的外汇管制规则往往涉及外商投资制度)。2015年,印度修改了《金融法》(the Finance Act,2015),(4)THE FINANCE ACT,2015,NO.20 OF 2015,blob:https:∥www.sebi.gov.in/db165382-a8d3-4ec3-a61c-1a67afa23442.(2015-5-14)其第143、144条对1999年《外汇管理法》第6条“资本账户交易”、第46条“中央政府制定规则的权力”、第47条“印度储备银行制定规则的权力”作出调整,弥合了外商投资规则制定权和监管权的划分漏洞。根据新规定,印度储备银行负责债务工具类(Debt Instruments,包括政府和公司债券、贷款等)外商投资监管和规则制定;而印度政府负责非债务工具类(Non-debt Instruments,如公司股权投资、不动产交易等)监管和规则制定,且债务和非债务工具的区分由印度中央政府与印度储备银行协商后决定,这实际上扩大了印度中央政府的外商投资管理权限。据此,2019年10月,印度财政部发布了《外汇管理(非债务工具)规则》,(5)Ministry of Finance.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Non-debt Instruments) Rules,2019.https:∥taxguru.in/rbi/foreign-exchange-management-non-debt-instruments-rules-2019.html.(2020-10-17)印度储备银行发布了《外汇管理(非债务工具支付和报告方式)条例》。(6)Reserve Bank of Indian.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Debt Instruments) Regulations,2019.https:∥taxguru.in/rbi/foreign-exchange-management-debt-instruments-regulations-2019.html.2019-10-17。新的规则取代了此前的《印度境外居民外汇管理(转让或发行证券)规定》(the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Transfer or Issue of Security by a Person Resident outside India) Regulations,2017)、《外汇管理(印度不动产的收购和转让)条例》(the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of Immovable Property in India) Regulations,2018)等制度。此外,具体的、综合性的外商投资制度主要由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the Department for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Internal Trade,DPIIT)制定。(7)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files/FDI-PolicyCircular-2020-29October2020.pdf.(2020-10-15)2020年10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根据前述规则和条例,更新了其2017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新政策于2020年10月15日生效。2020年11月,印度工业和内部贸易促进部又发布了修订后的《处理FDI申请的标准操作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for Processing FDI Proposals,简称《标准操作程序》](8)DPIIT.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for Processing FDI Proposals.https:∥fifp.gov.in/Forms/SOp.pdf.(2020-11-9),进一步明确了投资审判流程。
(二)国内立法与政策中的国家利益考量
1.特定部门限制
印度主要通过外资准入条件、禁止性和限制性投资领域、敏感行业和敏感地区或国家限制等方式规范和限制外国投资者的行为,以维护印度“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1999年外汇管理法》等规定,外国投资者可以通过 “自动路径”(Automatic Route)或“政府/审批路径”(Government/Approval Route,简称“政府路径”)进入印度投资,(9)印度允许外国直接投资进入的途径包括“自动路径”与“政府路径”。其中,自动路径意味着更少的限制与更自由化的监管,在自动路径下,外国直接投资无需得到印度储备银行或印度政府的事先批准。批准机构会根据外国直接投资的部门/活动以及投资性质而定。例如矿业部门需要矿业部的批准,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银行需要金融服务部的批准。而“政府路径”则需要事先获得印度储备银行或印度政府的批准。并针对敏感行业设置了安全审查程序。当前,印度仍然禁止外国投资者投资彩票、烟草、赌博等业务,且除获得豁免外,禁止私人投资原子能和铁路运营等战略部门(这些部门由政府拥有和控制)。在行业限制方面,根据2020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广播、电信、卫星(建设和运营)、私人保安机构、国防、民用航空器以及含钛矿物、钛矿石的开采和选矿等特殊监管行业,除须获得直接主管部门的批准外,还应通过印度内政部(Ministry Of Home Affairs)的安全审查并取得安全许可证(security clearance)。其中,《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特别强调了广播和国防领域外商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其规定,广播领域实行“开放”的许可制度,安全许可方有权从“国家安全”角度限制被许可方在任何敏感地区开展经营活动,印度信息和广播部有权基于“国家安全”和/或“公共利益”考量,暂停许可证持有者或被批准者的活动,被许可或被批准方应立即遵守印度信息和广播部发出的行政命令。同时,被许可方不得进口或使用任何被认定为非法和/或对网络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设备,并确保其所提供的广播服务设备不会构成任何安全隐患,不违反任何有效规定和公共政策。此外,为“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合理提供广播服务目的,保留修改许可条件或加入必要新条件的权力。在国防领域,(10)2020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将“自动路径”下的投资限额从此前的49%放宽至74%,“政府路径”下可实现外商100%控股。2020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规定,国防部门的安全许可证由印度内政部根据印度国防部的指导方针授予,同时印度政府保留审查国防部门中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任何外国投资的权力。
2.敏感国家限制
2020年4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发布2020年第3号文件,修订了2017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11)Government of India,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Department for Promotion of Industry and Internal Trade FDI Policy Section.Revie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licy for curbingopportunistic takeovers/acquisitions of Indian companies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Press Note No.3(2020 Series).https:∥dipp.gov.in/sites/default/files/pn3_2020.pdf.(2020-4-17)第3.1.1条(12)原3.1.1条款规定,除被禁止投资的部门/活动外,非居民实体根据印度直接投资政策在印度进行投资。但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公民以及在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设立的实体只能通过“政府路径”才能在印投资。同时,禁止巴基斯坦公民或在巴基斯坦成立的实体投资国防、航天和原子能等领域。而修订后第3.1.1条(a)款将国家范围由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扩大到所有与印度接壤的国家,且将“投资者”范围界定为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实体,或投资的实际受益人位于该接壤国家或属于该类国家公民。同时,修订后第3.1.1条增加了第(b)款,根据这一条款规定,如果直接或间接地转让印度境内某一实体的任何现有或将来的外国直接投资所有权,导致实际所有权人属于第3.1.1(a)款的限制范围,则该实际所有权的变更也需得到政府批准。的规定(该文件内容已纳入2020年《综合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中),其目的是遏制COVID-19大流行期间外国投资者对印度公司进行机会主义收购行为,(13)Ministry of Commerce & Industry.Government amends the extant FDI policy for curbing opportunistic takeovers/acquisitions of Indian companies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15711.(2020-4-18)针对性地提高了来自中国等与印度接壤国家投资者在印度投资的门槛。按照新规定,凡与印度接壤国家的实体或投资的实际受益人(the beneficial owner)(14)文件修订内容尚未对“所有权”“权益所有权人”等概念进行界定,有印度学者指出具体概念可参考其他文件的定义内容,例如,对“所有权”的定义可以参考《主方向——印度境内的外国投资》(the Master Direction—Foreign Investment in India)中的规定,即印度公司的所有权指占该公司资本总计50%以上的实际持有。对“权益所有权人”的界定可以参考印度2013年《公司法》(the Companies Act,2013)第90节、2018年《公司(重要实际所有权人)规则》[the Companies (Significant Beneficial Owners) Rules,2018]以及2002年《防洗钱法》(Prevention of Money Laundering Act,2002)的相关规定,即最终拥有或控制某一实体或者代表某一实体进行交易的人(包括对法人行使最终有效控制的人)。参见:Jidesh Kumar and Prithiviraj Senthil Nathan.Revie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Policy of India for Curbing Opportunistic Takeovers/ Acquisitions of Indian Companies Due to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https:∥ksandk.com/investment/9226/.(2020-4-18)位于该接壤国家或属于该类国家公民的,其投资只能通过“政府路径”进行,而此前只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两国受此“政府路径”的限制。同时,新投资法律制度加强了对权益所有权(the beneficial ownership)取得的限制,如果直接或间接地转让印度境内某一实体任何现有或将来的投资权益,导致实际受益人属于第3.1.1(a)款限制范围内,则该实际所有权变更也需得到政府批准。
二、国际层面:印度投资条约制度的变化
(一)印度投资条约领域的转型
印度签署的国家投资条约和印度相关投资条约、投资仲裁政策,奠定了印度对外国投资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和救济框架,也是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印度是国际投资领域的重要参与者,尽管其兼具资本输入国和资本输出国双重身份,但印度似乎更介意国际投资协定对其公共政策空间的约束,以及由国际投资协定所带来的挑战和仲裁败诉的成本与风险,在更激进的国家利益保护理念下,印度总体上更强调东道国的绝对主权和管制权,放弃了当前以投资者保护为重点的双边投资协定主流范式。(15)王彦志、王菲:“印度2015年双边投资条约范本草案评析——White Industries v.India案裁决阴影下的重大立场变迁”,《国际经济法学刊》,2015年第2期,第168页。尤其是2004年以来,印度政府不断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受挫,并面临大额经济赔偿,直接导致印度重新反思国际投资条约在国家与投资者利益保护方面的平衡问题,并试图采取对国家利益更为有利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在印度投资条约与投资仲裁领域转型的推动因素中,最具重要影响力的案件当属澳大利亚怀特工业公司(简称:怀特公司)一案(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td v The Republic of India)。(16)White Industries Australia Limited v.The Republic of India,UNCITRAL,https:∥www.italaw.com/sites/default/files/case-documents/ita0906.pdf.(2011-11-30)本案中,因印度法院一直拖延执行ICC裁决,怀特公司遂提起了一项特殊的国际仲裁,其主张仲裁裁决在印度法院被搁置9年时间属于不正当的、无法接受的拖延,违反了投资条约保证的提供“有效的主张索赔的手段”(effective means to assert claims)义务并导致其遭受损害。(17)Harisankar K.Sathyapalan.Indian judiciary and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a BIT of a control? Arbitration International,2016,0,pp.9-10.仲裁庭支持了该主张,裁定印度违反了其双边投资条约下为投资者提供“主张和执行权利的有效手段”的义务,并被要求履行此前裁决义务并支付相关利息和法律费用。继怀特公司一案后,2011—2015年期间,外国投资者又针对印度政府提起了数起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如沃达丰(Vodafone)(18)Vodafon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BV v.Government of India [I],PCA Case No.2016-35,https:∥www.italaw.com/cases/2544.、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19)Deutsche Telekom v.India,PCA Case No.2014-10.https:∥www.italaw.com/cases/2275.和日产汽车(Nissan Motor Co)(20)Nissan Motor Co.,Ltd.v.Republic of India,PCA Case No.2017-37.https:∥www.italaw.com/cases/7627.等公司就有追溯效力的税收索赔和违约纠纷等提起国际仲裁,如果印度在这些案件中败诉将直接面临巨额赔偿。
国际投资仲裁的压力直接迫使印度政府迅速采取行动,尤其是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着手推行的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改革计划。其中,以印度2016年《印度双边投资协定示范文本》(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简称为《2016年投资范本》)(21)Model Text for the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https:∥dea.gov.in/sites/default/files/ModelBIT_Annex_0.pdf.为标志,印度在国际投资条约和投资仲裁方面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除推出《2016年投资范本》外,印度政府还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投资条约框架改革措施,大规模终止和废除印度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自2016年起,印度计划对所有到期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以代替到期协定,(22)驻印度经商参处:印度计划重新谈判所有双边投资协定,http:∥in.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607/20160701366376.shtml.(2016-7-26)随后印度开启了大规模终止双边投资协定的行动,并主张投资伙伴国在《2016年投资范本》基础上与印度重新进行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同时,印度向多国提议通过联合解释声明(Joint Interpretative Statement)的形式,参照《2016年投资范本》对双方现行有效的投资协定进行澄清、补充和修改。(23)如2017年印度与孟加拉国签署了一份联合解释声明,双方在保留2009年双边投资协定的前提下,对该协定的内容加以调整和澄清。参见:Joint Interpretive Notes on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India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https:∥dea.gov.in/sites/default/files/Signed%20Copy%20of%20JIN.pdf.
(二)印度投资条约制度改革对国家利益的强化
1.投资仲裁方面
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上,印度通过阻止或拖延投资者提起国家投资仲裁来维护其国家利益。《2016年投资范本》第14.3条规定了“用尽当地救济措施”的原则,根据该规定,投资争端发生后,投资者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起一年内,向东道国的有关国内法院或行政机构提出索赔,以寻求国内救济措施,只有在用尽东道国国内司法和行政救济措施而仍未达成令投资者满意的方法后,或者投资者努力寻求国内补救措施后确定继续寻求国内补救措施将是无效时,投资者才能寻求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程序的救济。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与巴西于2021年1月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将国家利益保护推向了新的层级,该双边投资协定抛弃了主流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中广泛适用的投资者-国家仲裁机制,将投资争议推回到最传统的争端解决模式,即通过国家间仲裁机制、双方建立的索赔委员会或者外交途径解决。(24)Prabhash Ranjan.India-Brazi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A New Template for India?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0/03/19/india-brazil-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a-new-template-for-india/.(2020-3-19)尽管该投资协定不完全代表印度双边投资协定改革初衷和方向,但此次印巴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也反映出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充分维护东道国管制权和国家利益,反对国际投资仲裁的基本政策走向。
印度的国家利益倾向不仅体现在对前述“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限制或否定上,还表现在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中。由于印度并未加入《关于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公约第53条第1款关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执行的规定尚不适用于印度。同时,德里高等法院在Union of India v Vodafone Group PLC United Kingdom & Anor (2017)(25)CS(OS) 383/2017 & I.A.No.9460/2017.http:∥lobis.nic.in/ddir/dhc/MMH/judgement/07-05-2018/MMH07052018S3832017.pdf.(2018-5-7)与Union of India v Khaitan Holdings (Mauritius) Ltd &Ors (2019)(26)CS (OS) 46/2019,I.As.1235/2019 & 1238/2019.http:∥lobis.nic.in/ddir/dhc/PMS/judgement/29-01-2019/PMS29012019S462019.pdf.(2019-1-29)两个案件的判决中指出,尽管印度签署了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但印度作出了“商事保留”,德里高等法院认为投资仲裁是非商事性质的,因此法院没有义务适用《纽约公约》的规定强制执行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另外,在国内法层面,投资仲裁既不属于国际商事仲裁,也不是国内仲裁,印度《仲裁和调解法》中的仲裁裁决执行机制也不能适用,(27)印度《仲裁和调解法》第一部分“仲裁”规定了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第二部分“外国仲裁裁决的执行”规定了国际商事仲裁和外国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参见杨翠柏、张雪娇:“印度商事仲裁裁决执行制度”,《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2期,第77页。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国际投资仲裁裁决难以在印度得到强制执行。这既是一项制度缺陷,也可以说是印度有意采取的向制度漏洞“逃逸”的策略,变相阻止外国投资者提起投资仲裁,引导投资者与政府进行协商解决争端。整体来看,当前印度总体上对投资仲裁呈现出反对态度,印度屡次作为国际投资仲裁被申请方的经历最终可能将印度推向保护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28)Simon Weber.What Happened to Investment Arbitration In India? http:∥arbitrationblog.kluwerarbitration.com/2021/03/27/what-happened-to-investment-arbitration-in-india/.(2021-3-27)
2.双边和多边投资条约方面
印度在投资条约方面的国家利益保护倾向主要表现在对《2016年投资范本》对“投资”的狭窄定义和对“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的宽泛界定上。根据印度的立场,《2016年投资范本》作为印度与他国进行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依据,其目的是“为在印度的外国投资者和在外国的印度投资者提供适当的保护,平衡投资者权利和政府义务”。(29)Draft Indian Model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Text.https:∥www.mygov.in/group-issue/draft-indian-model-bilateral-investment-treaty-text/.但事实上《2016年投资范本》的大部分关键性条款并未能协调投资者保护和东道国监管权之间的冲突,而是侧重于加强印度对其领土内投资者和投资的管制权,以维护印度国家利益,这集中表现在《2016年投资范本》对“投资”的定义和例外条款上。《2016年投资范本》第1.6条将“投资”定义为:位于东道国,并按照东道国法律成立、组织和经营,并由投资者善意拥有或控制的企业。但对“投资”的定义还采用了投资者与资产相结合的界定方式,规定投资者和投资必须满足第9、10、11、12条规定的“投资”的具体特征和要求,包括遵守反腐败、披露、税收、遵守东道国法律等义务,并要求投资者和投资努力通过其管理政策和做法为东道国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也就是说,一旦投资者未满足前述要求,则该“投资”将被排除在投资协定的保护范围之外,无法享有投资条约中的投资者权利或据此提出投资条约仲裁。在例外条款的规定上,《2016年投资范本》第16条规定了宽泛的“一般例外”情形,包括为维护公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确保金融稳定、平衡国家收支、维护公共卫生和安全、环境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目的,东道国在认为“必要”时可采取普遍适用的行动或措施。根据第17条“国家安全例外”规定,东道国采取的与可裂变和可聚变材料或产生这些材料的材料有关的行动,在战争或其他国内或国际关系紧急情况下的行动,有关武器、弹药和战争工具的贩运等的行动,以及为保护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免受破坏的行动等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属于违反投资条约的行为。《2016年投资范本》“附件一”还规定了“国家安全例外”的不可裁决性,凡缔约方因“国际安全例外”违反投资协定义务的,国际投资仲裁庭均不具有管辖权。由于《2016年投资范本》并没有对“一般例外”的“必要”作出说明和限定,“国内或国际关系紧急情况”等情形也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东道国根据第16条、17条例外条款的规定,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和灵活的政策空间,极易导致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和滥用以及投资问题的“政治化”。此外,由于《2016年投资范本》中对“公平和公正待遇”条款的狭义规定,以及排除了“最惠国待遇”和税收措施规定,《2016年投资范本》并未能平衡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与东道国的监管权,其背后的目的似乎是助力印度政府在未来免受双边投资条约索赔和投资仲裁裁决对印度财务造成影响。(30)Prabhash Ranjan,Pushkar Anand,The 2016 Model Indian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A Critical Deconstruction,Northwester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Business.2017,Volume 38,Issue 1,p.52.也因此,《2016年投资范本》本质上已与其印度所主张的立法意图相悖,带有强烈的保护主义特征,倾向性地维护了印度国家利益而对外国投资者的权利关注不足。同时,印度试图以联合解释声明等方式修订和澄清已有的投资条约、终止并重新谈判大部分双边投资条约的最终目标,均是力图在新的投资保护规则中维护和实现印度国家利益。同时,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问题上,印度的审慎、拒绝态度也彰显了其保护主义与保守主义,如在谈判中印度主张在RCEP中纳入以保护国家基本安全利益为由的数据本地化措施条款,(31)Kirtika Sunejaand Dinesh Narayanan,India wants data localisation in RCEP for security interests.http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news/economy/policy/india-wants-data-localisation-in-rcep-for-security-interests/articleshow/71549390.cms.(2019-10-12)并最终基于经济安全与中印关系拒绝加入RCEP。(32)Sumit Sharma,India has good reason to reject the RCEP.https:∥asiatimes.com/2020/11/india-has-good-reason-to-reject-the-rcep/.(2020-11-15)
三、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一)制度变化中的“中国”因素
近年来,由于中印地缘政治等原因,中国被置于印度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这也集中反映在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制定、修改过程中对“中国”的针对性,以及专门对中国投资者“量身定制”的歧视性条款。如尽管2020年4月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发布的2020年第3号文件表面上将所有与印度接壤的国家列为“敏感国家”,并实施限制措施和特殊审查,但因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一直属于“敏感国家”范围,而尼泊尔、阿富汗、不丹和斯里兰卡等邻国对投资印度的兴趣不大,因此普遍认为印度此举主要针对中国。(33)Remya Nair,Govt revises FDI policy over fears of Chinese takeover of Indian firms amid Covid-19 crisis.https:∥theprint.in/economy/govt-revises-fdi-policy-overs-fears-of-chinese-takeover-of-indian-firms-amid-covid-19-crisis/404438/.(2020-4-18)同时,根据新的《标准操作程序》,前述来自“敏感国家”的投资者和投资除按照“政府路径”取得投资项目主管部门政府审批手续外,必须接受印度内政部的强制性安全审查并取得安全许可。
不仅如此,2020年7月23日,印度政府修订了《2017年财政通则》(the General Financial Rules,2017),(34)Ministry of Finance:Restrictions on Public Procurement from certain countries.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640778.(2020-7-23)修订后的通则允许所有政府机构以国防和与国防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项(包括国家安全)为由,对来自与印度接壤国家的投标者施加限制。根据新的规则,只有当投标人在印度工业和国内贸易促进部设立的登记委员会处注册登记后,与印度相接壤国家的投标人才有资格投标货物、服务、工程等政府公共采购项目。该命令的采购人涵盖了从政府处获得财政支持的所有公共部门、自治机构等。在采购责任主体上,印度中央政府认为,尽管各邦政府采购由各邦主管当局负责,但各邦有义务维护国家政治与安全,考虑到各邦政府在印度国家安全和国防中的关键作用,印度中央政府援引《印度宪法》第257条第1款(35)印度《宪法》第257条为“在特定事项上联邦对邦的管理”,其第1款具体规定为:各邦行政权的行使不应妨碍或者损害联邦的行政权的行使,联邦的行政权包括在印度政府认为必要的情形下向邦发布命令的权力。参见《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北京:中国监察出版社,2012年,第824页。之规定,要求邦政府和相关单位在政府采购中执行新规定。(36)在一些有限的情形下,印度政府也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如放宽为遏制COVID-19疫情的医疗用品采购的限制,免除了印度政府提供额度或发展援助国家投标者的事先登记要求。同时,印度开支部(The Department of Expenditure)制定了一份关于公共采购的详细命令,以限制邻国投标者的方式来保障印度国防和国家安全。印度对《2017年财政通则》的修改同样对中国投资者产生歧视性影响,中国投资在政府采购相关项目中被重点限制,可以推定,印度试图在政府采购相关环节大范围排除中国企业。(37)“印度限制中企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world/20200731/2417124.shtml.(2020-7-31)
除以传统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采取限制性政策外,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变革也切准了与投资相关的经济、科技、数据、互联网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以及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显著优势。如当前数据处理业务和商业化出售等使得数据成为数据密集型潜在投资者寻求收购的关键资产之一,数据引起的互联网和数据安全、个人数据保护等难题也成为印度投资法律制度所关注的重点。2019年12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向印度议会提交了《2019年个人数据保护法案》(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2019),(38)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Bill,2019.Bill No.373 of 2019.http:∥164.100.47.4/BillsTexts/LSBillTexts/Asintroduced/373_2019_LS_Eng.pdf.《2019年个人数据保护法案》涵盖了个人数据保护机制,对数据本地化和商业化、“数据受托人”模式、尽职调查和收购、数据跨境转移等方面作了规制。标志着继《2000年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2000)和《2011年信息技术规则》后,印度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数据立法;在禁用59款中国应用程序几天后,印度政府曾针对此事重申在印度开展数字和互联网业务的国际公司必须遵守印度有关数据安全和个人数据隐私的法规,外国投资者在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投资,必须符合印度政府建立的规则和监管框架。(39)NayanimaBasu.Foreign firms have to follow India's rules pertaining to data security and privacy:MEA.https:∥theprint.in/india/foreign-firms-have-to-follow-indias-rules-pertaining-to-data-security-and-privacy-mea/453466/.(2020-7-2)印度对中国企业采取限制性措施即是为了其所谓的经济安全。当前印度对中国投资的思维模式正如印度商业与外交政策研究智库平台Gateway House中所提到的,中国科技巨头公司和风险投资资金已成为中国投资印度(尤其是印度初创企业)的主要工具,尽管中国对印直接投资规模仅有约62亿美元,但已全面渗透进印度的社会、经济和科技生态系统中,中国对印度科技行业形成了远超其投资规模和投入价值的不成比例的影响力。(40)如字节跳动(ByteDance)旗下的TikTok已经超过YouTube成为印度最受欢迎的应用程序之一;小米手机规模比三星智能手机更大;华为路由器也被印度广泛使用;在30家印度独角兽公司中,有18家有中国投资。参见:Amit Bhandari and Aashna Agarwal,China's strategic tech depth in India.https:∥www.gatewayhouse.in/chinas-tech-depth/.(2019-11-14)
仍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3月,印度修订并通过了新的《敌产法》[The Enemy Property (Amendment And Validation) Act,2017],根据其规定,如中印之间发生战争或武装冲突,印度政府有权对我国及我国公民在印财产采取监管甚至没收措施。(41)杨翠柏、张雪娇:“印度《敌产法》的修订及对中国在印投资的影响”,《南亚研究季刊》,2018年第2期,第77页。近来,印度屡次挑起中印边境争端,中印关系的紧张局势下新《敌产法》出台,明显加剧了中国投资者的恐慌。印度方面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在印度的大规模投资,新《敌产法》对中国对印发动战争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作用,甚至有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建议印度政府直接依据《敌产法》对中国在印度的投资予以没收。(42)Amit Agrahari,What holds China back from waging war on India? The Enemy Property Act.And the fear is real,https:∥tfipost.com/2020/07/what-holds-china-back-from-waging-war-on-india-the-enemy-property-act-and-the-fear-is-real/.(2020-7-2)因此,尽管印度政府尚未适用新《敌产法》对中国在印投资采取措施,但毫无疑问,该部法律已然是悬在中国投资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
(二)制度变化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首先,印度针对中国采取的歧视性投资法律制度,将中国投资全部纳入“政府路径”,并增加印度内政部的安全审批程序,提高了中国投资者和投资的准入门槛,增加了中国投资者的时间、资金成本,并带来投资项目的不确定性。同时,受中印特殊地缘政治关系影响,当投资项目本身与政治问题、行政腐败等因素发生聚合时,中国投资者所面临的投资成本和风险将被成倍放大并可能处于不可控状态。整体而言印度对中国投资者的投资法律制度是歧视性的,印度的新政策将削弱中国投资者及其投资在印度市场的竞争力甚至被迫“出局”。
其次,印度投资条约理念和制度上的变化也将对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产生普遍性的不利影响。一是受到印度终止双边投资协定浪潮的影响,2006年中印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简称《中印投资协定》)(43)根据《中印投资协定》第16条第1款,协议有效期为10年,期满后除非一方通知另一方终止本协议,协议有效期自动延长10年,并以此顺延。于2018年10月3日被印度单方面终止,且由于印度未能加入RCEP,中印间在投资者保护上缺乏基本的国际投资保护法律框架,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也陷入投资条约保护缺失的窘境;印度政府制定的对中国投资者不利的法律制度和采取的歧视性、专断性行为将难以直接在国际法层面加以评判。二是印度对国际投资仲裁的排斥,将导致中国投资者在面临投资争端时难以得到有效、公平的解决。印度对用尽当地救济和东道国国内解决的重视,中国投资者将国际投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解决时将可能面临更多的来自印度政府法律制度和司法判决的制约,代表性的是印度“禁仲裁令”(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44)“禁仲裁令”(anti-arbitration injunction)是指由一国国内法院向当事人甚至仲裁庭或仲裁员颁布的终止或暂停仲裁程序的命令。参见:[法]伊曼纽尔·盖拉德:《国际仲裁的法理思考和实践指导》,黄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印度政府在McDonald's India Pvt.Ltd.v.Vikram Bakshi & Ors.以及Union of India v.Vodafone Group PLC United Kingdom & ANR CS(OS)等国际投资争端中多次试图使用“禁仲裁令”制度禁止外国投资者寻求国际投资仲裁。制度,印度政府利用该制度,向印度国内法院提起诉讼,拖延或阻止投资者将投资争端诉诸国际投资仲裁解决;同时,由于国际投资仲裁裁决难以在印度国内得到强制执行,因此即便中国投资者取得有利的仲裁裁决,该裁决也难以得到充分履行。
四、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法律制度变化的中国应对
(一)中国应对的难点分析
1.投资问题“政治化”
中印地缘政治关系决定了印度仍习惯性、常规性地以“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为由对中国投资者投资印度行为设限,将投资问题“政治化”。但理论上,地缘政治包括国家有机体、陆权论、海权论等传统地缘政治和以文明冲突论、网权论为核心的现代地缘政治。(45)李涛、张秋容:“印度地缘政治战略及对我国边疆安全的影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145页。印度对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施加诸多限制,正是基于传统地缘政治的权衡。一方面,由于中印边境分歧、印巴长期紧张关系和中巴友好关系等政治因素,中印经贸合作与中国企业在印投资向来属于印度的敏感议题,印度对中国投资者实施限制政策具有传统性——印度习惯于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角度审视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并将泛化后的国家利益渗透到中印经贸关系之中,对中国投资者进行大规模设阻甚至排斥。如在不动产取得和转让方面,印度《外汇管理法》及印度储备银行1999年《外汇管理法下不动产购买或者转让规定》(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of Immovable Property under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1999)对中国公民在印取得、转让、租赁不动产的行为进行特殊限制或规定了额外审批程序。(46)Reserve Bank of Indian,Master Direction—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of Immovable Property under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Act,1999.https:∥www.rbi.org.in/SCRIPTS/BS_ViewMasDirections.aspx?id=10196#:~:text=As%20per%20the%20provisions%20contained%20in%20Foreign%20Exchange,than%20agricultural%20land%2C%20plantation%20or%20a%20farm%20house.(2016-1-4)根据现行规定,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关切国家或地区的投资者需要获得印度储备银行的事先批准才能在印度购买或租赁不动产(不动产租赁期限少于5年的除外)。同时,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往往与政治、领土、外交等事项挂钩,一些随机因素尤其是中印关系波折的干扰甚至主导着印度对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法律制度的变化,为中国企业投资印度所面临的政策变化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尽管中印间拥有巨大的投资需求与合作潜力,但两国信任赤字难以弥合,印度将国家安全问题与投资制度相杂糅,随意调整投资规则、对中国投资者采取不公平的限制性、歧视性措施的行为,降低了中国投资者对印度的信心和信任,也对中印经贸关系产生了深远的不良影响。
2.印度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滥用
印度国内投资法律制度中涵盖了广泛的“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条款,并作为印度监管外国投资者和投资的主要依据,但印度国内投资法律制度并没有对印度“国家安全”作出明确界定。“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抽象性、概括性导致印度政府在使用“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条款时绝对的自由裁量权,且在程序上,印度外商投资申请的审查程序属于政府内部程序,印度政府无须经过任何听证或协商程序,也无须向申请方提供任何理由,即可批准或拒绝外商投资申请。而在国际制度层面,一般认为一国在战争或其他紧急情况下为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而采取的任何必要措施都不应被认为违反其国际承诺,国际投资法律也只能规制常态意义下的国家行为,一国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承诺不导致其基本安全利益的丧失,因而“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为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非常措施提供了例外的免责事由。与此同时,作为一个不断扩张的概念,“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语义的不断变迁也加大了对其界定的难度。(47)如有观点认为,传统上对国家利益的严格解释已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不仅包括传统的军事威胁、间谍和恐怖主义,还包括疾病传播、自然灾害、内乱、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重要产业受国外控制等。参见:余劲松:“国际投资条约仲裁中投资者与东道国权益保护平衡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第133-134页。加之安全利益往往属于东道国自行判断条款,在举证责任负担上,外国投资者承担了不属于安全利益的举证义务。因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条款的模糊性为印度任意解释和滥用东道国管制权提供了便利且实用的工具。如印度政府以维护主权和完整的名义,强行以中国应用软件从事有损印度主权、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为由,援引《信息技术法》第69A条和2009年《阻碍公众获取信息的程序和保障措施》的规定,禁用中国多款应用软件。(48)郑孜青:“中企在印投资风险预警与应对”,《中国外汇》,2020年第16期,第14页。尽管中国投资者可以指责印度的行为,但“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条款的抽象性、不可裁决性和举证困难的特定,仍增加中国投资者借由法律途径维护合法权益的难度。
(二)中国应对的策略分析
1.国家视角
虽然当前形势复杂,投资印度的前景也不甚明朗,印度作为我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国,我国必须积极应对、妥善处理在印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称《十四五规划》)第12篇中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并明确提出要“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支持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提高跨国经营能力和水平。引导企业加强合规管理,防范化解境外政治、经济、安全等各类风险。推进多双边投资合作机制建设,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境外投资立法”。因此,首先可以从国家层面探索解决当前我国投资者在印投资所面临的困境,坚持底线思维,在较长时间内做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一是加强政府间对话、增进战略互信,推进中印间双边和多边投资合作机制的建设。当前,即便2006年《中印投资协定》在满足特定条件下仍能适用,但其条款措辞的模糊性、文本的简约性、投资保护模式的陈旧性等特点已然弱化了其协调东道国与投资者利益的功能,无法满足中印投资者需求,随着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新一轮改革,我国应及时评估与印度签署新的投资保护条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并力图在新的投资协定中平衡国家利益和投资者利益,限制和明确“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条款的适用范围和具体适用条件、细化投资者待遇和保护条款。两国应该清醒认识到,两国投资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找到双方利益共同点和交汇点,共同致力于减少投资壁垒,加强投资审查机制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将投资问题“去政治化”,才是双方的合作共赢之道。
二是中印间地缘竞争关系长期存在的客观困局决定了,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面临的限制性、歧视性、不稳定性法律制度和措施的情况将成为常态,且无法从根本上予以避免,因此风险规避和预防就尤为重要。对此,我国应从国家层面加强智库建设,加大对印度投资法律风险的研究,发布并实时更新更为细化的、更具操作性的印度投资指南,构建“常态评估”与“紧急预警”相结合的投资风险警示机制。加强对企业和个人投资印度的监督管理工作,制定投资目的国风险等级目录,并据此分类、分级施行对外投资报批、审批手续,以行政手段协助投资者投资管控境外投资风险。
三是从国际法和外交层面加强对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的保护。印度对“投资者-国际争端解决”机制的排斥、中印双边投资条约的缺位、以及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关的国家保护主义,导致中国投资者难以通过投资仲裁或者诉讼手段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在此情况下,应考虑传统对境外投资者的保护模式,在必要时通过外交协商、谈判等传统途径维护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同时,如印度对中国投资者“朝令夕改”、援引《敌产法》没收投资者财产等对我国投资者造成重大损失时,我国应保留对印度采取反制措施的权利。
2.投资者视角
当下,由于“投资者-国际争端解决”机制被广泛认可和适用,国际投资中投资者母国的外交保护作用已然极为弱化,中国在印投资者也必须脱离国家“父爱主义”的思维模式,妥善管控投资法律风险,积极应对国际投资争端。首先,中国投资者须做好投资前准备工作,熟悉印度相关法律制度,做好项目尽职调查。要保持对中印关系和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变化的敏感性、警惕性,及时掌握印度投资法律制度动态,注重投资全流程的尽职调查,了解“政府路径”下所需申报材料和相关程序,避免不必要地增加审批时间或导致审批无法通过。尤为重要的是,中国投资者必须构建完善的合规审查机制,遵守印度有关投资、劳工、环境、税收等方面的一般性法律制度和相关行业的特殊规定和政策,确保合法合规经营。
其次,中国投资者应适时调整投资策略和布局,理性构建投资模式、合理配置投资资源,提前研判法律和政策风险,制定应急性与替代性方案。要加强投资合同的谈判与签署工作,实现投资合同中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中小投资者而言,由于自身风险管控和承受能力不足,应尽量避开到印度等高风险国家进行投资,即便是资金实力雄厚的投资者,也应注重在印投资的“轻资产”运营,注重具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审慎进行“长线投资”,在紧急情况下及时撤离投资和转移在印资产,将与印度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领域的风险作为防范重点,以更加灵活、高效、建设性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同时,在印投资企业要主动承担和履行其社会责任,加强企业“本土化”运营,培养与当地社区的良好关系,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
最后,面对印度采取禁用中国应用软件等歧视性、专断性措施,中国投资者仍可考虑利用现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与投资保护制度解决投资争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当前,尽管2006年《中印投资协定》已经终止,但根据协定第16条第2款“本协定终止之日前作出或取得的投资,本协定应自本协定终止之日起继续适用15年”之规定,中国投资者在2018年10月3日协定终止前完成的投资仍然受到2006年《中印投资协定》的保护,如印度政府的任何行动影响到中国投资者在上述日期之前的投资,投资者仍有权利用《中印投资协定》的相关条款提起投资仲裁。即便不能援引《中印投资协定》维护合法权益,也要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谈判,并向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提起诉讼,多途径并用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结 语
当前,经贸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已成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支持者面临的重要挑战,更为极端化的国家利益和安全问题也被多国纳入其经贸法律政策的首要考量因素。国际环境的间接影响,与印度激进的国家利益保护战略和民族主义情绪的直接作用,印度一方面在国内投资法律制度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强化了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并针对性地加强了对中国投资者的审查和限制。另一方面,在国际投资法律制度改革(49)当前,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改革主要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推动下进行,主要围绕国际投资治理与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新一代国际投资条约制定、现有国际投资协定的现代化、提高投资政策的一致性和协同效应、国际投资仲裁改革等议题展开。参见UNCTAD,UNCTAD's Reform Packa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egime (2018 edition),2018.https:∥investmentpolicy.unctad.org/uploaded-files/document/UNCTAD_Reform_Package_2018.pdf.的大背景和印度面临的国际投资仲裁重压下,印度试图单方面对其双边投资协定进行“换血”,并对国际投资仲裁采取消极甚至排除的态度。整体而言,印度在其投资法律和投资条约制度中的“国家中心主义”趋势,反映出对国家利益保护的偏向性和对投资者权益保障的严重不足。可以预见的是,印度投资法律制度与印度国家利益的交互作用与深度融合以及法律制度对“国家安全”的敏感反应,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不稳定、歧视性等问题将更为凸出,中国投资者在印投资也将受到更严格的安全审查和更广泛的限制性措施。对此,我国必须在国家层面和投资者层面“双管齐下”,妥善应对印度投资法律制度的新变化与其中的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