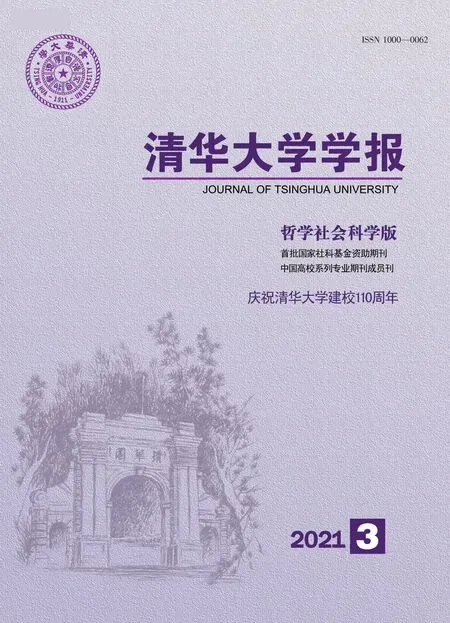论司马光时代的新法改废与新旧党争
——兼与赵
张呈忠
北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五日,在位19年的神宗皇帝去世,年仅9岁的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伴随着皇权的更迭,政坛发生了剧烈的变动,新党旧党正面交锋,经过了一年左右异常激烈的明争暗斗之后,到元祐元年(1086)四月,旧党已然有大获全胜之势,新党悉数遭到贬斥,新法大半以上被废除。在短暂的一年时间里,复杂而尖锐的政治斗争贯穿始终,构成了这段历史的主线。
尽管如此,政治斗争并非是这段历史的全部内容。罗家祥先生提出新旧党之间也存在着逐渐缓和矛盾的可能性,“两大政治派别的许多官员有不少共通之处,不仅对一部分新法的严重弊端有相同的认识,而且对另一部分新法的实效也所见相同”,但是“实际主宰皇权的是对变法素怀不满,且又疏于国计民生的太皇太后高氏,其所委以朝政者则又是进入垂暮之年、刚愎自用但却众望所归的司马光,从而致使北宋政治迅速发生了悲剧性的变化”。①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9页。方诚峰先生也认为“反新法者的态度有了缓和,支持新法者有了反思”,而最终冲突无法消弭的主要原因在于掌握主导权的是“接触新法最少、反对新法最力”的“少数派”高氏和司马光。②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页。赵冬梅教授《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宋朝政治》一文提出了与前人全然不同的观点,她认为司马光也是主张“新旧并用,力求和解”,但司马光政治上“幼稚”而且“孤独”,“既无人才队伍,也无经验、手腕、对策”,朝政方向实际为太皇太后和激进的台谏官所主导,所以最终和解破灭,司马光的和解主张无法实现。③赵冬梅:《和解的破灭:司马光最后18个月的宋朝政治》,《文史哲》2019年第5期,第24—40页,下文简称“赵文”。如果说将司马光定性为当时政坛上的少数派,但因其位高权重且受到高氏的特别信任,尚可以理解元祐政治的基本走向,倘若连司马光也都主张和解,激烈的新旧党争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新党是在神宗朝积极推行新法、受到皇帝重用的臣僚,旧党是在神宗朝对新法持反对立场的异议之士。所谓“新旧党争”,既包括围绕着新法的政策分歧,也包括人事上的权位之争。反过来说,如果存在所谓“新旧和解”,自然也应包括政策上的新法旧法可协商和人事上的新党旧党可合作两个方面。政策上的共识固然可能促进和解,但并不等于人事上就一定可以合作,而政策上的分歧往往会加剧人事上的矛盾。元丰元祐之际,新旧党争异常激烈是已然发生的历史事实,新旧和解仅仅是对于一种历史可能性的探讨,这种历史可能性的判断往往又是基于对和解与斗争两种力量大小的比较。那么,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下新党旧党和解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司马光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这是本文所要着力探讨的问题。
在前人的研究中,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析往往是分列各派别或者代表人物的主张、行为,对于历史演变的具体进程笼统论述,时间线索并不明晰。实际上,这段历史虽然短暂,但各方势力的消长和政局演变的趋势都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说,可以将这段时间的政局演变分为三个阶段:(一)元丰八年三月至五月:高氏和蔡确等共同进行朝政改革,宦官队伍大调整,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监司被罢黜,若干苛政被废除,人事上参用新旧;(二)元丰八年六月至九月:司马光、吕公著等旧党被高氏召回后举荐了大批旧党人士,并与蔡确等人围绕着新法废罢问题发生冲突,特别是在三大新法问题上针锋相对,旧党势力明显增强;(三)元丰八年十月至元祐元年四月:新旧党的冲突升级,台谏官发动了支持司马光、“驱三奸”的斗争,经过最为激烈的役法之争后,蔡确等人彻底失败并出局。以下对这三个阶段进行详细剖析,对前面提出的问题进行解答,并对赵文提出商榷意见。
一、蔡确等对神宗之政的变革
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神宗逝后月余,朝廷颁降诏书说:
恭以先皇帝临御四海十有九年,夙夜励精,建立政事,所以惠泽天下,垂之后世。比闻有司奉行法令,往往失当,或过为烦扰,违戾元降诏旨,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实惠,或妄意窥测,怠于举职,将恐朝廷成法,因以堕弛。其申谕中外,自今已来,协心循理,奉承诏令,以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敢有弗钦,必底厥罪。仍仰御史台察访弹劾以闻。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甲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473—8474页;佚名:《宋大诏令集》卷一九四《诫励中外奉承诏令称先帝更易法度惠安元元之心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15页。
对于这一诏书,两种《哲宗实录》有着不同的解释。蔡京提举编修的《旧录》说:“时蔡确等虑法寖改废,故降是诏,然卒弗能禁。”南宋绍兴重修的《新录》则说:“蔡确知有司奉行新法,例皆失当,过为烦扰,实惠不孚,则不能不更法也。法少更,则身必不安于位,是诏诚确等有以启之矣。”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甲戌条注,第8474页。二者的共同点是认为这一诏书体现了蔡确(等)的主张,不同点是《旧录》认为蔡确(等)的目标是防止神宗的法令遭到改废,《新录》则说蔡确认识到当时新法在执行中存在诸多问题,更法是势所必然。
诏书中明确说到当时有司奉行法令存在着往往失当的严重问题,“或过为烦扰”,“或苟且文具”,“或妄意窥测”,但就诏书的整体意思来看,维护神宗诏令的意旨是明显的。因此,《旧录》《新录》的判断各得其一。这份诏书正充分体现了元丰末以蔡确为典型的新党大臣的理念:在坚持神宗法度的基本原则之下对新法进行局部的变革,从而达到维护神宗法度的目的。
在事实上,神宗去世之后不久,在高氏和蔡确等人的主持下对神宗之政的系列变革已经展开。但是,这一阶段的变革或被淹没在司马光“元祐更化”的叙述之中,或被说成是高氏绕过宰执进行的。司马光还朝的时间在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才被任命为门下侍郎,可以说三月至五月的政事变动都和他没有直接关联。苏轼在为司马光所作的行状中说:“公(司马光)方草具所当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罢减皇城内觇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无状者三十余人,戒敕中外无敢苛刻暴敛,废导洛司物货场,及民所养户马宽保马限,皆从中出,大臣不与。”①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88—489页。他将这一阶段的种种举措描述为高氏主导,与蔡确等人无关。苏轼的这种说法对后来的史家影响非常大。南宋吕中认为“废罢新法等事皆从中出”,并且说“人皆谓新法之改出于司马入相之时,而不知公之未至也,凡废罢等事皆从中出,非章惇蔡确之所抑,亦非有待于司马光吕公著之所教也”。②吕中撰,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卷一八,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23页。南宋王称《东都事略》、元代官修《宋史》都沿袭这一说法。③王称:《东都事略》卷一四《世家二·英宗宣仁圣烈皇后高氏传》,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107页;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二《后妃上·英宗宣仁圣烈高皇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625页。但这一说法是大有可疑之处的。
神宗逝后高氏掌握了最高权力。但是,神宗在位期间高氏很少参与朝政,④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285页。垂帘之后在短时间内她也不可能直接过问诸多政务细节和具体的人事安排,所能倚重的只能是在位的宰辅群体。神宗去世之时,王珪为左相(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右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韩缜知枢密院,章惇门下侍郎,张璪中书侍郎,安焘同知枢密院,李清臣尚书右丞。在这个宰执群体中,王珪虽贵为首相,但历来“无所建明”,而且五月十八日就去世了,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庚戌,第8517页。因此实际权力最大的是蔡确。蔡确在元丰二年五月任参知政事,元丰五年为右相,王珪死后成为首相。史书中常常可见“蔡确等”的说法,与蔡确亲近者至少有章惇和黄履(御史中丞),这样的一个铁三角可谓是当时政坛最为强劲的政治势力,⑥王化雨:《北宋后期三省奏事班次考》,《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第107—108页。重大政治事务的处理不可能绕过他们。从制度架构上讲,改法的权力非高氏所能独揽。元丰八年四月八日有诏书说:“诸官司见行条制,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具其状随事申尚书省、枢密院……传宣或内降,若须索及官司奏请,虽得旨而元无条贯者,并随事申中书省、枢密院覆奏取旨。”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第8472—8473页。因此这一时期的政事变革,宰辅蔡确、章惇等主持其事,高氏也行使其最高权力,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三月八日哲宗和高氏第一天听政就下诏将开修京城壕人夫和一批军器制造兵匠遣回其所属州,并分别赐钱。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辛丑,第8460页。苏辙后来说“访闻京城四门外所在白骨如麻,多是昔日筑城开濠死损人夫”,⑨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栾城集》卷三七《乞葬埋城外白骨状》,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1页。可见这是当时承受着苦役的一个群体,又在京城之中,所以最先进行更改。此后朝廷推出了一系列举措,涉及政策与人事上的重大变动,以下分别进行论述。
(一)对神宗所重用的宦官的贬斥。神宗重用了大批宦官来处理政务,而高后垂帘之后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宦官以收揽权力,罢黜神宗重用的宦官势所必然,而这也符合宰辅们的期待。首先被剥夺权力的是神宗最倚重的李宪。李宪长期领兵西北,负责对夏战事,直接听命于宋神宗。在神宗病重之际,宰辅大臣已经向神宗建言抑制宦官的权力,“门下省每奏李宪怙权难亲事,语次,(章)惇言用李宪事不可为后法,公(王珪)历数宪招权怙势状”,而神宗“颔之,云当罢宪内职”。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条注,第8449页。故三月一日李宪因为奏边功不实,罢入内副都知。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二,元丰八年三月甲午,第8448页。三月二十六日,李宪见领职任一并改差入内押班梁从吉。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己未,第8463页。李宪的权力被削夺后,朝廷对外战略自然也会随之而作调整。四月八日,包括宋用臣、冯景在内的15名宦官转出,高氏亲信宦官被安排到重要位置:阎安、冯宗道勾当御药院,老宗元、梁惟简并勾当内东门司,梁惟简兼太皇太后殿祗候,老宗元兼皇帝殿祗候。此举乃是内廷宦官的大规模更换,明显体现了高氏的意图。这一日又有诏令对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和提举京城所进行调查,户部侍郎李定负责其事,这实际上是针对神宗重用的另一宦官宋用臣,他是这两大机构的提举官,朝廷直接下诏将几个堆垛场废罢,并且诏尚书省左右司,取在京免行纳支钱窠名取旨。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第8473、8470页。五月二日,梁从吉代宋用臣提举皇城。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甲午,第8507页。三日,根据李定的上奏,朝廷下诏对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和提举京城所管下的诸项市场业务进行调整,废罢若干市场,将所收诸种课利一并送到内藏库收纳。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乙未,第8512页。宦官甘承立也被调查,当时他奉神宗之命到荆湖地区采买修京城的木植,四月监察御史安惇弹劾他“于逐路制造上供生活,以和雇为名,强役工匠,非法残害,死者甚众”,还“藉势营私,为害不一”。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五,元丰八年四月,第8502页。六月甘承立被押赴湖北提刑司取勘。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丙戌,第8547页。
(二)对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掊克监司的贬黜。元丰八年四月朝廷开始对京东、福建等地进行察访,对两路监司进行人事调整,这是在蔡确等人主导下进行的。笔者对此已有专文论述,兹不复赘。⑥张呈忠:《元丰时代的皇帝、官僚与百姓——以“京东铁马、福建茶盐”为中心的讨论》,《社会科学》2017年第8期,第137—152页。
(三)对若干新法的改革。比如四月八日,放宽对京东、京西等路保甲养马的部分限制,针对市易息钱实行大姓户放七分、小姓户全放的政策;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第8470、8472页。四月二十四日,诸民户欠元丰七年以前常平、免役息钱,各特减放五分;⑧徐松辑,刘琳等点校:《宋会要辑稿》食货七〇之一七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205页。五月八日户部建议诸路调查各处市易抵当的设置是否合理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庚子,第8515页。等等。
(四)参用新旧大臣。旧党方面,比较典型的是刘挚在四月十四日自滑州召为吏部郎中,梁焘也在同一日自京西北路提刑召为工部郎中。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第8476页。而司马光、吕公著的进用也和蔡确有一定关系。⑪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3页。新党方面,立场相对温和的曾布在五月二十六日被任命为户部尚书。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戊午,第8523页。
以上政事之中,宦官队伍的调整和高氏关系最为密切,但神宗重用的宦官牵涉诸多朝政,因此废罢之际也离不开外朝的支持和参与;而监司的整顿、新法具体政策的更改,蔡确等人的作用更为明显;至于大臣的任用,司马光、吕公著等高层的进用,高氏的态度自然更为重要,而中层官员的调整恐怕主要依靠蔡确等人。从三月到五月,诏令下达的频次和整顿宦官、监司的速度与规模都体现出很强的急迫感,如四月八日下发的诏令即有十余条,可以说这显示出当时蔡确等新党大臣改革弊政、摆脱危机的巨大决心。神宗朝对外积极扩张的开边战略、官营垄断的理财政策以及大型都城建设工程,在高氏和蔡确等新党大臣的主导下明显呈收缩态势。蔡确等在人事上参用新旧,对神宗朝若干弊政进行改革,确实表现出和解的积极姿态。
这一时期的改革最受好评,而且这些好评多是来自旧党方面。苏轼见到邸报中罢保马、堆垛等事,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连说“可贺!可贺!”⑬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一《与腾达道》四十,第1488页。五月司马光称听闻这些诏旨下达之后“四方之人,无不鼓舞”,并且说太皇太后和皇帝对于天下之事“靡不周知”。①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90页。六月韩维上奏说:“臣窃闻陛下浚发德音,斥宋用臣等出就外省,罢其所领职事;黜吴居厚使离本道,责以掊克扰民。中外喧传,晓然知陛下忧国爱民之深意,莫不欣悦相贺。”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丙子,第8533页。吕公著也上奏说:“臣伏见陛下自临朝以来……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从罢去。中外闻之,无不欣喜踊跃。”③吕公:《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285页。他们都将功劳归于高氏和哲宗。苏轼在写司马光行状的时候为了称颂高氏有意识地隐瞒了蔡确等人的功劳,因此后世史书中蔡确等人的作用湮没不彰。
二、马、吕进用与三大法之争
神宗去世之后,司马光获得了救星般的人望,“司马相公”是民间舆论中“相天子,活百姓”的不二人选,屡屡受到京城百姓的欢迎和聚观。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壬戌,第8465页;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六《司马相公人望所归》,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可以说,司马光的时代已经来临。蔡确进用司马光,实际是顺势而为。
对于离朝15载的司马光来说,这种至高的人望是如何获得的呢?显然这不是因为他的政绩,也不是因为他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而是因为他在熙宁新法推行之初反对立场最为坚决,始终是反新法的旗帜人物。与其他官员相比,他对新法的参与最少,也因此完整地保持了自己立场上的纯洁性,这构成了他彻底否定新法的重要资本。神宗之死为朝政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契机,司马光在元丰末受到京师百姓欢迎的种种场景,体现的是普通士民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和对朝政更新的热切企盼,元丰末年的政局危机衬托出了司马光的伟岸形象。
对于新法,司马光主张全面而迅速地废罢。他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措辞极为严厉,对熙丰政事和人事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否定:一是否定王安石“作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以聚敛相尚,以苛刻相驱。生此厉阶,迄今为梗”;二是否定边鄙之臣“行险徼幸,大言面欺,轻动干戈,妄扰蛮夷”,“使兵夫数十万,暴骸于旷野,资仗巨亿,弃捐于异域”;三是否定“生事之臣”“欲乘时干进,建议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变茶盐、铁冶等法,增家业、侵街、商税等钱,以供军须。遂使九土之民,失业困穷,如在汤火”。他将群臣和先帝区分开来,认为“此皆群臣躁于进取,惑误先帝,使利归于身,怨归于上,非先帝之本志也”、“而群下干进者,竞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⑤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第988、991页。司马光不仅否定新法,也否定建言和推行新法之人,称他们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而迷惑、误导了神宗皇帝,从而导致了病民伤国的局面,这些纷更祖宗旧法的群臣是有罪的。在《请更张新法劄子》中他将新法比作毒药,对于误饮毒药的人来说,只能立即停止服用,而不能说每天减少一点服用量,以此来表明对于新法的废罢刻不容缓。⑥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四七《请更张新法劄子》,第1007—1008页。
就对新法的主张而言,无论是变革的方向还是从变革的速度,司马光都是非常激进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旧党的温和路线,其代表者是吕公著。
吕公著六月回京入见高后陈述他的主张,七月六日出任尚书左丞,是继司马光之后第二位出任执政的旧党人物。和司马光一样,吕公著对王安石是持全面否定态度的:“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但与司马光相比,吕公著在改法速度上的主张要温和得多,他强调“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把要改革的新法分为两类。一类是可在进行调整后保留的新法:“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须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财,中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相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即对于青苗、免役、保甲三大法吕公著主张改而不废。另一类是要全部废除:“至于保马之法,先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远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①吕公著:《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第1285页。
在对新法的基本态度上,马、吕二人都是否定的,这体现出旧党的基本立场。二人的分歧一是在改革速度上是缓还是急,二是对于三大法是废还是改。从这个角度来看,吕公著所代表的旧党温和路线反倒与蔡确等新党的主张较为接近,但这仅仅是政策主张上的接近。有“共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可以一起共事,如何看待新法和如何对待新党并不是一回事。
高氏将吕公著的劄子交付给司马光阅览,司马光说:“公著所陈,与臣所欲言者,正相符合。”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8552页。尽管二人主张有分歧,司马光却认为“正相符合”,这是因为在对新法的根本立场上、在开言路与用正人的问题上,司马光与吕公著有着更多更深的共识。
吕公著先是明确提出要“选忠厚骨鲠之臣,正直敢言之士”,“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时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癸未,第8546—8547页。后来又声称“广开言路,登用正人,此最为当今急务”,并举荐了6名官员,分别给予评价和建议授予的官职:“臣伏睹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议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礼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8551—8552页。以上这个6人名单可以称之为“吕公著名单”。
司马光随后举荐了20人,其中有6人他给予了评价:“吏部郎中刘挚,公忠刚正,终始不变;龙图阁待制、知亳州赵彦若,博学有父风,内行修饬;朝请郎傅尧俞,清立安恬,淹滞岁久;直龙图阁、知庆州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朝请郎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秘书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愿,修身无缺。”他强调这6人是“素所熟知,节操坚正,虽不敢言遽当大任,若使之或处台谏,或侍讲读,必有裨益”。另有14人,⑤赵文中将14人误作15人,总共举荐20人误作21人。司马光列出了官职,“新翰林学士吕大防、兵部尚书王存,礼部侍郎李常、秘书少监孙觉,右司郎中胡宗愈,户部郎中韩宗道,工部郎中梁焘、开封府推官赵君锡,新监察御史王岩叟,朝议大夫、知泽州晏知止,朝请大夫范纯礼,知登州苏轼,知歙州绩溪县苏辙,承议郎朱光廷(庭)”,并称这些人“或以行义,或以文学,皆为众所推伏。臣虽与往还不熟,不敢隐蔽”。在举出这20人后,司马光还列出5位他认为可以倚信的“国之老成”——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和韩维,建议高氏也让他们“各举所知”。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第8553页。这个25人名单可以称之为“司马光名单”。
这两份名单尤其是司马光名单值得特别重视。前人虽有论及,但大多未能深入。仔细分析两份名单,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司马光名单一下子开列出25人,可见司马光对自己识人与用人的高度自信,而5位资历甚高的老臣,也经过司马光的肯定而被介绍给高氏,这足以显示司马光的特殊地位,也可见高氏对司马光的特别信任。
第二,司马光名单中的这25人在反对新党和新法的根本立场上是一致的。他举荐的前6人的品格共同点是“节操坚正”,他对放在第一位的刘挚的评价是“公忠刚正,终始不变”。可见司马光最为看重的是政治立场坚定。对于那些始终如一推进新法者,司马光会认为他们节操坚正并举荐吗?当然是不会的。司马光既然认为新法的推进者都是基于个人私利而误导皇帝的罪臣,自然不会承认他们的立场是符合道德的。“节操坚正”指的是对新法的反对立场一贯坚定,而所谓“众所推服”的14人,自然不是为新党所推服,和5位国之老成一样,都是在反对新法中颇有声望的人物。因此,25人中没有一个新党中人。当然这25人的政治主张并非完全一致,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希望众人的主张能够完全一致,这本来就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以基本立场划线,司马光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①方诚峰认为司马光名单反映出司马光的多元主义主张,林鹄否定此说。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34—35页;林鹄:《也说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与方诚峰兄商榷》,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242页。笔者赞成后者的观点。
第三,司马光说前6人是他所熟知的,后面14人“不熟”。但这“不熟”的14人中,苏轼、苏辙与司马光有近20年的交情,赵君锡早在英宗朝就被司马光举荐同修《资治通鉴》,后因遭父丧未能参与,可见司马光所说的“熟知”有着极高的标准。司马光和14人中的个别人可能没有直接接触,但称他们“众所推服”就说明他对这14人的政治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不熟”的表达有其客观的一面,也有政治修辞的一面。即便是对于这些所谓的“不熟”者,司马光也荐举甚力,比如他对朱光庭就“累称于朝”。②刘挚撰,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忠肃集》附录一《请坚持朱光庭太常卿新命》,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70页。
第四,吕公著对“正人”的强调,鲜明地体现了他以新党为奸邪的旧党立场,而司马光举荐的人物完全涵盖吕公著所举荐的,可见司马光和吕公著在政策主张上虽然有激进与温和之别,但那只是“内部矛盾”,在判断“正人”的标准上他们有着更深层的一致性。
第五,所谓“登用正人”其实质意义就是在组织人事上占据主导权。将20多名官员授予中央部门的要职,就意味着要相应地罢免之前在位的官员,这可以说意味着全面夺权、高层重组。因此,两份名单的出台标志着旧党全面夺权斗争的正式开端,排斥熙丰旧臣的意图明明白白地展现出来。台谏官是马、吕二人共同强调要占据的职位。吕公著更是明确提出了御史中丞、侍御史的后备人选。司马光虽然没有指明所举荐者可任官位,但从吕大防、王存、范纯仁等人的资历来看,他已经在考虑执政的后备人选,举出五位“国之老成”则是指向更高职位。很快马、吕举荐的人物就获得了重用,比如七月范纯礼为户部郎中,九月梁焘为吏部郎中,苏轼为礼部郎中,台谏官方面孙觉在七月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戊戌,第8562页。刘挚在九月十八日任侍御史。刘挚随后建言“六察御史并许言事”,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己酉,第8597页。此前只有监察之权而无言事之权的监察御史获得言事之权,这也增强了旧党在言路的势力。自从马、吕进用以后,新党在重大人事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两份名单的出台对新旧党势力之消长具有决定意义。
五月二十六日出任门下侍郎的司马光在宰辅中权位次于左相蔡确、右相韩缜和枢密院长官章惇,而且长期以来远离朝廷让他在回朝之初孤立无援,“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识不过三四”,⑤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第二书》,第1231页。处境并不乐观。司马光首先发动舆论攻势,在三月的时候他就建议高氏“明下诏书,广开言路”,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壬戌,第8466页。此后又一再重申此项主张。“广开言路”既是司马光一贯的政治主张,也是当时背景下非常有效的政治策略。广开言路,固然是可以批评新法,也可以称赞新法,但在政治面临危机而且权力转移成为大势的局面之下,批评的意见必然会超过赞颂的声音,言路一开对于自元丰以来执政的新党大臣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但五月五日朝廷所下“求言诏”让司马光非常不满,因为其中有六句话设置了言事的限制:“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炫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这六句话实际是直指上书言事的动机问题,对上书言事者来说带有恐吓的意味。司马光认为这个标榜求谏的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乙未,第8508页。请求将这六句话删去,前后三次乞改前诏。韩维、吕公著也上书响应司马光,最终他们的主张得以实现。六月二十五日,朝廷下诏说:“应中外臣僚及民庶,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民间疾苦。在京于登闻鼓、检院投进,在外于所属州、军,驿置以闻。朕将亲览,以考求其中而施行之。”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丁亥,第8548页。在关于“求言诏”的较量中,司马光等人的主张获得了胜利。③陈晓俭:《论宋哲宗登基后的两次诏求直言》,《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20—24页;高柯立:《宋哲宗即位求言诏探微》,见包伟民、曹家齐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2016)》,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36—150页。这是神宗去世之后旧党与新党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但是,这一阶段司马光废罢新法的政治主张屡遭抵制。七月三日司马光上劄子提出“尽罢诸处保甲、保正、保长使归农”。④司马光撰,李文泽、霞绍晖点校:《司马光集》卷四八《乞罢保甲劄子》,第1019页。但在此之前枢密院听闻司马光要上奏,抢先一步进呈,最后朝廷七月六日同意依枢密院主张,府界、三路保甲罢团教,每岁农隙赴县教阅一次。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进呈,蔡确等明确反对司马光的保甲主张,“执奏不行”,最后的结果是“保甲依枢密院今月六日指挥”。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甲辰,第8566页。八月八日朝廷下诏青苗法不立定额,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八月己巳,第8580页。十六日诏免役宽剩钱不得过二分。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八月丁丑,第8584—8585页。在三大法的改革上,这显然远远低于司马光的预期。司马光在九月初再次严厉批评青苗、免役、保甲、保马诸法。⑧司马光:《上哲宗乞省览农民封事》,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八,第1287页。
尽管这一时期很多新法进行了改易更革,但青苗、免役和保甲三大法的改废之争已经进入僵持阶段。获得言事之权的监察御史王岩叟在九月上书乞罢青苗、免役和保甲,他说七月以前的政事令人满意,但“七月于今,未闻勇决,犹郁天下之望”,其原因在于奸朋邪党欺惑陛下,在他看来青苗、免役、保甲这三项“民之大害”,按照目前颁布的几项政令,其害还保留了七八成,认为这是因为“奸邪”缺乏改革的诚意,只是“略示更张,以应副陛下圣意而已”,其矛头直指蔡确、章惇等人(但未提及姓名)。⑨王岩叟:《上哲宗乞罢青苗免役保甲》,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一一八,第128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戊午,第8602页。王岩叟的主张与司马光完全一致,可见在台谏系统中司马光开始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从司马光和王岩叟的上奏来看,到九月的时候朝堂论争的主要分歧已经很明显了,关键就是三大法是改还是废的问题。改法进行到这一步,可以说已经触及了蔡确等人的底线。另有记载说元丰末司马光谕令户部尚书曾布增损役法,曾布推辞说:“免役一事,法令纤悉皆出己手,若令遽自改易,义不可为。”⑩脱脱等:《宋史》卷四七一《奸臣一·曾布传》,第13715页。曾布的态度也反映出在大法的问题上新党大臣的坚持。由此可见,司马光废罢新法的主张不得不在高层人事实现大调整后方有实现的可能。
三、司马光与台谏官的“驱三奸”斗争
十月起,政局演变进入到新的阶段。十月六日宰相蔡确作为山陵使陪护神宗灵柩离开京城,至二十四日下葬永裕陵之后方才回京。这期间发生的两件事对蔡确等新党势力的瓦解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一是右相韩缜在高氏面前大肆攻击蔡确。此前蔡确、黄履曾明确反对韩缜拜相,故韩缜借机报复。①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第46页。这纯粹是由于权力斗争的缘故,与新法改废无关。其二是关于台谏官的任命问题。十月十六日,在任命范纯仁、唐淑问、朱光庭、苏辙和范祖禹为台谏官时,知枢密院章惇坚决反对,结果范纯仁和范祖禹以亲嫌之由而罢,但唐淑问、朱光庭和苏辙分别任左司谏、左正言、右司谏。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丁丑,第8606—8607页。
此时旧党已经在言路占据绝对优势。十月二十二日,因刘挚之言王安石的弟子陆佃、女婿蔡卞被罢经筵,司马光所熟知的赵彦若和傅尧俞分别兼侍读和侍讲。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癸未,第8616页。三天之后,同样因刘挚之言,京西路运副沈希颜、提点开封府界公事范峋被罢。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丙戌,第8619页。元祐元年正月,因监察御史孙升的弹劾,市易法的建立者吕嘉问被罢。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辛丑,第8707页。二月十二日,刘挚取代黄履担任御史中丞,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辛未,第8770页。不久之后,在朱光庭弹劾之下,黄履出知越州。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20页。蔡确、章惇和黄履的铁三角开始瓦解。
自十月开始,台谏官们发起了更猛烈的政治攻击,如吕公著所说的“举时政之疵谬,指群臣之奸党”,他们不仅严厉斥责新法,而且指名道姓地弹劾蔡确、章惇、韩缜等人。刘挚弹劾蔡确在担任山陵使时“慢废典礼,有不恭之心”,随后的几个月中他弹劾蔡确的章疏共有十道之多。章惇反对谏官任命之事被刘挚、王岩叟批评为“侵紊政体”“越职肆言”。朱光庭弹劾蔡确“为臣不恭”,又言“章惇欺罔肆辨,韩缜挟邪冒宠”,并且“章数上,其言甚切”。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己丑,第8629、8628、8630页。权位高于司马光的三位宰臣都受到弹劾。十二月十六日朱光庭将蔡确、章惇和韩缜三人指为“三奸”,主张退三奸而进三贤(三贤指司马光、范纯仁、韩维),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子,第8674—8676页。此后他又多次重申此项主张。
台谏官们纷纷指出当时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执政大臣之间的矛盾,他们将司马光描述为奸臣包围之下受妒忌和嫉害的对象。刘挚说:“近者一两月以来,政事号令之见于施行者,旷然稀阔,中外颙颙无所闻见。深求其故,皆以谓执政大臣情志不同,议论不一之所由致也。”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己丑,第8692页。他认为司马光是“以至诚直道独行孤立”,“而庙堂同列,略无诚心助光为善者,不惟不助,而又有妒忌、嫉害之心”,“陛下虽用司马光,而反使(蔡)确等牵制之”,从而导致“大病根本皆在”。⑪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第8729—8730页。苏辙也说“近者每发一政,三省、密院议论纷然,至忿争殿上,无所适从”,他认为只有罢去蔡确、韩缜才能解决这一问题。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20页。诸如此类的弹劾不胜枚举。
当此之时,司马光对高氏和哲宗提出了“独断”之说。他认为“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万一群臣有所见不同,势均力敌,莫能相一者,伏望陛下特留圣意,审察是非”,他引用古语“谋之在多,断之在独”和蔡邕《独断》说:“今执政之臣,虽各相与竭力,同寅协恭;若万一有议论必不可合者,欲乞许令各具劄子奏闻,望陛下精察其是非可否,以圣意决之。”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一月丁巳,第8648页。所谓“邪正忠佞,各有所存者”显然是司马光有现实针对性的说法,并非泛泛而论,他认为当时的情况已是“势均力敌、莫能相一”,他希望高氏和皇帝要在是非之间作出明确决断。司马光的独断主张显示出他和台谏官在政治行动上形成了事实上的配合。
朝政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至元祐元年年初役法之争达到高潮。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已在病中的司马光上劄子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他主张按照熙宁元年以前旧法人数定差,并且规定了地方执行中上报问题的五日之限。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乙丑,第8759页。这是司马光的主张最不受支持的一次,旧党中人如范纯仁、范百禄、苏轼等都表示不赞成。但是二月十七日司马光再上劄子论役法说“望朝廷执之坚如金石”,至于“小小利害未备”则自可徐徐更改。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丙子,第8797、8798页。他对自己的役法主张有着超乎寻常的固执。如果将司马光定性为“少数派”,那么就这次役法主张而言,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不久之后,知枢密院章惇上章对司马光的主张层层反驳,他抓住了司马光论役法劄子中的一些自相矛盾之处,提出“熙宁元年役人数目甚多,后来屡经裁减,三分去一,岂可悉依旧数定差?”他认为司马光“务欲速行以便民,不知如此更张草草,反更为害。望风希合,以速为能,岂更有擘画?”指斥司马光“不讲变法之术,措置无方,施行无绪,可惜朝廷良法美意,又将偏废于此时”。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27页。章惇对司马光役法主张的批评有理有据,击中了要害。⑤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263—267页。纯粹就是非而言,章惇比司马光的优势要大得多,然而最后的结局全然相反。
在此次论役法之时,司马光在致吕公著手书中说:“比日以来,物论颇讥晦叔谨默太过,此际复不廷争,事有蹉跌,则入彼朋矣。”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丁巳,第8737页。司马光对吕公著“谨默太过”的态度提出批评,并且说如果吕公著不支持自己,再不进行廷争,就会“入彼朋”,这是从原则立场的角度对吕公著进行了明确的告诫。章惇的上书引发了朝野上下的纷纷议论,吕公著请求置局详定役法,他说司马光的役法主张“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未完备处”,“今章惇所上文字,虽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命令大体。早来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段不通商量。况役法元不属枢密院,若如此论议不一,必是难得平允”。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37页。吕公著不否认章惇的文字有可取之处,但明确批评了章惇的心态和行为,并建言枢密院不应当再参与役法讨论,而由朝廷选专人加以详定。吕公著上奏之后,二十八日朝廷诏令韩维、吕大防、孙永、范纯仁详定役法,讨论役法的权力掌握在旧党手中,新党完全被排斥在外。
对此事最为激动的是台谏官们,他们对章惇的弹劾纷纷而来。台谏官们承认章惇所言不无道理,但是章惇心术不正,应当罢免。最典型的莫过于右正言王觌的说法:“光之论事,虽或有所短,不害为君子;惇之论事,虽时有所长,宁免为小人。”⑧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乙酉,第8814页。他认为论事之长短是次要的,正邪之辩才是主要的。就连与章惇关系较为密切的苏辙,此前仅弹劾蔡确、韩缜而未涉及章惇,此时也加入到弹劾章惇的队伍中来。⑨刘昭明:《二苏与章惇元祐交疏考》,《人文与社会研究学报》第45卷第1期,2011年4月,第12—15页。他弹劾章惇“明知光所言事节有疏略差误,而不推公心,即加详议,待修完成法,然后施行,而乃雷同众人,连书劄子,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后论列可否,至忿争殿上,无复君臣之礼”,批评章惇“不过欲使被差之人有所不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但得光言不效,则朝廷利害不复顾”,斥责章惇“用心如此”,不应该“置之枢府”。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第8908页。苏辙强调的是章惇用心险恶,玩弄权术以打击司马光,同样是从道德角度立论的。
役法论争是此一时期新旧党争的生动一幕。司马光的役法主张遭到章惇的抨击,反过来促成了旧党内部的团结,吕公著的明确表态,苏辙等人的积极弹劾,使得本来占理的章惇成了众矢之的。
元祐元年闰二月是高层人事变动最关键时期:二日,蔡确罢相出知陈州,司马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四日,吕公著门下侍郎;十八日,李清臣尚书左丞,吕大防尚书右丞;二十三日,章惇罢知枢密院事;二十七日,安焘知枢密院,范纯仁同知枢密院。②徐自明撰,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28—551页。后因台谏官的反对,安焘仍任同知枢密院。宰执中已然形成了新的人事格局,吕大防、范纯仁两位新晋宰执都在司马光名单之列。在王岩叟看来,“蔡确、章惇既去,其余无大奸”。③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〇,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第8936页。新党之中被罢的还有户部尚书曾布、权知开封府蔡京、试礼部侍郎蔡卞等。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庚戌,第8911页;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第8904页。接任户部尚书一职的是司马光、吕公著的两份名单中都有的李常,而司马光对李常任户部尚书掌管国家财政尤感满意。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一,元祐元年闰二月辛未,第8990页。此月也是新法被废罢的重要时期。八日,在司马光的建言下,朝廷下诏罢诸路提举常平官。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祐元年闰二月丙申,第8877页。新法最重要的地方管理机构被撤销,新法推行的组织人事基础不复存在。四月韩缜罢相,“三奸”尽去,吕公著升任右相,文彦博平章军国重事,韩维任门下侍郎,旧党掌权的局面更加稳固。
从元丰八年十月到元祐元年四月,这一阶段人事变动最为剧烈,走完了从新党旧党势均力敌到旧党完胜新党完败的全过程。
四、司马光与元祐政治的历史走向
以上分析了元丰元祐之际新旧党势力消长的主要过程。在新旧党的交锋之中,司马光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斗争姿态,台谏官坚持不懈的弹劾发挥了配合司马光的作用。前人多认为司马光是导致新法废除、新党被逐的关键人物,以上的述论更加详细地证明了这一基本论断是完全成立的。
司马光是否如赵文所说有和解主张呢?赵文对“和解”的定义与本文开头所说的政策上可协商、人事上可合作有所差异,赵文认为司马光既要推翻新法,也要“新旧并用”,其“和解”之意主要指人事上的合作。对于司马光这样一个有重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来说,在元丰元祐之际的历史转折关头,主张和解还是主张斗争,是关乎王朝命运的重大问题,自然不能是含糊不清的。现存史书中未载司马光有此类言论,司马光的奏疏中未有一字提及“和解”主张,司马光也从来没有荐举过一个新党人物。那么,司马光的“和解”主张从何谈起呢?
赵文所依据的是朱熹的两条史论和《邢恕家传》中一段文字。在引朱熹的史论之前,赵文引用了李焘和黄震的论断,史家李焘认为司马光并没有参用熙丰旧臣,黄震的看法也是一样,而朱熹批评司马光“这边用几人,那边用几人,不问是非,不别邪正”,还批评“温公留章子厚,欲与之共变新法”,而后赵文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直接判定李焘和黄震的判断有误而朱熹批评的内容符合实际。这让人颇为费解,如此关键的问题,为何只有结论没有论证?朱熹的两条史论并不能作为史料,唯一的一条史料是《邢恕家传》中一段文字,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注文之中,内容如下:
盖(刘)挚元祐初任言责,(蔡)确犹在相位,与王岩叟排击不已,司马光深不以为然。时傅尧俞为秘书监,温公即属令谏挚止之。且云:“蔡非久自去,何必如此行迹?”挚既以奏疏,即答尧俞云:“已做到这里,如何住得?”傅亦以告恕也。方确之为山陵使也,公著及光已尝为恕言,欲假蔡以节旌,处之北门或颍昌矣。蔡初既力引光,已而同在门下,相得甚欢。章惇则自任语快,常以光为钝,不是持正(蔡确字持正)见容,岂可处也?时京师知事者,皆闻此语。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九,元丰八年九月己酉条注引,第8598页。
赵文虽然引用了李焘对《邢恕家传》“固妄也”的评判,但未见有任何分析,就直接下了断言:“《邢恕家传》固然有虚妄自饰、言过其实的成分,但其中所透露的司马光执政初期谋求和解的宽容政治态度,我以为是可以接受的。”实际上,此段史料只能说明在如何对待蔡确的问题上司马光较刘挚的态度更为从容,无法证明司马光执政初期谋求和解。若细致分析,其中可疑之处实在太多。
这段史料中说司马光对刘挚弹劾蔡确不以为然,让傅尧俞阻止刘挚,刘挚并不同意,而傅尧俞将此事告诉了邢恕。按傅尧俞为秘书监是在元丰八年十月十六日至元祐元年闰二月十八日,邢恕在元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权发遣随州。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〇,元丰八年十月丁丑,第8609页;卷三六九,元祐元年闰二月丙午,第8904页;卷三六三,元丰八年十二月丁亥,第8683页。从时间上看,最有可能发生在元丰末而不是元祐初。台谏官有独立言事之权,不受宰执干预,③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1页。而且理应坚持保密原则,如王岩叟所说,“论事之体贵乎密”,“不密则不足以成就机事”,“故事,台谏官论事,不相通议,亦不关白官长”。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五,元祐元年二月壬戌,第8748—8749页。当时刘挚弹劾蔡确的章疏“未赐降出”,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第8730页。司马光何以知之?即便司马光知晓此事,他通过傅尧俞干预刘挚言事已经有违典制,傅尧俞将此机密之事告诉邢恕更是匪夷所思。后文说司马光和吕公著已经决定好了如何安置蔡确,并也把此事告诉了邢恕,这恐怕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首相之去留,并非司马光和吕公著可以决定,纵然有高后的高度信任,他们私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也断然不会把这样的最高人事机密泄露给外人,和赵文所说的司马光不与吕公著等人商量也明显相矛盾。因此这段材料漏洞百出,也没有其他可以相印证的材料,孤证难立,李焘不取此段材料仅在注文中以史料保存体现出史家的严谨态度。
回到赵文对“和解”的定义上来看,既要将新法全部废除,又要跟蔡确、章惇共事,这本来就是两个绝对不可能同时实现的目标。废除新法的最大障碍是蔡确、章惇,倘若新法全部废除,蔡确、章惇自然也不会留在宰执之位上。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不可能如此矛盾。
逻辑学中有这样一个基本常识:如果前提是错误的,无论推论的过程多么合理,最后得出的结论必然是无效的。司马光主张新旧党和解的前提无法成立,以此为前提的任何结论都必然没有意义。伪问题得不出真答案,既然司马光没有新旧党和解的政治主张,也就不存在为什么司马光的新旧和解主张无法实现的问题,由此引发的各种议论都毫无讨论的价值。实际上,为了支持这一错误的前提,赵文中有很多论述矛盾的地方。
台谏官的问题是赵文论述的一个重点,赵文认为台谏官与司马光不尽同调,举出了苏辙的例子,这一观点基本是可以成立的,但在后文指出台谏官和新晋宰执之间的矛盾已经变成了“代际分歧”,台谏主张清算而宰执(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主张和解,将台谏官与马、吕、范视作对立的双方,这恐怕难以成立。
首先“不尽同调”不等于“尽不同调”。司马光缺乏政治盟友的说法仅仅在任门下侍郎之初可以成立,最晚到元丰八年十月的时候,旧党大批进用,台谏系统已为旧党掌控,新旧党之间已经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台谏之中至少有刘挚、王岩叟的主张和司马光完全一致。刘挚是司马光的亲密盟友,邓广铭先生称其为“司马光的忠实信徒”,①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134—135页。另见陈晓平:《论刘挚及其著作》,见刘挚撰,裴汝诚、陈晓平点校:《忠肃集》附录四,第676—723页。这是恰如其分的。司马光认为王岩叟“进谏无隐”,称赞他说:“吾寒心栗齿,忧在不测,公处之自如,至于再三,或累十数章,必行其言而后已。”②脱脱等:《宋史》卷三四二《王岩叟传》,第10897页。司马光完全肯定王岩叟对他的支持与配合。其他台谏官基本上也都是坚决支持司马光的。苏辙后来所说的“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赵文将这句话误作“时台谏官皆君实之人”,③赵文注明所引出自《苏辙集·栾城后集》卷二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原文是“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见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112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二元祐元年七月丁巳条注引(第9300页)苏辙文时误作“时台谏官皆君实之人”。并以苏辙为台谏官来否定苏辙这句话,其实毫无必要。尽管苏辙与司马光存在某些主张上的分歧,他认为自己不是“君实之人”,但在基本立场上他和司马光是一致的,在役法论争中他旗帜鲜明地弹劾章惇维护司马光便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赵文认为到元祐元年闰二月,太皇太后与台谏官之间的接触开始变得密切起来,相互配合,深刻影响了朝政走向。但实际上早在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蔡确就已经具表请辞,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六,元祐元年二月甲申,第8808页。他被罢相已是定局,到闰二月二日罢相,这自然是此前数月朝堂斗争的最终结果,而不是高氏和台谏官刚开始密切接触就作出的决定。即便是闰二月以后,在人事任命上宰执的作用更为重要,平田茂树认为这一时期“在人事决定上,较之言路官的屡屡上奏,太皇太后向宰相的咨问、回答、决定以及宰相的发言产生了巨大影响”,⑤平田茂树:《宋代的言路》,林松涛、朱刚等译:《宋代政治结构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3页。这是符合实际的。台谏官凌驾于宰执之上主导朝政方向,恐怕要在改变宋朝的基本政治制度之后才可能实现。
第三,赵文所说的“代际分歧”涉及年龄、资历和政治经验差异,但并没有指出差异达到何种程度会造成代际分歧。从年龄上看,范纯仁生于天圣五年(1027),刘挚生于天圣八年,仅相差三岁而已,王觌、王岩叟、苏辙虽然年轻一些,但到元祐元年王觌已经51岁,苏辙47岁,王岩叟44岁,都已进入中老年行列。就政治经验而言,这些人都有在中央不同部门和地方不同机构任职的经历。赵文认为司马光是特别缺乏政治经验的,又和此处强调宰执政治经验丰富互相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要否认旧党内部存在矛盾。在闰二月以后,新旧党势力对比发生根本性变化,旧党成为压倒性的力量,如何处置落败的新党成为当时政坛的主要论题之一,旧党内部人事上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分歧凸显。赵文所提到的“务全大体诏”就是一个明显的体现。时人更多的将其主旨归纳为“安反侧”,⑥刘挚等:《上哲宗论安反侧不必降诏》,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二二,第211—218页。故本文称之为“安反侧诏”,其内容如下:
朕惟先帝临御以来,讲求法度,务在宽厚,爱物仁民。而搢绅之间,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旨掊克,或妄生边事,或连起犴狱,积其源流,久乃知弊。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惩革也。敕正风俗,修振纪纲,兹出大公,盖不得已。况罪显者已正,恶钜者已斥,则宜荡涤隐疵,阔略细故,不复究治,以累太和。夫疾之已甚,孔子不为,御众以宽,有虞所尚,为国之道,务全大体。应今日前有涉此事状者,一切不问,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归美俗。布告中外,体朕意焉。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元祐元年六月甲寅,第9248页。
“安反侧诏”出台于元祐元年六月,是吕公著、范纯仁政治主张的体现,以高氏手诏为依据,是高氏与范纯仁、吕公著在人事问题上达成共识之后的产物。司马光与此诏的出台有什么关系呢?赵文认为:“司马光等新晋宰执希望和解,然而台谏官却主张清算。元祐元年春夏,围绕着一则诏书,双方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较量。”显然赵文认为司马光也参与了这场较量并站在台谏官的对立面,但在后文中全然不见和司马光相关的论述,看到的宰执一方只有吕公著和范纯仁。
围绕着此诏吕、范与台谏之间确实矛盾尖锐。台谏官们要求收回此诏。但反对此诏的并非全是台谏官,如给事中胡宗愈也表示要删去诏书中“言者勿复弹劾,有司毋得施行”二句。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一,元祐元年六月甲寅,第9249页。因此,“安反侧诏”引发的争论并非全然是宰执和台谏官的矛盾。病中的司马光在这个问题上的实际态度难以确知,但从当时的政治逻辑出发,完全可以说围绕“安反侧诏”的争议是旧党之中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矛盾。从措辞来看,该诏书依然是站在新党有罪的立场上,“自新”的说法依然是针对有罪之人。“安反侧诏”的相关争议所反映的只是在对待新党问题上究竟还要不要进一步追罪的问题。对政敌不再追罪与进行合作,两者之间还有着很远的距离。
从“安反侧诏”最终的结局来看,七月十一日颁降之时只是删去了“言者勿复弹劾”六字,其他文字均得以保留。这和台谏官收回诏书的诉求相去甚远,吕、范的主张可以说一时间基本得以实现,而远没有到赵文所说的此诏成为一纸空文的地步。而赵文为了说明此诏因台谏官的推动变成了一纸空文,举出了杜纮的个案。元祐元年七月,在神宗朝任刑部郎中的杜纮被任命为右司郎中后,确实遭到了右司谏苏辙的弹劾,但赵文没有指出的是苏辙所言未起任何作用,不仅如此,过了不到一年杜纮又升任大理卿。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〇一,元祐二年五月辛未,第9769页。杜纮个案恰恰构成了赵文观点的反例。实际上,吕、范与台谏官之间此后又发生了若干次博弈,最终在元祐二年以后此诏才失去了效力。③王化雨:《从“慰反侧之诏”看元祐时期宋廷调和新旧的尝试》,《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第57—59页。
同样体现旧党内部分歧的还有青苗法问题。元祐元年八月,司马光针对范纯仁恢复青苗法的主张向高氏说:“不知是何奸邪,劝陛下复行此事!”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四,元祐元年八月辛卯,第9367页。此言一出就已经杜绝了任何调和的可能。司马光明确地把支持青苗法者视为“奸邪”,对于旧党同仁尚且如此,何况是对于新党呢?所以将新旧矛盾定性为“忠奸”矛盾的,并非如赵文所说只是台谏官,司马光一直秉持这样的主张。
因此,闰二月以后朝政上的分歧不是台谏官与新晋宰执的分歧,而是旧党之中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既体现在政策上,也体现在人事上。所谓温和路线和激进路线也只是大致而言,吕公著、范纯仁属温和一派,刘挚、王岩叟属激进一派,相对清晰,但苏轼的态度就比较复杂,他固然是司马光差役法的反对者,同时又是最坚定的青苗法反对者,可见当时人的共识与分歧是多层次的,究竟哪一派是多数,哪一派是少数,恐难遽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司马光是旧党激进路线的代表,这种激进路线在整个元祐时期都是主流。⑤罗家祥:《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第114页。
结 语
神宗去世之后,变革神宗之政是政坛共识。作为最坚决的新法反对者,司马光的人望一时间达到顶峰,政治上的司马光时代在神宗去世之际就已经开始了。尽管当时没有人明确提出否定神宗,但无论是蔡确、章惇,还是司马光、吕公著,他们的行为在事实上都构成了对神宗之政的否定,只是否定的程度有着不同。
总的来说,对吴居厚、宋用臣等人“掊克”“扰民”之类行为的否定,是当时新旧党的共识,从实质上讲就是对神宗之政的纠正,但纠正到何种程度,歧见甚多。苏辙说:“陛下即位以来,罢市易、堆垛场及盐、茶、铁法,此蔡确之所赞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罢保马等事,此韩缜与宋用臣、张诚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确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确等亦否之。”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七,元祐元年二月丙戌,第8819—8820页。这些本来可以被看作是蔡确等人功劳的事情,在旧党看来从立场上讲就缺乏正当性。在当时的背景下,变革新法对于新旧党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新党来说,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意义上的改法行为,都是自我否定;而对于旧党来说,他们所提出的任何意义上的新法批评,都意味着原来立场的延续。这正是当时蔡确等人的尴尬之处——废除新法是对先帝的不忠,不废新法则被说成是顽固不化、没有诚意。蔡确等人道德形象可以说在当时已经崩溃了。尽管蔡确等人一开始依旧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但其行动在司马光的光环之下显得非常被动,此时他们已经身处他人的时代无论怎样表现都会被弹劾。
在当时的政坛上,就政策角度而言,确实存在着一些相近的看法;但从人事角度来看,和解的可能性并不大。即便是旧党中较为温和的力量如吕公著等人也不主张政治和解。只是在旧党完全掌权之后,吕公著、范纯仁主张对中下级新党官员网开一面,让他们改过自新,不予追究。新旧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是以司马光、吕公著为代表的旧党的基本看法,是由其反新法的基本政治立场决定的。就此而言,达成政策上可协商、人事上可合作双重目标的和解只是新党蔡确等人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也必然陷入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并不仅仅是由司马光和高氏少数派造成的。司马光固然是某些政策上的少数派,特别是在役法主张上,一度成为极少数派,但在人望上,他始终是绝对的多数派,是旧党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道德上的认同感、人事上的立场问题都要远远高于具体的政策分歧。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马光去世。一个疏离了高层政治15年的人,在短短十几个月时间里就基本实现了废罢新法、驱逐新党的目标。赵文却认为“历史赋予他的任务,他却一件也没有完成”。“历史”本身不是创造的主体,也不可能赋予司马光一件又一件的任务。司马光以病残之躯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将他的政治能量发挥到了极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既是时代环境的造就,也是他的自我成就。
首先国家形势与舆论环境造就了司马光的崇高威望。“司马相公”的道德名声并不是因为政绩而获得,而是因元丰危机的时势所造就。舆论环境对司马光非常有利,他始终以其巨大的威望力压蔡确、章惇等人。其次是太皇太后高氏的坚定支持。李昌宪先生用“非常信任、言听计从”八个字来形容太皇太后对司马光的态度,②李昌宪:《司马光评传》,第245页。这非常符合历史事实,司马光名单的出台正是这种高度信任的集中体现。第三是司马光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魄力。他力主开言路而造声势,举贤才而夺权位,这显然不是一个政治上“幼稚”的人可以完成的。他意志坚定,甚至可以说他固执,但他正是以固执的态度表明决心,在原则问题上绝不放松,虽然最后实现的目标打了折扣,但也是在高标准的基础上打的折扣,并且在面临“绍述”压力之时,③朱义群:《“绍述”压力下的元祐之政——论北宋元祐年间的政治路线及其合理化论述》,《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3期,第123—142页。司马光这种固执的态度也是回击压力、镇定人心的有力武器。他举荐贤才的名单,奠定了元祐政治的基本人事格局,仅此一项足见其政治能量之巨大。
司马光废罢新法、驱逐新党目标的实现,对于北宋王朝的命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的千秋功罪究竟该如何评说?这一问题虽然不会有最终答案,但仍值得今人深思求索。了解这一时期各方政治势力消长与政局演变的基本过程,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无意义。